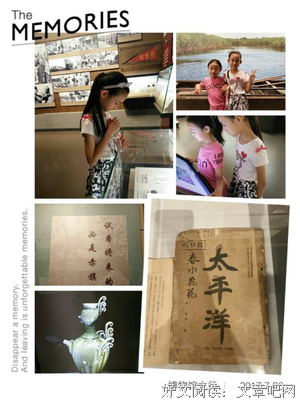《相约博物馆》读后感锦集
《相约博物馆》是一本由[英]安妮·扬森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20-7,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相约博物馆》读后感(一):见信如晤 | 日影飞去,字入水中
两个位于不同世界角落的人,通过54封信件建立起联结。如果你曾被《查令十字街84号》感动,那你也一定会喜欢这一本。
一直觉得写信在这个即时通讯的时代,是格外珍贵的选择。需要时间抵达的事物更显得郑重,有着更深的愿力。时间在文字中被塑造出一条来路,使人仿佛获得一种废墟之中无形的恒久性,越过了脆弱与限制。
能有可以书信往来的人,是多受眷顾的一件事。
整本书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和张力,但是敏感又温柔,太过适合温柔冬夜。
《相约博物馆》读后感(二):把我人生写给你听
这是个通过信件讲述的故事。写信的双方都已经人到中年,儿女均已成人离家、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各自察觉有某种危机在内心爆发,在现实生活中却无人可诉。对蒂娜来说,在内心发酵的是她错过的生命的无限可能:一辈子没离开的故乡、没有实现的冒险和已经没感情的丈夫。对安德斯来说,中年危机是妻子自杀后留下的巨大虚空和疑问。这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因为一封偶然的信件而开始互相写信,成为一对笔友,在纸上独白和反思,偶尔讨论,却总是互相支持。
蒂娜的一生都围绕着故乡打转,出生在英国东英吉利的村庄,和学生时代的男友奉子成婚,就此开始一辈子乡村农妇的生活。她更像是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见到的女人,一辈子安稳,安住于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标准,一生默默奉献。等到头发快要花白,终于如梦初醒,怀疑自己是不是委屈了自己,却始终等不到足够的理由开始向往已久的旅行:
我奉献了自己,首先是牺牲给了父母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所认同的社会标准,他们不让我流产,也不让我在拥有孩子的同时保持单身。其次,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农田。我的丈夫一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只要拥有土地、作物、存粮就心满意足,随之而来的就是每个季度都要完成的工作。我满足于此,但是季节变换是如此无情,工作数不胜数,我根本逃不开。从我献祭自己开始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很久那时候我太年轻,过了许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是在牺牲,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准确的说法了,我就是在献祭。爱徳华每天都很满足,有什么东西也能带给我一样的满足感呢?或许是去丹麦的旅行吧一一那样就足够了。然而我生命中的空白区域要是用这样轻率的方式着墨过多,似乎又太过分了。蒂娜想去丹麦是因为托兰人,Tollund Man在那里。托兰人是一具被酸沼封存的尸体,死于久远年代的远古献祭。解剖显示他分明是被绞杀,可那历经了千年的面容却如此安详。一个被献祭、被谋杀的人难道不该充满怒火吗?这个疑问也许就是蒂娜如此迷恋托兰人的原因。也许她想知道,她对自己人生的献祭会终于何处?她此刻的懊悔和对自己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会不会有一天也终于托兰人式的安详?
给蒂娜回信的考古学家叫做安德斯,他是丹麦锡尔克堡博物馆的馆长。他的生活围绕着考古发现打转,在妻子死后显得格外空旷和寂寥。蒂娜的来信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他开始练习用英文写信,学者像蒂娜那样关注自然里微小的变化,比如骑自行车上班时路过的湖水的颜色,而不是习惯性地把路程视作从A到B的一条线。他开始从蒂娜那里获取建议,比如如何处理女儿的未婚先孕,是否应该支持女儿不告诉孩子父亲自己怀孕的决定——毕竟蒂娜是个过来人。
他俩的信件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独白和冥想。他们并没有真正讨论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更多的时候只是利用纸面和电子邮件的空白来整理自己的思绪。与其说他们是在对对方说话,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对方扮演的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只是在那里就够了。这种感觉其实很像在博物馆里看几千年前的骸骨或是物品——你的凝视分明是从现代通往古代的,但冥冥之中却会听到来自古代的回响。千年之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思考?他们幸福或是难过?这些已然消失在时光里的问题以物品的形式向现代人默默呈现的同时也在默默发问——2020年的你如何生活?你如何思考?你幸福或难过?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人类啊,你可学到了真正的智慧、可以不负这一生?你的睡脸,可似托兰人那样安详?
当然这个故事还是有曲折的情节的,在书的后半段,蒂娜的生活终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终于决定离开困住了她一辈子的土地。安妮·扬森的文字沉稳而耐心,非常适合让蒂娜和安德斯的一两封信送你进入安详的睡眠。
《相约博物馆》读后感(三):关于写信这件小事
1
这本小说结构特殊而简洁,由54封信件构成。
两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一个失去妻子的小博物馆馆长,一个一辈子困在农庄的家庭妇女,机缘巧合下,不抱什么期待地慢慢通起信来。淡淡的叙述,静静的思考,逐渐加深的理解和感情。
与其说为了交流,他们写这些信时更多是各自在书写中梳理自己的想法,不期然就走到了近乎心灵知己的阶段。两人互相没有批判、没有挑剔,也没有指手画脚,边界清晰,礼貌克制,全然接纳,看起来比心理咨询效果还好哦。
看得我也很想写信,本该写点读书笔记或书评的时候打开文档更想要先记录一下对写信这件事的热情,被这本小说激发的久远热情呢。一直以来自是知道在写作中可以梳理甚至深化头脑中的想法,可以自己陪伴自己,帮助自己,默默成长,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笔友,有一点交流,还是很羡慕的呀。
回想起来,大学时刚刚离开家,是最想写信收信的阶段了。还参加过所谓杂志的笔友,收到的很多都是日常很无聊、写信猎奇的信件,渐渐都自然消散了。那几年互联网刚刚兴起,大学生之间还很喜欢聊天室聊天,写信多半也就只有一点点家信了吧。
大概2004年前后,遇到过特别欣赏的邓姐姐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提到跟朋友逛街的经历、对日本的看法等等。那是想要通过长邮件进行深度交流的努力,我实在是深感荣幸。但那时候自身真的太年轻太肤浅,无法对话,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拖了几拖,这个深入沟通交流的机会就错过了。
过了几年,有次同学聚会之后,很想跟某同学深入交流,给她写了很长的邮件,但她并没有回复。后来意识到,是我自己的问题。当时写的内容大概有一种改造意愿,虽主观是帮助别人的义气,但口气中想必是隐含着对她当时情况的批判性,人家自然是不愿意回复的。
那几年还有类似博客的写作,偶尔收到一点老朋友的交流回复,后来微博微信热起来,就更没有深入交流了。在豆瓣写过点,也没见多少回复交流,可能我这人并不是一个让别人有交流欲望的状态吧。
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9月孩子上高中以后,每周给他写一封邮件。大概写到今年春天吧,这半年就没写了。之前邮件也都有来无回,他一共就回过一次,还是用的英文。
现在又想起来好想要写信,可朋友们没有会愿意跟我写信的,网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聊得起来,恐怕就还是写给自己儿子吧。就算他现在不怎么认真看,但存放着以后也是个痕迹。如果我死了,或者老年痴呆了失智了,而他想我了,也可以回味,或者以后他对自己孩子也有一些复杂情绪了,也可以参考。甚至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在我的文本之外增加自己的东西,互相有个呼应,形成可以传给后辈的文本。
总之,写信不是你想写就能写,对面那个收信人实在还是很重要,相约博物馆的两个人实在是很可遇不可求呢。实在不行,要不就写给“未来的自己”吧。记录下此时此刻的经历和心情,多年后自己回味,也还不错。
2
说回小说本身,小说作者出这本小说是处女作,但她必定不是第一次动笔,只不过这可能是首次完成一个长篇吧。
首先,文笔很细腻,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都很有独到之处,看得出日常的积累,不会是一时灵感突发,也不是全凭想象。
其次,文本的节奏很稳,不动声色。两个主角性格都不怎么极端,都比较收敛,淡然,但娓娓道来中慢慢就形象丰满起来。故事情节不是那么澎湃起伏,但读完回头看看,情节推进、草蛇灰线,恰到好处。
作者推出处女作之前至少也是经过大量阅读写作练习的,这也给了我这种只写日记不敢创作的人一点启发和信心。人生阅历也是一种阅读。对于写作而言,功不唐捐,所有的人生经历和回味思考,所有的阅读、记录、反思和练习,都会成为作品的土壤。
3
再说回文本,小说很棒,只是对很年轻的读者来说可能会稍微有点阅读门槛。
形式是新颖别致也很有效的,54封信,没有其他文本,就靠信件本身,展示了两个人、两个家庭、两种生活方式。
情感基调是疗愈的,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积极的鸡汤的。中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稍微有点开心的事情刚一分享完就掉进冰窟窿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情节是缓慢推进的,毕竟中年人的生活也不怎么回去一时冲动大起大落。
所以阅读起来需要一点耐心,也需要调动一些生活积累,才能对主人公形成一定的共情。而不是读推理小说那样被情节拉着走。
《相约博物馆》读后感(四):社恐之歌唱出心声,人与人之间真有舒适沟通的可能吗?
最新一期的《脱口秀大会》中,王勉弹唱了一首职场社恐之歌。
“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你赶紧掏出没有信号的手机”、 “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因为迎面走来总得寒暄几句”、“等他回头再等下一班”等歌词唱出广大网友的心声,听来带感又字字珠心,网友直呼“太真实了!”“感觉生活被偷窥!”
说到社恐,每一个漂泊在大都市的现代青年应该都不陌生。豆瓣上的“社恐抱团取暖”小组,成立于2008年,目前有近27000个成员,人员分布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等各个城市……
组内的发帖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惊呼“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不想接陌生电话,但又好奇号码是谁社恐影响到面试怎么办迎面打招呼的过程太可怕了甚至,经常还有人问怎么开口要回自己的充电器(光是想象这些场景就已经脚趾扣地、头皮发麻)
面对工作、恋爱这些人生大问题时,社恐患者常常感受到的,是力不从心。
社恐两大难题:没工作、没对象社恐敢恋爱吗?--不敢,觉得没人会喜欢这样的我其实,许多社恐患者并非不想与人打交道,而是维持这种交流所需要面对的种种意料之外的状况,常让人身心俱疲。
我们一方面觉得和不熟悉自己、不理解自己的人交流是浪费时间,另一方面又在心底渴望着被人真正理解,尤其是渴望遇到一瞬间心有灵犀的默契。
我们羡慕的生活方式,是像《树上的男爵》中的柯西莫那样,生活在树上,与人群疏离地交流,随时可以感受到树下的喧闹,也可以随时躲起来,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孤独如我,社恐如我,有一天突然发现,社恐患者寻找一个真正理解自己的人,使自己不必日夜在孤独中行走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给人写信。
01|
不同于“咻”的一下就发送的电子邮件。
为了写一封信,你需要寻找合适的信纸,把思绪和心声斟酌字句写在纸上,装进信封,甚至会考究地使用火漆盖戳,精心挑选合适的邮票,出门亲手投进邮筒。
一套进行下来,像是一场古老的仪式。
“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是写信的推崇者,他说:
“写信的意义,不仅在于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交流,也在于从脑到手、从手到纸面的过程本身,在于那种花力气亲手创造一件作品的感受。书信真的是一种惊人的时间容器。”让人不禁想起那个“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纯真、质朴的时代。
我们知道层出不穷的通讯软件让交流变得多么便捷,但我们还是想保留一份逐渐被人们抛在身后的温柔与优雅。
02|
事实上书信交流带来的感动并没有完全被年轻人忘却。
以信会友,以信传声大有人在,或是写给志趣相投的笔友,或是写给未来的自己,甚至还可以写给萍水相逢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话题“你现在还在写信吗”目前有8.4万浏览量,小组“亲爱的,你还写信吗?”有近29000名成员。
“写信”似乎成为了一个暗号,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速食主义至上、人际关系淡漠的网络时代中,寻找惺惺相惜的同类。
我们写信,追求的不只是信息的传达,在递送过程中的等待,也是书信交流的意义之一。
慢慢等待的滋味,在社会齿轮高速运转的如今,被我们遗忘了不少。
避免了面对面交流的无所适从,避免了即刻送达的令人眩晕的速度,在写信的过程中,仿佛想说的话伴随着一部分孤独,寄送到了一个有回应的树洞、一片未知的时空当中。
当写信对象是个未曾谋面的人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电影《玛丽和马克思》中,8岁的玛丽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小女孩,喜欢动画片“诺布利特”、甜炼乳和巧克力。
玛丽的妈妈是个酒鬼,而在茶叶包装厂工作的父亲平日只喜欢制作鸟标本。孤独的玛丽没有朋友,一天,她心血来潮给美国纽约市的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询问美国小孩从哪里来,并附上一根樱桃巧克力棒。
44岁的马克思患有自闭症及肥胖,碰巧也喜欢看“诺布利特”动画片及吃巧克力。
二人的笔友关系从1976年维持到1994年,期间各自经历了许多人生起伏,直到成年的玛丽终于来到纽约看望马克思……
两个“社恐患者”通过写信建立起了深挚的友谊,有许多年他们未曾见面,但他们认定了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这句台词,令无数观众动容。
它既精准地描述了身处人群中的我们感受到的孤独,又难得的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希望的图画:
也许我们也可以像故事中的主人公,在遥远的远方遇到真正理解自己的人。
写信,似乎给社恐患者获得理解提供了一个隐微的出口,一点闪烁的希望。
相似的故事还可以在英国作家安妮·扬森的《相约博物馆》中看到。
相约博物馆评价人数不足[英]安妮·扬森 / 2020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03|
他叫安德斯,他是丹麦锡尔克堡博物馆的馆长。他每天和木乃伊、陶罐这些千百年前的东西打交道。他的妻子在一次海上旅行中独自一人走到狂风暴雨中的甲板上,从此生死未卜再无音讯,他才发现这一生中他们从来不曾互相了解。
她叫蒂娜,英国东部小镇上一个普通的农妇,日复一日做一些养鸡、打扫之类的琐碎活计。她的儿女已经长大成家,她最好的朋友因病去世,她从小与好友筹划的旅行只得搁浅。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十年,却感觉自己的每一天都在重复,生活没有意外没有波澜。
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因一场意外的通信而产生了悠长而奇异的连接。跨越700英里的距离,54封信件的交流中,他们越来越熟悉,许多面对亲人时也难以说出口的话,被写在信中传达。
在雪花般往来的书信之中,蒂娜和安德斯的人生在你我面前徐徐展开。
他们遗憾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悠长的人生、怀念的人生······
捧读的我们仿佛成为他们人生的窥视者,但从他们的人生境遇中我们也能感同身受。
蒂娜说:
“我收到的大部分电子邮件都是农作物特价优惠通知,要么就是提醒该我运营农贸市场里的蛋糕摊位了。而你的来信则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我枯坐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停车场里,感觉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放错了房间,这个房间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安德斯说:
“我们的经历显然非常相似:我们都出生在战后的世界,这个世界并没有利害冲突;我们都结婚了,有孩子;我们都没有承受身体上的苦痛。每当我在深夜醒来,都会疑惑,说到底,我是不是浪费了自己的机会?我是不是应该用自己被赋予的时间和才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在作者舒缓、深沉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们各自怀揣数年的、坚硬而隐秘的孤独,以及这份孤独是如何慢慢融化的。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彼此理解的可能。
孤独是每个人需要终生面对的课题,每一个看似习惯了孤独的人,心中都燃烧着被人理解的渴望。
《相约博物馆》勾勒出的这一场相遇也许过于幸运,带上了一丝童话色彩,但至少给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我们分享了一份希望,在我们互不接壤的岛屿上,开一扇沟通的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