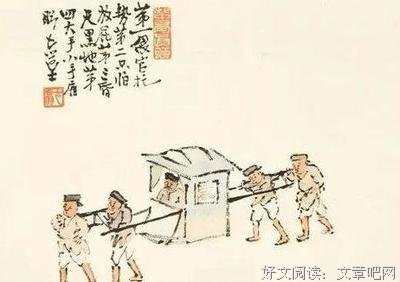《豆棚闲话》读后感摘抄
《豆棚闲话》是一本由艾衲居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46图书,本书定价:0.87元,页数:1984-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豆棚闲话》精选点评:
●一本神奇的书
●读后感觉一般,开篇尚可,正文不逮三言二拍远甚。有些乡村野语有点意思。
●多好的书啊,姐都不忍心还了
●通篇尽是弘扬所谓忠孝节义来表现「礼失而求诸野」,炎夏消过、霜气逼人时,豆棚才让这些闲话者们自行推翻,不再以空谈来混日子。
●整体架构很有意思。具体的故事感觉前几个更感兴趣,也有一些思考,后面读着读着有些乏了
●叙事结构还是有些新意
●绝妙的想象力
●艾衲居士讲故事的结构与卜伽丘不谋而合。有些好奇,《首阳山叔齐变节》 对鲁迅写《采薇》有多少影响?
●一本可爱的茶余饭后的小书
●应该算是半文言了吧?果然比文言文看起来省事儿多了啊!私以为除了前两个故事、一是关于晋文公的介之推死于大火的另外一个版本,二是关于西施的新解,其他的反而觉得一般般。
《豆棚闲话》读后感(一):现世主义者的短篇小说
2010年在北京听课时读的,当时因为上这门课的老师强调一定要看,我便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
短短十来篇文章的集子,却深刻地反映出那时底层人对所谓神鬼、所谓报应的强烈怀疑,尤其是最后一篇,更写出了颠覆性的结论。这让我更觉得,中国人大半是现世主义者,只看重现世的利益,而那些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关于灵魂、关于良知的深刻拷问和反思,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整本书有点像《一千零一夜》的形式,每天讲一个故事,直到那个讲故事的地点----豆棚倒了,作者也就顺势结束了全书。
时隔太久,现在也只能隐约想起个大概,具体情节都已不记得了。
《豆棚闲话》读后感(二):《 介之推火封妒妇》
中等小户在自家空地搭个棚子,放任豆藤弯弯曲曲缠满了,自成一个纳凉的好去处。豆棚下,男女老少铺了凉席边乘凉边说故事。
开篇的题目为《 介之推火封妒妇》,是一位乘凉的老者讲的故事。有个叫做妒妇津的地方,过往的妇女都要脸上抹灰扮的丑陋不堪。这地方有座庙宇供了个石尤奶奶——“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紫色伛兜面孔、张着簸箕大的红嘴,乃是个半老妇人,手持焦木短棍,恶狠狠盘踞在上;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伛偻苦楚形状的男人,朝着左侧神厨角里。”这男人便是男一号介之推。两人原也是郎才女貌来着。
介之推因追随晋国公子逃难不告而别,石尤不明就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妒恨恼怒得胸中长了如石一般的妬块。“俗语说,女傍有石,石畔无皮,病入膏肓,再消融不得的了。”
十九年后,男一号护主回国并找到石尤。石尤将介之推五花大绑,“我也不愿金紫富贵,浪迹天涯,只愿在家两两相对,齑盐苦守。” 直到朝中友人来到山中放了一把大火,火势由搅着石罅峦光的袅袅微烟演变得火炽风狂。石尤抱住介之推两人一起烧成灰烬。但石尤胸中的妬块却完好无损,被当成宝贝送给晋国公子。这宝贝搅得后宫不睦,只得又请出了个叫做“百炼降魔破妒金刚宝锤”的仙物才将它打碎。
其余的故事似乎都不如这篇精彩。暂记录之。。。
《豆棚闲话》读后感(三):典到琴书事可知
据说古代一落魄世家女子不得不卖书易米时曾写诗一首
典到琴书事可知,又从架上检元诗。先人手泽飘零尽,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鸡林求易得,他年邺架借应痴。明知此后无由见,珍重寒闺伴我时。
北岛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其实我要说的是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
不管从什么方面看,这都是一本奇书妙书。
第一篇故事已是惊喜连连,说的是介子推当初如何死的。怎么死的呢,原来是他娶了个妒妇,那妒妇将他困在山中,他左思右想没奈何,便放一把火把两人烧死了。第二篇也不落俗套,讲的西施范蠡,原来里面另有来历,不仅不浪漫,还颇有几分龌龊。就着开首连篇,足以称作当年的“先锋小说”了吧。
而后的故事平平,无非是人世的因果报应,只要你安下心来做好人,便是阎王让你今朝死,你也能凭这一点德扭转命运。这是儒家思想。就凭前面这几篇,我想这艾纳居士必定是落第学子,心里装满了孔孟之道,却又出仕无门,一股恶气便把古今中外所有高尚浪漫传说统统解构。
那本书的前言说最经典的当属伯夷叔齐首阳山上的故事。故事经典,结构经典,用词经典,果然是经典之作。但我想若要作者本身来选,他倒未必觉得这篇好的,他也许觉得最后一篇好。
最后一篇讲一个姓陈的斋长在豆棚下讲什么佛教道家统统是放屁,信不过的,语言流畅,是书生口吻。最后这个斋长被众人轰走了。不久豆棚塌了,众人便道,都是这个人的胡言乱语,把咱们的豆棚都弄倒了。
我不知怎的对最后一篇特别生出感悟。我拿不准作者的立场是怎样,可于我,却在陈斋长身上找出了一丝无奈。
典到琴书事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满架诗书敌不过果腹的口粮,满腹经纶终究换不来一朝温饱。智慧,把人钉在了十字架上,你的身后全是血,众人不过用你的血装点成一扇桃花,野狗又来围着这一点腥气厮杀。陈斋长的悲哀在于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是世界的早产儿,注定要夭折。
前面的嬉笑怒骂推倒重来,说到底不过是歇斯底里的悲伤和凄凉。
很多人在难过的时候反而会写出很诙谐的东西。苏东坡是这样的。但苏轼真真是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他太强大而健全了,他不需要任何病态的发泄,他不需要恨这个世界,因为他就站在世界的制高点。
可艾衲居士,一听这个名号,便想出一个萧瑟、沉默,甚至看起来有点懦弱的书生。他的“乐”,不过是痛苦的大海上那一点点浮萍,没有根基的,随波逐流的。
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句话放到《豆棚闲话》中,同样合适。
毕竟以前的书生轻易不写小说,定是心里有了不吐不快之事才要这样一涌而出。
我喜欢他用最后一个故事封住了底,豆棚塌了,故事没有了。
于是我们听到几声叹气。远处竟飘来一阵哭声,细听却又像有谁在笑。
《豆棚闲话》读后感(四):《豆棚闲话》的闲话
早春三月,屋前屋后的闲余空地,植下几株羊眼豆秧。待到豆藤长出的时候,觅得几块木头、几支竹竿,在豆藤缠绕攀爬之处搭起棚子。豆藤顺着竹竿、棚子弯曲生长,豆叶也一天天的肥厚起来。待到盛夏来临,豆棚已被豆藤豆叶密密缠满,月上柳梢时,人家或抬着小凳、或放把躺椅,或就地铺条凉席,凉风习习,满目青翠,遍开的豆花随风送来阵阵清香。男女老少将手中的蒲扇、团扇徐徐轻摇,不由荣辱皆忘。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豆棚的主人,早在豆棚上备得了些许清茶、瓜果。无论是乡间野老,还是懵懂少年,只要肚子里有些谈古论今、博人一笑的段子,便可登棚说书。豆棚所讲的故事,时间上至夏商下至崇祯;人物有大夫、隐士、佛陀、道人、官兵、流寇、富商、乞丐、清客、员外、书生;有太平盛世痴儿一朝发迹的不经之谈,亦有流寇满地时割头尤生的诡异故事……月儿越爬越高,人们笑谈、评说的声音渐渐低去,人去棚空,这剩一个静谧、安详的星夜。
豆棚里的故事,一夜夜的讲述着。有时,说书人整夜都是原原本本的讲着一个扣人心弦的大故事;有时,说书人围绕一个话题,尽数搬出肚子里装着的无数小故事。每个夜里,说故事的人都不尽相同,而每则故事与故事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豆棚讲故事的这种形式与结构,极似古代阿拉伯小说集《一千零一夜》与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早在十世纪中叶,巴格达作家哲海什雅所收集编写的四百八十则小故事,哲海什雅为串起这些互不相干的神话、传说,特意编出一个故事:山努亚国王每天娶一个女子次日清早再杀掉的她们,为阻止国王的暴行,宰相长女桑鲁卓每天晚上为他讲一个故事,桑鲁卓的故事无穷无尽,直讲了一千零一夜,终于感动国王。十四世纪时,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为纪念1348年3月到7月,死于瘟疫的十万佛罗伦萨人,以十位躲避瘟疫的青年男女(三对情侣和四个女子)为主角,让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直讲了一百个故事,结集为《十日谈》。在豆棚里讲故事,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一样,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索”(郑振铎语),构建这些大大小小、故事套小事的文字迷宫,就是《豆棚闲话》。
《豆棚闲话》成书于明末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1644-1722)。时间较《一千零一夜》约晚半个世纪,较《十日谈》约晚四百年,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文学成就上,《豆棚闲话》也无法与这两本不朽的世界文学遗产相提并论,胡适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在《豆棚闲话笔记》写中道“此中十二篇都不是好小说,见解不高,文字也不佳”。《豆棚闲话》内容杂陈、思想激愤,每多荒谬不经、追求新奇的翻案文章。
《豆棚闲话》的编者是圣水艾衲居士,其真实姓名和身份已不可考,胡适认为艾衲居士是杭州人,因为“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既杭州西湖”,因为《水经注》里已经写明“明圣湖”即“西湖”。天空啸鹤漫题的《豆棚闲话叙》说:“有艾衲居士者……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况这猢狲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生涯, 岂还待守株之兔。”这篇“叙”中先是鼓吹艾衲居士有惊世脱囊的才学,又透露他没有并未通过科举出头地。“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艾衲居士参加过明末清初兴盛的士人结社,但这也不能帮助他卖去一肚诗云子曰。不第的落魄书生为稻梁谋,只有撰书卖文、担任教职、算命医卜这么几条路。
世事的惨烈动荡、个人的艰难生计,让艾衲居士愈加愤世嫉俗。他虽然参与结社,但却又看不起那些社中的士人,不相来往;寒夜青灯,面壁著书,胸中孤愤难平,因此“莽将二十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将世人最为熟悉的种种故事大作翻案文章,在字里行间肆意痛责、漫骂,有时甚至达到刻薄恶毒的程度。天空啸鹤在“叙”中又说“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艾衲居士虽然在小说最后一章中批驳佛老“彼佛老倡修谬说,僧道姑尼四等,男女游手游食,骗钱安享,做那淫逸不道之事。”但却深信因果报应,小说近一半的篇幅大力宣扬善恶必报天道轮回,(第三章“朝奉郎挥金倡霸”;第四章“藩伯子破产兴家”;第五章“小乞儿真心孝义”等),面对战乱之后的新朝,作者思想深处的不安与矛盾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在胡适先生看来,小说与中国古代优秀的小说相比,显得格调不高、文字斑杂,所以“见解不高,文字不佳”。
中国的话本小说的特点,一为劝诫教化、一为探新求奇,《豆棚闲话》在“探新求奇”这一面上的确上是作足了文章,加之作者艾衲居士是明末遗民,经历了明亡清兴那个乱离兵火的时代,思想颇多矛盾冲突之处,写书基本是以“泄愤”为目的,所以此书尽管在见解和文字”上“不高“、不佳”,但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可不提的一部以翻案致胜的奇书。
《豆棚闲话》实在是圣水艾衲居士的一本泄愤之书。
豆棚里的更多闲话 http://tlccd.tianyablog.com
《豆棚闲话》读后感(五):祛魅的豆棚
尽管从艺术成就上看,它难称顶尖佳作,然而其中尚不乏引人瞩目的特色,从形式上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三点值得注意之处:
1、“屏风”结构
首先,十二则“闲话”,都由“豆棚”或转喻或隐喻地引出故事:如第四则,以种豆的经验比喻人成长道路,说明“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的道理,引出故事;第九则,则从豆荚饱满写到秋天寒冷,人们衣服渐单,不免令游手好闲者生出不良之心,从而讲到一个少年堕落的故事。同时,各篇还遵循着时间顺序。第一则起首,叙江南夏天人家种豆以乘凉;最后则以“当秋杪,霜气逼人,豆梗亦将槁也”结束。由此,“豆棚”成为从外部串连十二篇的形式要素,整部拟话本就像一面由十二扇组成的围屏,不松不紧地连成一体。这是历时性层面的“屏风”结构。
从共时层面来说,一层套一层的叙述手法,亦是“屏风”结构。在书中,作者大多并不直接叙述故事,而是叙述说故事的情景,转述他人的讲述。作者叙述一群人在豆棚下闲话的场景,再直接引述说故事人的话和众听者的议论;而说故事人也常常在讲述中采用直接或间接引述,以完成叙述。好比传统中国画中采用的“重屏”母题——一幅画中有屏风,而屏风上又有画,屏风所绘之物与屏风之外的其他元素构成了丰富的互动关系,起到扩充画面语义的功能。在《豆棚闲话》文本内部,充满了互相指涉、层层转喻,由此形成了富于流动感和层次感的“屏风”效果。
譬如第一则“介之推火炉封妇”,作者先描写豆棚之下众人的情态,作者的声音为第一层;说故事者为“老成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此为第二层;“老成人”说到第二个故事(“成了神还妒的事”),拈出自己遇到的一个“驴夫”,“驴夫”开始讲述“石尤奶奶”的故事,此为第三层。
在这样的“重屏”叙述中,作者与说话人的距离自然地拉开了。作者不再等同于说话者,于是每个故事都不被完全地信任,确凿的判断被悬置,本就恢诡谲怪的故事便愈显扑朔迷离。
2. 真实与虚构
在《豆棚闲话》中,“超自然”的情节俯拾即是,虽然故事的主体是人事,却多搀杂着魑魅魍魉。
幻想性文字用得格外“离谱”的,当数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这个故事里,豺狼虎豹都被赋予了人格,不仅有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还谈论忠义节操,其细处写得逼真自然。尤其特别的是,这样的情节与人人皆知的伯夷叔齐故事联系在一起,更显出真幻错杂。如果说鬼神之说尚属古中国语境下可以接受的观念性语境,那么动物的人性化举动则明显为文学笔法的虚构杜撰了。夷齐之事,在儒家正统中被标榜为忠义的典范,似乎为不可颠覆的史实;而在艾衲居士笔下,这一故事却与非真实情节相勾连,似乎造出不得信其为真又不得疑其作伪的阅读体验。
故事寻求着读者的相信,却因其显然的荒诞而冲击着自身的真实性,形成了强大的张力。作者仿佛在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故事或叙述的虚幻性。
3、第十二则的“反叙述”
仅从第十二则全篇议论的表达方式来看,它就与前十一则区分开来。在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中,陈斋长发表了大段的议论,他从儒家所秉持的天地观念出发,否定鬼神的存在,抨击老子的道家学说,猛斥佛理和佛教对世道人心的损害,指出因果报应观的虚妄和求神拜佛的惑乱。
在第十二则的末尾, 众人发表议论:“可恨这老斋长,执此迂腐之论,把世界上佛老鬼神之说,扫得精光。我们搭豆棚,说闲话,要劝人吃斋念佛之兴,一些也没有了。”在此,《豆棚闲话》的文本实现了内向的解构。前十一则故事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和生死循环的基础上,而且往往有鬼神司命出现,以传达讽刺和劝谏之意;第十二则却作为一种“反叙述”,将前面的十一则故事都予以消解。文本内部的冲突构成了彼此之间的张力。
事实上,陈斋长的一些议论,与前十一则所流露出的许多观点有共同之处。譬如陈斋长所说的“奉佛者,白昼百方为恶,无所不至,及夜间焚香诵经,祈免罪获福”,就和第六则“大和尚假意超升”所极力讽刺的部分僧人的虚伪相一致。而陈斋长的核心依旧是劝人为善,重视现世的修为而非来世的幸福,强调传统的忠孝仁义伦理,与前面各则故事的宗旨也是统一的。这也就说明了,作者(而不是各个说话人)的态度并非简单地认为陈斋长所持皆“迂腐”,否则作者也不会耗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记述这一篇论地谈天。
在整个《豆棚闲话》的各个故事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肯定任何一种观点,而这也是《豆棚闲话》的新趣所在。一种以讽喻劝诫为核心宗旨,但又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似是而非和不断游离的态度,营造了自嘲和游戏的氛围。
以上三个方面的形式特征,共同显示着一种从“故事”到“小说”的过渡性。
与作为书场艺术的“说话”相比,作为拟话本的《豆棚闲话》大大增强了议论性。每篇开头都有议论性的文字,表达一些普遍性的道理,再引出故事。有时一篇包含好几个故事,彼此相连相关,相映成趣或互相补充。如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在西施的故事之前就简略讲述了妹喜、妲己、褒姒这几个“妖物”的故事。“正话”和“入话”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已经改变,传统的“说话”在《豆棚闲话》里进一步瓦解,显露出文人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
更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叙述《豆棚闲话》不再执著于给出“故事”,而是展现“讲故事的风景”。讲故事人和听故事人都进入了作者的笔底,都出现在电影镜头的“画框”内,一切都处于被叙述中,都是作者安排的“镜头”所呈现的画面。
在《豆棚闲话》中,它不再像这一体裁最初所模拟的话本那样,作者与“说话人”合一。“说话人”与作者(至少是外在形式上)实现了彻底分离,而且固定的“说话人”不存在了。豆棚世界是一个充满引语的世界,诸多声音在其中交错,多声部的复调效果取缔了意义中心,导致了意义的多元化与不确定。
当然,在几个“讲故事人”的叙述内部,还是能发现相当典型的故事化和说书化特征。可以看出,作者在具体的写作中,坚持着对“说话”技艺的传承和把玩,同时又在总体的结构组织上,不自居、也不创造任何叙述权威,将言说背后的“责任”抛给各个讲故事的人。这反应了写作观念和技法上的杂糅性和过渡性。
在历史文本的改写中,作者对已有定论的几个人物进行了“祛魅”。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里,如紫髯狂客所评,作者“将一千古美姝,说得如乡里村妇;绝世谋士,说得如积年教唆……解鸱夷,解夷光,注西湖,谈选女事,皆绝新绝奇,极灵极警,开人智蕊,发人慧光。”
在明代后期,人们认识到人欲是人的天性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不可也不必消除净尽。第七则写到的叔齐变节,就是基于人欲而敷演的故事。这一则完成了对叔齐乃至一系列“守节”行为的“去圣”。有研究认为,第七则实是借给叔齐翻案来讽刺明清易代时变节之人,我以为这一判断未免过于简单。倘若真是讽刺,何必让齐物主讲出一番道理,又何必以一批顽民的“口似圣贤,心同盗跖”来映衬叔齐坦然“变节”的行为?在故事中,“齐物主”说道:“道隆则隆,道污则污。从来新朝的臣子,那一个不是先代的苗裔?该他出山,同着物类,生生杀杀,风雨雷霆,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这段话在在点出了“应天顺人”的道理,把叔齐下山看作合乎规律的做法,是十分开明的。在此,“事功”与“仁义”合流,顺应时势成了仁义的另一个向度。
随着历史的推移,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叙事日益式微,出现了“讲故事艺术的衰落”,“它的最早的特征是近代之初小说的兴起。”在《豆棚闲话》中,说话伎艺场上的说话人权威被“众声喧哗”取代,完成了叙事声音的“祛魅”。作者饶有意味地与各个说话人保持着距离,传递真理和经验的“故事”也逐渐蜕变为不重在给出真理的“小说”。从书场到豆棚,就是“说话”的瓦解和它向案头化的“小说”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