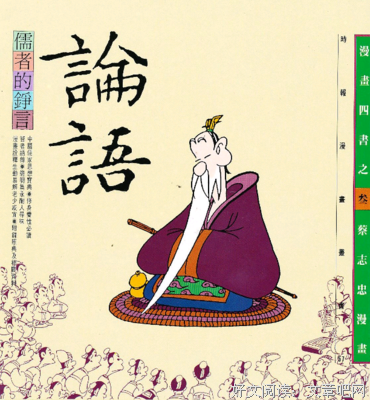《論語義疏》的读后感大全
《論語義疏》是一本由[梁] 皇侃 撰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36.00元,页数:10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論語義疏》精选点评: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论语》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249)等编纂的《论语集解》,二是梁皇侃(488—545)的《论语义疏》,三是南宋朱熹(1130—1200)的《论语集注》,四是清刘宝楠(1791—1855)的《论语正义》,其中尤以皇侃《论语义疏》性格鲜明,引人注目。
●对于皇疏的体例而言,看刻本是有必要的
●皇侃《论语义疏》是南北朝时期学者疏解《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其何晏“注”与皇侃“疏”体现了成书前诸代学者研治《论语》的学术积累,虽然自宋代以后皇侃疏因被邢昺疏代替而渐次失传,但在中国失传的皇侃疏却在日本流传有绪、治者不乏,正可谓“吾道东矣”。哈哈哈哈
●蛾術叢書第二種,影印大正十二年懷德堂本論語義疏十卷,武內義雄校勘記一卷,書後附桂文燦論語皇疏考證十卷。
●有武内义雄的《论语义疏校勘记》和桂文燦的《论语皇疏辨误》。比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好得多~
《論語義疏》读后感(一):自海外归来的《论语义疏》,好书
本书为《蛾术丛书》第二种,影印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论语义疏》十卷,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一卷,书后附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十卷。 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怀德堂(大阪汉学私塾)纪念会同仁商定请武内义雄(1886—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复其六朝旧体。武内义雄以日本旧抄本中年代较早的文明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其他十多种抄本、刊本。大正十二年(1923),武内义雄校订本出版,即“怀德堂本”。怀德堂本《论语义疏》正本四册外,校勘记另为一册。武内义雄又专写了《校论语义疏杂识》一文,对《义疏》的来历、现存皇疏旧抄本、皇疏之原形、经注之异同、疏文之衍字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廓清了不少围绕在皇疏周围的疑团。学界普遍认为怀德堂本选择底本好,参校本多,基本恢复了皇疏钞本旧貌,远优于根本逊志本。
《論語義疏》读后感(二):《蛾术丛书》第二种《论语义疏》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论语》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其中尤以皇侃《论语义疏》性格鲜明,引人注目。
解经形式上,皇侃吸收玄学、佛学谈经说法之制,开创了儒学史上的“义疏”学。“义疏”在文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分“科段”,二是设问答。所谓分科段,是指对经注文进行解构,分章、分段来讲解。
皇侃《论语义疏》以魏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江熙《集解论语》等汉魏以来40多家通儒遗说汇编而成,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集汉魏六朝《论语》学之大成,为我们研究六朝《论语》学提供了绝好的史料。但自南宋以后,《论语义疏》便散佚国外,漂泊东瀛500年,乾隆时期才重新回传到中国。
日本宽延三年(1750),根本逊志在其师荻生徂徕的鼓励下,校订了足利学校所藏抄本皇疏十卷,以《论语集解义疏》的名义予以刊行。足利学校本属文明本系统,但抄写年代较晚,是日本大永年间(1521—1527)的抄本。根本逊志刊本最大的贡献是扩大了皇疏的流传,但有两大缺陷。一是根据明代邢疏刊本格式重排了皇疏经、注、疏的体式;二是在校订时师心自用,有以邢疏或《经典释文》更改经注、随意删除疏文的现象。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鹏航海至日本,购得《论语集解义疏》而还。后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将此书进呈四库馆,由此《论语集解义疏》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有武英殿刻本传世。
日本学界也对根本逊志本变易体式、臆改文字表示不满。大正十一年(1922),怀德堂(大阪汉学私塾)纪念会同仁商定请武内义雄(1886—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复其六朝旧体。武内义雄以日本旧抄本中年代较早的文明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其他十多种抄本、刊本,订正了根本逊志本不少错误。大正十二年(1923),武内义雄校订本出版,即“怀德堂本”。怀德堂本《论语义疏》正本四册外,校勘记另为一册。武内义雄又专写了《校论语义疏杂识》一文,对《义疏》的来历、现存皇疏旧抄本、皇疏之原形、经注之异同、疏文之衍字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廓清了不少围绕在皇疏周围的疑团。学界普遍认为怀德堂本选择底本好,参校本多,基本恢复了皇疏钞本旧貌,远优于根本逊志本。
本书为《蛾术丛书》第二种,影印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论语义疏》十卷,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一卷,书后附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十卷。
《論語義疏》读后感(三):皇侃的《论语义疏》
原文链接:https://m.douban.com/book/review/9488741/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论语》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其中尤以皇侃《论语义疏》性格鲜明,引人注目。
解经形式上,皇侃吸收玄学、佛学谈经说法之制,开创了儒学史上的“义疏”学。“义疏”在文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分“科段”,二是设问答。所谓分科段,是指对经注文进行解构,分章、分段来讲解。
皇侃《论语义疏》以魏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江熙《集解论语》等汉魏以来40多家通儒遗说汇编而成,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集汉魏六朝《论语》学之大成,为我们研究六朝《论语》学提供了绝好的史料。但自南宋以后,《论语义疏》便散佚国外,漂泊东瀛500年,乾隆时期才重新回传到中国。
日本宽延三年(1750),根本逊志在其师荻生徂徕的鼓励下,校订了足利学校所藏抄本皇疏十卷,以《论语集解义疏》的名义予以刊行。足利学校本属文明本系统,但抄写年代较晚,是日本大永年间(1521—1527)的抄本。根本逊志刊本最大的贡献是扩大了皇疏的流传,但有两大缺陷。一是根据明代邢疏刊本格式重排了皇疏经、注、疏的体式;二是在校订时师心自用,有以邢疏或《经典释文》更改经注、随意删除疏文的现象。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鹏航海至日本,购得《论语集解义疏》而还。后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将此书进呈四库馆,由此《论语集解义疏》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有武英殿刻本传世。
日本学界也对根本逊志本变易体式、臆改文字表示不满。大正十一年(1922),怀德堂(大阪汉学私塾)纪念会同仁商定请武内义雄(1886—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复其六朝旧体。武内义雄以日本旧抄本中年代较早的文明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其他十多种抄本、刊本,订正了根本逊志本不少错误。大正十二年(1923),武内义雄校订本出版,即“怀德堂本”。怀德堂本《论语义疏》正本四册外,校勘记另为一册。武内义雄又专写了《校论语义疏杂识》一文,对《义疏》的来历、现存皇疏旧抄本、皇疏之原形、经注之异同、疏文之衍字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廓清了不少围绕在皇疏周围的疑团。学界普遍认为怀德堂本选择底本好,参校本多,基本恢复了皇疏钞本旧貌,远优于根本逊志本。
本书为《蛾术丛书》第二种,影印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论语义疏》十卷,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一卷,书后附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十卷。
《論語義疏》读后感(四):《论语义疏》的三重结构
声明:此文源于网络
正文:
作为南北朝仅存的义疏体著作,皇侃《论语义疏》在体式上是既释经文、又释注文,所以其文本包含了三重结构,就像是三个由小到大的同心圆:最里一层的圆是《论语》原文,中间的圆是汇集了汉魏八家注释的《论语集解》,最外层的圆则是包括皇侃自己的疏在内的、由皇侃汇集的三十多家六朝注释的《论语义疏》。这种注疏体式的结构特点,使该文本包含了三层义理结构,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语》本身的主旨是什么?包含了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二,汉代注家主要在哪种方向上对《论语》作出了诠释?何晏作《论语集解》又对此作了怎样的调整?第三,皇侃及六朝儒者又是怎样作出时代性的诠释和转换的?
《论语》一书,无非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其中涉及孔子的形象、情感、思想和学说,所以任何《论语》注释之作,都是在考察、解说、定位孔子的形象和思想。汉人解释《论语》会塑造一个孔子形象,阐说一套思想义理,魏晋南北朝人又会塑造另一个孔子形象,创设一套新的思想系统。但是,无论后人对《论语》的注释如何地重点不同、方向各异甚至众说纷纭,《论语》作为《论语》学共同的文本对象,总有其自身基本的结构和内容。简略地说,《论语》一书包括这样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构成《论语》符号系统的典章文字,即《论语》全书的字词章句、名物典制、历史文献等等;第二,是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所倡导的仁道思想,也就是他关于君子、仁爱、忠恕之道等的道德学说,以及对圣贤君子人格境界的设定;第三,是在臧否时政当权人物的言语中吐露出来的关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设想,也就是孔子的王道思想和礼制名教学说;第四,是关于天道性命的思想。《论语》中孔子虽然较少谈及天、命、性等概念,但也绝非“不可得闻”,只是讲得平实而少作阐发而已。
《论语集解》保留的汉代注释有四家,分别为孔安国《古论训解》、包咸《论语章句》、马融《论语训说》和郑玄《论语注》。孔安国的注重在训诂,兼及大义。包咸的《论语章句》重在离析经文、疏通句义,着眼于交待背景知识。马融的《论语训说》既注重对名物制度的诠释,又好援引纬书解释《论语》。郑玄的《论语注》既重字词和名物制度的训诂,又善以礼说《论》,侧重于对《论语》道德、政治方面义理的阐发。总之,汉代《论语》注释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诠释《论语》的:一是训诂,一是章句或义说。训诂是就文字的形、音、义来做解释,章句则是整段逐句地解说,指括其文,敷畅其义。训诂侧重于对《论语》第一层内容即典章文字的诠释,章句学侧重于对《论语》第二和第三层内容即仁道思想和王道、礼制的诠释。训诂学的解释旨在还原文字、文本的“原意”,围绕文本、文字的可靠性、真实性而全力考证,可以说是着力于具体方法或技术操作的层面上。章句或训说并不局限于对文本零星字词的解释,而注重对《论语》中史实及篇章大义的解说。汉代章句、训说并不以辨名析理的方式演绎思想,而是多用实证的方法,故而详于对实事的铺陈或对史料的搜罗,所以这种解释又难免显得滞重而烦琐,对于《论语》更深层的思想仍然缺乏发掘。
既是基于对于汉儒烦琐学风的厌弃,也是对于汉儒注释缺乏理论深度和不能应对魏晋之际变乱时世的不满,何晏等人于是试图通过编辑整理过去的《论语》注释来改造旧学、缔创新学。《论语集解》改造旧学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即“集诸家之善”和“有不安者,颇为改易”。所谓“集诸家之善”,就是于汉魏众多的注释中,有所鉴别和选择地摘取一些存留下来。所谓“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则表示编者已经对某些注释作出了有目的的改易。“从他所集的前人的成说来看,多半是属于儒家的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方面,这些已经形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次,何晏对此并未持有异议,……从他感到不安而加以改易的部分来看,多半是属于天人之学即高层次的哲学思想方面。”何晏等人开创新学的方式,则是“自下己意”,即舍他人之注不用而自己作注,并且往往于微妙处搀夹玄言。用何晏自注和郑玄的注解做一比较,即可看出:“郑玄纯为汉儒说法,重章句训诂,主张以经解经,典章制度必明白切当,且偶有灾异谶纬的说法。何晏则一扫依傍,纯由老、易入手,遇有可染指处,则语涉玄理。”因此可以说,《论语集解》是在有意转换汉学、开启玄学。
构成《论语义疏》第三重结构的,是皇侃援用的一部分江熙的《论语集解》以及当代通儒的注释。这些注家中既有如范宁、颜延之、贺玚等名儒硕学,也有如王弼、孙绰、李充、殷仲堪、顾欢等善解玄理之名士,更有如沈居士、释惠琳等佛家硕学之流,基本网罗了魏晋六朝几乎所有重要的《论语》注家。《义疏》所集注释仍保存有不少汉代注释的风格,但总体上摒弃了烦琐的名物考证和冗赘芜蔓之风。而体现出《义疏》不同于汉儒注释、从而反映六朝思想新特点的注释,主要是受玄学思潮影响的玄儒的注。众所周知,玄学是通过重新诠释“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并着重开发其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拓展其思维路向的。以玄学注解《论语》成为六朝时代一种自觉的、占主体地位的方法。“三玄”与《论语》的交汇,体现出儒道会通的时代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论语义疏》对《论语》的解释就趋向于把《论语》平实、现实的旨趣往思辨、玄远的方向提升,所以它侧重诠释的是《论语》第四层内容即天道性命。
“道”这个概念在《论语》一书中本为孔子的仁道,在玄学时代则多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天道。王弼率先搀入《老子》义,称“道”为“无”,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把实体性的道诠释转换为无名无相不可名状的“无”,使道具有了虚灵玄通的灵动性。王弼以后,在《论语义疏》中所收集的后玄诸家谈“道”,多着重渲染“道”形上而虚玄的一面。如皇侃说:“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无形相。”⑩在《论语义疏·为政》篇里,皇侃又进一步把道、无、有等概念作了理论的关联,发展了王弼以来的道论,其中写道:“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为有,贤人所体也。”皇侃以形上与形下的区分来界说“无”与“有”,显然是本王弼以“无”解“道”的思路,把《论语》中的“道”彻底形上化、非实体化,这与汉儒的宇宙论迥然异趣,而进到了形上的本体论。
性情之论也是《论语义疏》着笔甚多且颇有新意的主题。汉儒多以阴阳元气说论性情,又多言性善情恶,趋向于把性情对立起来,故多否定情而肯定性。魏晋六朝人则多抛开阴阳谈性情,而以体用、动静谈性情。因篇幅之限,兹仅引皇侃在疏“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时所论性情之义,论曰: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
这里,作者论述了三点:(1)性无善恶,而有浓薄。(2)情为心之欲,有邪正。(3)性与情,犹火与热。这些都与汉代阴阳生成论的性情说不同,而火热之喻,更是用体用关系来解释性情。对《论语》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文本不曾言出的内涵,而是六朝注家在诠释中创造性地作出的引申。正是这些引申而出的性情论,继续成为宋明儒学所热烈讨论的主题。
从以上对《论语义疏》三重结构的分析可知,《论语》本身的意义与汉儒对它的诠释以及与魏晋六朝时代的再诠释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了文本诠释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表现为文本诠释者处在不同的诠释立场和诠释境域中,诠释者所接受的知识传统、学术背景以及个人资质等等构成了他的诠释境域,海德格尔称之为“前理解”,加达默尔又把它叫做“前见(偏见)”。加达默尔指出,这些“前见”就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传统,它构成为我们观看事物的“视域”。理解和解释总有两个视域,一是理解者自己身处现实中的当下视域,一是文本的视域,诠释最终是这两个不同视域的融合。由于读者是历史地变化着的,所以文本也就始终向新的生活经验开放,允许每一代人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延伸它,从而生成新的意义。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方式的诠释所生成的不同意义,又不是各自独立地封闭的圆圈,而是在效果历史的作用下共同构成为传统。《论语义疏》以其三重结构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诠释学意蕴。作为最原始、最核心的文本,《论语》是被《论语集解》包裹着的,而《论语集解》又被《论语义疏》包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已经使三者浑然一体而难于分辨所谓“本来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