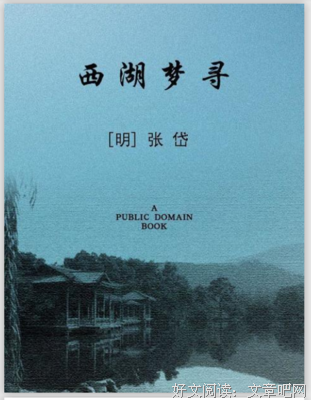西湖梦寻读后感锦集
《西湖梦寻》是一本由(明)张岱 著 / 李小龙 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湖梦寻》精选点评:
●西湖得一张岱。幸也。
●张岱的散文写得真的很好,沉浸在私人化的寓情于景和怀古当中还很感伤。就是他的诗和前人诗的对比实在是大型惨案现场。不比不知道,东坡真文豪(。但我觉得他超可爱,像一个正文发刀,又在作者有话说的框框里说笑话的讲述者。
●作为第一个读这本书人,义无反顾的打个五星… 初印8000,小龙哥哥要火
●古文最唯美灵动,张岱不枉为一代才子!
●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
●书经典,点评更经典
●赶在去杭州玩之前,先把这本书读完啦~~
●读张岱西湖梦寻渐生再去西湖按图索骥之感。陶庵之描写实为精当,又串掇古仁人志士文人雅士于西湖留下的笔迹和风流韵事,读来恍若在时光隧道穿行。所谓史笔诗心,此书是也。亦不失研究明清文学,对证校改的工具。
●张岱的诗真是有烂得可以,他还特喜欢把自己的放到最后,总结下东坡乐天李贺的诗后再看,那简直是惨不忍睹。但同时,他记录的西湖一面是声色犬马,风月宝鉴;另一面又是光风月霁,夜色撩人,真应了那句经典的“淡妆浓抹总相宜”。
●没人觉得这个注真的是个渣吗?------看了一年多了=。=......最近都是在收烂尾书,嗷,再也不一次性看十几本了=。=。扯得远了。明清,有了曹雪芹与张岱,这辈子都够用了。
《西湖梦寻》读后感(一):只可看,不敢爱
宝玉的前生是张岱吗?
那种对世间美好的真爱,那种实则高贵的谦卑,无与伦比的眼界,还有与生俱来的柔软……这样的男子只可隔着历史的烟尘,文字的山水好好欣赏。世间有哪个女子能经受如此“水做的”男子?
扯远了。
张岱的文字从大学时候看起,歇歇看看,而看张岱的日子必然是波折之后的停宁期。想想阅读和人的心境似乎也有微妙的对应。这两本书最近得到我两个班同学的热爱追捧,托我买书的人有好多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久前我们上了《陶庵梦忆序》。明清笔记体的小品文我经常当做课外读物推荐给学生,而文科生也会很容易的喜欢上他们。这类的书一路看下来,唯有张岱给我一种江湖感,一种举重若轻的深沉。奇怪的是,如此男子如此奇书,似乎满纸人世烟尘,但就是看不到张岱的红颜艳事。浓墨重彩如张岱,灵魂却是素色。
《西湖梦寻》读后感(二):西湖景点指南
《西湖梦寻》写于康熙十年(1671),距今(2020)349年。共72则,大概是72个景点吧。
我推荐此书有2个原因:
1. 从后往前推,清代是距离当代最近的封建王朝,那时的语言文字和现在的语言文字十分相似,读起来比较轻松,自己阅读也可,也适合带着小孩(10岁-16岁之间)阅读。(虽然我大学修了汉语言文学,但对古代汉语的钝感还是很明显的,若是从小接触一些简单有趣的古代汉语,钝感逐渐消退,变成对汉语的“敏感”。)
2. 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名胜(cultural landscape) ,如果单纯游玩,可能会觉得跟你家里的湖差不了太多。但实际上,西湖之所以有名气,更多是诗人文人赋予它的文化。尤其是从苏东坡之后,名气更甚。读着此书罗列的景点,可以了解西湖的文化内涵。之后,自己去游西湖,或者带着孩子去旅游都是不错的一本旅行读物。
我没有仔细读完,此书要在今天还给图书馆了。
摘录其一《西湖总记 明圣二湖》在此:
自马臻开鉴湖,而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淡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
余弟毅孺常比西湖为美人,湘湖为隐士,鉴湖为神仙。余不谓然。余以湘湖为处子,眠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之时;而鉴湖为名门闺淑,可钦而不可狎;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晴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
故余尝谓:“善读书,无过董遇三馀,而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馀。董遇曰:‘冬者,岁之馀也;夜者,日之馀也;雨者,月之馀也。’雪巘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涳蒙,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即湖上四贤,余亦谓:“乐天之旷达,固不若和靖之静深;邺侯之荒诞,自不若东坡之灵敏也。”其余如贾似道之豪奢,孙瀛之华瞻,虽在西湖数十年,用钱数十万,其余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实有增曾梦见者在也。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
这是张岱对西湖的高度概括。中国当然不止一个湖,有鉴湖,有湘湖,各有特色,而西湖胜在冶艳,文人韵士争相奔走。
西湖那么美,怎么游玩好呢?借用了董遇的读书之法,要利用好冬天,夜晚,以及下雨天。另辟蹊径,因为这些时间大家都不去,你去了,不正好吗?可以申请领略西湖之美。
除此,张岱还概括了对西湖贡献大的几个人:白居易,林和靖,李泌,苏东坡。
也有一些有钱人,比如贾似道,孙瀛,花了很多钱在西湖上,但他们不足道也。
另外还随手翻到了很有趣味性的一篇《小青佛舍》。
以后还会读读这本书的其它版本,再随缘寻一个好的版本的二手书买下来。
2020年12月26日 于深圳
《西湖梦寻》读后感(三):步履匆匆,岁月温柔
书中写:“善读书,无过董遇三余,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说的是三国时期有一名木讷好学的青年叫董遇,有人向他请教读书之道,他说:无他,读一百遍自然就明白了。那人又问,时间从何而来?董遇答: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张岱是有趣的文人,在他的书中,总能读到一些奇闻异谈;他也自诩不爱随波逐流,是个风雅之人,喜爱在人少清净时观景,《湖心亭看雪》可窥一斑。我是俗人,是在去年十一黄金周去的西湖,随着《西湖梦寻》感受一二。
我们住在灵隐寺的一间民宿内,店主约莫五十岁左右,人很和气。她儿媳妇在店里做帮衬,爱穿着宽松的棉布裙子,上面有彩色的晕染,和阳台上盛开的雏菊花浑然一体,交相辉映。小店外面有一方小小的空地,刚好放下一张小圆桌和三把小椅子,一旁的角落也被充分利用起来,放了两盆绿油油的植物。夜晚,和爸妈乘凉聊天,店主居然端了三杯茶水过来,我问她我们似乎没有点饮品,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说:聊天的时候应该配上点茶叶嘛。我们也笑了。这边人的生活节奏很慢。他们不像是在做生意,而是在和客人分享他们的生活,与其说他们热爱工作,不如说那就是他们的生活。
张岱是在四百多年前到访西湖,他写三生石上的神话传说,(我们的住所后面就是三生石,去看了看,摸了摸,凉凉的)也写湖心亭、十锦塘的枝叶扶苏。
十锦塘,一名孙堤,在断桥下。“断桥残雪”者,是谓:堤阔二丈,遍植桃柳。岁月既多,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最为有趣的是,他写六贤祠的故事,宋代西湖本有两个三贤祠,一个在孤山竹阁(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一个在龙井资圣院(赵阅道、僧辨才、苏东坡)。相传,宝庆年间,府尹袁樵把孤山竹阁三贤移到苏公堤,并了个亭子做生意卖酒。于是,有人写了一首诗:和靖、东坡、白乐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满面生尘土,却与袁樵趁酒钱。
我们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书中写的六贤祠。
书中写西泠桥“薄暮入西泠桥,掠孤山,舣舟茂树间,指林麓最深处……”我们去看了,奈何游人很多,有不少拍婚纱照的,其中一对颇有喜感,新郎矮胖,长相也实在难以描述,新娘靓丽大方,看上去并不登对。我想去看林逋的放鹤亭,路过“苏小小墓”,这并不是真的墓,只是一个纪念和地标罢了。很多年前,一位才女的风花雪月,很多年后,无数游人慕名而来,有小孩子攀爬上去,一手拿着快融化的冰棍,一手黏糊糊地去扣“苏小小”三个字。
西陵苏小小诗: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边水土养文人,不仅有白居易苏东坡,也有一生不仕不娶的林君复,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佳句和“梅妻鹤子”的美谈。在“舞鹤赋刻石”和“林和靖墓”前,我想拍照留念,无奈几个孩子在“舞鹤赋刻石”前跳皮筋。未能得愿。
“你们都去了哪里?”店里的女孩一脸好奇的问我们,我们细细说与她听,并且给她展示了一番我新买的旗袍。“你穿上真好看!”她眼神澄澈,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河坊街生气勃勃又古香古色,我们喝了碗藕粉,看了胡庆余堂,爸爸说这是胡雪岩创办的,他是很厉害的人。我买了一本《诗经》。河坊街小吃很多,但我却回忆不起那天的嘈杂声了,只觉得一切都很静很美,像小溪一样缓缓流过,或许是和家人在一起吧,人会变得温柔。
这边桂花很多,到处都是甜甜的香味儿,似乎有点香得过了头。当地人告诉我们,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原来是这样。
西湖梦寻,带回一片琉璃的彩云。
《西湖梦寻》读后感(四):杭州西湖的文人基因
张岱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亡前。那时候他作为富贵公子,生活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此段可谓“天上”。而第二阶段则是明亡之后,作为明代遗民,他的生活马上堕入了困境,遍历了炎凉世态,可谓“人间”。然而,正如苦难往往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张岱的“从天上坠入人间”的遭遇不仅没有阻断他的创作生涯,而恰恰相反,使他产生了更多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品。
《西湖梦寻》著于康熙十年。所谓梦寻,是老年的张岱寻找他年轻时的梦,也就是说对他年轻时了解的西湖进行一个回顾。他写书的时候早已经进入清朝,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对西湖的回顾实际上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明末)的回顾。那个时代对于当时的张岱而言,就像梦一样美好,但是又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再现了。从文笔上讲,张岱并没有赋予特别强烈的感情。所有的篇章都显得风淡云清,这个估计是当时中国文人“克制感情”的普遍做法吧。
然而,仔细读读,张岱文字背后的情绪还是很容易感觉到的。这种情绪有忧愁的成分(“美景不可再得”),但是也同样有对于传统华夏文化的忠诚以及对于异族统治者抗争的成分。比如,卷二西湖西路中有关飞来峰的记载。讲到元代杨琏真伽作为朝廷派驻江南的佛教总管,在江南倒行逆施,深受当时江南人民的痛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叫真谛的和尚,乘杨琏真伽正在试图盗挖古墓,突然冲出用木棍击伤杨琏真伽,“裂其脑盖。众人救护,无不被伤”。而杨被打后,也不敢声张,只能说真谛和尚乃韦陀显圣,偷偷的放弃了盗墓的行为。事实上,张岱本人年少时也曾经在飞来峰砸毁了一尊杨琏真伽根据其自己面貌雕刻的塑像。张岱记录这些故事,也应该有以古讽今,表示对清政府对抗到底的意思的。
杭州之所以始终能够使传统文人一个遐想的空间,并不仅仅是西湖自然风光有多么优美,而是在于隐藏在其中的从唐末到近代的历史。或者说是这上千年间各种文人们的内心所想都化作了珍珠散落在湖山之中。这些珍珠就是隐藏在山水中的某个亭子,桥梁,雕刻,石碑,古塔,荷塘,坟墓,古泉等等。西湖及其周边的景观并不是某个皇帝或者富人一次营造而成的,而是一代一代文人的集体创作以及再创作的结果。这也造就了西湖景观的不可复制性。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于西湖景观非常推崇,并且在北京的皇家园林中反复进行复刻。如今天的颐和园其主体景观就是模仿西湖建设的,其中的西堤事实上就是西湖苏堤的复刻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皇家园林只能得到西湖的“形”,而无法把西湖的“神”搬过去。因为即使拥有巨大的权力,皇帝一人之力与一千年文人们的集体意志相比也是渺小的。
比如就以西湖中的孤山为例。孤山最早在于唐朝就有记载。当时孤山主要的景观是孤山寺。作为西湖中唯一的天然岛屿,孤山在唐代应该是作为一个远离城市的佛教场所存在的。唐代张祜的诗句“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就描述了这么一个富有禅意的场景。而宋代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隐居故事以及他自己临终前“犹喜曾无封禅书”的自我评价又给孤山带来了一种儒家文人保持自己的气节,不愿意和道德上有亏的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典范。可以说林和靖的故事等于在孤山建立了一种文人的标杆。这个标杆将始终影响孤山乃至杭州文化。
在南宋,孤山一带被皇室贵族所占据,然而元明时期它又回归到了民间。而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在孤山南坡建立了行宫,使孤山的精华部分再次被皇族所占据。但是行宫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而清代覆灭后,民国政府又在其废墟上建立了中山公园。纪念共和国创始人的公园建立在封建皇帝的行宫遗址之上,应该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吧。不仅如此,民国建立后很多反清烈士的陵墓被建在孤山山脚下,所以在民国的那一段时间孤山应该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的人文景点。后来虽然大部分陵墓被迁移到了鸡笼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内,但是鉴湖女侠秋瑾的陵墓最后又迁回了孤山,屹立在西陵桥边上,与中山先生的公园相对而立。
在孤山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山公园和秋瑾墓之间。这是清末民初浙江的几位篆刻家在这里结社的地方。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是书画家吴昌硕,著名社员包括黄宾虹,李叔同,马一浮,丰子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李叔同出家时,他把自己所有的印章都交给了西泠印社,埋藏在印社山间的石壁上,称之为“印藏”,之后世间就再无李叔同,而多了一位弘一法师。走进西泠印社的月亮门门,沿着台阶登上山顶可以看到一座刻满经文的华严经塔。塔上的《西泠华严塔写经题揭》就是后来弘一法师的手书。在西泠印社中,还有一个石室。这个石室是建社初期特意为从浙江余姚出土的一块东汉石碑所建。这块石碑被称为“汉三老碑”,因为上面刻有汉代当地的一位“三老”地方官吏的祖孙名讳和忌日。其书体介于篆隶之间,在文字发展史上非常有价值。当初该碑出土后,差点被转卖到了日本。最后在社长吴昌硕等人的努力下,通过募捐和社员义卖书画,才得以筹得重金,购买下了这块古碑,并且建立石室将其永久的保藏在西湖之畔。清朝皇家宫殿终成为废墟,但是代表文化的西泠印社却在其边上大放光彩。孤山终究还是属于文人的领地。
隐士林和靖时期的孤山属于文人,然而到了南宋则被皇室占有。到了元明孤山有一次回到了文人手里,但是到了清朝再次被皇室占有。而到了民国之后,又一次回到了文人的手里。孤山就这一次一次的在文人和皇权之间易手。实际上,孤山的历史也就是杭州西湖历史的缩影。每当皇帝,贵族,达官贵人势力增加,西湖往往会被他们占据。然而,就如同东去的大江之水一样,时间最终会淘尽这些权贵的影响,而最后能够在西湖留下自己身影的往往是那些文人们。他们的文化基因终将融汇到了湖山之中,成为了每一位热爱西湖的文化人的共同财产。而张岱的《西湖梦寻》毫无疑问也是这一财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