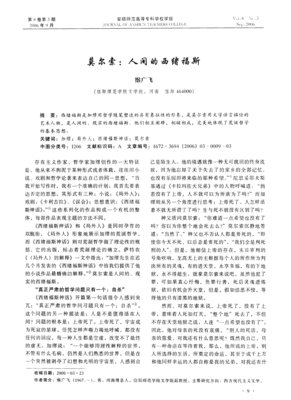《西绪福斯神话》读后感锦集
《西绪福斯神话》是一本由[法] 阿尔贝·加缪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绪福斯神话》精选点评:
●重读加缪,虽然没有读出新的东西来,但对他的作品和人格钦佩并未减少,修辞以立其诚。的确,加缪并不是以哲学思辨著称,而是以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为主题、为人类寻找幸福之路的作家。这次特别注意了一下现象学的部分,这是之前没在意的。加缪的作品源自他的生活,源自他对世间的爱,从荒诞意识的觉醒,到对荒诞命运的积极反抗,否定自杀、虚无主义,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可能是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后唯一可以给人救赎的哲学了。“荒诞-反抗”也可以看成苦和对苦的解脱之道的探索,只不过这种反抗是立足于一种激情、对抗,而不是一种寻求和解的寂静之道。
●这是一本越早读越好的书,可惜加缪/翻译行文并不对中学生那么友好。我第一次读时很囫囵,记下了加缪的“准则”可毫无感触,反而是日后在生活和其他作品中逐渐明白了类似的观点。这次重读难免有些唏嘘,虽然例证和逻辑上我并不为他背书,可他说的我总算明白,却又不是因他而明白。
●荒诞主义!有爱的很。我终于成为了一个荒诞者,义无反顾地投入生活。Btw翻译可以润色下。想把“xx的人的xx”改成“xx之人的xx”。。。恩。学校破图书馆淘了半天才淘到的好书。
●没有永恒,杀死上帝,无意义,对抗,“人与其生活的离异 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 正是荒诞感”
●没读完
●这位“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以其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神的蔑视变得无比强大,从而超越命运的摆布。“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由此推理,加缪判断: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缪认为,荒诞的不是人本身,也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共存中。《荒诞的推理》论自杀,到《荒诞的人》《荒诞的创造》更为精悍。加缪对陀翁《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与卡夫卡评点深刻。尾篇《西西弗神话》最优。“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他在沉默中静观他的痛苦,沉默与静观中包孕加缪荒诞哲学完整的幼芽。人是受时间支配的,但人有时也必须支配时间,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他就确立了他对时间的位置,因此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并由此而产生恐惧。他希望着明天,但这明天却是与死亡相联系的,是他本该加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
●不好意思,我连中学生都不如,总算读完了,再您妈的见
●荒诞产生于人和世界的共存与对立,这种对立产生于人的意识。荒诞无处不在,荒诞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人们,牵动着人们脆弱的理性与坚强的入世观念。 人是短命而渺小的,所以寄希望于永恒,通过献身集体和历史来接近永恒。加缪打碎了这些无谓的梦,也解放了很多挣扎在这些梦里的灵魂。他区分了荒诞与虚无,指出自杀不是荒诞的解(自杀取消了人,从而取消了荒诞,但没有解决它),荒诞是无解的,面对荒诞,人惟有义无反顾地生活。在荒诞这个起点上,加缪给出了一条反抗的道路,但这反抗是没有终点的,找到终点便违背了反抗的初衷。
●人太傻,未完全懂
●生活是各种各样无尽的荒诞。
《西绪福斯神话》读后感(一):荒诞者
“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
“人们可能认为自杀紧跟着反抗。但是不对。因为自杀表现出不反抗的逻辑的结局。因为根据它所提出的允诺,它正是反抗的反面。如同跳跃一样,自杀是尽其所能的接受。一切都至善至美了,人又回到他的本质的历史中了。他的未来,唯一的、可怕的未来,他已分辨出来,并投入其中。自杀以它的方式解决了荒诞。它把它拖入同一种死亡中去。但是我知道,荒诞是坚持不懈的,不能解决。荒诞逃脱了自杀,因为它同时是对死亡的意识和拒绝。”
“而野心不过是通向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的道路。”
的确自杀者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我曾是那样的人,在抑郁时候。
恩。我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拒绝死亡的荒诞者。
《西绪福斯神话》读后感(二):20200506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判断人生值得过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与疾病共存。” “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 “对荒诞的人来说,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一切都从有洞察力的冷漠开始。” “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没有轻蔑客服不了的命运。” “我让西绪福斯留在山下!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西绪福斯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也断定一切皆善。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征服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西绪福斯神话》读后感(三):伽利略表示自己开得起玩笑
P6一处译文郭版和沈版迥然有别,分别都说得通,不影响整体立论,但却对伽利略开了个小小玩笑:伽利略放弃了真理还是弃绝了生命?
郭宏安译文: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为了本体论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这个真理能值几文,连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
沈志明译文:
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断去死的。伽利略掌握着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一旦这个真理使他遭遇生命危险,他便轻而易举地弃绝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但不值得。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
*注: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他做对了。相反,从生殖行为来讲,这位学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P.S.摘引相关背景资料:
1.1615年,伽利略从佛罗伦萨前往罗马捍卫科学真理。所幸受朋友庇护全身退回佛罗伦萨。
2.1633年,伽利略第二次到罗马,被教廷审讯并判终身监禁。6月22日,伽利略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宣布放弃以前的著作和言论。
3.此后9年,伽利略一直被幽禁在佛罗伦萨,直到1642年1月8日逝世。期间,他仍暗中整理自己的著作,并寄到荷兰的一家出版商那里。
据上,从局部事实可以说伽利略放弃了真理(2.),但放眼看也可论证伽利略为真理是意愿弃绝生命的(1.&3.),因此脱离原文来理解的话,两种译法均可自圆其说。至于加缪本为何意,不见原文不便揣测。
《西绪福斯神话》读后感(四):生活向前,哲学向后
“荒诞”是加缪哲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前提。当人类的意识与这个陌生的世界相遇,它便有一种野心,试图给用理性的普遍、统一与绝对来认识世界,给世界以本体论的解答。对于这种野心,世界总报以模糊、矛盾与杂多,不断地提醒人们,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道无法填补的裂痕。“荒诞”就是这种人与世界的对立,这种对立产生于人的意识,产生于人对完满的怀念。荒诞主义否定完全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承认人类理性的边界。“这种对统一的怀念,这种对绝对的渴望,说明了人类悲剧的基本运动。”“非理性、人类的怀念和从它们的会面中冒出来的荒诞,这就是一出悲剧的三个人物,而这出悲剧必然和一种存在所能够具有的全部逻辑共同结束。”[1]
“荒诞”本是一个文学术语,哲学上的荒诞源于解构,源于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解构的哲学方法指出形而上学无非是建构的产物,宗教和道德也是如此,都是反生命、反自然的迷梦与神话。尼采击碎了建构哲学的大厦,指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终究是一个幻想。自此,荒诞得到哲学上的证实,就这样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毫无遮掩的余地。荒诞杀死了形而上学,进一步展示了它强大的毁灭力量。
加缪和他的哲学,就站在这样的起点上。
随着古典时期的终结与现代哲学的发展,传统价值逐渐崩塌。二十世纪中期,经受了二战的浩劫后,在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对未来充满质疑与迷惘。“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的?”这一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母题再一次刺痛了人们脆弱的心灵。“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乐土的希望。”[2]外部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同时崩塌,使得越来越多的被“放逐”的人们被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面对这样的困境,加缪并不企图建构出一套精密的哲学体系来解决荒诞,在他看来荒诞是无解的。他更关注在荒诞下人应当怎样生活。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3]人应该怎样面对荒诞?加缪首先否定了自杀,自杀在人与世界的对峙中取消了其中的一方——人,因此自杀只是取消了荒诞,却没能如愿地解决它。加缪认为人只有接受荒诞,并在荒诞中义无反顾地生活。
“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4]加缪认为,一切试图给予生活某种意义的行为都是背叛生活。何况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在尼采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意识到,哲学对于人的认识和世界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哲学失去了几乎全部的研究对象,就连语言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哲学已经奄奄一息,只有与其他学科结合才能保持一点生命力。但人的生活却生生不息。生活不为哲学统治,更不随哲学灭亡。荒诞杀死了价值,却杀不死人的生活。
“这样,我就从荒诞中引出三种后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5]加缪认为,在荒诞面前,一切经验都是等值的,生活得“好不好”难以衡量,因此人们应当追求“生活的最多”。正如将滚落的巨石一次次推向山顶的西绪福斯,徒劳而幸福。[6]加缪用西绪福斯的神话隐喻全人类的命运,即生活是无休止的反抗,找到终点就违背了反抗的初衷。加缪宣告了世界的荒诞,又将生活从价值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后迷惘颓丧的一代青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加缪哲学的社会意义。
但即使是这种“生活得最多”的主张,也无法完全支配人们的生活。今天,大多数人仍认为生活是有好坏之分的,人们依然有奋斗的目标,孜孜以求之。我认为,重要的不在于生活的价值是什么,而在于谁掌握了界定价值的权力——是尼采口中的“偶像”,是主流话语,还是每个人自己?可以说,谁掌握了界定价值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人的生活。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就有依附主流和坚持独立两条生活的道路。服从带来内心的平和安逸,但也伴随着个人意志的无力;独立要求人重新建构自己,并对自己负完全的责任,加缪的“自由”也会带来重担。而这两条道路也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的论域中,孔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使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成为圆融的整体,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思路。这样看来,与其说荒诞打碎了人对生活抱有的幻想,不如说荒诞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起点。生活本身依然有无限可能。
[1] 加缪,《荒诞的墙》,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
[2] 加缪,《荒诞与自杀》,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
[3] 加缪,《荒诞与自杀》,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
[4] 加缪,《荒诞与自杀》,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
[5] 加缪,《荒诞的自由》,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
[6]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