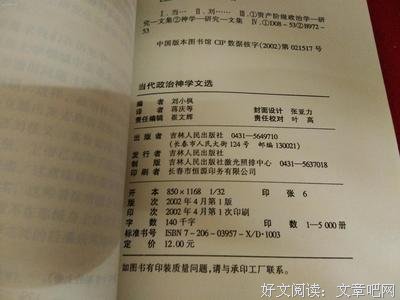保罗政治神学读后感精选
《保罗政治神学》是一本由(德) 陶伯斯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保罗政治神学》精选点评:
●陶伯斯认为保罗的《罗马书》只有从政治的角度上理解才能够挖掘真正的内涵,保罗并非要贬低犹太教,而是效仿摩西成为新宗教的创始人,这与弗洛伊德的摩西解读有着相似,暗地里是与施密特的政治神学较劲,试图将保罗理解为从下到上完成这一使命。这本书是定哥翻译的。
●更推荐陈佐人牧师对政治神学的理解
●这个月算是把2016年读过的陶伯斯重新读了下。对于基督教和保罗、施米特的理解更进了一步、甚至对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理解也有所深化。但不敢说完全消化了陶伯斯,很多犹太性上面的东西,自己的体悟明显还是不到位的。
●反复阅读,被洗脑,对我启发之大,不可阻挡
●复盘一遍,线索清楚了很多。清醒,刻薄,所以用最断语甚至是嘲讽点通了很多问题。巴迪欧误解了陶伯斯,他的保罗比起来就太过于鸡汤了。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吐槽。
●律法并非万物的始终,人与人之间’甚至‘还有’逾越‘与’违背‘律法的关系——爱,怜悯,宽恕。
●此书虽以陶伯斯的讲座为本,但从编排上看,编者还是希望把此书作为施密特的注解。陶伯斯讲话并不依定稿,而是即兴发挥,他的这次讲座有一种“时间如此迫近”的末世体验。这种迫近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是针对个人的。人皆有死,但在最后的末世之前,人的死是有先后的,一个一个的。对于个人保罗来说,他并不是改信,而是奉召,是被“拣选”。一切都是“拣选”,事情已经被上帝决定了,行动不可能有意义。保罗奉召成为使徒,这与他的犹太人的自然性质无关(神子也与犹太人的自然性质无关)。保罗的书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罗马又是皇帝崇拜的中心,陶伯斯断言,《罗马书》就是对皇帝的政治宣战。《罗马书》的结尾提到保罗想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这面对的是犹太基督徒。保罗拒绝犹太人的特殊性,“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意味着:他信仰上帝,上帝
●陶伯斯与施米特两位西方大思想家的相互碰撞和影响,涉及政治哲学、神学,非专业人士可能不大看得懂。不过译文非常赞,文笔流畅,尤其说明性的文字可读性很强。结合施米特的相关图书阅读,启发性会很大。
●3.5
●Temp d'apres
《保罗政治神学》读后感(一):啃硬骨头
跌跌撞撞接触到政治神学的话题,看到译者居然是吴老师。缺少阅读这类书的背景知识,硬着头皮啃硬骨头,还是云里雾里。只好记录一些观点。
一种是信任,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信仰关系之中,个人原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的誓约受到某个无条件者的限定和规定;一种是让人皈依的信仰,对……的信仰,一个个体,共同体则成为已皈依的个体之间的一个誓约。对……的信仰,绝对不只属于希腊,而且是一种弥赛亚逻辑的核心。
一切都蕴含在称呼语之中的标题,也就能够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容;基督教的文献是一种抗议如日中天的皇帝崇拜的文献;一项契约得以缔结,而缔约的双方对它的解释完全不同。否则,政治就不存在了;有基督徒存在的事实,并没有进入犹太人的意识。
事功?受拣选?普世?使保罗同以基督耶稣面目出现的上帝之爱相隔离,保罗愿意成为基督的诅咒对象。
节日本身就是宽恕;从仪式中发展出神学;保罗把自己理解为摩西的超越者;基督教的起源在根本上不是耶稣,而是保罗;实体被转化为主体。
精神是最高贵的概念,是新时代及其宗教的概念。此世的圣灵,上帝的圣灵;隐喻的意义、历史的意义;人们如何使上帝解除自己的誓言?
需要就在完满本身之中; 我们的道德及其结果并不符合我们有意识的意志。
在改信的语境中,信仰被理解为摆脱律法的自由;在奉召的语境中,信仰则被规定为对上帝的服从,并且被规定为一种政治颠覆的行动。
《保罗政治神学》读后感(二):保罗视阀下的政治神学
保罗视阀下的政治神学
作者:王政民牧师
汉语学界已经知道Jacob Taubes的名字,虽然陶伯斯的著作并未进入被引介进入中国,但是在对施密特和政治神学的理解时,那种政治神学的框架是经过陶伯斯再度阐明的。将基督教和公共生活扯上关系,汉学界对此有瘾,这或许源自长久以来公羊学的余荫,也或许和操汉语者的民族天性使然。在施密特之前,使用“基督教宪政”“公共神学”“基督教公共性”为经世工具的人,大概受益于新教的圣约神学,美利坚建国之后,政治家思考这一神佑国度的历史时发现,是圣约神学最终导致了“联邦制”政府的出现,且圣约神学的教会长老治理架构是参议两院代议制的雏形,而充当圣约神学和联邦制政府的一种中介则是“联盟神学”。
不过,20世纪的欧洲人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在大陆传统下,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对社会建制根本无法输送建议性资源,所谓圣约神学,真正的意图是促进“世俗性”政府的出现,把“神”的绝对性价值排除出世界之外,是欧洲人这么做的。不过,与其说是主动排挤神对政治秩序的参与,毋宁说是观察到了神根本从未参与在政治秩序的运行。所以,陶伯斯站在了施密特的阵营里,开始对“自由主义者”不屑一顾,并提出建议,劝说自由主义者重新认清“启示”的传统。
陶伯斯认为,美国或者其他的政治技术,姑且把与启示对立的政治学理念称之为“技术”,毕竟陶伯斯和一切站在思想谱系保守一边的人,压根不承认“政治学”的存在,美国的政治技术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错认了基督教的启示性。启示是基督教的核心,在对这个核心的把握中,灵智人一度和大公派产生抵牾。按照陶伯斯的看法,在一个神竟然不看顾的世界上开始的公共生活,是政治神学的题中之义。而所谓宪政的超验之维,从来是彼岸的事情,这个彼岸到底能给“在岸”输送多大的支持,经过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对此发言权很大。而陶伯斯这位柏林自由大学的诠释学教授,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说实话,任何一个犹太人只要反思,就能重新认识真的上帝,何况作为诠释学和政治哲学家的陶伯斯呢。
陶伯斯著述颇多,除了对施密特的理解之外,其晚年讲座的信息经整理为《保罗视阀下的政治神学》一书,算是对灵智人政治视野的一次继续开拓。近些年来解释保罗思想者不乏其人,也成果频出。对保罗的解释,可以有两个阵营,如果巴特和陶伯斯等作为灵智人阵营的话,圣公会牧师保罗莱特则算是另外的阵营了。双方都在延续深度挖掘历史背景信息的考据功力,莱特认为保罗的称义观是教会观的一部分,成圣观则是末世性的。这突破了人们传统的理解力,而又深深为之折服,但是陶伯斯走的是另外一个对“原始保罗”的分析,这个分析正和陶伯斯的好友约纳斯做的,挖掘到了晚期古典的精神,这个精神即是保罗甚或摩西所阐述了“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eople of god ”,即通过对罗马人“宣战”,让罗马人知道自己是“此世异乡客”( strangers in this word )。这对莱特等人的原背景解读保罗震撼不小,不过两种“解风”和“品质”截然不同,陶伯斯们甚至不会去看莱特的作品。
现代世界的本质,在陶伯斯看来是“Nihilism”,保罗面前的罗马基督徒正在被告知这一存在事实,而政治正是源自对此存在的爱。爱归爱,如何理顺虚无时代的人人和人神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罗马基督徒作为外邦人,听到保罗自己的见证,被召(called,chosen)而非通过conversion,成为上帝的百姓,这是“让世界震惊”的。以色列人的优越再也不存在,世界不是按照律法规约来建构,秩序的意义不大,甚至是nihilism,即虚无。成为虚无的原因很简单,上帝不依据“秩序”的美,而called人。那么,这对此时刻的汉语公共神学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的时刻,是政治转型,社会进步,而底层信众开始谋求政治声音的时代。依陶伯斯看,这类声音作为政治工具还可以,假如较了真,真的铺就秩序、民主和宪政的堂奥的话,不免又陷入了一个虚空。
陶伯斯并没有给当时战后的德语学界打哑谜,而是切实的为虚无时代的人们提出了一条出路,即保罗的盼望“aestheticized messianism”,保罗深信恩典来自世界之外的弥赛亚信念。保罗也深知自己曾做过法利赛里面最“优秀的人”,未改变行为而直接被召的经历,使得他确信,唯有启示之神,在混乱秩序结束的时候,方能将恩典一股脑的倾泻到人世。其视阀下,政治神学,源于为虚无之中的人,寻找避免瞎折腾而有的至终恩典。
王政民,当今较有名的自由派牧师
《保罗政治神学》读后感(三):我们为什么需要保罗?
并非解经,而是在对施米特进行回应,核心问题在于,共同体何以可能?施米特以断然的姿态说:“主权者就是能够对例外状态做出决断的人。”在奇迹般的例外的时刻,宪法终止了,一切问题都变成了政治神学的问题,共同体的边界依靠敌友之分来划清。陶伯斯抗拒这种“自上而下”的思考,以权力为出发点的思考,而选择“自下而上”的路径,因此,他必须走向保罗,因为“律法并非万物的始终,人与人之间’甚至‘还有’逾越‘与’违背‘律法的关系——爱,怜悯,宽恕”(p245)。陶伯特选择《罗马书》而非更感人的《哥林多书》解读。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保罗并非十二使徒之一,而是从迫害教会的扫罗奉召而成在尼禄手下殉教的保罗的。对保罗来说,他所要挑战的对象有二:1.犹太人的种族的共同体;2.罗马帝国的秩序。选择成为基督徒,即是背弃了自己的种族出身——犹太人。为此,他是被诅咒的(Anathema)。保罗从犹太人成为了外邦人,但外邦人通过信仰成为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保罗试图以此消除教会中犹太人基督徒与外邦人基督徒的政治区分。以色列并不是因此被上帝抛弃,而是成为更普世的以色列。
摩西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提醒上帝守住与以色列民族的约,否则上帝的公义不存。读过旧约我们可以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个信实的人,但神拣选雅各甚至在他出娘胎之前。这样的拣选有何公义可言?这完全不符合理性。无怪乎本雅明会说他的历史哲学受到了施米特的启发!被救赎与此世的努力无关,自然的秩序终点是衰亡,被宽恕只因为你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时候近了”,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他随时还会再来——那么在当下,任何革命都不值得!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首先承认有一位弥赛亚。神的救赎与你无关——但若不如此你将永远看不到希望的星光,永远困在自然的秩序里,而那就是万物的消逝!救赎无法轻易到来,必须直面虚空,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正因为神的秩序里唯有毁灭才是永恒,救赎才有意义,这正是奇迹之意。彻底的革命既是无作为。
尼采咒骂保罗,耶稣不过是个善良的白痴,是保罗,这个法利赛人,同时也是罗马人,以维护律法的狂热给加利利的木匠戴上王冠,彻底否定了罗马的律法(nomos)。“被钉于十字架而死的人才是掌权的那人!”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是彻底对立的。“这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把弥赛亚式的反抗普世化了”(p182)。保罗的基督教和其实质的犹太性,令西方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现代性的颓废从耶路撒冷就开始了(阿甘本后来说希腊哲学也难逃其咎)。
保罗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受拣选乃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因此仪式同样不能划分共同体。“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核心的、唯一的义务只有一项:对邻人的爱。“爱意味着,他者是必需的,没有他者,便寸步难行”(p92)。笛卡尔错了:作为自我的主体并不是最重要的。
施米特不承认法的彻底毁灭,他宁愿接受最糟糕的状况(例外状态在独裁者的决断下成为常态),这一点把他推向了纳粹。施米特、陶伯斯、和本雅明都承认人的非自主性。施米特依次为根据确立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为统治论层面提供了神学的正当化;本雅明要求否定尘世(profane)的幸福,而陶伯斯要求我们在世界(welt)和精神(geist)之间进行权力分离。黑格尔的 geist 自进入现代后已经是声名狼藉了,只有坚持这一分离,才能为那些在低处的人们思考,才能维护“混乱”,才能守护住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保罗-斯宾诺莎-基尔克果-尼采-弗洛伊德,陶伯斯指出的,是一条反叛者的道路。
.S.哪个热爱本雅明的人不对阿多诺被黑喜闻乐见呢。
这只是自己做的笔记存档。我写不下去了。
《保罗政治神学》读后感(四):《保罗政治神学》读书笔记
陶伯斯的讲座梳理了保罗在诸个世纪以来的接受史。保罗开启了两条出路:一条是正统的“进入教会”的路子,一条是马克安(Marcion)所走的路。后者是一种灵知论倾向:新约的耶稣基督之父不同于旧约的造世之神,造物主对这个世界的创造是一种“可怜的创造,到处都是蚊虫叮咬”,而耶稣基督之父是“陌生的上帝”(deus alienus)。保罗的律法批判的攻击目标是希腊化时期的“掌权者神学”,即盛极一时的罗马,而马克安将这种律法批判拨动一下方向就用来反对旧约。而哈纳克认为马克安主义的潜在接受史历经奥古斯丁的恩典说、路德的基督论(信仰取代事功),一直贯穿到19世纪规定“基督教本质”的努力(施莱尔马赫、黑格尔、托尔斯泰、高尔基)。而在陶伯斯看来,保罗虽然开启了将外邦人纳入到教会当中去的“普遍主义”的工作当中,但是他仍然能够坚持《旧约》作为正典的标志的有效性。保罗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充当“和事老”,在两种宗教间挖掘各自的辩证法。流俗之说认为一极是犹太教的“通过仪式化获得宽恕”,另一极是基督教的“通过解放获得拯救”,而陶伯斯要挖掘的是犹太教传统中的“解放”这一极。
【引言】
保罗的犹太教宗教史的角色仍需要被挖掘,陶伯斯强调自己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非哲学家的身份来解读《罗马书》。
【第一部分 《罗马书》讲解】
【《罗马书》的收信人】
称呼语非常关键,保罗不是“认信”(Bekehrung)(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而是“奉召”(Berufung),“保罗认为自己是奉召为使徒”(p20),关键在于“从犹太人成为外邦人”(p20,保罗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由于保罗不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他也没见过耶稣,他没有作为使徒的正当性,所以“他必然是一种新的使徒”,所以“奉召”就是一项【正当化策略】。
以罗马书对抗罗马的【皇帝崇拜】:
《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它是一篇政治宣战,“《罗马书》就是一种政治神学,一篇对皇帝的政治宣战”(p24),“一种抗议如日中天的皇帝崇拜的文献”(p21)。
【耶路撒冷与普世传教的正当性】
《罗马书》第15章的结尾涉及到保罗将在马其顿所募捐到的钱款亲自【送往耶路撒冷】;捐款的目的是力图【获得正当性】,而不仅仅是关系到爱人,因为“谁要是接受这笔钱,那么他就等于是接受【外邦基督徒】的钱”(p26),捐款的意图就是在外邦基督徒教会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教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犹太人认为基督徒不属于誓约的民族,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而保罗实际上宣称“谁若有了信仰,那么他就有了割礼的等价物,即【事功】(Werke)。
【法:法律与称义】
保罗的激进性:
奋锐党人(Zelot)对罗马发起圣战,政治弥赛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且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保罗是一位奋锐党人,甚至超越了奋锐党人:“他的回应方式是一种抗议,一种【价值的颠覆】:不是律法,而是被律法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才是掌权者”(p37),这使得其他一切渺小的革命家什么都不是;保罗的这种价值重估把弥赛亚式的反抗【普世化】了,这种普世主义意味着以色列的“【受】拣选”,“以色列现在要经过改造,然后最终形成一个‘普世的以色列’“(p38)。
尼采与保罗:
“尼采在保罗那里揭示出来的东西,价值重估的天才,恰恰包含在对律法概念的批判之中”(p40)。
保罗的任务:
对保罗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上帝民族】并使之正当化”(p44),这基于这样的基础是“上帝的忿怒要灭绝这个民族(以色列),因为它犯了罪,因为它不忠诚”(p44)。
【受拣选与被抛弃】
赎罪日将上帝和摩西之间的争执转换成仪式,节日本身是【宽恕】,要穿丧服,但有两种情绪:一是“当一个人被裹在丧服之中时,他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属于德国浪漫派;另外一种就是宽恕,宽恕的意思是“整个共同体都被宽恕了;这种孤独的自己恰恰并不存在”(p58)。保罗和摩西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个民族犯下了罪过,这个民族拒绝了弥赛亚。而保罗把因为拒绝弥赛亚而招致的上帝之怒,同因为拒绝律法而招致的上帝之怒相提并论,这是【以色列同上帝关系】的最低点,但对保罗来说,这个废止一切既定关系及其连续性的最低点,就是【重新建立上帝民族】的地方。当保罗说他受到基督的诅咒时,这是一种毁灭——“上帝的民族不再成为上帝的民族”(p62);赎罪日有一种让每一个犹太人都能体验到的力量,陶伯斯和罗森茨威格一样,倾向于【从仪式中发展出神学】。
【圣灵:对救赎史的逾越和这个世界的克服】
在保罗的语境中,就圣灵而言,【信仰与事功的对立】对应着【圣灵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对立】,圣灵的原则赋予保罗以【超出种族纽带】的自由,这样一来保罗在此把自己理解为摩西的超越者;他借助经文来证明“向外邦人开放的时刻到了”(p66),他的忧愁在于他要背弃一切;圣灵的逻辑超越了既定的自然秩序,在保罗的普世化方案里,圣灵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范畴,超越传统的持存及其规范要求,并且超越上帝民族的【种族界限】;“圣灵(精神)成为一种改造一个民族、改造文本的力量”(p74);保罗不想抛弃犹太民族,但是要使得他们充满妒忌,因为吸纳了外邦人。
保罗对耶稣的【双重义务】的简化:
保罗把耶稣的双重义务(对邻人的爱、对敌人的爱)变成【邻人之爱】这个单一义务,这是因为上帝首先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得救,而是【缔造一个新的上帝民族】;而在保罗那里,邻人之爱和上帝之爱合而为一,媒介就是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第二部分 《罗马书》的影响】
【这个世界的陌生人:马克安及其后果】
希望的前提是分离,“当人们能够面对面地看见对方时,就不需要希望”(p92);信仰意味着“我走进了黑暗之中”(p92);爱意味着“我不是以自己为中心”(p92),我有需要,他者是必需的,爱是对我的需要的承认。陶伯斯认为,保罗与灵知派的不同在于,对保罗而言我们需要【共同置身在基督的肉身】之中,而灵知派认为【每个人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完满的】。
马克安的上帝是陌生的上帝,人们【同上帝的爱相分离】,而使得产生这种分离的造物主必然拥有恶魔的特征——他很强大,但与【拯救】无关;马克安使耶稣拯救之爱的福音同《旧约》处于一种无法化解的对立,因为《旧约》所记载的恰恰是上帝的忿怒及其后果;教会制造了一种旧约与新约的和谐,而马克安恰恰在这一点上反对教会。
马克安与保罗:
马克安在什么地方抓住了保罗的一种意图?这在于“保罗所假定的上帝之爱离得非常非常遥远。由于许多来源于地上、天上或掌权者的力量,这种上帝的爱、耶稣基督之父的爱遭到中断”(p95);而路德在一定程度上攫取了马克安的保罗;马克安创立了一个禁欲的教会,这使得所有成员需要不断地招募,这种思想的根本在于“通过抽掉世界的种子,迫使世界因饥饿而就范”(p97);而在犹太人那里没有婚姻是不完整的(灵知派是反犹的);由于自诩大地上的陌生人,理由是“与一个另类的最高权威发生关联”(p99),这就隐含着一种【颠覆的潜能】。后来,德国自由派神学、自然神论也都攻击《旧约》,这些论证总是“让正义与爱相互对峙”(p101)。
【绝对者和决断的奋锐党人:施米特与巴特】
一战使得德国自由派神学的文化新教的综合土崩瓦解;巴特批判自由派神学;施米特试图克服相对主义,批判实证法学的中立性,批判世俗化,以例外(奇迹)的卡里斯玛式的【正当性】来反对议会制的常规【合法性】,对施米特来说,现时代的正当性背后隐藏着主体的一种武断的自我授权(以此来反对布鲁门伯格),施米特对现代性中的世俗化持批判态度,他坚持神学与政治的实质统一。
【作为世界政治的虚无主义以及审美的弥赛亚主义:本雅明与阿多诺】
本雅明:
《罗马书》第8章与本雅明的《神学政治残篇》(《历史哲学论纲》相似;本雅明在两方面是一个保罗分子:一是他有一种保罗意义的受造概念,“本雅明看到了受造物的痛苦,受造物的徒劳”(p120),要在毁灭中自我实现,追求消逝是世界政治的任务,这种方法是【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同罗马帝国毁灭的原因如出一辙(保罗的策略);二是本雅明否定凡俗秩序的宗教意义,在统治与拯救之间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阿多诺:
阿多诺的弥赛亚是否实现是无关紧要的,它是一位审美主义者,音乐发挥了一种救赎的作用,陶伯斯认为这太天真了。
【出圣经宗教记:尼采与弗洛伊德】
超验与内在:
对本雅明、施米特、巴特而言,超验是不可或缺的,这在世俗世界的危机中得到了见证;而在斯宾诺莎、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而坚持现实的终极【内在性】。
在斯宾诺莎那里,预定说的含义是摇摆不定的,既可以用【神的视角】,也可以用【自然的视角】,后者是一种【必然性】,斯宾诺莎实际上认为【神即自然】。
尼采作为反保罗的角色出现,但能够辨析出内在联系。在希腊哲学那里,真理属于【少数人】;在基督教的视野中,通过“穿过基督”,真理适合【一切人】,基督是为所有人而死,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保罗的乌托邦式“所有人都在基督之中成为一体”(p135),与之相反,尼采的乌托邦式“为了认识,人需要闲暇。闲暇意味着,另一些人完成劳动”(p136),尼采提出了“生成的无辜”,在一个内在的宇宙之中,占据统治的是生命的【等级秩序】和价值。尼采与弗洛伊德都把罪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建构】,对尼采来说,罪来源于以某种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名义对肉身实在的压迫;对弗洛伊德来说,罪产生于那种奠定社会秩序的暴力行为的压迫。他认为罪是那种【俄狄浦斯情结】,“孩子已经妒忌父亲,并且想杀死父亲,因为他想得到母亲”(p146);与弗洛伊德类似,保罗所关心的也是从某种罪责关联中获得【拯救】,“关心罪这一基本经验的弗洛伊德是保罗的一个直接继承者”(p148);弗洛伊德对摩西的关注是一个颠覆性的方案:废止律法,不仅仅是摩西的律法,还是【资产阶级的律法】,给人类带来全部神经恐惧症的资产阶级习俗。弗洛伊德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儿子的宗教】,它必须【罢黜父亲】,那位古老的父亲上帝屈居第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