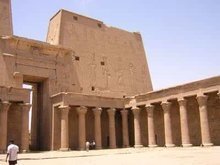《桑戈马尔守夜者》读后感锦集
《桑戈马尔守夜者》是一本由[法]法图·迪奥梅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5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桑戈马尔守夜者》读后感(一):是在达喀尔和桑戈马尔交流,是在丰州和阎王交流
这真的是来自异域的文字,言语中流淌着来自非洲大陆独特的文化气息。
译文不知是否是出自原文一样,语句如诗一般流淌,在整部开篇就能清澈地感受到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和心意。这数不尽的问句,是出自库姆巴呢,还是出自法图自己呢?
我可能是第一次阅读这种非洲口语文学的作品,非常奇特,非常独特的感受。这叙述就如同我就在库姆巴身边,一点一滴的看着她的日常生活。
在库姆巴这个人生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能如同在她身边一样,贴心地感受到她的情绪,她是独立的、自主的、坚定的有自己的想法和信念的人,她坚持的相信对于桑戈马尔的信仰能帮助她和她的爱人相遇,无论在哪里。
于是她开始写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要给她们的孩子留下一个完整的父亲的记忆,不要让她们的孩子对于父亲的印象是空白,只能去揣测,去想象,去描绘一个父亲的概念;又或者说,她把这些文字留给自己,在文字中书写她们共同的同年,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婚姻和她们的爱情,去记录她自己的情绪,她的心情,她的感受。也许她在以后的某一天再翻开这些文字,她就能够清晰完整的看到自己的这一段人生,对爱情的触动,生活的烦恼,和朋友的感情。
所以她在白天度日如年,无论岳母还是母亲那些不理解她的牵挂,对她的照顾,还是亲朋好友不知何意的安抚絮叨,又或是对于照顾孩子的烦扰。她都抱着同样的一种心态去期盼夜晚,去期盼在夜晚的文字中,在桑戈马尔的帮助下和爱人的相遇。
啊,这些不断的感叹词和升降调的语句,加重了你和库姆巴的感情同化。你更亲切地感受到她的心事,感受到她的坚定。她忍受着频繁地拜访,她得不到她需要的平静去哀悼她的爱人。
那些朋友的故事又清晰地向读者,向我们展现了那非洲西部的风光,让达喀尔,让塞内加尔更加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脑海,就像身边的一座小镇,而不是千百公里外陌生的名称。
时代,时代的束缚在这个女性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即使经受过教育,也不能完全冲破那片束缚,但是她在努力做,努力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
她成功了,她开始和她的爱人对话,她积极勇敢的做一个新的自己,她冲破了村庄的束缚,或许就像作者一样,走向了那些人认可的都市,作为独立的自己开始了属于自己和孩子的新生活,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只是自己。
合上书本,一瞬间你感觉这个故事并不遥远,也许就在不远的乡村间,城市里,同样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只是我们有没有把它记述下来呢?我们会不会这样不断地口述,不断地反问呢?
《桑戈马尔守夜者》读后感(二):梵高没有疯,是上帝总变卦
曾经有过一次溺水的经历。
喉咙被水塞满,无法呼吸,胸腔很痛,引起强烈的咳嗽,嘴里往外吐水,依旧无法呼吸。
那种恐惧感是极其强烈的,内心撕裂出两种声音:
“我不会就此死去吧?”
“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去?”
依旧是窒息,只好用力的去咳嗽,将喉咙中的水咳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呼吸,一次又一次的咳水,在消极与积极的各种念头中,求生本能战胜一切,最终在某一次咳水的过程中,一丝空气悄然钻入体内。
重新活过来的感觉,竟然如此之妙。
在阅读《桑戈马尔守夜者》时,我在作者法图·迪奥梅的文字中,感受到了这样的窒息感。
2002年9月26日,位于非洲的一个小国家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特大海难。
原本可以载550名乘客,其中包括52名船员,但出事当天却有1034名乘客拥上客轮,其中多数是到首都做小生意的商人,他们都在为自己能挤上这条船感到非常高兴。
于是,这艘客轮在大西洋海域沉没,除少数乘客获救外,大多数乘客船员遇难,从而再演“泰坦尼克”号的沉船悲剧。
库姆巴的丈夫布巴,就在这场船难中失去了生命。
成为寡妇的库姆巴,无处排解自己的烦忧。
白天,面对人们的安慰与关心,库姆巴沉默不语。夜晚,感受到了逝者的呼唤与桑戈马尔的低语,库姆巴开始与之对话。
库姆巴整夜都在倾听桑戈马尔守夜者的话语,努力的梳理着,但是告诉身边的人,无人相信。
没有人在夜晚听到过什么桑戈马尔守夜者的低语,只有库姆巴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罢了。
库姆巴成了别人口中的疯子。
码头上,水手们的妻子为了缓解焦虑,总是会谈论起库姆巴,流言四起。
而面对库姆巴,人们又十分友好的与之打招呼,关心她是否过的好不好。
多么的讽刺,面对刚刚失去丈夫的自己,自己的生活怎么可以用“好不好”来形容?
这些问候,在库姆巴看来,那些虚伪的客套,不理也罢。
然而库姆巴的缄默不语,却遭到了更多的非议。
即使是自己的婆婆,刚刚痛失儿子的婆婆,也无法理解库姆巴的悲伤与固执;而母亲的关怀,在库姆巴看来,也毫无必要。
“戏我哭笑无主还戏我心如枯木,
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清醒,
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无慈悲,
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
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
库姆巴作为“寡妇”,被旁人加上了太多的标签,却没有人问过库姆巴是否愿意如此。
而库姆巴的情绪,也如同《易燃易爆炸》一般,愤怒、无奈、撕裂。
越是去反驳那些说自己是疯子的话语,越会被当成疯子。
库姆巴不在理会那些愚蠢的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不再告诉别人自己夜晚听到的话,她决定拿一个本子,将这些记录下来。
记事本不会怀疑她在夜里的那些秘密,也不会将她说的话当成笑料去传播。
库姆巴生活在岛上,她知道晕船的痛苦只能独自承受;她也发现守丧之苦同样无人分担。
“让他们说去吧,我只管继续写下去!她这么鼓励着自己。最后,她不再渴望被理解,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追求之中。”
通过写作,库姆巴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她不再是别他人所定义的“寡妇”,她是充满愤怒,向往自由的库姆巴。
通过写作,库姆巴找到了保护脆弱心灵的方法。
她不再因为他人的话语而受伤,她是敢于反击,敢于拒绝的库姆巴。
通过写作,库姆巴找到了保持自我的方式。
面对众人的蒙昧与无知,库姆巴不想与之同流合污,她要保持着独有的清醒。
写作,库姆巴捍卫住了自己的那一口空气。
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他人的不理解,面对这个世界对“寡妇”的束缚,库姆巴就像快要溺死的人一般。
而写作,是那维持她活下去的一口空气。
没有人能够让她说出自己的痛苦,同时,库姆巴也不想引起他人的不安与批判,她只能等待夜晚降临,等待桑格马尔守夜者,等待打开记事本畅游自己思想的时刻。
库姆巴在流言蜚语中快要溺死过去,写作给了她一口活下去的空气。
但失去了丈夫的爱与关怀,让她又十分的渴,她像是在大地上迷失方向的鱼,渴望着水,库姆巴渴望着爱。
库姆在夜里祈求桑戈马尔守夜者,她通灵唤来了丈夫布巴的灵魂,诉说着自己的烦恼与无奈。
布巴安慰着她,支持着她,守护着她,爱护着她。
却被婆婆误会库姆巴在夜里用手机与旁人勾搭。
这一切都那么的滑稽与可笑。
可,生活还需要继续。
为了帮助库姆巴迎来新生活,库姆巴的婆婆希望库姆巴可以嫁给自己丈夫的哥哥,而库姆巴的母亲希望库姆巴可以嫁给自己的侄子。
非洲,拥有辽阔的草原和隐秘的丛林,因此也诞生了许多原始部落,这些部落都拥有一些风俗习惯,在十分注重家族的部落,他们有一个习惯法,就是每一个家庭的血缘链条都必须世代相传,不可中断,只有这样,一个家族的财产才不会外流。
因此,如果一个男性没有后代去世,则由他的弟弟娶寡嫂为妻,所生的子女归入死去哥哥名下,并集成各个的财产。
而这样,库姆巴也有了新的归宿。
在旁人看来多么理所应当又幸福的选择,在刚刚自我觉醒的库姆巴看来,是多么的愚蠢。
她不想再被这些传统所禁锢,她讨厌她那个封建的婆婆,更讨厌这个顽固不化且残缺的家。
在夜里,有布巴的鼓励,在白日,库姆巴才有勇气拒绝。
是的,生活还要继续,但库姆巴选择依靠自己,而非依靠传统习俗中的男性力量。
真的存在桑戈马尔守夜者的低语吗?
那是库姆巴对自己的低喃,以此来重新铸造原本破碎的心与信仰。
库姆巴真的疯了吗?
她只是在用旁人不理解的方式去自愈。
库姆巴真的见到了布巴了吗?
也许那只是另一个“库姆巴”在鼓励着自己前进。
会有人能看懂库姆巴的文字吗?
库姆巴并不在意。
周遭环境如此混乱、愚昧且无知,生活还如何前进?
当柔软的内心充满坚毅,一切问题都不再会是问题。
那梵高疯了吗?
梵高没有疯,是老天爷总爱变化,让他感到头晕目眩,手中调色盘的颜色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桑戈马尔守夜者》读后感(三):暴风雨摧毁了她的一切,而她把风暴关进了本子里 | 新书试读
非洲文学、女性写作、改编自于现实事件、打破生死界限的魔幻奇旅,叠加了这些鲜明要素的《桑戈马尔守夜者》,仅仅是精美的封面就已经吸引了不少读者。
这本由新锐非洲裔法语作家——法图·迪奥梅写作的小说,以真实事件2002年“乔拉号”沉船事故为背景,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遭遇丧夫之痛,深受传统束缚的女性,是如何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的。
主人公库姆巴是一位生活在塞内加尔尼奥焦尔岛的年轻女人,她深爱的丈夫布巴,以及他们的好朋友都在这场船难中丧生。沉浸在悲痛中的库姆巴,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召唤逝者。于是每到夜晚降临,她就用书写的方式抵抗遗忘和悲恸,思考自己与非洲的未来……
深思熟虑之后,她决定不再把自己夜里听到的声音告诉别人,也不再浪费时间去说服瓦西亚姆或是其他任何人。被那些聋子猜测自己是否耳鸣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不,在剩下的三个月零十天的服丧期里,库姆巴不会再把自己夜里听到的内容对外说出一个字。
她想,无论怎样,总有比别人的耳朵更好的同伴:一个记事本!因此,当睡意引她来到黑暗的剧场时,她便在防风灯殷切地注视下开始写作。
“再没有比自己的心灵更宁静,更无忧无虑的隐居处了……所以要常常给自己这样一个隐蔽的巢穴,让自己重获新生。”库姆巴也许并不知道这条来自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位皇帝,斯多葛派著名哲学家,著有《沉思录》)的忠告,尽管如此,她的直觉引领她走向了智者们所说的心灵庇护所。一旦下定决心,库姆巴便觉得她成为了自己这艘船的船长。
Les Veilleurs de Sangomar
目前无人评价
Fatou Diome / 2019
从达喀尔回来之后,她第一次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度过这些意外,而不是仅仅去承受。纵使船舶多么颠簸摇晃,只要舵盘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便没那么可怕了。库姆巴独自一人迎击黑夜,在夜里书写着。
她独自一人乘着晚风,在夜里划船。连她的妈妈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她又还有什么选择?至少,一个记事本不会怀疑她在夜里的那些秘密。库姆巴生活在岛上,她知道晕船的痛苦只能独自承受;她也发现守丧之苦同样无人分担。
死亡不仅让逝者远离我们,也同样让那些我们曾以为亲近的人渐行渐远。苦难不仅让脸颊日益凹陷,也让身边人变得越来越少。库姆巴把这些也写在了本子上。她把她的记事本看作是海滩上的贝壳——她像个孩子一样,把自己的不幸都说给它听,想要摆脱这些苦难——暴风雨摧毁了她的一切,而她把风暴关进了本子里。
她把那拼命想要抑制住的呐喊都发泄在纸上,这样才不会吓到在她身侧熟睡的小法迪吉娜。库姆巴吞下了多少分贝才能把这隐忍的呐喊转化为无声的叹息?从此以后,她把这些呐喊变为旋律写在纸上,这也让她的胃能够腾出些地方用来吃饭。
从此以后,当夜晚带来危险时,库姆巴便用笔将黑夜攫取,再把它粘在地毯上,直到清晨来临。就像布须曼人(又称“桑人”,是生活于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一个原住民族)装备着长矛与水壶勇闯卡拉哈里沙漠(属非洲南部内陆干燥区,处于卡拉哈里盆地中央)那样,库姆巴也用本子和笔来面对她的服丧期。她希望能像这样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稳住阵脚。
另外,她笔下还有宁静的河湾能让海上遇难者在鹈鹕的注视下停靠岸边、找回呼吸,鹈鹕教会他们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羽毛,哪怕是在暴风雨中。库姆巴有充分的理由用自己的方法获得安慰。
法图·迪奥梅
她充满斗志,悄悄确定了航向。库姆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划动船桨,也许她是在逆流而上,不过这不再会打扰别人的睡眠。诚然,她想,人们害怕孤独,所以认为群居生活大有裨益,然而,当有些事情触及到了灵魂,那第三方的意见往往不会带来多大帮助;本以为别人的意见会缓解自己忍受的折磨,却往往带来更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就算在极少数情况下语言能带来安慰,但笨拙的话语却常常只会给人迎头痛击。因此,真正的勇气在于保持沉默。为了能够表达自己不再打扰别人,也不再让自己感到内疚,库姆巴只好待在密闭的房间里,求助于手中的笔。
在她的思绪里,写作给她陪伴,给她方向,同时也让她能够免于婆婆的喋喋不休。一个本子,一支笔,若是有人能拥有这样的乐器并在心中引起共鸣,那他的朋友一定不会少!库姆巴这样鼓舞着自己。
无论是佛利亚舞曲还是萨拉班德舞,她的笔尖随着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连那些烦心事也跳起了华尔兹,并且作为一个称职的舞伴,无论探戈舞曲多长,它都不会不小心踩在你的脚上。
至于那些纸页,它们总是始终如一又如此开放,它们永远不会抛弃你,不会对任何谈论感到厌倦,不会因为你的颤音去评判你,不会将你丢弃到溪谷深处,不会颐指气使地强加给你任何真理,而是会将你的感冒治愈,却不会猜测你的精神状况,让你感到被冒犯。
写作,库姆巴小声说,这是在把上帝对你做的事展示给他看,让他为自己创造出的可怜生物负责。永恒的沉思以及每日因良心审判而做出的忏悔,这一切已经让作家足够虔诚,若是艺术施加的苦行仍无法将他带往天堂,那便再也没有人能够抵达那里了。
库姆巴会继续写作,这将是她去往布巴所在王国的方式。流言蜚语说她发了疯,她却毫不在乎。闪电常常被人咒骂,但它让爱说闲话的人忙于各自的事情,库姆巴也是如此。她的闪电便是写作,让她远离那些窃窃私语,那些认为她偏离了航向的船只残骸。这些陷入淤泥的残骸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想法,它们永远不会想到也不能轻易地握住一支笔杆。
让他们说去吧,我只管继续写下去!她这么鼓励着自己。最后,她不再渴望被理解,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追求之中。服丧期间,库姆巴的记事本就是她的倾听者,是她的救生筏。
不过没有了布巴,她还剩下什么珍贵的东西值得挽留?也许,可以给她的女儿留下一些回忆。法迪吉娜肯定有一天会问她:“妈妈,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以前很帅啊,爸爸照这张照片的时候多大呀?妈妈,爸爸是做什么的?我的爸爸他是哪种人啊?告诉我吧,妈妈……”
为了以后能够应对女儿提出的这些问题,库姆巴想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把关于她与布巴之间的一切都写下来:在那些满怀希望的季节,无数小细节让每天的日子有了幸福的味道,尤其是,她爱人脸上绽放出的笑容。
老照片上,布巴迷人的微笑渐渐泛黄,却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是他们的爱情在微笑,永生永世无法磨灭。丘比特永生不死,普赛克(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赛克原本是人间公主,美貌非凡, 后爱上丘比特。历经磨难后,他们的爱感动宙斯,后者赐其永生,与丘比特过上幸福的生活)哪怕再悲伤也不会死去,库姆巴亦是如此。
在萨卢姆,尽管哈马丹风(也称“魔风”,源于撒哈拉沙漠中心,每年冬季几内亚湾沿岸都会遭遇哈马丹的侵蚀,它会携带撒哈拉沙漠的红色细沙,导致能见度降低,引发干旱)趁机大作,肆意的野火与悄悄溜入沙丘脚下的盐粒同狂风合谋,但生命总是会像猴面包树一样春风吹又生。若是有人对此抱有怀疑,那他只需去问一问尼奥焦尔岛上的红树林,尽管在每次收获牡蛎时,红树都会被截断根部,但是它却把苦涩的汁液排出,然后在交错的海湾之中耐心地等待重生。
人类也是如此,尼奥敏卡人身为贵族后代,从不会屈膝下跪,也不懂得什么是放弃。几百年来,大西洋咆哮着、翻滚着、侵袭着,但姆贝冈·恩杜尔(萨卢姆王国第一任国王,萨卢姆王国也是因他而得名)统治下的萨卢姆王国总是越发繁荣,萌发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