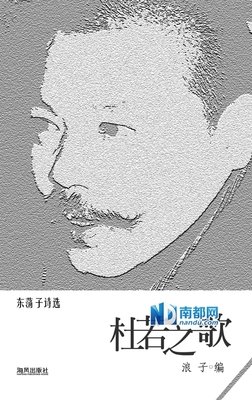如呼吸一般去爱的诗人、编辑和作家 | 王渝专辑:小品文、诗歌和人
“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这正是诗人和作家王渝的人生写照。她如呼吸一般去爱,写下一首首蕴藉优雅的诗,和一篇篇清风明月般的文章。
王渝小品文四篇
忆儿时祭灶
腊月二十四日祭灶王爷。我从放寒假就开始盼望这一天。早上起来先往厨房跑,一再叮嘱我早饭要吃乌龟蛋加芝麻汤圆。然后巡视有甚么可以顺手捏了抓了往嘴里放。所谓乌龟蛋就是糯米粉搓成的小圆子,只比米粒大一点。照顾我的戴妈总是随后跟来,押了我去洗脸刷牙梳头。
家里祭灶的事都是戴妈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前一天我已经听见她分派厨房要多做糯米的甜食,也叫车夫小陈买糖果时多买些牛皮糖麦芽糖。戴妈已经告诉过我许多次,灶王爷跟我一样爱吃糖。所以我觉得他可爱。至于为他准备的糯米甜食牛皮糖麦芽糖却是为了黏他的牙齿,让他张不开口说坏话。戴妈加重语气对我说:“你不听话,做的坏事,他都会报告玉皇大帝。”原来灶王爷也挺可怕啊。
灶王爷画像贴好,供桌摆好甜食糖果,开始祭灶王爷。我鞠躬时心里默念:“灶王爷请你多吃麦芽糖,不要说我坏话。”戴妈跪拜口里咕噜说个不停,我竖起耳朵听。她好像在跟灶王爷讨价还价地说:“糯米糕里面放了桂花,吃到嘴里又香又甜,你千万记住多挑好的话讲啊。小孩子不懂事,做了什么,你就当做没看见吧。请多吃麦芽糖啊……”
那年头我还没接触过希腊神话,不知道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向来是又爱又怕又糊弄他。
写于2016年12月20日
遥想叶老师
叶老师是叶嘉莹老师。我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一本去年的《印刻》杂志,封面是叶老师,有她的专辑。读了后兴犹未足,回到家便上网先看为她做的访问,还有她讲解诗词的录影。
九十多岁的叶老师依然光彩照人,言说敏慧,随口背出诗句。讲诗词时她依旧保持高中教我们国文时爱跑野马的习惯。讲某一位诗人的作品,她会引用许多其他诗人作品来比较说明。
她教我们国文跑野马之外,时时会讲些有趣的故事。所以上国文课我总是全神贯注,唯恐有所漏失。有次她讲对联讲到水部失火,烧毁了部分房舍,后来就让一位姓金的尚书来主持修建事务。有人为此写出上联“水部火攻金尚书大兴土木”,征求下联。实在不好对。上联里包括了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啊。直到有天那里工作的中书官跟人发生口角,这位中书官说不准官话,有很重的乡音。于是有人叫道有了下联,那是“南腔北调中书官甚么东西”。
她兴趣广,电影爱看,现代文学也喜欢,还为周梦蝶的诗集《还魂草》写序。她说因为教书人家说她爱为人师,其实她更爱为人学生。她在国外就曾去听过西方文学理论的课。
最过瘾的是,我在网上找到叶老师讲《小词中的儒家思想》,一共有七讲。听叶老师,看叶老师,想叶老师。她真是老的太漂亮。
写于2016年9月17日
恶梦,近来的恶梦
今天早上又做了这同样的恶梦。梦里是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单,我记不得借了甚么书,而书目那一栏怎么也看不清。到底是甚么书呢?开始焦虑,同时觉得这是一张催我还书的单子。这样的梦最近我做了好几次,每次惊醒后,半天还弄不清幻焉梦焉真焉?此时我虽然身在梦里,却知道是在做梦,下定决心要醒过来。好不容易真的醒了,我赶快找出借的书,全部都在,这才放下了心。
以前我借书的图书馆,我都经常被罚款,不是过期,就是丟失。我们住在郊区时,有次我接到图书馆的电话,问我是否借了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我反问他有记录没有,他说没有,只是问问。令我十分生气,居然无辜成了嫌疑犯。可是那段被罚款的日子里,我从来没做过关于借书的恶梦。
我在曼哈顿中城上班的时候,常到中城图书馆借书。不断地被罚了几次款后,我改变做法,改借为买。我通常借的都是侦探小说,丟书的罚款虽然不贵,也要十来块钱。这家图书馆天天都把要出清的书放在一角,五毛钱一本卖出去。其中侦探小说甚多,我便常常买两三本,心安理得,再也不用担心罚款了。
搬来皇后区后,法拉盛图书馆成了我的最爱。中文藏书多,特別是日本推理小说多。我至今借书没出过错,结果却落得做起忘记还书的恶梦。
写于2017年1月4日
我爱胡思
这里所说的胡思,不是指胡思乱想的胡思,而是指一家叫“胡思”的二手书店。
去年(2017)十一月,我们在台北的短租公寓,设备完善舒服。但是,所在的位置却有点麻烦,位于纵横交错,七扭八拐的巷子里。我每次出门,立即头昏。买了一杯咖啡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过有天迷路时发现一家二手书店,叫“胡思”。爱乱想的我一见钟情,把迷路的焦虑忘得一干二净,就径自走了进去。书店宽敞明亮洁净,一排排书井然有序。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士,微笑着亲切招呼我。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他,不是那位亲切男士,是书店。徘徊书架间,我选了三本:两本莫迪里亚尼(Modigliani)和一本新井一二三。新井这本《我和阅读谈恋爱》,读得我恨不得参合进去三角恋。她谈的全是日本作家,有我熟悉喜爱的,有我不知好奇的。我在靠窗的咖啡座那里要了咖啡,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三本书台币两百元,合美金才六块多。离开下楼时,我想以后会常来。
果然,后来每次回住处之前,我忍不住要进去逗留一阵,选一堆书抱到咖啡座,边喝咖啡边翻阅。字里行间,有时恍如闯进一片新天地,有时却像碰到老朋友。总之,都是欢喜。有天出来时我手里拿了四本书,两本是没读过的推理小说,一本赤川次郎,一本夏树静子。前者幽默,后者构思细腻。另外两本则是读过的《麦田投手》和《开放的人生》。前者版本可爱,很小,手掌般大,最适合随身携带。后者则是王鼎钧先生的畅销书兼常销书,我读过,而且读过了几次。我所以买它是因为这本书每一篇的后面,都记下了读书心得,工整的蓝色钢笔字,似乎出自中学生手笔。心得后面,有些出现红色的改正,有些则是批评。如此一来,这本书中收藏了三个人的心思--作者的,学生的和老师的。我越读越感到有意思。比如《康老子》这篇,作者王鼎钧在题目下的引言是:最恶劣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再犯。心得写的是:最糟的错是一错再错。红笔在心得旁边画了几个圈表示赞赏。另一篇的心得,红笔批语是:字太草。还有一篇针对心得的三句批语是:这三种都没有相关性。最后一页上红笔写道:文章中的你较缺乏己见,只能因循作者原意加以引申,而无法外放发挥,是为本文小庛。批语下方老师签了名,还盖了印章。非常的亲切可爱。看来,这是一位有心的老师为学生设计的作业。这本书我特地带回纽约来送了给鼎公,算是另类礼物吧。
回纽约前一天,我在那里碰到了诗人林焕章。他正在忙着整理东西。他告诉我是在取回挂在墙上展览的画。原来这里不但提供字画展览,而且举办文艺座谈。我们既然遇上,他也不整理画作了。他请我喝咖啡,挑了座位,我们聊天了。跟许多诗人一样,像张默、管管、北岛,他现在也爱上画画。应我要求,他跟柜台要了两个纸盘子,就在盘子上画了起来。两张都画的鸡。其中一张是一只大公鸡带了一群小鸡。我说太喜欢这张了。他不画母鸡带小鸡,而画公鸡带小鸡,除了饶有童趣,多半还着意显示男女平等的观念吧。他一直关注儿童写诗,他编辑的那本《儿童诗选集》我时常翻阅,那些可爱的童心带给我不尽的喜悅。例如林于立的《照镜子》:你是我/我也是你/你被关在冰块里/跳不出来/我挤在大自然里/跳不出去/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我这么想着时,他叫我看窗外。他说最喜欢接近黄昏的时候,坐在这个位子看外面。真的,我们正对台湾大学的大门,和沿着它的新生南路,树木,校舍,行人和车辆形成非常欢乐的景观。他告诉我他常常下午来坐在这里喝咖啡看书看窗外。我想的是:明年回台北,我也要常常下午来这里,除了喝咖啡看书,还会碰见他啊。
写于2018年1月
王渝诗歌两首
夜很静
夜很静
静到白昼的失语症都消失
静到听见心深处流出的所想所思
静到自己能和自己对话
絮语
细雨纷纷
撩醒沉睡的窗幔
浸润期待的盆栽
至于桌椅沙发已开始悄悄回应
夜很静
静到我得以从容地走访了一圈
別人的梦境
咖啡馆中
我认识他时
还不曾认识你
他认识你时
你们都不认识我
绕过诗句砌成的小径
我们聚会在
异国的咖啡馆
头顶的天窗
扔进来破旧脏乱的
贫穷风景
我们怡然将这一方小天地
坐谈成我们的波西米亚
虽然那个来自东欧的女侍
僵硬的待客之道一如她僵硬的英语
王渝访谈刘大任:岩上无心云相逐
刘大任的小说近三年来在国内出版,引起相当的重视。2016年底,刘大任的作品才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小说《当下四重奏》一经问世即引发追捧。在众多读者的期待下,刘大任的三部小说集《羊齿》《晚风细雨》《枯山水》新书发布会次年即在天津跨界书店举办。推动成就此壮举的伯乐是胡洪侠先生。胡先生认为,刘大任在文学品质、语言、故事结构能力和价值观表达上,都达到了巅峰极致,当代少有作家能企及。胡洪侠表示,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会在四五年之内将继续引进刘大任的小说、随笔、文论等二十余种。
这么一位杰出作家,海外对他却不熟悉。2013年他的《枯山水》在台湾出版时,我跟他做了一个访谈,正可以帮助对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亲近他认识他。所以,特别烦请唐简帮我编辑整理转发。
──王渝
岩上无心云相逐
——刘大任谈写作的未来、现在与过去
王渝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刘大任新泽西郊区家中的客厅,边喝茶边聊天。话题围绕着他的创作。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新作《枯山水》写作时的状态和他现在对文学的看法。我们谈得十分投入,桌上的水果和糕点都被冷落。落地窗外的草坪和树木在微雨中绿得晶莹。
你的新作《枯山水》,去年(2012)底出版,距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期间你是不是开始在酝酿新一阶段的创作?我知道你对国共内战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对于瞿秋白、张国焘等等几位人物尤其兴趣浓厚。是不是在这个短篇集子后,准备写个长篇呢?我很好奇,想听你谈谈未来的写作计划。我们从未来开始,然后再回到现在好吗?
如今我对长江大河小说有所质疑,觉得不太有希望,要突破十九世纪那些作品的成就不太可能了。另外一点,像在美国,或者日本,现在写这类小说,都是为拍电影提供素材。所以,作者的构思基本是围绕着拍成电影时产生的效果。
从前那些大河小说影响一代知识份子,又由他们推动社会,发生启蒙作用。第一,这样的作用,我现在看不到了。第二,自己正在探索美学的观点:到底什么值得写,如何写。像我三十多岁时写的《浮游群落》,现在看起来觉得很粗陋。当时有个藉口,要把自己看到的经历过的传承给下一代,亦即台湾的大学生。心目中对象既是大学生,写的也跟大学生活相关。
回头看,四十岁以后写的一些比较短小精炼的袖珍小说,两三千字,多则四五千字。洪范出了一本,《秋阳似酒》。现在看,觉得那个才是我要走的方向。特别是这种体裁,表达的内容可大可小,小的可浓缩到一千两百到一千七八百字,像《四合如意》。
既然你提到美学的观点,我们就顺着这条思路谈下去。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对于作家来说,持怎样的美学观点和他的创作关系太密切了。
在美学方面,我有几点要求。第一,文字力求简练,从简练中表现力度,而不是采用重复堆砌长句子的形式去追求多样性和复杂性,让人看得头昏脑涨。这大约是我年纪大了后,读史记和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代文学从胡适的语体文开始慢慢向前推进,特别是后来台湾的现代诗,让我体会到文学的文字和口头的语言很不一样。像胡适的语体诗,现在看就觉得离文学很远。但是,从胡适提倡白话文,书写也是一直在进步,到了朱自清更上一层楼,到了鲁迅则起了极大变化。鲁迅写作揉和古今,文字的文学性大大超前。后来吴祖缃便是延续他这条路,非常精炼,脱离口语。加上后来七页诗派对诗语言的改革,再往后则是台湾现代诗对现代中文的改造。文字的文学性越发突显。我如今写小说,很注重这方面。
第二个面临的问题便是内容的表达,小说多半是讲故事,问题是怎么讲。终极追求应该是诗意。你可以仿效传统章回小说,也可以学西方马奎斯的魔幻,或者其他大师的手法。海峡两岸都热衷模仿学习西方大家。但是,我不想走这条路,还是希望从传统中吸收养料,然后慢慢融会贯通建立自己的风格。我们绘画、写文章、写诗都强调留有余不尽,强调留白。留白是中国传统美学观点的关键所在。我很注重这个观点,希望在留白的地方,让读者不止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使他们能在阅读过程中扩大想象。
第三则是为什么写作。基本上我所有的写作,无论是散文、评论或者小说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怎么活?活的过程中观察到些什么?通过反省分析,得到了什么感悟?亦即从自己生活的核心出发,放射式地扩及到许多相关方面。所以,我的写作实际上跟我的生活是表里一致的关系。而生活本身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传承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传统读书人所关心的历史、人类前途、国家前途,以及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
你提到文学中的诗意,能不能具体谈谈?
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创作之所以吸引我,与其说是传道解惑,不如说更在于那种起自凡庸平常而又有所超越飞升的非世间的奇谲之美!其实,用这句话很难诠释什么是诗意。我想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秀陶几十年后返乡,夜色朦胧中从火车窗子看出去,看到一个农家大院坐了许多人,吃喝聊天很欢乐。他们不会想到,远方归来的异乡人在对他们的一瞥中,激发出怎样的感想。这个瞬间的感受,平铺直叙可能写不出味道,但是他写成散文诗,处理得好,带出无尽的意味,这就是诗意。
说到这里我要做点补充。文学的美学观点,除了注重留白和诗意,还需要做到大气和正派。年轻时也曾喜欢标新立异,后来读多了想多了,逐渐增加了鉴赏力之后,发现能够留下来的经典作品都大气而正派。我算是幸运,比较早有了这样的领悟,也比较早就摒弃了标新立异的心思和做法,严格要求自己把锋芒收敛,不要显露。
我喜爱日本小说,像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比较遗憾的是,一般说来,他们的作品喜欢走偏锋。可是,话说回来,谷崎润一郎的名作《细雪》,很是大气。
讲到生活的内容,你的经历比较特别。就拿居住地方来说,你们住过亚洲、美洲和非洲。你兴趣也非常广,而且不是点到为止,都是深深地沉浸其中。不只是参与文学活动、社会活动,打球、种花、养鱼也都是如此。就拿你书房这缸彩虹鱼来说,刚刚我吓它们一跳,它们也吓了我一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胆小的鱼,我才靠近鱼缸,它们就忽地全躲起了。你刚才便详细地跟我介绍了他们的特性。还有,你喜欢打高尔夫,便写了关于高尔夫球的书。这恐怕也是创举吧?
确实,我写作都源自生活,包括养花植树的兴趣、打球运动的参与和感受,还有阅读的思考,全都息息相关。不问这些是否有价值,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真实。因此,我的写作便是生活里面自然的感受。我不会像某些作家,决定了写作题材后便去搜寻资料,甚至如果写精神病院,便去那里体验生活,然后从收集的资料,观察到的现象出发去写作。我这样说,有人或许会认为从生活出发,我的写作范围会受到限制,会狭窄。其实不然,如果生活接触广泛而且不停发展,体会细致,思考角度独特,又能往深处挖掘,那么写作范围绝对狭窄不了。
三年前回台湾,《印刻》杂志办了个座谈,老朋友尉天骢和我对谈。他问我,从生活累积的种种经验,难道不能写出像《齐瓦哥医生》那样的作品。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稍作思索后说的是,大约不会去写像《齐瓦哥医生》那样的小说,而是会写《枯山水》之类的作品。当时我正在酝酿《枯山水》的写作,后来果然一篇篇写了出来,出了书。我想当时,我的反应恐怕很让天骢失望。我想,如果讲台湾的小说,陈映真在他心里还是占第一位。但映真也没有大河小说,天骢也许觉得遗憾。
《枯山水》中的作品,有些在发表之前我就有幸先睹。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拿你们院子里的花木来打比喻,好像看着它们抽芽,长出枝干,增添绿叶,开出美丽的花朵。阅读时我感觉到,你那些散文集子,或者散文似的小说,像《晚风习习》《细雨霏霏》都似乎是你这一系列短篇的铺垫。这两篇散文写法的小说,既是从你自己的生活引发,却也如王德威所言带有国族寓言的色彩。你的笔触深远,表层叙述的下面蕴藏多层次厚实的内涵。《枯山水》令人想到“禅”,在日本便是指的禅意的花园。你创作时是否受到禅宗的影响?
我不曾好好研读过禅宗。只在大学时代稍稍涉及过。因为哲学系可以申请佛教奖学金,一学期五百台币。我赶快找了些佛书禅书来抱佛脚,写了篇论文交出去。就这么看了些这方面的书而已。我对宗教始终不太投入,反而是对自然科学的书籍很感兴趣。对于许多人,到了七十岁以后,死亡和神成了很大的事。可是对我来讲却不是那么重要,大概是受了孔老夫子的影响。未知生,焉知死?对生活还有欲望,还有要求,还有冲力的时候,你大概对死亡对神会看得比较淡。到今天我基本上还是个无神论者。
《枯山水》中的“枯”字,可能让人误会。你参观过日本禅寺的“枯山水庭 园”,不会觉得“枯”吧?虽然没有花木与水,却一点也不枯,反而质地、纹理、脉络和气象都很鲜活。
真的,你这本《枯山水》中的作品,和日本禅寺的“枯山水庭园”相契合。谈谈你写这些作品时的状态,好吗?
或许是到了这个年纪的关系,很向往柳宗元《渔翁》中那句“岩上无心云相逐”所表现出的“自由自在”意味。致于实际的操作经营则得自一次阅读,那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本谈盆栽的书。
陈耀广(PeterChan)是英国的盆栽专家,他写的《盆栽的奥秘》(Bonsai Secrets),如今已经成了经典著作。他对盆栽设计原则的总结,真正触动了我。比如简朴、安静、自然、摒弃流俗,不对称中取得和谐,以及暗示无限的空间。这种种对我写这本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本书中的素材基本上都建立在生活的回忆中。我希望能做到像盆栽那样缩龙成寸,蕴含大千世界。
关于你的写作,我们谈了未来,谈了现在,应该谈谈过去了。最初你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路的?听你中学的同学说,那时你似乎并没有显出文学的爱好和写作的兴趣。
说起来挺有意思,在师大附中的时候,我对文学一点也没有兴趣,到图书馆借的都是福尔摩斯、亚森罗平,什么《地心漫遊记》之类的书。一直到考大学那年的暑假,在家被老爸逼得背这书背那书,弄得很烦,大约出于反叛的心理,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另外的书来看。这样找来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那个暑假看了不少这类大部头的书,于是开始对文学有了朦朦胧胧的印象。被考试逼得反叛后,接着便去想,人活着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小说里面都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于是内心文学的种子萌芽。
不过,最大的影响还是朋友。最先影响我的是史作柽,经他介绍,读了些叔本华、尼采。我们俩都在法律系,都对法律没兴趣。他比我大三五岁,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在台大附近租了个小房间,我常去他那里玩,听古典音乐。他画画,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他介绍我读文学和哲学的作品。两年后,我们俩都转到哲学系,有志探讨人生的意义了。学校老师和同辈朋友都不谈这些。我的转系看起来很不合情理,虽然我不喜欢法律系的课程,成绩却很好。
另外一位朋友就是郑秀陶。我们大学暑期军训在同一个连。那时早上洗脸、刷牙,扩音器放的是古典音乐,我跟着哼的时候发现身旁有个胖胖的人也在哼,那就是郑秀陶。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开始文学、艺术地瞎聊,互相交换书看,跟着他我读了些波特奈尔、艾略特。我们两个人都对台湾正兴起的现代诗、现代画感兴趣。他还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诗,怎样才是好诗。和他一起渐渐结交了一些从事现代画、现代诗的朋友,也认识了尉天骢、陈映真、纪弦他们。
史作柽为我打开哲学之门;郑秀陶则为我打开了文学之窗。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你在台湾就开始写作,那也正是台湾现代文学崛起之际。后来到了海外,你一直关注台湾的文学,也一直不停地写作。你怎么看待台湾文坛这么多年来的发展?
张爱玲的独特写作才华,我绝不否认。但是文学上的大家,要有广阔的胸怀,历史担当的勇气。她对这些是完全不顾,而且由于她成长的家庭环境,特别能观察人际关系中的小奸小坏,表现得细致而曲折。她小说中的细节很耐读。她同代作家的作品与她的相比就显得粗糙。她这样的作家西方很多,属于二流,读者众多,名气很大,但是不会得到像张爱玲在台湾文坛那样崇高的地位。
我觉得从你在台湾开始写作,你就是执着于探讨人生和关怀社会,也许那时年轻,行动多而感觉模糊。现在这个走向就相当明确了。最后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写完一篇作品后的感觉如何?有没有惶惑不安,沮丧到不知所以?
我写完一篇作品倒是有放下担子后的轻松感觉。你说的那些混乱不安,我都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历。那种感觉存在,就意味着我的写作尚未完成。一旦觉得作品完成了,我感觉很好,换上了放假的心情。
写于纽约2013年 7月初
刘大任自撰小传
诞生于抗战时期,留下了逃难、空袭的记忆,尤其难忘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架势和防空洞中的惊恐。
文学上开窍较晚,二十岁左右才在朋友影响下开始创作,四十岁以后,火力转旺,当然是因为胡打胡撞、挫折、沮丧之余,意外增加了历练。
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写作,主要围绕生活体验,谈不上什么派别,文字力求简练,故事力求留白,论事则力求击中要害。
忽然就七十岁了,也出了二十多本书,不过,好像还未死心。自己都想知道,还能活出什么来。
王渝:你自撰的小传中,我想应该加进1948年随父母到台湾。1960毕业于台大哲学系,同年在《笔汇》发表短篇小说《逃亡》,引起文坛注目。曾参与当年台湾现代文学活动,还和邱刚健一起办过《剧场》,介绍《等待果陀》。从2009年到2012年出了七本小说集:《晚风习习》《残照》《浮沉》《羊齿》《浮游群落》《远方有风雷》《枯山水》和《当下四重奏》。此外还出版了十多本散文和评论。
(王渝)
责编:唐简 Jane Tang
喜欢请点赞
【王渝简介】 著名诗人、编辑,生在重庆,曾在南京生活,在台湾长大,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后留学并定居美国,现为海外华文作家笔会顾问;曾与友人共同创办《儿童月刊》,鼓励儿童创作,尤其是儿童诗;曾为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会长,代表该会出席布拉格的会议,任文学刊物《今天》的编辑室主任和散文编辑、《科学月刊》台湾修辞编辑,以及《华侨日报》纽约副刊主编。发表诗歌若干,著有随笔集《碰上的缘分》。
点击阅读更多忆乡坊的文章
唐简:那些男男女女在美国移民法庭上的真泣假哭 | 上帝会爱你的
唐简: 老狗特德
唐简:马拉喀什的敏娜
唐简:雅皮客栈
子姜:在春天的二月里讲一个爱情故事 | 这世上是否有超越一切的爱情?
纽约蓝蓝:纽约地铁里的那些事
【小说】一楠:约会
【小说】二湘: 费城实验
常少宏:玛利亚,你在哪里?
黄冰:亲爱的邓君
加小编微信,拉你进忆乡坊读者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