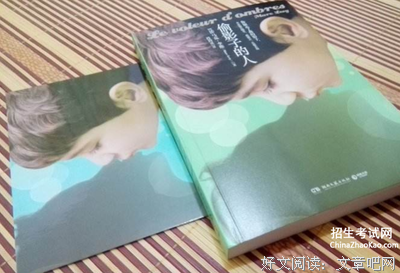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摘抄
《拎起寂寞的影子》是一本由林清玄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一):台湾旧时光,挡不住的逝去与新生
林先生的书,总给人一种千帆过尽后的淡然。这本《拎起寂寞的影子》也是。这是一本缅怀回望的书,因为书中讲述的乡村和都市发生的故事,是即将要远逝的皮影戏,虔诚向妈祖进香的老人,小渔村里坚守的老师,还未商业化的如室外桃源的武林农场,在北投温柔乡的侍应生,没有中国内蕴的台北建筑等等,都隐约感到他们在挥手告别。这些时代的产物纵然是叱咤当时,午夜梦回之际,恐怕也要黯然。
开篇的皮影戏,奠定了全书的基调。颇暮气的演出团队,连评委都不清楚皮影戏的审美,何况观众,大家像猎奇一样观看着。“地方戏剧的命根在民间,愈是通俗愈是大众化的地方戏剧,它的生命也愈能长久,反之,如果它失去了民间性,也等于浮动了命根,随时都可能灭绝”台湾最老的皮影戏师傅蔡龙溪接受采访时,说他90多岁了,收过9个徒弟,其中8个去世,还有一个也改行做房地产生意了,他本想培养自己的儿子,反被儿子说:“阿爸,你不要害我,皮影戏没前途了,你演一世人的戏有得到什么?”
书中还有写了几个远离城市喧嚣和文明的小岛和乡村。作者对小岛的景色做了如诗如画的描述。在小门岛上的居民顺应大海的脾性,在贫瘠的岛上讨生活。稻田的周边,用珊瑚礁堆砌出正方形石墙,房子也是用珊瑚礁堆砌的,冬暖夏凉,经久不坏。目前生活了四十六户人家,男人出海捕鱼,小孩钓鱼挖蚵,妇女种植花生番薯。夕阳下,海边拾贝的女人,映照着斜阳红霞,美丽的身姿显得深刻鲜活。但在离岛上生活,也面临着教育资源缺乏的窘境。比如大仓岛上,那些老师来岛上教学,要么是退潮是涉水而过,要么涨潮时等船过来。
在美丽的小乡村,美农小镇,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香蕉,稻米,烟草,大片的种植地像油画般,美农的格调不是高贵如兰,而似开在野风中的小花。这三样作物都要付出持久的劳动力获利确相当微薄的。他们培养下一代受高等教育。但是基本会留在城里工作。虽然也怀念故土,但对于一个落后乡镇,怀念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着重写了城市的阴暗一面。在北投,允许卖酒卖唱卖笑卖青春。在浓妆艳抹的脸庞下,女侍应生每天和陌生人打交道,职业化的笑容,苍白乏味的生活。很多出卖青春并不是自愿的,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解救经济窘境的工作才选了这条路。面临废除女侍应生户的营业,作者是更关注她们后续的生存问题,但这并不是一纸废除通知可以解决的。
在面临城市化的进程中,有些东西会随着时代远去,即使不舍,也挡不住历史的齿轮。会有新的文化覆盖,像层层的化石。这个过程也会产生一些毒瘤,能否转为良性,需要我们找到病根。我们能做的是记录,试图去理解。我们缅怀过去,后人也会缅怀我们的当下。春天过去,百花凋零,我们会哀伤,可是郁翠的夏天会到来,一边逝去,一边得到,这就是林先生笔下的台湾旧时光。
《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二):寂寞,是自己的回忆无法感同身受。
“明天交香蕉,在橘子园那个场,不要忘记了。”
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年前的老家。“明天收麦子的过来,咱们一起去场上交。”睡梦的呼吸中,鼻子已经把稻草烧焦伴着饭香味儿传递到了大脑。我还没来及睁开眼睛,脸庞已经被妈妈略带冰冷的手轻轻地捧住,“该起床了,今天要过麦熟了”。
麦熟,就是北方对于小麦收割季节的一个方言。由于北方都是平原地貌,每家每户耕种和收割的时间都差不多。在商定好的收割时间内,劳动力多的帮助劳动力少的,没有一户会掉队。
就像林先生在书里描述的那样“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们兄弟唤起来,给我们每人一件沾满香蕉汁的香蕉园工作服及一顶遮阳的斗笠,然后吃一顿丰富的早餐出发。等我们到抵香蕉园时,爸爸和工人们已经忙了一段时间,成熟的香蕉已经收割好摆置在地上。”
到达麦田的时候,能看见一大片麦子已经被割倒了打成捆放在地上,大人们还在弯着腰挥舞着镰刀继续收割。我挎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放着鸭梨、苹果、还有装着白开水的大水壶。长长的田垄,南北有1公里,我选在中央的地段,找个树荫凉坐下来,等着大人们呼喊:“来点水喝!”“来点吃的!”我就会挎着大竹篮送过去。天很热,但是能感觉到一丝丝的凉风。伴随着风,你能闻到刚割下来的、麦茬的青草香,有的时候我会特别顽皮地闭上眼,靠鼻子闻麦茬的味道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
太阳西斜,大人们已经将小麦捆儿都运到了打麦场上。打麦场往往是几家通用的,每家守住自己的地盘,开始给小麦脱粒。几轮劳作下来,会有一个小小的中场休息。热心邻居摊开一张桌子,买来冰糕招呼大人小孩过去吃。这时候我的邻居——老二叔儿,拿出他的二胡开始演奏。
“嘿嘿,我也是瞎拉,瞎拉,你学不学,我教你?”
老二叔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更别提一儿半女。一辈子勤勤恳恳,经常主动帮助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家庭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就在红白事儿上打打杂,北方俗称“捞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嘿嘿一笑,然后掏出糖让我抓着吃。
二胡的声音包围了打麦场。这时候我会找个高高的麦秸堆,躺上去边吃雪糕边听。你说,这个曲子是怎么被他的作者想出来的呢?为什么我听这曲就会快乐,听另外一曲就会悲伤呢?
慢慢地,二胡的声音就被大人们聊天说笑的声音盖过去了。某个人小声的说个荤笑话,大人们哄笑成一团,打打闹闹的就起身继续干活去了。老二叔红着脸,双手极不自然的继续拉着剩下的曲子,声音越来越小,后来完全听不到了。等我爬起来看的时候,老二叔连人带二胡已经不见了,大人们还在热火朝天地干活,仿佛他和二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第二天碰见老二叔,我称赞他昨天的曲子不错,他特别兴奋的跟我说;“嘿嘿,我也是瞎拉,瞎拉,你学不学,我教你?”我笑着摇头跑开了。
寂寞,是自己的回忆无法感同身受。
林先生是一个很细腻的人。细腻到他字间流露出来的每个情绪都能够及时触达到你的内心里。他描写的关于皮影戏、关于某个年龄段、某个信仰、某个人群,不论哪个点都能触动到我们的内心。关于寂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的内心深处,每一段回忆都是快乐伴随着痛苦相互交织而来。回忆小时候的麦田、小时候的打麦场,是因为长大后再也闻不到空气中的麦秸香,再也没有全家上下有序分工去完成一项任务的团结和快乐。回忆老二叔的曲子,是因为没有延续乡野艺术的那种传承。回忆本身是快乐的,但是回忆的过程真的很痛苦。
人生海海,我们都是寂寞的演者,但是我们不要。
《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三):这本书,林清玄在谈寂寞
“我儿子小时候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理想’。儿子在其中写道,我想做科学家,想做医生,想做教师,想做水手,想做企业家,想做的职业太多太多,所以一时还不能确定。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将来一定不会当作家。我好奇地问儿子,为什么,当作家不是挺好的吗?儿子的回答却令我大跌眼镜,儿子说,我才不当作家呢,我要保护我的头发……”
在四川师范大学演讲时林清玄讲出这小故事,讲完后他举起手,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头顶。
林清玄从不吝于“黑自己”,对自己的容貌更是不屈不挠,他曾说,“一次我看报纸,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自杀,因为她总是遭到别人的嫉妒,感觉压力很大。如果因为长得太漂亮而自杀,那我已经死了100次了。如果因为长得太丑而自杀,我至少已经死了10000次了。”
以至于提到林清玄,我的第一反应是一位风趣幽默、自信达观、从容淡然的火云邪神。
印象中林清玄的文字,朴实而充满禅意,自带滤镜,过滤掉世间的贪馋痴苦,只留下纯粹的爱。
“面对人生难以管理的生老病死,我们能以起承转合去寻找心灵的故乡。人总是有限制的,但有梦总是最美的。”“我觉得对孩子,要宽容和鼓励。孩子是你手中的箭,你只要拉满弓,然后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射去,至于这只箭掉在什么地方或是被风吹落,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林清玄先生的文章,大多从身边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事例,谈到人生的至善至美,充满禅意的喜悦,吸引人们进入一种质朴寻常,又自主尊严的精神境界”。
《拎起寂寞的影子》带我看到了林清玄的另一面,文艺青年的浪漫与无力。
在《一张发霉的影窗》中他写到:
“皮影戏的寂寞不仅来自它自由两个团体来参加盛大的比赛,也不仅来自表演者本身寻不到知音的寂寞,更深沉的寂寞是源发于整个地方戏剧命根浮动的民间,在浮浅的声光影像追逐中,所有的地方戏剧恐怕都难逃寂寞的命运吧。”“到我这一代要收起来了,不能害子孙”。张天宝半生与皮影为伍,下这个决心,我们便能体味他内心的苦楚了。九十岁高龄的蔡龙溪同样与皮影戏相伴半生,他有9个徒弟,其中8个已经离世。他希望小儿子可以继承衣钵,但显然儿子没这个打算。“阿爸,你莫要害我,皮影戏没前途了,您演一世人的戏又得到些什么?”
得到了什么?蔡龙溪也不清楚,大约是养大了几个孩子吧。
皮影艺人的无奈,亦是落寞的传统手艺的无奈。
《大甲妈和她的子民们》中林清玄讲了台湾人民对妈祖的崇拜,身怀六甲的孕妇、花甲之年的老人、年轻人因妈祖而聚集,徒步8天到妈祖庙朝拜。
“他们为什么放着家里的活不做,来跟随妈祖呢?他们用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两百多公里路而毫无怨尤呢?尤其他们行进的时间都是凌晨子时,他们如何能在疲累中忧心无旁骛地虔诚呢?”带着这些问题,林清玄跟随朝拜人群的步伐,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
信仰,来朝拜的人大多是还愿的,他们有一种力量,等同于伊斯兰教徒的麦加,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印度教徒的释迦圣地的力量。也许,在一个我们未知的角落,真的有一个迷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牵引着信徒们,一步步走向它。
《海的儿女》中,林清玄带我们走进大仓岛小学,整个小学一共四十名学生,五名教职人员,三个班级,分别是一年级十三人,三年级十八人,五年级九人,每两年招生一次,明年变成二四六年级。
吕家五兄妹就读于该小学,老大读五年级,老二和老人同在三年级,老四和老五同在一年级就读。五兄妹恰好是学校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父母出海打渔,孩子在学校读书。
还记得亲戚来我家说,儿子又考了第8名,她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丝毫没有长进。我当时想,这亲戚要求真高,第八名在我看来挺好的了。后来和别人聊起,才知道那孩子班里一共八个人。村里的希望小学,缺学生,缺老师,缺资源。
挺悲凉的,那孩子初中辍学了,没两年学校收不到学生停办了。
林清玄说,“我回头望向大仓小学,心头有很深的感触。大仓那一群海的儿女,在他们老是的教导下慢慢地接触了辽阔的世界,对两百年没有学校的岛民而言,大仓小学的本身便是一种深刻感人的美。”
美,我没看到,聊胜于无吧。
卖槟榔的小贩的生存,红灯区女性的生存,花农、武陵人、制陶人,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农业与商业,林清玄用悲悯的笔触,写下台湾的落寞。
《拎起寂寞的影子》是寂寞的影子,是台湾的影子,也是林清玄的影子,不同的侧面构成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就如他喜欢喝酒,微醺便停,喜欢喝茶,更在乎品茶的心情,林清玄一生都在寻找“正味”,有了正味,方能正行。正的伴侣、正的朋友、正的道理,找到那个正味,慢慢的去提升境界。
《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四):成年人的孤独是怎么流落到童年的
“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又美丽,又聪明,但是不快乐。 觉得自己老是孤单,人生对我来说,像是观赏一场球赛,热闹,却都是陌生的人。 妹妹自然是不能谈了。 用人也没有什么可说。” 在林清玄的新书《拎起寂寞的影子》中,那个叫蓝小玉的大一肄业生如是说。彼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孩子是牛津大学一位62岁老教授的,但她又不肯嫁给他,也不肯拿掉孩子,只好来未婚妈妈之家。 这似乎是一个叛逆少女的故事,但那种深入骨子里的孤独却从文字弥漫进空气,仿佛呼吸间便可闻到。这个女孩的童年为何如此孤独呢?她说她爸妈一年300天不在家,其中有200天在国外,他们对她唯一的意义就是拼命卖东西。的确,无论多奢侈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来,但爱与陪伴却不能。 有时候,见不着面的时间太久,蓝小玉连“爸妈”都叫不出口了,甚至忘记该怎么称呼他们。那个时候,她会偷偷哭泣,长得越大,哭得越多。 但是没人关心。后来遇到那个离过几次婚的大学老教授,对他的学问深深着迷,迷到跑去和他同居,直到怀孕。后来,蓝小玉自我检讨他们之间并无情爱,只是那时她太需要一位父亲了,教授的出现,恰好成了她的移情对象。 蓝小玉满怀憧憬地怀了孩子,她想要给他全部的爱,但是孤独却如影随形,她终是没勇气面对这一切,某天,她从未婚妈妈之家不告而别,落荒而逃。蓝小玉最终还是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她要了孩子,却让孩子和她小时候一样,要面临同样见不着爸妈的生活。这究竟是宿命还是人的劣性呢? 透过林清玄的文字读蓝小玉的故事,我仿佛听到她那叫人落泪的声音在唱:“人皆有父,翳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故事本身已叫人心碎,但更让人难过的是现实。现在孩子们整体变聪明的同时,也过早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向我倾诉他的孤独,忧伤而认真的表情叫人看着心疼,现实却又无法帮到他。 孤独和寂寞在林清玄的这本《拎起寂寞的影子》中随处可见,就像很多正逐渐没落找不到传人的手工艺,比如皮影戏。就像林清玄在参加完比赛后得出的答案:它仍是寂寞的。“皮影戏的寂寞不仅来自它只有两个团体来参加盛大的比赛,也不仅来自演者本身寻不到知音的寂寞,更深沉的寂寞是源于发于整个地方戏剧命根浮动的民间,在浮浅的声光影像追逐中,所有的地方戏剧恐怕都难逃寂寞的命运吧!” 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便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但我们终究不是圣人,芸芸众生依然陷于其中不可自拔,只能眼见着那些孤独寂寞不断生长。 林清玄曾说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但寂寞却侵入每个人的心间。纵观我们整个人生,其实都难挡寂寞。在人生的两个终端,有谁不寂寞呢?也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之一,便是学习如何对抗寂寞吧。 林清玄是著名作家,是台湾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各类奖项最多的一位,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的作品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散文更是独树一帜,自成风格,饱含深远的禅意,充满智慧,又兼具诗意之美,学生时代便极爱他的文字。他曾说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但寂寞却侵入每个人的心里面。 这本《拎起寂寞的影子》风格不同以往,以他亲自丈量体验的脚步,用真实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台湾当地最贴近普通大众生活的行当,通过最具代表性的当事人的经历和眼光,展现其历史兴衰。作者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对那些难以排解的寂寞充满无奈,虽满目惆怅,又饱含深情,亦满怀新的希望。作为林清玄作品中相对独特的存在,值得你入手品读。 拎起寂寞的影子评价人数不足林清玄 / 2020 / 天地出版社
《拎起寂寞的影子》读后感(五):让民间百态不再寂寞
“这些演者已经年老,他们现在还能维持一定的体力来演出,可是年寿有时而尽,艺术无时而穷,他们一辈子追赶皮影戏艺术的脚步纵使不停,在时间的冲流下,恐怕终究到头来也是一片惘然吧?”
《拎起寂寞的影子》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只以为这也是一本散文集,毕竟林清玄“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的名头不是白听那么多年。当然以一种固有印象去评判一本书的体裁,就和道听途说为一个人下定论一样荒谬无知,我们不了解的林清玄的另一面,或许可以从《拎起寂寞的影子》中窥见一二。
我们都知道甚至学过林清玄的散文,却很少看到他身为记者的一面,不仅是散文,他的报道文学写的写格外出彩。
“非虚构的报导文学已成为极热门的文学形式,也几乎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它必然也会成为极有影响力的文学形式。文学和艺术有更大的弹性、更多的方式才会产生更优秀的作品。”
从林清玄自己对这本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但是其实际深意,只有看的人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们可能都认识台湾的一种戏种——布袋戏,毕竟借助流媒体的翅膀,加上其本身的魅力,布袋戏在海峡两岸都非常火爆。有很多人从最开始熟知《金光布袋戏》,一直追到如今的《霹雳布袋戏》,它宏大完整的世界观,精美绝伦的人偶,独特有趣的演绎手法,都让它十年如一日的绽放着自己的光彩。
布袋戏但相比之在海峡两岸都熠熠生辉的布袋戏,有谁还知道台湾的其他戏种呢?在漫长的时光流转中,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的一些民间艺术,未必就有如布袋戏一般的好运气。《拎起寂寞的影子》听起来多么得的诗情画意,但看了之后才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悲凉与希望。台湾皮影戏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时空递变中逐渐变得寂寞的一缕影子。
说到皮影戏,大部分人可能只知道它是我国的国粹之一,论及其历史渊源,稍微了解一点的也能说道一二,但是再多可能就有点为难了。看,皮影戏对大部分的人们而言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虽然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的艺术价值极其珍贵,但是至于它是不是一如往昔的繁荣昌盛就未必知道了。台湾布袋戏限制于地域因素,它的生存空间只会随着时间的变迁变得越来越没落。
林清玄实地走访了台湾最后的五个皮影戏团,采访了不同看众对皮影戏的看法,了解了它逐渐没落的原因,也思考了它今后的命运该如何绝地求生的变革。林清玄遇到了90多岁高龄仍然会不自觉大叫“不要动我的戏尪仔”的蔡龙溪,也采访了“一日宰九猪,九日无猪宰”的徐福能,从他们交谈的话语中,我们能很真切的感受到皮影戏日暮西山的悲凉,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皮影戏的热爱。即使穷途末路,晚景凄凉,他们仍然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皮影戏发光发热。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然国内的继承者们有后继乏力的无力感,但是艺术的生命力总是能在绝境里重新爆发。
如果说,在乡村的脸中,皮影戏在逐渐走向不可逆转的没落之路,那么在城市的脸中,我们看到了皮影戏在外来力量的注入之下,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希望。
“台北人看野台戏”,就像我们每个地方一年一度的庙会一样,搭个台子,虽然简单,却也让这些皮影戏、布马戏重新找到了表演的舞台。虽然说这样也远远不够,但是确实也在慢慢变好。
从《拎起寂寞的影子》所在的时间线里,推进到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如今台湾省还有6个专业皮影戏团,从五个到六个的发展,不知道又是多少年如一日的岁月磨练出的新生力。
影子虽然寂寞,但总有人还在不断努力着。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复兴,总得有人来举起它们生命的火把。
《拎起寂寞的影子》,不单单只有皮影戏,还有更多的时态民生,人间万象,林清玄以其独特的文笔和非凡的思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时代肖像。就像在思考谁来关心地方戏一样,说来关心并解决这些时代乱象呢?这个问题在文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些答案需要我们这些看官们自行思考。
注:图片来自网上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