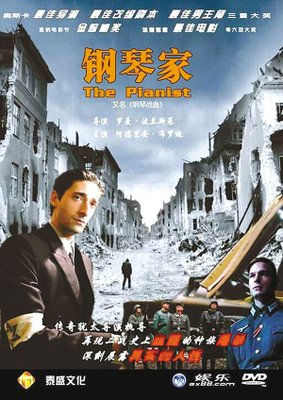《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经典读后感有感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是一本由[英] 伊迪丝·汉恩·比尔 / [美] 苏珊·德沃金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读后感(一):这样的生还经历,又有几人可得?
关于纳粹与第三帝国的著作不胜枚举,不管是宏观历史分析还是个人视角叙述,已有许多关于人类那段惨痛历史记忆的反思文字。但为什么我们仍需要反复讲述那段历史呢?我们从一手资料和叙述那里了解得还不够多吗?
恐怕是的。
这是一段常读常新的历史,它涵盖了人类已知的所有罪恶与希望,恰如《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大屠杀中的一个幸存奇迹》涵盖了逃离纳粹魔爪的所有可能。这是一个在敌人后方、在敌人家里幸存下来的故事,是一段千方百计逃脱、生存、维持信念的真实历史。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发生在本书作者伊迪丝·汉恩·比尔身上的故事。
伊迪丝出生于1914年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她的父亲经营商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错,伊迪丝甚至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年轻女性中极为罕见。伊迪丝与她两个姐妹的成长是快乐的,但在1941年德国纳粹入侵维也纳那天,她的少女时光骤然结束。她被遣往德国北部的劳动营,从事极不人道的体力劳动。次年她被遣返维也纳,在朋友帮助下化名格蕾特·但纳,潜往慕尼黑,在全是德国人的环境中周旋生存。她与维纳·弗特结婚,后者在战争中升为军官,维纳当然介意伊迪丝犹太人的身份,但还是选择接受了她,两人生下一个女儿。1945年德国战败,伊迪丝重申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成为勃兰登堡家庭法庭法官。两年后,她与维纳感情彻底破裂,协议离婚。1948年,苏联企图吸纳伊迪丝为东德安全部密探,她逃亡至英国。之后,伊迪丝在英国和以色列生活过,最终于2009年病逝于伦敦。
这个故事的曲折传奇之处太多,但最戏剧性的一点,恐怕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个女人选择与一个男人步入神圣殿堂,除了喜爱之外,更是为了续命。这在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彼时竟成了最好的打算。更离奇的是,这对夫妻分别贴上的犹太和纳粹两个标签。这种身份的截然差异并非噱头,伊迪丝在“委作潜艇”的日子里需要隐藏的又何止是民族身份这一项。她不仅不能表现出自己正常的智力水平和认知水平,甚至必须表现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貌,变成一个标准的“雅利安妻子”。
伊迪丝的生命经历愈传奇,就愈证明了纳粹强权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有多悲惨。试下一下,在鄙夷犹太人的环境里作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在夺命劳动营里收到爱人的鼓励信件,在无路可逃时受到好心夫人的指点,在须改头换面、抛弃身份时得到好朋友的倾囊相助,在逃亡之时受到属于敌人一方的男性之庇护……这些何其幸哉的遭遇,岂是人人得享的?而恰是这一连串的幸与不幸,交错在伊迪丝的生命里,让她戏剧性地成为了一个生还者。这样的生还经历,又有几人可得?甚至不必与普里莫·莱维或米克洛斯·尼斯利这样从灭绝营里爬出来的知名生还者比较,光是看看伊迪丝母亲克洛狄德的遭遇便可知晓。克洛狄德被从维也纳遣往波兰,之后立马音讯全无。可以想见,作为年迈女性的克洛狄德,应该属于集中营里第一批被处死的犹太人。
本书首版印刷于1999年,甫一出版就获得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在出版15年后(即2014年),这本书突然再度占据各大图书榜单的首位,这更佐证了“那段历史常读常新”的观点。正如本书的合著者、美国剧作家苏珊·德沃金所说:“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图书市场的奇迹,但我从心底里觉得,这是因为充满危险的时代、关于生存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们人类的心头。一次又一次,我们须得反复质问自己,当我们活在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困苦之中时,该如何自处?”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为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读后感(二):经历了那样的年代与时代,她毕竟活下来了
原来以为,这是在讲故事;在仔细瞧了瞧之后,却发现作者就是主人公本人,这是她的一本回忆录,是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对于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奥斯威辛对于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所以,作为一名1914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伊迪丝·汉恩·比尔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她个人的足够幸运,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在20世纪30年代,一名奥地利年轻女性能够进入大学深造,而且差一点就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不但有资格成为律师,并且能够做法官,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但是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对奥地利的吞并,让这一切戛然而止。这是原名伊迪丝·汉恩的这个奥地利年轻犹太女孩的个人不幸。在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不幸比比皆是,算不了什么。当然,如果她有机会去了英国,或者去了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能够离开欧洲,或许凭借她的学识,她以后多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过时势就是那样的,她没能离开奥地利,所以可想而知,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能够幸存下来,直至二战结束,真是了不起。
确实不能够再多要求什么伊迪丝什么了——并不只是她挺身而出反对纳粹才可以证明什么。当她于1941年被迫前往德国北部的劳改营里劳动,13个月里每周劳动80小时,却只能分配到仅供充饥的食物的时候,她活下来就证明了她的坚韧;当她于1942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化名格蕾特·但纳潜往慕尼黑,进而认识纳粹军官维纳·弗特,并向后者坦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两人最终结婚、生女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责怪她什么,那也是时刻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度过艰难的每一天——更何况,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把自己的身份证明藏在了书籍的夹层之中放入地下室,证明她没有忘本;而在1945年德国战败后,伊迪丝重申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成为了勃兰登堡家庭法庭法官;3年后,由于不愿被苏联吸纳为东德安全部密探,伊迪丝逃亡至英国;直至在1984年移居以色列,又移居英国……
这一段令人难忘的个人经历,最值得玩味的是伊迪丝与维纳的相识和结合,要知道,后者当时的身份是一名纳粹军官。两人显然都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要知道,当时伊迪丝虽然用的是其他人的身份、名字,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位拥有纯雅利安血统的姑娘;但她却没有向维纳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伊迪丝足够勇气,却也是在冒着生死之险;维纳作为纳粹军官,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他显然没有在那个时候维护了伊迪丝——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忠于纳粹德国,而是忠于了爱情与婚姻!
二战时的经历,战后拒绝苏联的邀约进而逃亡英国,伊迪丝无疑是在一次又一次冒险。用她自己后来的话,“此事关乎我的个人气节。我可以假装为另一个人,假装为德国人。我可以欺瞒每一个人,但我必须告诉他真相”。显然,这句话也适用于解释她为什么会拒绝为苏联人工作,应该同样也是因为“此事关乎我的个人气节”。
所有的一切,不需要拔高也不需要指责,这只是一个欧洲犹太人在非常时候的一段非常生存故事,也非常不可思议。仅此而已。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读后感(三):歌利亚的幽灵
埃及衰落,巴比伦覆灭,罗马帝国破碎。强大的敌人一个个死去,流浪的犹太民族历经浩劫延续至今。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些强大的敌人们似乎从未真正死去,他们宛如巨人歌利亚的幽灵,牢牢寄生在犹太民族的灵魂之中,吸吮犹太人的每一丝恐惧。
1938年,德奥合并,纳粹接管奥地利。24岁的犹太人伊迪丝目睹歌利亚巨大的幽灵再次升起。
大卫王尴尬的后裔
“在维也纳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来到这个城市。”与其他彻底同化的维也纳犹太人一样,伊迪丝并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不同。与同时代的奥地利女孩儿相比,她甚至是非常幸运的。有温馨和睦的家庭,有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菲比,父母支持她攻读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身份的割裂不时困惑着伊迪丝,学校里的老师会盘问她在家中是否讲希伯来语(来自本书同名纪录片),帮同学完成数学作业却被反呛一句“你们犹太人怎么都那么聪明”,而母亲则会因为她吃了一根血肠大发雷霆,父亲绝不允许她和基督徒通婚,连想象都不可以。一方面,父母并没有刻意教导子女犹太人的习俗、语言、信仰、教律,而是认为犹太文化如同乳汁哺育孩子们,不需要刻意教习。而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对这个柔弱、保守、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古老民族充满了好奇和偏见,尽管大部分同化的犹太人无论是外貌还是信仰都与本地人无异。
伊迪丝在书中写到:“每一代犹太人都承受身为犹太人的负累,却不曾被赋予犹太人的力量”
犹太人与主流人群之间始终隔着一层薄膜,人们这样善于划分你我,扎人又不致命的偏见和格格不入的身份让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尴尬的局面。然而,这些不致命的尴尬即将发生极其危险的质变。
善与恶的博弈
从偏见到屠杀的距离有多远?
纳粹接管奥地利后,对犹太人的恶意在种族主义肥沃的土壤上无限膨胀。犹太人贪婪,犹太人精于算计,犹太人满腹阴谋,犹太人千百年来趴在其他族类身上吸血。根深蒂固的偏见突破了道德的壁垒,并将这种偏见作为迫害行为的注解,奥地利犹太人的处境逐渐走向危险的境地。最开始是限制犹太人出行,在咖啡厅电影院划分犹太人的区域,接着是在街上辱骂殴打犹太人,用枪口押着犹太人擦洗街道上的地砖,从犹太人家中抢走财产,接着抢走他们的家。
从伊迪丝的叙述里,我们得以窥见歌利亚的幽灵是怎样一口一口吞噬着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吞噬掉他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巨大的幽灵背后,满是为虎作伥的“其他人”,有曾经的朋友,有左邻右舍的熟悉面容。
伊迪丝写到:“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是否真心相信这套说辞?当然不信,他们并不愚昧。然而,他们历遭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他们渴望过上好日子,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偷窃。犹太人贪婪成性这一信念,就使得他们有了托词,心安理得地窃取犹太人的所有。在这样的处境里,每一个人给自己制定规则。无人迫使他们虐待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善待我们。然而,极少数的人选择友善。”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在作恶,毕竟作恶实在太方便,太顺手了,太名正言顺了,你甚至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让这些犹太人多工作一会儿,让这些犹太交出他们的录音机,让这些犹太人滚出电影院。毕竟事不关己,甚至有利可图,毕竟犹太人并没有直接死于这些微不足道的恶意。既然小恶可为,大一点的恶行也可以。于是伊迪丝被迫前往种植场做苦工,劳动强度足以摧毁任何健康的身体。而她设法保护的母亲,被送往波兰的集中营。
再黑的夜里,也会有星星,尽管稀少,但也格外闪耀。
正如善与恶的博弈从不停歇。伊迪丝多少次感觉快活不下去的时候,好心人的善意总会及时出现,拉她一把,尽管那些人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行善者也有冒着生命危险。在种植园感觉快要腐烂在芦笋田里的时候,有米娜和她互相打气,探讨哲学和法律;在工厂被要求完成不可能的生产量时,女主管偷偷教给犹太女工们传授经验,趁人不备顶替他们,好让犹太工人能休息十五分钟;伊迪丝回国后遭遇爱人和亲人的双重抛弃,故乡已无犹太人的容身之地,纳粹博士的太太冒着生命危险接纳伊迪丝,铤而走险将伊迪丝送往德国。
尽管传奇,但伊迪丝就这样靠着人们那么一点善意生存下来。也许只需要一点点善意,就可以救活一个人。
潜艇岁月
凭借朋友和博士太太的努力,伊迪丝变成了雅利安女孩儿格蕾特,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潜伏。
一切只为了活下去,活下去。
讽刺的是,检查她身份证件的官员评价伊迪丝:一看就是典型的雅利安血脉。
恐惧如影随形,哪怕是作为格蕾特,日子也并不容易。潜伏意味着伊迪丝必须噤声闭气,伪装成一滴海水消融在敌人的海洋里。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智慧和机敏必须被深埋,伊迪丝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一句话一个词都有可能将她送入绝境。到处都有告密者,到处都有狂热的纳粹分子。不是希特勒选择了德国,而是德国选择了希特勒。
哪怕在丈夫维纳面前,伊迪丝也不敢展现真正的自己。尽管身为纳粹党员,维纳并不真心信仰纳粹,尽管维纳知道了伊迪丝的犹太身份依然坚持娶她,尽管隐藏的自我直接导致了战后维纳和伊迪丝关系的破裂。为了活下去,伊迪丝没有选择。
除却利害关系,伊迪丝和维纳的结合中最主要的成分仍然是爱情,即使维纳并不是菲比那样的灵魂伴侣。他们的婚姻中不可避免的掺杂了“避难”的因素,但爱情从来都不是能轻易提纯的东西。伊迪丝违反自己的规定,冒着危险和维纳约会了第二次。而维纳在回家前总是透过钥匙孔偷看伊迪丝做饭的身影,他爱着家庭的温馨。当战争结束,伊迪丝潜伏多年的自我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爱也随着调转的地位逐渐熄灭。很难说是幸运或是不幸,时代巨大的扭矩让人们的命运错误地拼接在一起,再痛苦地割裂开来。
本书有一部同名纪录片,镜头里90岁的伊迪丝回忆起自己传奇的一生仍会微笑,会流泪。谈及幸福的青年时代,伊迪丝的眼里仍然闪动着当年朝气蓬勃的模样。那是1933年,她的爱人菲比说到“坚信会有这样一个阶级。没有主人,没有奴役。不分黑种人,不分白种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基督徒。只有一个人种——人类。”
87年过去了,伊迪丝和菲比的宏伟梦想仍未实现,或许在下个世纪也难以实现。而歌利亚的幽灵总能在人间找到新的宿主,有时它是种族主义,有时它是恐怖主义,有时它是民粹势力。
如果伊迪丝跌宕传奇的一生能提醒我们些什么,那一定包括:警惕歌利亚的幽灵,它从未远去!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读后感(四):她走过地狱
对现在的人生感到迷茫时,我总会产生这样的幻想:可以随意拨动时间,飘在太空(?),成为整个世界的旁观者。想看世界的转动与运行,想立刻看到过去与未来,而不是身处其中接受生活日复一日的捶打。虽然一觉醒来,还是只能透过我的800度近视眼看到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过幸好,未来的事无从得知,我们至少还能听人讲述遥远的、从未经历过的那些故事。
试着想象一下,你为了活下去被迫丢弃了姓名、出身、信仰,进入一个已经谋杀了你数百万同伴的社会,每一天都在担心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你还嫁给了一个与打算杀死你的人有相同信念的男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一怒之下将你投往地狱。你该如何活下来?对了,想象的大背景是二战时期,而你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
如果这是一个生存游戏,我不敢说自己能够活到最后,现实中却真的有人凭借着机敏、智慧与勇气做到了。
1914年,伊迪丝·汉恩·比尔(Edith Hahn Beer)出生于维也纳,被女性朋友抱怨“你们犹太人怎么都那么聪明”的伊迪丝上了大学——这在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年轻女性中极为罕见。但就在她即将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时,德奥合并,她的考试资格被取消。更深的噩梦随即而来,1941年,德国纳粹入侵维也纳那天,她被遣往德国北部的劳动营进行极不人道的体力劳动。次年伊迪丝被遣返维也纳,在朋友帮助下化名格蕾特·但纳,潜往慕尼黑,在全是德国人的环境中周旋生存。她在慕尼黑遇到了德国人维纳·弗特,维纳向她求婚,即使在她坦白自己是犹太人后也不在乎。秉持着“绝不显眼”的原则,伊迪丝在“委作潜艇”的日子里不仅不能表现出自己正常的智力水平和认知水平,甚至必须表现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貌,变成一个标准的“雅利安妻子”。“由于偶然的幸运,由于一些善良人的干预”,伊迪丝活了下来,于2009年去世。
但轻飘飘的一段话若是拿来总结一生,未免有些残忍。我没有自信讲好这个将伤痛一点点袒露的故事,背后的每一分痛苦与恐惧,只能让她讲给你听。在这段涵盖了人类已知的所有罪恶和希望的历史之中,勇气和意志或许能创造奇迹。
文/[英]伊迪丝·汉恩·比尔 [美]苏珊·德沃金
德国任命阿道夫·艾希曼根除维也纳犹太人,他的政策成为第三帝国“清除犹太人”的表率。扼要地说,他令我们以尽可能高的代价逃离。富裕者须将全部财产转让给政府;家境一般者须以高价购买车票,价格高昂得离谱,致使父母无法负担,被迫选择哪个孩子离开,哪个孩子留下。
纳粹接管之后,我们是何等的混乱与恐惧,我该如何向你形容?及至昨日,我们依然生活在理性社会。今天,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校友、邻居、老师,手艺人、警察、政府官员—全都跟发了疯似的。一直以来,我们早已习惯将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称为“偏见”。多么文雅的词汇,多么委婉。事实上,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与他们的宗教一般古老。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与生俱来,他们在必然仇恨我们的教育之中成长。德奥合并一开始,那层庇护着我们免于他们仇恨的文化薄膜,便尽然褪落。
抗议者在马路旁书写反纳粹标语。党卫队随手揪住犹太人,顶着枪口逼他们擦洗,奥地利人在一旁围观,嘲弄取笑。
纳粹广播将这个世界的恶行和罪孽全都归咎给我们。纳粹称我们为次等种族,紧接着又说我们是超人种族,指控我们筹划谋杀他们,劫夺他们的所有一切;他们宣称,为了阻止我们征服世界,他们自己必须先征服世界。广播说,犹太人必须被剥夺一切财物。我父亲工作之时倒地身亡,然而,他并非真的以工作挣取我们这套舒适的公寓——包括客厅的皮椅、我母亲的耳环——实际上,他是以某种方式从奥地利基督徒那里偷盗而来,现在,奥地利基督徒要“名正言顺地”收回这些财物。
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是否真心相信这套说辞?当然不信。他们并不愚昧。然而,他们历遭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他们渴望过上好日子,而最快捷的实现方式就是偷窃。犹太人贪婪成性这一信念,就使得他们有了托词,心安理得地窃取犹太人的所有。
我们坐在自家的公寓里,等待这场疯狂结束。我们的身躯因恐惧而瘫软。迷人、机智、翩翩起舞、慷慨的维也纳,必定会起来反抗这场疯狂的骚乱。我们等了又等,疯狂仍未结束。疯狂不曾结束,我们还是一等再等。
对于犹太人的限制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不能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我们不能行走在某些街道。纳粹在犹太人店铺橱窗打记号,警示市民不可在此购物。咪咪被干洗店解雇,因为基督徒雇用犹太人已属违法行为。汉丝被勒令停学。
理查德舅舅到那间光顾了20年的咖啡馆。现在,咖啡馆分隔为犹太人区与雅利安人区。他坐到犹太人区。因为他的头发浅色,模样不似犹太人,一名不认识他的侍者说,他须移步到雅利安人区。然而在雅利安人区,一名认识他的侍者说,他须回到犹太人区。最后,他决定还是作罢回家。
路易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是维也纳犹太人当中一大首富。他试图出城。纳粹在机场将他拦截,押进监狱。不知他们在狱中对他做了什么,结果终归是他深信自己应该将所有财产转让给纳粹政府。然后,他们将他释放。党卫队接管他坐落于欧根亲王大街的罗斯柴尔德宫,更名为犹太人移徙出境中心。
人人都在谈论离开。
“兴许,我们可以去巴勒斯坦某个集体社区。”我向裴比建议说。
“就凭你?我可爱的小老鼠?干农活?”他笑着抓挠我,逗我发痒,“可爱的小手指会起水泡的哦。”
我在英国领事馆排队,排了数日,指望获准去英国做家庭女用。维也纳的犹太女孩似乎都来申请了。
一个亚洲男士挨近我和堂妹爱丽,向我们鞠躬,笑盈盈说道:“两位女士若有兴趣观览东方奇迹......万里长城......紫禁城......我持有授权,为两位提供工作机会,任选一个中国城市。我们安排护照、交通、住宿。我的车就在附近。你们明日便可出奥地利。”我敢肯定有人跟他去了。
堂妹爱丽得到一份英国工作。我获得批准,但没有工作。
一日下午,汉丝没有回家。我和咪咪出去寻找。我们再回到家时,她仍不曾回来。妈妈开始哭泣。一个17岁的清秀的犹太姑娘,在反闪族、恶棍四伏的城市消失。我们不由得战栗。
午夜时分,汉丝回家来。她面容惨白,浑身哆嗦,绷着脸,似乎顿时苍老了。
她告诉我们,纳粹拉她上车,带她到党卫队值班室,拿枪顶着她的头,令她缝几打制服的纽扣。隔壁房间里,她看到一些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蓄着长胡须的虔诚男子,在纳粹的逼迫之下做荒唐的体操动作。那些纳粹觉得这样的游戏十分滑稽有趣。
汉丝反抗着不肯缝纽扣,有个混蛋威胁说,她若不闭嘴乖乖地干活,就要揍她。傍晚时候,他们放了她。然后,她就一直在街头游荡。
“我们得离开。”她说道。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读后感(五):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伪装身份文件、嫁给纳粹军官逃脱种族灭绝灾难
为了生存,29岁的犹太女孩伊迪丝将自己的身份证明藏在了书籍的夹层之中,放入地下室。
然后,伊迪丝更名格蕾特·但纳,一位21岁、拥有纯雅利安血统的姑娘,嫁给了纳粹军官维纳。
战争中艰难求生的犹太民族
1938年7月6日,法国埃维昂难民会议上,32个国家集体表示拒绝接受犹太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军事地位在欧洲日渐占据优势,这时的欧洲各国都不愿站在德国的对立面上。因此,当得德知德国欲迫害犹太人时,各国政府纷纷示意本国驻德公使不要为犹太人提供庇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犹太民族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
据统计,德国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了将近600万欧洲犹太人,其中还包括100万儿童。整个世界当时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为纳粹种族主义学说的牺牲品。
在这次难民会议之前的1938年3月15日,在希特勒的高压协迫下,99%的投票者都赞成德奥合并。
德国吞并了奥地利。
奥地利并入德国后的第二天,所有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赶到大街上。纳粹让他们跪在地上用刷子清洗路面。
自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黑暗生活。
犹太姑娘伊迪丝·汉恩·比尔很幸运地自这场浩劫中存活下来。她将自己的经历著成《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一书,让读者跟随她的人生重新审视那段冷酷的历史。
往事不堪回首
1914年,伊迪丝·汉恩·比尔(Edith Hahn Beer)出生于维也纳。她的家庭是传统犹太家庭,不过,伊迪丝的父亲从不曾教导孩子们如何做真正的犹太人,他深信犹太民族的传统已经根植于孩子们的生命之中。
因为家境相对富裕,和伊迪丝父亲的开明,伊迪丝得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在学校的伊迪丝经常被朋友们抱怨说:“你们犹太人怎么都那么聪明”。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就在伊迪丝即将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时,德奥合并,她的考试资格被取消。
1941年,伊迪丝被强行送至芦笋种植场工作。在这里,超强的体力劳动、紧缺的食物供给,让伊迪丝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糟糕。
伊迪丝守着六周工作结束后就能够回家的期望,却不知,她在这里的时间被延长再延长。
从4月到10月,伊迪丝回家的时间被无限拉长。后来,伊迪丝又被转移到阿什尔斯莱米纸厂工作。
纸厂的生活比种植场好些,但非常有限。伊迪丝在纸厂一直工作到了1942年6月,阿什尔斯莱本的盖世太保终于通过了她回维也纳的申请。
伊迪丝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被强行带离维也纳,她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回到维也纳的日子,伊迪丝居无定所,亲人朋友谁都不敢收留伊迪丝。伊迪丝的恋人裴比除了尽可能地给伊迪丝一些帮助之外,别无他法。
无法生活下去的伊迪丝决定离开维也纳。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伊迪丝潜往慕尼黑。
在她的身份证明上显示的名字是格蕾特·但纳,她的血统是纯雅利安血统。
慕尼黑开启新生活
伊迪丝在慕尼黑遇到了她的丈夫维纳,一位纳粹军官。维纳因车祸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得以不必前往战场。
遇见伊迪丝的时候,维纳有妻子有女儿。然而,维纳爱上了伊迪丝,为了能够和伊迪丝在一起,他决定和妻子离婚。面对向自己表明心迹的维纳,伊迪丝既紧张又兴奋,她无法相信维纳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仍旧决定和自己在一起。
慕尼黑这名白色骑士,勇猛无畏地追求我、爱慕我,他所给予我的,不仅是安全,还有爱。我当然接受。 我接受,并且为自己的幸运而感谢上帝。维纳并不是一位坚定的希特勒信仰者,他让我想起了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青年训练营K队长,
K队长曾经上过战场,并在战争失去了一只眼睛;K队长是神枪手,百发百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甘心成为青年训练营的一个小小队长,导演塔伊加·维迪提并没有交待。我们无从获知在K队长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是,他并不是随口说出“盖世太保会杀掉帮助过犹太人的人”的;他也不是偶然出现在乔乔家的;他更不是看错了证件上的数字而没有当场揭穿艾尔莎的。
K队长清楚地知道罗茜在为何事奔忙,他知道罗茜在家中藏匿着犹太人,他也知道罗茜被盖世太保抓捕。
所以,他才会在泳池边以随意的口吻“劝阻”乔乔告发艾尔莎;他才会在盖世太保进入乔乔家的时候,“假装”路过迅速赶到;他才会明知艾尔莎不是英加也帮助她隐瞒身份;他才会在把乔乔推出战俘队伍时说:你母亲罗茜是个好人,对她的死我真的很抱歉。
电影中的K队长同现实生活中的维纳一样,早已看清了希特勒最终下场。
伊迪丝和维纳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平静的时光。随着女儿的出生,维纳最终被征兵,伊迪丝重新回到了四处奔波的状况,不同的是,这一次,伊迪丝要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安吉拉一起奔波。
战争结束之后,伊迪丝将自己的身份证明自书籍夹层之中取出,她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本名,自己的学历 证明。这之后,伊迪丝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法官。
伊迪丝多方努力终于将丈夫维纳自苏联战俘营接回家中,短暂的相聚时光之后,维纳因为接受不了伊迪丝成为一名职业女性而选择离开她。
应该说,维纳是真心爱着伊迪丝的, 他无视种族选择和伊迪丝生活在一起的行为令人敬佩;不过,维纳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或者可以用大男子主义来形容维纳。他要的是一个千依百顺的妻子,另外,他对伊迪丝生下的是女儿也颇有微词,维纳更想要个男孩。
伊迪丝的法官工作因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企图吸纳她为东德安全部的密探而结束。
苏联指挥官说:我们帮助过你,现在你必须帮助我们。
伊迪丝无法接受这样的“指令”,她认为这将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所以,伊迪丝假装听从安排的同时,千方百计弄到了离开慕尼黑需要的一切证明文件,终于在1948年底离开了德国逃亡至英国。
伊迪丝·汉恩·比尔的一生坎坷,充满传奇色彩。
在日后被问及为何会向维纳坦白自己的身份时,伊迪丝说:此事关乎我的个人气节。我可以假装为另一个人,假装为德国人。我可以欺瞒每一个人,但我必须告诉他真相。
伊迪丝说,感谢所有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而其实,正是伊迪丝的正直善良、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意志帮助她最终走出了那段黑暗岁月。
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拯救了伊迪丝的性命,让她最终成为了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之一。
写在最后:
法国埃维昂难民会议之后,多国拒绝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却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
1938年7月的一天,17岁的犹太少年艾瑞克·高德斯陶伯跑遍多国领事馆都没有人愿意给他发签证,心怀绝望的她,最后来到了中国领事馆。
令高德斯陶伯意外的是,他在这里一下子拿到了20多张签证。这个消息迅速在犹太人中传开。从第二天开始,中国大使馆门前排满了渴望得到签证的犹太人。
然而,何凤山的这一举动令纳粹德国非常不满,他们向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当时不愿与希特勒为敌,于是他下达命令给何凤山的上级,要求何凤山停止发放签证。
强压之下,何凤山依然没有停止对犹太人发放签证。纳粹军没收了何凤山办公的房子,他就租了一间小屋坚持办公。然而,不久后何凤山被调离了维也纳。
据统计,截至何凤山离开维也纳之时,他至少帮助4000多名犹太人逃往上海。
2005年,联合国誉何凤山为“中国的辛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