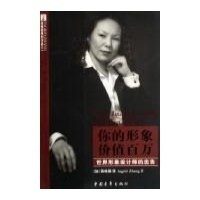《英格丽·卡文》读后感精选
《英格丽·卡文》是一本由[法国]让-雅克·舒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本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格丽·卡文》精选点评:
●记忆的碎片拼成的华丽人生。
●放荡中留下的纯真,善意孕育的恶毒,满书都是电影圈造梦者的复杂精神世界。舒尔讲的仅仅是英格丽、法斯宾德、安迪沃荷和伊夫圣罗兰们吗?他所描述的是所有伟大表演者奇观般的精神世界。他们对他人消隐自我,对自我消隐作品,最后所能留下的似乎只有一地焚烧过后的无序灰烬。
●一本叙述方式不同的书。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它最成熟之处在于整个的统一性,仿佛多种材料的完美糅合,让人完全看不见缝合的痕迹
●看不懂啊
●喜欢里面讲到的香水
●天啊,这什么鬼东西。这写法真是灾难,特别是对一本长篇小说来讲
●意识流,很漂亮,但是我不喜欢
●只属于少部分人的书。描写太动人了,读她就像置身于一场梦,只关于爱。
●美丽的歌声。
●这本书让我把空间名字改成梦游
《英格丽·卡文》读后感(一):英格丽·卡文
她也实在说不上好看。小时候遭遇炸弹毁容,皮肤溃烂,遮掩创伤过早地与她相伴。
如同一般成长的代价,起初是可见的伤痕,病愈已是少年;追随而来的心灵的磨砺:战争与废墟,事业与颠簸,爱情与死亡。
天赋异禀的好嗓音,爸爸是名爱好音乐的纳粹海军军官,那幢被炸弹结束命运的大房子,每个楼层曾摆放着相同的四种乐器,爆炸是最强音(革命、战争的狂啸,在《V字仇杀令》中是一出怒放烟花的交响曲)。
她成为法斯宾德的妻子,那位三十几岁即因毒品离世的天才导演,长得丑陋,还是个同性恋,她成为他的女演员,“女演员都是婊子”法斯宾德说,他和她结婚,一年即告离异,他表现得像个偏执的疯子(法斯宾德喜欢她的男性气质,现在想来法斯宾德那部向《蓝天使》致敬的影片《劳拉》,会不会是向有着一副男性脸庞的无与伦比的玛琳•黛德丽致敬呢?)。
伊夫•圣•罗朗也出场了。一个暧昧的角色。在她身上剪裁出一条长裙,“一条成功的裙子应该给人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她有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呢?她说法斯宾德的葬礼是可笑的,让大家围着空棺材哭,尸体却在解剖,是他自己导演的吗?
她后来嫁给了让-雅克•舒尔,本书作者,《英格丽•卡文》是他的第三部小说,获得2000年度龚古尔文学奖,他在书中的名字是“夏尔”。万花筒般的对那个时代的追忆,文字涂成画面,文字无法替代画面,读起来很累,更何况摸不着边的冥想,故意的。“格里菲斯被他女主角的美深深打动,于是发明了特写,用以更详细地捕捉它。”(戈达尔),舒尔也如此珍爱英格丽吧,无以复加的联想、拼贴。
那张法斯宾德身前留下的纸条给了舒尔灵感,纸条上是对英格丽一生的编排,是剧本构思?法斯宾德计划导演一部关于英格丽的电影?他死了,那张纸条活着,如遗嘱一般落到承继者手中,若干年后变成了一本书,一本有着电影画面的书,还得了大奖,“爱比死更冷”的法斯宾德会想到吗?
《英格丽·卡文》读后感(二):走近英格丽的歌声与生活
摘自《珠江时报》 作者:郑 媛
在写出获得2000年龚古尔奖的《英格丽•卡文》之前,让•雅克•舒尔只出过两本反响平平的小说,而且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人们只知道他出生于1941年,是马赛人,25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一个字,得了个“懒鬼作家”的绰号。大作家、龚古尔奖评委米歇尔•图尔尼埃断言:“这是一本不会陈列在书店的新书橱窗的书。”可是老伯乐也有相错马的时候。这本书当年就在法国销售23.4万册,还在《读书》杂志年度“二十大好书”中排名第二位。近日,该书由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英格丽•卡文其实是让•雅克•舒尔的妻子,一个歌星、影星,是作家、导演法斯宾德的前妻。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一所营房里,英格丽•卡文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还有他们的指挥官——她的父亲,在“元首”的画像的目光注视下,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这是她第一次登台献艺,那时她才四岁半。她父亲指挥一个海军基地,有空时坐在钢琴边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英国的轰炸机来了,炮弹让这座小城和她家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漂亮小姑娘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她的皮肤出现可怕的变态性反应,全身都是伤口,裹着毛巾和绷带,就像“一具长着一副金嗓子的干尸,一个有活动关节的布娃娃”,常常疼得彻夜难眠。她在音乐的旋律与疾病中长大。成年之后,她主演的音乐剧《把世界停下来》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在这个时期,法斯宾德带着他的剧本《卡策马赫尔》找上门来,请她出演里面的一位小城的歌唱家。两年后的1971年,她向他求婚。她和他一起合作拍摄了《四季商人》、《一年十三个月》等多部电影。这段婚姻结束后,她来到巴黎,在科克托的一部电影中扮演女王。在蒙梭大道5号,伊夫•圣•罗兰直接在她的身上为她裁剪出一条美妙典雅的裙子。她在巴黎穿着那条裙子初次登台,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后来她与让•雅克•舒尔住到了一起,两人相依相伴,直到现在。
《英格丽•卡文》以英格丽•卡文的生平为线索,用“小说”的形式,通过她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顺序的限制,割断了逻辑衔接的故事情节,仿佛法国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一部手法随意的电影。《新观察家》评论说:“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书的最后部分,舒尔最终立起了一个形象:一个歌手,一个女人,这同时也是小说本身的形象,就像一组流动的拼贴画,神奇的,同时又是犹犹豫豫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走近英格丽的歌声与生活,走近法斯宾德、圣•罗兰和舒尔,也就是走近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梦想。”
《英格丽·卡文》读后感(三):如果她不是英格丽·卡文
【读品】罗豫/文
恕我孤陋寡闻,如果不是法国作家让-雅克·舒尔以小说《英格丽·卡文》荣膺2000年的龚古尔奖,恐怕这辈子都不太有可能听说英格丽·卡文这个名字。巴黎、纽约也好,香港、上海也罢,绝大多数影星、歌星和他们身上的服装一样,最时尚,也最容易被遗忘。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英格丽·卡文几张容颜渐衰的照片、几首听起来很难有什么共鸣的歌曲。仅凭这些,实在难和小说中那个神采斐然、华贵神秘的女人对上号。
然而对号入座是一个强大的磁场,稍一放松警惕就要被吸走。站在磁场中心放眼望去,文学只是润色过的八卦、剪裁过的花边、历史的嫁衣。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恳切地仿佛句句是真,又美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里面有民国“人物”的趣闻,也有胡兰成自己的才情。好的历史学家和好的文学家同吃这道菜,应该“您请!您请!”地礼让。
很多时候,阅读外国文学不可避免的文化背景差异,往往会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益处。就此而言,那些荷尔蒙水平不会被异邦文化符码唤起的人,对一本小说永恒文学价值的认定,一定最有发言权。但2000年龚古尔奖的评委们似乎不这么想。当时,评委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古安在谈到评委会的评审意向时说:“2000年,评委会想要评出能够见证即将逝去的世纪的书……”乍一听,还真不知道这是在评什么。其实,女人引领时尚、时尚引领女人的法国,认英格丽·卡文为那个“逝去的世纪”的吉祥物,就像此前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老江湖”君特·格拉斯,都不该算作意外。
《英格丽·卡文》是舒尔二十五年来唯一一部作品,在这之前,他也只出过两本小说。不过能得到“懒鬼作家”的绰号,原因恐怕不止于此。懒到直接拿自己的情人和她所在的演艺圈轶事来写小说,名字都懒得改,也算名副其实了。写法倒一点儿也不纪实,叙事是意识流方式,像极了那些用废报纸拼贴起来的现代艺术。至于他所使用的胶水和点缀,似乎正是那些最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逗到“二十世纪法国”上的名词标签:战争、废墟、舞台、时装、香水、戛纳、巴黎、制片人、妓女、精神分析……法国上流社会那些恶癖满盈的演员、导演、交际花、贵族,也纷纷在英格丽的传记中跑龙套助兴——英格丽在舒尔的笔下真是众星捧月,热闹非凡。这还不够,舒尔对她的描写也是不吝笔墨,上至眼影下至裙摆无不大肆铺陈。舒尔当然不回避英格丽的童年磨难和古怪性格,但他已经站到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边界上,再往前一步,就是公然的雕饰了。
舒尔还算守住最后一步。小说获奖后,巴黎媒体对英格丽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舒尔的兴趣,介绍和专访频频见报。英格丽·卡文敢对记者说:书出版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对那些想了解我身世的人说,去看这部小说吧,那里面没有谎言。对于一个当年大红大紫、如今年老色衰的女人,这本书的确是最好的礼物。作为情人的舒尔,这是最大的成功;但对于作家舒尔,是最大的失败。一个“懒鬼作家”,要是没有遇上英格丽·卡文,恐怕未必会与龚古尔奖有缘。二位彼此间投桃报李,也许会成为一则另类的“文学佳话”。
《英格丽·卡文》读后感(四):“东写西读”之《英格丽·卡文》
如果看一部传记,我们连传主是谁都不清楚,算是很失败的事情,当然,这失败不关我们的事,是传主和作者的失败。本书就是一部典型的传记文学。而英格丽•卡文这人是谁,有多少人会知道?在网上搜索一下,也只能找到此人的几张照片和几首MP3而已,据说,是位曾经很红的歌星和影星,德国人,后来一直在巴黎生活,仅此而已。按理说,本书可以算做很失败。
问题的关键却不在这里。先不说这本书曾经获得过2000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虽然这奖已经足够显赫了,但也不足以说明这本书有多成功。一般说来,现在去书店里看,哪本书是没获过奖的,腰封上满满登登地写着,容易让人麻木。也不要提这本书作为传记来讲,其资料有多么翔实。我们连英格丽•卡文这是谁都不知道,关于她的事情,又关我们什么事?真正能体现出本书价值的,真正值得我们深入进去阅读的,倒是本书的描写功夫,以及,弥漫于全书的,一种慵懒而浪漫的气息,这在其他传记文学中是很难看到的,却叫人沉醉得很。
“她的身体就是音乐。她和她的影子就像转瞬即逝的生动的象形文字,面对这幻影,我们混乱无序的生活好像不存在,历史,她的和我们的历史消失了……把这个昙花一现的痕迹留在了舞台上。”像这样浪漫而深情的文字,组成了全书对英格丽•卡文的叙述。甚至,全书开始的那一段,对于4岁时的小英格丽•卡文的描写,都有了一些幻想与传说的味道:1943年,四岁半的美丽小女孩“一只手抚摸着西伯利亚兔皮大衣的扣眼上吊着的那只白色毛皮绒球”,对着几千名雪地中的德国士兵歌唱,而空气中,除了歌声以外,就只剩下白雪掉落的声音。这哪里是什么传记的写法呀,分明就是一部长长的情书。
事实的确如此。本书的作者,让-雅克•舒尔其实是英格丽•卡文的丈夫,作为一个作家,在25年的时间里,他却只写过唯一的一部作品——《英格丽•卡文》,好像命运只是安排好了,让他积攒起所有力量,为他的妻子和他们的爱情,写作一部长长的纪念情书。在他的笔下,他的妻子具有了一种华贵、超然而神秘的气质,而关于英格丽•卡文的所有事迹,全都成了最直观、最善良、最充满感情的主观记录,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不管是演艺界的华丽,还是巴黎上流社会的风情,全都成了一个女人的陪衬,也成了,一个男人表达爱意的背景。
作为一部传记,作家采用的却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仿佛沉醉了自己的梦境之中。叙述的顺序,并不是传统的时间,而是变成了感情的流转,是一个被爱情的迷雾蒙住了眼睛的男人,在醉眼中所见的,关于爱情的记忆。他仿佛一直站在一旁注视着她,收集关于她的一切片段,她的天赋,她的痛苦,她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都成为了他刻骨的记忆。而现在,他将这一切写了出来,英格丽•卡文在本书获奖之后,对蜂拥而至的记者说道:“书出版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对那些想了解我身世的人说,去看这部小说吧,那里面没有谎言”。而此后,按照浪漫一点的想法,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一个曾经辉煌的演员,他们,应该携手天涯去了,他是她的“懒鬼作家”,一生只为了书写她;她是他的最大骄傲,一生被他仰望;但到了最后,他们互相成就了对方,爱情完美到如此程度,真是很好了。
《英格丽·卡文》读后感(五):平底锅与百合花
摘自《天山网》 作者:洁 尘
我不敢肯定我有没有听过她的歌;但可以肯定的是,之前我肯定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她是英格丽•卡文,而他是让-雅克•舒尔。这本译林2007年12月版、金龙格翻译的《英格丽•卡文》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作者是让-雅克•舒尔,传主是他的妻子、德国歌唱家英格丽•卡文。
我阅读这本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而这两个原因其实跟作者和传主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个原因是《英格丽•卡文》是2000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另一个原因是英格丽•卡文的前夫是德国电影天才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而这部书里,涉及了不少关于法斯宾德的故事。
我之所以说不敢肯定我有没有听过英格丽•卡文的歌,那是因为我应该是听过的,但我完全没有印象了。英格丽•卡文和法斯宾德曾经合作过包括《四季商人》在内的好些部电影,我应该是看过和听过的。现在,我的碟柜里就放着一堆法斯宾德的片子,包括《四季商人》,但我似乎没兴趣抽出来温习并确认一下。
应该说,我对这个英格丽•卡文没有什么兴趣,虽然她曾经是著名的同性恋者法斯宾德的妻子,这个身份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让我想象一下的话,最美好的英格丽•卡文应该跟罗密•施奈德气息相通吧,一个混合了柏林和巴黎气息的艺术家。但在我的心目中,法斯宾德的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主演《莉莉•玛莲》、《玛丽亚•布莱恩的婚姻》的汉娜•许古拉。
应该说,在看了这本传记体小说之后,对传主英格丽•卡文没能产生兴趣,应该归咎于让-雅克•舒尔。这本书,我前前后后看了有半个月。封底摘录的国外书评中有一段说,“它用魔魇法迷惑你,使你陷入流沙泥潭,用甜言蜜语哄骗你,就好像一种乡愁……”甜言蜜语我没读出来,但流沙泥潭却真是那么回事。有书评家说,这部书有很多种读法——20世纪70年代纪事、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但对于读者来说,它就是一幅时空倒错、意识横流的拼贴画。书里有一个女人说,“英格丽是女歌唱家中的保时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女歌唱家意味着高档和速度。其实,《英格丽•卡文》一书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个特点——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时尚文化圈的梦境般的扫描以及快速剪切拼贴的叙述方式。
断断续续看这本书的半个月里,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经常不太明白作者舒尔在说什么,就仿佛是电视出了故障,很多时候只看到屏幕上的一张嘴在不停地一开一合,但听不到声音。偶尔,一两句话或者一两个词汇又飘了出来,被我抓住了。这些话里面有关于女人的,“无法抵御诱惑力的女人都是些发育迟缓的小女孩,只需要在多年之后把它衔接起来,这种诱惑力已经记录在身体里面,从头到脚。”也有关于法斯宾德的,“他这种表达感情的无力,他整个身体对世界的倾听,他像个动物一样的沉默、不幸,这就是他的命。”还有一个挺绝妙的关于英格丽•卡文的比喻,“平底锅与百合花”——主妇和荡妇……
这本书那流沙泥潭的感觉真是有点奇妙,它有点下蛊的意思。我每天翻几页,看了半个月,读完了也不知道英格丽•卡文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但这个过程真挺有趣。这样的读书状态似乎有一种坍塌、融化的趋势,这种坍塌、融化是冰淇淋似的,甜蜜的、陶醉的、但又是令人腻味的令人眩晕的。
让-雅克•舒尔说他更喜欢北方城市那种庄严、寒冷、清苦、与世隔绝的味道,这让我莞尔。这个法国人!应该说他在向往庄严、寒冷、清苦和与世隔绝的同时,在笔下筑造了一个炎热、混乱、奢靡和人声鼎沸的世界。这种反差呈现在了《英格丽•卡文》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部小说那古怪的文本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