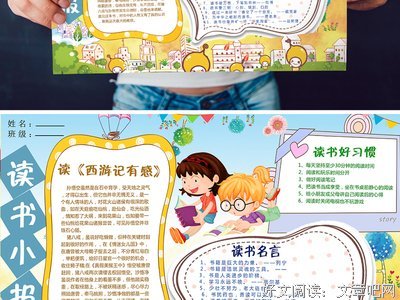《名门》读后感精选
《名门》是一本由[英]谢福芸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名门》精选点评:
●当时的中国人在当时的家国巨变之下的一系列真实反应和实实在在的欢乐,憧憬,忧虑和惶恐。
●对这样类型的书欲罢不能!
●浮光掠影式的写作。有非常好笑的地方,也有动人的部分,大多时候,给我的感觉是繁琐以及浅。
●感觉挺好看的,值得花时间阅读
●2018就快过去了,可以自豪的说这一年没有虚度。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读书是永恒的主题。有些事情不可预测,只有读书从未跑题。
●大約是當時讀《尋找·蘇慧廉》的時候知道的這一套書,彼時好像剛出版不久,買了放家裡一直沒有讀。像是回憶錄,也像是一本民族誌,一些有趣的故事大約還能當作史料來看待,這套書的主編沈迦說,「有意戴上的面具,不經意一個側身,還是仿佛驚鴻一瞥」(頁384),確實是這樣。頁122,「朝廷幹城」大約是「朝廷幹臣」?
●多亏沈迦老师在喜马拉雅上发布了听书,让我利用好时间能听到这部历史。很惊讶觉得自己离谢福芸(她不断口称的:外国人)更近,更像现在,来反观离我们远去的先祖和文化。她完全没有在晚清的官宦家庭里强行推销基督教,而是非常尊重地融入中国家庭。她的爸爸可是大名鼎鼎的传教士苏慧廉。听完了。甚好
●没有想象中的好
●谢福芸写的好,译者的文笔也很优美,从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更迭背景下的中国。不过文中对翁同龢(宫大人父亲)的赞美跟历史还是有差别的,翁家出于和李鸿章的私怨,对各种洋务运动都是反对的
●很好看的书,值得一看哦。
《名门》读后感(一):英雄总是前仆后继,绝不会消亡
在读这本书之前,中国近代史,或者说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我而言一直是概念模糊又心之向往的时代。
旗袍,洋装,中西交融,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结合体。
在读这本书之后,那段历史仿佛生动起来,不再是历史课本上干枯晦涩的介绍,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优雅,谦卑,善良和传统,改变了我对它的理解。
“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曾这么说过,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谢福芸把中国视为了她的使命,她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生活过,和中国的年轻人结为亲密的朋友,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她对中国的热爱和尊重,而同时她又是客观的。
虽说书中的人物都是当时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家族,但她从生活的细腻之处去描写,比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在保持着传统辈分和严谨阶级规矩的同时,又不乏逗趣,活力,亲密,相互扶持和善良。
令我感受更深的是,谢福芸的修养,她尊重他人,尊重不同民族的信仰和习惯,有着站在其他人角度去思考的同理心,但她也始终保持着自我独立的观点和坚守。也正因如此在她在中国有如此多的挚友吧。
记得在今年的疫情之前我还去参观了五大道博物馆,看到了民国时期在五大道生活的人们家庭内部的摆设,从起居室到餐厅,都是考究而细致的。所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更有代入感,故事里的她在天津的中国家庭里生活了数月,从细碎的生活里窥探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清政府的瓦解,人心惶惶,动荡而混乱一直是我对那个时代印象,但看了她讲述的故事,发觉大多数老百姓依然要在动乱中努力过自己的生活,读书,劳作,只不过不能再用以往的观念来看待了。
故事以励诚的来信结尾,信里讲述了励诚的父亲宫大人在临终之时对他的告诫:“记住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我只能留给你这则信条,你要像珍惜我们家族的荣誉一样珍惜你的姓名。”
励诚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惦记着人民的福祉。”
英雄总是前仆后继,绝不会消亡。
《名门》读后感(二):名门之下
《名门》一书的英文原名是Two Gentlemen of China (也有译作中国绅士),立马让人联想起莎翁早期的喜剧作品Two Gentlemen of Verona(维罗纳二士),不知道谢福芸在给本书起名的时候是否有意模仿莎翁。本书描摹的对象,与其说是中国二绅士,不如说中国的两个士绅家族,甚至很大篇幅用于描写士绅家族中的女性,因此,“名门”的中文译名可以说是很妥帖的。
书中可以瞥见谢福芸(书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应是苏福芸,作者嫁给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之后从夫姓谢)一家从英伦带来了如同唐顿庄园里的主仆情谊:苏家在时局动荡之时带着中国仆从一起进入英使馆避难;作者的父亲汉学家William Edward Soothill不让妻子辞掉一个厨艺不佳的山西厨子。在谢福芸的眼中,中国仆从不论是对外国主人还是中国主人都一样地忠心耿耿,这自然是英国阶级社会与晚清中国阶级社会的一个融合点。
苏福芸对中国文化无疑是洞悉的。她说,“中国人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他们黑色的眼睛可以洞察一切伪装,当他们发现谁已经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时,就会出自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称颂这位“君子”的智慧”;“在中国,要把‘家族’放在首位,民族和社会只能任凭雨打风吹去。”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已观察到南方人比北方人在新生事物比如现代教育上更强的接受能力。
苏福芸对中国局势的认识也存在基于其自身阶层的历史局限性。她将庚子闹拳的暴力与对外国人的敌意仇视完全归咎于少数狂热分子的疯狂,而不去反思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情绪的激化,不提及彼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而导致民怨沸腾此类更深层的社会制度及经济问题,不得不说略显狭隘,与中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之分歧如出一辙。中国的教科书中总是对法国大革命一味持赞扬的态度,认为是翻天覆地开辟新世界的壮举,而国外学者则很早就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暴力与血腥,倾轧与专制。
在苏家与两个中国士绅家族的往来中,有零星对晚清女子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位遗孀创办了女子学堂并收养孤儿,在山穷水尽之际,向地方长官写信求助,未得支持,无奈之下只好以命要挟,若在指定时间内援助不能到位就以死抗议。最终,援助没有来,这位女子如承诺般以死明志,抗议政府对女子教育的轻视,让人唏嘘不已。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以死抗争的故事,但不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清白,像这位女士,为不相干的人,为非传统意义上忠君爱国之事以死明志,既非出自君之意、父之教、夫之言之人,是罕见的,或者说,这般流传下来的还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是稀少的。
一朝天子一批名门,名门之下是无数的普通人。尽管苏福芸对书中两个士绅家族推崇备至,我却始终被那位籍籍无名又寂寂而终的女士吸引了目光。世道维艰,一个普通人选择做正确的事,本身就是一件不普通的事。
《名门》读后感(三):异乡人的乡愁 ——有关谢福芸和她的中国题材小说
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译本,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案般寻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
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
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由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宫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获得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是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这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中文作品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他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物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没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笔下的中国故事,“我”都亲历其中,与书中被描述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异样目光来关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种有着强烈个人感情投注的文字,用在小说的笔法中,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转用英语写下“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中立的立场,投入小说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
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物,谢福芸描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稔。这种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经在书中描述他的中国旅行的感受:
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心态。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妪。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女中,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也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
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与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对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状态观察和描写的作品。
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第二部小说,她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大学者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谢福芸在书中说:
我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国家的一小部分的残酷和懦弱就玷污整个国家吗?如果我们那么做,那我们也同样要因为其他人的英勇和忠诚而向这个国家致敬。我们自己也不同样希望别人这么评判我们吗?
她所竭力描述的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度里的故事,竭力用笔墨还原她所认识的,跟这片大地相关的所有人。“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
而《崭新中国》,其实我更愿意称之为“英勇的国度”,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
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捞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创办人和继任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也在北平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
谢福芸写作的四部关于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她的汉学家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生活过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他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甚至他们自身,都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
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来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虽然她不属于这里,但这个异乡人,把她最浓烈的乡愁全部书写进这四部作品,用文字构建了一个优美而真实的国度。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曾经提到文字的力量,用在此处正好可以印证百年前谢福芸所做的书写的意义:“正如伟大的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写这些诗句的我不在了,读这些诗句的你们不在了,但写出那些诗句的语言和你们用它阅读那些诗句的语言却将留存下来,这不仅是由于语言比人更为长寿,而且还因为它更适应于突变。”
《名门》读后感(四):当两种文化初相遇 ——读谢福芸“旅华四部曲”有感
金丹霞
一
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每每回首,常觉心惊: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从身体到心灵,都该经受了怎样的“风刀霜剑严相逼”?
亲历那个时代的英国作家谢福芸在其处女作《名门》开篇即说:这场变动,使得中国人也好,在华的外国人也罢,人生由此而改变。
这本1923年出版于英国的作品,在面世95年后,终于辗转归来,回到字里行间深情描写的故土——中国。一同回来的还有谢福芸的另外三部作品——1929年出版的第二本中国故事《中国淑女》、1938年出版的《崭新中国》、凭借回忆写下的最后一本《潜龙谭:北平新事》。沈迦主编的这套四卷本《谢福芸旅华四部曲》,2018年5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谢福芸,生在宁波,长在温州,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又重返中国。一生六次访华,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父苏慧廉,著名传教士、汉学家,在温州定居20余年,后出任山西大学堂校长。
虽然谢福芸的作品被冠以“小说”之名,但据沈迦考证,除了人名虚构外,其他几乎全是非虚构的。她客居的“名门”是翁同龢家族,她记述的女校是民国北平名校“箴益”……也就是说,她以纪实的笔调记录下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她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二
一百年前,随着鸦片和军舰一起到来的,还有一批批“洋人”。他们漂洋过海,来到神秘的中国,并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字。
这些文字遭到谢福芸笔下的中国青年励诚愤慨地批判:“很多洋人的笔下,对中国人都存在着严重的偏见,比如说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不敢说真话,只知道养猫,喂老鼠,像兔子一样挤在一起过活。”
上世纪三十年代,差不多和谢福芸同时代的林语堂出版了《中国人》一书。在引言中,他表明自己写这本书的背景即是有太多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误读。他引用了一位署名为J.D.的作家发表的文章《英国人在中国》,描述了那些在中国的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和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
——不幸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
所以,迫不及待的,我翻开谢福芸的书,我想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出生在中国且度过了童年岁月的外国人眼中,会是什么样?
三
“从我们西方人的角度来说,没人觉得中国的老房子有多舒适,要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太多了。”
“我并不了解应当如何遵从中国的那些礼仪,生怕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就冒犯了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从谢福芸笔下,我处处看到的是两种文化相遇初期的小心翼翼,彼此试探。当然这相遇的前提是愿意满怀善意地去了解。彼此之间都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从生活习惯、服饰穿着、日常饮食直至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双方的一惊一乍让今天的我们看来,尤为会心——
“在我后续做客的日子里,宫家的姐妹们或那些老妈子们,常常伸出手来努力抚平我头上的卷发,为的是达到她们认为好看的标准。”
“我随身带了一件深蓝色的丝绸浴袍,结果被宫伯母夸赞成是我最好看的一件衣服。每当家里有贵客来访,宫伯母就会喊上我,并且让我穿上那件蓝色浴袍。当然,我都照做了。当她向客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说我的这件衣服可是我的衣橱里唯一一件看上去不那么古里古怪的衣服了。”
特别可笑复可叹的是,谢福芸和她的中国结拜姐妹花儿怀着同样的好奇,决定同睡一床的第二天早晨,“老妈子们在门外踟蹰不安,对花儿的命运感到很焦虑。她们一定在想:小姐她还活着吗?那个‘洋婆子’有没有在晚上变成可怕的狐狸或猴子?当她们看到花儿一切正常的时候,纷纷舒了口气。”
谢福芸的笔调轻松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她也在和宫家兄弟姐妹们亲密无间的嬉戏打闹中,纠正着自己对中国人家庭生活的许多成见,“一时都有点缓不过神来”。那温馨友爱的氛围让她恍然觉得这就是大洋彼岸自己的家。
好多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和行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眼光打量之下,呈现出另一种面目,于细微处显出了作者的敏锐——
“中国人可以造出世界上最美丽、最精致的园林,但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却不懂得如何去欣赏绿色的原野、繁茂的花丛、整齐的草坪、林间的小路。”
“中国人并非不爱花,他们更偏爱娇嫩的花朵,更偏爱精心呵护的花朵,更偏爱一花独放而非百花齐放。”
“中国绝大多数的官僚,看起来脸色都很暗淡,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普遍不喜好运动,哪怕只是走走也不乐意。”
“中国人是一个很讲理智的民族。只要他们还平平安安地活着,只要没有受到剥夺生命的威胁,他们会表现出强大的耐性,什么都不会去做。但是,一旦给他们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他们也会像死了兄弟一样愤而反抗。在这点上,其实与我们外国人是一样的。”
“中国人的很多礼数,在很多方面是一些不必要的矫饰。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出于面子。”
……
文化首先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上,行为的方式上。谢福芸的眼睛如一面镜子,让今天的我们仍不得不反观自省。
四
谢福芸最打动我的是她对于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她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女性,她和她们交谈,教她们英语,成为她们的姐妹,走入她们的内心。
她同情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带着终身不能复原的跛残。想到她们畸形的脚,以及每走一步所需要承受的疼痛,“中国女人能够步行出门,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她疑惑年轻的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外国的妈妈们那样,每天带孩子们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她感慨年轻人也许最羡慕西方的,就是独立的家庭生活。年轻的丈夫可以免受家长的干涉,从而学会如何去爱和尊重自己的妻子。
她鼓励困惑中苦苦求索的新女性,多少代人的脚一直都被裹着,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习惯放开束缚的感觉,才能重新学习直至慢慢习惯像自由女性那样地行走。
林语堂曾断言: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要宽广博爱的情怀。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整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同伴有着深情厚谊,并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觉得谢福芸担得起这样不同寻常的使命。
这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女性,她和母亲甘冒危险,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眼皮底下,将中国朋友的财产安全转移,不负所托;
这是一位真诚睿智的女性,她对清廷高官直言不讳: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大清的官员,你是一个中国的官员,你的首要任务是对你的国家负责,而不是对一个皇朝负责。
这是一位内心坚定的女性,尽管她受到热情周到的礼遇,却始终坚持理性的认知: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人坐到了我旁边的座位上,又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了我的手上。我握住了那只手。我知道那是一只中国人的手,圆润的手腕,纤细的手指。这不禁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曾经握过的另一只手,那是我天津的中国妹妹花儿的手。那次也是这样平静而坚定的握手,没有犹豫不决,但胜似千言万语。”
《中国淑女》中这段谢福芸和吴小姐握手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这两位相识不久的东西方年轻女性,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但并不妨碍她们默契地执手相握。我觉得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我从中读出了意味深长。
好的作品总是历经时光磨砺,却越发显出它的价值。当前中美贸易战骤起之际,中国仿佛再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口。此时此刻,读谢福芸的作品更是别有一番感受。那么,让我们来读读这段话吧——
“解决民族矛盾和争端的途径也许恰恰来自当事双方本身,世间很多重大事务其实都是这样。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基础一直都在那里,它就是我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欢笑与泪水,遗憾与恐惧,亲情与友谊,一起造就了人类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