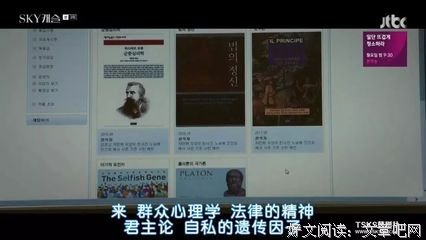君主论读后感摘抄
《君主论》是一本由(意) 马基雅维利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242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14-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论》精选点评:
●结合当时时代来说,这本书实在是太先进了!
●此译本的翻译比较注重文字的优化,调整其文字偏向文言化,算是一个特色。与其他译本比起来,各有千秋。
● 狮子无法躲避陷阱,而狐狸无法保护自己抵御豺狼,因此一定要像狐狸才能够辨认陷阱,一定要像狮子才能够惊吓豺狼。最善于模仿狐狸的人是最成功的人。
●十六世纪的自省力。治国,还需君主自身的智慧。
●马基雅维利真是个狠角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学畜生活的一个小型里程碑(不是)。一百年后我也喜欢小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实说,比较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思想明显不如中国韩非子的法、术、势完整深邃。在西方被千夫所指的《君主论》其实不过是说出点实话罢了,让伪善的道德统御一切的西方中世纪真是虚伪的可怕。
●勉强读完,没怎么看进去,就模糊记得讲一些政策道理。
●借了书,祝我快点读完它!更新:我看不下去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君主论》读后感(一):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推崇的是一种君主专制,其构成要素除了最核心的符合标准的君主(如顺应民心、精于诡计、懂得何时慷慨何时吝啬、具备军事才能等),还需要常备的自有军事力量(呼之欲出的现实主义)与良好的法律。若说柏拉图觉得政治(国家)是为了让人得以过更良善的生活,马则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和平稳定——因为人性自私会自相残杀,故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的道德基础被马给切断了,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君王。所以可以说,政治在马这边都被降格了。
《君主论》读后感(二):一位爱国的人写的政治书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字字珠玑。
为了拜读这本闻名已久的大作,我在看的时候还专门拿了支笔打算做笔记,看到最后一页才发现此书堪称全程高能,哪里需要做摘抄啊。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把中世纪西方政治一直遮遮掩掩的那点事全写出来了,而且说的一针见血,十分到位,与传统的伦理,美德相悖的其实就是后几章的实话:作为一名君主,重要的是保有自己的政权,其他的残酷手段,该用的时候就得用,至于百姓,军人,贵族,只要能够巩固发展政权,都不用看着这些人脸色办事。
这本书被称为西方政治学的始祖,的确实至名归,别说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算是在同时期的中国,这本书也足够惊人了。(至于作者与法家相比,这个鉴于不了解所以不说了。)
虽然过段时间可能就把书上写的东西忘完了,但现在对于这本书的政治学我只能说受益良多,它完完全全地诠释了中世纪的一位君主应该如何做,为什么要如此做。对外邦的势力,对本邦的军备,以及对于自己的名誉和大臣们的溜须拍马,都给了详解。具体的非专业人士,不予评论,豆瓣那么多书评,该说的也都说了。
马基雅维利写这本流传后世的书主要是为了献给美第齐家族,此书最后一章---为解救意大利免于蛮族蹂躏进一言,为意大利的的安危而焦急,希望美第齐殿下能够重整军备,完成建国大业,其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整本书并不是满口道德文章的劝告,而是明白大胆地将一名君主应该遵从的原则一一告知,再借以意大利之现状鼓动人心,以期完成意大利的统一。
在我看的那本书序言中说最后一章并非将其格局缩小,然而在我看来,最后一章反而将其格局扩大了,将其从剖析政体,执政为君的实用手册上升到了民族情感的自白,尽管其情感只是作者本人的。
在我看来,马基雅维利非但不是凶狠残酷的,在《君主论》一书第五章提到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邦将永不服从于君主统治,该书不少地方还提到民众支持的重要性,以上种种足以表明,此人只是在剖析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罢了,并非专制独裁的捍卫者。
也许是我思维太过奇葩,居然能在一本论述君主权术的书中看到人性的光辉与些许温情。可能是我觉得一个有着如此激情的爱国者如此深爱祖国土地的人,不会将自己的同胞视为牲畜驱使。
《君主论》读后感(三):马基雅维利谈为君之道
马基雅维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政治的视角,那就是去道德化的视角。他把伦理和政治分开,因为政治是,必要的恶: 不发动战争就日暮途穷的时候,战争是正义之战;不拿起武器就走投无路的时候,武器是神圣之器。
马基雅维利谈到君子必须以自己政权的稳定为重,不要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去攻击小国家,不要让外国雇佣兵帮自己打仗,不要凡事都听底下的意见,不要优柔寡断。尽量让人们觉得君主拥有良善的品德,要有自己的军队,要亲贤臣远小人,要把不好干的活分给下属,让他们承担不好的名声,以避免民怨沸腾。
马基雅维利的书献给的是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我在《美第奇家族》(又名《翡冷翠名门》)这个剧中见过。这个美剧虽然情节进展很快,但可以帮助你理解佛罗伦萨以及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强大的美第奇家族。看完这个美剧,再来看这本书,很多东西就更好理解了。
摘录最后一段热血沸腾的呐喊与呼吁: Your illustrious house take up this charge with that courage and hope with which all just enterprises are undertaken, so that under its standard our native country may be ennobled, and under its auspices may be verified that saying of Petrarch: Virtue against fury shall advance the fight, And it is the combat soon shall put to flight; For the old Roman valour is not dead, Nor in the Italians' breasts extinguished.
但愿殿下杰出的家族本着义不容辞的情操,怀抱义无反顾的希望,担负起这一项重任,好让我们的祖国在您的旗帜下显得尊贵,在您的吉星引导之下应验佩托拉克的诗句:
美德反击暴虐,战争结束很快
古罗马的勇气还在亚平宁的血液中流淌,
意大利人向往的这份荣耀在胸中还在激荡。
《君主论》读后感(四):马基雅维利:喜剧诗人与政治哲人
毓秀
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里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性的开创者,何谓现代性,这个概念耳熟能详但一直没有定论,在我看来,所谓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过渡亦或者一个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不过是现代性的附属物。现代性的核心理应是相信人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审慎和决断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随虚无缥缈的命运随波逐流。现代性所关注的乃是《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所讨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自己的政府。作为一名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要写作《君主论》进献于翡冷翠的僭主美第奇公爵,其最在意的并非个人的荣辱,而是变局中的欧罗巴的历史出路。
而马基雅维利观念的根据,首先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的批判上。对于当时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样做不但有在理论上溯本清缘的作用,更有现实的考量。自10世纪末克吕尼运动对教会的改革以来,教皇一跃达到了欧罗巴世界权力的顶峰,但这也导致了教会过多地参与世俗,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使得说意大利语的地区被外来的君主争霸,久久不得安宁。《君主论》里他盘点历代政治得失,认定教会对意大利的分裂负有首要责任,教会既无法实现一个世俗国家的职责,又总是越俎代庖,这是他将宗教从政治当中放逐出来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基督教败坏了公民的德性,是罗马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
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政治观念里,政治永远与德性相伴,政治家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德性的完善,政治本身并非自主自足的场域。希腊哲人与基督教父共享一个目的论世界观,都认为世界统一于善/上帝,事物由低到高乃是对更完美的事物的模仿与向往,世界的本质潜藏在事物自身当中,等待其显现。所谓存在,乃是本质的实现,是本质在实在界中真实的出现,因为在实现之前,本质原是一个可能性而已。当本质从可能性的层面进入实现的时候,它才真正地存在了。草木之所以成长为草木的样子,是因为种子潜藏了草木的本质;动物之所以发育至成熟体的样子,乃是因为动物自身潜藏了成熟体的本质。而人,就是趋向至善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认为,人是城邦的动物,人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城邦的自然秩序,人参与政治是为了德性的实现,是为了完善自己。而在奥古斯丁眼中,人是上帝的羔羊,一切所行都应趋向上帝。他在《论上帝之城》发展出了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念,区分了属世和属灵的场域,将属灵的世界置于属世的场域之上,人若是参与政治乃是为了救赎,是从此岸世界走向彼岸世界。不论希腊哲人还是基督教父,政治都不是自足的场域,都是顺从于某种目的,以某种应然来规范实然,对政治的研究首先是规范性的。
一如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最早引入了第二位演员,这使得古希腊悲剧从带有颂歌性质的一人表演转化为表现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文学作品。喜剧诗人马基雅维利改造了“德性”(viture)的意义,将之还原为能力,将政治中性化,政治从理想降格成专门的一项技艺。将道德/权利进行自然主义的转换,还原为某种能力并非马基雅维利的首创,马基雅维利在欧罗巴世界革命之处,乃在于他如实地指出政治自有其运作之规律,使实证性的政治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尽管他本身是出于敏锐的洞察力而非采用实验科学的手段得出他的结论。
李猛转引施特劳斯的话说过,“马基雅维利不像修昔底德的作品那样令人感到悲凉(sadness),我们可以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找到喜剧,戏仿和讽刺,但却似乎找不到悲剧因素。但既然人的生活并非只是喜剧,那么人性的一个侧面就始终处在马基雅维利的视野之外。那么,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不能让我们感到修昔底德式的悲凉呢?施特劳斯认为,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没有对“普通”事物的神圣感。没有这种“神圣感”,悲剧就失掉了它的自然基础。”
充裕的理性却缺乏对人世的敬畏,导致他彻底解构了加诸政治之上的诸多应然,将赤裸暴力从诸般限制中解放出来,从此无所顾忌。在马基雅维利的语境里,政治不再与中世纪自然秩序的美好世界挂钩,而是事关生死存亡之大事。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开端乃是生存与安全,而其终端乃是善与正义。马基雅维利保留了开端却忽略了终端,亦或者说在他笔下,政治的开端既是目的。人参与政治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完善自己,而是诉诸于某种必然性,即寻求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必然性,统治者应对时事的必需(necessary)。
马基雅维利对必然性的强调建立在相信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预设上,而在他的语境里,所谓的命运,指的就是政治。弗里德里希·希尔在《欧洲思想史》里认为:“他接受方济各会属灵派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变趋势是越变越坏,政治科学只能设法使列国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中解脱出来。各种政治理论便以世界历史为舞台,进行各种试验,看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当然,重要的是有真正受过良好教育又十分能干的人来掌握,通过宗教、法律和军队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大众都能享受幸福。”
在解构完一切以后,国家理性的出炉便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意大利语是Ragione di Stato——英文是reason of state,中文也翻译为国家理由)。在马基雅维利死后二十年,也就是1547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焦万尼·德拉·卡萨才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术语,但是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里完全包涵了如下观念:“国家/君主为了行善,必须能够作恶,必须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强势和狐狸般的狡诈;为了谋取公共福祉和保存必要的权势,以最终保存和发展更大的美德而对付邪恶,掌权者在应对时势的“必需”时可以运用不合法律和寻常道德的手段,可以无视宗教、道德和司法的限制。”
马基雅维利人为制造了政治与日常生活的不同,抑或者说政治中的公共道德与政治家私人道德的不同,从而将政治的视野从动机论转换到后果论,对政治家的发问从“汝所欲为何”转换到“汝所行结果如何”。在马基雅维利之后,便是霍布斯按约建立的利维坦,国家以自身为其合法性,国家而非上帝成为道德合法性的源泉。
政治哲学是历史的发明,同时也在发明历史,其所关注的乃是如何规范政治来规范故往今来,今日耳熟能详无甚出奇的观念,在彼时却有开天辟地的涵义。因此我们在讨论某种政治哲人理念的时候,总是绕不开对观念谱系的梳理,马基雅维利亦是如此。更何况一个人的经典化往往是层累而来,在话语的传播中容易失真,不还原历史也自然无从理解其价值。说到底,所谓意义同样是人为制作的技艺之一种。
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之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原因在于平民/步兵取代了贵族/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不单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扩大化,同时也象征着欧陆贵族阶级的没落。对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的发明,而频繁的战争则是中世纪的自然状态。战争虽说都是残酷的,但中世纪的战争乃是贵族之间的竞技,如同春秋时期,参军乃是少数人的荣誉和特权,其目的乃是恢复某种秩序。因此战争固然频繁,其过程对平民的侵扰较小,以对方服输、屈服为目的,不论胜负双方都保留着各自的尊严。服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
然而当战争将平民也裹挟进去以后,服兵役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战争的残酷性骤然加强,不但对平民的欺损加大,仿佛绞肉机一般将国家的气血吞噬干净,更是改变了战争规则:胜利成为最高目的,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战争从游戏变成读博,赢者通吃,败者输的倾家荡产。所谓的和平,降格为暂时性的停战,为下一次更猛烈的战争休养生息。
马基雅维利所置身的时代,正是中世纪与近代的转折点,他眼前是英法百年战争的落幕与封建骑士制度的崩溃,他身后是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觉醒,欧罗巴从春秋贵族的车战游戏步入战国平民的血肉屠宰场。陆续登场的绝对主义国家之间的生死场,从喜剧诗人的曼陀罗中召唤出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而马基雅维利无可奈何地用他的笔为这种竞争的正当性正名。马基雅维利的观念创造了历史,但其本人不过是揭穿了皇帝的新衣,如实描绘出了现实。他所传授的秘传心法并不见得比后人更加高明与诡诈,然而在象征的世界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秦始皇并不比后世的暴君在作恶上更有想象力,他之所以被唾弃和崇拜,无外乎他是首开恶例者。是以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恶性的军事竞争,破坏了中世纪/春秋的自然秩序,仿佛癌细胞病变,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怪兽进入了黑暗森林。为了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供应常备军就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收税就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就需要打压贵族的地位,破坏地方自治。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与贵族议会被不断打压,多阶级并立的封建社会扁平化,向直面王权的原子个人社会迈进。
在东地中海肆意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西欧列国现成的模版与最好的教师,从地理上最近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开始,君侯们争相充当实证主义革命的排头兵,后来者纵使不乐意,为了生存也不得不群起效仿,结果正如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里所说:“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集权化君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自由的封建国家被对峙的利维坦取代,浮士德挥舞着他手中的铁棍,希望以炼金术来恢复国家的元气,然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使顺民提前了衰老的进程。
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视野,不难发现这样的历史进程总会在不同地域重复上演,当整个政治生态恶化,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解构了传统的枷锁和防火墙,解放了自由的才智和无边的欲望,对赤裸权力与工具理性日益崇拜,相信它们无所不能,之后的必然结果是虽然能获得短暂的利益,却不得不因为对手日渐无下限而疲于奔命。这仿佛是打不开的死结,劣币迟早驱逐良币,政治生态愈发恶化,公民因为丧失荣誉而日益怯懦与犬儒,用麦考莱的话说,他逃避危险,不是因为不知羞耻;而是因为:在他生活的社会里,怯懦不再可耻。于是直到有一天蛮族卷土而来,轻易征服脚下民众,然后重新启动这一进程。
但我死后,谁管他洪水滔天,从哈布斯堡家族对土耳其征服机器的艳羡与效仿开始,仿佛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个又一个新的霸国出现,青出之于蓝而胜于蓝。彼时欧罗巴人的心声,仿佛李鸿章在帝国末季的感慨:“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列国角力之所,乃是生育马基雅维利的北意大利富庶城邦。某种程度来说,北意大利是整个欧罗巴的缩影,在全欧洲刚起步的春秋事业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早已预演完毕。这些城邦曾拥有光荣的历史,然而如今却已沦落。在但丁的时代,教皇党与皇帝党的宪法斗争中涌现无数英雄人物,而今却民德败坏,斯文扫地。他们彼此之间依旧争斗不休,却再无能力抵御大国的争霸。
意大利人曾经并非不能保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德国皇帝觊觎北意大利的财富曾多次组织入侵,却被各共和国坚决阻于城下,不得寸进,鳌拜下地域更加辽阔的江南远比红胡子轻松惬意,前者率领数千精锐裹挟着数十万降虏所向披靡,后者却只能在北意大利弹丸之地焦头烂额,毁掉了德国的命运。喜剧诗人马基雅维利如今只能在剧本中追忆往昔,眼睁睁看着看着意大利人在蛮族面前屈膝纳贡,仿佛晚期罗马剧情的重演。共和国早期的德性在对权力无底线的争夺中与党派双方同归于尽,只剩下承载光荣往昔的尸体留给后人惨淡经营。政治哲人马基雅维利根据故往教训知晓未来之黑暗,但意大利众邦已经腐败透顶,无力回头,现实政治又逼迫他饮鸩止渴,总结更精巧的权术以应对权术。
欧洲人能从这条不归路里回头,仰仗于西北欧一角改天换地的变化,然而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