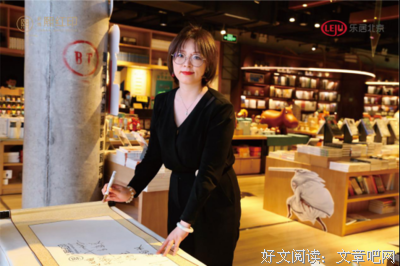《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读后感摘抄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是一本由罗杰·弗莱著作,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精选点评:
●抛开弗莱的艺术美学思想不谈,单就作为一个艺术批评者,意识到并呼吁艺术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支持青年装饰艺术家上,弗莱就足以让人感动。克莱夫贝尔能遇上弗莱这样的老师,并发扬弗莱“有意义的形式”的思想,是他的极大幸运啊。沈老师的导论非常精彩,适合读完全书后再读。
●沈语冰翻译得不错......当然更不错的是弗莱的美学思想。。。。。他之后的艺术批评家,应该没有人能超越他了吧?至少目前还没有。。。。。
●除了艺评外还有对当时人们对艺术理解的微弱吐槽,看着挺有趣的。后三分之一关于对伦勃朗马蒂斯艺术家个人的批评写得挺好的,但到了具体作品的解释上就有点模糊了。前三分之一对于印象以及后印象派的评述有种下定义的感觉。(或者说他本就想对它们进行定义区分)
●弗莱的文章很耐读呢
●喜欢后期弗莱多过早期
●批评的魅力从弗莱的语言里流露
●不走极端的客观派,贴切而又中肯,不似某些偏激的唯形式主义者。很赞同那段话—“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可以产生意义,但是必须依附主体才能产生叙事。”
●克莱夫贝尔的幸运就在于遇到了弗莱这样的老师。
●天,翻译的太烂了!怪不得接触过的海外艺术史研究者都对国内某人评价不高。(mark下,再涉及到这本书就直接去看原著)
●还行吧,有的东西建筑等不是很感兴趣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读后感(一):《伦勃朗:一种阐释》
贴了书中的一篇艺评给喜欢伦勃朗的读者。这里不能贴图,去小站读吧,18张插图哦,在这里:
http://site.douban.com/widget/works/1911999/chapter/11520914/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读后感(二):[译者导论(一)] 后印象派画展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
沈语冰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为《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文版(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所撰写的译者导论的第一部分。它讨论弗莱围绕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撰写的一系列辩护文章,这些文章系统地发展了他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从而为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罗杰•弗莱和他的时代”则联系弗莱的中期写作,着重论证弗莱作为一个形式主义者介入各种社会生活的程度,澄清将弗莱偏面阐释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误解(见《新美术》,2009年第6期)。第三部分,则聚焦于弗莱的晚年论文,探讨了弗莱如何调整与修缮其理论基础,从而将自己从形式主义美学的教条化与学院化倾向中拯救出来(见《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罗杰•弗莱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形式主义艺术观的人,但是,说他是形式主义批评观,乃至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仍然是有理由的。弗莱的形式主义批评观有两个渊源——德奥及意大利艺术史中的绘画形式分析与鉴定传统,以及法国现代艺术批评观——他是第一个将这两个体系整合在一起,并提出系统的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人。
事实上,是法国画家兼批评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在1890年率先宣布“一幅画,在它是一匹战马、一个裸女,或是一则奇闻逸事之前,本质上是一个覆盖了以一定秩序汇集在一起的色彩的扁平平面。” 然而,是弗莱,追随着德尼,在1910年前后的一系列论文中,以其关于抽象形式的“现实性”与“古典性”品质的大胆断言,挑战了当时的模仿性艺术和叙事性艺术的流行标准,从而发动了英语世界对“形式主义”的法典化进程。作为在1910年和1912年将法国新艺术引入伦敦的两届展览的主要组织者,弗莱成为现代主义在英国的代言人。甚至“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这一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术语,也是弗莱的杜撰:“哦,让我们就叫它后印象派吧;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出自印象派之后。”
由于弗莱的名字与20世纪初后印象派的推广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忘记,当他的第一个拓荒式的现代艺术展在伦敦展出时,他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弗莱就一直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馆长;他擅长15世纪意大利绘画,将自己在科学方面的训练转化为一种“科学鉴定”的明显的经验主义方法。然而,收入本文选的一篇写于1894的论文《印象主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mpressionism”),揭示了弗莱从一开始起就急于捍卫现代艺术。弗莱在生物学方面的科学训练可明显见于他对印象主义的科学基础的集中分析,这一点只因其结论而稍有缓和,在这个结论中,他坚持认为美而不是科学才是艺术的最终理由。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冲动,弗莱最著名的还是他的艺术鉴定。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对15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家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分析,第二项主要工作则是出版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谈话录》(Discourses)评注本。弗莱为此书撰写的《导论》(也收入本文选)主要关心的是其历史背景,但也预告了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商标的许多东西。弗莱在为其美学思想奠定一个十分清晰的社会语境的前提下,一开始就讨论“雷诺兹其人”,并用下列一些词汇描述他的“道德品质”:“完整”、“可爱的明智”、“超然”,以及“远离琐碎与狭隘”等等。这些词汇与弗莱及其布鲁姆斯伯里的同道们之后用来定义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态度的那些词汇一脉相承。同样,弗莱断言,雷诺兹将他的美学建立在对作为一种“人类经验表现”的“统一性”的追求上,而不是建立在单纯“模仿的机械手法”上。 最后,弗莱将雷诺兹的理论详细地运用于鲁本斯(Rubens)与凡•艾克(Van Eyck)画作的比较,奠定了弗莱对特定画作的形式分析的方法基础,而这一方法在他后来对现代绘画的捍卫中变得极为高明。
《一篇美学论文》(“An Essays in Esthetics”)仍然是对艺术中存在着独立于被描绘的主题的“设计的情感要素”(emotional elements of design)这一基本的形式主义信念的最清晰的早期陈述。然而,1908年,在弗莱为牛津大学哲学学会所作的演讲《造型艺术中的表现与再现》(“Exp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Graphic Arts”)中,他早已发展出了许多后来出现在《一篇美学论文》中的思想。
从回顾的角度,人们早在《印象主义的最新阶段》(“The Last Phase of Impressionism”)中就可以看到弗莱对现代艺术的大无畏的支持。这一趋势更明显地见于他为德尼的《塞尚》(“Cezanne”)一文所写的译者导言中。在前文中,弗莱将塞尚、高更(Gauguin)之类的画家与拜占廷画家进行比较,认为拜占廷画家为罗马艺术虚弱的印象主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风格,这种风格植根于“对最基本的元素的深思熟虑的调协”之中。同样的观点也可见德尼文章的导言,在那里,弗莱考虑了德尼认为塞尚得益于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断言,并且提出:“不正是埃尔•格列柯在拜占廷的线描传统中受到的最初训练,启发了他跃入一种直接表现的艺术方法吗?” 这一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也适用于《造型艺术中的表现与再现》所断言的基本原理:在“原始”绘画中被认为是缺陷的东西,可以比单纯模仿性的艺术更有利于表现性的艺术。
当然,收集在本文选里的论文,最著名的当属弗莱主持的两届“后印象派”画展,以及为展览所作的强有力的辩护。我曾指出,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乃是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 克利斯朵夫•里德(Christoph Reed)认为,这组文章虽然没有被收录在弗莱后来出版的批评文集中,但它们对于理解弗莱形式主义美学的起源与影响,是至为重要的。作为其思想的记录,这些论文得以在面对来自各个角落的攻击时做出迅速的反应,提供了对形式主义历史发展的无比珍贵的记录。除了在记录弗莱本人的思想发展方面的意义外,这些论文还拥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记录了他的观念首次面对观众时的方式。
这组文章包括:《后印象派画家》(“The Post-Impressionists”)、《格拉夫顿画廊之一》(“The Grafton Gallery--I”)、《后印象派画家之二》(“The Post-Impressionists—II”)、《一则关于后印象派的附论》(“A Postscript on Post-Impressionism”)、《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格拉夫顿画廊:一则辩护》(“The Grafton Gallery: An Apologia”)等。
《后印象派画家》一文的主旨,是要界定“后印象派”这一术语,从而揭示它与印象派的差异。在弗莱看来,“印象派主流沿着记录此前未曾记录过的对象侧面的轨迹行进;他们对于将光影的嬉戏分析为丰富多彩的鲜明色彩深感兴趣;对大自然中早已十分迷人的东西加以提炼。……然而,后印象派画家并不关注记录色彩或光线印象。”此其一。其二:“他们(印象派画家)对于事物现象那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妨害了他们传达事物的真正意义。印象主义鼓励一个艺术家画一棵树,如其在某一刻、某一特定情景中显现在他面前那样画一棵树。它是如此坚持他精确地再现其印象的重要性,以至于其作品经常完全无法表现一棵树;因为转移到画布上之后,它成了一堆闪闪烁烁的光线和色彩。树之‘树性’完全没有得到描绘;在诗歌里可以传达的有关树的一切情感及联想,统统被舍弃了。”
毫无疑问,在后印象派画家中,塞尚仍然是风向标,他的意义被认为是带领后印象派画家走出印象派过份的自然主义,从而为走向表现开辟了道路:“当塞尚想要描绘大自然中为印象派画家所关注的那些新颖面向的时候,他首先会将注意力集中于能产生原始艺术的杰作的那种融贯的、建筑般效果的构图。由于塞尚展示了从事物现象的复杂性过渡到构图所要求的那种几何的简洁性,是如何可能的,他的艺术对后来的画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他的艺术中发现了指南,可以帮他们走出自然主义曾经将他们带进的死胡同(cul de sac)。”
《格拉夫顿画廊之一》是弗莱发表在《国家》杂志上,针对美术界与公众的批评而作的著名辩护。批评中的主要观点认为,后印象派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激烈的反传统中最为晚近、最为暴烈的事件。而弗莱的辩护所采用的策略则是,他断言后印象派画家所反对的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而不是自古——特别是原始绘画——以来的传统,因此,他们其实是真正的传统派——比文艺复兴所确立的传统还要传统。他说:“不难证明,在格拉夫顿画廊展出作品的这群画家,事实上是任何晚近的艺术家团体中最为传统的群体。我乐意承认,他们确实反对19世纪照相式的视觉观念,甚至反对最近400年来陈腐的现实主义。事实上,他们代表了想要超越文艺复兴运动在绘画中所确立的那种过于精致的图画装置的最为晚近的,同时,我相信,也是最为成功的尝试。一言以蔽之,他们是真正的前拉斐尔派。不过,之前的尝试——例如我们自己这边的前拉斐尔派绘画运动——带有某种有意识的拟古主义,而这些艺术家却似乎是在对于现实情境的纯粹必然性的感知中,偶然发现了原始赋形的原理。” 对此,人们当然可以再作评论。但弗莱除此修辞策略外,更重要的是阐明了现代艺术的基本律令,即对个人表达的需求。弗莱指出:
自然,人们立刻就会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艺术家要如此放纵地抛弃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数个世纪里已经赋予人类的所有[绘画]科学的东西?为什么他要任性地回到原始艺术,或者如人们嘲弄时所称的野蛮艺术中去?回答是,这既非任性也非放纵,而是出于必然,假如艺术想要从其自身的科学方式的不断累积的、毫无希望的臃肿中解放出来的话,假如艺术想要重新获得表达思想情感的力量,而不想诉诸拜倒在艺术家危险技艺之下的好奇与惊叹的话。
弗莱这一阐明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对艺术进步说,特别是将艺术进步等同于再现技巧的完善的理论的批判。弗莱的这一批判极其尖锐,但我认为,迄今也尚未失去其合理性:
这里,一个根本的谬误在于,认为艺术中的进步等同于再现自然的技能中更容易衡量和确定的进步。我们所有的艺术史都染上了这个错误,理由极其简单:再现能力的进步是可记可教的,而艺术的进步却不可能作如此轻巧的处理。因此,我们会认为乔托只是在提香那里达到顶峰的绘画技艺的准备阶段,却忘记了每一位艺术家获得一种再现技能,就意味着他既获得了一种新的表现可能性,同时也失去了其他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是弗莱最伟大的洞见之一,也是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最坚固的基石之一,它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在今天也还拥有确定无疑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弗莱重述了他在《后印象派画家》中已经提出过的后印象派与印象派之间的差异。概括起来讲就是:印象派绘画是纯粹感官的,亦即纯粹视觉的,而后印象派绘画则还要回应人类的理智要求。这一点既是对前文的总结,更是对前文的提升。弗莱对后印象派绘画的本质的阐明无疑更清晰了。他说:“现代艺术已经来到了印象主义,在那里,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便捷与精确描绘任何可见的东西,同时也是在那里,在赋予绘画的任何一部分以精确的视觉价值的同时,它在述说被描绘的事物的任何人性意义(human import)时却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并不能从物质上改变事物的视觉价值,因为整体统一于此,而且仅止于此。要赋予对大自然的描绘以回应人类激情与人类需求的能力,就要求重估现象,不是根据纯粹的视觉,而是根据人类理智预定的要求。”
《后印象派画家之二》是弗莱发表于《国家》杂志的第二篇辩护文章,与第一篇为后印象派画家作整体辩护略有不同,这篇文章重在为个别画家的特征辩护。最著名的仍然是对塞尚的评论。他认为塞尚最伟大的地方是在印象派的色彩中见出秩序与“建筑般的规划”来。在《埃斯塔克》(L’Estaque)之类的风景画里,“难于弄清的是,人们究竟应该赞美它为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此清晰地加以重建的、对于辉煌的海湾结构的充满想象力的把握,还是应该赞美它赋予闪亮的大气以如此确定明度的那种知性化了感性力量。他观看大自然的脸,仿佛它是从某个匪夷所思的珍贵的结晶体中切下来似的,每个侧面都不同,每个又都依赖于另一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它们预告了弗莱17年之后的塞尚专论的基本主题,一是揭示塞尚的工作方式包含了感性观察中的知性参与;二是认为塞尚眼中的大自然非常独特,呈现为一个结晶体的效果。这两个主题,后来成为贯穿于《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的基本主题,而这两点在这篇1910年的文章里都已经有所预示。
该文其余的篇幅主要给了凡•高(Van Gogh)、高更、马蒂斯(Matisse)与毕加索(Picasso)。单单看看这一张名单,人们就不得不惊叹:弗莱从一开始就已经抓住了欧洲现代艺术史的全部开创性的伟大人物。请注意弗莱写这篇文章的时间:1910年。其时,欧洲的极大部分艺术批评家(更不必说普通公众了)都还在现代艺术破晓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呼呼大睡。认真阅读此文的读者将会发现,他们的惊讶更有毋庸置疑的理由:弗莱用了区区四千字,就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最初10年的全部现代艺术史的核心。后世的任何一位现代艺术史家对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及毕加索的分析和评论,都没有在弗莱的这篇短文之上增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弗莱为《国家》杂志所写的《一则关于后印象派的附论》,回答公众与批评家对后印象派画展的批评,继续为展览辩护。在众多批评中,一位名叫萨德勒的先生的批评显然更对弗莱的胃口,他们的分歧与其说针对后印象派画家,还不如说针对艺术史的评价。在这位萨德勒看来,乔托(Giotto)的技法是有缺陷的,亦即还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盛期的“科学再现法”。而弗莱则认为乔托的作品“是某种东西完整而完美的表达,没有任何人在他之前或之后曾经说过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精神体验的最终而又完整的表达。契马布埃(Cimabue)所缺欠的是不是技法,而是再现科学。他足以说出他想要的东西,却不足以说出脑海里想着提香(Titian)与委拉斯克斯(Velasques)的萨德勒先生想要的东西。” 显然,两人的分歧代表了两种艺术史观:进步的艺术史观Vs.钟摆的艺术史观。
还有一位名唤霍利戴的先生,他批评塞尚的《浴者》背离了自然。弗莱对此的驳击极其高明,充分显示了他那种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般的英伦知识分子的自重和孤傲,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剑桥学派的严谨与丝丝入扣的辩论风格。弗莱的基本观点是,艺术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它之所以是艺术恰恰因为它背离了自然,否则,与自然一般无二,还需要艺术作什么呢?此亦为中国画理论所固有,谚曰“江山如画”,而从来不说“画如江山”。弗莱说:“从这种角度看,塞尚的《浴者》完全被他说中了,不过不幸的是,霍利戴先生说得太过了。他所说的一切几乎都适用于拉斐尔(Raphael)的《圣母子》(the Virgin and Child)素描。要是霍利戴先生想要维持其立场的一贯性,他必得说,谁看见过一个女人的头部那鹅蛋脸上会有两到三道轮廓线,谁看见过头发底下会露出头盖骨的线条,谁看见过她的脸颊上会有许多平行的黑影线?霍利戴先生必定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他忘记了,艺术利用自然的再现作为表达的手段,但是再现本身却不是目的,因此不能成为批评的准则。”
《后印象主义》是弗莱在第一届后印象派画展结束之时,在格拉夫顿所作的演讲,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由上述一系列论文所构成的第一回辩护的总结发言。我认为,对那些真诚地想要了解现代艺术批评史,甚至是想要了解现代艺术史的人来说,对那些曾经对现代艺术感到困惑不解,或者正在对当代艺术中的大多数现象和作品感到匪夷所思的人来说,弗莱这篇辩护词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
开篇伊始,弗莱就开宗明义,表示自己的演讲对象主要是介于以下两类人中间的听众:一类跟他本人一样,是后印象派的热情赞美者,另一类是那些认为后印象派画家及其画展,彻头彻尾就是一群骗子与骗局的人。对于前者,弗莱当然已无需多言;对于后者,弗莱当然也无需多言。但出于宽慰对手考虑,弗莱诉诸林肯的名言(“你不可能一直欺骗公众”[“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指出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就让时间来宣布它的失败吧。
对此,我想补充几句。时间当然早已证明了弗莱的对手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宽慰,因为时间不仅证明了他们的敌意已经被宣布失败,也证明了他们的短视同样已经被宣布失败。这里,值得一提的到是,为什么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以骗子和诈骗犯来揣度他们所不解的事物的故事?我认为,有一个参考答案可以解释这一切:知性的偏狭与趣味的固执。除此之外,惟有道德上的自我崇高感,成了他们惟一的选项。
接着,弗莱交代了这个讲座的基本目的:“是试图解释这一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艺术家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尝试加以解决的。这一问题就是,要发现想象力的视觉语言。也就是说,要发现怎样安排形式与色彩,才能给予视觉以刺激,从而最深刻地激发想象力。”
毫无疑问,“发现想象力的视觉语言”,这是一种新的表述。弗莱似乎已经意识到,要说服那些不相信后印象画派纯粹是一个骗局,同时发现自己对这些画作又感到难于理解的善良的观众,他需要一种更一般、更普遍的美学理论。他的这一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以同意的共识之上:“艺术家的工作不单是对可见事物的复制与如实拷贝——人们会期待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有所偏差地再现和歪曲视觉世界。”因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了:什么程度的偏差与歪曲是可接受的?
弗莱的回答是:“有多少歪曲——与现象总和有多少不类似——对艺术家来说是允许的问题,总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其答案也全然不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他的意思:有多少歪曲或偏差是允许与可接受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史的问题。美学家想要越俎代庖、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总是陷于虚妄:绝大多数陷于思辩的浪漫癖,偶尔则陷于唯科学主义的偏执狂。你无法从理论上来回答“多少偏差与歪曲是合理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历代艺术家一直在试图加以回答的问题,他们以他们的作品回答这一问题,他们的回答构成了一部艺术史,确切地说,一部风格史。
在接下来的段落里,弗莱再次体现了一个偶像毁坏者的性格,他毅然决然地将矛头指向学院派:
学生们一般关心的那个艺术时期——1300年至1500年——碰巧是产生了大量杰作,而且呈现了走向更为圆满的再现科学的持久而又相当稳定的进步的时期。对那些从事教授艺术这种悖论性工作的人而言,这一进步仿佛是一种天赐之物。在所有那些极其难于捉摸的人类激情与情感现实中,艺术是其中成功的、却很难破译的记录者之一,但是在这里,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得到轻松而又生动的展示,人们甚至可以据此出试卷,并给予严格的打分。由此,艺术被把握为一个不断克服再现自然中的困难的凯旋过程。
在今天的美术学院,一张“好画”的标准仍然被严格地规定为技巧上的完善甚至“正确”。因为,正如弗莱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惟有固执地捍卫绘画“正确”与否的标准,教师才有可能据此出题并给予打分。因此,绘画“正确”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技法问题,而是一个教学体制中的权力问题。然而,现代主义的实质之一恰恰就是对这种体制中的权力的反叛,它宣布“正确”只是学生的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第一步就是从“画错”开始的。换言之,只有坚持“画错”,才有可能从可习得的、可重复的、精益求精的学院主义中脱离出来,从而走向真正的艺术。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说过“有多么偏差或歪曲是允许或可欲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史问题,弗莱还是尝试性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说它是美学理论也未尝不可,但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假设性的解释。他说:“这[艺术家怎么画]完全取决于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的性质及特征,取决于艺术家会采纳何种程度的自然主义。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些围绕着日常生活的种种絮屑之事产生的思想情感和情绪——那种与文学中的喜剧性手法相应的艺术——会要求大剂量的现实性,会不得不要求十分精确而又详细的自然主义;但是那些属于我们天性中至为深沉、至为普遍的部分,却很难真的为任何与实际现象逼真相似的东西打动,并得以释放。”
显然,弗莱将“围绕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絮屑之事产生的思想情感”分配给了“与实际现象逼真相似”的自然主义画法,而将“我们天性中至为深沉、至为普遍的部分”分配给了某种带有更大的普遍性的画法,亦即一种并不单纯诉诸人类感性——一般而论被认为是因人而异的,而且还诉诸人类理解力——通常来说是人人共通的画法。这就为以后印象派画家为代表的理念及其技法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不仅如此,在证明塞尚式的变形的正当性的同时,弗莱还没有忘记顺便批评一下艺术家的作秀癖与公众的起哄乐趣:
当一个艺术家被要求要在对可见事物的再现中做到高度的完整性时,他的精力通常在再现的过程中就消耗殆尽。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种壮举,它是如此不易,以至它的实现总能引起人们对艺术家技艺的惊异与赞叹,于是,公众与艺术家之流惊叹于这种神奇的走钢丝表演,忘记了这只不过是通往其他目标的手段而已,忘记了艺术应该唤起比那些我们用来迎合杂技演员或台球手的一般情感更为深沉、更为强烈的情感。
学院派艺术家坚持再现的正确性和完美性标准,实质是要巩固其体制性权力,而公众对这种正确而又完美的技艺一往情深,则强化了他们的地位。须知,从宙克西斯(Zeuxis)的时代以来,公众就一直站在杂耍般的艺术家一边。如今,国内的走钢丝艺术家则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来宣扬艺术中的技术至上论。此是后话,这里只是顺便提及而已。
超越再现的画家,则“诉诸充满想象与静观沉思的生活的倾向”,弗莱接着说。我认为,这一次他给出了最终答案:
现在我得试着解释什么是我所理解的艺术通过感官直接诉诸想象力的观念。根本不存在着艺术家为什么应该再现实际事物,而不该拥有线条与色彩之音乐的自明的道理。他毫无疑问可以拥有这样一种音乐,这形成了他的诉求中最本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也许能从一个单纯的图式中,获得强烈的审美愉悦,要是它在构图方面非常高贵,在处理手法上又充满活力的话。……独特的线条韵律与独特的色彩和谐,自会产生其精神效应,总能一会儿产生一种情感,另一会儿又产生另一种情感。艺术家通过线条,通过色彩,通过抽象形式的节奏,以及通过他所使用的物质材料的质地,跟我们做游戏。……韵律是绘画中根本性的、至为重要的品质,正如它在所有艺术中的重要性一样——再现则是第二位的,而且永远不能侵犯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韵律的要求。一个艺术家出于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出于他所领会的想象力的必然,从而画下关于现象的任何事实之时,也就是他背离艺术表现的规律之日。正是这些规律,不管它们是多么困难和难于发现,构成了一件艺术品必须遵循的最后标准。
正如著名学者克利斯朵夫•里德所说的那样,在所有这些捍卫首届后印象派画展的文章中,弗莱都试图平衡抽象的要求与再现的要求。在《后印象主义》一文里,弗莱认识到“与实际现象符合的一定程度的自然主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是有必要的。”而仅有形式与色彩的游戏是不够的。毋宁说,弗莱聚焦于这种带有形式姿势的作品与再现性主题材料交互作用,以便在观众中激起一定的反应的方式。他认为,“围绕着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产生的情感和情绪”,可以在写实主义艺术中得到最好的传达,而“那些属于我们人性中至为深沉、至为普遍的情感”,则将在更抽象的形式中找到它们的表达。弗莱也没有认为抽象艺术永远高于他称之为“照相式视觉”的东西。也不是说,抽象艺术总是更好的艺术,而是说抽象艺术在现阶段是合适的。写实主义的法则——弗莱冠以“文艺复兴时期确立起来的过于精细的绘画技法”——在它们盛行的年代,激起了“充满激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到了19世纪,它们已经成了一种“与想象无涉的死亡事实的驱壳”。因此,像塞尚与马奈那样的艺术家,放弃了“现象的科学”,转而拥抱“表现性设计的科学”。他们的原始主义标志着历史的伟大车轮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转折,正如它在对视觉意义系统的发现与再发现中所走过的道路那样,我们已经认识到,每一个转折都“获得了新的表现可能性,同时也失去了别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弗莱倾尽全力为后印象派,从而为整个现代艺术运动辩护时,他的美学观也正在走向成熟。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诸如“有意义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表现性的形式”(expressive form)等术语的运用上。请注意弗莱公开使用“有意义的形式”这一短语的时间:1910年。众所周知,这一短语曾被冠在弗莱的学生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头上,并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作为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在中国广为传播,从而造就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国内学者所写的《西方美学史》或《西方现代美学史》之类的著作中,通常会有一章涉及形式主义美学,会提到罗杰•弗莱,但把他放到克莱夫•贝尔后面,仿佛克莱夫•贝尔才是主角,而他的老师——为贝尔十分敬仰的弗莱倒成了次要角色。我们都知道,克莱夫•贝尔撰写了《艺术》(Art)一书,并因此走红。但史料表明,出版社最初约请的是弗莱,只是弗莱对这类通论性的书没有多少兴趣。作为经验主义者,他更看重批评现场以及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与评论,因此将这件事扔给了自己的学生克莱夫•贝尔。贝尔比弗莱小15岁,年轻气盛,接下这一工作后,立刻就将西方整个美术史和全部美学推到重来。他提出了一套著名的理论,认为艺术的根本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是Significant form(在中文版里被译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然而,让我们读一下弗莱1910年的演讲稿:
后印象派画家如何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发展而来,这确实是一段令人好奇的历史。他们吸收了大量印象派的技法,吸收了大量印象派的色彩,不过他们究竟是如何从一种完全再现性的艺术向非再现性与表现性的艺术过渡的,却仍然是一个谜。这个谜存在于一位天才人物令人惊异、难于解说的原创性之中,他便是塞尚。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无意识的。在以无与伦比的狂热与力量沿着印象派的探索路线往下走时,他似乎触摸到了一个隐蔽的源泉,在那儿,印象派赋形的整个结构瓦解了,一个有意义的与表现性的形式(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的新世界开始呈现。正是塞尚的这一发现,为现代艺术重新恢复了全部消失已久的形式与色彩语言。
请注意,“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也可以译为“有意义的形式与表现性的形式”。很难考证弗莱在其他非公开场合,最早是什么时候使用这一短语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贝尔发表《艺术》的1914年,这个词在罗杰•弗莱的那个圈子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之物了。贝尔拿到这个术语后,将它当成一个口号,到处去宣讲,他成了“大师”,而真正的原创者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历史”总是如此:善于喊口号的人成为大师,真正的原创者却为人们淡忘。
最后,稍微谈一下弗莱同样发表于《国家》杂志的、为第二届后印象画派展览辩护的文章。两年之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塞尚已经被经典化,因此弗莱已无需再为他辩护,转而将主要精力花在对现代艺术三大师的后二位的诠释上:马蒂斯与毕加索。简单地读一读这些段落,读者将不难领会:后人所写的全部现代艺术史,已经无法为马蒂斯和毕加索增添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弗莱已经道出了一切。这就是弗莱作为现代主义的“天使”——弗莱曾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秘密精英组织中的“天使”——对现代艺术的最大贡献。还值得一提的是,文末对毕加索之走向纯粹抽象所表达出来的谨慎的不解,已为弗莱艺术批评的后期生涯作了铺垫。
注释:
1 详见拙作《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美术研究》,2008年第4期;并作为附录收入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28页。
2 Maurice Denis, “Definition du neo-traditionisme,” Art et critique, August 1890; reprinted in Theories, 1890-1910, 4th ed. Paris: Rouart et Watelin, 1920, pp.1-13.
3 参Desmond MacCarthy, “The Art Quake of 1910,” The Listener, February 1945, pp.123-124; reprinted in Memories,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53, pp.178-185.
4 Roger Fry, “The Philosophy of Impressionism”, unpublished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for the Fortnightly Review, 1894.
5 Roger Fry, Introduction to The Discourses of Sir Joshua Reynolds, London: Seeley, 1905, pp.vii-xxi.
6 Roger Fry, “The Last Phase of Impressionism”,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March 1908, pp.374-375.
7 Roger Fry, Introduction to Maurice Danis, “Cezanne—I,”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January 1910, pp.207-208.
8 参拙作《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载《艺术时代》,2009年第8期;关于两届后印象派画展,以及弗莱为之辩护的一般史实,详见拙著《20世纪艺术批评》第一章“罗杰•弗莱与形式主义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0页)。
9 Christopher Reed, eds., A Roger Fry Read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50.
10 Roger Fry, Introduction to Manet and the Post-Impressionists, 1910, pp.7-13
11 Ibid.
12 Roger Fry, “The Grafton Gallery--I”, The Nation, 19 November 1910, pp.331-335.
13 Ibid.
14 Ibid.
15 Ibid.
16 Roger Fry, “The Post-Impressionists”--II, The Nation, 3 December 1919, pp.402-403.
17 弗莱对塞尚工作方式的揭示,详见拙作《塞尚的工作方式:罗杰•弗莱和他的形式主义批评》,载《批评家》杂志第一辑,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第92-112页;并作为“译者导论”,收入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
18 Roger Fry, “ A Postscript on Post-Impressionism”, The Nation, 24 December 1910, pp.536-540.
19 关于弗莱“钟摆的艺术史观”,请参阅我对弗莱艺术史观的评论,见《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第80页注2、102页注7等处。
20 同注18。
21 Roger Fry, “Post Impressionism”, The Fortnightly Review, 1 May 1911, pp.856-867.
22 Ibid.
23 Ibid.
24 Ibid.
25 Ibid.
26 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51.
27 同注21。
(原载《世界美术》,2010年第3期)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读后感(三):[译者导论(二)] 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
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罗杰·弗莱与他的时代
沈语冰
[提要]本文是作者为《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文版所撰写的译者导论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后印象派画展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讨论弗莱围绕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撰写的一系列辩护文章,这些文章系统地发展了他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从而为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即本文)则联系弗莱的中期写作,着重论证弗莱作为一个形式主义者介入各种社会生活的程度,澄清将弗莱偏面阐释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误解。第三部分“对形式主义的再认识:论弗莱的晚年思想”,则聚焦于弗莱晚年论文,探讨了弗莱如何调整与修缮其理论基础,从而将自己从现代主义理论的教条化与学院化倾向中拯救出来。全文请参看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出。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罗杰·弗莱为后印象派所作的辩护的主要观点,它们构成弗莱美学思想的核心成分。
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人性中最为深沉、最为普遍的情感,因此它在人的感官(视觉)的基础上必定还会诉诸人的知性(或理解力),从而趋向于某种程度的设计或赋形。但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却以人类心智中更为重要的侧面的表达为代价,不断追求精确化的再现科学,这种再现科学的最晚近的形态就是印象派。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坚持个人表达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现代艺术的赋形语言:以一定程度的变形或者甚至抽象取代照相式的写实主义,以纯粹色彩与线条的造型,取代了光影与明暗法。
尽管这一概括有过于简单化的一面,但我认为,仅仅出于论辩的需要,这样一种概括经常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弗莱的这一理论被越来越简单化地还原为一种有关形式主义美学或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教条:艺术史的必然逻辑就是走向抽象;艺术的本质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审美情感完全以形式为对象,而对艺术中的内容的关心则属于生活情感的残留,根本不是审美情感;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理解艺术形式,普罗大众只会对艺术的内容感兴趣。等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期,这些观念不仅在一般所谓的艺术界和艺术家工作室里不胫而走,而且在一般公众中也越来越流行,直到成为二战以后欧美艺术史的标准内容与艺术教科书的陈腔滥调。在这个过程中,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阿尔弗兰德·巴尔(Alfred Ball)、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等人对形式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理论的不断推广普及和还原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克利斯朵夫·里德(Christopher Reed)所说,在某种意义上,弗莱的作品是它自身的成功的牺牲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对他所支持的现代艺术家异乎寻常的增长的兴趣,意味着他的大多数形式主义写作很快进入了艺术话语的主流,而且——经常是经过过分简化的——成了现代主义的常识。在20世纪中叶现代主义鼎盛期,弗莱被誉为抽象艺术的先驱,尽管对他的观念的参照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人们不得不怀疑,他的著作之被简单的引用,要远远多于被认真的阅读。如今,在一个被标举为“后现代”的时代,尊敬已经倒转为讽刺。然而,弗莱的著作经常被含含糊糊地加以引用,却很少被彻彻底底地加以阅读,因为弗莱是一个比头脑简单的抽象艺术的支持者复杂得多的思想者。[2]
弗莱在题为《艺术与生活》(“Art and Life”, 1917)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形式主义的分离假设:艺术作为一个与生活相分离的领域,有它自己的演化逻辑,有它自己的“由其自身的内在力量……所决定的变化的节奏序列。”[3]通常,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弗莱形式主义的最集中表述。但是,正如弗莱的密友弗吉妮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注意到的那样,该文所主张的艺术与生活的分离,直接来源于战时语境。当时弗莱竭力想从欧洲社会普遍的崩溃中为艺术挽回某些乐观主义情绪。她注意到,弗莱在这里的观点既与他的其他写作不协调,也与他的为人相矛盾。而将艺术与生活重新联结起来,则成为弗吉妮亚·伍尔夫的《弗莱传》的重要主题,它暗示了,弗莱之所以能“从战争中康复”,是因为他坚持认为艺术与生活可以分开,尽管伍尔夫争辩说:“审美理论似乎是为了竭力想要解决私生活问题。疏离,正如他反反复复强调的那样,乃是艺术家最迫切的需要。难道它不还是私生活继续下去的需要吗?”[4]
确实,声言艺术可以与生活分离的观点,与弗莱的整个事业形成巨大的反差。弗莱出身于1866年,晚于拉斯金(John Ruskin)、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及其同时代人。尽管他终其一生都在提升和捍卫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他却从未失去将新的艺术方式与新的生活关联起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渴望。弗莱的职业生涯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赶上了唯美主义及“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行将结束之时。植根于拉斯金道德化的写作,且以莫里斯的中世纪作坊的复兴为例,“艺术与工艺运动”谴责工业革命对工人的影响,提倡回到行会制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以王尔德(Oscar Wilde)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则培育了脱离日常世界的实用律令的艺术感性的浪漫观念。本来,这两个运动无论就其宗旨来说,还是就其趣味来讲,都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弗莱却将它们奇迹般地实现了调和。尽管有许多历史学家反对这两个运动,然而,拒斥大规模生产消费品而钟情于较少、较好的事物的审美趣味,与致力于高度手工艺化的产品生产的朴素生活的理想,确实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赋予这两个运动以一致性的是它们那种通过重新想象日常生活的形态,从而将审美与社会改良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收入《弗莱艺术批评文选》第二部分的文章,充分地揭示了弗莱正是这一时代的产儿。在这里,不仅美学与现代主义绘画之间的联系,立刻找到了在建筑、装饰等实用艺术中的运用可能,而且详尽地反映了弗莱要将美学理论运用到博物馆管理、美术教育等社会生活中去的热切意愿。
由于弗莱的生平涉及艺术史、艺术理论与批评、艺术教育、博物馆管理、陶艺、建筑、实用设计、著述、出版、媒体等与艺术有关的几乎一切领域,人们不得不惊叹于他那旺盛的精力和体魄,更不得不震惊于他的抱负和志向的全部高度与整个范围——收集在本文选第二部分的论文,可以部分地见出这一点。眼下我只举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将弗莱看作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形式主义者”是多么荒谬,顺便也说明,作为一个偶像破坏者,弗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这个例子就是他在英国建筑师协会所作的题为《一个画家关于建筑的异端邪说》(“Architectural Heresies of A Painter”)的著名演讲。演讲得到了建筑师布鲁姆菲尔德爵士的响应(他接受了《泰晤士报》的专访),也惹恼了许多伦敦的建筑师。著名的《建筑师》杂志对此发表了一则妙不可言的声明。弗莱在出版该演讲稿的单行本时,干脆将这则声明印在了扉页上:
《建筑师》(Architect)杂志说:“《泰晤士报》用了半个专栏的篇幅报道了里杰纳尔德·布鲁姆菲尔德爵士(Sir Reginald Bloomfield)讨论罗杰·弗莱最近在学院所宣读的一篇论文的访谈录。我们相信要是新闻报刊能通过一个克己的法令,从此不再报道愚蠢的言行,那么我们用不了多少年就会使生活摆脱臭名昭著的猎人的侵扰。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被误导的人会做他们明知错误或荒谬的事,要是他们得到人们关注的话,而一盆绝对沉默的冷水就能使我们免于堕落作家、未来主义者、潜在的革命者及其他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所说的‘从来不会错过机会’的家伙所带来的麻烦。”[5]
要想概括弗莱当时所面对的英国皇家学院建筑师协会的总的敌意氛围,没有比这则声明更精彩的史料了。弗莱在这里被明确地刻画为“臭名昭著的猎人”,与“堕落作家、未来主义者、潜在的革命者”、“机会主义者”等等为伍,做出了“愚蠢的言行”、“错误或荒谬的事”。这种种指责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现代学术(艺术亦然)已经被划分为一个个明确的专业分工领域,因此不属于本领域的人便属于闯入者(即他们所谓的“猎人”)。本领域的专家则是天然的护法师,他们不仅掌握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行话(jargon),而且掌握着本专业(确切地说本技术)“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他们,手中握有裁量别人“懂不懂”、“愚蠢不愚蠢”、“错误不错误”、“荒谬不荒谬”的戒尺;并且,也只有他们,自居为真理的拥有者或道德的至善者,动辄以“骗子”和“诈骗犯”之类的罪名指控他人。一句话,他们构成了现代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宗教裁判所。
然而,弗莱并不在乎这一套。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偶像毁坏者,他认为,除了对真理的不竭探索以及对美的不懈追求应该能够得到报偿的信念外,没有什么先天的条件可以确保任何人的专家或权威地位。而他的谦卑,他的业余爱好者的态度,反而增添了后人对他的无限敬仰。请看他是怎样来结束这篇“异端邪说”的:
但是,我请求你们相信,无论我今天下午的表演多么缺乏机智,我都并非出于邪恶的固执或是肮脏的嫉妒,而是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也许相当荒谬的信念的牺牲品——这个信念就是:从人类的长期效应来看,对美的追求与对真理的追求一样重要。[6]
在这样妙不可言的开篇与令人感慨的结尾之间,弗莱的讲座集中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偶像摧毁者的大无畏风采。在这样一个伦敦最著名的建筑师云集的场合,他一口气列数英国近代建筑的十大弊端,其直言之勇气,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对建筑史了解不多,但直觉告诉我,弗莱的演讲在20世纪20年代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也能深刻体会那些在座的建筑师们,听了弗莱的演讲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事实上,时间证明弗莱是对的。他对英国近代建筑十大弊端的指控,既尖锐深刻,又富有洞见。后来的建筑史表明,在弗莱所批评的那段英国建筑史上——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直到20世纪最初20年——的确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建筑。因此,不奇怪的是,著名的建筑史家佩夫斯纳(Pevsner),对于完全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弗莱为自己所设计建造的住宅,会感到震惊,并且带着赞美的口气将它与欧洲最重要的现代建筑师阿道夫·罗斯(Adolf Loos)位于奥地利的别墅建筑相提并论,认为它是“独立当代风格在英国建筑演化中的里程碑之一”。[7]
然而,对于那种动辄以专家、权威口气指责那些以其真诚、追求真美的人为“猎人”、“骗子”、“诈骗犯”的态度而言,殊可奇怪的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作品,竟可以使他们的裁判失效、威信扫地。他们一定弄不明白,何以作为一个画家、一个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的弗莱,能够说出有关他们专业的什么东西,能够告诉他们专属于他们的领域的某些知识。范景中先生曾说:“我深知,很多人不想把艺术视为天下公器,他们觉得那是懂艺术者的专有之物,他们抱着专家的优越态度,高视傲兀,目空一切,正如歌德所说,当他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会表现出固执,而当超出他们的专业领域时,又会显得无知。”[8]
那么,弗莱究竟在这个演讲中告诉了那些专家们什么东西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建筑的基本美学原则。这里,我不想冒险去概括这些原则,文稿就在眼前,读者诸君自可辨识。这里,我权且引用一些国外学者的评论,以助谈资。克利斯朵夫·里德指出,令熟悉建筑史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弗莱1912至1921年间的建筑评论,领先于更为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宣言,例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thitecture)的程度。作为现代建筑史上最著名的文献之一,该书1923年初版,1927年由弗莱的“奥米加”工场艺术家费德里克·埃切尔(Frederick Etchell)译成英文。然而,远在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宣言发表之前,弗莱就早已开始了以现代主义原理来评论建筑的工作。弗莱论证了一种现代建筑的语言,它建立在建筑的“工程之美”的基础上,其典型有如“美国的纯粹实用性建筑,特别是巨大的谷仓”,也预示了柯布西耶对“作为新时代的第一批成果的美国谷仓与工厂”的欢呼。弗莱将他在捍卫后印象主义绘画与雕塑中发展出来的修辞,运用于建筑分析。他认为,建筑之美乃是建筑师“内心精神状态的明确符号”,以及“造型观念的表达”。在同一点上,勒·柯布西耶说道:“通过他对形式的安排,建筑师实现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乃是其精神的纯粹创造。通过形式与形状,他……激发造型情感。……于是,我们才能体验到美的感觉。”[9]正如弗莱论艺术的写作一样,他对建筑的现代原理的表述,尽管在其阐明伊始尚处于边缘,但从回顾的角度看,却位于现代主义建筑史的中心位置。[10]
一个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可以如此领先于艺术实践,这可能是一个特例,其中似乎不存在太多的隐含。但是,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何以一个大多数建筑师认为不懂建筑的人(一个“臭名昭著的猎人”),事实与历史却证明他比那些专业建筑师更懂建筑?难道那些建筑师在智力、能力与趣味方面都不如罗杰·弗莱吗?我看未必。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观念,他们囿于狭隘的专业视野,因而看不到弗莱所能看到的东西。在各个艺术领域中,技术性要求越高的艺术门类(比如建筑、电影)——我不是说技艺,因为每一门艺术都需要技艺,而且不存在技艺要求的高低问题;我是说工程技术、物理与化学知识等所谓科学技术——越容易产生对技术的单纯依赖,从而出现因技术而生的权力与垄断。权力产生**,垄断产生暴利;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绝对的垄断则产生绝对的暴利;而绝对的**加上绝对的暴利,则绝对不允许“猎人”染指,绝对要求颁布“懂与不懂”的垄断标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这个原理,在艺术领域中也没有例外。
将形式主义基础奠定在一种主观信念而不是权威主义的趣味标准中,这一点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批评家们的写作中一直得到强调。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在其导论中宣布“一切美学体系的起点都是对一种独特情感的个人体验”。[11]当贝尔描述“好的批评”应该“避免将批评家的意见强加于人”,相反,批评家的角色应该“以其热情感染他人”,俾使“他们也能体验到审美领悟的战栗”时,他心里想到的也许就是弗莱(事实上他真的以他为例)。[12]弗莱本人,则更加强调批评的主观性。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比贝尔更为开放,更带怀疑论色彩,更少确定性,也更少教条语气。
弗莱批评理论的这种临时性和开放性,特别表现在他与克莱夫·贝尔严格的形式主义理论的差异中。弗莱谨慎地欢迎贝尔提出的不同于日常情感的“审美情感”说,但是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不同于贝尔。第一,他坚持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不单单是形式,而且还是“图像”,都可以在文学和绘画中结合在一起,以便唤起“审美情感”,因此,他暗示,可以有一种建立在形式与图像的关系之上的“真正的形象艺术”。第二,他不相信“有意义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是自足的,并且暗示,其意义事实上来自与生活经验相关的某种外部成分。弗莱染指两个不确定的领域,这些问题将伴随着他一生,直到他去世也未曾解决:视觉艺术中的形象塑造(illustration)与形式设计(design)之间的关系,有意义的形式与可见事物之间的关系。
收入本文选的《一种新的艺术理论》(“A New Theory of Art”),是弗莱对贝尔的《艺术》所写的书评,最清晰地呈现了他与贝尔之间的差异。在最关键的段落里,弗莱指出:
他一开始追问什么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的品质**同而又独特的因素。他发现艺术品拥有“有意义的形式”。我们如何认识有意义的形式?通过它激发审美情感的力量。读者或许会问:什么是审美情感?贝尔先生会回答说,就是由有意义的形式所激发的情感。看上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不过,我们确实迈出了一步。……于是我们就把由某些形式关系所激发的情感,从生活事件或它们在想象性创造中的回声所引起的情感中,区分出来。这是贝尔先生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过正是在这儿,我希望贝尔先生能够更大胆些,更周全些。我希望他扩展他的理论,将文学(就其也是一种艺术而言)也考虑在内,因为我敢说,伟大的诗歌能激发类似绘画与建筑的审美情感。为了使他的理论更彻底,贝尔先生就得表明,《李尔王》(King Lear)和《野鸭》(The Wild Duck)中的人类情感,也是附属性的,而不是这些作品根本的和本质性的品质。[13]
这一段落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弗莱对贝尔理论的内在缺陷的认知,其一,是其循环论证的嫌疑;其二,是贝尔的理论无法扩展至文学理论,因为很难想象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意义,仅仅在于其形式安排(即语音、语调、节奏、韵律、结构等等)。这一书评,也暗示了弗莱将会提出一种不同于贝尔的视觉艺术理论的替代理论,但弗莱还没有觉得有匆忙总结的必要。
这里,弗莱对形式主义的阐述与克莱夫·贝尔对它的通俗化之间,可以作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弗莱拒绝了Chatto & Windus公司让他总结他的美学的机会,建议贝尔来实施这一计划。弗莱终其一生都更青睐简明的论文那种持续不断的洞见,贝尔却为一本书所暗含的一种界定性的、整全的理论方案的可能性所吸引。弗莱的书评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注意到贝尔的书那种“确定无疑的口气是我感到陌生的”。弗莱无法分亨贝尔的自信,而他的怀疑似乎预感到了后人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他既怀疑形式美学的纯粹性,也怀疑它与艺术家目的的关系。总的来说,弗莱特别强调批评家的主观性。弗莱认为,贝尔是通过“虔诚的信念”而不是通过“合理的确信”来加以论证的。
今天,不仅形式主义理论的基本信念遭到了种种质疑,就是康德(Kant)以来作为西方美学史的核心观念之一的“形式愉悦”这一概念本身也遭到了批判。指责它的人认为,强调愉悦的个人体验,是压倒了“所有其他愉悦……压倒了在劳动、学习以及知识生产中,与现实对象及其物质转化的所有其他生理的、知觉的或心理的互动。”在这种观点看来,这种分化只是对发达资本主义“不断加剧的劳动分工的需要”的支持罢了,而“现代主义牢笼”显然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控制的体制。[14]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多半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总是假定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内在关联。他们乐此不疲地援引的例子就是,被现代主义叙事神话化了的高更,他去塔希提岛时乘坐的航轮,就是当时的法国殖民当局从欧洲开往太平洋的。这种论证的滑稽之处在于,他们假定,比方说,只要你使用了父辈的金钱——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象征——那么你就无法脱离跟资本主义的干系。为此,他们可以将福楼拜(Flaubert)、塞尚、整个布鲁姆斯伯里群体,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这些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经济学家们碰巧都继承了少量遗产,可以不必从事劳动生产,因而得以专门从事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批判工作。高更当然比他们更倒霉,因为他乘坐了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轮船,所以成为欧洲向海外的文化殖民的一部分。
要跟这些人讲道理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在西方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并非人人都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者。为弗莱等人辩护的克利斯朵夫·里德就认为,形式主义中的逃避主义倾向也许能导向这类文化运用——亦即为资本主义所用,但是审美愉悦却并不必然排斥其他的担当形式,超越的抱负也并不必然具有强制性。正如可以证明的那样,超越人们的当下立场的物质条件的志向,乃是任何变化观的基础;而审美超越的观念经常带有这一隐含的意义。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案中,形式主义对主观审美反应的依赖,不仅仅是一笼统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一种将艺术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律令中,以及从由陈腐的审美判断所主宰的统治阶级的控制中拯救出来的深思熟虑的尝试。[15]
对弗莱来说,更进一步,对整个布鲁姆斯伯里群体来说,面对艺术品的超越的情感体验,乃是现代主义的本质。新艺术似乎将观众推进到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从而脱离维多利亚传统的虚伪与伪善的钳制。弗莱为推广他带进伦敦的艺术所做的讲座、所写的文章,乃是改变人们观看、思考与行动的更广阔的动机的一部分。弗莱雄心与抱负的幅度,可见于本文选的各个篇章,在那里他将他的理论既适用于当代人物,也适用于历史人物,既适用于建筑,也适用于装饰艺术。将这些文本与他用来解释并捍卫后印象派的文章最清楚不过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作者的强烈使命感,亦即他想要劝说他的读者改变观看方式的欲望。不管是形式主义美学的理论结构的展开,还是提供对一幅特殊作品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弗莱的散文从来不会失去其劝诫的特质。他在大量充满敌意的观众面前所捍卫的艺术品,如今已成为西方文化最常见的、最著名的纪念碑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些文章的成功的证据。[16]
在文化体制的历史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在英国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一个如此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聚集在大学体系之外的伦敦。”[17]继承所得的钱——尽管非常微薄——允许布鲁姆斯伯里成员将他们自己维系在各种体制的边缘。因此,尽管弗莱的生涯交错地与主流艺术杂志、博物馆、画廊以及大学联系在一起,他却并不依赖任何单个机构,因而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挑战各种体制化的实践,并推广艺术展览与教学的新形式。弗莱的成就或许可以用他所宣扬的改革已成为当下的规范的程度来加以衡量,这些规范如今已成为新一代批评家的批判对象。弗莱论艺术体制的写作如今也面临着批判,但是,正如里德所说,“这一事实不应该模糊这位改革家曾经拥有的热诚”。[18]
弗莱明显地将关于艺术的主流观点等同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却是他急于想要挑战的。总的来说,收集在本文选中的论文,都反驳了将弗莱刻画为一个势利的、想要强加一种僵硬的审美评估体系的唯美主义者的漫画形象。相反,这些文章表明的是,一个敢于将艺术从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者的体制性控制中拯救出来的社会活动家的激情。
前文已述,弗莱与贝尔更富教条色彩的形式主义理论的重大差别在于,他几乎从来没有否定过立体感、三维性、再现因素在现代绘画中的意义。在弗莱的整个生涯里,他都在寻找一种品质,他有一次宽泛地称其为“体积与空间在其三维中的互动的最大可能。”为了表示对绘画中的立体感的强调,“造型的”(plastic)一词随着弗莱对法国画家、批评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的论文《塞尚》(“Cezanne”)的翻译,进入了他的词汇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塞尚“寻求造型美”(cherchant la beaute plastique)。到弗莱的文章《造型设计》(“Plastic Design”),这个词开始占据弗莱美学的中心位置,它被宽泛地界定为属于“绘画的”(“pictorial”)领域,与“插图家或线描家”的作品相对立。
如果说弗莱那些意在推广后印象主义的文本展示了旧的表现主义词汇的顽固性的话,那么他对前卫运动的反应也记录下了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的重叠,这揭示了弗莱的形式主义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与世隔绝、密不透风的。而那种机械的、密不透风的形式主义,则被认为是后来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特征。这里当然不是长篇比较这两位现代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与现代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的地方,不过,简单地作一个勾勒,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罗杰·弗莱更清晰的认识。
格林伯格对弗莱的引用很少而且相当肤浅——尽管在其晚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谈话中,格林伯格列出弗莱为两三个值得一读的批评家之一。格林伯格的傲慢由此也可见一斑。不过,在他最著名的文集《艺术与文化》(Art and Culture)一个讨论伟大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T·S·艾略特(T. S. Elliot)的上下文里,格林伯格对弗莱作了这样一个评价:“一个实证主义的伟大时代能够产生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它还产生了罗杰·弗莱,甚至是克莱夫·贝尔过于简化的艺术批评。‘有意义的形式’的观念1914年前后充斥英国学术界的空气,我禁不住会认为这种想要在视觉艺术经验中孤立出本质因素的尝试对年轻的艾略特产生了某些影响。‘纯诗’先于‘纯画’(有意思的是,弗莱翻译并注释了马拉美的诗集),但是‘纯’艺术批评却先于‘纯’文学批评。”[19]
这里,格林伯格在肯定了弗莱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弗莱的纯艺术批评领先于艾略特的纯文学批评,而艾略特可能是格林伯格唯一敬仰的批评家——当然也暴露出了他对弗莱的某些偏见,还有就是混淆了弗莱与克莱夫·贝尔之间的差异(不过,他的混淆程度要比国内美学家来得轻一些,格林伯格至少明白弗莱与贝尔之间的先后次序,这种次序不仅仅是岁年和历史时间上的,更是重要性与历史地位上的)。格林伯格多多少少继承了弗莱形式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形式分析的基本术语,例如“造型”(plastic)、“平面”(plane)等等,但他并不像弗莱那样在乎“造型性”(plasticity),相反,他经常抛开弗莱借自沃尔夫林(Wolfflin)等人的“平面”概念,越来越倚重“平面性”(flatness)概念。
尽管他俩通常被宣布为同一个阵营里的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代表,弗莱与格林伯格之间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首先是个人气质方面的:弗莱“温和的好斗性”——这是他用来形容贝尔的词——与英国绅士般的优雅与明晰;格林伯格的“傲慢与粗旷”。一直以来,格林伯格激起了长久的争论。他对艺术所下的判断那种确定无疑的语气令许多人震惊,认为他是威权主义的、傲慢的和不恰当的。这种理直气壮不仅导致他卷入了与他所喜爱的艺术家的紧密关系,甚至还导致了他改变了他们的某些作品。但更多地,两人的差异是时代形成的。弗莱是在20世纪初为现代艺术作出辩护的,他试图从拜占廷绘画与意大利“原始绘画”的历史角度来赢回后印象主义画家的合法性,因而这种辩护是试探性的,是一种美学的假设与重视个人审美经验的个体修辞。而格林伯格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写作的主要年代——40与50年代——对形式主义与前卫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主要形式,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在美国,美术馆和博物馆,大学课程和艺术杂志,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均支持形式主义路线是不可避免的和正确的。[20]
人们通常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看作一个“唯美主义精英的遁世小集团”,但收集在此篇中的文章表明,这一形象将受到弗莱以拉斯金、莫里斯以及一般艺术与工艺运动的精神所从事的高度公众化的事业的检验。这些文章还表明了弗莱以唯美主义精神所从事的写作的历史语境,这一精神提出了艺术家个性的观念,用来证明对主导文化的个体反抗行为的正当性。收入本文选的“奥米加”创建文件,表达了弗莱对艺术与工艺运动的使命的最强有力的阐明;与“奥米加”的最后岁月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写作则提供了唯美主义最清晰的遗产。这两个运动的共同点,还有弗莱从不放弃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审美的更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讲具有深刻的含意,不管这里的“我们”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抗争中的亚文化群体。[21]
由此可见,将弗莱理解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者”是多么错误。在国内美学界,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就是:形式主义(在中国长期的政治话语中,它早已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就是主张形式高于内容,甚至根本无视内容;形式主义者则是资产阶级等级制的维护者,他们提倡艺术脱离生活,脱离大众;形式主义就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无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力,等等。弗莱的例子表明,实情殊非如此。如果说弗莱确实认为,在艺术中,形式是比内容(主题内容)更重要的表达元素,那么,他深深地介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一生事业表明,一个形式主义者与一个社会改革者,并不必然就是自相矛盾的。[22]
注释
[2] 参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2-3
[3]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9.
[4] Virginia Woolf, Roger Fry: A Biography, 1940; repri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pp.214-215.
[5] Quoted in Roger Fry, “Architectural Heresies of A Painter”, Chatto & Windus, 1921.
[6] Ibid.
[7] Nikolaus Pevsner, “Omega,” Architectural Review 90, August 1941, p.45.
[8] 范景中主编:《美术史的形状》,“序言”,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6页。
[9] Le Corbusier, Towards a New Arthitecture,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hells,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27, p.33.
[10] 参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p.172-173.
[11] Clive Bell, Art, New York: Fredrick A Stokes, 1914, p.6.
[12] 参Clive Bell, Since Cezann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2, p.155.
[13] Roger Fry, “A New Theory of Art”, The Nation, 7 March, 1914, pp.937-939.
[14] Benjamin Buchloh, “Since Realism There Was…(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factographic art), in Art and Ideology, New York: 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1984; reprinted in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ssues in Contemporary art, edited by Howard Risatti, Englewood, N. J.: Prentice Hall, 1990, pp.92-93.
[15] 参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56.
[16] Ibid., p.58.
[17]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New York: Viking, 1983, p.248.
[18] 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232.
[19] Clement Greenberg, Art and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240;中译本见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84页。
[20] 对弗莱的“折衷主义”与格林伯格“体系化”之间的差异的讨论,已经由查尔斯·哈里森作出。参Charles Harrison, “Modernism and the ‘Transatlantic Dialogue,” in Pollock and After: The Critical Debate, edited by Francis Frasci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p.217-232。不过,美国学者约翰·奥布莱恩已经论证过格林伯格的批评事实上要比后来的评论者们所能想象的更为“临时性”,尽管连奥布莱恩也承认“格林伯格想要做到临时性的意愿在50年代开始消失。”参John O’Brian’s introduction to Clement Greenber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Vol.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1] 参见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186.
[22] 关于现代主义的党派性原则,以及“为艺术而艺术”并非没有社会关怀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详见拙著《20世纪艺术批评》,“导论:什么是现代主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原文发表于《新美术》,2009年第6期。)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读后感(四):[译者导论(三)] 罗杰·弗莱的晚年思想
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再认识:论罗杰·弗莱的晚年思想
沈语冰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为《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文版(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所撰写的译者导论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后印象派画展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讨论弗莱围绕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撰写的一系列辩护文章,这些文章系统地发展了他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从而为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罗杰·弗莱和他的时代”则联系弗莱的中期写作,着重论证弗莱作为一个形式主义者介入各种社会生活的程度,澄清将弗莱偏面阐释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误解。第三部分(即本文),则聚焦于弗莱的晚年论文,探讨了弗莱如何调整与修缮其理论基础,从而将自己从形式主义美学的教条化与学院化倾向中拯救出来。
关键词:罗杰·弗莱 形式主义 现代主义
英国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是世界公认的形式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之一,而形式主义美学则是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基础。但是,在弗莱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越来越强烈地质疑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形式主义原理,或者不妨说,他事实上已经走到了与那种被简化了形式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程度。甚至在战前,弗莱的现代主义也以其对“古典性”的强调,从未放弃过艺术史的传统遗产。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以下两段话加以比较,当能发现他个人从早年的反叛到晚年的“回归秩序”(rappel a l’ordre)是显而易见的。一段是他在推广后印象主义时,他那种一切向前看的文本:“现代人试图找到一种与现代世界观的感性相适应的绘画语言。”[1]另一段是他在1924年论法国绘画的话:“它们是多么传统啊!……我会认为,鲁本斯(Rubens)会在马蒂斯(Matisse)的画里认出自己的后裔,正如马蒂斯会认可他的遗产一样;巴托罗梅奥(Bartolommeo)会立刻理解毕加索(Picasso)想要的东西;17世纪的伟大构图家们(普桑[Poussin]是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一个),会多么清晰地感知到德朗(Derain)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秘密。”[2]
弗莱本人放弃了——或者至少是修正了——一度在他看是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形式主义原理,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出版于1926年的文集《变形》(Transformations)的导论中。在界定“再现在造型艺术中的意义与目的”时,弗莱说:“这始终是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性质的症结所在,对此,我并不羞于承认,在不同的时候,我提出过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肯定不同于彼时的立场——那时我坚持纯粹造型方面的绝对重要性,而且几乎是暗示,没有别的东西需要考虑进来,而这时,我强调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绘画的戏剧性可能的东西。”[3]
放弃了这种严格的形式主义后,弗莱坦承自己准备“调和,或至少是解释,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态度”。[4]于是,这就成了弗莱晚期写作的计划:通过将再现与形式主义范式综合起来而又不放弃纯粹审美经验的理想,从而将现代主义重新整合进更广阔的艺术史传统。
对国内读者来说,弗莱的《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将是饶有趣味的,趣味之一就是弗莱在建构成熟的现代主义理论时对中国书法的明确指涉。在一些强调“中国中心论”的西方汉学家看来,弗莱在建构其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参照,应当被理解为一个“中国体为西方用”的个案,说明了“现代性”根本不是一个源于西方的事实,而是一种跨文化的建构。[5]撇开这一点不谈,弗莱的这篇重要论文,至少给了我们某种新的启示。他对于线条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作用的论述,反过来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艺术的世界艺术史意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弗莱在论述现代素描的新的可能性时,将线条的意义阐发得淋漓尽致:
因为这里蕴藏着素描最伟大的魅力之一——亦即,一方面是事物的无限复杂性与丰富性,另一方面则是心智的单纯几何式抽象,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并不是被带向一个点,而是带向一条线。在艺术中,世界的这两个不可通约的侧面在某种程度上被还原为一个共同的尺度,而在素描中这种调停则在其最简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向度中被呈现出来。因为纯粹理想、清晰而又合乎逻辑的素描有可能成为直线与已知曲线的一种单纯机械的图表,另一方面,纯粹写实而又精确的素描则有可能像大自然那样混乱无序、难于认识。伟大的制图家确实获得了一种明晰而又可辨认的秩序,却不失生活的丰富性、坚实性与无限性。线条的品质拥有一种可识别的韵律,却又不机械,这就是线条的感性。这里,最显而易见的东西无疑是线条可以有无数变化,可以在其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上调整自己以适应对象的形式。[6]
然而,从认识弗莱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一论述,还不如以下的论述更富有意义。与马蒂斯“书法式”的素描相比,弗莱强调了他的另一种素描,即“结构式”的素描:
如果我们转向马蒂斯的另一幅素描,我们就能发现一种相当不同的处理手法——在这儿,线条要刻意得多,在速度上更缓慢,较少狂热,就其本身来看也较少吸引力。尽管它仍然保持着敏感性,但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更多地关注线条的位置,它们唤起量感与质感的观念力量,而不是线条的品质本身。这是一种更为确定的造型与建构性赋形手法。是那种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才成为可能的综合的典型;这些艺术家不认为大自然的个别事实是神圣的,因此除了必要的形式外可以自由地省略它们,不再描绘而是造型地建构它们。因此,这样的赋形不是靠描绘那些我们从解剖学上知道的形式,而是靠发现那些赋予整个情境以造型有效性的最终要素,事实上,是靠发现那些从造型上讲并不能表现解剖功能的线条,来获得其融贯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种素描,作为一种对形式充满激情的表现方式,在我看来才比那些追随文艺复兴传统的大师们所画的任何素描都更为圆满。[7]
这里,重要的是马蒂斯的这种“结构式素描”在弗莱晚年的理论探索中的位置:将绘画的再现因素与抽象因素综合起来。在弗莱看来,马蒂斯的这类素描无疑提供了最佳的范例:
就我所知,这些就是现代艺术在线条赋形方面所做的努力的结果。首先,这是一种更加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的综合的形式结构——一种更加有力的统一性,恰恰是因为艺术家不再听命于大自然的任何特殊事实,而是必须在每一个情形下重新确定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偶然的东西。其次,这样一种建构性的赋形是从韵律的角度加以表现的,而其韵律则要比过去的数个世纪里获得的种种节奏更为自由、更为微妙、更有弹性,也更具适应能力。[8]
也就是说,马蒂斯的这类素描既满足了人们传统上对于外部世界的一定程度的图画再现的需求,也满足了更挑剔的现代观众对于建构性赋形(而不是照相式再现)的韵律的要求。而再现性的具象内容与韵律性的抽象形式,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成了弗莱晚期写作的根本问题。
收入本文选的《毕加索》一文,是弗莱1921年写的,颇能说明这个阶段的他对于抽象绘画的态度,首先,弗莱一如既往地强调抽象绘画(或者至少是带有抽象意味的建构性赋形)在现代造型艺术中的重要性。他说:“不管抽象绘画在比再现性绘画更充分、更纯粹地表现与唤起情感方面成功还是失败,在两种情形下,这一努力都已经在将我们抛回赋形的内在必然性方面显示了巨大的重要性。它已经迫使我们去探索并理解那些规律,对于这些规律,艺术家们在对再现的兴趣与刺激的压力下,总是视而不见。”[9]
弗莱是最早认识到毕加索之返回具象绘画的意义的人之一。他热情拥抱毕加索之重返具象绘画,这一点似乎与我们对形式主义的坚定奠基者的漫画化形象相矛盾。事实上,不仅是我们对弗莱作为一个个人的看法需要改变,而且是我们对形式主义本身的理解也需要接受挑战。请看他是怎么提供对纯抽象绘画的思考的:
许多年以前,当这些抽象绘画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曾说过,我们还不能立刻就判断它们能走多远;我们得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我们对这种诉诸视觉的抽象手段的反应能发展得多快。我想,时光的流逝已经表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感性是能够获得发展的。在罗森伯格先生(M. Leonce Rosenberg)的画廊里,有一系列年轻的立体主义艺术家的画展,他们都或多或少彻底地从毕加索开采过的材料中,发展出了个人风格。也就是说,通过对形式的近乎纯抽象的运用,他们每个人都成功地给出了一种独特而又个人的表现。这表明,在从最少量的再现中创造出表现形式的冒险,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不可能之事。但是,当我们开始考虑他们所表现的东西的品质时,我得承认,就个人而言,我感到有些失望。当我们考虑到建筑中的非再现性形式之作用于我们的情感效果时,它是多么强烈,多么巨大,在刹那间就包围并控制了我们的整个想象生命,我们就会希望,立体主义绘画的抽象也会产生同样的炽热和说服力。然而,不知怎么地,迄今为止这一点好像并没有发生。我们感到困惑,被取悦,也被迷住了,但从来不像再现在其中扮演着更大角色的画作那样令我们深深地感动。这也许只是意味着,抽象形式的语言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我们对这种语言的反应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还没有一个有足够情感驱动力的艺术家已经运用了这种媒介。[10]
弗莱晚年最重要的写作,构成他一生事业高峰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Ce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精微广大之至,很难加以概括。不过,从弗莱后期写作的一般趋势的角度看,我们也许可以将此书的特征刻画为一种形式分析基础之上的心理分析。在此书中,弗莱运用详尽的绘画形式分析法来探索创作这些画的那个人的个性。该书开篇就将塞尚的事业呈现为一个“发现他自己的个性”的过程,而那些描述性词汇——“塞尚是如此小心谨慎……他是如此卑微”——既可以用来形容塞尚这个人的性格,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绘画的基本创作法。美国学者维切尔(Beverly H. Twitchell)说:“透过弗莱的文本,人们看到了一个英雄般的、几乎存在主义式的形象,尽管弗莱专注于对早年塞尚的大量心理刻画。他用来描写或分析其作品及其形式、色彩和构图的措辞,常常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塞尚的态度。对塞尚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的描写,呈现了他对画家的强烈同情,并暗示了他甚至已经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处境。塞尚对臣服于沙龙的屈辱与失望,他在其作品面对误解和敌意时所感到的艰辛、自重与孤独,都能在弗莱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对应。弗莱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作为形式主义批评使者的立场,与他面前的塞尚作品之间的平行。”[11]
总之,与一般所论弗莱的形式主义形象截然相反,他一生伟大的总结,出人意料地表现得如此开明与阔大,以至,再将他形容为一个唯形式是问的形式主义者,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就是故意歪曲了。正如我在此书的中文版中评论弗莱的形式主义艺术观时所说:“弗莱在这里所作的总结,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不管你如何分析一个艺术家的童年不幸、创伤或情结(弗洛伊德主义),不管你如何揭示一个艺术家所处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和阶级地位等等(马克思主义)——仅举两例——为了理解他的艺术,人们最终都得落实到对他的作品的物质材料及其形式的分析之上。换句话说,直面物质材料及其组织和安排(形式),是我们理解一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也许最为重要的通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理由称之为‘惟一通道’)。但是,正如弗莱在本书中曾经诉诸塞尚早期的情感教育(见第二章),以及塞尚生平中的两个插曲(第八章),特别是诉诸塞尚的心理分析(散见于各处)等等事实,已足以表明的那样,弗莱虽然是一个形式主义批评家,却不是唯形式主义者。唯形式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现在被有趣地称为艺术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概念风马牛不相及),它断言只有艺术品的媒介特质及其组织方式(形式)才是本体,而所有其他因素统统是非本体,言下之意便是,都是边缘的、无关紧要的;不仅无关紧要,而且,对这些‘外围’因素的研究和分析只会‘污染’艺术的纯洁性。我认为,唯形式主义想要断言其‘最重要性’,甚至‘惟一性’的做法,不仅无助于人们理解艺术,反而助长了种种矫揉造作的学究气,以及更加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的专家作风。在这个问题上,我一贯重申的立场是:在对艺术的理解中,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换言之,各种思想方法和批评手段都是我们趋近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全部理论工具箱中的工具。不管怎么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之辩,已经足够雄辩地为我们指出:仅仅分析形式不足以揭示其意义,因为,意义并不存在于那些形式(线条、色彩及其组织安排)的固有的必然性之中,而是深深地嵌入制作这些形式的人与观看这些形式的人所构成的相互游戏的整个语境中。”[12]
在弗莱那里,传记研究、对画家个性的强调,与对于作品的形式分析并不是不能兼容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激怒后世那些遵循形式主义路线(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符号学、结构主义)的专家们的狭隘神经与偏执心理的地方。尽管《塞尚》一书最伟大的方面可能仍然是它强大的形式分析,在这方面,弗莱著作无与伦比的伟大,是举世公认的。此书极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对塞尚作品的形式要素作详尽的研究。但是,形式分析与心理分析,并没有被认为是对立的方法论,它们在弗莱尝试将线条、色彩与质感读解为超形式的美德的暗示中是同时共存的。正是这种方法,启发了后来的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的塞尚研究,他将形式分析法与精神分析法、图像研究法等结合起来,开创了塞尚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此,我也有一个评论:“弗莱在这里指出静物画似乎特别切合塞尚的性格,是着意于静物画这个画种要求画家长期间的静观,以及静物画适合于塞尚那种对形式和结构的探索的要求而言的。不过,弗莱在这里也暗示了某些别的东西(可参看本书最后一章《最后的裸女》对塞尚性格中谜一样的另一面的提醒)。而恰恰是这一点,启发了后来的美术史家和美术评论家夏皮罗对塞尚作出了出人意料的研究。夏皮罗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趣而卓有成效地分析了塞尚静物画的另一种意义:‘那是在某些特定的作品中,由大帷幕与复杂但平衡的水果所构成的完美秩序,而这正符验了一个观点:苹果对他而言相当于人体。如人所知,塞尚渴望画女性胴体,但他深恐在女模特儿面前出丑——他顾忌本身的冲动会由于想像力自由激发在绘画上——这在他较年轻时,会导致暴烈的激情出现于其画中。’因此,夏皮罗的结论是:苹果一方面代表其性渴望,另一方面又显示其性压抑。(Meyer Schapiro, “The Apples of Cezanne: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Still-life”, in Modern Art,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9, pp.1-38)这在国内的唯形式主义者或艺术本体论者看来,可能令人困窘,或使人发怒:塞尚的苹果居然还有故事可讲!我引用这个例子的用意并不说夏皮罗道出的就是真理,而是,任何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方法,都是可用的,我们并不需要划地为牢,以为过去过分陷于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现在就得校枉过正,不承认形式分析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会使我们从根本上丧失对艺术的洞见,而这种洞见无疑正是夏皮罗这样杰出的、从不教条的艺术史家提供给我们的。正因为有了弗莱、夏皮罗等学者的努力,我们在对伟大艺术家的理解上才有可能步出傲慢的专家态度和浮夸的学究气的黑洞。”[13]
我们还可以将弗莱在《塞尚》一书中所作的努力,与他稍早对法国著名诗人马拉美(Mallarmé)诗歌的翻译联系起来看。因为弗莱后期论艺术的写作,显然受到与文学的比较的激励,揭示了他对语言的新兴趣,这种兴趣激励他对视觉艺术中的叙事性进行重估。在弗莱为他所译的《马拉美诗集》所写的导论中(写于1921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提出了对于诗歌本质的三种可能的解释:
有三种可能的诠释:(1)我在上面试图加以描绘的语词-形象复合体,乃是诗歌的根本品质,滑稽模仿则是它的助手,因为滑稽模仿对诗歌的领会来说具有一种心理辅助作用。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歌德说诗歌的根本性质在于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是对的。(2)旋律是诗的本质效果,而语言形象只是,不妨这么说,形成了一个可供由旋律所引起的模糊情感得以流动的渠道。(3)这两种东西进入一种化学的化合状态。它们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诗歌的独特的根本性质。[14]
接受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教育的人,一定会说诗的本质就是弗莱列举的三种可能解释中的第二种。然而,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形式主义者,弗莱却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一解释。而且,对于第三种解释,他也不大相信,而且举出了诸多理由。令我们最感意外的是,他明确地指出:“在承认旋律性节奏是诗歌所独有的效果的同时,在承认它能强化诗歌的语词-形象效果的同时,我仍然倾向于认为,语词-形象序列及其氛围,乃是诗歌最为根本的性质。”[15]
对于唯形式主义者和“艺术本体论者”而言,这无疑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但是,对于真正喜爱文学艺术的读者来说,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且不说像歌德那样伟大的人,他的深思熟虑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就是一般议论,也不会倾向于认为诗歌的本质(大而言之,文学的本质)就是语言的语音、语调、节奏、韵律。我不知道持极端形式主义观点的人如何安顿莎士比亚(Shakespeare)、伦勃朗(Rembrandt)、托尔斯泰(Tolstoy)等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者。正如我在另一个语境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也要对另一种倾向保持警觉,特别是当文艺自主论渐渐演变为‘文艺本体论’,并且以一种矫揉造作的学究气和装腔作势的专家态度断言‘语言即一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并且津津乐道于语音、语调、韵律、节奏、能指、结构的条分缕析,而根本无视作品最基本的思想情感、内容意涵以及作者的思虑、不平、关切、梦想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文体,甚至超越语言的。这一点,正如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所说:‘我们都能感受到托尔斯泰的伟大,但我们很少有哪个人是通过直接阅读俄语来了解托尔斯泰的。’诚然,我们必须说,经过翻译,托尔斯泰的文本一定经历了不少损失,但是,我们也可以断然地说,即便单纯借助于译作,我们也能体会到托尔斯泰的伟大;而且,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文体大师这一点并不妨害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许还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16]顺便说一句,托尔斯泰作品的可翻译性,似乎印证了歌德关于诗歌本质的断言是正确的。
在视觉艺术领域,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属于一个量级的画家无疑是伦勃朗。安顿伦勃朗果真成了弗莱晚年的一个心结。因为,对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而言,伦勃朗似乎构成了一个难于回避的挑战。弗莱认为伦勃朗的“心理想象力是如此崇高,假设他用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话,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家或小说家之一,而他的造型建构能力却同样出类拔萃”。[17]除了这种赞美,弗莱对伦勃朗的研究反映了他与自己的形式主义遗产作斗争的激烈程度。在弗莱的早期写作中,伦勃朗只是一带而过的名字,但在其晚年的论文里,他却成了一种持久的扰人的在场。在弗莱论素描的系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不无挫败感地提到伦勃朗,因为伦勃朗无法纳入他的形式主义评估体系:“伦勃朗总是以其才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他深刻的想象洞察力与过人的天赋之间的斗争,激起人们的兴趣。”[18]而1921年的《毕加索》一文则将伦勃朗刻画为一个“他自己奢华的天赋的牺牲品”。从表面上看,这种非难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暴露了在他的书信中非常明显的焦虑:“我必须写写普桑和伦勃朗,不过,长期以来我都试图在这两个人身上做一种调停。但是,他俩让我害怕。”在另一处,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再一次回到对普桑的绝对崇拜——我能追随他画中的每一笔,彻底认同于他,就像是我自己画的一样……伦勃朗在他最好的时候,我也完全跟得上,不过我把他当作一种神圣的启示来接受,他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力。”[19]
因此,收入本文选的论文《伦勃朗:一种阐释》(“Rembrandt: An Interpretation”),体现了十分珍贵的价值,它记录了弗莱想要解决他对伦勃朗的矛盾心理的决心,伦勃朗的成就显然挑战了他的美学原理的基本信条。而弗莱写于1934年的文章《伦勃朗的〈浴室〉》(“The Toilet, by Renbrandt”)则表明了他终于对这位艺术家感到自在了。文章开篇就能读到的形式分析轻轻松松地与对主题内容的兴趣和谐共处。弗莱对伦勃朗处理其主题内容的方式的欣赏,并没有停留在对自然形状与人类形体的概括性指涉上。弗莱甚至赞美特殊的叙事因素,即伦勃朗在对拔士巴(Bathsheba)的刻画中那种“深刻的心理兴趣”。在这篇极具典型意义的论文里,弗莱已经有勇气面对一个不断地刺激着他的二难,促使他对战后的整个形式主义美学作出重估:“让我们承认,对这幅画的全面理解要求我们既能感受到其心理动机,也要能感受到其造型动机。然而,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人们在并不清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情境的时候,也能激赏它的造型与绘画诉求。而当我确实弄清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动机之时,我感到了另一阵欣喜的袭击,但是,这两种喜悦是合为一种更强烈的情感,还是各自为政的情感?”[20]弗莱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对于他无法作出决定这一点,现在他似乎已经不再感到焦虑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绘画的双重性质》(“The Double Nature of Painting”)一文才显示出特别的意义来。在此文开篇,弗莱就提出了有两类不同的艺术:
当我们浏览所有的艺术门类——诗歌、音乐、绘画等等——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都清清楚楚地归入两个大类。在第一个大类中,伟大的作品是由艺术家对对象、人类及其情境,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的再现构成的。在另一个大类中,对这些事物的再现经常被彻底拒绝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因此,音乐与建筑能够确立起伟大的形式构成,几乎与数学命题满足我们的理智一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审美官能,也就是说,不指涉任何外在于它自己的形式构成的东西。这样的构成包含了一切信息,以及对所涉问题的一切解决方案。它们是自我充足的,无需外在的支持。与此相反的是,诗歌与绘画迫使我们去认识外部现实的指涉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作品本身。这一点对所有诗歌以及几乎所有绘画来讲,当然是对的。[21]
值得注意的是,弗莱明确地将绘画归入诗歌一边,而不是更纯粹的音乐与建筑一边。在这个前提下,他再一次捡起了抽象画这一话题,并且——如今已经不再令我们吃惊——指出,抽象画不如带有具象因素的作品更能打动人。他说:
今天,我们毫无疑问已经看到了画家们一种想要逃避这一规则,想要确立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任何自然再现的绘画艺术的英雄般的尝试。我们称之为抽象艺术。我认为,我是最早为这一冒险辩护的批评家之一;20多年前,我甚至希望这会导向一种新的艺术启示,不过,尽管不少最有天赋的艺术家,特别是毕加索,确实在制作技艺精湛、高度平衡的构成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却缺乏那些最伟大的再现性作品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必须承认,我发现,由这些视觉构成所带来的魅力,远不如我们在音乐中所发现的那些类似的声音构成来得动人。当我们反思,经由一些视觉形式,例如圆柱体、立方体与球体等等的分布,建筑对我们的情感能产生几乎与音乐同样的效果时,我们就会感到更加惊讶了。当然,人们必须考虑到建筑是三维的,而抽象绘画只有两维这一事实。我认为,这里存在着抽象绘画缺乏情感感召力的真正原因,因为很明显的是,对由扁平画布提供的任何空间深度的暗示,都是缘于一种透视效果,也就是说,缘于对艺术品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再现。不参照再现,人们就无法在画布上构建体量或空间。所以,回到我的要点,尽管存在着抽象的尝试,但大体而言,绘画一直是,或许仍将保持为一种再现性的艺术。[22]
《绘画的双重性质》这一讲稿直到1969年才出版,而这已经是弗莱去世30多年之后。这篇文章长期为现代主义者,也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忽略,这一事实说明了人们不愿意面对弗莱写作生涯的复杂性。现代主义者担心弗莱晚年的这个讲座稿,将会瓦解他们最珍视的形式主义的基础。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急于宣布弗莱等人的经典现代主义理论下课,因此不愿意看到这些经典现代主义理论中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思想肌理与复杂层次。
到1929年,当弗莱着手为期六讲的广播讲座《绘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Pictures”)时,他的第一讲就是《讲故事》(“Telling a Story”)。用形式主义方法来研究叙事问题,这是弗莱在与文学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方法。他不再将主题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予以打发,但是,重新激发的对叙事的兴趣并没有导致弗莱拥抱一切奇闻逸事类的艺术。维多利亚时期的学院派画家,如路克·费尔德斯(Luke Fildes)仍然是嘲弄的对象。现在,区别不在于形式艺术与叙事艺术之间,而在于不同的叙事类型之间。乔托(Giotto),跟马拉美一样,“只跟这个故事最根本的心理事实,亦即这一情景的巨大对立与对比打交道,我们发现这样一种荒凉而又简化的手法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力量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戏剧的根本。”[23]弗莱的目的是要保留形式主义者对超然或“无利害”静观态度的信念,同时又抛弃只有抽象形式才能激发这样一种审美反应的陈旧教条。在弗莱的广播讲座中,他竭力想要澄清真正审美的叙事与仅仅是奇闻逸事式的叙事之间的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出版于1930年的专题《亨利·马蒂斯》(Henri Mattisse),除了对马蒂斯做出了后人难于企及的开拓性研究外,令读者备感兴趣的是他对马蒂斯绘画的一般原理所作的解释,那就是将“绘画的双重性”当作基本假设来接受。所谓“绘画的双重性”是指“我们被迫在同一个时刻意识到一个既是涂满了丰富多彩的色彩的表面,又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生活并活动其中的三维的世界。绘画的这一模棱两可的性质,既构成了[艺术家们的]一种折磨,也成了[他们]灵感的来源。艺术家本人也拥有双重性及双重忠诚。一方面,他渴望实现他的视觉,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制作者;他渴望讲述他的经验,他也想要创造一个对象、一个偶像、一个珍贵之物。而视觉与珍贵之物——艺术品,则总是相互冲突。他的视觉与他的手艺总是拉向不同的方向,而他的轨道则由它们的相对力量及其距离决定。在漫长的绘画历史中,我们有可能研究这一由两股力量所决定的轨道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艺术,这两股力量的其中一股或是另一股几乎被减化为零。”[24]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读到了后来的著名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贡献——当然这个贡献是建立在弗莱的开拓性事业之上的——亦即对西方绘画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三维错觉主义向现代艺术的二维平面性的过渡这一主题的阐述。[25]但是,与后来的格林伯格不同,弗莱并没有强调平面性,他的主旨似乎也不在于提供现代艺术史的所谓演化逻辑,而是对马蒂斯绘画的个人兴趣。
以弗莱的新视角来看,是马蒂斯,而不是任何别的后印象主义者,看到了单纯的抽象追求背后的东西,“他们也为如何将这种方法与他们继承得来的传统中和起来而大伤脑筋,不过,不知怎么地,他们也确实决定要为油画重新发现艺术品(objet d’art)的品质——尽管还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来。”“就我对欧洲艺术史的了解而言,还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对绘画的双重性主题做出了如此众多令人愉悦、出人意料而又使人狂喜的变化。”[26]
总之,弗莱一战后的论文,对于想要把他的批评实践从演变为一种学院主义的可能性中拯救出来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在1918至1934年的文章中,他热情洋溢地从他原有的批评理论中剔除了大量东西;而这个批评理论却是他战前经历千辛万苦才得以创立的。但我们不得不认为,弗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全部事业的终极效果,远不是变化多端、零碎任意的,相反,某些因素贯穿于他的批评生涯的始终。
即使是在敌意的包围中为现代主义辩护时期,弗莱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后印象派绘画,特别是塞尚的“古典性”的强调。在他进一步深化其批评理论时,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了他深深地介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程度。而在后期对原有理论进行调整与修缮时,他的早期思想不是被推倒了重来,而是明细化、精确化了:该舍弃的被舍弃,该突出的更加突出了。事实上,新一代的读者在弗莱的疑惑、他的社会目的感,或是在他蔑视一切权威的性格中,能够发现一个更加令人同情的人物的诞生,而不是一个被脸谱化了的“形式主义之父”的形象。
我希望,这个文选的出版,一方面,能帮助我们提高对弗莱写作的多样性及其范围的认识,另一方面,能有助于读者认清在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现代主义的复数性质,以及从它的诞生到被宣布下课的阶段中的种种衍变与发展。我们对弗莱晚年思想的这种重新梳理,当然丝毫也没有削弱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现代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的尊敬,相反,在意识到他是怎样一个偶像毁坏者的同时,他还是怎样一个真诚的求知者和爱美者,我们反而会油然而生敬仰。毕竟,对他来说,捍卫对真美的追求,要比冒着被学院化和教条化的风险,去提供一个封闭而又貌似圆满的体系,重要得多。说到底,弗莱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倚重现场感觉的批评家,一个相信自己直觉与经验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蔑视一切外部权威,信任自己的理性与内心律令的学者。即使在其60岁以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他站在罗浮宫内,他也能够“忘掉我的所有理论,我写过以及想过的所有东西,并试着绝对遵从自己的印象”。[27]与时同时,发自内心的强大信念与理智力量,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改变了20世纪思想进程的伟大的知识分子,足以与同时代的剑桥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相提并论。
注释:
[1]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Windus, 1920, p.238.
[2] Quoted in 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306-307.
[3]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13.
[4] Ibid., p.14.
[5] 参包华石:《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我认为,将现代性单纯解释为弗莱等人的话语建构,而非塞尚等人的先行实践,是站不住脚的。参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注3。
[6] Roger Fry, “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December 1918, pp.201-208.
[7] Ibid.
[8] Ibid.
[9] Roger Fry, “Picasso”, The New Statesman, 29 January, 1921, pp.503-504.
[10] Ibid.
[11] Beverly H. Twitchell, Cézanne and Formalism in Bloomsbury,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7, p.118.
[12]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第十章注23,第117页。
[13] 同上书,第十章注1,第99-100页。
[14] Roger Fry, “An Early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s of Mallarmé”, in 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p.297-304.
[15] Ibid.
[16] 徐岱、沈语冰主编:《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导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17]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p.27.
[18]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p.253.
[19] Roger, Fry, Letters of Roger Fry, Denys Sutton, e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2, p.505, p.566.
[20] Roger Fry, “The Toilet, by Renbrandt”, The Listener, 19 September 1934.
[21] Roger Fry, “The Double Nature of Painting”, Apollo, May 1969, pp.362-371.
[22] Ibid.
[23] Roger Fry, “The Meaning of Pictures I: Telling a Story”, The Listener, 2 October 1929, pp.429-431.
[24] Roger Fry, “Henri Matisse”, in Christopher Reed, A Roger Fry Reader, pp.401-415.
[25] 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6] 同注24。
[27] Quoted in Jacqelin V. Falkenheim, Roger F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Formalist Art Criticism, Ann Arber, Michigan: UMI Reserch Press, 1980, p.127.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