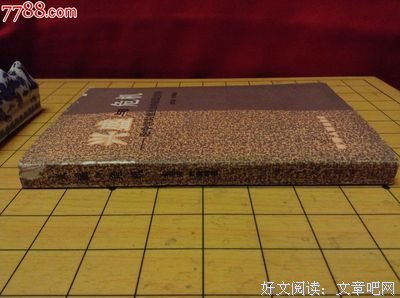《兴盛与危机》读后感摘抄
《兴盛与危机》是一本由金观涛 / 刘青峰著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1.50,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兴盛与危机》精选点评:
●利用系统论方法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构建宗法一体化超稳定结构,与无组织力量之间的嬗变,推演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自圆其说,可爱可信
●由于刻板印象和偏见,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几个字,不免满腹狐疑。文中提出很多问题,可是解释只能让我半信半疑。
●锐气可嘉,文史功力不足,且有主题先行之嫌。宏观的心灵史学确实应该是这样的思路,再深化一百年肯定会好很多,再说现在也有computational sociology approach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数学模型对社会学的又一次入侵
●从经济、政法、意识形态这三体系统来分析兴盛与危机。在宗法一体化已消失的社会中,超稳定结构转为普通稳定结构,一旦无组织力量积累到结构无法承受时,会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取代呢?阿米巴系统?
●查阅履历竟然发现金老师曾是所里的研究员。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还是蛮新鲜的,虽然会感觉有些不靠谱,尺度不好把握。
●终于读完了!写的太好了!
●八十年代的书,思想很超前!
《兴盛与危机》读后感(一):规律
描写历史规律的书很多,本书看起来似曾相识,原来写法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吴思的书有结构上的近似,就是由问题导入,梳理结构来解释问题。看来做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样用起来比较科学易懂。
作者名字有点耳熟,网上查询才想起是80年代的牛人。他从经济、政法、意识形态这三体系统来分析兴盛与危机。
在宗法一体化已消失的社会中,超稳定结构转为普通稳定结构,一旦无组织力量积累到结构无法承受时,会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取代呢?90年代至今,应该是通过经济改革来使现有的一体化加强了,未来呢?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还是柔性更替?
《兴盛与危机》读后感(二):兴盛与危机
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阐述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不过不知道是成书太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感觉里面数学相关的部分还是太粗糙了,而且由于我是用电子书看的txt文件,里面的图例无法看到,非常遗憾,不过感觉如果在能从博弈论或者墒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可能会更加透彻。书中的论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让人感觉是拿着结论去找论据,然后再推出结论,有点急于证明自己理论的感觉。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其实一本书是好是坏,并不一定在于所说的理论有多正确,更多是的看他能不能给读者以启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做的挺不错的
《兴盛与危机》读后感(三):《兴盛与危机》读后的几点小感触
怎么说呢,几点体会吧:1.那个年代有这样的观点,还算是很新颖很有创新思维的吧,突破的持续N多年的的唯“经济决定论”的所谓的先进史观;2.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者虽然对经济决定论有所突破,但全书贯穿始终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社会进步论,全书史料引用及分析句句不离“马克思”,时代特色还是很分明的;3.作者在每章描述分析之后都有一段观点总结,越看越觉得作者意有所指,联系到写作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大的社会(政治)环境,作者似乎意在阐述“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对中国传统历史“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国不断的在“崩溃——修复”中的重启,无不暗指当面对旧社会中结构的萌芽时,不要将其用“一体化结构”“强控制”消灭掉,要给予新结构萌芽成长的机会,这样才能走出无限循环的“停滞繁荣”。4.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学著作,作者对史料的分析应用有时候真的确实略显随意,且结论先行,史料论证的嫌疑很大。不过依然还是为作者的创新精神点赞,也确实很有启发性。20181013
《兴盛与危机》读后感(四):解极为精炼,足以评6星
【摘引自亚马逊tigerdh1980网友】
曾经的历史课本都是骗子,后来看了无数有趣的故事以及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猜测理论,如《明朝的那些事》、《狼图腾》等。
《剑桥中国史》、《黄仁宇系列》等下了苦功夫的专业研究,也难以让我信服。
金观涛,是我至今为止感觉最深刻、最准确的科学历史学家。
看到此书是80年代出版,可叹我到21世纪才在网上看到,现在才第一次买到实体书。中国科学的种种阻力,可见一斑。
金观涛在历史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盛世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对非专业读者来说,前2本比较容易阅读,而且见解极为精炼,足以评6星!可惜卓越没有啊O(∩_∩)O~——第三本的主题对普通人相对陌生,加上专业性的术语比较多,看起来挺费力,也就5星吧。
建议先买前2本,逐渐理解“系统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之后,再买第3本。
《兴盛与危机》读后感(五):包遵信为本书写的序《史学领域的新探索》
(浓厚80年代色彩)
还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那儿读到一篇论文打印稿。它就是现在这本论著的雏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当时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进而对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叹赏。与那篇论文相比,现在这本《兴盛与危机》分量已多了好几倍,但读了它,依然会使你耳目一新。
一部学术论著,我说它“迷人”,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其实,科学上任何创新的价值固然是在它能给人更真切的知识,但它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让人领略到一种美的快感。美学上有所谓“以美引真”的说法,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就是这个道理?这部论著从结论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学论著未曾道及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虽与史学有缘而又没有八门的人,读了以后有种闻所未闻的新奇感,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这种感受。现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正在热烈地争论着。这场争论的引发点,就是作者那篇论文的发表,把这个非常困惑人的老问题向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与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讨论相比,目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再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放开了视野,从历史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初露的势头,却也非常令人可喜,而这一特点在这本论著中则是最为突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就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对“超稳定系统”这个说法,当然只能褒贬随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这种从历史整体观上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这同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百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个长处。
说到方法论,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学家的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虽则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人们不免狐疑:难道历史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何况这种肯定或否定虽是截然对立,但从方法论上深究,它们往往又都是从同一原则出发的。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有些被称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很难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非但没有给理论增添什么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理论的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而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抗。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克服这种倾向但空喊重视理论也同样于事无补的。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
改进。
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地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历史科学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现状,而是满足于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不能给这个现状打开一个缺口?至少它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
作者在这本论著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说的,这些方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目前不少同志对它们都还是相当生疏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抵制它,用一项“西方资产阶级货色”的大帽子堵住它?这是我们相当熟悉,也是屡试屡败的老办法。鲁迅有篇随感录,题目叫做《来了》。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总是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就都闻风而逃,最终难免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吃过这种盲从和自大的苦头,虽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谁也不愿再来充当一次现代堂·诘诃德式的英雄罢。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控制论、系统论,它们只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中引用现代科学方法,这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念。这本论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令人费解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的同志,却总要在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有谁向前跨越一步,他们就惊慌不已,斥之为“标新立异”,甚而干脆就给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好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只是亵读他们圣洁灵魂的污水。如果这也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那恕我不敬,那只不过是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思想贫乏症。他们的虔诚虽
然令人起敬,他们的表现却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既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成果,不管这些成果是由谁创造的。这在原则上难道还容怀疑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心胸、眼光和魄力。诚然,在历史研究中吸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同它们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确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这本论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它的出版不是为我们探索这个新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吗?
我不懂控制论,对于历史研究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但我读了这本论著却不觉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现的那些历史场面仿佛让你身临其境,可以说就是一个一个活的社会,因而给你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层次分明,给人一种清晰感,不会使你如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只有政权易姓的改朝换代,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说法当然还是有的,那就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那时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等等。诚然,这是农民阶级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这种解释如同说古人没有宇宙飞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样,虽则千真万确,难免流于空泛,所以
与其说它是什么历史规律,还不如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况且它又怎样与另一个理论,即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一致呢?正象作者讲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就这样陷入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实际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超的鸿沟,现在该是填平这道鸿沟的时候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社会科学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迈步。在这一学术思潮中,我们却迟迟没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如经济学),中国史研究的大门,好象还不曾有现代科学来叩问过。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否当作代表史学领域这一新潮的初现?我以为是可以的。
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坛上,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深信我们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远比这位西方哲学老人更有气度,更能宽容,奖掖后进的热诚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同辈人,只是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这本论著也只是带有探索性的尝试,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当然难免。行家里手如果有严肃的批评,那也是完全应该、非常有益的。但愿不要因其还有斑疵,就不屑一顾;倘是囿于见闻,斥乏为怪,那就不足为取了。
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北京东郊新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