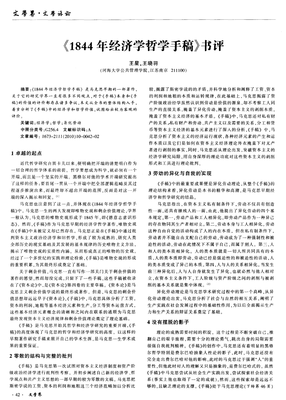《经济学是科学吗?》读后感精选
《经济学是科学吗?》是一本由(英)罗杰·E.巴克豪斯著作,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学是科学吗?》精选点评:
●本书给我提示最多的部分,是作者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实证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讨论。在二者融合之前,这恐怕是一个永恒的议题。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关于方法的争议,乃至历史学背景的经济史家和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家的争议,就来源于此。
●比想象的好看,是对战后经济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扫盲。推荐。
●未介绍行为实验,仅仅突出演绎理论与统计计量的矛盾,然后用一章简单介绍非主流经济学,令人失望。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那些写论文的同学:你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用了理性偏好假设了吗?你认为你分析的经济系统是一般均衡的吗? 很多人写论文仅仅是“应用统计学”,套上了经济学的外衣,却没有回归到经济学自身的逻辑上。希望经济学研究能多带来一些经济学的“洞见”,而不止是一个计算机的角色。
●可以。
●经济学界的学术争鸣,到最后比拼的是什么?到底怎样才算是“科学”的经济学?这种标准又受哪些非学术因素驱动?非正统经济学是不是一直在那里自说自话,不受主流待见?这些问题,通常的经济学教材不会回答你,却恰恰是这本小书致力于探讨的。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者,还是素人爱好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
●泛泛而谈的作品,开头章节的实例还不错,中间的战后经济学史介绍地比较零散,各个学派蜻蜓点水,索性不如就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然后再考察其能否为科学。最后一部分的评价系统一些,不过仍然没有深入计量经济学,所谓范式转变,或者统计,要么意识形态中的一项。应该说本书要研究的问题可能不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可以说清楚的。
《经济学是科学吗?》读后感(一):经济理论啥时候是“有效”的
翻译的有点不通顺,且必须有经济思想史及多元经济学(不是单一新古典的)背景才能读明白。感触五点吧:1、经济学的政策,无论理论多么完美,需要真正实践开才能找到问题,所以我朝的特区/试验区制度其实是很科学的;2、经济学的理论要有效,需要有适宜该理论的环境,当大部人都按某理论行动时,该理论自然容易有效;3、诸如拍卖这种经济理论可用性强,是因为清楚界定了问题,而且各个参与方有明确的规则,这样可以应用最优化策略(其实用AI也可以吧),但是诸如经济转型这种设计多参与方,且无明确规则的事件,经济学很难发挥作用;4、该书刻意回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框架,其实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强行引入的代表性经济主体,但是就像玩桌游一样,起码得明确各自的身份和目的,整个博弈才可以动态演化下去,要是所有人的角色都是无差别的,那最终这个游戏必然归于所谓的均衡;5、主流宏观经济学所涉及的数学计算可能很复杂,但期基础是高度抽象但概念相当简单的模型(这个看怎么理解,要是把经济学做成类似阿基米德集合体系的美妙系统到时正确的路径,但是想根据这种来指导经济生活就所差甚大)
1、2点属于共鸣;3属于新知(一家之言);4、为自己评论;5、总结的不错
整本书直接读最后一章就行
《经济学是科学吗?》读后感(二):什么是“合法的”经济学?
不知为何最近迷上了有关经济思想史的书,本书作者Roger Backhouse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他在本书中探讨了一些有趣而又难解的问题。说实话,推荐序中称本书不太烧脑,我不能同意,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学功底,可能不明白作者在讨论啥。
(一)经济学有用吗?
作者列举了四个例子:(1)拍卖理论运用于电信拍卖,获得成功;(2)休克疗法指导俄罗斯转型,代价沉痛;(3)理论上来看,自由贸易(全球化)是有利的,为何争议如此巨大?(4)研究资产定价的诺奖得主为何投资失败?为何没人预见金融危机(来自英女王的灵魂拷问)?
结论是:当问题得到具体界定,且运行环境与理论假设相符时,经济学很有用(例如拍卖理论的运用)。但如果问题更大、更复杂时(经济转轨需要制度配合,金融投资会遭遇“动物精神”),经济学的运用就不那么成功。
(二)经济学是纯粹科学还是与意识形态相关?
作者回顾了二战后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尤其是宏观经济思想史的风起云涌。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轮番登场。他们的学说究竟是“硬科学”还是捍卫理念,是探寻真理还是时势造英雄?有趣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很多受资本家资助的智库兴起,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所以有人说自由放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阴谋。
(三)什么是“合法的”经济学?
我觉得这是全书最有意思的讨论。自然科学研究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什么是对,什么错,show me your evidence。如果想要当医生,要取得医师资格,不是谁都能当医生的,而且行医是有明确的规范的。那么经济学研究有明确的规范吗?什么才是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似乎没有。所以非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奥派)经常抱怨遭受主流新古典的打压。而主流内部也有争论,例如阿克洛夫、希勒、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罗默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批评。
作者的观点,目前占据主流的数理化形式的研究范式,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看上去最“严谨”、最“科学”、最容易被接受。作者认为好的经济学,经济理论我们需要,严谨的实证研究我们也需要,但在此之外依据常识、经验的判断同样重要,但这方面更接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不受人重视。
读完之后的感受,经济学不可能是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凯恩斯说好的经济学家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不过现在大家好像在后面三个方面做得差点。
读完本书让我想起皮凯蒂的最新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不平等也是被意识形态包装,让大众接受。法国经济学家的传统,爱写书、爱参与公共辩论、爱提政策主张,或许更贴近凯恩斯的提倡吧。因此我更尊重皮凯蒂这样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不是数学游戏,不是发论文竞赛,你要做点什么。
《经济学是科学吗?》读后感(三):斯蒂格勒:60岁以前别去碰方法论问题
张 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这是一本出自经济思想史家之手、结合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史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一旦涉及方法论问题,往往让人敬而远之,这个领域确实过于艰深。但这本书并不烧脑,甚至不必正襟危坐读之。之所以能把复杂的方法论问题简单化,并且写得引人入胜,除了作者力图“让本书的主要观点……以非经济学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现给读者”之外,还与作者本人有关。
本书作者罗杰·E.巴克豪斯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是当今经济思想史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治史者著书立说喜欢“寓教于史”,治思想史者也不例外。他们在论证自己观点时选择的史料本身往往就足够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作者的学术身份决定了这本书的风格。此其一。其二,巴克豪斯个人的观点较为中性,从而没有太多说教,让观点各异的读者可以相对平和地阅读,不至于产生抵触进而弃读。正如他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历史故事综合起来,进行修正和放大,并告诉世人,这些故事如何嵌入一个范围更广的故事情节当中。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既不会是保守的(为现代经济学的成就而喝彩),也不会是革命性的(为了推翻当代正统思想而揭它们的伤疤)。”这种态度对于涉及方法论问题的著作尤为必要,因为在方法论领域,不同阵营的经济学家更容易剑拔弩张。
方法论对于任何学科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但主流经济学对它却不怎么待见。乔治·斯蒂格勒曾告诫同行,60岁以前别去碰方法论问题。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说方法论领域难度太大,没必要把青春耗费在这上面。但在我看来,这种告诫另有深意:对于按主流经济学标准程序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一旦过早进入方法论领域,很容易对自己笃信的学说产生怀疑,于是信念动摇,即便不至于改弦易辙,至少思想上也会彷徨痛苦,所以干脆别去碰。待年纪差不多了,还有兴趣的话再去琢磨,到那时,个人思想的一切改变都无关紧要了,而且也不容易改变了。这或许也是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方法论(和思想史)缺位的原因之一吧。
方法论真有那么“可怕”吗?是的。正如本书讨论的话题: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试问,按照主流经济学标准程序“生产”出来的经济学从业者,有几人会质疑经济学不是科学?在主流经济学的圈子里,如果否认经济学是科学,那么“你作为经济学家的资格就会让人怀疑”。但是在方法论领域,关于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这本讨论方法论问题的书,就是对这个争论的生动呈现。
经济学中的争论司空见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争论算是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争论了。不过这种争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内部矛盾”。尽管我们看到了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炮轰宏观经济学,看到了保罗·罗默“叛出师门”这类“大事件”,但这些人和事只不过是自家兄弟之间出现点不愉快而已。克鲁格曼攻击的对象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则是自己搞了个模型来替代他认为错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罗默不过是抱怨团结在罗伯特·卢卡斯周围的那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不带他玩。这样的争论不是这本书关注的对象,它关注的是经济学“灵魂深处的斗争”(struggle over the soul)。
经济学中还有这样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它的“斗争”、“资产阶级”之类的用语在西方的经济学界不是几乎绝迹了吗?沉浸于主流经济学者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了解的是被有意无意屏蔽了的经济学信息,因为他们没有涉足真正的方法论领域,接触到的最多是“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经济学”这种方法论伪命题。这样的“斗争”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书中谈到的“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便是一个事例。有关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是这种“斗争”的集中体现。这个争论的完整表达应该是:“主流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维护者认为它已经是科学,反对者认为它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维护者和反对者分别来自经济学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不了解非正统经济学,甚至不知道非正统经济学的存在,自然不承认或者不知道经济学中还存在斗争,只会认为“(正统)经济学的批评者们根本不了解这门学科”。
来自非正统经济学阵营的批评者并非天外来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他们和正统经济学家一样,都是由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对主流经济学的掌握程度与正统经济学家无异。他们由于师承关系或者别的偶然因素,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思想史、方法论,从而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等非正统经济学学术传统,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因此,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更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因为更了解,他们看得到这门学科的问题和缺陷,看得清这门学科的本质。只不过他们受到正统经济学圈子的排斥、打压甚至迫害,成为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所屏蔽的对象,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非正统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是全方位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层面,到理论、方法和政策,两个阵营截然不同。这两个阵营的对立通过本书中的一段叙述可见一斑。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这个问题,正统经济学阵营中的计量经济学的看法是:“富有科学性就是要通过严谨的方法得出研究结果,就是运用数学方法获得比运用文字分析方法可能得到的更加严谨的结论。科学严谨性意味着逻辑严谨性,要求经济学应关注准确定义的数学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因此,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就是要简化问题,将它们用公式表述出来,形成几组方程式,从而可以用合适的数学方法加以操作。”而在非正统经济学阵营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具有科学性意味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更多、更可靠的经济观察,获取定量数据;拒绝接受理论的一成不变,允许经验观察……对理论进行检查和检验;要有理性,不感情用事,尽可能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运用与相关领域科学知识相一致的行为或动机前提,尤其是心理学;创建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
判断这两种认识孰优孰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经济学并非只有一种声音。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接触另一种声音的机会。读者不一定会接受这种另类声音,但兼听则明,它或许有助于读者认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去为改进这种经济学作出贡献。当然,这本书也有可能就是让某些读者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的那个偶然的机会。如果是这样也不可怕,多元化比一元化更有利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
对于后一类读者来说,这本书只是为你们接触非正统经济学打开了一条门缝,不妨把下面这些已在国内出版的书籍当作通向非正统经济学殿堂的阶梯:菲利普·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杰弗里·M.霍奇逊著《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能动性和达尔文主义》;马克·R.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一卷);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马克·拉沃著《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霍华德·谢尔曼著《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
《经济学是科学吗?》读后感(四):书中金句摘录
“能够提出最有发展前景的新思想的,往往是那些在经济学行当内部潜伏最深的人,那些严肃对待数学模型和其他招致批评的技术的人。”(本书作者)
“我相信,经济学家提出观点的时候如果更谦虚,那他们将会受到更严肃的对待。当然,公共文化为了炒作,喜欢将所有的观点都推向极端。这种倾向其实是帮了经济学家的倒忙。”(本书作者)
“这一大群勇敢的异端分子……他们跟随自己的直觉,宁愿懵懂地看见不完美的真理,也不愿继续支持错误的思想。运用简单的逻辑,而不是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假设,得到的这些真理,实际上清晰明了,前后一致。”(凯恩斯)
“对本就很简单的数学概念做如此艰苦的文献研究是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特点,从推进该门学科的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还需要一种极为邪恶、不讲道德的脑力运动。”(萨缪尔森)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出有效和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设’。”(米尔顿·弗里德曼)
“当然,确实如此。你知道,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这40多年来,我所接触的大量证据都表明它(经济学理论)非常卓有成效。”(艾伦·格林斯潘)
“他们都反对同一件事情,即主流,无论它是什么……之外,在一个叫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人……与像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Eichner)的某个人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动脑筋思考才能发现的联系……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似乎主要是一个知道自己反对什么的共同体,但是没有提供非常系统的、能被描述为实证理论的任何东西。”(罗伯特·索洛)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在政治上仍是倾向于保守。我说某人在经济事务上是一个保守派,意指这个人希望大多数经济活动都由私营企业来搞,并认为通常要抑制私有权力的滥用,要通过各种竞争力量来激发劳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乔治·斯蒂格勒)
“经济学这门学科从来都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时期那样自信过:我们知道,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盖棺定论性的最新研究成果,投入-产出分析和线性编程很快就将使其不仅优雅精妙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新古典综合学派’已经成功地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见本书第7章]加入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微观经济学之中。简言之,真正的经济学就是一座教堂,随时将全部真相显示给我们。”(Backhouse and Middleton)
“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包括……具有相当强代表性的学术型经济学家,以及经过严格技术培训和具有严肃背景的其他经济专家。因此,当中央银行必须转型,从有序金融市场条件下以遏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转变为广泛的市场和资金非流动性条件下以金融稳健为导向的央行时,就面临着来自这方面的巨大阻力。的确,过去30多年间在英美大学普遍获得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培训可能导致他们对整体经济行为的认真调研以及对与政策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认识倒退了几十年。这是对时间和其它资源的浪费,个人和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Willem Buiter)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爱德华·普莱斯考特(Edward Prescott)、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古典学派的理性预期,以及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和其他许多人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阐述)[主要是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的理论] 是自我参考的,至多是不关心窗外事的自娱自乐。他们研究的内在动机更像是出于内在逻辑、知识沉淀资本和对已有研究项目的美学困惑,而不是出于强烈渴望,去了解经济运行方式,更谈不上在经济危机和金融不稳定时期经济如何运作了。因此当危机发生时,职业经济学家们措手不及。”(Willem Buiter)
“[某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这种主导地位会造成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它肯定并不是必然包含共同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当今经济学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对大部分人而言,市场通常有效,但有时也失效。政府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不太好。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帮助他们。这里没有什么意识形态。”(Olivier Blanchard)
“我想同其他人成立一个学术研究组织,向大学、研究生院、新闻广播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提供市场经济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权威研究成果。”(哈耶克)
“一旦尘埃落定,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探究经济学教学是否已被人数不多但很危险的某个流派所攻陷。”(《卫报》)
“看着一个抽象的图形,我或许能看到一只兔子的轮廓。其他人同样看着这个抽象的图形,或许认为它是一头大象。但是对于我来说,看见大象就意味着失去了看到兔子的机会;两者不能同时被看到。对于经济学理论而言,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让你竭尽所能努力看到我的兔子…… 以后,如果你仍然更喜欢大象(或者转而发现了一只鸭子)那你就随意好了。”(Kregel)
“[我们应该]将经济学理论看成是一系列概念模型,旨在用简化形式从不同方面表述总是更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鉴于这些较为简单的模型可能是更为现实但也更为复杂的后续模型的原型,所以对它们的研究要加以保护,以免受到非现实性的指责。”(Koopmans)
“遗憾的是,这种经过理想化和美化的经济愿景导致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所有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他们对经常导致泡沫和泡沫爆裂的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对胡作非为的机构带来的问题熟视无睹,对可能导致经济的操作系统出现突然的、无法预测的崩溃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置之不理;对监管者在对监管失去信心时所造成的危险置若罔闻。”(《纽约时报》)
“通常而言,经济学中使用的方法,要么包含某一现有理论的应用,而很少注意该理论和所研究的体系是否密切相关;要么更糟的是,建议改变该体系使其能够与理论的那些假设相一致。”(菲利普斯)
“为什么要颇费周折使用模型呢?凭借以往有关经济是如何运转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当前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观察,难道不可以作为政策判断的基础吗?这确实应该是政策判断的基础,但是若不借助于模型,做出这些政策判断将是异常困难的,而不是简单的。……选用合适的模型,关注那些经判断对理解这些问题而言是最基本的因素,从而使经济问题得到简化,变得明确。至关重要的是,模型也是对经济过去通常的运行状况以及当前和未来运行状况发生变化的程度进行实证定量研究的框架。由于这些普遍但实际的原因,制定货币政策需要使用经济模型。”(英格兰银行)
“本学会的主要宗旨是促进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定量和实证定量两种方法统一起来的研究,促进采用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以及富有建设性且严谨缜密的方法所进行的鞭辟入里的研究。”(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具有科学性意味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更多、更可靠的经济观察,获取定量数据;接受‘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观点,要以一种允许基于经验观察,包括统计分析和实验检验,对它们进行检查和检验的形式来陈述理论和假说;要有理性,不感情用事,尽可能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运用与相关领域科学知识相一致的行为或动机前提,尤其是心理学;创建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Rutherford)
“经济学是研究表现为欲达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
“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不但没有因为拒绝采纳其践行者的忠告而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削弱,反而还得到了加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由于越南赤字支出给经济带来的有力刺激而得到证实,而不是否认。”(Bernstein)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从(国家干预的)共识管理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这个过程(主要)应归功于新古典经济政策取得成功的证据不断积累,尤其是在东亚的成功,与其他许多国家以前政策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形成鲜明对照。”(Polak)
“有些保守派人士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不智之策的结果。但我认为它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诚然,政府缺乏远见、被动迟钝以及决策失误在经济从衰退快速陷入萧条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若无政府管制,我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萧条之中。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积极、更有智慧的政府,以防止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偏离正轨。放松管制的举动,夸大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复原力——自我修复能力,有些做过了头。”(Pos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