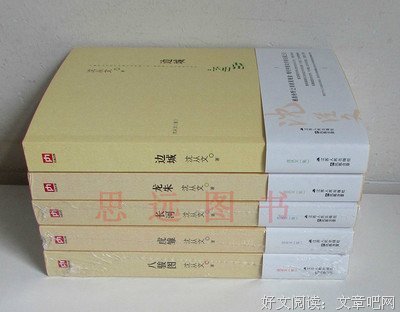《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摘抄
《沈从文全集.1-17》是一本由沈从文著作,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2002-1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沈从文全集.1-17》精选点评:
●除了沈从文我还能爱谁?
●随意,干净,散漫,平缓,朴素,透明,淡泊,清新
●文字很温柔,多读几遍依旧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意义。
●笔力动人。
●虽然这个老头晚年有点不务正业,开始研究下蛊。但我真喜欢他。
●纯朴,生命与悲欢离合之中,如草木虽弱却美而坚强
●闷~
●《灯》《丈夫》 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 《灯》的叙事艺术
●阅读第10卷。沈从文凡是作乡村题材的小说,都实在写得太漂亮了,个人非常喜欢。但他似乎一写到自己身边过亲近的人,抑或以此的原型,就要做出一种姿态,显出特意烘托的样子。大先生这个角色,简直糟糕透了,里面提及的大篇政论,也过乏味。此外描写距离太远的人,也没有拿捏好尺度,虹桥集就是一例。
●直到今时许多故事才刚刚能懂些了 好比走过的路
《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一):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少女时代的张兆和多么幸运,遇到沈从文这样一个浪漫的人。
读《湘行散记》,惊讶于沈先生狭窄的船舱里把湘江沅水写的这般浩浩荡荡,那水手、那吊脚楼里的妇女,多少命运就沉浮在世事风云里。一个时代的小缩影。——当然,也告诉我们给情人的书信是该这么写的。
沈先生是天才,驾驭文字的天才。他没有郁达夫那般科班背景,仅仅依靠几年文书的经历和自我刻苦努力,竟成就了这样的造诣。据说诺贝尔文学奖差点落在他头上。然而那些光环都不重要了,在我来说,他确确就是一个天才。
前年在北京,去老作家李树型的寓所里拜访,随身带了一本他老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作礼,猜想他定会喜欢。
走进他书房,却一眼看到他书柜里的沈从文全集,我们相视会心一笑。
《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二):了不起的大作家沈从文
以前看汪曾祺的小说,知道他曾师从沈从文,也很推崇沈先生。爱屋及乌,我就去看了沈从文最有名的小说《边城》,但当时对他那种乡土味的口语文字风格不太喜欢,小说也没有看完。
再次接触沈从文,是从他的短篇小说集开始,《鸭子集》、《蜜柑》、《老实人》、《入伍后》、《好管闲事的人》,集集好看,篇篇精彩。这时候才开始领略沈先生的巨大魅力。有人说过,沈先生的语言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只要看上几行就能辨认出。我个人以为这种独特和魅力就在于沈先生将汉语口语的单字、古汉语的单字和当时正在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双字词这几种语汇混合使用,并且构造出复杂绵延的长句。句子的构成元素和结构的双重特性使得它不仅读起来富于变化而且表达出的意涵很有一般西方文学因为丰富的形容词副词嵌套和从句结构才具备的复杂精致的特点。
沈先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出身于乱世中正在败落的士绅家族,童年时无拘无束地享受了乡村大自然的奇趣和快乐,远未成年时却又独身开始行伍生活,终于成为以创作谋生的作家。一颗爱好自由感情丰沛的心灵体验生活的种种境遇,观察世间的万千人生,化作笔下源源不断的文字。沈先生的笔有一种魔力,能让人穿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受他和兄弟朋友童年的欢乐天真,以后所见所识长官、屠夫、兵士的五味人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颗心灵自身经历的丰富生活和留下的无羁思绪情感。
沈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这就更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他退出文坛令人扼腕和遗憾。沈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个异数,于革命文学的大潮中形单影只,没有被唤醒民族、推波革命这样大时代的理念浸没,因为他始终有对个人、情感、美好、不幸的敏感神经。因为此,他才能写出让人向往,令人感动,使人唏嘘;也因为这颗心灵的敏感,他痛苦地放下了文学之笔。
沈从文先生两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是上天终究是公平的,他留下的不朽作品和情怀就是对他的最好褒奖和纪念。
《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三):为短篇小说、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正名
小说是文学之王,大多数文学家都通过小说来获得承认,而大多数获得认可的文学家靠的是长篇小说,靠写短篇获得世界承认的作家不多。沈从文的主要著作是不是《边城》、《湘行散记》?当然不是,他本应以短篇小说得名。他的短篇是世界级的。
他最擅长写短篇,因而他的中篇和长篇写得少,也没显得那么突出,文学史评论家可能以为短篇不能成为一个人的代表作品,可是没有他那数十篇精品短篇小说的神作,《边城》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文学地位。
一个好的短篇的分量也许比较轻,但当你把下一个短篇当成台阶,要有所突破时,那你的脚步几乎比登天还难。而沈从文、芥川龙之介这样的人正是靠这样的台阶,踩着前人,踩着自己,一步步迈向他们的文学之神之位。
这世界上可以称之为精品的短篇、中篇、长篇都不多,一个好的短篇可比一个中庸的长篇难写多了,当然写一个完美的中长篇难度更大,因篇幅越长,小说的连贯性、整体性就越难把握,《包法利夫人》是一个篇幅和完美度的极限。
也许我们可以听听沈从文在《灯》中利用小说人物说出的心声:”他们根本不知道写一篇短篇小说有多难。”
在中长篇中掺水是稀松平常的事,可是想一想在短篇中掺水——只能毁了这部作品。
当然,长短篇的创作完全不是一个范畴,因此很多作家在不熟悉的篇幅下有失水准。
很多人写中篇、长篇,靠量取胜,写得很多,就是留不下什么精品,突破不了前人,先重复别人,再重复自己,在作品章节之间重复,在一篇篇作品中重复。
许多人把短篇小说当作小品,其实他们写不好短篇,短篇小说更容易见高下,是一种更接近完美的文学形式,完美的长篇几乎不存在,写长篇的人容易自我感觉良好地大家一起烂下去
沈从文的小说(我是说其中的精品)几乎每一句都是诗,连读起来还是一首诗。有些短篇即使在最后戛然而止,还是让人回味无穷,醍醐灌顶,堪称“未完成的完美小说”。
有人问我沈从文当年真的能得诺贝尔奖吗?我想说,在我的心里,他的作品的分量够得两三个诺贝尔奖,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人只能颁一次。
《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四):《沈从文全集》勘误
尾注嫌简略,多如下,“鲁迅,现代作家”,名人无所谓,不知名的人至少应当标明籍贯生卒年月。否则不如白文不加注。小说散文卷对版本更迭应有所交代,视情况录入作者后期曾经增补删除段落,比如《萧萧》一文,就我所见到的,结尾部分有三种版本。
总体看小说卷散文卷疑误处较多,或者底本原如此,编辑保留原貌。但于今人较易误解处应于尾注存疑。书信卷为作者家属所编辑,也因书信以原信为底本,错误较少。信件注释因为亲属关系,尚佳。
疑误字在正文中位置以数码0132808形式标出。误字下划横线。01意为第一卷,328意为三百二十八页,08为第八行。正文标题算一行,分章数码算一行,页眉标识不计入。书信卷书信编号不计入。诗歌卷与资料卷未计入。
0132808,“扬三打哈欠”,由文后尾注知或为“杨”之误。
0220511,“于是本来的几个人也全来了”,由上文“还有四个不来呀”,疑“本”为“未”之误。
0320602,“在预备上路以前,苦不先应当相熟得同傩喜先生一样”,“苦”疑为“若”之误。
0343621,“世界上是没有女人要我爱她的,。”两标点共用,沈从文著作中尚有多处,其他版本也有。当为作者当时习惯用法。
0425702,“他只望阿黑的险”,“险”当为“脸”。
0431914,“女人以为来客是一个学生了很随便的问”,“了”疑为标点符号误排。用“了”亦通。
0636013,“(就作)为曾听到的神气,把脸转到”,“为”当是“未”之误。
0700724,“历史上很在点名气的圆明园遗址”,“在”疑为“有”之误。
0731214,“是正如药济师在药瓶间”,“济”疑为“剂”之误。
0800922,“是有住到江边小乌篷船(上穿红衣打水粉的年轻女人才能享受的)”,由文意“是”当为“只”。
1013504,“水擒杨么”,“么”当为“幺”之误。也有作么的。
1114525,尾注①在正文中不见有标号。疑在“滩长廿五里,不到十分钟可以下完”后。【附】尾注“①原信旁注:‘共四十里廿分钟直下,好险!’”
1119703,彩图下括号内标注“以上五幅彩图文字引自”,实则此卷共五幅彩图,标注之前只有四幅彩图,此标注之后一页还有一幅彩图,当标于彼处。
1206411,尾注⑤《官场现形记》条,作者“李嘉宝”,当为“李宝嘉”。
1209405,“得谨慎小心,你到的原是个深海边。身体从(不至于掉进海里去)”,“从”当为“纵”。或原为“從”,通“縱”,即今“纵”。简化为“从”。
1401817,“可怜又可配的中国人”,“配”疑为“佩”之误。
1423103,“(穆)脩就手夺取”,上文已有“穆修”,两“修”当择取一种统一。
1601212,“盼望唐虞再世那样文字的’”此句只有后引号无前引号。
1607205,1608207,1608208,三处“邵循美”,“循”为“洵”之误。据卷二十一,信19621207“致邵洵美”页二八五有作者补语“因这里和邵循正常在一处,总把兄名误写,真是抱歉”可知。
1626817,“一个人上面撞进去了”,为引用《野草•秋夜》中文字,“人”为“从”之误。
1636810,“我个工作侧重在”,“个”后疑缺一“人”字。
1716905,“不仅堕落了文学运动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碍这个运动明白的(正常发展)”,“白”疑为“日”之误。
1722212,“因生活或感情遭受挫折时使尔灰心了”“使”疑为“便”之误。
1724010,引诗“短歌徵吟不能长”,“徵”为“微”之误。
2025915,“一会会有关门了”,“有”疑为“又”之误。
2038707,“每顿也未荤二素”,“未”当检视原信。
2100701,“吃的还比较好,家中一月廿有个鸡蛋,隔天(把可吃吃蛋汤了)”,“一月廿有个”疑有错讹。
2127301,其他各图片名称后说明文字用括号,此处未有前括号,当循例补入。
2414721,“(她却说已够好了,比别人)别多了”,“别”当检视原信。疑为“好”字之误。
2729121,“(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此句为谈话记录中冯至所说起始句。别人说话文字并未用引号。此处只有前引号,无后引号。当删。
第二十卷图片质量极差。与他卷迥异。
《沈从文全集.1-17》读后感(五):Forgotten kingdom
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小说,我却还是习惯把他当一个散文家。
标准是什么呢?大概小说者,大多醉心虚构,抟拿住混沌的一团——一个开头,哪怕一个有枝有节的观念呢——搓揉、捏塑,往上贴一些陶土与颜料,最终形成一具凹凸起伏、线条妥帖的器物。可散文家就笨得多了,欢快时顺流直下,遇到烦心事,眼前雀跃的坦途被遮蔽,便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说不出在烦恼什么。
周作人讲,散文是“科学”的,摆不脱人伦物理。他总说自己想藏起来,可每次都被左左右右的人物拖出来讲几句话——“言”与“不言”之间,是散文生长的地带。沈从文通人情、懂世故,尤其依托乡邻,批评时仍寄托关怀、传递亲热,不使人感到侵犯,这是“大先生”必修的功课。而现代文学,其文运、争论,依据的是传媒逻辑,即迅速赶赴传统的边界,选一个光线最强、最受瞩目的位置,拼全力冲撞过去,方能引起对手与公众的重视。因此,沈从文能组稿,办刊物,甚至成为青年作家的领袖,跟人辩论起来却总流露委屈口气,不擅争长短、“搞事情”,盖因为“大先生”的认知。
他一次次回到湘西,看到虎雏们逃走了、街景里并肩走过的女学生投身了革命、旧有的神话人物无不四散,也不多问、不多说,只感叹“这也就是历史,是人生。使人温习到这种似断实续的历史,似可把握实不易把握的人生时,真不免感慨系之!”他知道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神与自然的工作是天然可信任的)。只把断续的一小部分曝露在你面前,恰恰出于天地仁厚,给难堪的人生留一点体面。沈从文听这些故事,“哦...哦...”两声便过去了,深知不该多问。他小说里那些中止的情节、断续的留白,正出于此伦理的直觉。
人少年时感受的一切——审美的、价值观的,乃至一个触痕、一些气味,才是最强大的乌托邦吧。沈所理解的“人性”,如何能脱开湘西的影子呢?这和“本土性”倒没关系,却与“人”之成形过程中种种崇高的非理性连通紧密。渐渐长大,抽枝发芽,也是乌托邦崩毁、消灭的过程。当年以为理所应当的事物,逐渐变成需要争取、拼全力才能保留的残碎鳞片——否则,要眼睁睁看它消失吗?
我出生的市镇在沿江的丘陵地带,没有高山,然而单从老城区走到开发的新城,不过二三公里,就要上上下下花好一番力气。当地的小孩子喜欢跑动,喜欢放开自行车的踏板,从坡顶冲下来,因此养成一股野劲儿,爱探险,在各种地方钻来钻去。我小学的同桌是学校有名的刺儿头。他个子小,手脚却长、大,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经常为一点消息(不外乎打架、上网、滑旱冰)就高高地挥舞起来。他总是清楚小镇里不为人知的角落,譬如哪一家的房子最好看,从哪里走能绕开狼狗的警戒,打柚子吃。
我们的学校在半山腰处,因老城区,四周密密麻麻挤满了房子,有的废弃了,有的翻修一新,招人艳羡,猜想房子的主人到哪里发了大财——总是可以打听到的。有一次,他带我走到一个隐秘的水泥坡顶,大约五到十米的样子,有模糊的鸟形浮雕,怂恿我滑下去。我打量那隐藏在灌木丛中、幽暗不可知的坡底,出于不愿被看轻的心理,咬牙照做了,连衣服也擦破。他大笑,告诉我这是他新开辟的上学路。
老师自然不喜欢他,叮嘱我不要借他抄考卷——因他数学考得不错,引起了怀疑,虽然并非我的功劳。家长会,他的父母从不现身,他却照样来学校找我们玩儿,在教室外的草坪疯跑。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从小跟着小姨生活。再后来,听说他打架犯事,重伤了别人,被逮住。我加他qq,始终没有回应。我常回味那些家长会的晚上,一群伙伴在黑暗中大喊彼此的名字。那种喧闹、充满生气的场景难再复现,可是这么多年,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想要呼朋唤友、啸聚山林的热烈心情是没有变的。
这些上蹿下跳的小孩子,留给我的影响远远多过看电影、聚餐、唱k的无聊聚会,我却与他们渐渐疏离了。大约2008年,本地舆论开始流传重点/普通中学的划分。得益于家庭支持,我考进了距家乡更远的重点高中,在窄而霉的出租屋求学。我的同学大多来自工整的公务员和教师家庭,生活安稳,读书、论辩中不乏真诚的见解,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起伏的丘陵被江岸平原所取代,我心目中理所应当的“自由”大概如此:有冲撞来去的活力,也有勇气选择自己热爱的事业,为之勤勉努力。
我认同岳昕在自述里所说。直到两年前,我独自来京的第四个年头,才惊觉以往在家乡享受的种种庇护、散漫的成长空间,乃至于做梦的权利,在中国无不是“特权”。大城市剥离这些,将人还原为孤立无援的“公民”,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我想起那些童年玩伴,其聪颖、热情,常令我自愧弗如。许多成绩好的却中断了读书,聊起来说是家里安排,愤愤一阵也就完了。只是少年时养成的一切印象,仍保留下来,以为那才是健康、合理的人生。
如今,媒介伦理已取代小规模的人情交际,叫人应付不来,如此将受侵害者剖露在公众面前,常使我感到进一步的残忍。入文学系、写东西、结交同好的新友,不过为将气味、氛围、最为我珍贵的美丽物什也分享给别人。若斗胆换一个词——普遍化,则连带更为整全的理想,希望每个人都能跟随心之所好发展,不遭遇无来由的侵害或阻拦。似乎那些女性议题,对于正义、平权的诉求,并非来自未来的展望,反而是为了回到已被遗忘的乌托邦之中——在当下看来,后者则是更为无力的理想,因其本身就包含了遮蔽与欺骗。没有办法,仍可设想那个王国,设想所有人(包括抗争者在内)热情地生长;设想与那些外出打工的少年玩伴,再次逃到荒乱的稻田,听各样的声音,在渐渐充沛的小河旁边捕捉极其细小、灵敏的鱼苗——尽管常常是倏忽不可得。
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