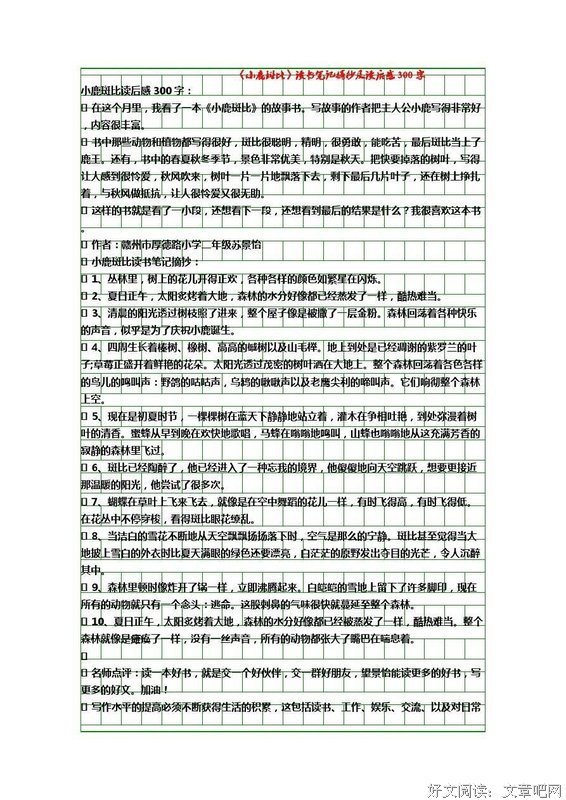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摘抄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是一本由[日] 铃木忠志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精选点评:
●现代人早已遗忘了自己的身体
●体育-舞蹈-戏剧
●修订版重装上市啦!就问你们新封面好不好看!
●病中休养读读铃木忠志还挺合适的。他聚焦于身体(脚)的戏剧观非常纯粹,纯粹到一本书中都会觉得略有重复,但是如此纯粹的生命力又召唤人们到剧场和排练厅去感知
●见到铃木忠志先生的第一天,我的生命轨迹就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
●相当有诚意的再版,设计和用料都特别实诚~远离都市为戏剧而养成身体,是非常令我欣羡的路数。
●“现实主义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给观众幻觉。” 第二次注意到的地方和前次完全不同。单说铃木的人生,那是最让我羡慕的一种。
●读书大概也是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书,两年前的我可能看不下去,可是现在却觉得简直字字真言,尤其那些作者在实践中持续思考所得的关于希腊悲剧的见解,相当独到。 “这就是作为匠人的技术型演员和作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间的区别,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一生都在面对持续创造的挑战。”P71 ,感觉这句他是在表扬自己。
●这是一本很哲学的戏剧书
●稀里糊涂地翻完了 希望有机会在日本看一场剧呀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一):铃木的“野心”
铃木真正厉害的不是他颠覆了人们对经典戏剧理论固有的认知,而是他从不把戏剧封闭在戏剧中、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是一个让观众在剧场里笑或哭,然后在离开剧场后就遗忘一切的导演,戏剧对他来说是一种实验,一种冒险或一种途径,他要借助戏剧辨识人们忽略与未知的感情,触碰社会更多的面向,让人们带着思考看世界,带着思考去改变世界。
这真的不是一本只说戏剧的书。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二):【品 · 鉴】一些感想……
日本话剧大师铃木忠志先生关于戏剧哲学最重要的思考文本,全书最重要的为《关于导演》《关于表演》以及《文化就是身体》三篇,之后为六篇短论或演讲文稿以及一篇访谈,可视为其与西方表演体系的直接对话。
书中插图不多,但都具有很强的美感,配合新版封面,增加了本书的收藏价值。
曾有朋友问我为何在看书之前,就对本书如此推崇,简而言之,除了西方斯坦尼表演体系外,日本的京剧与日本的能剧,代表了不同的戏剧传统与戏剧审美。而铃木忠志,正是站在这一交汇节点上的重要人物。
然而,这样谈难免泛泛。除非你直接阅读铃木对戏剧的哲学思考,恐怕很难理解在艺术世界中如此“逆流而上”的意义。通过类似现象学“放入括号”的方法,铃木将构成戏剧的一层层结构,拆开,将空间、剧本、编排等等依次排除,而在演员与观众的相互“观看”之间,发现了戏剧的元。这里的观众,恐怕不仅是坐在台下,实体的观众,更重要的还有剧场仪式中,不可见的精神寄托。由此出发,铃木重构了表演与戏剧的关系,驳斥了现实主义对于日常现实的谬误认识,指出艺术现实在表演中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寻找到了古代能剧表演的现代意义。
一般认为铃木忠志是一位表演艺术家,铃木训练方法的开创者,但通过本书,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强调身体训练的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学思考。
世界之为肉身,身体寄寓历史,古代能剧演员通过不断的动作重复,达到将历史接引入个体的独特境界。而铃木所创设的训练方法,也正式试图用独特的姿态训练,引导演员重新感受身体,感受大地的意义,感受如何填满整个空间的方便法门。
在结尾说句题外话,将话剧目为这时代不得不学的重要课程之一,有感兴趣的,或可一起,定能让你对惯熟于胸的生活,产生一种新的体验。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三):关于身体性的存在和信息性的存在
我非常非常地喜欢这本书,不过对于书中所说的“动物性能源的消失”或者说人的身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忍不住想要去做另一番思考。
首先,显然每个人对于身体的内在知觉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信息社会中,我们逐渐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某些人信息性的存在远远超过了其身体性存在的重要性。譬如许多网红、vlog博主,他们在网上的形象不仅构成了他们主要的形象,甚至成为了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
其次,我逐渐观察到信息媒介对身体媒介的倒灌:人们会在现实的交往中,模仿乃至直接引入虚拟沟通的模式:比如说见面聊天时模仿某个著名的表情包,或者即使两个人坐在一起,也继续用手机聊天等等。
说到底,普通人对于身体的感受最鲜明的时候是有限的:性、吃、搏斗/竞赛、疾病时,人们对身体的感受较为明确,其余的时间,人类的感受则主要来自眼睛——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
因此,身体性和信息性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眼睛。凡是能被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可以信息化、虚拟化,同样也可以从虚拟世界倒灌,实体化。
当然还有耳朵听到的听觉信息,但听觉信息有趣的地方在于,不管在什么媒介下,人们听到的东西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现场、“新鲜”的声音和录音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视觉信息的差异却大得多。
因此,提高身体感受性的重要方式,在于减少或者说改变使用眼睛的方式。
比如说,铃木在书中有有意无意地忽略眼睛:一是他对于足部的欣赏和珍视,一是他有丰富的在夜间行动的经验,还有离开信息丰富的东京来到人迹罕至的利贺,都有助于减少眼睛的使用,从而增加了人对于身体的感受。
除了这些,书中提到的“铃木训练”我想其实也是一套一改变使用眼睛的方法为主要目的的训练方法:眼睛的用途,不再是吞食、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而是退居次要的位置,为人在实际的运动中提供提示;比如说人在运动中,或者在做饭的时候,眼睛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做好饭,或者为了达到运动的目的。
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被眼睛主导,变成眼睛的奴隶而不自知,从这种角度上,也许说眼睛是蛰伏在人体内的怪物也不为过吧。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四):戏剧在讲些什么?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的狂热爱好者,无法细数历史上有名的戏剧,也没有看过几部戏剧。
我看的第一部剧是林奕华导演的《聊斋》。懵懵懂懂中看完了全场,明白了一些内容,迷惑于另一些内容。之后又看了林导的音乐剧《梁祝的继承者们》,也去了乌镇戏剧节看了《特洛伊女人》,但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时睡着了3次,在中场的时候离场在也没回来。
戏剧,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能够从戏剧中得到什么?
看完这本书,我自己得到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生命。
戏剧,其实讲的就是生命。
铃木忠志眼中的戏剧发生于观众和演员之间,也发生于观众和演员共处的特定场所。演员用其想象力创造了一个虚构空间,试图将观众邀请到这个空间里,传递生命的自发真实。这种传递是否“有效”,便取决于演员由这种自发真实引发的内在状态是否充盈,能否激发一种鲜活的身体感知。
也是因此,身体在戏剧中很重要。而身体,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
戏剧的文本,无论是古希腊悲剧样式、现实主义还是荒诞派戏剧,则是生命的写照。古希腊悲剧充满了强烈的情绪和激烈的行动,是一种悲剧的、戏剧化的生命形式。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平平无奇的、反复平常的生活内容与人内心压抑情感矛盾者的生命。荒诞派则描绘了一种无法逃离日常的生命。所有这些生命的写照又必须通过另一些真实的生命以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一代一代的生命消逝和延续中不断变化。
生命是不断变化的,戏剧也是。古希腊的悲剧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在现代舞台上演,人们是很难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生命力量。戏剧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而变换。这一观点其实在林导的剧中也可以感受到,梁祝的故事不再发生于传统书院而是发生在艺术学院,坟墓也不再是坟墓而是博物馆,梁与祝既男性人格格也有女性人格。导演和演员通过对空间的重构重新唤起了文本的内在生命力。
我想这就是我喜欢戏剧的原因,讲述着生命,充满着生命力,给予观者生命的能量。
去年在乌镇水剧场看的《特洛伊女人》《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读后感(五):铃木忠志的戏剧与超越戏剧
铃木忠志的戏剧与超越戏剧
本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20年第5期
1984年,当铃木忠志写下他那篇最重要的戏剧文献——《文化就是身体》时,他的剧团已经从东京迁到深山里的利贺村,并走入了在这村子里的第十个年头。
利贺村身处日本的富山县,村里沿河修起两条道路,成为唯一的出入口。冬季积雪逾米,道路一旦被积雪或是滑坡阻断,几乎成为深山里的孤岛,与高速增长的日本彻底隔绝开来。从1975年起,铃木忠志将自己的剧团驻扎在此,并在至今的四十余年间在这里训练、演出、举办戏剧节,和写下了长长短短的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又以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为名、汇编成集,题为《文化就是身体》,译为各国文字出版,中国大陆的版本则是2017年方成,2019年又作了修订。书中所录,举凡戏剧、社会、人生话题皆收入其中,这些文章贯穿铃木的各个时期,从而勾勒出他的创作脉络与思想轨迹,最终又汇流为他“文化就是身体”的核心思考。
然而初到利贺之时,日后文章中的许多认知,对铃木忠志来说尚是朦胧的。彼时对于外人而言,这个导演和他的剧团更是让人难以理解——由于演员们每日最主要的生活除了寻找谋生之法,就是高强度的身体训练,如书中所述:“有些村民……一度怀疑我们联合赤军旅,借用合掌家屋作为基地,进行秘密军事训练。”(《孤独的村落》)。对于铃木当时已获得的“日本前卫戏剧代表人物”之类的名头,村民们尚一无所知。
一 “安保斗争”的遗产:“戏剧——社会”、“日本——西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安保斗争”正席卷日本全境。二十出头的铃木忠志亦投身其中,并在这股炽烈的政治潮流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同年(1961年)和剧作家别役实等几名早大的同学共同组建了剧团“新剧团自由舞台”。活动了五年后,又与团员们合力租下了东京一个咖啡馆二楼的空间作为固定演出场地,并将剧团改组为“早稻田小剧场”。“安保斗争”作为铃木前期创作的社会背景,虽很难断言对于他造成了怎样的直接影响,但这一社会运动中一些居于中心化位置的议题,的确可以在他的演出和理论中看到投射,并在日后的创作与思想轨迹中形成延续。
在《文化就是身体》书中所录、成文于2011年的《铃木忠志访谈》里,铃木回忆道:“像易卜生、布莱希特、契诃夫等都想要改变社会,都确信当前的情况已经不可忍受……1960年代日本戏剧艺术家——那时我刚刚起步——也类似如此。他们试图通过作品传达某种强烈的信息。我们说:‘在日本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像寺山修司和我,我们基本上是把戏剧用作一种社会运动。”从中可以看出,“戏剧——社会”这组关系在铃木的创作生涯之初,就成为了他的关注重点。这一时期的铃木对“戏剧——社会”强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视角,其一,他认为戏剧的发展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与社会深刻相关;其二,戏剧与社会在关联方式上,并不是以戏剧作为手段反映社会现实那么简单。在铃木看来,戏剧与社会的连接点,在于新的戏剧形式的创造。当以新的戏剧形式来正面回应新的社会问题时,形式才能得以持久、具备生命力,同时戏剧才能对社会形成持续性的影响。而形式创造一旦不去正视社会问题,只能沦为一种景观,很快就会被更新鲜的形式所替代。
“安保斗争”带来了那一代年轻人在战后对于社会运动的空前参与,也让将戏剧形式与社会挂钩看起来十分自然,但实际上,这种视角在当时的日本戏剧界最初是居于边缘位置的。日本将世纪初由西方传来的、区别于歌舞伎等传统艺能的演出形式称为“新剧”,到五、六十年代,“新剧”进入发展的兴盛期,从业人员、演出场次、观众数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然而在戏剧形式上,面对同时代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新剧”舞台却固守着二、三十年代沿袭而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放在铃木“戏剧——社会”的视角下来看,“新剧”的形式就是和社会问题毫无关系,而成为了一种抽象的技术体系。对于整个年轻一代而言,战后“新剧”都已经是严重脱离日本现实却又牢牢主宰着剧场界存在。铃木忠志的前期思想也因而带上了对于“新剧”的反叛性,这种反叛集中又在对于“新剧”的写实主义美学和方法的批判上。铃木完全不认可“新剧”导演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日常生活的再现,在他看来,契诃夫这样的现实主义剧作大师并不是要将现实生活场景原样搬到舞台上,而是用一个在本民族文化里充满诗意和隐喻的场景,把人物隐秘的心理状态抽象外化出来,把这样的场景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其他民族的舞台上,只能是拙劣和庸俗的。他的剧团更是明确以推出别役实的荒诞剧作为演出目的,在七年时间里连续排演了别役实的《象》、《门》、《马克西米利安博士的微笑》等五个剧本,和“新剧”的写实传统彻底决裂开来。
在铃木这里,反写实作为一种艺术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基于在“戏剧——社会”的问题上让二者直接挂钩,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对“日本——西方”这组关系的自觉。 “日本——西方”在“安保斗争”的时代并不是一组抽象的对立关系,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冲突:安保条约的签署使得日本实际成为美国的附属,民族本位思想亦在此时兴起,加之驻日美军犯罪事件的发生,种种因素推波助澜之下,日本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反美情绪的高潮。而此时的 “新剧”界由日共掌握着领导权,其背后的苏联则正试图调整冷战格局、缓和美苏关系,于是“新剧”界在“安保斗争”当中不仅毫无作为、甚至谴责学生的行为,这让年轻艺术家们对上一代剧场前辈变得极为失望并走向决裂。在六十年代,反写实即反“新剧”,反“新剧”又带上了由日本出发抵抗美苏霸权的政治意味,反美苏的另一面则是对于日本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寻求,“日本——西方”成为那一代年轻艺术家创作中几乎天然存在的视角。铃木曾回忆:“六〇年代的日本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急于模仿西方事物,我希望能够改变这样子的现象。”这种视角又为下一个阶段的超越提供了准备。
二 从文本到身体,从“日本——西方”到“传统——现代”
“当日本社会面对西方影响,从一个农业团体网络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时,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也随之产生。”(《关于表演》)。由六十年代末进入七十年代,铃木从“日本——西方”的思考方式出发,将之置换为“前现代——现代”,并使之与戏剧形式挂钩,从而生产出自己的一系列理论。
1968年,别役实退出“早稻田小剧场”。失去剧作家的铃木不再以推出某类剧本为中心,转而开始以解构、拼贴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从西方当代剧本、日本歌舞伎剧本、日本近代小说截取片段,将之改编、并置在一处,以《关于戏剧的东西》为名创作了一部新戏,1969年完成演出。新戏将演出的重点由剧本转移到了演员表演上,女演员白石加代子从此成为铃木作品的固定主角。次年的续作《关于戏剧的东西2》更使得铃木与白石声名大噪,铃木被冠上“日本前卫戏剧代表人物”等名头,并带着这个戏开始参加各国戏剧节。同年,早稻小又推出了《关于戏剧的东西3》。三连作的演出让铃木完成了在自己创作中由文本中心到演员中心的转换,白石加代子的表演也由是被视为铃木忠志戏剧观念的具现。
如果说60年代中前期,铃木让新的戏剧形式与社会挂钩,以“反写实”来批判业已脱离社会现实的“新剧”,到了60年代末,这种挂钩更加直接和深入:他对“新剧”的反动更为彻底,从反写实走到了反文本中心;反文本中心又不是简单追随某种西方剧场的新潮,而是由于他发现了建立自己全新戏剧形式的基点——演员的身体。在铃木一直以来所思考的“戏剧——社会”的脉络下,演员身体成为他连接戏剧与社会的新的媒介。
大约在70年代中期,铃木完成了日后被称为“铃木方法”的演员训练体系,此训练强调演员的下半身,要求对于重心、呼吸与能量的控制,其基础来源于能剧、歌舞伎的特殊身体性。1974年,铃木排演了古希腊剧本《特洛伊女人》,大幅裁剪了原剧本、并将贝克特的一出短句和诗人大纲信的诗作拼贴进其中。白石加代子与能剧演员观世寿夫担纲主演,他们独特的身体特质籍由“铃木方法”呈现而出,震撼了日本与西洋观众,铃木从此被认为跃居世界大师之席。1976年,剧团由东京迁至偏远的利贺村,走入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动物能量”(或译为“动物性能源”)的概念被铃木从社会学引入戏剧之中,并成为他贯穿至后期的核心理论之一。所谓“动物能量”,指人力、畜力等能源,“非动物能量”即风力、火力、电力等,社会学上以此两者的使用比率来区分现代化与前现代化。铃木将这个标准应用到剧场后发现,大多数当代舞台作品都很现代化,换言之,大幅度依赖着“非动物能量”。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人类身体的潜在能力和各种机能正经历着急剧退化,同时以“动物能量“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已大大弱化了。而这一社会结果直接延申到舞台上,就是声光电的广泛使用和演员对于自身身体意识的普遍弱化。为了面对现代社会 “非动物能量”的过度使用所导致的人的机能衰退,铃木将剧场里的焦点转移到了作为“动物能量”的演员身体上。
对于演员身体的关注,一方面是铃木在“戏剧——社会”问题上的新的切入点,一方面是对于“日本——西方”问题的拓展。当铃木将“动物能量”的概念引入剧场,并且将之付诸实践时,他把营养来源放到了日本传统艺能上。首先是能剧:“日本能剧,则是一种几乎不使用非动物能量的前现代戏剧形式一直存在到今天……本质上,能剧弥漫着一股纯粹以人的技能和能力把东西创造出来的精神,我们因而可以把能剧视为前现代戏剧的缩影,一种由动物能量驱动的作业。”(《文化就是身体》)。歌舞伎也同样如此。铃木对于能剧与歌舞伎的吸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艺能的形式移植到当代剧场里、嫁接出一个“民族化”作品,而是从重心、呼吸、能量这几个被他称为“看不见的身体”的角度去重新发现传统艺能,从这个角度用和传统艺能同样的身体原则来重建一种新的当代表演。建立这种新的表演的目的,则是在当代社会重新为人类找回作为“动物能量”的身体。在“日本——西方”问题上,铃木一方面从身体切入,由深层次发现民族戏剧特性,从而重建当代表演;一方面从当代社会视角入手看待民族戏剧,发现它能为当代社会提供营养的部分,让“日本——西方”和“戏剧——社会”两组问题直接挂钩。
尽管能剧与歌舞伎往往是以一种高度“日本化”的面目为人们熟知,但当铃木看待这些来自本土的艺术样式时,并不去把它们作为西洋艺术的对立面进行观察,而是将“日本”与“传统”挂钩,将“西方”与“现代”挂钩,对于日本“现代化=西方化”的现实,铃木并不去否认或回避,而是对这一过程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于是,当他在自己的戏剧中运用来自能剧和歌舞伎的身体要求时,他所做的不是一种对艺术进行本土化的行为,而是抛弃了“日本——西方”的地域性二元对立,用适用范围更大的“传统——现代”的思路来提取传统艺术的价值,将自己的创作变成为了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行动。在铃木这里,能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日本的固有艺术,而是在于它蕴含着前现代的传统;能剧作为前现代传统的价值,也不是在于它的古旧,而是这个传统——作为“动物能量”的演员身体——能够指出当代社会的问题,在剧场里提供一种持久的对抗手段。
三 “文化就是身体”
1976年,“早稻田小剧场”迁往利贺。铃木买下了村中的一座日本传统建筑合掌造,由建筑大师矶崎新重新设计、改造为剧场“利贺山房”。铃木以这里为基地,大幅展开戏剧活动,在世界各国讲学、巡演、开设工作坊,连续出版评论集与理论专著,并在1982年创办了“利贺国际戏剧节”。1984年,“早稻田小剧场”改组为“利贺铃木剧团”,铃木频繁和不同国籍的演员合作,排演西方经典剧本。此后的数十年间,又有四座剧场在利贺陆续树立起来,利贺从一个偏远小村庄成为世界性戏剧重地。
从剧团迁至利贺直至今天,铃木从“动物能量”的概念出发,一直以“文化就是身体”作为自己的核心理论,延续着“戏剧——社会”的思考脉络。铃木如是定义文化:“当人类与自然或世界接触时,会通过五官感知和接受外来刺激,并做出反应。那些制约和修正这些反应的社会规则,我视之为文化……从这个观点看来,文化存在于群体如何使用动物能量的方法当中,以及人们对管控能量的规则所给予的共同信赖。”(《传统与创造力》)。而在现代社会,“一个依靠非动物能量的社会必然是更文明的。然而,对我而言,一个文明社会不一定能够就是一个文化社会……为了应对现代化削弱演员技艺的现象,我努力地还原表演中身体的整体性……我们创造一个机会,重新巩固我们当前已被肢解的身体技能,复苏身体的感知和表现能力。只有全身心投入去这样做,才能确保我们的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继续发展。”(《文化就是身体》)。
作为对这个观念的实践,他把自己的训练法“铃木方法”发展为了完整而周密的系统,这套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西方许多戏剧院校的基础课程。铃木非常有意识地把这套训练法视为超越戏剧本身的手段,他明确表示,铃木忠志训练法不是为了戏剧而存在的,他只是借助戏剧这种途径通往某个目标。而目标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要让演员重新意识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衰退的身体感知。通过让演员找回自己作为动物能量的身体,由此既成为更好的演员,也成为现代社会里更好的“人”。
上世纪80年代起,铃木让不同国家的演员在自己的剧中同台出现,共同运用“铃木方法”演出,又各自使用母语,剧本也往往是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契诃夫,这让他的作品充满“世界性”色彩。而同时,在谈到作品的主旨,和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时,他的出发点又一次回到了日本本土,更多谈论日本具体的当下问题。60年代“日本——西方”的视角到70年代替换为“传统——现代”,进入80年代后又发展为了“本土——世界”,虽然把关注点重新放在日本的特性上,但不是为了区别于西方,而是从对于本土的思考出发而到达世界:“我试图传达的寓意,只想是批评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但是我传达寓意的对象却不单单是日本人……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产生想要改变社会的意愿,超越了那个国家的界线而引起普遍共鸣时,就成为了伟大的艺术。”(《铃木忠志访谈》)
从“新剧团自由舞台”到“利贺铃木剧团”直至今日,铃木在他六十多年的岁月中由城市到村庄,践行着他的戏剧,又超越了戏剧。各个时代,无论他的演出如何发展,理论如何转向,铃木始终以浓烈的情感探索着这一切的可能。在利贺的第十年,铃木忠志写下了一篇名为《孤独的村落》的文章,文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都只是凡人众生。不管觉得自己有多强大,我们到底都无法改变太多的事物。我们的作品看起来再多么有革命性、多么有影响力,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然而,我们必须勇敢地、毫无顾忌地往前推进——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艺术家生存的核心悖论。我们必须一直追求自己的理想,直到死去的那一天。正是这种转瞬即逝的共同特质,把戏剧和生命紧紧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