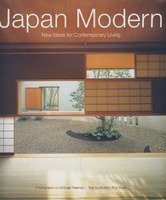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100字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由[日]柄谷行人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精选点评:
●以系谱学的追根溯源发现“文学史”、基督教、儿童、临床医学和透视法等知识话语中隐藏的“颠倒”,从而对现代性作出质疑和批判。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底色和后结构主义影响。标题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正如作者所说,他把标题中的每个词都放入引号来反思。柄谷意在摧毁“文学史”,即把明治初年文学放到现代国家成立的诸种“装置”下理解,展现文学现象和日本政治的复杂共生共谋关系。“风景的发现”是纲目,所谓“风景的发现”隐喻着将原来没有的东西(如“内面”“自白”)叙述为不证自明的建构行为,而这种行为和日本走向现代是相伴而生的,这一思路从实例上再次说明文学并非空中花园。柄谷此书也是一本西方理论点鬼簿,但出入自如并做了批判,如扬弃《疾病的隐喻》尤好。中日都历经了“浓缩”的现代化进程,以此审视现代化中的遮蔽,是本书最大启示。附序中指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闭环,眼光毒辣。阅读不需要日本文学和日文基础,虽然看完又迫切地想学日语了!总之强烈推荐!
●行文中引用的哲学家都是我的菜
●好看
●看不懂,硬啃了一半,脑仁疼得厉害,先放着吃灰了。
●虽然读不太懂,但在读了四个月网络小说后,用弯弯绕绕的术语和全然陌生的日本文学涤浣一下思维也不错。
●之前有幸读完定本译文了,买一本放着的目的在于万一哪天遇到了活的柄谷,扑通跪下之余还可以掏出来要个签名……(拿《民族与美学》要签名感觉还是太寒酸了
●德曼对柄谷行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柄谷行人将日本文学史或日本本身,追溯到“现代”这一观念,它们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相关联。日本现代文学的诸内容其实与现代国家的制度相互渗透,因其作为一种制度在现实中有着特定的认知机制。我们所说的文学的“现实”不过是一种透视法装置的表达,世界以及现实的“深度”不过是由某人的固定视角所发现的事态。而透视法就是在此过程中同时创造出主体和对象的装置。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德曼式的解构主义方法,柄谷行人试图寻找促使现代文学成为不证自明的那种基础,并将之分离在现实条件之中。
●触及生命的一本书。它也自有它的生命。
●半年前多读过老版,这几天抽空读了读新版。前两章主要讲理论,后面几章差不多是基于理论的文学批评实践。柄谷行人的出发点是基于从文学史的存在者链条来定义文学的做法的怀疑,所以他要回到没有任何前提的文学本身上去(回到实事本身)。这样利用了悬置方法后柄谷行人得出了已被建立的内面(主体)发现风景(客体)的结论。柄谷行人认为这个主体是一个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P15),这是一个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形象。但是柄谷行人认为这个主体的生成是现代意义上的,是拉康、阿尔都塞式的一个被构建,在“装置”基础上生成的主体(也可能是被压抑而生成)。新版前言里关于民族主义和文学的关系值得一看。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一):个人的举例理解1.0
一、 风景的发现
认识论上的“颠倒”装置以及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制同时发生形成“共谋”关系
背景:20世纪70年代于美国这一“外部”的场域获得了从“起源”上观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视角,又在和解构主义者的交往中受到了启发
10所谓“风景”,正是拥有固定视角的一个人系统地把握到的对象。
风景不过是语言,是过去的文学。就如同中国古诗里的风景,人们不会关注真正在诗中看到了什么,而是在“风急天高猿啸哀”里感受到诗人的悲戚,很少人会在眼前思索这么一副画面。后来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真正能够想象出作者所看到的衣服图样的人很少,但是我们读者知道,衣服描绘的本身是华丽。文字本身的想象代替我们去看见。
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夏目漱石所质疑的就是所谓的风景是否是其本身的样子,是否只是我们在西方的影响下所思考认知的。作为养子的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命运是否可替代,相同,他也在思考日本文学是不是该走现在的路,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总之,就是因为对现状的不满,大师们在结构上另辟蹊径,探索日本文学的出路。
二、崇高
18 康德:崇高在于我们内在的理性之无限性得到了确认。
我们一直认为美是主观的东西,但是却是在对象物(客观)上面发现崇高之美。浅显一点,这是一种颠倒,是一种陌生化的手法。通过创造一种新的透视视角来观察世界,以发现被忽视的风景。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二):三四五章摘要
三、写生文 夏目漱石:作者对人世的态度是大人对待孩子、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 幽默:显示了既可以是自己同时也是他者力量之存在 四自白 宗教性质的自白、忏悔仍旧存在。宗教仍旧以别的方式顽固地存在于现代社会进程中。 《蒲团》写的只是“丑陋”的心而不是“丑陋”的事情。当然这个形容词是作者本身加的。意淫在宗教看来也是罪过。这是一种无以类比的颠倒。人们时时窥视色情的发生,在这种监视下,“内面”诞生了。因为禁止而诞生。至此,真理和性和自白以某种形式挂钩。 73“初看起来西欧社会仿佛已远离基督教,而实际上社会的各个方面仍是由基督教组织起来的。“ 自白是为了反抗,支配者是不会自白的,自白本身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权力意志,于是自白就形成了。 描写方法中除了主人公外均不可透视 五疾病的隐喻 104 医学本身即是中央极权的、政治的、而且其中有着将健康与疾病对立起来的结构 疫情时期了解医学方面心情更加急切。原本我就对医学方面十分关心,认为即使不是专业人士,也十分有必要自学医学常识,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多听多看。但是在医院每当拿出稍微有点专业的问题询问医生(我并没有挑衅意味,单纯是关心自己),就会遭到专业人士的恶意:究竟谁才是专业的? 在这个时候对医学垄断的厌恶更加强烈。但是在大多数时刻,只能将信将疑,今天医患关系的某些嫌隙可能源于此。
儿童的发现这一章做了一个浅显的归纳 好多地方仍旧存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短评(随记)
岩波定本前三章改动不小。本来前三章就是这本书吃重的地方,改后感觉更为清晰。
这次重读有几个体会,均关乎这部随笔之作为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巨大影响。我觉得大概是柄谷完成了非欧美学者的普遍期待。面对这批需要西方坐标才能定位的本国文学作品,如何摆脱补余的位置和影响的焦虑,真正讲出既贴合文本、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柄谷“现代化的实验室”是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现代制度作为今日世界弥散性、决定性的存在,在西方漫长的发展里被“自然”化,反倒是在并非其源地的非西方展现出了其运作机理,所谓“露骨的存在”。而如果着眼于柄谷的论证技术,柄谷也做了很好的示范。这本书中对西方理论的征引还没有像《作为隐喻的建筑》以后的作品那样形成了系统的反思视角,更多是直引,但也大多准确恰切,柄谷首先完成了向日本学界妥帖绍介西方理论的任务。而全书以“制度”和“颠倒”为核心框架,每章都扣在这个主题上,理论与现象比例得当,又保持了一定的弹性(从定本和初版本之间的众多修改即可看出),容纳了其他对话者进入的位置,又给自己留下了未来的延展空间。也是个很理想的博论框架了。而着眼于理论贡献的话,柄谷对“起源”(Origins)的理论提升不亚于萨义德对“开端”(Beginnings)的偏爱[虽然我个人感觉感觉柄谷的“起源”没有突出这一复数向度]。后世再做起源史,是绕不开柄谷的了。而当“起源”与“颠倒”结合,看似是“回到起源”,其实恰恰是为了颠倒起源,或言,对起源的自然化。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僵化搬迁和机械对应,对现代毫无保留的接受,无疑是对“渗透于我们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追认”,而柄谷几十年的理论追求都是:寻找能够挑战“现代”之为“现代”的资源。漱石、子规、二亭叶四迷、志贺直哉,柄谷对他们的论述角度是:在那个我们被变为“现代”的时刻,而后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起源”里,有颠倒“现代”的潜能。只有从“潜能”的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抵达文学的历史性。读第三章胜过读几大册假如没有文学史。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四):被发明的现代性
现代的发生(近代化)在东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间错综着落后、侵略与不平等、民族、战争、西方、语言等等问题,本书集中探讨在东方的语言与心理(也即现代文学)在现代(西方)化的被动/主动影响下,短时间内的迅速清算、发明并建立新文学的历史。柄谷行人在这一问题上迅速寻找了一个客体对象——“起源”,他假定日本文学现代化存在一个起源,或者说他想在一个看似平缓被动的文学历史中分割出一条清晰的古典——现代三八线来。
这样一个探寻现代文学起源之旅的开始是迷人的,犹如跟随福柯及其后继者打破顺畅的正史,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被吃掉的真相和人——风景与内面是被现代人突然“发现”的。这些心理(自我与环境/风景的对立)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心理习惯,然而在现代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古典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自我意识地扩大,因此现代文学无非写了一种状态:一个自我意识觉醒(认识到自我之外是一个彻底陌生、固定的风景)的人身处一个不属于自我的客观荒原中怅然若失。所谓人之“内面”,并非是一个真正不可认识的主观自我,而是被定义的,被允许存在的和真实的人之内面。在私小说一类的“内面文学”中,内面本身成了一种可被观赏的风景,这一特别之处是内面文学会给现代读者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通过言文一致(尽管做不到彻底),通过一种自白制度(罪-欲望和秘密的揭露)。现代文学发生了,在柄谷行人看来这意味着现代人——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的出生。
书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柄谷行人在例证“风景的发现”时,以古典东方的写意传统作为不同于现代的古典“风景”。也就是说,古典文学艺术中的风景并不是一种客观的“风景”而是经过主观加工和传统引用后的一种意象象征。但现代的风景从一出现就是一种外在于自我的客观存在。事实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恐怕大有人在,宇文所安认为中国诗歌是有非虚构传统的,相反华兹华斯(对柄谷行人是现代诗人)的诗歌中的风景是无所谓非虚构与否的。
何以出现这种鲜明的对立观念?
如果直接问柄谷行人古典文学的写意风景中究竟有没有“风景”?他或许会抛置出一个新的问题,今天的现代读者是如何看古典文学的?如在古典中发现“风景”(宇文所安)恰恰是一种完全的现代阅读心理。古典文学中当然有可以被认为是“风景”的叙述,但这对当时人的阅读心理来讲,是不重要的。
柄谷行人提醒读者警惕自然而然的顺畅历史的同时,读者也要自发地警惕一种被揭露的“真相”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好书,提供了一种关于现代性对话的可能。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五):对东方文化观的一次祛魅
正文开始之前,我必须对柄谷行人吹捧一番。老早就听说柄谷的大名,但心里对他的期待值并没有很高,故此第一次读他选择了这本据说较能全面代表柄谷学术观念的作品,想着如果寡淡无味就无需再读了。在读本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分别读了一点朗西埃与阿甘本,但在翻开本书后,朗西埃与阿甘本带给我的震撼迅速淡化了,要我说的话,这两位欧洲学术明星在柄谷行人面前实在有点相形见绌。我后来反思此事,怀疑自己是不是仍然有一丝“东方的自卑”?此前我竟无法想象一个来自亚洲的理论家(好吧,因为我私底下不把萨义德当成亚洲人,斯皮瓦克也不算,而柄谷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能够使我如此折服。
首先得强调这本名字看起来像是“文学史”的书绝不是一部文学史。
在第一章“风景的发现”中,柄谷以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为起点,引出漱石对日本文学史观的质疑和创新,再到对日本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言文一致运动”,二叶亭四迷、国木田独步、森欧外、正纲子规、高滨虚子、北村透谷、中村光夫、坪内逍遥甚至柳田国男、冈仓天心等一系列近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探讨了“风景”这一过往处于被忽视地位的主题逐步在现代性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中显形。“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风景的发现”正是对其起源的溯源,这里蕴含着一种现代性固有的颠倒,柄谷以考古学式的梳理指出此种颠倒所造成的对历史的遮蔽(它使历史变成了“历史性”)。
紧接着就是“内面的发现”。内面,因在符号论式的装置之中的颠倒而得以出现。在“言文一致”的进程中,口语化写作的“汉字御废止”使日本文学重新思考自己与中国人不同的汉字经验,从表意到表音,汉字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而被消解,语言通过声音性直接获得意义的过程正是内面的发现。这一演化,并不局限于文学,它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科学观对内面的覆盖源属同流。
此覆盖较为直观地体现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视角问题,柄谷先是提出了“写生”的概念,在后文中又指出“透视法”这个颇具现代性属性的装置。作为风景的陌生客体通过透视法的颠倒生产出了“主体”,主体再以先验的视觉性决定了绘画的角度,此时的“写生”被定义为“科学的”,但它只是脱离了内面的“写实”而已。柄谷认为国木田独步的写作与卢梭的某些文本类似,在他那里语言与主体不再分离,互为一体,这种意义上的写生突破了“写实”。
“所谓自白制度”、“所谓病之发现”和“儿童之发现”这三章里,柄谷继续着以内面的发现为出发点思考其中颠倒因素的追溯。这里我认为最有趣的是把疾病曾经作为象征和隐喻扩大为文化观念的问题,柄谷举了德富芦花的《不如归》使得结核病神话化的例子。另一方面,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隐喻》中认为,对某些高危疾病(如癌症)的治疗成为可能之后,疾病的隐喻也会不攻自破。然而柄谷在此提出质疑,疾病的治愈使得患者从隐喻中解放出来,但隐喻本身并没有消失,它只会更换一种形容而继续存在。在原始文化中,人们把疾病当成神秘化的无常力量看待,而现代医学的胜利又使得人们发现了“病原体”这一对象,从此疾病从飘渺的神话变成了敌对的客体。西方医学似乎将“病”看做了产生作用的主体,“治病”就是把治病之主体实体化了,这一观念本身就含有病态成分。不需说,这与自西方启蒙运动肇始的理性中心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把疾病视为医学的或者神学的,还原到一个“原因”上去,这造成了我们对诸种关系的系统性的忽视。
在“关于结构力——两个论争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坪内逍遥与森欧外对于文学的“无理想”论争。坪内逍遥举莎士比亚为例子,认为莎翁并没有高举“无理想”的大旗,但其作品不能被归类为任何一种“理想”,莎翁却被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柄谷认为逍遥提出的此种“无理想”乃是未经透视法剖析出“深度”的理想。森欧外的理想却需要一整套透视装置来制造“深度”,而且带有“大小”的阶层属性。“深度”,或者深层,正是基于一种透视法制造出来的“精神的视觉”。这种视觉效果并非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只是一种作图原则,使透过事物、话语来观察的方法成为可能的,只不过是作图上的灭点而已。而这个存在最终也可能会被吸收进透视或历史主义的展望中去。
“文类的消灭”一章,柄谷以坚持形式主义的漱石为例,漱石在森欧外与坪内逍遥的论争中倾向于逍遥。森欧外相信类型是不可并列的,他谈的是类型的消灭,结合自己作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优越性”,欧外只承认文学发展中的“美的阶段”。但漱石否认了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浪漫派与自然派的划分更多是在命名上,两者实际上互有牵扯,很难割裂,因此并非只有一者才能存在于文学史而另一者必须被排除。巴赫金也很重视类型,他说“类型是文学发展进程中创造性记忆的代表”,“为了正确地理解类型,有追溯其渊源的必要”。现代小说是在文类开始消灭的时候诞生的,“现代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暗含着某种阶段性进化的假象和对多类型的覆盖,而超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者们又试图恢复类型。漱石却是通过多类型的写作实践,把主体视为复数的自我之堆积,与现代小说这一综合统一的虚构斗争。
柄谷行人自身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在政治上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历史学思想与福柯有相似之处,文学评论方面又带着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影响,而他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也很亲密。单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涉及的庞杂知识背景和纷繁的哲学流派就足以看出柄谷学识之惊人。因此阅读这本在作者34岁时写下的“代表作”,需要不小的耐心和足够的理解能力。
之所以说本书是对东方文化观的一次祛魅,并不是说柄谷像萨义德那样专门去反思东西方文化交际之中的世界性问题,而在于柄谷以多种西方哲学的分析手法对日本文学的这次考古,证明了东方其实一直都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文化浪潮之中从未远离,柄谷的这次尝试重新定义了我们与西方思想及其方法的关系,在西方文化面前,东方既不像一些自大的亚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各有体系,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完全没有自我”。地球可能从未被分化为两个阵营,除了在名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