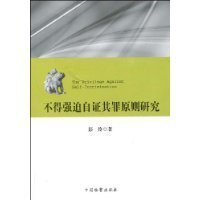自证读后感锦集
《自证》是一本由姚治华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证》读后感(一):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81-89讀後
繼續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頁81-89,記如下。
一、世友有沒有否認「一智是其他智的境界」?
《自證》頁83:「世友說智不是境界,即不是對象,……但仔細考察《大毘婆沙論》,我發現世友在此觀點上與毘婆沙師相矛盾。當討論是智還是境的數量更多時,毘婆沙師明確說:『智亦境故……彼智相應、俱有等法及智自性皆是境故。』據此,我們總有比智更多的境。這一矛盾或許顯示了迦濕彌羅和犍陀羅說一切有部論師間的不同意見。」
世友說「非境界故」,是說「一智不是其自身的境界」,但沒有否認「一智是其他智的境界」。而毘婆沙師說的「智亦境故」,是說「一智是其他智的境界」,不能理解成「一智是其自身的境界」。毘婆沙師的「自性不知自性」就意味著「一智不是其自身的境界」,這和世友「非境界故」是一致的。
二、「三和合」所生的是什麼?
《自證》頁85:「儘管眼或感官在認知一個對象時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若沒有感官、對象和識三個要素的結合,不可能有認知。然而,在認知智自身的情形下,我們見不到這三個要素,更不要說三者的結合。世友從此角度駁斥智之自知:『若自性知自性者,世尊不應安立「三和合觸」,謂眼及色為緣,生眼識,三和合故,觸乃至廣說。』」
這裡引用《婆沙》原文,最後部分應句讀為:「三和合故觸,乃至廣說。」「三和合」,說的是「觸」是怎樣生的,並不是說「識」是怎樣生的。「識」本身就是「三和合」之一,不宜說「三和合生識」或「感官、對象和識三個要素的結合產生認知」。
由此,《自證》頁85-86說:「認識僅在此三個要素可以獲得並且結合在一起之時才是可能的。缺少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認識就不能發生。然而,智的自知只有一個要素,即識,因此這是一種不可能的認識。此外,說一切有部與經量部就『觸是否三個要素的和合』進行論辯。」
由最後一句看,《自證》有時候也明白「三和合」是在討論「觸心所」的問題,但不知為何前面總把應當屬於「觸」的含義解釋成「認識」。
三、「自知心是不善故」是說「惡心」還是一切能自知的心?
《自證》頁87引窺基的解釋並說:「『自知心是不善故,此為正智,非邪惡故。』此論證中暗示著這樣一種假設:一切心是有漏的或惡的。除了持『心性本淨』的大眾部之外,主要的佛教部派都持這一觀點。」
《婆沙》的「若自性知自性者,不應建立『惡心遍體皆是不善』,以了自體非邪僻故」,是說,假如自性本身也是所知的對象,惡心儘管在了別其他對象的意義上是「惡心」,但在了別自身的意義上不能說是惡心,因此,在這種可了別自體的假設下,惡心不會「遍體」皆是不善——了別自體的一分不是。窺基的解釋也是這個意思。從中看不出來《自證》所認為的「暗示的假設:一切心是有漏的或惡的。」
我想,也許《自證》是把針對「惡心」說的「自知心是不善故」寬泛地理解成了「(所有)『了別自體的心』是『不善的』」,才認為暗示著「一切心是有漏的或惡的」之假設。實際上,「自知心是不善故」只針對假使能了別自體的「惡心」而說——善心假使能了別自體,它依然是善,因為是如實的了別,也是正智。「是不善」是說惡心的自體是不善,是說「所了別」的性質,《自證》把「是不善」當成在說「能了別」的性質了。當然,在了別自體的假設下,能了別和所了別是同一物,但我們要清楚這句話在語法上的結構——「自知心是不善」應理解為:自知『心是不善』,而非:『自知心』是不善。因此,「此為正智」是說,能夠知道「不善心是不善」的智是正智,它當然是善的;而不能理解為「正智」是不善的。這和「心性本淨」的論題是沒有關係的。
四、以「四念住」「四諦」等為例論證「自性不知自性」的邏輯是什麼?
《自證》頁86-89之小節名《解脫論》,其中說:「世友對智之自知的其他駁斥與解脫論議題相關,包括邪見、惡心、四念住、四諦之智、前世記憶以及他心智。……第二組解脫論議題與修習四念住和證悟四諦有關。……」
我覺得,毋寧將該小節歸入前一節《知識論》。雖然《自證》把它叫做《解脫論》,實際上這些都是邏輯與思辨上的推論,和《知識論》一節的邏輯沒有差別,只是舉了具體的例子。
四念住的例子中,世友說「若自性知自性者,則四念住應無差別,以身念住即法念住,乃至心念住即法念住故。」
《自證》頁87-88對此解釋道:「據說一切有部的觀點,修習四念住或證悟四諦都應該漸次而行,因位它們彼此不同。故此建立不同階次的修行,以表示不同層級的果位。……」
這沒有說出世友的邏輯。為什麼說「若自性知自性者,則四念住應無差別,以身念住即法念住,乃至心念住即法念住」?
因為,能知者,是「法」,假如身念住能知自身,它就是「『身念住』念住」,「身念住」是「法」,那麼,「『身念住』念住」就是「法念住」。同樣,受念住以「受念住」即「法」為對象,也是「法念住」——既然一切能知都是法,當它本身作為所知被自身了知的時候,它就是「法念住」。
這和「惡心」的例子類似,都是從概念的邏輯上來說明為何不能認同「自性知自性」。這還是邏輯上的「理證」,而不是解脫實踐上的「事證」。
《自證》頁88:「而大眾部則持有這樣一個觀點:當某人進入現觀時,他能在同一時間證悟四諦或修習四念住。」
這句話暗含著「有部不認為行者可在同一時間修習四念住」的意思。其實,「修習」不是「習修」,《自證》這裡說的「修習」,其實就是「修」——否則就必須翻譯成「習修」。「修」不僅包括「習修」,也包括「得修」,不僅包括「現在修」,也包括「未來修」——這是《婆沙》反復強調的。既然「得修」也是「修」,就應當明白,有部認為,在現觀之前,行者就能在同一時間修四念住。
這裡再解釋一下《婆沙》「復次,若自性知自性者,四聖諦智應無差別——以苦智即道智,乃至滅智即道智故」的含義。
「苦智」的對象(所緣)是「苦」,但苦智本身(能緣)是「道」,假使說苦智知自身,那麼,苦智知「道」,苦智不就成了道智嗎?同樣,集智、滅智都是道,如果知自身,也會成為「道智」。這和「四念住」的例子仍然是一樣的邏輯,都是純粹從思辨上展開的,不是在談解脫實踐。
五、「緣自相續」是「緣自體」「緣自品」的含義嗎?
《自證》頁89:「更重要的是,此智不能知其自身,因為這與『他心智』的本性相矛盾。然而,此處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他心智能通過禪定證得,某人在禪定中怎麼可能不知其自心?因為在一般理解中,禪定是一種自察和自省的修習。此問題在《大毘婆沙論》中有所討論,毘婆沙師給出了答案:『又他心智,雖加行時亦緣自相續,而成滿時唯緣他相續。』……因此,我們面對一個兩難情形:如果智知其自身,就沒有他心智;如果有他心智,就沒有智之自知。」
《婆沙》引世友「他心智」的例子來證明「自性不知自性」,和前面「邪見」「惡心」「身念處」「苦諦」等例子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緣自相續」和「自性不知自性」的問題其實沒有多少聯繫,因為「自相續」不是「自體」「自品」。
《婆沙》說「他心智雖加行時亦緣自相續」的「緣自相續」,是說緣非現在的自心,比如緣前一剎的自心。前剎那心望此剎那心是「自相續」,但不是「自體」「自品」「自性」。
世友的邏輯非常簡單:「他心智」如果能了自體,就該叫「自心智」。《婆沙》這裡的「緣自相續」雖然也是討論「他心智」為什麼叫「他心智」的問題,但和「自性不知自性」的問題關係不大。
六、其他
1、
《自證》頁81:「世友和覺音都是來自犍陀羅的說一切有部學者。」
「覺音」當作「妙音」。
2、
《自證》頁81引《婆沙》:「問:何故名智?答:能知、所知,故名為智。」
不宜點頓號。「所知」不名智。
《自证》读后感(二):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124-140讀後
繼續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頁124-140,記如下。
一、領納現量的「能領納」與「所領納」是什麼?
《自證》頁124:「②它領納益或損的受;③其對象即受一定在現在;④它與『了餘境識』的根現量同時生起;⑤但它不與第三種現量即覺了現量同時生起。」
能領納是「受」,所領納不是「受」,是「自所隨觸」。否則就有「受」領納自身的過失了。「其對象」也一樣,即「自所隨觸」。領納現量當然與識同時生起,但不一定與「依根現量」同時生起。有領納現量時不一定有依根現量。依根現量只在取「五外境界」時才生起,領納現量在不取五外境界時也可能生起。第五點說得不夠嚴謹,領納現量和覺了現量可以同時生起,只是領納現量不與緣它自身的覺了現量同時生起,並不排除與緣其他的覺了現量同時生起。
同樣,《自證》頁125:「領納現量的對象是內在的受,……而領納現量因其領納受的內在傾向……」
兩處「受」皆應作「自所隨觸」。
《自證》頁124:「我們發現眾賢在其領納現量的定義中,對這些點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明確:受如何關聯於『了餘境識』?此受是一種境界受,還是一種對內在的觸的受,即自性受?眾賢似乎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為他進一步澄清了他的定義:『(領納現量)即自性受……』」
眾賢說得很明確。受和「了餘境識」是相應關係。了餘境識是心,受是心所,俱時而轉。「謂了餘境識俱生受正現前時……」,「俱生」即表示其相應關係。此受是自性受,如前所引,《自證》列出第二個問題後,就發現眾賢對此給出了回答。
二、覺了現量是什麼意思?
《自證》頁125-126:「我們看到,眾賢以『我曾受如是……』之類的反身性表述來解釋覺了現量,而這類表述也被經量部和瑜伽行派用以論證自證的存在,……眾賢自己不用記憶來證明覺了現量的存在,相反,他將覺了現量定義為記憶。」
眾賢沒有把覺了現量定義為記憶,眾賢對「覺了現量」或者說「覺慧現量」的定義是「謂於諸法隨其所應證自共相」。
舉例來說,滅法智就是覺了現量,它不是記憶。
《正理》:「此中若就依根、領納說類智境非現見事,則滅法智理亦應無,滅非依根、領納境故。若就覺慧,則不應言類智所緣是比智境。是故一切如理所引、實義決擇皆現量智。」
同樣,《自證》頁126:「如果覺了現量是對現前的感知或經驗的記憶,它就不能與根現量或領納現量同時,並且其對象必須是在過去,如眾賢明確說:如苦受等,必為領納現量受已,方有緣彼現量覺生。如是色等,必為依根現量受已,方有緣彼現量覺生。」
覺了現量,並不是「對現前的感知或經驗的記憶」,它的對象也不一定必須在過去。眾賢舉的「苦受」「色等」的例子,是緣領納現量、依根現量的覺了現量。然而,覺了現量的所緣,並不僅限於領納現量、依根現量。不能拿覺了現量緣過去的例子來證明它的所緣必須在過去。
《自證》頁126:「眾賢的覺了現量或現量覺給出了一種反思模式的自知。」
「反思模式」和「自知」都把「覺了現量」理解得狹隘了。覺了現量既不限於反思,也不限於自知。
另外,《自證》頁126之圖2-2,將三種現量關係稱為「第一剎那」「第二剎那」,其實,覺了現量緣依根、領納,是不限於緣前一剎那的依根、領納的,兩剎那、百千剎那之前的依根、領納也可以緣。
三、自性受能「了知其自身」嗎?
《自證》頁127:「他們承認智或識能在隨後的剎那由反思了知其自身,自性受也能以同樣的方式發生。」
這是把自相續中前剎那的智或識看成後剎那的智或識「自身」了,即便按照這個「自身」的定義,此受在緣前受時,此受也不叫自性受,而叫境界受。領納隨觸的,才叫自性受。自性受不能領納其自身。
如果按照有部固有的定義,將「自性」看作「自身」的話,任何受都不能緣取或領納其自身,智和識也不能了知其自身。
四、室利邏多僅承認有部「十大地」中的前三是「心所」嗎?
《自證》頁134:「說一切有部……。在任何既定時刻,心必定與一個或多個心所同時生起。」
宜刪去「一個或」,有部正統見解認為,心不可能僅與一個心所同時生起。
《自證》頁136:「這十個是受、想、思、觸、欲、慧、念、勝解、作意和定。室利邏多僅承認前三個是心所。」
室利邏多不是「僅承認前三個是心所」,而是「僅承認前三個是『大地心所』」。像「慧」「念」,室利邏多也承認是心所,只是不承認是「大地心所」。
五、訶梨跋摩認為「自體自知」嗎?
《自證》頁138-139:「訶梨跋摩以下文反駁大眾部:『又可取法異,故能取亦異。如人或自知心。云何自體自知?如眼不自見、刀不自割、指不自觸,故心不一。』這段文字令人困惑,因為如果我們只注意眼、刀、指等譬喻,它似乎是在反對自知。……我認為,它們是用於解釋這個問題:『心云何自體自知?』這意味著,雙方不是在論辯心是否知其自體,相反他們僅僅是在心如何知其自體上有分歧。……訶梨跋摩則堅持,一個心不可能有兩個對象,不同的對象需要有不同的心來了知。因此,以外在對象為對象的心,必定與以此心自身為對象的心有所區別。」
這是誤解了訶梨跋摩的反問語氣。引文宜斷句為:「又可取法異故,能取亦異。如『人或自知』——心云何自體自知?如眼不自見、刀不自割、指不自觸——故心不一。」
訶梨跋摩的邏輯是:假如心只有一個,「人或自知」的說法就不能成立了,一個心怎麼可能自體知自體?可見,一個人,必有多個心。這樣,每個心都可以被此人的其他某些心知。「人或自知」就成立了。如訶梨跋摩隨後說:「又云何當以此心即念此心?無有一智能知自體,故非一心。」這裡的云何仍然是反問語氣,不是設問,和前面的引文邏輯是一樣的。
《成實論》:「以燈破闇,眼識得生,眼識生已亦能見燈及瓶等物。」
《自證》頁139解釋為:「此分析的有趣之處在於,眼識參與到燈之中。如果我們將此分析應用於心自身,那麼照明他物的心是燈,而知其自身的心則是眼識。正如眼識與燈不同,這兩個心也應該是不同的。據此分析,眼識是在燈點亮之後生起的,這似乎暗示自知是在認知其他對象之後生起的。」
既然說「這兩個心也應該是不同的」,就應該明白這不是「自知」,正如訶梨跋摩沒有說「眼識見眼識」,「眼識生已」也只是「能見燈及瓶等物」,「等物」是不包括眼識自身的。這是在表示「不能自知」。
六、《成實論》「算數人」的比喻是在說什麼?
訶梨跋摩用心不能自知來反對唯有一心,對方舉例反駁,有個例子是「算數人」:「如算數人亦能自算亦算他人,如是心一能知自體亦能知他。」
對此,訶梨跋摩表示:「又算數人能知自色亦知他色,故名相知。」
關於這個譬喻的論辯,《自證》頁139-140解釋為:「上文中提道的大眾部的另一個譬喻與古印度的算命實踐有關。據訶梨跋摩的觀點,算命是獲得了知他心的神通力的三種方式之一。另外兩種方式是,像鬼神那樣生得此能力,以及像佛教修行者……,算命者與之不同,他通過識讀他人身體之相,或通過使用這些相的魔法咒語,來認知他心。……據訶梨跋摩的分析,此譬喻與自知無關,因為算命者之心並不以此自身為對象。相反,他通過識讀自己身體之相來了解自己的命運,這與識讀他人身體之相沒有什麼不同。」
《自證》把「算數人」理解為「算命者」,並引用《成實論》「知他心三種:一相知、二報得、三修得」等來解釋這裡的邏輯。實際上,這個譬喻和算命沒有關係。
算數,就是數數。比如,一個房間裡,其他人有五個,加上我自己,共六個人。一個人在數人頭的時候,不僅能數其他人,也能把自己算進去,對方用這來證明:自知是可以的。這裡的關鍵不是「知他」,不在能把他人算進去,而在能把自己算進去。對方舉算數人的例子是要表示,「汝言取可取異,是事不然,心法能知自體」——你說能取和可取必然不同,能取不能把自己作為可取,不是這樣的,心法能知自體,比如一個人在算人數的時候,就可以把自己也算進去。
訶梨跋摩意思是:算數人的例子中,能算的是心,我們是在討論心法能否知自體的問題,而所算的呢?是色。自色、他色,都是色,色當然和心不同,這怎麼能證明「心法能知自體」呢?
這和「算命」沒有關係,說的是心是否自知的問題。
《自證》頁140:「總之,訶梨跋摩沒有與大眾部就心是否能了知自身進行論辯。相反,他是在心如何了知自身方面與大眾部有分歧。」
如上已述,訶梨跋摩就心「是否自知」與對方進行了反復論辯,並堅持心「不能了知自身」。
《自证》读后感(三):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61-80讀後
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第二章談及有部等理論的內容(頁61-80),記如下。
一、有部認為「多剎那下,只有世俗智能知一切法」嗎?
《自證》頁69:「這就是為何毘婆沙師說當多剎那被應用於世俗智之時,全知是可能的。世親在其《俱舍論》中說,佛不因為他能在一剎那之思中了知一切而被稱為全知。相反,他的全知意味著一種能了知一切的心相續……」
其中,第一句的「世俗智」是不應該被提及的,尤其是在與下文相聯繫的時候。因為,如果要表示「在多剎那下,全知是可能的」,則不應該限制在「應用於世俗智」之下——世俗智的「知一切法」和佛的「知一切法」是為了討論不同問題而施設的,不宜因為表述的相近而綰合起來。
實際上,當多剎那被應用于非世俗智(無漏智)之時,也可以知一切法。當談到佛的「知一切法」「遍知」時,更應當強調的是無漏智,而不是世俗智。
為了理解《自證》何以如此認為,先來看《婆沙》原文:
「若作是問:於十智中,頗有一智知一切法耶?應答言有。謂世俗智。如是問於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智中,頗有一智知一切法耶?答有。謂世俗智。若即於此世俗智中,作如是問:頗二剎那頃知一切法耶?答有。謂此智初剎那頃,除其自性相應俱有,餘悉能知。第二剎那,亦知前自性相應俱有法。故答言有。今此唯問一剎那智,故答言無。」
《婆沙》這段是要解釋,說「世俗智」「一智知一切法」的時候,「一智」的「一」,表示「某一種」,而非「一剎那」。因此舉「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說明此處的「一」表數字、種類,不表「一剎那」,不宜與《發智論》「頗有一智知一切法耶,答無」的「一智」混同——後「一」不表數字、種類,而表「一剎那」。
因此,在問「頗有一智知一切法耶」的時候,要麼是問「有沒有一剎那之智可知一切法?」要麼是問「有沒有一種智可以知一切法?」是不宜把「一智」同時既作「一剎那智」又作「一種智」理解的。
在談及「一剎那」還是「多剎那」的問題——即部派爭議時,是大可不必涉及「十智之中,到底有沒有哪一種可遍以一切有為無為為所緣境」的問題的。
同樣,《自證》頁67說:
「然而,當全知被限定於說一切有部阿毗達摩的十智之一世俗智時,並且在多剎那的語境下,說一切有部並不否認全知,如《大毘婆沙論》所言:……」
其中,「當全知被……並且」是不應該保留的,因為當全知不被限定於世俗智時,「多剎那的語境下,說一切有部並不否認全知」照樣成立,甚至「即便只以非世俗智而言」,「多剎那的語境下,說一切有部並不否認全知」也一樣成立。
頁68討論「十智」的部分,其實和本小節的標題「一剎那之智」聯繫不大。因為在多剎那的前提下,無漏智(非世俗智)也「能以一切有為法和無為法為對象」,只不過「十智」沒有單立「無漏智」,而是把「無漏智」細分為「法智」「類智」,或者「苦智」「集智」「滅智」「道智」——「十智」之所以按照這種方法來細分,恰恰是因為「無漏智」比「世俗智」更重要,更值得細緻地了解。
《自證》頁68說:「十智之中,僅有世俗智能以一切有為法和無為法為對象。而其他智僅能觀想佛陀教法的一個特定方面,而沒有了知一切法的能力。」
這固然不錯,但「僅有世俗智能以一切有為法和無為法為對象」的真正原因是「世俗智」並不值得給予過度的關注而將它像無漏智那樣細分為「緣有為之世俗智」「緣無為之世俗智」以及「緣欲界之世俗智」「緣上界之世俗智」,否則,在細分的框架下,每一種被細分了的世俗智也不能「遍以一切有為法和無為法為對象」,這和「一剎那」還是「多剎那」的問題是沒有多少關係的。
二、有部認為或必須承認「佛的全知是有漏的」嗎?
《自證》頁70:「我們看到,瑜伽行派將全知的能力歸於無漏智。但在說一切有部的觀點中,從法智到他心智的無漏智,並沒有全知的能力,因為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只能緣取一個特定的對象。據他們的觀點,僅有漏世俗智能知一切法。」
這是很大的誤解。在有部看來,無漏智顯然有全知的能力,如先以法智、後以類智而「遍知」(如果認為「遍知」不是「全知」,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本文暫時不討論這個問題)。「法智」「類智」都是無漏智。
再看《自證》得出「據他們的觀點,僅有漏世俗智能知一切法」這一推論的《婆沙》原文:
「若即於此世俗智中,作如是問:頗二剎那頃知一切法耶?答有。謂此智初剎那頃,除其自性相應俱有,餘悉能知。第二剎那,亦知前自性相應俱有法。故答言有。」
設問的前提是「若即於此世俗智中」。這是單針對世俗智發問的,假使問的是「若於無漏智中,作如是問:頗有多剎那頃知一切法耶?」答案照樣是「有」的。
《自證》由上推論說:「然而,如果這樣的話,說一切有部所面臨的一個困難是,他們必須承認佛的全知是有漏的。」
但在有部自身的文獻中,能發現相反的見解。《婆沙》說「通達遍知唯無漏」,又說,「問云何說三十四心剎那得一切智。答彼說此依無漏心說。不論入出滅盡定心」,這皆可表明,有部認為「遍知」「一切智」是以無漏心成就的。
至於《大智度論》所提到的「唯有世俗智能緣一切法,以是故說一切智是有漏相」,我在有部文獻如《婆沙》《正理》中,沒有發現有部持這種見解的證據。
三、其他
1、
《自證》頁72引《婆沙》:「勿有因果。能作、所作,能成、所成,……,能覺、所覺無差別過……」
此處宜句讀為:「勿有因、果,能作、所作,能成、所成,……,能覺、所覺無差別過……」。原文想表示的是「勿有因、果無差別過,勿有能作、所作無差別過……」
2、
《自證》頁73:「遍行因指凡夫的煩惱和習氣。」
遍行因,是指前已生的遍行諸法,能作後同地染污諸法的遍行因。並不是凡夫的所有煩惱都是遍行因——非遍行煩惱就不是遍行因,未來世遍行煩惱也不是遍行因。如《婆沙》說:「謂或有執,一切煩惱皆是遍行。為止彼執,顯諸煩惱有是遍行有非遍行。」《正理》說:「有遍行隨眠非遍行因,謂未來世遍行隨眠。」
另外,不僅遍行煩惱是遍行因,其相應法、俱有法也是遍行因。如《婆沙》說:「復次,為遮相似相續沙門意故。彼作是說:遍行隨眠唯與隨眠為遍行因,彼相應法唯與隨眠相應法為遍行因。為遮彼意顯遍行隨眠與隨眠及相應法為遍行因。彼相應法與隨眠相應法及隨眠為遍行因。故作是說。問遍行隨眠於諸隨眠俱有法等亦是遍行因不?設爾何失?若亦是者此中何故不說?若非者何故於相應法是而於俱有法等非耶?答:應說亦是。以與一切染污法皆為遍行因故。問:若爾此中何故不說,答:彼相應法與彼隨眠同一所緣同一行相極相隣近,是故說之;生等不爾,是故不說。」
3、
《自證》頁73:「異熟因指每個行為都有善或不善的道德特征。」
無漏善不是異熟因。
4、
《自證》頁7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能作”“能成”“能引”……等詞都是對智的描述,這些術語表明毘婆沙師是如何理解智的。」
認為“能作”“能成”“能引”等「都是對智的描述」,則把前者範圍理解窄了。比如,“能作”“能成”等也可以是對「無漏忍」的描述,而無漏忍不是智。再如,作為異熟因的受、想等也是“能作”“能成”等,它們也不是智。
5、
《自證》頁76:「眾賢認為,這沒有意義,因為虛空也依於其他的有為法,它依據其他的事物而建立,並非依其自身而立。」
這段所據《正理》原文是:「理亦不然,以虛空等望所生法他性極成,法為他緣理極成故。」意思是:「這是不對的,因為虛空對所生法來說,顯然是別的法(他法、他性),(而不是所生法自身,)一法作為他法的緣,是完全成立的。」
6、
《自證》頁79:「此外,龍樹論證說,『如果燈能照自身及他物,那麼暗也必定能遮暗自身及他物』。但是暗並不能遮暗自身及他物,因此並不能推測燈能照自身及他物。」
這裡的「他物」,原文是「彼」,原文的「彼」其實並不是泛指一切燈、暗之外的「他物」,而是對燈指暗,對暗指燈。
該偈頌是為了解釋這個問題:「若燈有力,不到闇而能破者,此處燃燈,應破一切處闇——俱不及故。復次燈不應自照、照彼。何以故?若燈能自照,亦能照於彼;闇亦應自闇,亦能闇於彼。」
意思是:假如燈能自照也能照暗的話,暗就應該能自暗也能暗燈。如果把此處的「彼」理解成「他物」,偈頌要表明的「燈能照暗」見解隱含的矛盾就不明顯了。
7、
《自證》頁80:「這個論證非常有趣,因為它承認光和暗之間有邊界,此即對象的邊緣。黑暗不能到達對象體內;當有光時,先照亮對象的表面,然後擴展到其邊緣,一直到依據光的亮度所能達到的地方。」
這是解釋《佛地經論》的「如瓶衣等體雖非闇,無燈等照邊(anta)有闇障,不得現見,燈等照時除彼邊闇,令得現見,說名為照。」
從原文中,似乎看不出「當有光時,先照亮對象的表面,然後擴展到其邊緣……」這種「有先有後」的意思。我想,邊(anta)也許指「內部」,說瓶衣等雖然體不是暗,但內部因為有暗障礙,不能現見,假如用燈等照瓶、衣的內部,就可以看見了。《自證》說「黑暗不能到達對象體內」,用「體內」來解釋「邊」我覺得很妥帖,「不能到達」卻似乎說反了。依原文,恰恰此時有暗障,還沒有「除」。以燈照時,才除去暗障。
《自证》读后感(四):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103-123讀後
繼續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頁103-123,記如下。
一、有部認為一心不可以是另一心除能作外的任何因嗎?
《自證》頁104:「然而,他們並不否認一個心能成為另一個心的能作因。這是因為能作因是最普遍的因,它能應用於除了其自身的一切法。」
第一句宜表達為:「然而,在能作因也算因的情況下,他們並不否認兩個心能互為因。」這裡說的是互為的關係,不是單方面的。如果就單方面說,有部也不否認一個心能成為另一個心的同類因、異熟因。之所以在考慮能作因的情況下,兩個心能互為因,是因為後心可以是前心的能作因。
《自證》頁107:「總體來說,說一切有部認為一心可以是另一心的任何緣,但不能是其除了能作因之外的任何因。」
如前已述,有部認為,一心可以是另一心的同類因等。
二、法救的「一和合生」在強調什麼?
《自證》頁107:「大德法救進一步解釋說,生起多個心所的和合或作意與生起心的和合或作意是同一個,而這些心所『雖皆名心所,而體類各異』。」
法救只說「一和合生」。「一作意生」是其他人的說法。「雖皆名心所,而體類各異」,已經不屬於對法救的引用,而是婆沙師的總結。不過,這總結是法救、有師、婆沙師都認同的。
另外,「一和合生」「一作意生」的「一」,強調的是「唯一」,而不是「同一」,想表達的意思是:和合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第三個,而不是要強調:生心所的和合與生心的和合是同一個。當然,既然唯一,自然只能是同一個,不過「同一」不是法救說的重點。
三、他心通的例子在解釋同分智時有「暗示某人能回憶起他人的經歷」嗎?
《自證》頁110:「後一個例子令人困惑,因為它暗示某人能回憶起他人的經歷。」
這裡說的後一個例子,《發智論》原文是:「又如有二知他心者,互相知心,雖彼二人不往相問『汝云何知我心』,亦不相答『我如是知汝心』,而彼二人由串習力得如是同分智,互相知心。」
此處並沒有「暗示某人能回憶起他人的經歷」。例子後所說的「有情亦爾,由串習力得如是同分智,隨所更事,能如是知」已經不在所舉比喻的範圍之內了。
四、「於所緣定」的「定」是什麼意思?
《自證》頁111:「第二個使得記憶成為可能的要素是『一切心、心所法,於所緣定安住所緣』。『所緣定』指在滅盡定之前的一切禪定階段,到了滅盡定就不再有所緣對象。」
「於所緣定」的「定」,是確定、決定的意思,和「禪定」沒有關係。
《自證》頁111:「它們中的任一個,都依其意趣和方式各自不同地感知此對象。……如果對象對一切心都顯現為同樣的,將會有『餘心聚所更,餘心聚能憶』的過失。為了避免此過失,他們堅持對象對每個心或心所都顯現為不同的,以至於它們是在感知不同的對象。例如,一個有一百個孩子的父親,毫無差別地是他所有孩子的父親。然而,在他孩子們的眼中,他這個父親有一百種不同的形式。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此處樸素實在論讓位於視角主義。……」
這一大段完全不是《婆沙》原義。《婆沙》原文是:「……謂於一所緣有無量心心所聚轉。此一所緣如以此理趣以此性類以此法式與一心心所聚作所緣事,與餘無量心心所聚作所緣事亦爾。如一心心所聚以此理趣以此性類以此法式領受此所緣,餘無量心心所聚領受此所緣亦爾。譬如一人而有百子,此一人如於一子作父事,於餘子亦爾。如一子於父作子事,餘子於父亦爾。」
這不是《自證》所認為的「各自不同地感知」「顯現為不同的」「感知不同的對象」等。相反,《婆沙》說的是「亦爾」,一所緣是怎樣與「一心心所聚」作所緣的,也是怎樣與「餘無量心心所聚」作所緣的。反之亦然。
《自證》認為的「以至於它們是在感知不同的對象」也不是原義,「對象」是同一個,否則就不叫「於所緣定」了。「百子」的比喻,恰恰是要說明作用機制的類似,而不是不同。
《自證》頁112:「使得記憶成為可能的三個要素,即同分智、恆常的對象和強烈的受意……」
「恆常」宜作「確定」。有部否認有為法是「常」。
五、眼是「隨轉色」及「俱有法」嗎?
《自證》頁113:「對於化地部來說,心和心所的俱有是『此隨轉色及此隨轉不相應行』。例如,眼是眼識的俱有,因為眼是隨眼識轉的色。……例如,當某人將滴眼劑滴入眼中時,他不能看見滴劑管,因為它太近了。」
「此隨轉色及此隨轉不相應行」是「俱有法」——這是有部的觀點。另外,眼並不是隨轉色。在以「此隨轉色及此隨轉不相應行」來定義「俱有法」時,眼不是俱有法。
所舉例子中,不是不能看見「滴劑管」,是不能看見「眼藥」。「如籌霑取安繕那藥置於眼中,極相近故眼不能見」,見省略的賓語是「安繕那藥」,不是「籌」。
六、有部怎樣解釋「受樂受時如實知我受樂受」?
《自證》頁114-115:「然而,在其他說一切有部阿毗達摩的著作中,能發現對受之覺知問題的長篇討論,我們並未見到關於此問題的一致立場。例如在《舍利弗》的《法蘊足論》中,……」
由於《法蘊足論》有「受樂受時如實知我受樂受」的句子,《自證》認為這表示《法蘊足論》認為現在的心能知現在的受,因此和《婆沙》見解不同。
實際上,《法蘊足論》這句話是引契經的,《婆沙》對此有解釋:「又如已受而說今受。如契經說受樂受時如實知受樂受,乃至廣說。彼亦已受而說今受,非於受時可了知故。」
《婆沙》的解釋《自證》隨後(頁116)也提到了,但沒有由此修改頁114-115的見解。
七、《成唯識論》對眾賢「執取受」「自性受」的理解不準確嗎?
《自證》頁117:「對比眾賢自己的陳述,我們發現護法的重述不夠準確。例如,眾賢自己將領納所緣的受稱作『執取受』,而非『境界受』。此外,他把自性受定義為『謂能領納自所隨觸』,此中受和觸之間的同時性並不明確。」
《成唯識論》的「境界受」就是眾賢說的「執取受」。「執取受」的定義是「謂能領納自所緣境」,這和「境界受」的定義「領所緣」是一樣的。
至於《自證》說「自所隨觸」「此中受和觸之間的同時性並不明確」,其實,「自所隨觸」就是指與自身相應的觸,「相應」的定義中包含了「同時性」。《成唯識論》將「所隨」稱為「俱」,是同樣的意思。從「由此,觸於受若時為所領,是時非所緣;若時為所緣,是時非所領,故緣、領事別」中也可以看出來「自所隨觸」是與自身相應的觸。
八、《婆沙》《雜心》等「相應受」是什麼?
《婆沙》:「所說受名總有五種:一自性受。二現前受。三所緣受。四相應受。五異熟受。自性受者,如說三受。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現前受者,如大因緣法門經說:阿難當知,受樂受時餘二受便滅。應知如是所受樂受是無常苦滅壞之法,離我我所。如是苦受、不苦不樂受應知亦爾。所緣受者,如識身論說:眼色為緣生於眼識,三和合故觸,觸為緣故受。當知此受能領受色非數取趣,色是眼觸所生受緣,非數取趣。如是乃至意法廣說亦爾。相應受者,如說有樂受法、有苦受法、有不苦不樂受法。云何樂受法?謂樂受相應法。云何苦受法?謂苦受相應法。云何不苦不樂受法?謂不苦不樂受相應法。異熟受者,如此中說:順樂受業、順苦受業、順不苦不樂受業。」
自性受,是受心所;現前受,是現前的受心所;所緣受,是受心所——針對所緣說的;相應受,是受相應法;異熟受,是異熟業。其中,自性受、現前受、所緣受是受心所;相應受、異熟受不是受心所。
《俱舍論》:「總說順受略有五種:一自性順受,謂一切受。如契經說:受樂受時如實了知受於樂受,乃至廣說。二相應順受,謂一切觸,如契經說:順樂受觸,乃至廣說。三所緣順受,謂一切境,如契經說:眼見色已,唯受於色不受色貪,乃至廣說,由色等是受所緣故。四異熟順受,謂感異熟業,如契經說:順現受業,乃至廣說。五現前順受,謂正現行受。」
需要注意的是,《俱舍》的「所緣順受」和《婆沙》的「所緣受」不同。《俱舍》的「相應順受」和《婆沙》的「相應受」狹廣不同。
《自證》頁117-118:「在《大毘婆沙論》中,自性受由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等三受來定義。然而,法救在其《雜阿毗曇心論》中將自性受理解為受本身……眾賢對自性受的理解不同於這兩個傳統。在他的理解中,自性受接近上文提道的五受之一相應受。」
實際上,《婆沙》和《雜心論》的「自性受」是一樣的,都是受心所,無論是否現前。「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是舉例來表示這些都是「受心所」,一切受心所都不出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之外。它們並不是「兩個傳統」。
《自證》認為眾賢的「自性受」接近《婆沙》的「相應受」,實際上,《婆沙》的「相應受」說的是「受相應法」,而不是「受心所」,《婆沙》為了解釋「受相應法」,特意舉出「樂受相應法」「苦受相應法」「不苦不樂受相應法」來表示「相應受」是與「自性受」相應的法。眾賢的「自性受」其實就是《婆沙》的「自性受」。
《自證》頁:「……相應受。此受被法救定義作『受相應法』,世親在其《俱舍論》中進一步將此受限定為『觸之受』。他說:『相應受是觸之(受),如經說「應感受樂觸」。』」
實際上,《俱舍》對「相應順受」的定義是「一切觸」,指的是觸心所,而不是受心所;從《俱舍》的「順樂受觸」也能看出來是觸心所。《自證》在「觸」後補充了「受」字,將「相應受」誤解成了受心所。
隨後,《自證》說:「……它們是異熟受和現前受。前者是樂業、苦業或不苦不樂業之受,而後者是現在的樂受,它不包括苦受和不苦不樂受。」
《自證》在解釋異熟受的時候又補充了「之受」,並解釋為受,實際上,異熟受是異熟業,不是受。而現前受,如果是苦受現前,那就是苦受,不苦不樂受現前,那就是不苦不樂受。《婆沙》說「如是苦受、不苦不樂受應知亦爾」。
《自證》頁118-119:「同時,當他認為受的本性是『隨觸而生領納可愛及不可愛、俱相違觸』時,他將相應受與自性受合併為一了。」
眾賢此處只提到「執取受」「自性受」,並沒有提「相應受」,而且《婆沙》等所說的「相應受」不是受,是受相應法,《自證》將相應受誤解為自性受,由此說眾賢「將相應受與自性受合併為一」。
九、受的產生在「三和合生觸」之後嗎?
《自證》頁119:「觸不僅是……。然後,觸產生受,……」
不宜說「然後」,觸和受是俱時生的。
十、護法「受定不緣俱生觸故」是在破斥眾賢嗎?
《自證》頁122:「更重要的是,法寶區分了『領納』和『緣取』。他說:『證受自領,皆非應理。若受還領受,即違文「若時為所緣,爾時非所領。若時為所領,爾時非所緣」。』據他的理解,自性受不涉及對觸之緣取,因為它只是領納觸。」
將「領納」和「緣取」區分開的是眾賢。法寶只是述眾賢之說,所提到的「若時為所緣」等,也是眾賢的說法。另外,自性受也可以緣觸,只是不緣隨觸。也就是說,自性受緣取的觸,不是其領納的觸;領納的觸,不是其緣取的觸。
《自證》頁122:「因此,當護法以『受定不緣俱生觸故』為理由來破斥『受領納觸』的可能性時,他是錯誤的。」
我們應該明白《成唯識論》破斥的對象和步驟。「彼說非理,受定不緣俱生觸故」,這一句並不是在破斥眾賢的新薩婆多義,而是破斥本薩婆多,本薩婆多還沒有區分「領納」和「緣取」,不能拿眾賢重新定義過的「領納」來認為護法此處的破斥錯誤了,因為這一句還沒到針對眾賢的時候。何以知之?窺基《述記》後面說「三、彼復救言:受領觸者,似俱時觸說名為領,非緣名領」,這時候才提「非緣名領」,才是眾賢的思路。護法對該思路的駁斥是「似因之果應皆受性」及以下的部分。
《自證》頁122:「在此點上,窺基通過追問『既不緣前觸,如何名為領』來捍衛護法。對這些瑜伽行派學者來說,緣取是領納的前提。」
窺基這句並不是「捍衛」護法,而是針對在未區分「領納」和「緣取」時,對方的另外一種可能的設救思路,即「不是領納俱觸,而是領納前觸」。
《自證》頁122注釋5:「注意窺基此處將『觸』理解為先於『受』……」
「觸先於受」不是窺基的理解,是窺基假設對方的救法,「若觸前受後,後受領前觸」,「若」表示設想對方這樣救,隨後即駁斥了這種救法。
《自證》頁123:「然而,眾賢自己堅持一個相反的次序,即領納先於緣取。他說:『由此觸於受,若時為所領,是時非所緣;若時為所緣,是時非所領。故緣、領事別。』我們看到,法寶在用相反的次序引用眾賢時,甚至都已經受到瑜伽行派的影響,而將優先權給予緣取而非領納。」
眾賢完全沒有「領納先於緣取」的意思。法寶的引用,「若時為所緣,爾時非所領。若時為所領,爾時非所緣」,和眾賢是一模一樣的意思。這兩句誰在前誰在後意思沒有差別。《自證》認為「受到瑜伽行派的影響」的「將優先權給予緣取而非領納」,也不是瑜伽行派的見解,如上所說,是假定的對方設救法。
《自证》读后感(五):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90-102讀後
繼續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頁90-102,記如下。
一、「他心智」一例中,能確定世友影響了法救嗎?
《自證》頁90:「在此方面,他緊隨世友從他心智角度對智之自知的駁斥。」
「他」,指大德法救。說法救「緊隨」世友,是一定要證明了法救晚於世友或至少與世友同時,並在此說上受到世友的影響才可以。
《自證》在《附錄 重要著作者的年代》中將法救繫年於2世紀,這是依據魏查理等,但魏查理的繫年依據,《自證》並不清楚。《自證》頁213說:「魏查理等(1998:261)引用普桑來支持此年代,但我在普桑處並未找到此說的出處。印順(1992:268)推定大德法救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這個年代相當早。」
印順法師的見解是,法救「大概與(阿毘達磨論師)世友同時,或者多少早一點」,《自證》見及而未依。
在有把握確定法救的年代之前,不宜說在「他心智」的例子上法救「緊隨」世友。
二、「知他性亦爾」的「爾」指什麼?
《婆沙》說:「若知自性及他性者,云何而知?如知自性是自性,知他性亦爾耶?如知他性是他性,知自性亦爾耶?」
後兩句,《自證》頁90解釋為:「是用知自性的方式知他性,還是用知他性的方式知自性?」
原文這兩句意思是:「如果說知自性是自性,知他性也是自性嗎?如果說知他性是他性,知自性也是他性嗎?」若說得明白一點,意譯的話:「如果是把自性理解成自性,是不是把他性也理解成自性了?如果是把他性理解成他性,是不是把自性也理解成他性了?」
這裡談到的是知的結果,而不是知的方式。兩處「亦爾」的「爾」,分別代表「是自性」「是他性」,即上句的後半部分;《自證》將「爾」理解成「如知自性」「如知他性」,即上句的前半部分了。
因此,《自證》說:「如果知他性如他性,且知自性如他性,那麼『知他性如他性』是正確的,但『知自性如他性』則識錯誤的。」
這裡的「如」,原文都是「是」:「若『如知他性是他性,知自性亦爾者』,則『知他性是他性』可是正,『知自性是他性』應是邪。」「是」表示知的結果,「如」是不符合原義的。
《婆沙》:「若爾,應無邪正二智體相差別。」
《自證》頁90解釋為:「在兩種情形下,都有著不能區別正見與邪見的過失。」
這個解釋也說得過去,更好的解釋是:「如果這樣,邪智和正智就是同體的。」區別還是能區別的,前面說的「……是正」「……是邪」就是區別,問題不在於「邪智」「正智」不能區別,而在於它們「體是一」「同體」,或者說它們的「體」不能區別。前面(作用)的區別就是為了導出「同體」的過失,下面才作「不同體」的假設。這句話的解釋中,「體相」一詞是不宜忽略的。另外,原文的「智」不宜解釋為「見」,因為「智」「見」廣狹不同。比如「無漏忍」是「見」不是「智」。
三、「自共相如次能所緣」是什麼意思?
《正理》:「若謂自共相如次能所緣,理亦不然,前已說故。」
前半句,《自證》頁97解釋為:「他聲稱智『能將自相、共相依次作為對象』。據此立場,智能知其自相,也能知其共相。」
實際上,這句話意思是:「如果說自相是能緣、共相是所緣,那也不對,前面已經解釋過了。」其立場並不包括「智能知其自相」,而是「自相是能緣」,所緣才是共相。《正理》接下來的解釋「既不自緣自相為境」,表示「不自緣自相」也是對方認同的,分歧只在「是否緣自體共相」。
《自證》頁97接下來說:「但是這提示了一種不同於第一個論敵所暗示的次序:智首先知其自相,然後知其共相。此觀點更接近佛教邏輯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現量比比量更為根本,因此,自相的知識比共相的知識更為基礎。眾賢對此論敵沒給予細緻回復。相反,他只是重複了在回復第一個論敵時得出的結論:……非常不幸,眾賢沒有依據自相與共相智區分進一步闡發他對智之自知的駁斥,因此,我們不得不止步於此。」
實際上,「自共相如次能所緣」中並沒有「先後次序」的意思,而是「自相、共相分別是能緣、所緣」的意思。「智於自體不知自相、共相可知」和「若謂自共相如次能所緣」並不是「第一個論敵」和「第二個論敵」的關係。
《自證》認為的「更接近佛教邏輯學家的觀點」即「智首先知其自相,然後知其共相」,是誤解原文而產生的,原文並沒有「此觀點」和「第二個論敵」,眾賢自然不會對此觀點進行駁斥。
四、《婆沙》引「智相應識」的邏輯是什麼?
《婆沙》:「為止彼宗顯識與智其體各別。如契經言『智相應識』。」
《自證》頁98解釋為:「如《大毘婆沙論》所引的一部經中所說,智與識的主要不同是『智相應識』。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互相相應。毘婆沙師明確指出『諸智皆識相應,非諸識皆智相應』。這是因為智與作為心相應或心所的慧密切相關,因此屬於心所一類,而識與心相同。」
這裡沒有解釋出原文的邏輯。《婆沙》的邏輯是:既然契經說過「智相應識」,就意味著「智」和「識」的體是不同的——因為一法不能與其自體相應,那麼,說「相應」,就表明二者各有其「體」,是不同的法。
「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互相相應」也沒有理解原文意思。不宜用「互相相應」的表述,因為任何相應都是互相的。
《婆沙》「諸智皆識相應,非諸識皆智相應」的意思是,凡是「智」生起的時候,一定有生起的「識」與它相應;而在「識」生起的時候,不一定有生起的「智」與它相應。為什麼?還是因為「無漏忍」的例外。不是《自證》後面解釋的「這是因為……」等原因。
五、有部認為「智從根本上說是個無漏法,而識是個有漏法」嗎?
《自證》頁99:「毘婆沙師也承認智與識之間的另一種不同:智從根本上說是個無漏法,而識是個有漏法,如《大毘婆沙論》中所說:『一切清淨品中,智為根本;一切雜染品中,識為根本。』此觀點也被瑜伽行派採用…… 在他們看來,佛教修行的全部目的就是轉識成智。」
智是一切清淨品中之根本,並不意味著「智從根本上說是個無漏法」。《婆沙》說,「或有執智唯是道支,識唯是有支,如犢子部。以契經說正見是道支、行緣識故。為止彼宗顯智與識俱通二支,但隨強說。」可見,智和識,都可以是有漏的,也都可以是無漏的。「智」從根本上說是「慧心所」,「慧心所」有有漏的,也有無漏的。「識」也可以是無漏法。
《自證》認為的「也被瑜伽行派採用」的「智從根本上說是個無漏法,而識是個有漏法」之觀點並不是有部觀點。
六、「智唯是道支,識唯是有支」是什麼意思?
《自證》頁99:「此外,毘婆沙師不同意犢子部『智僅以道支作為對象,而識僅以有支作為對象』的觀點。毘婆沙師堅持,道支和有支都可作為智與識的對象。」
原文前已引,犢子部意思是「智唯是道支,識唯是有支」,是說智本身唯是道支,不是「智僅以道支作為對象」。這裡的「道支」「有支」都是從「能緣」(智、識本身)的含義上來說的,不是從「所緣」(智、識之對象)的含義來說的。
換句話說,就是前面解釋過的,犢子部認為:智都是無漏的,識都是有漏的;而有部認為,智和識都是通有漏、無漏的。
七、「一切法非我」的「觀點」是有漏的嗎?
《自證》頁101:「……當涉及相應的解脫論範疇時,這種區分就變得重要了。『一切法非我』的觀點是有漏的和世間的,而『苦諦是非我』的觀點是無漏的和出世間的。如此一來,謂語『非我』就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有漏的,以『一切法』為主語;另一個是無漏的,以『苦諦』為主語。這意味著識的全知僅在有漏的世間是真的,而在無漏的出世間則不然。」
我們先來捋一捋《自證》何以得出這種觀點。
《婆沙》為了解釋「若時以慧觀,一切法非我,爾時能厭苦,是道得清淨」這句話到底是說緣一切法還是緣苦諦之非我行相,給出了許多不同見解。
「有說,前半說有漏慧,後半說無漏慧。如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
這種見解是說,前半句觀「一切法非我」時的慧,是有漏慧,後半句觀「苦諦非我」時的慧,是無漏慧。這裡說無漏、有漏,是針對現起的「慧」說的,不是針對「某個觀點」說的。
《婆沙》說:「有說,非我行相其義決定,是故偏說。謂空行相義不決定。以一切法有義故,空約他性故。有義故不空,約自性故。非我行相無不決定,以約自他俱無我故。由此尊者世友說言:我不定說諸法皆空,定說一切法皆無我。」
可見,「一切法非我」,這個觀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有部不反對。只是無漏非我行相不緣一切法,但這不意味著那些無漏非我行相不緣的法——集諦、滅諦、道諦不是「非我」的。
該見解說的是世俗智和苦智緣境廣狹的不同,得不出「這意味著識的全知僅在有漏的世間是真的,而在無漏的出世間則不然」之推論。
《自證》頁101:「如果我們將『非我』的觀念理解為煩惱的對治,那麼它就必須有特定的對象。此特定對象就是『我』見。……然而,『非我』之有漏識並不限於特定的對象,因為它不滅除任何煩惱。」
任何識都有特定的對象(所緣),有漏非我行相也有特定的對象。而且,有漏非我行相也不是總「緣一切法」的,凡夫可以緣一個杯子作非我行相,這就是有漏非我行相,所緣就限於這個杯子。如果認為有漏非我行相有時可以緣杯子,有時可以緣其他,因此叫「不限於特定的對象」的話,無漏非我行相有時可以緣欲苦,有時可以緣上苦,也不能說限於欲苦或上苦。
八、《婆沙》此處的「一切熾然」是為了解釋什麼?所解釋內容是有部的正統理解嗎?
《自證》頁102:「在闡明全知之識的有漏性之後,毘婆沙師接著調和此全知之識與《發智論》中相反的說法:沒有識能了知一切法。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是:……」
如前《讀後(頁61-80)》所記,有部、《婆沙》並沒有「全知之識是有漏性」的見解。
《自證》這裡說的,「毘婆沙師接著調和此全知之識……」的「全知之識」並不是「了一切法」的(沒有緣自品),而《發智論》「了一切法」的「一切法」是包括自品的,這兩個「一切」所指範圍本來就不同,因此,談不上「相反」,也就不存在「調和」的問題。
在「是否緣自品」的問題上,《婆沙》和《發智論》毫無分歧——都認為不緣自品。這裡「一切法非我」的「一切」非彼一切,如果將「一剎那了彼(《發智論》所謂)一切」定義為「全知之識」的話,《婆沙》這裡根本不是「全知之識」。
《婆沙》接下來也解釋了它不是「一(剎那)識了一切法」的「全知之識」:「緣一切」,可以像有些人那樣理解成「緣幾乎一切」的意思,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樣理解成「二剎那緣一切」的意思——即一剎那沒有緣一切。
《自證》接下來又說:「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是:『一切有二種,謂「一切一切」「少分一切」。此中但說少分一切。』為了支持此區分,他們也給出其他例證,其中使用了『少分一切』。例如,當佛陀教導說『一切如焰』時,他並未確切說『一切法是如焰的』,因為無漏法實際上並不是如焰的。在全知之識的情形下,被排除於『少分一切』之外的是識自身及其相應和俱有法。」
這裡的「一切如焰」,是《婆沙》所舉的「一切熾然」。實際上,《婆沙》舉「一切熾然」的例子,是為了解決剛才說過的另一個問題的,即:「若說緣苦諦非我行相者,云何說觀一切法非我?」
回答這個問題的一種思路(有餘師說),是認為契經「若時以慧觀,一切法非我」的「一切法」,不是真正的一切法,而是「苦諦」,就苦諦稱一切法。
「一切熾然」是表示就苦諦稱一切法,不是像《自證》解釋的表示就除自品外的法稱一切法——雖然這兩處都是在將「一部分」稱為「一切」,但在《婆沙》在後一處(除自品外稱一切)並沒有舉「一切熾然」的例子。
舉「一切熾然」的例子,是「餘師」所為,要表示約苦諦說一切,而餘師這種解釋恰恰是《婆沙》覺得牽強的,因為《婆沙》認為「然決定有緣一切法非我行相」。
九、無漏識「即使在多個剎那也不能盡知一切法」嗎?
《自證》頁102:「但這僅適用於有漏識,因為無漏識即使在多個剎那也不能盡知一切法。」
這個問題,前《讀後》已經討論過了,無漏識在多剎那可以盡知一切法。《自證》之所以認為不能,是因為《婆沙》這句話:
「非如無漏非我行相——雖多剎那亦不能緣一切法盡。」
這裡說的不是「無漏識」,而是「無漏非我行相」,「無漏非我行相」是緣「苦諦」的行相之一,而「苦諦」僅僅是「無漏識」所緣的一部分。不能把緣苦諦的無漏識理解成全部無漏識。
十、其他
《自證》頁94:「同時,他引用了稱友《阿毗達摩俱舍論疏》中所引的同一段經文來拒斥……」
「他」指眾賢。這個說法沒有問題,只是為了避免誤解,可以不提稱友疏,或者放在後面提:「後來,稱友疏也引用了同一段經文。」眾賢時代早於稱友,《自證》的表述可能會讓不熟悉繫年的讀者理解為稱友的引用在前或者更重要。
《自证》读后感(六):王路:姚治華《自證:意識的反身性》頁141-151讀後
繼續讀姚治華老師《自證:意識的反身性》(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頁141-151,記如下。
一、訶梨跋摩認為「一切法無我」的「一切」指什麼?
《自證》頁141:「首先,他不認為我們在前幾章中討論過的契經偈頌『一切非我』中的『一切』意味著『一切法』,相反,它僅指各種界和處。他說:『若智行界、入等,名一切緣』。」
《自證》是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搞混了。契經偈頌「一切非我」的「一切」,《成實論》不是認為它「指各種界和處」,而是認為它指「苦諦」,「苦諦」確實不是一切法。而「各種界和處」,確實是一切法。
《成實論》:「問曰:經中說,若能以慧觀,一切法無我,即得厭離苦,是道為清淨。此智慧除自體及共生法,餘一切法緣。答曰:此智但有漏緣,非無漏。所以者何?此偈中說即厭離苦,故知但緣苦諦。」
《成實論》認為,「若智行界、入等,名一切緣」的「一切」,和「若能以慧觀,一切法無我」的「一切」是不同的。前者指諸界或諸處,後者指苦諦。而且,前者包含真正的一切法,因為「若說十二入則更無餘法」。
二、「法不自知」和「意能自知」的「自知」含義一樣嗎?
《自證》頁141:「說一切有部否認『處之智』等能知一切法,因為它不能知此智自身及其相應和俱有法。為了駁斥此觀點,訶梨跋摩主張:『能知,若緣入等,是名總相智。總相智故,能緣一切。所以者何?若說十二入,則更無餘法,故知此智亦緣自體。』」
所引原文中,有個容易忽略的細節,訶梨跋摩要駁斥的對方的見解是:「此智不知相應、共生等法。」
首先,需要知道,這裡的「相應、共生」是對方的思想體系下的術語。另外,訶梨跋摩的「能知」,只是對對方的「相應、共生等法」說的,是不包含自體的。如前篇《讀後》提到的,訶梨跋摩認同「無有一智能知自體」,分歧只在於是否知相應、共生等法上。
那麼,為什麼訶梨跋摩說「故知此智亦緣自體」呢?因為在訶梨跋摩這裡,唯能以「總相智」緣自體,是不能叫「自知」的,因為「總相智」不能知「自相」(之全分)。
對「意能自知」的俗語,稍後將詳細討論,要言之,訶梨跋摩同意的是「意能自『緣』」。
「法不自知」和「意能自知」,兩個「自知」是廣狹不同的,前一個「自知」唯限於「知自體」「知自相」,後一個「自知」雖然可以說成廣義的「自知」——即將「緣自體」「知總相」也包括進來的自知,然而,訶梨跋摩在討論法相問題時,總是以第一個「自知」為真正的「自知」的。只是由於「意能自知」是世俗共許的表達,無論有部還是訶梨跋摩,都必須依自己的理論體系對其作出解說。這種解說是不能看成「自知」的定義的。
訶梨跋摩這種思路,眾賢在《正理》中駁斥了,眾賢連「緣自體」都不承認:「有作是言:智於自體不知自相,共相可知。理亦不然,已辯自體不以自體為所緣故。於自自相既永不能取,則定無有以自為所緣,既非所緣寧取共相?故應於此立比量言:自相亦應為自體境,自體相故,猶如共相。或應共相非自體境,自體相故,猶如自相。故緣共相理亦不成。」
三、「總相智」和「別相智」是什麼意思?
《成實論》:「又說:云何比丘名一切智?謂如實知六觸入生滅。——是名總相知一切法,非別相智。佛總別悉知,名一切智。是比丘總知諸法無常等,故名一切智。其名雖同,而實有異,名攝一分。」
六處包括內外六處,也就是十二處,是涵蓋一切法的。訶梨跋摩對「知六觸入生滅」的解釋是,是比丘以總相知,而不能以別相知,那麼,雖然叫一切智,其實不是一切智,而是一切智的一部分。
《自證》頁142的理解是:「對於訶梨跋摩來說,總相智儘管是『一分全知』,它也已經了知包括智自身在內的一切法。」
玩《成實論》語義,就知道訶梨跋摩這段是在表示「總相知一切法」是不夠徹底的,是屬於「一切二種,一攝一切、二攝一分」的第二種,是屬於假的「知一切法」。訶梨跋摩的想表達的讓步關係是:「總相智儘管也叫做『知一切法』,實際上僅僅是『知一切法的一部分』。」《自證》把讓步關係給反過來了。
《自證》頁142:「這裡此智的自知是其『總相知』的一部分。然而,此智一旦指向其自身,就認知了自己的別相,並成為『別相知』。因此,自知不必被歸類為『總相知』或桂紹隆所謂的『概念知』。」
說「此智的自知是其『總相知』的一部分」,恰恰說反了,實際上,總相知是自知的一部分。因此,在訶梨跋摩這裡,只有總相知是不足以稱為自知的。舉例來說,知道張三是個人,不能說知道張三是誰;知道張三是爸媽生的,也不能說知道張三是誰;人、父母所生,這些都是總相。以總相知,知的是不完全的,只能知與他物所共的某些特征,不能知與他物不共的特征——別相(或自相)。
自相,有廣狹兩種含義,廣義的自相——凡是自身所具有的相,都屬於自相,哪怕他物也有同樣的相,也可以把此相叫自相,這是不與總相對立的;狹義的自相——即別相,與他物不共的相。「別相」一般指狹義的「自相」,是排除掉「共相」的「自相」。
《自證》說,「然而,此智一旦指向其自身,就認知了自己的別相,並成為『別相知』」,這是誤解。總相(共相)是自相(廣義的自相)的一部分,但不可以說總相是別相(狹義的自相)的一部分。通過總相智緣自體,永遠不可能認識到自體的「別相」,永遠只能認識到自體和他物所共的相。訶梨跋摩說,「是名總相知一切法,非別相智」,可見,總相智雖然緣自體,但絕不可能成為「別相智」。
四、訶梨跋摩對「意能自知」是怎樣理解的?
《成實論》:「汝言無有因緣譬喻能知自體,此中有說『意能自知』言行者隨心觀,而去來無心,故知以現在心緣現在心。若不爾,終無有人能識現在心相應法。」
對此,《自證》頁143理解為:「除了明確斷言『意能自知』之外,這段話中還有幾個值得注意之點:……」
「意能自知」,不是訶梨跋摩的斷言,是句俗語,類似上篇《讀後》提到的「人或自知」,訶梨跋摩曾引用「人或自知」來證明自己的「多心」說;這裡,有人以「隨心觀」來解釋「意能自知」的俗語。「隨心觀」什麼意思呢?鳩摩羅什的譯語和玄奘不統一,但從語義上看,並結合《婆沙》曾提及的類似見解,可以知道是後心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個心過去了,新生起的心可以知滅去的心,同在一相續中,也稱為自知。這也不是「知自體」的意思,是「知自相續」。
訶梨跋摩不同意「隨心觀」對「意能自知」的解釋,他說,既然過去未來法都沒有體,「意能自知」還是應該理解為「以現在心緣現在心」。——如同前面已經說過的,只能以總相智緣。在唯能以總相智緣的情況下,雖然俗語叫「意能自知」,實際上不是自知,只是自緣。
《自證》頁144:「第二,現在的意識只能以其自身為對象,因為沒有過去和未來心。如同過去的感官對象一樣,過去之心已經滅去,不能作為現在心的對象。」
這句話如果限定在訶梨跋摩對俗語「意能自知」的解釋下,是可以的,但如果認為這代表訶梨跋摩的一般觀點,就不對了。因為訶梨跋摩明確表示意識可以緣無法,「亦有無緣生智」「又於過去未來虛空時方等中知生,而此法實無,此即是無緣知」。過去的境、過去的心,都可以作為現在心的對象,只不過這類對象的體是無,屬於「無緣生智」。在「意能自知」的說法裡,訶梨跋摩認為,緣去來心的「無緣生智」並不是「意能自知」的含義——能知體有,所知體無,怎麼能叫自知呢?
五、「若不爾,終無有人能識現在心相應法」是什麼意思?
《自證》頁144:「第三,建立自知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知曉與現在心相應的心所。最後一點是可疑的,因為它意味著心所與現在之心同時起作用。如薩斯特利所指出,這與訶梨跋摩的『心次第生起』和『現在之心沒有相應的心所』的觀點是相矛盾的。」
我們先來捋捋與此問題相關的訶梨跋摩的見解。
訶梨跋摩認為,一切能緣都是心,心所是心差別。訶梨跋摩並不拒絕流行的「心數」這個名字,只是認為它本質上是心。既然心所本質上是心,沒有不是心的心所,那就不存在心與心所的相應了。因此,「受等諸相不得同時」。說「當知心心數法次第而生」,訶梨跋摩也用「心數」的名字,但認為它實際上是心。
此外,訶梨跋摩對相應、俱有是如何解說的呢?
《成實論》:「汝言有根智相應信,經中亦說餘事相應,如說二比丘於一事中相應。又說怨相應苦、愛別離苦。汝法中色無相應,而此以世俗故亦名相應。智信亦爾,信能信無常等,慧隨了知,共成一事故名相應。汝言從觸即有受等俱生,是事不然,世間有事雖小相遠亦名為俱,如言與弟子俱行。」
可見,訶梨跋摩認為,「共成一事」是相應義,而俱生可以指次第相生。
再來看這句:「此中有說『意能自知』,言行者隨心觀,而去來無心,故知以現在心緣現在心。若不爾,終無有人能識現在心相應法。」
對「意能自知」這句俗語,「有說」的解釋是:以相續心知,這是把「自」理解成「自相續」,而不是「自體」,後剎那知前剎那,也叫「自知」了。有部不反對這樣的理解。訶梨跋摩的解釋是:心緣自體,說為「自知」,其實只是自緣,不是真正的自知。
「若不爾,終無有人能識現在心相應法」,不要以為這句話意味著訶梨跋摩認為,現在心有和它同時生起的相應法。因為訶梨跋摩明確說過,與心同時生起的心相應法是不存在的。——他這是在反對對方的理論:如果不是像我說的這樣,你們認為存在與現在心相應的心所法,又通過「相續」來解釋心可以知與其不同剎那的心,那麼,你們認為的與現在心相應的那些心所法,怎麼能被了知呢?既然不能知這些,又怎麼能說「意能自知」呢?
而有部,確實如訶梨跋摩所說,「此智不知相應、共生等法」。但在訶梨跋摩的解釋體系下,此智當然能知相應、共生等法,因為所謂相應、共生,在訶梨跋摩的語言體系裡,根本不和此智在同一剎那,也就是說,它們在有部的語言體系裡,不是相應、共生等法。
這與訶梨跋摩的「心次第生起」和「現在之心沒有相應的心所」的觀點,是毫不矛盾的。因為要「攻子之盾」,所以「以子之矛」,而不是以己之矛。
六、「樂等受來在身」是什麼意思?
由於《自證》沒有理解訶梨跋摩上述的攻擊是以對方之矛去攻,而以為訶梨跋摩出現了「矛盾」,所以接下來嘗試解釋這個「矛盾」:
「要處理這個問題,參考《成實論》中的一個段落是有幫助的。……但是經量部否認過去或未來受的實在性,因此,他們不認為他可能了知這些過去或未來的受。……」
實際上,經量部雖然否認過去或未來受的實在性,但認為它們可以被了知。
來看《成實論》原文:「問曰:經中說是人受樂受時,如實知我受此樂受。如實知何受耶?過去未來受不可得受,現在受不得自知。答曰:此經意說人受,是故無過。又樂等受來在身,以意能緣,故亦無咎。又於樂具中說樂等名,世間亦有因中說果故。又是人先受樂受,然後取相,故名受樂受時如實知。」
這裡,訶梨跋摩給了四種解釋,其中「是人先受樂受,然後取相,故名受樂受時如實知」,明確表示可以了知過去的受。
《自證》頁144:「現在受又如何呢?似乎訶梨跋摩讚同他的反方所說的『現在受不得自知』。此陳述有兩個含義。第一,受或所有心所,並非自知的;自知的能力唯獨屬於意識。」
如前已述,在訶梨跋摩的思想框架裡,受的本質是心,也就是說,受與意識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心。訶梨跋摩確實始終認為,受不能自知。心不能自知。意識,當然也不能自知。把總相智自緣稱為自知,訶梨跋摩許可這種俗說,就像許可把心差別稱為心數,但不許可它是真正的自知。
對「又樂等受來在身,以意能緣,故亦無咎」這種解釋(這是訶梨跋摩的解釋之一,但不是唯一),《自證》頁144解說為:「對於訶梨跋摩來說,是意識在了知現在之受。如此一來,受被了知了,而意識成為自知的。」
實際上,訶梨跋摩這種解釋的關鍵在「身」,他想說:這個樂受,其實不是受(心),受心當然能知它而沒有自知的過失。對方不同意這解釋而質問道:「為以受者故名受、可受故名受?」訶梨跋摩說:「於緣中說樂,如火苦火樂,是故以覺知緣,故名為受樂。又眾生受此受故,名可受為受。」
「以覺知緣」,訶梨跋摩把「知我受此樂受」解釋成「知我受此緣」,於此緣中說樂受名,實際上非樂受,那麼,能知是受心,所知是緣,這樣一來,就沒有自知的過失了。
七、訶梨跋摩認為「現在不是單一剎那」嗎?
由於對前引文的誤解,《自證》頁145說:「在這裡我們碰到了與之前相同的問題:這意味著受與意識相應嗎?它們在同時起作用嗎?訶梨跋摩充分意識到了此問題,並給出了下列解答:『是人先受樂受,然後取相,故名受樂受時如實知。』」
在訶梨跋摩的思想體系裡,受本質上是心,心和心是不會相應的,不會同時起作用的。而《自證》以為的訶梨跋摩的解答「是人先受樂受,然後取相,故名受樂受時如實知」,原文前面有個「又」字,是獨立的另一種解說。它和把「知我受此樂受」解釋成「知我受此緣」的解說,是兩種不同解說,一者是知過去法,一者是知現在法,不可混為一談。由於混為一談,《自證》出現了如下誤解。
《自證》頁145:「訶梨跋摩在這裡區分了『先』和『然後』,這意味著他像上座部一樣把現在理解為一個相續。因此,現在不是單一剎那,而是多個剎那的連續,在其中可以區分出『先前』與「然後」。儘管某人是在領納受之後才了知受,說『他受此受時知此受』也是正確的,因為『前』與「後」的區分仍然是在現在之相續中。因此,作為心所的受並非真的與了知此受的意識同時。相反,它們構成了一個相續,在其中意識了知受就是意識的自知。」
《自證》誤以為訶梨跋摩的「現在」中包含了多個剎那,在現在中「可以區分出『先前』與『然後』」。這誤解不小。《自證》說「作為心所的受」,在訶梨跋摩那裡不承認是真正的心所,而認為是心。
「是人先受樂受,然後取相」,訶梨跋摩的意思是:受心生,隨即想心生。依次生起的兩個心分別是受心、想心。
《自證》未明此義,頁145解釋為:「儘管前一剎那的樂受被認為是現在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正在消散之物,因為我們只能『取其相』,而不能直接感知此受。」
現在只有一剎那。受心也不是想心的一部分。想心起的時候,受心已經無體了。後剎那想心緣前剎那受心,是直接緣的。
八、《成實論》關於「法不自知」的看法前後不一致嗎?
《自證》頁148-151,終於注意到了《成實論》中明確表示「法不自知」的段落。
《自證》頁148:「它可能與我們前幾節的所有討論相矛盾。……在這裡意識的自知明確被否認,……然而,第一個理由直接違背了訶梨跋摩自己對意識自知的論證。……這一陳述現實訶梨跋摩在其關於自知的觀點上不一致。如何理解這種不一致?是他在撰寫其著作的不同部分時改變了想法嗎?……」
因為前面持續的誤解,《自證》嘗試用二諦理論來說明。
《自證》頁149:「易言之,自知是一種建構,而真實的情況是沒有自知。」
《自證》頁151:「現在讓我們回到訶梨跋摩的自知觀點中發現的『不一致』。……現在我們理解了訶梨跋摩一方面建立自知,另一方面又否定它,這並非真的自相矛盾,因為他是在以二諦理論來分析它。」
如前所述,訶梨跋摩從來沒有承認過自知,他解釋俗語「意能自知」時已經把「自知」的概念換成了「自緣」,這不能作為他認可自知的證據。二諦理論或可以說明《成實論》的其他問題,但在「心不自知」上,《成實論》是一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