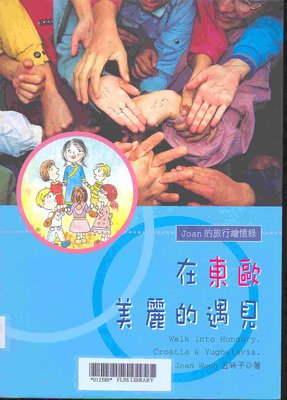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精选
《马家辉家行散记》是一本由马家辉 / 张家瑜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9.00,页数:81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家辉家行散记》精选点评:
●这里面附赠一小册《起点。》,讲的是马家辉的儿时故乡回忆。趣味十足。也可以称之为“马家辉版湾仔往事”。关于“搓麻将”那段可以多回味几次。
●有种迷人的气质在
●好读,好玩,有时还很好笑,行文看人,马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不过,好友看见《死在这里也不错》的书名,死活要把这本书没收……
●一点多醒来,读完已是五点。马先生点点滴滴,絮叨,至情。
●漫漫人生路,马家辉始终是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从前半生择其所爱,到用余生爱其所择,他活得恣意,也爱得真切
●这套书装帧很别致,图文排版也很讲究。附赠小册,记录的是童年记忆家庭往事。
●补标。2018年1月。有亮点,但也有弱点,有时候这两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即便多數都已讀過,即便讀得匆匆,仍舊是滿滿的感動。
●作为支持,是家辉在作家/学者之外的另一个面孔,有些故事已经在锵锵和圆桌派中听到过,很强的个人痕迹。越发可惜看不到那些犀利时评和影评,那些以后可能会成为了解HK的资料之一。以及,合著本的设计很有创意。
●https://item.m.jd.com/product/12291030.html?&utm_source=iosapp&utm_medium=appshare&utm_campaign=t_335139774&utm_term=CopyURL
《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一):你的路和我的路
还没有看,刚拆封,准备看完一本在这里更新一本。
那就先从包装设计开始说吧。
这个系列三本书的的护封都是微微黏在书本体上的,轻轻一扯就掉下来了。护封打开各是一张照片,这个设计就让我感觉实在是妙。
而《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书的本体更是被分成了双面开的两部分,有点阴阳的感觉。主要部分是马家辉的,另一就部分是张家瑜的。结合标题,是夫妻俩的两条路。
这个设计真的好爽好舒服啊……
《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二):到了终站的时候
以下内容摘自《死在这里也不错》(十年典藏增订版)自序
先说一个微博留言的小故事,据说真实:
一位网友买了老版本的《死在这里也不错》,午饭时在餐厅翻读,上司坐在桌子对面,没说半句话。午饭后,上司忽然把他唤到上上司的办公室,两个人望着他,脸上尽是安慰的慈悲笑容,轮流对他“晓以大义”,说什么年轻人千万别自寻烦恼,生活必须积极,为自己、为父母、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工作和学习,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网友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领导,我最近做事有犯错吗?请明确批评指示。”
上司焦急了,道:“我们担心呀!我们知道你在读一本什么‘死’什么‘也不错’的书,封面又是一张上吊的照片,担心你年纪轻轻,看不开,看不透,自寻短见,所以得跟你说几句,开导开导!”
好一场书名风波,唯望没替网友带来后续麻烦。
看书,毕竟如看人,你带着什么去看便会得到什么。写书也一样,书名构思亦一样。《死在这里也不错》,你看重的到底是“死”还是“不错”,往往关乎自己的心境明暗,而明暗变化有时,沉淡有时,光亮有时,所以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能够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联想和感觉。
所以书本值得重出与重读,尤其是作者自身非常喜欢的书。
《死在这里也不错》初版于2007年,由北京三联出版,薄薄的编排方式,精致细致,必须偏袒承认,这是我在十七八本散文作品里最珍爱的一本。眨眼十年,我由四十四岁的小叔变成五十四岁的大叔,人仍未“死”,日子也仍自觉“不错”,于是动念替旧书再编一个增订新版,纪念十载的读写因缘。而我是贪心之人,不仅增订此书,干脆把《日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和《温柔的路途》(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同时重编,《日月》还加入张家瑜的文章,改称《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合为“马家辉家行散记”,交由中信出版于读者眼前。出版社的朋友花了许多心血编排处理,这三本书的当下新版,便又成为我的最珍爱。
十年前读过老版本的朋友,跟我一样,成长了十年,不知道于此十年间可曾去过什么地方行走探索?会不会,我们可曾在地球某城某处相遇,甚至曾经都以旅途过客的身份聊过几句?希望我们没有在旅途上吵过架吧。但即使吵过,又如何?旅行不也是为了享受各种意料未及的喜怒哀乐?包括惊喜,包括抱怨,包括圆梦,包括迷途。日子就在跌跌撞撞里走下去,发生了便发生了,若以平常心对之待之,尤其事后回看,都可以觉得“不错”。
我们控制不了死亡,却可以控制心境。到了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在生命之旅到了终站的时候, 希望我仍能笑着说:不错,真的不错。
是为十年增订典藏新版序。
《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三):矛盾的旅行者(一)
这是第一本看了两篇序之后,觉得很有趣而往下看的书。《马家辉家行散记》典藏增订版,除了《死在这里也不错》,还合订了另外两本《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及《温柔的路途》,及别册《起点》。
马家辉,如果是《锵锵三人行》的观众,对这个名字应该比较熟悉,我是第一次听说。只因想读些游记随笔类的书籍,恰好推荐了这本,恰好看了书的两篇序,引起兴趣。
这是一个矛盾的旅行者,讨厌旅行惧飞怕黑怕人,却写了一本游记,是何等荒唐。所以他的游记是批判吗?还是无可奈何为之的抱怨?都不是,虽有部分公务使然,但作者是喜欢游历的,走喜爱作家走过的路,看喜爱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感受此时心境忆彼时思绪,并给出思考和见解。
“文艺而善感如家辉者,遇上今日种种化过浓妆的景区,血脉里的文化传承和眼前的俗野现实,其失落甚至愤恨可想而知。”
“文人毕竟是文人,从小背起的文字可以把肉眼解构得分外浪漫。就算到了三峡,分明一座水坝,他还是在江面冷风入到的夜里想起了‘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日三千里,郎行几岁归’。千年前的李白把诗句铭刻进进今人的肉眼;纵是平湖,你也看成了水急如箭的老三峡。”
梁文道写的序概括得正确,又无比生动。
普遍的旅行是看看风景,看看名胜,看看古迹,拍拍照,稍微深入的查查历史,查查典故,马家辉讨厌旅行,讨厌的就是这类普遍旅行吧。他阅读之广泛,所到之处均是追寻作家的足迹,感受作家的感受,找寻旧书店,探访故居,逛荡人少僻静之地,即使迷途,也能找到意外之喜。看似矛盾,却完全遵循了他的本性。
“旅行是为了相遇吧。人与地,人与人,人与万物,乍乍然在异地邂逅相逢,是这样一种绽放的惊喜。”
“不是说全球人类远祖全皆源自东非吗?任何人来到肯尼亚,便都不算旅行,而是‘归乡’,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这里游客其实都是归人。”
“最喜欢巴伦波因这句:‘即使只写两个音符,亦要说出个故事。’”
“什么是地球上最短的小说?据说只有一句话:‘当我醒来的时候,恐龙依旧在那里。’”
“诗是偶然遇上一个字,把它抓住,把它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变成永恒,而爱情,亦是,偶然遇上一个人,偶然遭遇一个情境,把对方抓住,变成永恒。虽是错觉,却是甜蜜的错觉,遇上,不错。所以岂可错过。”
语言朴实,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没有拗口难明的话语,触及心底柔软的地方,似有微醺感,又似有微微的惆怅感。
经常惊起,仿佛跟作者在同一时空,问了你想问的问题,答了你心中的疑问,道出你潜藏的想法。
很羡慕大女孩,有如此老爹,带着走南闯北,感受文化与爱,全无旅途疲累。心灵得到充实,身体之劳顿亦可忽略不计。
自觉我的旅行太流于形式仅流于表面,到此打卡一游,在朋友圈宣示主权似地得意洋洋,过眼云烟,如此旅行,正应了伴侣的那句话,这里跟我的老家没什么不同啊。
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这不是二选一的替换关系。灵魂,是需要一直旅行的,徜徉书海,飘向远方,给予想象,当身体来到时,似曾相识,那感受之深必格外深刻。
《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四):报纸专栏和10万+微信文是一回事吗?
马家辉在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时,梁文道还是一个在香港读书的中学生。彼时,前者为香港某大报副刊的专栏供稿,与其远隔重洋的梁文道从那方寸之地了解美国学院生活和彼邦学术,这可能也是他们之间最早的交集。梁文道自己也曾说,在做马家辉的朋友之前,首先是他的读者。这样的缘分放在今时今日,或许不会再有吧。谁还通过报纸专栏这种过时的方式了解世界?究竟还有多少人在看报纸,更不要提什么报纸专栏!
十年前,马家辉把自己的游记文章整理后,出版了《死在这里也不错》一书,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还有人这么写游记,把自己的缺点(怕飞、怕冷、怕黑、怕人)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尽管如此,他还是一次次往外跑,坦荡地写下自己在路上的那些窘境。这样一种状态,梁文道有一个精准的比喻,把马家辉的旅行看作抽烟,每一次都想要戒掉,但每一次也都戒不掉。
可是,谁曾料想,这十年的时间,势易时移,那些让我们曾经痴痴守着发行时间购买的报纸都渐渐消失,我们也从看报纸、杂志,变成刷手机、刷平板。我们一边感叹纸媒的凋零和珍贵,一边无情地抛弃曾经阅读纸媒的习惯,追着热点和10万+跑。谁还在读报纸专栏?
大众用手指决定了那么多家纸媒的命运,而纸媒甚或出版社对此看似也毫无办法,不是打着转型升级的幌子开始新媒体运营,对10万+这样的数字趋之若鹜,就是在新一轮知识付费大潮下随波逐流,毫无自己的个性可言。那么,作为读者,报纸专栏和10万+微信文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那么,就先让我们把时间调整到此刻。十年后,马家辉终于出版了扬言创作已久的长篇小说,在自己50岁的时候,终于可以成为一位名正言顺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囿于方寸之地书写的报纸专栏作家。而这部小说,得了好几个重要奖项,也得到两岸三地不少知名作家的肯定和推荐。然而,由于这本小说的光芒太盛,与他的小说(此处指台湾新经典版出版时间)同时出版的文集《小小事》很容易让人忽视,这本书也是他第九本以专栏文章为主的短文集结作品。
我想起十年前的自己,如饥似渴地在各类报纸(还有杂志)的书评或是副刊中找寻自己喜爱作者的身影,马家辉正是我找寻的作者之一。那个时候,还没去过香港,也像中学时的梁文道那样,通过马家辉的文字来了解香港在发生什么,香港人在关心什么。
十年间,去了好几次香港,每次去都不会忘记买报纸,保存着那厚厚一叠报纸,就是为了那几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时间在这些专栏作家身上好像从来没有流转过,依然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家辉会在出版了一本那么不同凡响的小说之后,愿意重新出版自己曾经的那些文章的原因吧。他根本不在乎十年后还有没有人读报纸专栏,就好像《死在这里也不错》在十年前刚出版时,他也毫不在乎地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读者面前一样。有这样坦率的作者也是读者的幸福。
这套书里,马家辉无意描述所谓旅行的意义,几乎都是私人的感受,有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致郁系”。他写自己在国外读书时的经历,大部分时候都是写自己给学生上课迟到,跑错教室,身体不适,如此种种。按现在的习惯性说法,就是几乎天天在水逆。
我记得,曾经还有过这样的讨论:报纸专栏是否可以被视作一种文体?当然,随着报纸的逐渐消失,这样的讨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只是对我这种可以称得上是阅读报纸专栏长大的人来说,知道马家辉还在写报纸专栏,还能读到他的专栏文字,真的是太好了!
《马家辉家行散记》读后感(五):顾文豪:马家辉的异乡记
马家辉的异乡记 作者:顾文豪 刊于2011年3月26日《新京报》(已获得作者授权)
按照福楼拜在《庸见词典》里的说法,旅行家“总是勇敢的”,而旅行毋宁“应该迅速完成”才好。害怕出门的我深以为然,情愿躲进他人的游记文字探头张望外间世界,要是写家笔下有神,呼风风来,喝雨雨止,遂乐得给自己的怠惰没出息找借口——有些地方合该更懂的人去看去写。
捧起马家辉的《温柔的路途》,起先亦当作旅途随笔来读,可越到后来,文字层层翻转,场景频频更换,面前展开的不止他观凤凰、临长沙、游韩国、下苏杭、赴德国、赏京都的脚步踪迹,反倒是越过这些场景所窥见的心灵走光。是的,“起步了,怎么停得了?”这是一册再平常不过的旅途辗转札记,却又是一份咀嚼之余别有回甘的游走心情,若不嫌冒昧地比附马家辉仰慕的祖师奶奶,那不啻是他也写了本自己的“异乡记”。不过他着实比张爱玲幸运,不用坐卧不宁地千里寻夫,可以和妻子、大女孩仨人随兴闲晃,即便不幸遇上这辈子都未曾见过的席地狂风,无纸无伞,自告奋勇“独自提着两个大箱子缓慢前进,一任风吹雨袭”,我担保他仍旧心意满满,有家的男人才有这般心甘情愿的负担;他也比张爱玲舒适,不必似她这般当“这世界像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的时候还催逼自己匆匆上路,虽然必须付出代价,再也看不到张爱玲那时候山青水绿的中国了,他得忍受所谓的古城凤凰深夜传出的震骇K歌声,“在噪音的空隙里偷取自己的微笑”,或徒然生气中国人的张家界没志气地贴上“好莱坞巨片《阿凡达》在此取景”之类的洋标签,好样的“文化旅游”,到头来不过是又一回戕害自家文化的短视“文化打劫”;他更与祖师奶奶一般纤敏,即便旅程迫促,也不忘斜眼扫视众生相,一一汇拢笔端,好比客途中意外拾得散碎零钱,就算派不了大用场,揣在兜里亦不自觉有值回票价之感:不论去到哪里,嘴里都含着槟榔的湖南男人活脱脱一台“会走会动的汽车小引擎,但不喷烟,只喷味”,在韩国的海鲜市场,惹他注目的不是男子精湛的磨刀和切鱼技艺,却是男子之妻一旁的崇拜眼神,多年的幸福才蕴积出这等温柔,又或喜在中国各地吃路边摊,要是夜里买吃更佳,因为他中意“灯下的热闹”,中意“灯下的人脸”,那简素白炽灯散播的阵阵暖意驱走的是“所有累积下来的妒恨与阴寒”。
如果是这样的走走、看看、写写,那至多是一册中规中距的异乡笔记簿,全然当不起“温柔的路途”之名的。事实上,马家辉的“异乡记”别有一解。他曾言:“天地有情,一念之间即可化陌生为亲近。家在远方,也在脚下;家人在故乡,也在眼前。处处无家处处家,不但不悲哀反而是一种温暖。”我揣想,人事栗碌的他仍旧尽量腾出时间带上妻儿出外周游,或非为一饱眼目,他大概并不认同也并不执拗单纯的“家”的概念,旅行看似去到陌生的异乡,谁说又不是逃离束缚、拘囿、牵制、压抑我们的所谓的家?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行,那合格的旅人是不是正该不让自己局促一地?如果加缪所言“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最多”诚然中肯有理,那走得最多最广是不是“活得最多”的别一种方式?早就明白“人生苦短,匆匆来去,有遗憾要走,无遗憾也要走”的马家辉,大概从未走在异乡的路上,恰恰相反,他一直行步在离开异乡、归返故乡的途中。
是这样更逼近生命本身的旅行,也许才出得来如此绵密专情的文字。说它绵密,是因为马家辉极善在文字间制造繁丽得一脸朴素的意象;说它专情,是因为他从不刻意打断文字叙述的自然语气,或者说,他在文字与世相面前始终秉持应有的克制。譬如开头一篇《明媚的下午》,如此明媚的题目写的却是难以言说的亲好往生。在安静轩敞的长沙咖啡店边饮咖啡边写作的马家辉突然接到台北电话,来电劈头动问,“姐姐在你身边吗?阿桑往生了。”楞了两秒的他稍稍定神,轻道,“她很快回来,我请她回电话给你”,随即挂机继续写作。待她回来,马家辉仍旧边写稿边说道,“你妹妹找你,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了”。待她通话完毕,一切如常。这时,不知哪里来了一个小孩,跑到他们的桌前,想要和他们说话,笑脸如明亮初阳。一头是白发往生,一头是红颜嬉闹,“生命轨迹在咖啡店的这个午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如常轮回”,而我们“不惊不怒,也没法惊亦没法怒”。
是的,不惊不怒,在生命面前我们都是孱弱的人。是的,不惊不怒,这也是马家辉文字书写的一个特色。我相信他本是多情敏感之人,自书中收录的照片而言,他着迷的很少是一处呆板的风景,多是人影穿梭风景之际的一个恍惚,换句话说,他在意人的身形影迹是怎样于无声处悄然生展又悄然熄灭的;而他的旅途札记,始终覆盖着一层迷蒙阴翳之美,这种美并非来自对书写的刻意形塑,而是漂泊各地、穿行书籍潜修而来的生命观照。无意揭示什么,因为所有的揭示有时不过是迟来的廉价体悟,无意改变什么,因为所有的改变有时亦不过是徒劳的自欺欺人,只须不惊不怒地步上路途,以一双温柔之眼窥看我们注定要离开的世界,也许那时会恍然,整个人生都会变得温柔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