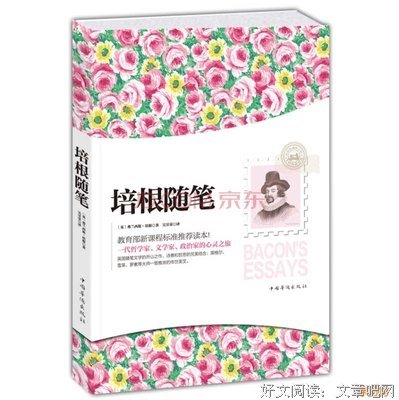罗素传读后感1000字
《罗素传》是一本由[英]瑞·蒙克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0,页数:6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罗素传》精选点评:
●几点感想:人过了一定的年纪,假如离开学术圈几年,再想回来就无路可走了。罗素低估了他那个时代以后的学术发展速度以及学科细化的水平。罗素对家族光环、政治名望充满了热忱,一面对辜负自己期待的亲人的绝情,一面陷于意识形态的困惑,在前后矛盾的判断中被利用和浪费。他造成了自己的悲剧。
●罗素为什么从专业的学术研究转向通俗写作?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的数学哲学理论在受到维特根斯坦攻击后站不住脚了,二是他关于婚姻和两性关系的言行在他那个时代太超前了,使他无法在剑桥大学立脚,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必须养家糊口,以维持贵族的生活水平,三是他的虚荣心,专业的数学哲学研究一般人没有兴趣,关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言论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他甚至尝试过文学写作,写过小说。
●后期读得比较快,但读到第十五章有关太太的实在受不了停下来。其实我很少停读一本书,一般都会坚持到最后。现在想,大概相比另一本,个人还是更喜欢维氏。罗素吧,实在对他和女人的关系和他的哲学处理方式不能有共鸣,以后会不会重读不一定,笔记今天也会整理完,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停了。
●一个哲学家的一百年。作者引用丰富参考材料,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罗素。
●瑞•蒙克在《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一书中,详细叙述了罗素后半生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素在其后半生中,尽管力图在哲学上继续有所作为,却很少得到专业哲学研究者的认可。在政治上,晚年罗素竟致力于反抗美帝,亦让人称奇。在公共生活之外,罗素糟糕的家庭生活,也让人不安。
●“罗素的观点最终总是变成针对他自己的致命武器,而他写给不同人的信件都被并置起来以揭露他的两面性。”——《传记家的报复》 ————————————————————在罗素的三位较知名传记作家中,瑞.蒙克算是比较经典客观的一位了。
●如果这部传记是公正的话,那他的人生真的是太不幸了。即使在公共空间影响力再大,家庭不幸福,又有什么意义。要是他能够一直做数学和哲学就好了,而不是后来跑去搞他根本就不懂的政治
●瑞·蒙克对罗素的总结是:“成就卓越,悲剧色彩浓厚”。罗素的主要成就是前半生关于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以及因前半生的成就而在后半生获得的荣耀。通读《罗素传》下册,罗素后半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的确不多,他的感情极度受损,婚姻多次破裂,罗素后半生较少做哲学相关的研究,而是转向了他不擅长的政治领域,撰写了大量报刊文章。即使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界并不买账,本书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根据瑞·蒙克的表述,这本书的内容部分来自过去文章的总结,有迫于生计的因素。(当然,罗素的政治文章或许平庸,政治见解或许幼稚,但他以诺奖得主的身份推动反核运动,这是个不小的成就。)本书作者认为,罗素所面临的灾难由两个基本性格决定:对精神失常的恐惧,强烈的虚荣心。这反映在罗素的一生。
●将罗素精神分裂般的偏执性格挖掘的非常透彻。翻译的有问题。
●看完都快一个月,我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碎,看着罗素的婚姻一个个破裂,他的儿女只有离开他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他的影响,一个孤独矛盾重重的幽灵,在他那么长寿的一生里,他为什么就没有学会好好面对在情感世界里脆弱的自己呢,为什么每次受挫处理方式总是压抑逃避或者冷酷粗暴,伤害他人。内心矛盾冲突的人制造悲剧的能力太可怕了,其自身也在承受痛苦煎熬,连锁的悲剧。
《罗素传》读后感(一):辉煌的功业,悲惨的人生
辉煌的功业,悲惨的人生 罗素的晚年似乎更冷酷无情,大儿子在与妻子离婚后得了精神病,也不管不问,在几次写的遗嘱中,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更不要说分配给他一点财产了。罗素也不允许他这个儿子的三个女儿(二个是亲生的,大女儿是妻子的前夫生的)与他有太多的来往,坚持自己和他自己的第四任妻子为三个孙女的法定监护人。事实上,他儿子的精神病并不严重的,只要有亲情的关怀,可能根本就算不上是病了。所以罗素去世后其家族的伯爵爵位还是由这个大儿子来继承,如果真的是精神病人,就没有资格继承爵位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罗素开始时拚命与三个孙女的亲祖母(也就是罗素的第二任妻子)和亲生父亲争夺法定监护权,后来又公开宣布放弃这种权利,使三个小女孩无家可归,老大回美国去了,老二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老三最后自焚而亡。 罗素死时除了第四任妻子罗素家族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他的女儿远在美国。 只有罗素与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小儿子因为他妈坚决要求儿子与罗素断绝关系,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罗素的影响,最后功成名就,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小儿子在罗素死以前,瞒着他妈,与父亲相认了,对罗素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了,这时他已经成年了。 罗素为什么这么冷酷无情?是不是因为他是孤儿这个原因。
下册中文翻译开始时还好,后来与上册一样问题多多,译者的中文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罗素传》读后感(二):凡人之于责任
找到一段似乎很适合作书评的话。
538.
更确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度年迈的老者:他在政治理想方面变得痴迷,认为美国推行侵略性对外政策,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他相信,在反对该政策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巨大贡献,让世界变得安全一些。罗素将自己的名声借给舍恩曼和平基金会从事的活动,显然觉得他所起的作用有利于整个人类。总体上说,他那时所持的立场非常清楚。但是,从细节上看,他常常显得摇摆不定,有时甚至头脑简单,不知所措。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一贯状态。罗素从来都不是非常老练的政治思想家。比阿特丽斯•韦布和其他人很早之前就说过,他总是希望得到解决政治问题的快速答案,所以倾向于将每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他常常以为,世界掌握在非理性的杀人者——马拉科医生——手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使用理性和仁慈为武器,对抗那样的情况。在他一生中,那样的倾向致使他接受草率的欠缺考虑的节制的政治理念。在他的垂暮之年,它们驱使他对世界事务形成了非常幼稚的看法,拒绝承认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质。在人生最后几年中,他接受采访中常常用到的一个短语是,“这很简单”。
——————
是不是很熟悉?
这种人在自媒体时代,我们见得多了。五毛,公知,自干五,键盘侠,什么都可以。他们在争辩中争夺着廉价而想象的权力,填补着空洞的自我。这很常见。罗素后半生的幼稚的政治活动,像极了燕郊一些不满社会的愤青教师,因为无法忍受自我定位与现实落差而参与地下结社,图谋“颠覆政权”的,可悲的失败者。
这本悲剧式结构的传记,解剖了一个通过幼稚的政治活动不断自渎的普通人,一个大写的撸瑟,和无数在现实中缺乏存在感与自我认同的人们一样。
他其实很聪明,但他坚持世界不能高于自我,这种稚嫩的,温室花朵一般娇气的唯我论倾向注定了其悲剧。为什么哥德尔的光辉照过了你,维的声名掩盖了你,就要佯装机灵地放浪形骸?书里的罗素本质上和沉迷二次元的肥宅没有区别,沉醉于久久的,久久的,自我迷恋。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属于天才的时代,活生生地把自己诠释成了一个小丑。
我不认为维后期的理论转向,能够比罗素从哥德尔的打击出走出来要更容易。或许罗素的悲剧说明,一个人若将智性或者肌肉或者任何一种自满的品性凌驾于德性,那么这个人的极限将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狭窄。
人生而为人,应该更仔细,审慎地思考德性这一回事。德性,还有美,在一个并不个体化,不流动,而是有一些先验和本质的视野。如果自我实现是天才之于责任的任务,那么自我认同,发现内在的德与美,或许就是凡人之于责任的坐标。
《罗素传》读后感(三):“新道德”怎么成了“不道德”?
英国哲学家瑞•蒙克同时也是传记作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数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些前辈学人自然就进入他的眼帘,进而成为他的笔下人物。《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被公认为是最好的维特根斯坦传记,而蒙克撰写的罗素传记其实也不遑多让。
罗素传分为两卷。第一卷《孤独的精神1872—1921》着重叙述罗素的童年生活和成年后的早期成就。第二卷叫做《疯狂的幽灵1921—1970》。罗素曾在其自传开头说:“有三股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在这三股力量中,“爱”放在了首位。罗素的情史非常丰富。他结了四次婚,离了三次婚,第四次婚姻时他已经年逾八十,有名可考的情人至少有七位。除了第一位妻子艾丽丝,罗素与其他女人的故事基本都亮相于蒙克书写的罗素传第二卷。
罗素虽然酷爱行走花丛,不过他并非世俗意义上喜新厌旧的花心渣男。因为他信奉“坦诚”原则,他并不向他的妻子或者情人们掩盖其他女人的存在,他也默许女人们发展其他性关系,甚至生下其他男人的孩子。换句话说,罗素想要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婚恋自由,并相信自己有能力维系、平衡彼此的爱恋。那么,情况如何呢?
对罗素一生影响最大的女人,是第二任妻子朵拉•布莱克。朵拉是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朵拉生下了约翰和凯特——罗素极其珍视的继承人。他俩之间不仅有爱情,有孩子作为情感纽带,还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近的价值观。为了推行新式教育,他们还一起创办了灯塔山学校。他俩之间还有协议,互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情,甚至邀请各自的情人同居一屋。罗素后来的第三任妻子彼得就是朵拉招聘的教师,在学校工作期间和罗素发展出情人关系,而朵拉也将自己的情人、美国记者格里芬带到了学校,并为格里芬先后生下一子一女。
这样的婚恋真的自由吗?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有的自由都是有边界的,一旦被打破,导致的崩溃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嫉妒乃人之天性。隐忍只不过是黑暗的发酵。蒙克的笔力如同解剖刀,男男女女的自私与虚伪,罗素想要表现大方却愤恨不平的心理展露无遗。其次,约翰和凯特很难在大人们的复杂纠葛中自如周旋,尤其是被罗素看重的长子约翰,无法成为父亲希望的男子汉,反而越来越内向怯懦,他后来的婚恋不幸终至疯狂,就是当初罗素埋下的苦果,而晚年罗素对这个自己曾经最喜爱的儿子的冷血态度,也让人对亲子关系生出困惑。另外,无论什么样的爱情,一旦掺杂了利益,就很难保持原味。朵拉的私生子让罗素生出继承权的担忧,万一约翰出事,家族的财产怎么办?猜疑既已滋生,便如冰纹悄然延裂。
“离婚门”的官司纷纷扰扰,拖了好几年,这下子罗素的名声臭了全世界,40年代他去美国教学接连遇到拒绝和公众抗议,就是因为他的道德瑕疵予人以不好的印象。而他为了维持生活所需,后半生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学术水平下降,虽然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等奖项,并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但前半生的成就再也难以突破。朵拉曾认为,她和罗素在反对陈规陋习的斗争中是同志,是引导人们获得“幸福的权利”的教育家,是宣传新的性道德观的先驱者。但现实以最嘲讽的打脸方式,粉碎了这一场幻梦。
蒙克在《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里谈到过一桩轶事。在剑桥的一次聚会中,有人想维护罗素在《婚姻和道德》中表述的婚姻、性和“自由的爱”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回答:“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去过了最糟糕的地方,那我无权评判他,但如果他告诉我,使得他能够去那儿的是他较高的智慧,那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保持不堕落的可能性完全依靠自我,依靠在内部觅得的品质。罗素自己也说过:“所有人类的活动,都是从两个根源中产生的:冲动和欲望。”罗素与朵拉等女性的这种“新道德观”的尝试,放置在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中是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胆实验,但这个实验恰也说明了人性弱点之根深蒂固。
附:
豆友的八卦考证贴:罗素的女人们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7800810/
乔纳森老师关于本书的严肃学术书评:《西方哲学史》是一本烂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MjM3NTMzNQ==&mid=2247484449&idx=1&sn=fac9f40ed4cdbe3bca612a8314878f89&scene=0#wechat_redirect
仿佛我读的是另一本书,见识隔着马里亚纳海沟,汗颜遁逃~好好学习。
《罗素传》读后感(四):转乔纳森: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一本烂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MjM3NTMzNQ==&mid=2247484449&idx=1&sn=fac9f40ed4cdbe3bca612a8314878f89&scene=0#wechat_redirect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流传甚广,现在出版英文平装本的Routledge出版公司说它是“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哲学书”,很可能是真的。
忘了是在高中还是大学时,我也找来中译本,读了一点,心里不禁犯嘀咕:这是罗素写的吗?转而去读文德尔班了。不过,对得享大名的《西方哲学史》的质量的怀疑,一直深植在胸。
最近,瑞·蒙克的《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严忠志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中译本出版,作者对罗素的后半生做了一些穷形尽相的描绘。我因此得以知道,原来对《西方哲学史》印象不佳的不止我一个人。
先看看《西方哲学史》的出版背景。1938年,66岁的罗素应芝加哥大学之聘来到美国。1940年夏天,罗素遇到一位有点理想主义情怀的百万富翁阿尔伯特·巴恩斯,巴恩斯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普通人的文化教育。哲学与资本的媾和开场了。
巴恩斯与罗素协商了几天,最后同意和罗素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工资为6000美元。罗素的职责是,每周举办一次哲学史讲座,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开始,经过5年的时间,最后讨论20世纪的哲学家(那些讲座后来成为罗素的畅销书《西方哲学史》的基础材料)。罗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头较紧,因此需要在社会上举办讲座,以便从基金会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巴恩斯当即将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两人签订合同,将这个数字写了进去。“一位富有的主顾(以18世纪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教书职位,工作不多,报酬不错。”在9月6日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如此总结了那一场交易。(《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第278-9页)
到了1942年秋天,罗素可能感觉钱还是不够花,于是就在外面接了私活儿。资本家不乐意了,心说,我大把银子养着你,你还在外面偷人?当年年底,巴恩斯基金会致信罗素,通知他已被解聘。
罗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后,随即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状告巴恩斯,理由是对方没有遵守1940年签署的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赔偿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获得的金额——并且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开始庭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罗素、彼得和康拉德(指罗素的妻子和儿子——引者注)不得不再次面临陷入赤贫的危险。(第295页)
“失去了——至少说暂时没有——来自巴恩斯基金会的收入,已经70多岁的罗素不得不埋头写作,依赖自由撰稿的收入勉强度日。”罗素真有点穷疯了,有稿就写,对女性时尚杂志的稿约也来者不拒。给《魅力》(Glamor)杂志的一篇稿子,就是替爱上有妇之夫的女性出主意的。据说这文章其实是罗素的儿子写的,罗素只是挂个名。哲学家西德尼·胡克就问罗素,你怎么写那种玩意儿?罗素说,不就为那50美元的稿费嘛。
1943年5月,他的财务状况开始改善。他从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那里,得到一笔预付稿酬,高达3000美元,是他那时为止得到的金额最大的预付稿酬。将要撰写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学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举行的讲座。(第297页)
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史》其实是为赚钱而写的,为了解燃眉之急。但书到底写得怎么样呢?瑞·蒙克有一段概述:
正如该书副标题显示的,其目的旨在将哲学史“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覆盖的范围上起古典,下至当代”。该书头两部分分别讨论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随后,这一目标踪影全无,直到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时才重新露头。读者的感觉是,该书布局不当,几乎堪称草草结束了事。例如,许多人认为,伊曼纽尔·康德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罗素仅仅使用一章篇幅,以批判的态度进行讨论,其结果让大多数人觉得不满。黑格尔著作等身,该书仅用15页篇幅阐述。尼采被当作泛泛而谈的讽刺对象,几乎难见具体内容。一方面,该书只字不提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另一方面,它却分别使用整章篇幅,大谈哲学史上影响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伦勋爵。这些做法让该书的质量大打折扣。此外,该书其后的部分屡屡出错,结果主观武断,观点变幻无常。就这两点而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罗素确实心急火燎,希望早点脱稿。(第299页)
这评价的确够低的。但并非瑞·蒙克一个人这样看:
当该书最终出版(美国版于1945年10月;英国版在一年之后)时,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C.D.布罗德(Broad)是罗素以前的弟子和崇拜者,曾经协助罗素重返剑桥大学,看到该书之后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全书笔调满不在乎,见解非常肤浅,结论过于草率,简直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第314页)
针对《西方哲学史》,尤里克·斯迈西斯——维特根斯坦的另外一位朋友和门徒——撰写了一篇书评,言辞甚至更为尖刻。斯迈西斯写道,“罗素爵士以前撰写了许多带有报刊文章风格的著作”,《西方哲学史》“体现了其中最糟糕的特征,但是质量比以前的更糟糕”。(第333页)
专家的评价低,架不住广大读者买账啊。瑞·蒙克写道:“虽然瑕疵比比皆是(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这些瑕疵),该书出版之后一炮走红,随即进入畅销书目录。它将罗素的财务状况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让他余生衣食无忧。”不光罗素有生之年如此,到今天,《西方哲学史》仍然是最畅销的哲学书。
不过,瑞·蒙克说“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意味着,例外至少是可能存在的。
事实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就为《西方哲学史》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书评,发表在1947年4月的哲学杂志《心》(Mind)上。由于是在专业杂志上刊出的,后来又没有收入文集,长久一来,这篇书评都极少有人读到。直到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重版《扭曲的人性之材》(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此文才作为附录重刊。
问题是,即便在新版中,书评的题目也没有出现在目录中,而仅仅作为“第二版附录”排在后面而已。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仔细读《扭曲的人性之材》英文第二版,也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篇书评。
其实,这是一篇特别精彩的书评,详尽、公允、文笔老辣,值得细细揣摩。伯林的话,这里就不一句一句地翻译了,撮述一下,他的意思是:《西方哲学史》既然是写给普通读者了,就别老拿专业水准强求它了。行文散漫,缺乏体系,缺漏多,东一句西一句,有头无尾,没有论证就“咣当”一下给你来句惊人论断,要么就是论证到关键处,让读者满怀期待之时,突然,没了;历史背景的交代相当随心所欲,也没与论述相交融,一开始还交代背景,等讲到近代,干脆思想背景什么的全不见了……所有这些毛病,其实都不要紧,因为你不就是来看罗素有什么见解的吗?那就看他一个人耍呗。罗素文笔优美,目光敏锐,就算有些问题忽略了或是没论证好,但他由始至终都是坦诚的,而且表述清晰极了。你还想怎么样?这就是罗素版的哲学史。
我自愧写不出伯林这样既有专业水准又饱含人性的书评。但愿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下面引一些英文段落,不爱读的请跳过。
总评:
It is a popular work, designed for thegeneral reader, and since it is written in clear and elegant and vigorousprose, with that peculiar combination of moral conviction and inexhaustiblentellectual fertility which in some measure characterises all, even the mostephemeral, of Russell’s writings, the general reader may be accountedfortunate.
The book is not, as was said above, intendedfor the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 and it may therefore seem captious andirrelevant to complain that he would often find it loose in texture andunsystematic, full of omissions and tantalising evasions, a rich and chaoticamalgam of unfinished beginnings, dogmatic assertions unsupported by argument,and again of argument abandoned precisely where he might well expectconclusions of an arresting and crucial kind to emerge; all this interspersedwith obiter dicta, often of memorable brilliance and insight, but usually leftto fend for themselves in an ocean of historical or sociological description;and that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scarcely likely to be of great help to him inhis own thinking.
or does it wholly fulfil its undertaking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ven the semi-philosophical reader or sophisticatedlayman: a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facts is indeed provided, but the selection of such facts sometimes seemsarbitrary; nor are they woven into the narrative sufficiently closely toperform the explanatory function for which ostensibly they are introduced.
The historical interpolations remainlargely detached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 save in chapters on the MiddleAges, where the interpretation grows somewhat thin and mechanical and obscures the rest of the story; when we get to thepost-Renaissance period, which is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genius of the author,such information grows progressively scantier, and by the time we get to thenineteenth century tends to peter out altogether, and we are left to facephilosophical views, e.g. those of Bergson, or of the logical analysts,virtually without the benefit of social or historical background.
结尾
To summarise this already over-lengthynotice: this work possesses outstanding merits; it is throughout written in thebeautiful and luminous prose of which Russell is a great master;the expositionand the argument are not merely classically clear but scrupulously honestthroughout. Important problems are sometimes omitted, or mentioned only to bepassed by, but they are never obscured or blurred, never provided with theappearance of solutions which both author and reader feel not to be answers toany genuine question. The author’s bias is open and avowed, deriving as it doesfrom liberal rationalism,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the intellect to solve all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of rational compromise to compose all practicaldifficulties so far as this is humanly possible – a view for which he hasstood, and indeed fought, all his life.
Russell shows a deeper abhorrence ofobscurantism and tyranny, particularly that exercised by clerical bodies andindividuals, than of any other human attitude, and his book, among other things,tends to emphasise how few and far between are the lucid intervals during whichreason is allowed to function freely, and how fruitful it is, and howbeneficent its works can be, when it is freed from fetters. Russell’s own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is so remarkable that future historians of thoughtwill in due course begin to apply to his thought and personality all thosecanons of scrupulou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cholarship to which the mosteminent among his predecessors have been submitted. This book provides a richsource of evidence for his attitudes towards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others,and in this, as well as in the dry light and unflagging intellectual stimuluswhich the common reader may obtain from it, its value and its interest reside.
说起来,中国读者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挺熟悉的。最近读到秦颖先生的《貌相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5月第一版)中关于何兆武先生的一篇,才明白《西方哲学史》为何在中国传播得那么广: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八十年代初曾热过一段,何先生是第一译者。他说,翻译这本书是上面派的任务,在“文革”中还给他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很久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也是他的同学告诉他,这书是毛泽东交代翻译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年代初,罗素和爱因斯坦发起了一个世界和平运动,运动的主题是反美帝国主义霸权。毛泽东很欣赏,便和周恩来联名发了一份电报,邀请罗素访问中国。罗素欣然同意。但临上飞机前还是取消了。因为罗素当时已经九十七岁,不可能完成访问的任务。他送给毛泽东一套《西方哲学史》。至于为什么只译了第一卷,何先生说,太费劲了,第二卷、第三卷就推掉了。
事实上,一开始,《西方哲学史》只译出了上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9月出版,是精装本,印数为2000册。后来《西方哲学史》中译本印了好几个版本,要想知道哪个是初版的,只需认准封面上的“内部读物”字样——有这个四个字的,就是初版,没有的,就是后来印的。
秦颖先生的叙述可能与事实有些微出入:罗素1970年逝世,享年九十七岁,所以他即使想来中国,也不会是九十七岁时的事。按瑞·蒙克的记载,爱因斯坦和罗素等发表反核宣言,是在1955年。从时间上考虑,毛泽东建议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史》,应该在1955年至1963年之间。
有时候,我们觉得一本书十分有名、流传甚广,其实,除了书本身有价值这个因素,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会左右它的传播——比如,因为是别人交代过的,你才有机会读到某本书。你现在明白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