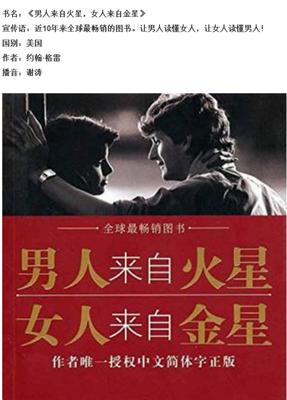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读后感大全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一本由[美]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一):触及他们的世界
以前我对于精神病人的认知是一种“可怜”。读书的过程,最大的感受就是,别以一个“正常人”的狭隘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书里讲了七个故事,都是作者亲眼所见,和对方接触的过程和感受。读着亦能身临其境,跟随者作者的思路去发现,去思考。
“正常人”易把事情简单化——以为失去了颜色,不就是黑白电视么;以为重见光明,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以为脑叶不好用,就直接切除了吧。 “正常人”易把事情复杂化——妥瑞氏的他,竟然也能实施手术;自闭症的他,在音乐里沉醉。 “正常人”达不到的境界——以近似照片的绘画,表现自己的记忆;自闭症一家人,对“正常人”的态度出,企图了解。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二):翻译太烂
作为neuroscientist,这本书的内容太棒了。从个体、人的理智、思想、感受出发来思考认知、心智,对于习惯把neuron、action potential、pathway作为思考单位的我,简直大开眼界。
但是,这版翻译太太太烂了。译者几乎没有生物学的知识,更遑论神经科学或是认知科学的背景知识了。但是这本书其实还是有相当硬核的部分,对于读者都要求相当的认知科学、神经解剖方面的背景知识。作为译者,不能准确理解作者的逻辑,不知使用合适的专业词汇,好好一本科普向读物,翻译得佶屈聱牙还词不达意,真是糟蹋了一本好书。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三):宽容他人,勇敢做自己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人的大脑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一部分功能遭到了损坏,其它部分可能会增强,进而发展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So,当我们失去什么的时候,请不要气馁,只要你热爱生活,必会找到一个美妙的世界。
书中的艾先生是一个画家,因为车祸,大脑中一部分受到损伤,成了全色盲患者。刚开始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他发展出敏锐的夜视能力,生活和事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还获得了一种美妙的人生体验。
史蒂夫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但其具有极强的记忆能力,音乐才能和绘画天赋。帕丁顿医生是一位妥瑞氏症患者,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所以,某一方面的缺陷尚不能阻止我们过好这一生,生活中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就如作者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也以自己的方式死去。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四):每个“疯子”都想成为正常人
之前有本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红了很久,后来又被拍成了网剧,图书也是一版再版。质疑声也颇多,有的人认为它是打着精神病的幌子,编成的一本书,作者不懂精神分析,不能称作“访谈手记”;而有的人则觉着看着看着,自己仿佛也不正常了一样。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它非常严谨。书由七个案例组织,案例中的患者各不相同,所患的疾病也不同。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症状,说明了采取的一些诊断方法,解释了病症的一些原因。从解释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严谨态度,有的医学、心理学名词,让人初看觉得混乱,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解。从这个角度说,似乎更适合心理学专业人士阅读。但患者光怪陆离的病症,又是我从未听说或接触过的。从这个角度说,普通人也可以阅读,更渴望阅读,毕竟有种走近科学的感觉。
说到严谨态度,不得不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奥列弗·萨克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是神经病学专家,又是畅销书,既是神经病学医生,又是一个患者。他因为遭遇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逃生,导致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的身份也开始改变。正是因为“医学的机缘”,他对人体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受到了患者更多的身心体验。
七个病患中有两个恰好有对比的感觉,一个画家艾先生因意外变成色盲,眼前只有黑白灰;一个盲人按摩师因手术重见光明。画家在车祸前的画作是抽象而又颜色丰富的,可意外之后,他却出现了短暂性的失忆,不记得自己发生了车祸,眼前也没有了绚丽的颜色,只剩下黑白灰,而这黑白灰三色还不纯净,白色也总有“脏脏”的感觉。幸运的是通过一年多实验后,他的黑白画也取得了成功。当医生告知艾先生,有可能恢复部分的色彩视觉时,艾先生却拒绝了。原因是他已经适应了这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他无法想象看见颜色之后会是什么情形。
而盲人按摩师维吉因无法适应光明世界,宁可再度失明。
每个“疯子”都想成为正常人,无论是适应病症,还是适应世界。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五):呼唤理解
这本比起错把妻子当帽子好得多,比起只是浅显综述各种例子,本文只聚焦在七个患者:看不见色彩的画家、活在过去的嬉皮士、患有妥瑞症的医生、失明寻求复明最终依旧安于失明的患者、沉浸追忆逝水年华企图复原故乡小镇的患者、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儿童和把自己喻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且不断尝试融入人们的自闭症患者,将病例与过去的病例研究比较分析,让读者更能了解这种病于患者而言带来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作者模糊了患者与精神医师的界限,像朋友一样对患者的过往娓娓道来,并且深入浅出分析过往至今疾病研究,更重要的是作者将重点放在患者本身,而非疾病。抛弃我们所谓的正常与异常的概念,以病患的视觉去看疾病对他们而言是什么,正是如此,从小到大的全色盲与盲人变成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拥有色彩体验和视觉感受后,生活对他们来说却更加踟蹰。
对于研究患有脑疾病而导致知觉缺陷的病人,人们是否能够简单治疗脑部而试图纠正患者前半生的知觉方式。随着科技发展,人们享受医疗资源优势的同时,对于知觉缺陷和精神疾病的治疗是否更该谨慎?是否更应该更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治疗方法,前半生以空间知觉事物一朝之内以视觉知觉事物的不适应导致的落差冲突如何排遣?人们能否对精神疾病患者从事正常社会活动一视同仁?书中患有妥瑞症的外科医生能够在手术过程集中精神而停止抽搐兴奋的例子让我感动。
好像人类从来都在担心科技发展过慢、抑或是医疗手段需要更新换代,但鲜有人提升随之而来的医疗关怀。在以电击试图改变神经连接,抑或是粗暴要求患者改变以前的一切试图融入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这是相当可怕的想法。
作者这本书非常出色得完成了他的任务任务:既让精神疾病导致的知觉缺陷为人所知,同时也传递了作者对患者的理解支持关心。实际上所有人初来人世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类学家,我们学习知识理解社交控制情感来让自己社会化,久而久之我们或许都忘了一颗心泵血只为一个生命。我们在社会过程中理解的正常概念限制了我们对很多异常事物的理解,这本书展示了这样的“异常”,并且呼唤我们的关注,亟待我们以一个人的视角来走进一个人。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六):我们是病人,更可能是天才。
前几年坐公交车去市区,在某站停靠后上来三五个孩子(可能是)。他们被一位大概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语言引导着“慢点走,扶稳。有人让座说‘谢谢’……”在重复的引导声中,我才注意到,刚上车的他们或眼神呆滞或行走不稳或肢体动作异于常人。我向车窗外扫了一眼——XX启智学校。那是我第一次离他们那么近。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在启智学校做志愿者的老师,无意间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位做志愿者的朋友说,她会在业余时间去教他们做手工或者画画,给他们上音乐课,做他们的小老师;他们虽然不善表达,但是他们的微笑是对你最好的肯定;和他们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们是如此童真,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甚至更加纯真;稍有不适的就是偶尔会遇见有点自虐的孩子把自己的手和胳膊都弄伤。她说那一幕觉得痛心,觉得那个孩子肯定缺少关爱,缺少我们的关爱。
作者奥利弗•萨克斯[美]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中描写了一些感知失调的人。 就像上面的那些孩子,“ 失序”是他们的(暂时)状态。
奥利弗在书中描述的都是奇怪的神经性疾病。像书中“失去色彩的画家”在意外失明(全色盲),认不清交通信号灯,无法辨认自己衣服的颜色,眼前的番茄漆黑一团,就连性生活都将面对着一具扫兴的灰色肉体。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想尽一切办法治愈自己。但没过多久,他却逐渐适应黑白色调,并神奇地开辟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彩色世界,并安然沉醉其中。那句“上帝给你关上了门,肯定会就留给你一扇窗”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经过一年多的实验和不确定后,他重拾画笔,独树一帜地步入稳定多产的黑白绘画世界。
一位色盲画家,让神经科学和色彩生理学研究再次肯定,人类的大脑皮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并且在受伤或全身瘫痪后,仍然可能重组且修改功能,更能因为身体某部位不堪使用,而以其他部位取而代之。
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神经科教授奥利弗•萨克斯不断剖析精神疾病带来的“问题”,似乎在引导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病人保持“意志自由”。对于庞杂多元的人类而言,任何形式的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猿人进化至今,我们也许早该探索人类尚未深掘的精神疆土。
我们是病人,更可能是天才。作为一名“病人”成员,我们应该怀有对病友的尊重,对那种不同思维,不同观点予以多多的包容与支持。
如果相关部门有力气,是否把每个地级市,甚至是县级都设置特殊教育引导学校,对某些“病人”实行零拒绝。再奢望一步,希望有一天能提升部分“保姆型”的老师,多培养“开发研究型”的老师。就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老师——他耐心浇灌,细心修剪,他让世间的美好、人类的希望走进被我们遗忘的角落,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七):天才与疯子之间的较量
读《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作者:苏术
中国有句古话叫:隔行如隔山。每一行业都自己的专业知识,行业与行业之间有纽带但是却不能共通。就像相交的两条线,有交点,却不是完全相交在一起的。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一行爱一行。当你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既然做出了如此选择就要尊重自己的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当你选择了做一个医生,就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有所提高,才是真的做一行爱一行。
我前几天刚看完奥利弗·萨克斯的《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非常棒。再次拿起萨克斯的书,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反而生出一种浓浓地熟悉感。
相比《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一书写音乐与神经学,《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所写的关于神经学的轶事就简单的多了。书里一共就讲了7个故事。
一、失去色彩的画家
二、最后的嬉皮士
三、精彩生活的妥瑞氏症医生
四、宁可再度失明的人
五、用画笔重建故乡的人
六、孤绝的奇才
七、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第六章写的是关于自闭症儿童。对于自闭儿童,我以前有写过关于他们的小说。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儿科专家说,和小孩子聊天,要把自己定位在和他们一样的高度,尊重他们,而不是站在大人的高度去否认他们。你可以蹲下身子,和他们视线统一,你会发现你所看见的会比你站在他们面前俯视来的更有趣。我喜欢和小孩子一起相处,那种感觉是和一堆大人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我会很放松,很享受小孩子的说话语气,我心里觉得他们小大人,又会觉得很幼稚(不带贬义)。那样小的人儿嘴里却说着大人模样的话语,真是可爱至极。我也会学着他们的模样,带着一点点趾高气扬的小大人模样和他们聊着各式各样的话题。我喜欢这种感觉。
说起自闭儿童,就会想起天才。我曾经看过一份报告说,天才和疯子仅一线之隔。所以我要说的是疯子也是天才。自闭儿童有很多原因导致自闭,可能先天的,也可能后天的。他们也许不擅长与人相处,但是也许他们在某一方面却是一个有较高敏锐度的孩子。
我记得以前看见一孩子,他对数字有超高的敏锐度。才七岁大的孩子,给他几组数字,且都超过五位,他能在几秒内记住并背诵出来。我很意外这样的孩子竟然会有自闭症,就像上帝给你留了一个窗,却关上了一扇门。
萨克斯还写了很多关于这类医学轶事,每一篇都让人颇有感触。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QQ:1147679123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八):非同一般的人类
如果说电影《雨人》让我们能用平常心看待自闭症患者,近年关于自闭症患者天赋异禀的报道则更令人刮目相看。惊人的绘画水平、音乐才华抑或计算能力,似乎是上天对他们社交能力缺失的补偿。美国神经病学专家、享誉全球的畅销作家奥利弗·萨克斯认为,这得归功于他们过人的专注力。疾病是造成不便的罪魁还是一种特殊优势?或许读过《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你会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答案。
萨克斯在这本书里讲述了七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有某种生理上的“缺陷”,同时也具有某项专长。一个正常人——比如研究者萨克斯——观察他们的生活,会先入为主地担忧其中的麻烦。你能想象一个画家变成了色盲还在继续创作吗?你敢让一个双手控制不住戳来戳去的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吗?你相信一个背井离乡十几年且毫无绘画基础的自闭症患儿能精确画出故土建筑吗?你能理解一个研究动物和人类的科学家实际上对人类情感漠不关心吗?实际上,他们做自己擅长的事得心应手,可能比普通人还更胜一筹呢。
这种矛盾是研究病因的极好素材,可能也是萨克斯选取这些案例的原因。譬如一般色盲患者很难表述清楚看到的景象,失去色彩的画家艾先生则是例外。一方面,他是因车祸突然变成色盲,有过非色盲和色盲的对比;另一方面,他的绘画能力也是种特别的表述手段,可以藉此勾勒出眼中所见。萨克斯分析了大脑辨识色彩的机理,研究发现艾先生的色盲或许可以治愈。然而此时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向时哭天抢地的艾先生竟然拒绝治疗,他已经适应了这个灰蒙蒙的世界,不想再重新适应一遍,何况新的创作风格让他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怎舍得放弃!
相比之下,同样有视力问题的维吉先生就没这么幸运了。自幼失明的维吉在新婚之际遇到良医,治好了他50年的眼疾。可惜这仅仅是生理上的治愈,维吉的大脑对于这新的视觉信号茫然失措,又不得不放弃原先触觉主导的世界,“在两个世界里,他都找不到安身之处”,陷入混乱的维吉一病不起。
这两个塞翁失马的故事令人唏嘘,大脑自我调适的可塑性又隐隐透出人类潜能:压抑了某部分功能会悄悄发展出另一部分功能。因此,失去视觉的人会拥有特别敏锐的听觉和触觉,长期触摸盲文的手指会变的特别粗壮有力,自闭症患者无法体会人性的复杂却能专注沉浸于事物本质。诚如萨克斯所言:“缺陷、不适与疾病,可以制造一个充满矛盾的环境,让人发挥潜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有人能言善道,有人能书会画,有人逻辑缜密,有人情感细腻,天赋顺应环境、体格、个性而来,为更好的生活做铺垫。尽管成年人的大脑不像婴儿期那样马力全开地适应调整,还是能够在持续刺激强化下诞生非一般的才华。拥有如此神奇大脑的人类啊,真是没有放弃希望的借口了呢!
——丙申年读奥利弗·萨克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九):“七个神经病”
在日常生活中,“神经病”这个词的意味颇为复杂。你可以用它来谩骂一个侵犯你的陌生人,也可以用它来嗔怪你最亲密的朋友,还可以用它来称呼一个有点疯癫但又无法企及的人物——“那人就是一个神经病”,无疑这语气中包含着一丝羡慕、嫉妒和恨。
当然,以上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神经病”。但在日常与科学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割裂,就“神经病”这个词来说亦是如此。所谓“神经病”,兼顾日常和科学而言,我们可以理解将其为,患者身上一定是“有哪根神经搭错了”。然而,正如我们日常言语的意义,这个“搭错了”产生的是疾病,但有时又会带来不可思议的现象。
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的《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就描写了 “七个神经病”精彩纷呈的故事。“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书中第七章的标题,刻画的是动物行为科学家坦普•葛兰汀的曲折人生。她能洞悉母牛的情绪,却无法领略人类错综复杂的情感;她能在“拥抱机”中获得安全感,却无法感受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妙。实际上,她是一名自闭症患者。相对于人类来说,她更像是一名火星成员,有时她视自己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在我看来,她在农场研究牛,与牛群生活在一起,更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牛类学家”。
本书中的人物,受到各种神经病情的肆虐,除了坦普•葛兰汀之外,还有“失去色彩的画家”,因为一次离奇的车祸,从此看不见色彩,最后却在“黑白画”领域大显身手;有“最后的嬉皮士”,曾经叛逆,迷失于嬉皮士风潮之中,后来因脑部肿瘤致使失明、健忘,却也了无烦恼,成了神圣的愚人,可一旦熟悉的音乐响起,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有“精彩过活的妥瑞氏症医生”,不时伸手一戳,跳上跳下,重复着奇怪的字眼和动作,可他又是一位受人景仰的外科医生和飞行员;有“宁可再度失明的人”,黑暗中摸索了四十年后重见光明,却掉入了一个举步维艰的新“视”界,他无法适应,直至重回原来的无光世界;有“用画笔重建故乡的人”,缘于一场怪病,三十多年不曾回乡,却能精准、生动地画出当地的一景一物;有“孤绝的奇才”,自闭症让他不及平庸,绘画才能却犹如一座孤岛,让我们见识了人类生命的丰富性。
读完本书,我们知道“神经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它代表着疾病与创造力。就像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本有一条平坦的道路但被堵住了,于是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前进,而另一条路是少有人走的路,注定要走得更加艰难,但是也往往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我们的脑神经工作起来大抵也是如此,千万不要忘了它会另辟蹊径,让我们的身体发生奇妙的变化。
实际上,如果我们只从科学的(外部的)角度来研究“神经病”,就有可能将病患仅仅看作一个有待治疗和恢复的客体,或者作为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如果科学家和医生抱持着这种态度,我们就可能会从病人身上剥夺掉他本来所具有的创造力。倘若非要研究的话,我建议像奥利弗•萨克斯一样,不仅面对前来问诊的病人,而且要去拜访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做一位“神经病”王国里的人类学家。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后感(十):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死去。—奥利弗•萨克斯
最近四五天,读完了这本《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强烈安利Logitech K480键盘,配合ipad使用,做读书笔记好用哭了!
开始正文部分!@#¥%……&*()——+
美国神经病学专家奥利弗·萨克斯不仅在医学领域享有盛誉,在文学方面也造诣颇深。这本集纪实、采访、社科于一体的著作,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脑神经科学的世界。我们能感受到人类心智和神经系统的繁复与奇妙。一点点微小的变异,可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进化形态。
我们用眼睛看世界,也用大脑看世界。用大脑看世界就是我们常说的想象。我们熟悉自己想象模式与思维方式,它决定我们的行为,并将伴随一生。读完这本书,我突然就想到一句日常怼人的话:“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说,你以为的世界和这个真实的世界之间可能存在出入,劝你别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奥利弗却用书中这7位各式各样脑神经疾病患者的故事告诉我们:甭管你得没得脑神经疾病,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并省察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将一些聋哑人、自闭症患者、妥瑞氏症患者视为“火星人”,完全不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无法走进他们的世界去“帮助”他们融入“正常人”的世界。可是切换到这些患者的视角时,我们在他们眼中又何尝不是一些古怪的“地球人”呢?又何尝没有做出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事情呢?
奥利弗将这些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在这本书里,他以客观平等的态度与这7位病患交流,甚至和他们共同生活、旅行了一段时间。他向我们展示了一颗颗奇特的心灵。每一个患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同样精彩的人生。因为大脑中某块区域受损而失去所有色彩的全色盲症画家艾先生,很另类地用黑白灰塑造了他自己的绘画王国; 由于颞叶系统损坏引起健忘症的格雷,唯独记得他最喜爱的Grateful Dead合唱团,在音乐的世界里不再有遗忘;患有妥瑞氏症的医生卡尔,努力战胜病魔并学有所成,成为受人景仰赫赫有名的外科手术医生;还有自闭的汤姆、史蒂芬, 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坦普……
作者对此的猜测是:如果一些疾病破坏了特定的途径,或是偏离特定的行事方式,可能迫使神经系统改道,令身体出现意想不到的成长与演化。这些病患的神经系统发生了些许病变,令他们蜕变成另类的存在状态。
疾病代表生命受到约束,不过病人倒不一定都有这种约束感。我所有的病人,无论问题为何,几乎都在积极地过日子。他们不仅无视自己的不便,反而往往因为身体的不便,更能体验出生命之美。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不要忘了,你在笼子外喂猴子的时候,那只猴子可能正在笑你。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以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人生就好,不管什么时候,一个人都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肆意潇洒,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