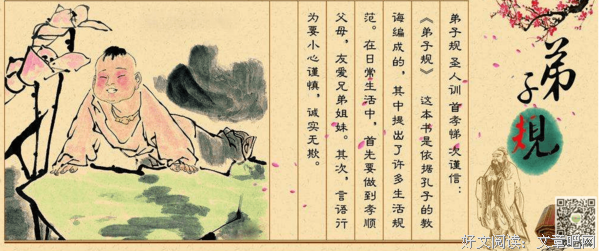《在适当时刻》经典读后感有感
《在适当时刻》是一本由(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01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适当时刻》精选点评:
●阅读它的过程,就像播放一张总是卡住的唱片。但是却和它的内容微妙的呼应……
●我爱上文学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那时我还在徒劳地适应学校里的生活;我抱着一本绿色的复习资料向教室的前门走去,她则站在门旁跟曾经的同学聊天,一步又一步,我缓慢地向她靠近,就在我们要擦肩而过的瞬间,她转过头来,脸上还残留着与密友聊天时的喜悦,眼神里的柔情,仿佛包容了我夜晚所有的孤独。
●任性而奇妙的语言
●私人感觉:因为布朗肖的诸多文本较之贝克特存在着情感(绪),因而对于它的阅读的恰当时刻是当读者持续沉浸在一个封闭的情绪中,往往因为某个人某件事而压抑,而哀伤,也即,再次成为记忆的囚徒。人永远都是记忆的囚徒,因而在正在行进之时,总是试图将这囚牢的边界拓得尽可能远,虽然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情感的流动,文字的流动,闭合的循环回路,逃离即是回归,此刻便是永恒。(在一众布朗肖译本中美感稍有断裂欠缺。)
●读布朗肖就像午睡醒来时的出神。
●haunting
●★★★★★ 读了两遍,可能基本上弄清了这本书的叙事结构,如果称其为叙事的话。叙事构建在“我”对那一时刻的回忆和思考之上,但是却永远游离在那一时刻之外,如同试图寻找城堡的K。卡夫卡和布朗肖是两个极端,一个善于利用“真实的”细节和荒诞,另一个完全游走于概念和叙事的边缘。空间和时间在书中都被极度地模糊化了,第二遍读的时候才发现有些部分可能是“我”和克劳迪娅做爱的描写。整部作品呈现出完全的虚无飘渺,难以理解。白昼和黑夜不仅仅是时间象征,它们也构成了这本书文学空间里的特殊内容。同样的,还有燃烧、颤动、画面、倒影……也许对照原文来看会好一些。读到最后,我意识到燃烧和倒影可能是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但是又超越柏拉图,因为它位于回忆和时间中。最后脱离叙事的独白对于我太晦涩了,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会抓住它吧
●然而翻译并没有其他几本精彩
●我们在阅读中好像都是收集古董的人,什么都收,而自己真正喜爱的古董却只能在偶然间寻得,我们为这一瞬间激动震颤,那一瞬间就是克劳迪娅的化身,于是我们疯狂地追逐她,殊不知克劳迪娅的震颤只是一种诱惑,它只意味着体验的消亡——朱迪特。阅读就是一场漫长的与这两个女人的相逢,告别又重逢的过程。
《在适当时刻》读后感(一):简述
写《在适当的时刻》,布朗肖已经不是处于人类物理身体青春期的人,在小说里,我们得知,“我”已经有了一定年龄,但他是“美丽”的北方人,如孩童般慌张又举止得体,莽撞激动又微妙冷静。
小说罕有地不涉及死亡,至少死亡并不能占有比爱更多的比例,布朗肖希望与读者共同探讨爱的可能,去爱是可能的吗?乃至于去爱一个最可怕的人是可能的吗?
——“言语,对我而言最伟大也最真实,闪耀的心,以你我相称的表达方式和夜晚的嫉妒。”
——“死亡,但为了死去,必须写作——终点!为了它,一直写到最后。”
《在适当时刻》读后感(三):昼闻纷乱
我们与白昼有真正的血海深仇,概念必然曝尸荒野,人们以游魂的姿态尽力返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慈悲的零涕,努力化作虚无,这沉重的肉身调着日常的肌理之羹,总是重复言说着不便忘却的召唤,而要把幻觉置于无上之位简直就是一场迷梦,混乱是具身再现的,追随每一次的念头,对于身体的流泻,抱有绵密之忧愁,因为在这无望的驻守中何其难以逼迫自己在白昼的冒险中残存躯体的完全,守望是最高的牺牲,却如此不得要领,那寂静的心跳,窗外大雪拥城,和夜的沟通同时密谋褫夺,当我在荒野游荡,那白色的飓风摧毁时间之舞台,我同时预感深沉的剥离发生在入睡之时,手的惶惑和空荡荡的抓握,譬如听见空无之壳的破碎,永远无法清醒的被动来临,告诫这时间有次序得退避如同它们生硬地盖下来,把上到手头的天空的声音压缩成薄片,在白昼与夜两相融化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点上,咏唱的威力于是堵住流淌的意念,你对天空的孱弱怀有看护之职责,这个诫命阻止你进一步向着永恒的空无进犯,属于声音的油性的黏腻之记忆的跳动,就算四方竖起坚墙也无济于事,它,中性的潮涌,比海上汹涌的夜之浪潮更加汹涌,那一个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对在场之在的守望最终迎来黑暗的收割并且在这黑暗中我属于遥远的过去的那厚重记忆仿佛一只盖碗破碎,破碎又重聚,在这样的漩涡和拼接的游戏,恍若游戏中,我再次感到身体和心灵被逗引至那无法回溯的遗失,如此失鹄的冲旋再没有任何具体的甜腥,我企图回到那幽幽黑夜四下空虚的启始之点,世界循环失去坚固的暗示和援助,唯有那散发寂寞的喃喃之声还在找寻一具早先的肉体,仿佛水中孑孓无定向的流播,在那样的时刻,毁灭与生成在那个时刻失去可辩的模样,在重复的迸发和微缩之核中渴望有快捷的打造和衰败,如同铁匠之锤打,而溶于时间之流的所有秩序都要在这柔波般的锻造下恢复或找寻它们从不曾具有过的坚实质地,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即拆即造即造即拆的模糊的舞台,在喧嚣爬满那可怜的幕布之时毁灭如同慈悲的抚摸瞬间到来,幻想同样不可靠,那些来来往往水一样游蹿的身影如同鬼魅上演惊悚的剧目,在那样的时刻,伟大的安静恰如伟大的轰鸣,时间的隐秘轨道飞驰,在那样的时刻,你看着那些绣满斑驳的镜子,在那样的时刻,空无在召唤,荒漠在扩张,一切失去其固定相貌的面孔涉足夜的疆域并在锻打中按时发派,此时你或许忆起那声响,那喃喃之声,像泡沫一样缀满大地和天空,每一缕偏振的光线中都蜗藏着一个暂时的空间,在发出声音,从那个点,到现在为止,好像有条不紊却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挥发殆尽,全部的噩梦来自于这样一种确信: 我是我。然而,我真的是我吗?
在适当时刻8.6[法] 莫里斯·布朗肖 / 2015 / 南京大学出版社《在适当时刻》读后感(四):巴塔耶:沉默与文学
[法]乔治·巴塔耶
lightwhite 译
在那种把莫里斯·布朗肖比作威尔斯(Wells)的“隐身人”的意图里,有一部分错位了的玩笑。首先,上述的作者从来没想让威尔斯的幽灵在解开身上的绷带时揭示的虚无(néant)显现出来。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布朗肖的小说作品所拆解——或摊开,如果一个人愿意这样说——的句子揭示了沉默。无论如何,我在这样的差异周围认出了一个精确的意象。布朗肖的作品具有一个唯一的对象,那就是沉默,并且,作者的确让我们听到了沉默,几乎就像威尔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隐身一样(电影从这个故事里汲取的东西被如此可怕又如此完美地揭露出来)。
玩笑,总而言之,具有这样的趣味:我们很难用玩笑表明布朗肖在其作品中赋予文学的角色;但没有玩笑,就更难办了。作者的确在其批评的写作(参见《失足》[Faux pas],《洛特雷阿蒙与萨德》[Lautréamont et Sade],《火部》[La Part du feu])中对自己做了这方面的解释,但一种感性的表述并不算坏。我应立刻提供这样的纠正:在威尔斯的意象里,有某种繁重的元素,一种不幸的挑衅,一种可怕的恐怖,它不只是一个困住我们的陷阱,它制造了悲惨的愚蠢灾祸。在布朗肖的书中,既没有陷阱,也没有捕获,只有一种藏在词语下面的最终之沉默的意象,如果它和衣物下藏着的可见之虚无一样惊人,如果它令人不安,如果它看起来甚至反对一切的安息,那么,它无论如何是中性的,它不能有任何的意图;最终——或许——它只给我们留下一种遥远的友谊感,一种遥远的共谋感。
友谊?共谋?这恰恰是布朗肖的悖论所在。我担心,对他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他的名字暗示了一个苦恼的世界,或暗示了苦恼所包围的反思。其实,我应该承认,作者表达自身的方式滋养了这样的一种感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文学会以各种的方式让人失望。它用文学几乎未获得的掌控强行提出了自身,但还要担心的是,这样的掌控一旦得到承认,读者就抱怨看不见它,最好是绝对看不见作者想要说什么。这样的印象没有道理。但它不可避免。
相反,我应该坚持一个事实,即莫里斯·布朗肖的“记述”(récit)没有分享我们时代几乎时髦的沮丧。《在适当时刻》不仅是一本幸福的书,而且还没有哪一部小说提供了这样一种对幸福的描述。如果这样一本书仍然给出了困惑,那是因为作者的表达模式把一种完美的不可见性引入了文学,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人突然从相反的方向转动胶片,而银幕上马的运动就消失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象试图以一种不那么精确的方式来指明的事情:绷带的解开揭示了虚空。对作者而言,虚无就好比沉默。他毫不费力、毫无厄运地被沉默深深地吸收了:惟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费力和厄运才开始。
一个人如何把过多沉默的注意力投向这样说话的作者呢(他所说的东西通过一种粗暴而可怕的撕扯,从语言中抽出了某种不是语言的东西,语言所终结的东西):
我唯一擅长的就是沉默。现在想来,这样巨大的沉默简直不可思
议,它不是美德,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想要说话,只是因为沉默从
来没有对自己说:小心点,你有些事必须向我解释,那就是为什
么我的记忆,我的日常生活,我的工作,我的行动,我所说的
话,还有从我指尖流出的文字,所有这一切,不论直接还是间
接,都没有对我整个人的真实关切透露过一点信息。此刻,开口
说话的我无法理解这一沉默。当我痛苦地回望那些沉默的日子、
缄口的岁月,好像面对一个无法进入的、不真实的国度,不向任
何人开放——最重要的是不向我开放。可是,我生命的很大一部
分就在那里度过,轻松自在、无欲无求,凭一种令我瞠目的神秘
力量。
失去沉默,我的悔恨无以复加。说不清是怎样的不幸侵袭了曾经
侃侃而谈的人。这不幸静止不动,一言不发;就因为它,我呼吸
着令人窒息之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整栋房子都无旁人,房外
亦无一人,但孤独本身开始张口说话,我则不得不反过来言说这
一说话的孤独。不是想要嘲弄它,而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孤独盘
旋于它之上,而在这更大的孤独之上,还有更大的孤独。每个孤
独都相继接话,想要压制那话语,让它沉默,结果反而都在无限
重复它,并使无限变成它的回声。(《死刑判决》,第41-42
页。)
沉默的难题不能被更加准确地提出了:沉默的难题是一个言说的问题,沉默是语言能够不说的最后一个东西,然而,把沉默当作对象的语言必定犯下了一桩罪行。
首先,选择把沉默当作一个对象的作家对语言犯下的罪行——就像乱伦者对法律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沉默本身所犯的罪行。我不知道一个作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地踏上无法逃脱的丑闻之路,起身反抗那规定所有人之行为和判断的重量。一个人如何设想逃避的可能性?不可避免的骗局同时也是欺骗的不可能性,因为我们必须回应的要求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但从那时起,一个人就无法进入这个王国,在那里,他将得知语言所不揭示的东西——对此,布朗肖已通过一种异常而骇人的努力,在他的书里说过了——在那里,一个人只在力量的极限处接受失败,并且,这最终只在一个条件下可以忍受:不断地服从失败所揭示的判断。
为了谈论一个谈论沉默的人,我只能亲自体验这场难度不断加大的游戏。但这不无补偿。我留有一个余地……我所说的或许是暂时的,并且至少被允许简化。如果我应谈论《在适当时刻》,那么,我没有或者至少现在没有和沉默的欲望联系起来,我还可以谈论这个由绷带的拆解所揭示的幻影,它无疑就是沉默并且只被沉默所揭示:它具有一种幸福感——它不同于威尔斯的隐身人的意象,即便它,相反地,没有从一个不那么可怕的时刻浮现。幸福和虚无,任何的预谋都无法获得这样的幸福,对它的预谋立刻在虚无中变成了这样的幸福。
一个人会怀疑我让只有严格才……的东西变得索然无趣……事实上,幸福似乎褪色了……
但我要更为清楚地表明,这种从沉默的扩张的荒漠里浮现的幸福,如果它源于一个遵守语言之日常法则的故事,那么,它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未知的。在我看来,我大约可以顺着概述这个故事。一个男人在一段时间过后回来寻找一个女人,朱迪特,他这样说她:“各种事件,被夸大的现实、痛楚,难以置信的念头显然在我俩之间漫长地堆积,外加一个如此深远的令人愉悦的遗忘,她很轻易对我的出现不觉吃惊。”(《在适当时刻》,第3-4页)但她当时和克劳迪娅一起生活;克劳迪娅“年龄相仿……自小就是朋友,对于朱迪特而言,她更像一个站在身后有着强硬性格且充满才华的大姐姐。”(第15页)克劳迪娅把她自己嵌在了朱迪特和叙述者之间。克劳迪娅没有被叙述者的预谋之缺席所击败,而是某种意义上被淹没了;他自由地找到了朱迪特。有时候仿佛是偶然地,记述遵循一个令人信服的现实的轻易的过程,那个现实无论如何从半睡着的现实中浮现:“炉火可能已经熄灭了。我怀着同情回想着那炉火,刚才它是那么容易就被点燃,在这个下雪的时刻。雪花渐渐被细小的雪尘代替,而后者由渐渐被某种令人鼓舞并闪耀的,某种更为显现的外部世界替代;它宛如某种执着的外表,几乎像某种显灵——为何会这样?白昼想要自我显现吗?”(第53-54页)然而,在接连不断的意象之间,存留着一个由记述之组织内部的缺席所创造的虚空,那样的组织把一系列的事件串连起来,但本质上缺乏人物的关注或意图,只有当下的瞬间占有了人物的时候,人物才被给予我们。如果这些意图被说了出来,那么,它们就仿佛遭到了否定,被还给了瞬间的轻盈。
她们各自有自己的家务事。“我将做这件事——我将做另一件事。”这和未来的宏伟计划,神圣的和另一个世界相连的决定一样重要。“我将拜访木材商!——我将到洗衣工那里去!——我将和看门人谈话!”这些言语在清晨从她们的茶杯上飞过,宛如永恒的誓言。“吸尘器!——渗漏的水!——堵塞的垃圾管道!”而结论,即整件事中最为凄凉的是:“莫法夫人将把这一切都清扫掉。”门开门关,嘎嘎作响。谨小慎微而又好打探是非的气氛不断地紧随着她们,貌似忙碌的、游手好闲的,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赋予她们的来去些许柔和的矫饰。(第47-48页)
但没有什么比这些“浓密的大雪”(第63页),比这“再次变成了一种暗淡的深邃”的雪(第65页),比这“如此阴沉(如此无谓的白色直至无穷)”的时间(第67页),更加地符合一种对同样乏味的未来的希望。在这些连续的时刻里,过去和未来从没有逃离关于当下的不确定的、徒劳的、沉闷的东西。然而,没有什么更加多变、更加绚丽、更加欢乐的了。但最终,在这个让动物的低沉的嚎叫不时地从中逃离的世界上,终结了思想的东西,乃是唯有沉默才知道如何包纳的幸福之意象(如果它不首先是那无止尽的沉默的一部分,就没有人表达过它)。
在此刻,没有白昼也没有夜晚、没有可能性、没有等待、没有担
忧、没有休息,然而一个站立的男人被包裹在这话语的寂静中:
没有白昼,然而就是白昼,以至于这个在低处倚墙而坐的女人,
这个半曲着身体,头部倾向膝盖的女人,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
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
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
发生,结局开始了。(第97-98页)
遗忘并非发生于事物之上,但我必须指明:在它们再次闪耀的光
明处,在这个不会摧毁任何它们的界限的光明里,但其将无限和
一种持续的欢乐的“我看见你们了”结合在一起,它们在一个重新
开始的熟悉感中闪烁,在那里其他事物都没有位置;而我,穿过
它们,我拥有反射的静止与善变,在诸多画面中游走并和它们一
起被拖拽进移动的单调中,看起来没有终点就如同它没有起点一
样。或许,当我站起身时,我对开始怀有信心:如果不知道白昼
开始了,那谁还会起来呢?但是,尽管我仍能够行进很多步,这
也就是为什么门会嘎嘎作响,窗户打开了,阳光又再次出现,所
有的事物又重新处在它们的位置,不可改变的、欢乐的、确定的
在场的,以一种关闭的方式在场,如此确认和稳定以至于我明白
它们不可抹去,在它们的画面再次闪耀的永恒中静止。但是,在
那里看见它们,在它们的在场中微微远离自身,且依靠这难以感
知的后退,成为一个反射着幸福的美丽,尽管我仍能够行进很多
步,我也只能在我自己画面的安静的静止中来来回回,这画面和
一个不再流逝的时刻漂浮着的欢庆相连。我竟能够深潜到离我自
身如此之远的地方,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被称为深渊的所在,而它
仅仅将我放置于一个节日的欢乐的空间里,一个画面永恒的再次
照耀,人们可能对此吃惊,我也会有同感,如果我没有体会到这
不知疲倦的轻浮的重量的话,天空的无尽的重量,在那里我们所
见的持续着,界限平展开,遥远处昼夜闪烁着一个美丽表面的光
华。(第107-108页)
在这样一种把充裕当作眩晕之坠落的无论如何被掌控了的语言里,一个人怎能看不到:意义将要揭示那已是虚无的东西,那仅仅作为闪光的瞬间,在这持续(和意图)的世界中,它只是加剧内心之紧张的空虚。
-------------------------
原文发表在1952年2月第57期的《批评》(Critique)杂志上,收于《全集》第12卷,第173-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