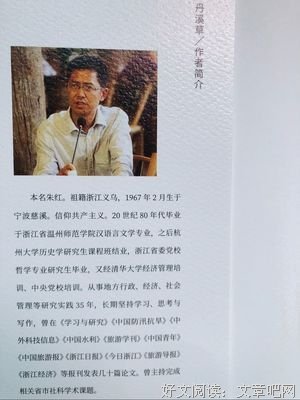《人类学》的读后感大全
《人类学》是一本由康赫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0元,页数:1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学》读后感(一):颜峻:死亡并不夺走听觉
本文刊发于《此刻》:《今天》改刊后创刊号头条
《人类学》读后感(二):人类学读后感
我在其他很多地方发现,有很多人没有读完这本书,有人说“这是一本防灰神器”;我父亲买来后看了一晚上就放在一旁。这并不是代表这书不好,而是代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它。 今天把人类学最难啃的第五章也全舔了一遍,结束了三个月的初步阅读,在此小结。 首先这本书的故事无法梗概。这并不是代表这本书没有故事性,相反这本书全是故事。由于它内容可以用庞杂来形容,我只能点一下: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作者通过他心中的史记一样的手法,通过众多人物来描绘了一个他心中的时代。这些人物选择并不是随便的,他通过一群艺术家(郁利,庞大海),商人(李旗,包利民),流浪者(大同),作家(麦弓),女孩(小孙,布蓝),外国人(迈克)等最具有代表性特殊性动荡性的人物来描绘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本书避开了那些工作生活较单调的人物(如许万松),毕竟他们的生活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有什么区别呢? 这本书除故事性外还具有语言性的特点。让许多人无法接受的各地方言是一例,有时的突然押韵也是一例,各种文体也是一例,这需要自行阅读。
不难发现书中人物性格鲜明但扁平,我认为作者将自己的一些特定性格抽离出赋予人物,所以通过人物可以看到一些作者的性格或经历。 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我好想吃红烧排骨和绍兴黄酒。还有,不禁感叹这本书真的牛x。
《人类学》读后感(三):地狱里的苦行僧——读康赫《人类学》
地狱里的苦行僧
康赫说北京城是一个巨大的子宫,孕育着十五年以后的繁种。现在的我们,也只是经历了更多物质生活的变种,和九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研究九十年代的北京,就不再只是观史知今的借鉴,更是为了看清我们自己,嗅到我们自己,这也是我第二遍阅读的原动力。
这本130万字的煌煌巨著,康赫似乎不需要人理解。他时而像诗人一样意气风发,时而又像疯子一样喃喃自语。方言,错乱的时空,随处可见的对话和大量内心独白,像是一道道栅栏,让那些投机主义者望而生畏。康赫以麦弓为引线,对他周围所有的人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如果把《人类学》看成是一幅清明上河图,那么康赫为所有的人配备了完整的肉体以及灵魂,内容翔实生动,对话如有在耳。康赫以他绝对的控制力,让你像上帝一样俯瞰着九十年代的北京。
康赫的叙事风格冰冷平淡,又生动饱满,像是在带我们参观着一座地狱。如果说前六章康赫只是在小心翼翼的叙述,那么到了第七章,他显然失去了耐心。箕子对着纣王呐喊,命运的极限多么简单,只有死亡这千篇一律的面孔,你却永远无法将其看透。麦弓的喃喃自语,我无法克服的愚昧,意味着我这一生无法冲破的平庸,我的感受力和知性的极限。康赫笔下主人公麦弓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而悲惨的过去使他一直处于一种旁观者的状态,怀着一种游戏的心态生活,冰冷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以刻薄冷血著称。但麦弓冷酷的外表下是一腔的热血,他有着坚定的信仰,不怕权威,不惧个人得失。他清楚地认识到地狱的黑暗却还想试着去改变它而不是离开它。但是对于没有信仰的礼教徒们,对于只有民众没有个人的国人来讲,他显然是没有受众的,个人主义死路一条。而不论是电影导演庞大海,艺术家郁利,子鱼,贺老六,还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李旗,他们都只是一群各种混乱爬行,彼此相互践踏的虫子,看不到任何希望。麦弓只能去跟瑞典文化参赞阎幽磬和一个整天抱着英汉词典的外国公使讲黑暗辩证法,讲中国人的精神通道,讲中国人三生万物的中庸,讲个体意识的培育。跟一个汉语都认不全的移民姑娘(俞琳)在床上读他的作品和剧本,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麦弓说:如果麻烦一定要来,我也不想刻意避免。还是在公使家里,符克馆长对麦弓说:“在专制的国家,你说的自我可能刚露出脑袋,就被嘎,切掉了”。麦弓平静说道,可以切啊,为什么不?他至少是一个头。是的,至少是一个头啊。
《人类学》读后感(四):奋勇啊然后休息啊,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一本十万字的小说,阅读时间根据文字质量在六个小时上下浮动。《人类学》有一百三十三万字,七十八小时。康赫写了八年,我读了六天。波澜壮阔的人群肖像,无孔不入的上帝视角,诡异多变的行文手法,数不清的故事,数不清的修辞,文字是用来享用的,看完最后一页,渺小的你重新活过了一遍。
渺小。你发现你二十五年来所有精彩绝伦的故事,在这本一千三百多页的书里,只能占到不足一手大的篇幅;你发现你写过所有洋洋得意的句子,不足康赫轻描淡写的一句“经过它周围的风,摸到了它可能的形状”;你发现当你仍然站在以前自以为上帝的位置上试图去谈论它的时候,居然如此无力。
无论如何,首先为自己生在康赫的时代而庆幸。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虚无的时代。前些日子,微博上出现了迷笛的主题曲,我没有听过,但是记住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歌词:切记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我想着,这是属于我们这个虚无时代的靡靡之音。就像康赫在书中写到的,饮酒、上床,饮酒、上床,有的人在出轨,有的人在窥私。第三章里阿同在大理向姑娘讲述的本子很有趣,一个故事五块钱。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了,有故事就好,虚无的生活不需要思考。一个故事五块钱,所以又是有钱就好,除了寻欢作乐我们不需要一切。
狂欢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曲。
麦弓是主人公,代表了一群人。冷血,迷失,才华,贫穷。就像我们的文青们。麦弓是主人公,还代表着另外一群人。勇敢,努力。我们的文青们悄然散去。
麦弓是浙江人,梅城,与绍兴不远,鲁迅的半个同乡。第一章里,麦弓是这么评价他的半个同乡的:“我们”没有出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拯救奴才,鲁迅那里只有“你们中国人”,一个绝望的攻击者的形象。
麦弓也一直这么做了。他写了纣王:只要活着,我就不能平静。写了堂吉诃德,甚至还有一个庞吉诃德。麦弓也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反抗周礼,孔子,老子,“能摸能玩的都带玉,玉指、玉足、玉茎、玉体,玉是中国的抚摸和狎玩文化的终极符号”。
后来,当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开始去单曲循环一首歌,腰乐队的《晚春》,里面不断重复着“奋勇啊然后休息啊,完成你伟大的人生”。文字读起来果然就顺畅了太多。麦弓直到最后一页,还在奋勇驱车前往新居:“看看最快速度骑到清河要多久”。而我们的奋勇是这样的:“吹了这瓶我跟你走”。
才华是一回事,努力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不妥,但是还不曾试图去反抗,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
《人类学》读后感(五):虚无与流动
过这本小说已经读完快三年了才写评论,书里很多细节都已经淡忘了。不过谈人类学应该是不需要细节的,这本书本身已经被康赫塞进了太多细节,多得随便翻一页都能谈,谈哪个又似乎都无法触及这座庞大迷宫的核心。
可能在一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大部分行为还和野兽无异的时候他们就诞生了自我意识,通过各种神秘学意识和原始的艺术创作进行自我的探索。这场自我意识的骗局是随着语言的出现而伴生的,语言为不同个体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而在交流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虚构的“我”作为端口。自我意识产生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又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层层叠叠的假象,并由此产生了各种虚假的期盼,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这种追寻必然导向阴郁的虚无主义,它本身就是没有结果可言的。
, 一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会有比较强烈的欲望和野心以及痛苦。麦弓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对麦弓那强烈的欲望至今仍印象深刻。他会全然不顾自己伴侣的撕裂与哀嚎,像个野蛮的畜生一样尽情的发泄自己的欲望。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也有和这野蛮强烈的欲望成正比的不切实际的价值期待以及与此相伴的阴郁和孤独,按严峻的话说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虚无主义者。尤其是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庞大冷漠,到处倾泻肆意横流的情感与立场被时代所引导的狂热合并为标准统一面目的现代都市,一个自我意识过强的人一定会是孤独阴郁甚至绝望的。
其实麦弓也并不是很重要,康赫的勃勃野心剥夺了他本应作为男主的待遇,他只是北京城这片虚无海洋的一个泵口,尽管有很多笔墨是写他或者围绕着他流动的。流动是这篇小说给人的一个抽象印象,康赫的语言流动的,从梅城到北京的人是流动的,北京城里的人也是流动的,他们的语言是流动的,他们精神,意识,与情绪也都是流动的。这流动不是平缓的,有各种暗涌和冲撞,这是这篇小说让人读起来很累的最大原因,这种流动的语言读起来就和晕车一样难受,与此相比,对方言的阅读障碍倒不算什么了。我是在17年的暑假读完这本书,闷热的没有空调的学校宿舍,电扇在头顶转着,我的脑子也在人类学里跟着各种暗涌旋涡转着,整整一个半月才结束了这场十分折磨人又让人完全无法放下的苦难旅程。
分隔线是打了一个不会取消,觉得挺好玩又多打几个。人类学已经读完三年了,书现在也不在手边,先随便写点,等后面找回书了重读一遍再写篇,这个就先当个草稿放这了。
《人类学》读后感(六):疯子和勇士永远不会衰老
写出《纣王》的人,必然流着和子姓商人同样不安定的血。
康赫的几本书里我最喜欢《人类学》,《人类学》中我疯狂地喜爱这篇《纣王》。两年过去,再读《纣王》,依然酷爱。这是承自热衷表演亲切的周人对完全不再拥有的勇气和疯狂的叶公好龙吗?还是不安的血在四处徘徊时感受到同类的亢奋嘶吼?
赢的秘密,必须藏在黑暗里。藏在黑暗里的星点闪光,划亮沉闷周礼遮盖几千年的千人一面。
“你不必担心衰老,我们都会在变得太老以前就死去。”“无趣的人总是能够长命百岁,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他们也一定要磨磨蹭蹭再活上几年。”“你闭嘴吧,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秘密,你想看到的并不是我想看到。”“可我怀疑那神秘的力量,那掌握了人间法则的盖天巨手,不过用世俗的秩序替换了欲望的真相,不过是人为自己设下的一个骗局。破坏,破坏,这迷人的强光,不可抵挡的诱惑。所有被决定了的,需要用破坏去再尝试一遍。”“谈论对于将来的忧虑是件耗费心力的事情,王叔若是愿意坐下来说话,也许能让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这些农夫的后人,唾面自干的卑贱种姓,我要给它们机会。”“我有恶人告诉我什么是恶,我有美人告诉我什么是美,这就足够了。”“姬昌的儿子伯邑考,尽管你和你父亲一样假模假式,却没有他的凶狠奸诈,正因如此,我对他多少还能容忍,对你的忠厚面孔却只有满心厌恶。”“人的勇气只能来自天生的胆魄而非后天的迂腐。”“我连此世的美名都不想要,你居然认为我会在意自己死后的美名。”“我不在乎你们想要在后人的记忆里装些什么东西。我只是给了你们一些我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从那时起,我的战士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旦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便无法相信自己的四肢和手中的刀剑。看,我的军队不仅被这群肮脏的鬣狗疯狂撕咬,好像还开始了自相残杀。”“尽管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他们却再也不会醒来,因为死亡很快就会接上他们的大梦。”“如果人间本身就是一个大牢笼,又何必将我从牢狱里放出来。”“箕子,为殷商的命运忧心忡忡的箕子,为了活命装疯卖傻的箕子,现在你的殷商已亡,那你的性命无忧,请举起手来挡住自己的脸,一直挡到别人无法辨认。”“可是哎,怎样的死亡才能配上我的骄傲?总不该是一片轻薄的丝绢,或是一截丑陋的绳索。啊,我的帝辛陛下,我的丈夫。”“这命运的线条,我曾经对它多么好奇,想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乏味,一切都是必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不接受任何人对它的挑战。此刻它看上去是多么清楚,因为我正站在它的末端,能够看到它的全部。是的,我看见了,但仍然只是可能,而不是那不可能。”“我挥霍了你们在人间的家产,现在就让我来挥霍我自己吧。”“出发吧,鬼侯,带好你自己的人马,不必操心过多。”《人类学》读后感(七):我的第二篇《人類學》評論
JZM時代的「人間喜劇」
——康赫的小說《人類學》
廖偉棠
過去十年,每當有港台小說家要我推薦他們所未知的大陸好小說,我必然會推薦康赫的《斯巴達》,但這部小說依舊是鮮為人知,就像它那俠隱江湖中的作者康赫。康赫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青年小說家,多年前我在《今天》雜誌讀到他的短篇小說時就這樣認爲,長篇《斯巴達》更證明了這一點。當年我是這樣向朋友推介的:「他的小說師承巴爾扎克和喬伊斯,對世界兼容並包,運筆看似自由即興,其實結構複雜窮極心思。他的小說人物嘻笑怒駡,出離這乖巧世界同時又擁有著塵俗的莫名活力,這也是他小說的魅力所在。」
沒想到十年後,他拿出了比《斯巴達》更為磅礴的作品,這部名為《人類學》的超長篇小說,無論它的寫作還是出版,在當下中國都近乎奇蹟。寫作難度來自康赫試圖書寫一部中國的《人間喜劇》,而且是餘威猶存的JZM時代的喜劇——也可以看作墓誌,涵蓋三教九流的七情六慾。而出版難度當然是指對尚未能蓋棺論定的一個時代的避諱,領導人的名字隨時會成為敏感詞的今天,這部小說有時佯狂有時任性有時尖刻地寫及彼時的半邊晴雨的政治空氣,如今即使是刪減本也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雷區。這部小說注定成為2015年最重要的中國小說。
「JZM使出了全力,要讓聲音傳得更遠。他不能像DXP那樣懶洋洋地喊。究竟是什麼口音?……我在她面前模仿J。」諸如這樣的片段在出版物中得以存留,除了編輯的大膽,也因為其本身的隱喻魅力讓人難以割捨,除了一個詩人,沒有人能從J的口音聯想到時代的難堪。《人類學》的故事背景是1999年初的北京,J全面接掌權力之後兩年,政治出現了一個表面上模糊的寬鬆期,所以那時也是所謂波希米亞北京的養成期,後崔健時代的搖滾、圓明園畫家村的化整為零、詩歌在BAJIU重創之後尷尬翻身……大量懷才不遇的外省奇葩連夜進城——《人類學》原本就打算叫《進城記》。
康赫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廣義的紹興人在北京,這契合了康赫和魯迅的隱秘關係,他是一個不掩飾自己的魯迅,「對於魯迅,無所適從是一個可以自由搏擊的開闊地帶」——主角麥弓如是論魯迅,也許是康赫的自我期許,他的小說人物常常陷入一種奇怪的無所適從,與卡夫卡人物的無所適從相比,他更接近魯迅的,因為康赫與他的人物一樣有一種偏執、近乎惡的生命力——這和那個骨子裡的魯迅一起屬於尼采的超人。
至於人類,他們看似以孤島實際上以蟻穴存在。小說內的人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與現實的人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除了主流社會的名人、惡棍,更多的九十年代圓明園藝術家和流竄的詩人們紛紛登場,甚至遠在美國的蘇珊.桑塔格,也在「老太太的疲勞症」一節表演了一把——康赫輕易地鑽進了她內心,把一位老公共知識份子作家的困頓與自負寫得唯妙唯肖,同時帶出的,卻是九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天真與自以為狡黠——小說中的其他影射,亦有此意。
在知識份子和詩人藝術家之外,有更多不同身份的人在演繹這那個時代的大起大落的命運。比如西北窮少年金志剛是一個最重要的串連式人物,以他最底層的宿命去交織其他人的流動:最終,大家都是向下流的階層,金志剛只不過比大家先到達煉獄。此外就是幾個不同階層的女性:布藍、孔令梅、湯娟等,承受著彼時的種種困頓,比男人們更熟悉悲劇的意義,卻也更從容,即使這從容在男人眼中是委屈是絕望,康赫卻熟知她們並無原罪,依然是手握蘋果的夏娃。但這是一個永恆的女性也不能引領我們上升的時代,更何況這些時刻抱緊你一起淪落的女性。
極端的富人和窮人之劃分也從那個時代開始。康赫能同時洞察兩者實屬難得,傳媒圈多年的浸淫讓他摸透了北京上層社會的幽暗,少年時代在南方農村的赤貧生活、青年時代在北京的浪蕩使他不忘底層的哀樂細節。民間知識份子麥弓的生存處境不是安貧樂道四字可以開解,而麥弓還鄉所帶出的近乎自虐的回憶也並非為了治癒,卻如此叫人動容:「她拿木棍打了我的腿。噢謝謝你謝你。我忘了我做了什麼,可是謝謝你謝謝你。尊嚴之光投在痙攣的肉體上。我們非凡的演出,血淚的喜悅。母嬤,我用冷漠和暴躁向你示愛,人世間最驕傲的崇拜。」
其實最打動我的是康赫剖析自我的激情,它掩蓋在剖析人類之下,其實一樣強烈,藉由一個夢魘一樣的意象凝聚:「光頭鐵匠一下把那隻小鳥吸成一具軟軟的空殼。」「這個打鐵匠,他現在還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也許以後會不一樣。同一棵樹的不同枝椏,梅林灣的梅城的上海的北京的,從各自的裂口分泌著各自的記憶,一陣苦澀一陣馨香,只是可能不會出現在過去。過去的馨香留在過去,在過去的裂口裏流著過去的汁液,不會再長出枝葉紛披的可能來,連接到現在,通向未來。它們沒有未來。」
吸進與分泌,激盪而完成,麥弓於是又成為江湖的隱喻,即便他和康赫都是這個江湖的畸零者、楚狂接輿。
《人类学》读后感(八):"从当代文学的谱系来看,它横空出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康赫的《人类学》:一个野心勃勃的作者,一幅斑驳陆离的都市全景图,一部兀立的奇书
作者:王宏图问世于2015年的康赫的《人类学》,可谓一部异常奇特、令人惊艳的作品。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是一部小众的作品,2018年获得“人民文学奖”后,影响有所扩大。从当代文学的谱系来看,它横空出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傲然兀立在文坛上。单就其体量而言,它庞大巨硕,足足有130余万字,堪称长河小说,单单这一点便足以使众多读者望而生畏。
康赫近影(摄影:廖伟棠)康赫近影(摄影:廖伟棠)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表现繁杂多变的都市生活?如果一味沿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难免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康赫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而以“人类学”作标题,便预示出作者非同寻常的抱负:他已不满足展示社会的某几个侧面,而是力图对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都市生活作一番全景式展示,上至官僚、商人、外交官、富有的艺术家,下至大学生、房东、妓女、打工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作者似乎摆出了人类学家的姿态,俯瞰着芸芸众生,将笔下上百个人物进行一番冷峻客观的剖析。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麦弓等外乡人构成了康赫描绘的人物群像的主体。纵观全书,没有清晰可辨的情节线索,林林总总的京漂们散落在千年古都北京的各个角落,它们各自逼仄、幽暗的生活空间构缀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被残损零散的空间所覆盖。这部巨型小说便是由成千上万不规则的空间组接而成,拼贴成一幅斑驳陆离的都市全景图。与此相适应,除了习见的叙述与描述,其他多种文体(幽默小故事、独白冥想、随笔、新闻纪实,尤其是戏剧性的对白)轮番登场。在康赫的笔下,吸引我们的主要不是视觉的图像,而是声音——那些从上百人的独特境遇以及它们在历史场域中碰撞而出的声音,斑驳纷繁,其中有喃喃自语,有流动不居的思绪、梦幻与狂想,有琐屑冗长的交谈、争辩,而对性与财富权力的贪欲构成了全书内在的主基调。滔滔不绝的众声喧哗让人头晕目眩,顿生倦意,又让人亢奋,急切地想窥视他们内心的秘密。
曾有人将《人类学》的写作风格概括为“巴尔扎克+乔伊斯”,它既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般宏阔壮伟的社会画面,又有乔伊斯对人内心深处幽秘意识显微镜式的展示。这一说法虽不精准,但也抓住了这部奇书的某些特征。它对读者也提出了很高、甚至是过高、过分苛刻的要求,要长时间地沉浸在它过于繁茂多汁的文字丛林中而不头晕目眩,不迷失方向,最后顺利回到明媚的阳光之下——很少人能经受住这一考验。在此,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评论《尤利西斯》的那番话让人颇生同感:“一切都是新鲜的,却又老是停留在最初的基调上。它的表象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枝繁叶茂啊,可同时它的实质又是多么的单调乏味啊!乔伊斯令我乏味得想哭;但这是刻毒而危险的乏味,是连最最平庸的东西都不能诱发的乏味……每一阵风,每一次日出与日落,每一声海的吼叫,每一个乐句都是不同的,然而它们又永远地重复着”,“它是最深意义上的‘立方主义’,因为它将现实的图景融入到了无限复杂的绘画之中,这一无限复杂的绘画的基调便是抽象客观性的忧郁”。
节选自《上下探赜 八方求索——近期中国文坛新变一瞥》,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4月22日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STASq6XViin-kyksn5T6Q
《人类学》读后感(九):失眠遗忘失败兜圈子和虚无之后
·我的软弱和面对故乡
辛会之后,麦弓回忆布蓝,头回说出“心抽痛,张开了嘴”这样的无力感受。我多么担心,怕作者给一天没有食物能量支撑下亢奋又虚弱的梅林湾英雄,一个突然转向世俗的结尾。
哦,没有。
我担心麦弓,因为担心我。
有一条无聊但安全的路时刻诱惑着我——捕获一个资优的丈夫,我能够轻易伪装成婚姻的准入者。
另一个诱惑——母亲面前乖顺的女儿。我不再给母亲打电话,听到她的声音,我马上萌生出满足她唯一愿望的冲动,为她愿望的不能实现,为不能够实现她愿望的我,伤心和绝望,大哭一场。
我软弱。
康赫在《人类学》描写了很多人的外貌,推断他们的性格。我没有从我的外貌上观察出什么。但躲闪的眼神,过多的语气词,没有必要的停顿,悄悄抓住上衣前襟、下摆、袖口的手……胆怯,我重复确认了这个我在理智上反感自己拥有的特点。
我没有勇气往家乡的人身上多看一眼。从贪污修路水泥工程款盖一个村委会章要请他开车去镇上找人拿章为此过年要摆宴席请客在乡间路上遇到我必然要停车问我要不要坐上去的村支书,到初一凌晨天还没亮前去拜年时的村里长辈。
前者通过凌驾于我的父亲母亲,拥有了我永远没法同他对视的权威;后者则是我承袭了她的敏感的母亲活在其中的舆论。
她说,你不结婚,我造了什么孽,让全村人这么看笑话。
我不觉得这话伤害了我。难过,是替生了一个使她不能完成人生使命的女儿因此永远陷入巨大痛苦的她。
这种超越理智的感情,通过理智持续地折磨我。我对她的歇斯底里感同身受,同时又为无法满足她的自己感到绝望。
年前,《人类学》我读到三百多页,大年三十的下午,争吵之后我躲进被窝哭了两个小时。
我没想哭,我控制不住我的哭。
当我平静下来,我看到平静下来的她饶有趣味地嘲笑其他大龄未婚的姑娘、被岳家嫌弃而离婚的村里小伙、结婚几年没能生孩子的我的同学——这个爱我和我爱的母亲。
年后读第五章,事前听说难读。
番薯胃、烂脚农民、疯婆子、冻死桥下的人、自尊又斗嘴迅速落败的母亲,一个性格强硬的人怎样面对这些回忆和感受?难读正好慢点,我仔细地读,想通过观察麦弓,学习处理故乡记忆和如今依然无力之处的方法。
记忆连同当时的感受永远储存,像琴弦一样碰一下就发声。我学到的方法是,当它响起,迅速把琴弦按住,与过去的连接还在,让震动停止。不能让这无力感伤的震动一直持续下去。
·了解婚姻的期待
在读这书之前,我对它还有一些理智之外的期待——一个在青年时期读哲学、如今大胆、缜密、有观察力的人,他的小说里会不会有一直困惑我的婚姻问题的新线索。
从上一辈的亲戚、亲戚的子女、同学、朋友,我观察了一部分人婚姻的样本,在里面没有找到乐观之处。“怎么过不是一辈子”,他们这样说,我推测他们的国外游和其他休憩方式也没能让他们很满意。
在读《人类学》之前,我先读了前传,对那时候和如今的我同龄的康赫的描写和表达的方式暗暗赞叹。里面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婚姻,我多少都了解。
我期待这个如今已经步入婚姻多年的人,在《人类学》这本新书里,有新的看法。我以往的经验,中年人对于自己的婚姻,必然三缄其口。
事实是,它的重点不是婚姻样本,假如出现婚姻(婚姻陷阱、猎物逃脱、婚内出轨、离婚再婚再离婚),它也只是人生样本的一部分。
我看过一些如今五十多岁的人充满温情地回忆1990s那段校园的好时光。假如一段回忆只有事件和感受又缺少细节的话,很容易被美化。
康赫还原了那个时代拥有不同合集的一个个群体,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代,我没有那个时代的常识,我觉得和当下十分相似。
“真是会写”,我读到麦弓在发表完关于个体、信仰、蠕虫的一番使人信服的高论后,再看“兆龙饭店的一只小蝶蛹”还是难以克制自己地被柳莳迟带入时,忍不住这样嘀咕。
我看到,在大部分时间一不留意,我是众蠕虫之一,轻易就被诱惑去做蠕虫。
可怕的处境,残酷的作者。
·无法掌握不想总结不能总结
不知道《今天》《今朝》人艺体,不知道来回变化的各种写作方式里的名称技巧,这让我有种隐秘的自卑和被排除在知情人之外的不安。一方面我本能地觉得知不知道这些不是很重要,一方面我又想假如我熟悉《楚辞》就能轻易知道他的那些引用里哪些变化了这样的变化又有什么含义。
另外,读着这么好的作品时,我依然有时痛哭失眠醉酒被骗觉得自己不具备任何可靠的能力。这让我判定自己不会是作者期待的读者,本能地想悄声沉默。
但我开始就决定参与作者的游戏,我也希望通过游戏规定的评论总结一下——不我不是总结这本书,这样一本大书我总结不了,我是在总结我自己。
破碎掉的自我的废墟或者叫垃圾堆,我希望像麦弓那样从别人从书籍从生活里任何地方学习和训练自己在废墟里穿行的技能,并且不会觉得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
《人类学》读后感(十):不知道生的时候,我喜欢看死 | 孤读客
y:史靖澜
康赫写了八年的小说《人类学》,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了两遍。在这期间,我应付考试,签证和手里堆积如山的论文材料,每天往返于教学楼和宿舍间两点一线的水泥马路,脚步匆匆,目的明确,如被蒙古骑兵追杀至大漠边际的西夏族群,除了挣扎着坚持,没有别的企图和希冀。所以这一千余页的砖头给我精神的刺扎感,被现实的忙碌消磨钝化,显得缓慢滞后,只剩下隐隐的痒了。
我的确可以从这自虐的阅读体验中获得病态的快感,因我自觉阅读从不是快慰的调剂,而是对舌尖对大脑的冲撞与挑战,阅读者是一座战争机器,要么发动起来厮杀与征服,要么拔去电源清空燃料,匍匐在大地上静静生锈长草。所以《人类学》堪称一片广袤的战场,地形复杂河流纵横,壕沟拒马铁网地雷星罗棋布,角色与读者带领各自的师团战斗冲锋,压制封锁,此消彼长,打出了上世纪末北京的混乱与躁动,中国的畸形和浮夸,众人的游离同荒芜。
若主人公麦弓当真是康赫自己,那环绕于麦弓四周时间空间的各色人物便是作者耐心收集的蝴蝶标本,他们以不同的面貌映射着所属种群的复杂繁荣,又冷冰冰地被缚在木框或铁制的容器中,拗出孤独的造型,这容器,恰好是北京。所以说那一群群外来人对北京的癫狂,不如说是北京疯狂地追逐着这些随风飞翔的蝶儿们,以丰富那本就拥挤不堪的库存,而这些蝶儿们的生死,则与这城市无关。
“我在长江以北思念的,在长江以南,身体率先开始拒绝。总是起一身红斑。低烧。咳嗽。鼻涕。痰。它是多么不安。无解。”
在十页关于南方梅城梦境似的回忆中,生理总与心理相关。思念总伴随病痛与不适,家乡潮湿而阴暗低沉,这与混沌的梦境的类似让身体的排斥现象有理有据,这个时代,乡愁开始瓦解,而归乡也褪却它原本的温暖色彩,成熟的权衡与出走对应,若不出走远方,家乡也会将你慢慢推出去,而回忆便不再清晰,甚至在日久年深之后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如雾笼罩。
如奥德赛般的麦弓在北京的汪洋上航行,却不是为了返乡,而是为了更远的漂泊。这位算得上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暂居在胡同里破旧污脏的小屋,与一群桀骜不驯的人类交际相处,互相换取生活的情报,他人的秘辛,天马行空的幻想与汁液淋漓的记忆,谈论最多的,除了彼此的女人和那女人麻烦的现实,便是各自对艺术,对写作近乎精神病发作的执着与自负。很难想象,正是这群看似稀奇古怪自以为是的人类,形成了首都最为廉价而疯狂的艺术家群体,烟,酒,长相一般的女人和几句充满性器的诗,就能唤醒他们的意识,获得他们的同情与关照,让你觉得,这以圆明园为圆心环绕的几座聚落,仿佛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天堂。
麦弓、金志刚、庞大海、陆震、郁利、子鱼一干等等,这群人的复杂跳跃的关系毫无规律地出现隐没,伴随的往往是狂欢似的酒场或饭局,孔子问道状的哲学思考,直白生硬的性爱氛围。以他们的眼,可以几不失真地复拓下现实世界的样貌,甚至是整个社会运行时留下的轨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无数有意思的象征的化用,那些不同名字的走马角色竟也能同真实的人物对应,光头的吃纸的诗人,珠光宝气的歌手,含笑挥手的领导,包括流连社交的活佛大师,每一个都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某某某,都带着看似不怀好意的讽刺和嘲弄。
而那些女性,那些如布蓝、汤娟、小孙、柳海萌、孔令梅的存在,则是使这男人的世界更具生态,出于一种平衡,也更似制造差异的考量。奈何她们的出现总有性,总有大段大段毫不节制的性爱场面,总有那些基调向下,略显颓丧的语气和态势,即便那一腔热血开上了服装店的汤娟,也在向母亲借钱投资店铺和自己的终身大事上胆怯迟疑,更多地是向男人寻求支援。所以我总习惯将康赫与匈牙利的纳道诗·彼得(Nadas Peter)进行比较,后者对于女性的态度在其千余页的小说《平行故事》(< Parallel Stories > 连篇幅和风格都与《人类学》极其相似)中可见一般,一种渴求获得主体意识和地位的挣扎贯穿始终,可仍未逃脱男人的掌控和牵连,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不同程度上的依赖,也屡屡释放出悲剧气味的暗示。康赫笔下的女性也大多如此,无法用沉沦来对其进行总结,但也像陷入流沙,越是挣扎,就越是深陷。
可能我在阅读时总关注到那些并不能算是重点的部分,但《人类学》却在这部分上惊艳到我。我极其佩服作者对日常生活近乎完美的复刻,他“一碗面条的肥皂剧”中一家三口日常争吵的状态细节,“开店宝典”中对开一家服装店需要点什么的头头是道,以及“地铁一号线”中对地铁众生相的描摹,简直是继承了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精髓,如此无孔不入,如此细致入微,如此真实,如此平淡,却又如此地充满了力量。然而许多人对于康赫文本之厚重的解释也多来自于此,若不是因为他这般费尽笔墨,《人类学》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厚度便可完成。然而康赫出彩的地方,不就是这些费尽笔墨看似与情节毫无关系的部分么?既然可以用这样大的题目为小说命名,其内容,又怎能不像百科全书一样,涉猎极广,书写极深呢?
我很喜欢在书的第五百八十页的一句回忆性的叙述:
“在我不知道生的时候,我喜欢看死。”
在我们还不了解生命为何的时候,年少时虐杀昆虫动物,看人经年累月慢慢死去,成为一种似是无知却也单纯得可怕的状态。因为不知生命为何,所以不去畏惧它的消逝。而面对《人类学》,面对众人席卷而来的故事和场景,我所能体会到的情绪是沉重,是悲剧性的。康赫笔下的北京,麦弓眼里的中国,人们行走生活其中多半负担累累,步履艰难,所以面孔是冷漠的,情绪是茫然的,而这,恰好是不知何为喜悦的存在,而不知何为喜悦,何为幸福的我们,更爱世上的悲剧。
这大抵也算《人类学》值得一看的缘由吧。
==========================
史靖澜:文学研究者,书评人;
“孤读客”是史靖澜在保罗的口袋的专栏,每周一篇;
lt;图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