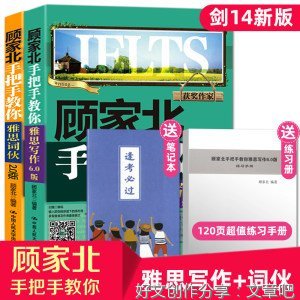搭 伙
搭 伙
老闫过来了。
他挑个货郎担,颤颤悠悠的样子,如同一只扇动翅膀的大灰鹅。老闫的货郎担里,并非是鸡毛换糖。而是他自个的铺盖卷儿(行李)和他营生糊口的买卖。
老闫是个卖野药的,盐河北乡人。
说老闫是个卖野药的,似乎有些贬低他了。用那个时候的话说,老闫应该算是个乡间郎中呢。
可盐河两岸,大人小孩子,都喊他老闫,无人喊他闫郎中。若是哪个人无意中喊出了闫郎中,听到的人不会认为是老闫,肯定会想到是另外的什么人。
老闫把他的“货郎担”,放在钱五娘家门前的空地上。
钱五娘家先前是开酱菜店的,门前有一块很平整的小场地。见天有小孩子在那里踢毽子、打拐腿子玩。老闫一来,小孩子们就被赶跑了,大人们要跟老闫说些腰酸腿疼的事呢。
头晕了,怎么办?
胳膊拐这儿怎么就抬不起来呢?
老闫一来,街坊四邻的毛病也来了。
老闫呢,你说头疼,他给你治头;你说脚疼,他就给你医脚。可遇到他医治不了的病症时,他就会告诉你:“你这毛病,快去‘天成’瞧瞧吧。”
天成,是县城那边的一家大药房。
可乡邻们一般的跌打扭伤、头疼脑热,都不愿往县城那边跑,只等着老闫过来瞧瞧就行了。
老闫最拿手的是劈疖子(脓疮)。他观察人们的脓疮时,如同瓜农们摸弄田地里的香瓜一样,看你那脓疱处只是红肿,尚未有脓头冒出来时,他会皱着眉头说:“还不熟,再等两天吧!”直到那脓疱冒出蜡黄色的小尖儿,他再红药水、紫药水地给你涂抹一番后,给你动刀子。
钱五娘守在家门口,看到老闫给人家劈疖子、挑脓疮,她自个也觉得某个地方不舒服了。于是,就摸着脖子问老闫,我这半拉脖怎么就不听使唤了?要么就说她腰椎的某个地方,酸胀得不行呢。
弄得老闫也不知该如何给她下药。
有一回,钱五娘还把她领口下面一处红疙瘩亮给老闫看。老闫看了看她那白颈下面的红点点,自个儿先乐了,说:“你那是蚊虫叮咬的,不要抓挠,过两天,自然就会好的。”
哪知,钱五娘夜里睡觉时,迷迷糊糊地乱抓一气儿,愣是把那地方给挠破了。
这一回,她再来找老闫看。
老闫却惊呼一声,说:“哟!你这不是发炎了吗?”随之,老闫便埋怨她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嘛,不要挠,不要挠。你怎么偏要挠呢!”
钱五娘说:“钻心窝地痒痒。”言下之意,不挠不行的。
“发炎了!”老闫气陡陡地说。
“那该怎么办呢?”钱五娘很是无助的样子问老闫。
老闫那会儿正忙着,他没有立马回答她。
回头,前来瞧病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老闫便招呼钱五娘:“来,你过来。”
老闫指着他跟前的小板凳,让钱五娘与他脸对脸地坐下来,且不紧不慢地拧开一个小瓶盖子,用棉团蘸出一团水嘟嘟的紫药水,让钱五娘把她领口下面的衣扣解一解。随之,轻轻地给她涂抹起来。
期间,老闫一边涂,还一边问:“疼吗?”
钱五娘不说疼,也不说不疼,钱五娘说:“还行。”
老闫就知道那地方沾上药水以后,可能会有些疼的,便说:“忍一忍,昂!忍一忍。”
钱五娘不吭声。
老闫就那么一圈一圈地往周边涂,涂着涂着,不知怎么就涂到钱五娘那鼓溜溜的奶子上了。
那时刻,钱五娘也没有恼。但她白了老闫一眼,似乎在说:“你个死老闫,没个正经的!”
老闫呢,他从钱五娘的眼神里,看出钱五娘的娇羞来,胆子随即就大了起来。于是,就在那个夜晚,他们可能就粘和到一起去了。
老闫是个光棍。
钱五娘虽说有钱五,可那钱五七八年前去山东贩酱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小村里人猜测,钱五在外头犯事了(犯罪了),或是死在外头了。
钱五娘守了他一年又一年。最终,她还是与那个卖野药的老闫,搭伙一起过了。
老闫把当年钱五开酱菜铺的小店,重新拾当了一番,新铺了红地砖,靠墙立了两面鸽子窝似的“药斗斗”,像模像样地开起了一家小药铺。
转过年,钱五娘给老闫生了个小丫头。应该说,那段时间,老闫与钱五娘的日子,过得还是蛮有滋味的。
老闫四处行医。
钱五娘跟着老闫学会了碾药、抓药。有小孩子来卖长虫皮(蛇皮)、鸡屎皮子(鸡内脏中消化食物的一层黄皮子),钱五娘也能一边奶着孩子,一边付钱给那些鬼头鬼脑的小孩子。
但,那些鬼精的小孩子不怎么喜欢钱五娘。钱五娘会挑毛病,总是说鸡屎皮子少了一块,或是说长虫皮是两节的,变着法儿克扣小孩子的钱。
老闫可不是那样的。老闫说五个鸡屎皮子可以换一个铜板儿。有小孩子拿来四个鸡屎皮子,他也会付给小孩子一个铜板儿。可那样的时候,若是被钱五娘在一旁抱着孩子看到了,她就会插嘴说:“怎么少了一个的?下回多带一个来。”弄得小孩子心里很是不高兴呢。
所以,小村里前来购药或卖药材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不怎么喜欢钱五娘,大家都愿意找老闫。
可这一天,前街卖凉粉的王婆子来药铺,偏偏不愿意见老闫,她招手把钱五娘叫到门外去,“咬”了半天耳朵后,等钱五娘再回来时,她脸上的表情就不对了。
当天晚上,钱五娘晚饭都没有吃,便合衣躺下了。
半夜里,老闫听钱五娘面朝里墙泣嘤嘤地哭,他这才知道,当初离家出走的钱五回来了。
钱五此番是瘸着一条腿回来的。
他那条腿是怎么瘸的?钱五不说。
小村里人只晓得钱五回来后,得知他的女人已经与别人搭伙过了,他没有去打扰人家,选在南场院一处小茅屋临时住下来。
隔一天傍黑,钱五娘掂记钱五一个人住在那茅屋里冷,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床花棉被(她与钱五结婚时盖过的),拧着一双小脚,给钱五送去时,见钱五窝在地上睡过的几块铺板还在,但钱五随身系带的东西已经拾当一空。
那一刻,钱五娘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她知道,钱五此番一去,今生不会再回来了。
返回的途中,钱五娘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心里想,也罢!那就回去与老闫好好地过吧。没承想,钱五娘回到家时,老闫与她那小闺女也不在了。
钱五娘慌忙去街口打听。
有人告诉她,说老闫的货郎担里,挑着那个小闺女,一路抹着泪水,向着盐河北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