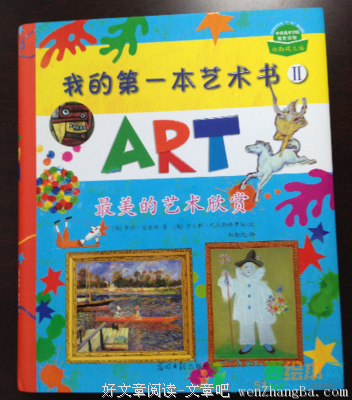《流动的盛宴》读后感10篇
《流动的盛宴》是一本由[美] 海明威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一):摘抄
加入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
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一个有教养的人,经常会对一个无赖不理不睬。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可能会结实一个粗鲁的人。
跟显贵的女人交朋友,对男人来说不会有多大的前途,尽管在交情变得更为亲密或者恶化以前,这种友谊能令人感到相当愉快。
你无法一遍遍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基本上不是一个处于静止状态的尺寸问题。这是一个能变成多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角度问题。
于是,他们不再是两个成人加上他们的孩子,现在是三个成人了。起初这样倒也挺刺激,而且也很有趣,就这样维持了一阵子。一切真正邪恶的事都是从一种天真状态中生发的。你就这样一天天地活下去,享受着你所拥有的而且毫不担心。你撒谎,又恨撒谎,这就把你毁了,而每一天都比过去的一天更危险,但是你一天天地活下去,恍如在一场战争之中。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二):海明威有话说,好基友司各特
海明威有话说 好基友司各特
——《流动的盛宴》伪书评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友谊其实就这么走到了尽头的,若是菲茨杰拉德读过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感谢上帝,无论海明威如何对他吐槽,并且将他的奇葩事迹如何浓墨重彩地大写特写,菲茨杰拉德对此却毫无回应也没有做出任何试图澄清的努力,因为死人不会说话哈哈哈。
1.Nice to meet you,你和你老婆发生婚前性行为了么?!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初次相遇是在巴黎丁戈饭店的酒吧间,那时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海明威当时坐在那里没想到菲茨杰拉德居然会到这里来,菲茨杰拉德走了进来并作了自我介绍,并向海明威发表了一番海明威作品以及如何了不起的长篇大论。这番恭维使海明威暗暗不快并在文中吐槽到“那张嘴在你熟识他以前总使你烦恼,等你熟识了就更使你烦恼了”,当然,海明威还吐槽他腿短,比正常的腿或许少两英寸。当菲茨杰拉德快讲不下去时,他开始了提问阶段,随后发生了此幕,直录译文如下:
“欧内斯特,”他说。“我叫你欧内斯特,你不介意吧?”
“问邓克吧,”我说。(邓克*查普林是当时著名棒球投手,和菲茨杰拉德一起看海明威的)
“别犯傻啦。这是认真的。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在你们结婚前在一起睡过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记得了。”
“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你怎么能不记得?”
“我不知道,”我说。“很奇怪,不是吗?”
“比奇怪更糟,”司各特说。“你一定能记得起来的。”
“很抱歉。真遗憾,是不是?”
“别像英国佬讲话吧,”他说。“放正经些,回忆一下吧。”
“你可以老老实实努力回忆一下嘛。”
这番话声调很高,我想。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讲的,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曾注意到他说这番话时在冒汗。
2.我都快要死了,你居然还能坐在那里读报纸
他们俩认识后不久,菲茨杰拉德邀请海明威一同乘火车去里昂把那辆丢在那里的雷诺牌小汽车领下然后一起开车回巴黎。回来路上因为汽车没有遮雨顶篷而不得不因避雨而在路边停车,期间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他们俩喝了几瓶白葡萄酒。后来菲茨杰拉德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来了。他告诉海明威他感到深深震动的事:最近有两个人死于肺部充血。然后海明威不得不解释肺部充血及其症状,甚至引述他从法国医学杂志上读到的论文给菲茨杰拉德听。随后菲茨杰拉德又问海明威他是否害怕死去,海明威说有时更怕些,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晚上时他们住进一家旅馆,于是发生了这幕,直录译文如下:
“你是个冷酷的人,是不是?”司各特问,我看了他一眼,明白我的处方错了,如果错不在我的诊断的话,还明白威士忌在跟我们作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司各特。”
“你居然能坐在那里读一张一文不值的法国报纸,而我快要死了在你看来却算不了一回事。”
“你要请我去请个医生来吗?”
“不。我可不要法国外省的卑劣的医生。”
“那你要什么?”
“我要量体温。然后把我的衣服烤干,我们乘上一趟回巴黎的快车,住进巴黎近郊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
“我们的衣服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干,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快车了,”我说。“干吗你不好好休息,在床上吃点晚饭呢?”
“我要量体温。”
在这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茶房才拿来了一支体温表。
“难道你只能弄到这样一支吗?”我问道。茶房进来时,司各特原先闭着眼睛,那神情看起来至少像茶花女那样濒临死亡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脸上的血色消失得这么快,我不知道血都跑到哪儿去了。
“全旅馆就只有这么一只,”茶房说着,把体温表递给我。那是一支量浴缸洗澡水的温度计,安在一块木板上,装有足够使温度计沉入浴水中的金属底座。我很快喝了一口兑过酸汁的威士忌,打开一会儿窗子看外面的雨。我转过身来时,司各特正盯着我看。
我像个专业医务工作者那样把温度计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你运气真好,这不是一支肛门表。”
“这一种该往哪儿搁?”
“搁在腋下,”我说,并把它夹在自己的腋下。
“别把上面指着的温度搞乱了,”司各特说。我把它又朝下猛甩了一下,便解开他睡衣上衣的纽扣,把这支表插在他的腋窝里,同时摸摸他的冷额角,然后又给他珍了脉。他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他的脉搏是七十二跳。我把温度计在他腋窝里放了四分钟。
“我以为人家是只放一分钟的,”司各特说。
“这是支大温度计,”我解释说,“你得乘上这温度计大小的平方。这是只摄氏表。”
最后我取出温度计,把它拿到台灯下。
“多少度?”
“三十七点六度。”
“正常的体温是多少?”
“这就是正常的体温嘛。”
“你肯定吗?”
“当然。”
“你自己量量看。我一定要搞明确。”
我把温度计的度数甩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温度计放在腋下夹住,一面注视手表。然后我看温度计。
“多少度?”
“完全一样。”我仔细察看后说。
“你感觉怎样?”
“好极了,”我说。我在回想三十七度六是否真的是正常。这没关系,因为这温度计始终稳定地停留在三十度上。
司各特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问他要不要我来再给他量一次。
“不要了,”他说。“我们可以高兴了,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一向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你身体好了,”我说。“可我认为你还是不要起床,吃一顿清淡些的晚餐,然后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动身。”我原打算给我们俩买两件雨衣,不过为此我就得向他借钱,可现在我不想为这件事开始争论。
司各特不想留在床上。他要起来,穿好衣服下楼去给珊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打电话,这样她可以知道他平安无事。
“她为什么会认为你身体欠佳。”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第一夜我没有跟她睡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跟她谈谈。你能明白这对我们俩意味着什么,是不?”
我能明白,但是我不明白他跟珊尔达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夜怎么能平安无事地睡在一起。
后来海明威还将此事改头换面地写成一个短篇《一天的等待》(1933)。
3.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我怀疑我的尺寸太小
“在珊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妻子)发生当时称之为第一次精神崩溃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碰巧同时都在巴黎。”司各特约海明威在雅各布路和教皇路拐角的米肖餐厅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司各特说有些很重要的事向海明威请教,他说此事的重要意义对他而言超过世界上任何事情,因此要求海明威必须绝对真实地回答。海明威称“我将尽力而为”,于是发生了此幕,直录译文如下:
最后在我们吃着樱桃小馅饼、喝着最后一瓶葡萄酒时,司各特说,“你知道,除了跟珊尔达以外,我从没跟任何女人睡过。”
“不,我不知道。”
“我以为曾告诉过你。”
“没有。你告诉过我很多事情,可就是没有讲过这个。”
“这正是我得向你请教的问题。”
“行。讲下去吧。”
“珊尔达说像我生来这样的人绝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说这就是使她心烦的根源。她说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话,我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
“上办公室谈吧。”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厕所,”我说。
我们回到餐室,在桌边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你没有问题。你没有一点儿毛病。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就显得缩短了。到卢浮宫去看看那些人体雕像,然后回家在镜子里瞧瞧自己的侧影吧。”
“那些雕像可能并不准确。”
“雕的相当好。大多数人会对此感到满足的。”
“可是为什么她会谈起这个呢?”
“为了使你不去搞别的女人。这是世界上使人不去搞女人的最古老的办法。司各特,你要我对你讲真话,我还能告诉一大堆,可这就是你需要的绝对的真话。你本该去找一位医生看看的。”
“我不想去。我只要你把真话告诉我。”
“那你现在相信我吗?”
“我不知道。”他说。
“走,上卢浮宫去,”我说。“沿这条街走去过河就是。”
我们过河去了卢浮宫,他注意察看那些雕像,可是依然对自己持怀疑态度。
“这基本上不是一个处于静止状态的尺寸问题,”我说。“这是一个能变成多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向他解释,谈到垫一只枕头和一些别的东西,也许知道了会对他有用。
“有一个小姑娘,”他说,“她一直对我很好。可是珊尔达说了那些话以后——”
“忘了珊尔达说过的话吧,”我对他说。“珊尔达疯了。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只要有信心,干那位姑娘要你干的事吧。珊尔达只是想把你毁了。”
“你对珊尔达一无所知。”
“好吧,”我说。“我们就到此为止。可你上这来吃午饭为的是问我一个问题,而我已经尽可能给你诚实的答复了。”
但他仍旧将信将疑。
4.不因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虽然在海明威眼中菲茨杰拉德像个孩子,会提出“无耻的问题”,做出“使人为难的事”,喜欢发表“长篇大论”,行为举止敏感神经质甚至有点滑稽可笑;但海明威对他的作品仍是极其称赞的,他在文中提到“我读完了这本书,明白不论司各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一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准能写出一部甚至更优秀的书来”。最后,我必须为到此为止还没有笑出声的读者写上一句教训话,使他们有所收获。虽然阅读在于乐趣,而不在于获得教训。但我还是写上一句吧:一个人品行优秀道德高尚但不见得就能写出好文章,但能写出好文章也不见得其人就品行优秀道德高尚,品行优劣道德高低与文章好坏到底是两码事。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三):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
其实,我想说,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呢。
可以说,本书是海明威对年轻时代他最美好时光的一段回忆,从他把自己最后与哈德利的离异归咎于那个可鄙的“引水鱼”把”有钱人“引到了他们的生活中,从而结束了他的这一席盛宴,足可见他对这一时期生活的留恋与怀念。
从圣米歇尔广场到塞纳河畔,从圆顶咖啡屋到丁香园咖啡馆,从巴黎冬天的阳光到期盼春天的到来,一个个朋友翩然而至。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清贫的生活中勤奋地创作着的海明威,一个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热爱的幸福的海明威。
我知道,许许多多人都向往着巴黎的浪漫,而我们不也处于这一席盛宴之中吗?相对于漫长的一生,在巴黎的这一段生活定格在海明威的记忆中,然而,他的盛宴仍然继续着、流动着,不仅仅在巴黎。一如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欣赏着各式的风景,经历着各种的事情,跟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同时又充当着他人人生的配角。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落幕时,这一席盛宴撤去了,而一席席新的盛宴又陆续的开始了,生命周而复始,自然原本如此的。无论是顾影自怜也好,功成名就也好,这场盛宴都是流动的,正如那流动的风景,被车轮抛在身后,留在心底的是美丽的回忆与满怀的感动。
我喜欢这部作品的名字——《流动的盛宴》,在心里轻读它的时候,有柔情、有感动、有伤感,更多的,是深情和敬畏。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四):读《流动的盛宴》
我读了汤永宽 译本、陈燕敏 译本及英文原著 ,还找了英文有声书 来听(在喜马拉雅 )。
但很可惜,在阅读这本书以前,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海明威 及其作品《老人与海》 ,却未了解过海明威生平,也未完整读过他的《老人与海》。
我只能用我笨拙的理解去记录这一次阅读。
笨拙的我只能把《流~》 当作一本经验性分享的书籍阅读(对于更深层次的升华我实在达不到),但是,它的描写,它的文字,优于大部分的此类书籍。它用词准确、描写细致,读起来常常让我忘掉了情节而沉浸在它优美的句子之下。所以,我总是回答不上的一个问题是:这小节说什么?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太难吧,所以,当我找到英文有声书时,听完一遍以后,又听了一遍,真的好舒服呢,享受,但是,我还是好难回答自己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所以,请原谅我的笨拙,我只能把书中描写的一切,当作是海明威本人的个人成长经验分享来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明威,是美国驻巴黎的记者,但是在书中,貌似并未描述他全职工作的事情,他书中所提到的工作是writting stories 。他特别喜欢在咖啡馆写作,身边也不乏指导他写作的朋友,如斯泰因小姐;还有一位借工作之便常常把一些好书借给海明威的朋友。。。他,还喜欢赌马,所以,更让我觉得,呵呵,名人也都是普通人,他们也有很普通的人的嗜好。
但是,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成功说明他并不是太普通的普通人。确实呢,至少他的朋友圈不是普通的,而且,他很有耐性,对自己的作品也很负责。他写不出作品时,并不会太焦虑,而是有自己舒缓的方式,放松过后,他往往就能提起笔继续写。他在书中有提到《太阳照常升起》 写好后,他朋友埋怨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初稿,他的意思是:还没有检查过的、没有修改过的只是未完成的作品,并不算是初稿。我想,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才会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作家的。
此书中让我涨姿势的还有:关于完成一部作品后的感觉、关于“我”如何面对一愁莫展、关于“我”所去过的地方的一切景物描写、关于“我”的人际关系。嗯,人际关系挺复杂的,而且提到的基本上都是大咖。我觉得这是作者成长过程中很难能可贵的一段经历,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人只是陪作者走过了一段路,但是我想,在作者看来,他们的出现,在他的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嗯,的确,有些人只会陪我们走一段路,但是,他们的出现也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重重的一笔。
嗯,到最后,请原谅我的笨拙,竟然只能写出这样的读书总结。而我,我也发现的能力在哪里。一直,我自认为,连科学技术的书籍、专业技术资料都能看懂,世间上没有什么书我是看不懂、我会理解不来的。可是,此书,我就是理解不来,也是很难读下来。毕竟,我更欣赏简单的胜过于复杂的(科学就是把复杂的用简单的方式描述出来的),但是细细读下来,我发觉,此书最大的特点,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描述准确,我只要好好地读书中的句子,我就能把整个画面想象出来,还原在我的脑海里,很真实。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恐怕不能出现这个效果。所以最终,我觉得,这书应该是文学作品中的上上品,我花时间阅读也是值得的。(但是,我此后应该不会再看此类书籍,我的能力不适合阅读此类书,读它们简直是和我自己过不去。)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五):巴黎永远不会结束
既然已经人在巴黎,《流动的盛宴》似乎早已经拜读过才对。但事实是,虽然5月份买了kindle后就第一时间下了书,却一直是断断续续一星半点儿得读着,到昨天才完全看完。
记得上大学以前,我喜欢一口气读完一本书,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畅快感,最疯狂的一次是上初中的时候,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开始看家春秋,一晚上没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把三本都看完,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作息紊乱。很奇怪的是,高中三年,写不完的试卷、作业、练习册,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自习,一段完整的空白的时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似乎再也没有一口气无间断得看完一本书了。大概从那时候起,我的阅读习惯就被改变了,以至于上了大学后虽然重新有了时间,却再也无法真正得静下心来读书。读书的时间开始碎片化,时断时续,读了下篇忘了上篇。
但是这样的阅读方式对于《流动的盛宴》来说,似乎是更好的。海明威的巴黎是流动的。我的巴黎也是变化的。每一天我都在经历巴黎的不同的一面。偶尔的闲暇,在地铁上,在睡觉前,在火车上,会突然想起该接着往下读。那么在上次停下来,和重新开始之间,流走的时间里,充满了我对巴黎的新的理解。我的生活,和海明威的盛宴,时而重合,时而对照,有时候我们都一同走过圣日耳曼大道,路过永远那么热闹的花神咖啡馆却永远不会推门而入来一杯坑游客的咖啡,有时候又惋惜于我眼中的巴黎已迥异于海明威笔下所言,莎士比亚书店也变得日渐商业化与流于形式的文艺。
《流动的盛宴》是零碎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地鸡毛的。
quot;There is never any ending to Paris and the memory of each person who has lived in it differs from that of any other. We always returned to it no matter who we were or how it was changed or with what difficulties, or ease, it could be reached. Paris was always worth it and you received return for whatever you brought to it. But this is how Paris was in the early days when 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六):回忆也是一种饥饿
海明威认为,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地描写它,使它在文字中获得感人的活力。我想,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人热爱的一切事物。距离是必需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的。在年老之后,海明威再次想起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一段青春岁月,阅读、漫步、写作、交友、与妻子相亲相爱……那一代美国人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岁月,在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一书中,存有珍贵的记录和发人深省的分析。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充满着对欧洲的向往,而又是什么使得伟大的寻根之旅注定要沦为再一次的迷失?这是20年代“迷惘的一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的问题。随意翻看海明威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述,竟然无意中发现,自己也曾穿行在他走过的大街小巷上。海明威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读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我不知道巴黎这个地方是否会一直在我心中,但在这个地方的经历种种却会使我长久地感到一种由衷的感激。
以下摘自本书:
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仅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大街,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一家雅净的咖啡馆。
假如午后我另取一条路线到卢森堡公园的话,我可以穿过几个公园到卢森堡艺术馆去。那里有不少名画,如今大部分迁到卢浮宫和热德波姆陈列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欣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那个时候我没钱买书,只好从“莎士比亚之友”租借图书馆借阅。那是西尔维娅·比奇设在奥维翁路十二号的图书馆兼书店。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上,这可是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生起一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架上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了许多已故和在世的著名作家的相片。这些相片看上去都像是随手拍下的生活照,就连已故的作家也像仍然健在似的。西尔维亚的脸线条分明,表情十分活泼,褐色的两眼像小动物的眼珠似地骨碌碌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她那波浪式的棕发从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去,在浓密处齐耳根剪平,正好盖在她穿的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外衣的领线上。她的两条腿也很好看。她对人和蔼可亲,性格十分开朗,爱关心别人的事,也爱开玩笑闲聊天。我认识的人中要算她对我最好了。
塞纳河支流的对岸是圣路易岛,岛上街道狭窄,古老的大厦非常美观。你不从那边走也可以向左转,沿堤岸走过相当于圣路易岛长度的路程,再往下走,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和西岱岛了。
塞纳河上渔人垂钓,生趣盎然;漂亮的驳船上忙忙碌碌,放倒烟筒驶过桥下的拖船曳了一串小货船;石砌的岸上有高大的榆树、法国梧桐,有几处是白杨树——有了这一切,我在河边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
我们认为我们是高尚的人,而我们鄙视所不信任的人则很富有。就是不该信任他们。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在里面多穿几件棉毛衫来语含有什么奇怪,只有那些富人才会觉得可笑。我们粗茶淡饭,吃得很香,我们暖融融地在一起,睡得很舒服,我们深深地相爱。
我们在夜幕中向家里走去,穿过杜伊勒里宫时,停下来,透过卡鲁埃拱门眺望黑暗之中的花园。这宫中夜色的后面是协和广场的明灯,再往后就是一长溜渐渐升高、通向凯旋门的路灯。回头再看看黑黝黝的卢浮宫,我说:“你真觉得三座拱门是连成一线的吗?这两座,还有米兰的赛穆瓦纳拱门?”
我们沿教皇路来到雅各路拐角,走走停停,看看橱窗里的画和家具。我们站在米肖饭店外面看了看贴出来的菜谱。
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我们又很年轻;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甚至连我们碰到的贫困、突然挣到的一笔钱,头上的月光,事情的正误,还有躺在你身边、在月光下熟睡的人的呼吸声,都不那么简单。
你在那里(卢森堡公园)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艺术馆去,而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所有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作画的;但我又想,也许它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人在失眠或者饥饿的时候常常产生这一类的想法,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发人深省。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别的方面感到饥饿吧。
出了卢森堡艺术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绪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馆,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像喷泉,鸽子在人行道上踱步,有几只停在主教们的塑像上。那里有座教堂,广场北边有家专卖宗教用品和法衣的商店。
从这个广场向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食品点而到达西尔维娅·比奇的图书馆的,像又绕过灰砖白石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在向右转完就到了。
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香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丁香园咖啡馆是最近的一家高等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坐在里面暖融融的,春秋两季却是在外面更舒服:把桌子放在内伊元帅塑像一边的树荫下,还可以坐在林荫大道旁宽大的遮篷下的固定方桌旁边。……丁香园曾经是许多诗人常常聚会的一家咖啡馆。……有这些人在,这个咖啡馆变成了很舒服的地方,因为它们互相之间很爱攀谈,也爱喝酒、喝茶、喝咖啡,爱看摆在报架上的报纸杂志。没有人故意显示自己。
我找到西尔维娅·比奇的图书馆以后读完了好多书,其中有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已出版的果戈理作品的英译本、康斯坦斯·加奈特译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以前在多伦多时就听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一位很不错的短篇小说作家,甚至可以说她是短篇小说的巨擎。然而,拿她的作品与契诃夫的比较,就觉得一个是事事讲究的女子精心编造的故事,另一个则是知识渊博、表达能力很强的医生写下的朴素明快的小说。曼斯菲尔德的作品有点像淡啤酒,喝这酒还不如干脆喝水。契诃夫的小说却截然不同,只有脉络清楚这一点清澈如水,他有几个短篇读起来像新闻特写,但还有一些是相当精彩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许多可信而不能信的东西,但其中有些情节真实到你读了不得不信的地步:他写出了人的脆弱和疯狂、圣洁和邪恶、赌博的愚蠢,正如屠格涅夫描写了风景和道路、托尔斯泰再现了军队的调动、战斗的地形、军官的形象和厮杀的场面一样。斯蒂芬·克莱恩写过描写美国内战的小说,但跟托尔斯泰的作品一比,他的小说就像一个病孩脑子里出现的色彩缤纷的梦幻,看得出他从未见过战争场面,只读过战役的描述、看见过布莱迪的照片。这些我在我祖父家也见过。在我读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之前,只有托尔斯泰的小说使我接触到了战争的真实场面;不过司汤达的这部小说通篇枯燥,对滑铁卢战役的描述是唯一精彩的章节。在巴黎这个在穷也能工作能过得好还能有时间读书的地方,走进这样一个文学上的新天地真像得到了一座金库一样。、
巴黎的生活永远写不完,在巴黎住过的人的回忆也各不相同。不论我们怎么变,巴黎怎么变,也不论去巴黎有多容易、有多困难,我们出游之后总要返回巴黎。巴黎总是值得眷恋的,不管你带去什么都能得到酬报。不过,这里写的是早年我们还很贫穷但很快乐时巴黎的情况。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七):人来人往--《流动的盛宴》
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过世后,编辑在他的遗作中整理出来的短篇集。这本书的大舞台在巴黎,海明威记录了他旅居巴黎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了北漂的影子。和妻子来到巴黎写作,租了锯木场上的小房子,生活拮据但是平淡幸福。在咖啡馆写作,在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借书看,偶尔去下作家沙龙。不知道为什么巴黎给人们留下了适合写作的印象。人来人往,巴黎的街道一次次的在作家笔下出现。海明威也在这里遇到了很多作家同伴,他们也是来了又走。或者并没有离开巴黎,只是离开了海明威的生活。在书中开头,海明威说,如果你有幸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那里他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是在离开巴黎很多年后写的这些文章。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那可以说他在多年后写下了一篇篇的美食评论。主菜是写作,甜点是赛马,饭后甜点是瑞士滑雪,葡萄酒是和作家同僚们的交往。
海明威在结束兵役后来到巴黎,同时期有很多和他相似的人来巴黎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和成名的画家,作家。巴黎自由的氛围就像灰暗世界的一点亮光,吸引着无数人。他们的生活仿佛被战争画上了休止符,战争结束后一切都是陌生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年轻人很难很快重新找到自身的定位,因此被称为迷失的一代。海明威让我看到了除了旅游景点以外的巴黎。那时候的巴黎还很年轻,像个少年人一样怀揣着梦想。城中的每一个人都做着自己的梦。在街头不起眼的咖啡店可能就是跨世巨作的发源地,一个落魄的街角可能会出现在大师的画笔下。一代代人,来了又走。如今的巴黎已经是不再青涩的少妇,成熟且妩媚。流动的不是巴黎,而是巴黎的人。
海明威说,即使是虚假的春天,也会让所有烦恼烟消云散。我正是在万物抽芽的春季读这本书的。看到漫山遍野的槐花低垂我才确定我的两只脚都踏出了阴沉寒冷的冬季。巴黎的冬季比西安的还要更漫长一些。可以想象那时的人们在冬天,除了进山滑雪外没什么适宜的户外活动了。如果我身处那时的巴黎,会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也会每天去咖啡馆奋笔疾书或者漫步在卢森堡公园寻找灵感吗,又或者有一个在固定时间去的小酒馆,那里有一个和我熟总是给我优惠的服务员,我也会去莎士比亚图书馆找绝版书看或者为了得到参加沙龙聚会的机会兴奋不已。在我去巴黎之前,光是听见这个名字就让我浮想联翩。等我真正去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和我的想象不符。比我想的更平凡但是又和别处不一样。在《流动的盛宴》中我看到了二十一世纪巴黎的影子。我还特意搜索了下名字在书中有提到的地址,现今大多都还存在。看来巴黎是提供盛宴的舞台,舞台上的人走来走去,但是巴黎,还是那个巴黎。
在我看来,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被称为流动的盛宴。每一座城市都给我展现出了世界不同的一面。我的回忆留在那个城市里,每当回忆到那个时刻的我,总有相对应的一座城市背景出现在我的脑海。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对年轻的我们来说那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要我说,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简单,都值得用心品味。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八):后悔读,les trucs fugiles
这是一本印刷、装帧非常棒的精装书。可惜的是,美椟之内装了一块鹅卵石。
每个人都有两面,海明威成功塑造了许多感情克制、少言寡语的英雄,最后,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做个彻头彻尾的长舌男,把文艺圈所有的鸡毛蒜皮、龃龉龌龊都写个遍。
这就象,一个拍文艺电影的导演,最后一部作品是记录片。
艺术是有营养又好吃的鸡蛋,生蛋的母鸡向来什么鸟都有。这在一些老文青的回忆录里可以一睹端倪。说到底他们都在一个圈、一个窝里。
我宁愿相信,这是海明威自娱自乐、从未打算出版的私人回忆录,名人一死,出版之事就由不得他了。
这本书是对海明威最后一枪的羞辱。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九):谁能告诉我任何一部英文版里 stein 小姐说的lost generation 那段话具体在第几页?
quot;It was when we had come back from Canada and were living in the rue Notre-Damedes-Champs and Miss Stein and I were still good friends that Miss Stein made the remark about the lost generation. She had some ignition trouble with the old Model T Ford she then drove and the young man who worked in the garage and had served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had not been adept, or perhaps had not broken the priority of other vehicles, in repairing Miss Stein's Ford. Anyway he had not been serieux and had been corrected severely by the patron of the garage after Miss Stein's protest. The patron had said to him,
'You are all a generation perdue.'
'That's what you are. That's what you all are,' Miss Stein said. 'All of you young people who served in the war. You are a lost generation.'
'Really?' I said.
'You are,' she insisted. 'You have no respect for anything. You drink yourselves to death . . .'
'Was the young mechanic drunk?' I asked.
'Of course not.'
'Have you ever seen me drunk?'
'No. But your friends are drunk.'
'I've been drunk,' I said. 'But I don't come here drunk.'
'Of course not. I didn't say that.'
'The boy's patron was probably drunk by el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said.
'That's why he makes such lovely phrases.'
'Don't argue with me, Hemingway,' Miss Stein said. 'It does no good at all. You're all a lost generation, exactly as the garage keeper said.'"
外加出版信息 书名 出版年月 出版社
thanks a bunch!!!!!!!
《流动的盛宴》读后感(十):巴黎,没个完。
自从遇见巴黎,就如同海明威自己所说“巴黎永远没有个完”。
《流动的盛宴》正是海明威自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生活的文字见证。一个女人、不期而遇的好友、兑毕雷矿泉水的威士忌、冰镇干白和葡萄牙牡蛎、赛马滑雪郊游……见识过中国贫困的我,怎么都不觉得这段日子属于贫穷,但绝对的幸福。致使我看完这本书都还情愿相信,那些是他在二十多岁时为了点缀生活而留下的文字,而不是六十岁在古巴的回忆。
他对此这般解释:“或许离开巴黎,我可以写出巴黎,就像当我在巴黎,我可以写出密西根。在那时这样说其实言实过早了,当时我并不懂这个道理,因为我对巴黎的了解还不够。但最后事情的确是这样发展的。”随着海明威在巴黎那段生活的结束,那个巴黎跟往昔的巴黎再也不一样了,“尽管巴黎始终是巴黎,而你却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贫穷的作家总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找到书源,也就是永不因为缺钱而少看书。
能从莎士比亚图书馆借书看使海明威兴奋无比,他对妻子哈德莉说:“我们要吃一顿很好的晚餐,喝合作社买来的博讷酒,你从那窗口就能看到橱窗上写着的博讷酒的价钱。随后我们读读书,然后上床做爱。”
海明威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借回了第一批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西尔维亚看到这些书后开玩笑说:“如果你要把这些都读完,就不会很快回到这儿来。”而海明威却为自己没钱交押金而认真,一本正经地说:“我会回来付押金的,我在我的住处有钱。”不过,想想他此时饿着的肚子也就不觉得好笑了。
除了莎士比亚图书馆,海明威发现塞纳河边的码头也有书摊会卖刚出版的美国书,价钱很便宜,交谈后得知是附近饭店房客离去时留下的,旅馆中的茶房就把这些书低价卖给码头书摊,“他们对英语写的书缺乏信心,他们买下这些书几乎没有付什么钱,因此只要能得到一点薄利就马上脱手。”看到这句,不免偷偷一笑,来自爱好的经验之谈总是最具吸引力的,那种取巧的喜悦也就能够感同身受。
饥饿
“在巴黎,你如果吃得不够饱,就会感到饥肠辘辘,因为所有的面包房在橱窗里都摆着那样好的东西,而且人们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桌边吃喝,因此你既能看到又能闻到食物。”海明威用了一个篇章专门写饥饿,描述了怎样在从卢森堡公园走到左岸的莎士比亚图书馆的路上,避开那些诱发饥饿的面包房和糕饼点心店。
此时的海明威已经辞掉记者的工作,专职写作,在默默无闻的写作日子里,写作和生计的不合拍所带来的不快在我看来是挣扎的,而对他来说却是好的锻炼,“如果你饿着走进卢森堡博物馆,饿得发慌,那些名画就全都显得更加鲜明……”这也是他在回忆时才能说出饥饿是有益的话吧,即使真的是饥饿促进了海明威的创作,又有谁会在忍受饥饿时真心称赞它的好呢,忍受饥饿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记得文中他曾自嘲,因为在饥饿状态下创作,笔下的每个人物才看起来都有好胃口,食物才能描写的那么诱人。
咖啡馆
去巴黎旅游时,寻觅海明威笔下的咖啡馆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认识巴黎的方式。咖啡馆是海明威巴黎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许多场景都是在那几家他常光顾的咖啡馆发生的,背景音乐我也总不自觉地加上jazz.20年代的巴黎是属于爵士的。
海明威常在右边口袋里放一颗七叶树的坚果和一条兔子的小腿去咖啡馆写作,以期好运。那么大的个子带着条毛快磨没的兔子腿真挺可笑。丁香园是海明威的根据地,离家近而且可供写作,在这发生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一个新流派的诞生》,还有和画家帕散相遇的圆顶咖啡馆……他喝上口朗姆酒就开始写作了,谁知道哪些短篇是在哪家咖啡馆里写成的。
书中出现的人物才应该算是全书的精彩。斯泰因和同性恋伴侣的公寓,西尔维亚帮助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真诚和善的庞德,特别是海明威在写他与菲茨杰拉德一起的旅途时,菲茨杰拉德所表现出的絮叨和可怜,他竟还向海明威抱怨自己生殖器不够大,于是海明威带他去厕所检验,在菲的继续怀疑下,海又带他去卢浮宫察看那些雕像的大小,向他解释其实是角度问题。。。。看到此,直接拜倒给“那张介于英俊和漂亮之间”的脸,恨不得马上去补看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太多的料可以拿来谈及了,在我不舍的看完这本书后更是觉得如此,夸张是必须的,就像海明威在60岁时写这本回忆一样,也有虚构延伸的成分吧。年轻时的海明威还是很英俊的,发了福留了胡子晒黑了后就不再属于在巴黎的样貌了,至少我这么认为,样貌会随着环境和心境发生变化。
眼看所有有关巴黎的故事快要收尾时,他诱惑我说:
“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
咳咳!好吧,等我先把生计的事儿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