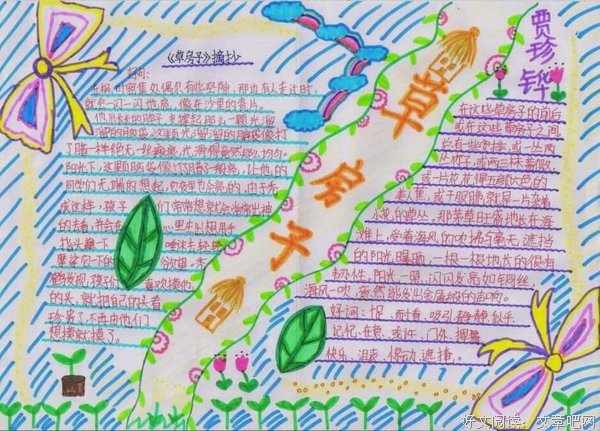食人魔花园读后感精选10篇
《食人魔花园》是一本由[法] 蕾拉·斯利玛尼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食人魔花园》读后感(一):食人魔花园里的厌食者
“你知道的,你和我们一样平庸,阿黛尔。有一天你接受了这一点,你会比现在幸福得多。”(P61)
“不满足的人会毁了身边的一切。”(P209)
“也许有一天,她能够满足于平庸的生活琐事,那他会很幸福,幸福得要命。”(P221)
在这永恒的重复之中,我们是如何忍受这样平庸的日常?平庸、缺乏诗意的日常。浮于表面的生活,明明是一潭死水,却还伪装着温情,看似美好却一触即碎。阿黛尔说,“情愿自己是食人魔花园里的一只布娃娃。”(P6)那么谁是那食人魔?什么是花园?丈夫、母亲、同事?家庭、工作、社会?她是破坏游戏规则和戳破表面平静的厌食者。
除了酒精,阿黛尔厌恶进食。她似乎也不是特别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呀。她很饿的时候,只不过要了一杯啤酒。每一个用餐场合,阿黛尔几乎都不怎么吃东西,“她喜欢一直都有饿的感觉……她培植着这份消瘦,将之当作生活的艺术来对待。”(P69)生活的艺术?如果抵制且战胜食欲可以成为某种生活的艺术,那么性欲呢?没有节制的食欲,会带来形体上的改变,而这于女性是不美的,读者当然不会想看一个油腻的胖女人,这会成为一个玩笑般的错误,喜剧式的嘲讽。但成瘾的性欲不同,会带来心理上的负罪,轻贱的肉体与沉重扭曲的灵魂,满足了自我于悲剧中的沉溺,从而实现“存在”。这样的“罪”是一种叛逆的美,堕落的深渊总是莫名别有一种吸引力。那么当无主的肉体为性欲所主宰,便足以支撑起生命之轻、日常之虚空了吗?
“为什么有人可以不惜付出正常生活的代价来换取一片虚空?”(P225)
因为这种“正常生活”未必是阿黛尔理解的“正常”。
这是她注定的悲剧。
对于阿黛尔来说,正是这种“正常生活”导致了她的“异常”。花园里的食人魔并不能允许阿黛尔这样的异己。与其说阿黛尔是一个不自由的灵魂,不如说她是一个不自主的灵魂。
“她曾在别人的欲望中活过一千遍。”(P128)她自己呢?谁又活在她的生活里?阿黛尔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她其实并不知道。但她认为自己已经看透了、厌倦了这日常。当她以自虐般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惩罚日常获得快感与存在感的时候,她又对生活做了什么呢?她和自己的上司、同事、好朋友的男朋友、丈夫的朋友,乃至任何人发生关系;她赤裸着躺在父亲的遗体旁边……当理查出车祸的时候,她想到得是:“(没有他)她不得不直面生活,真正的生活,可怕的、具体的生活。”或许阿黛尔与理查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两个因为过分抑制而终于周转不灵的个体,都是生活的逃避者。却又如此的渴望着被爱。阿黛尔与理查彼此都有着双重生活。他们都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她从未真正逃离世界,他从未真正宽恕。他们无法沟通,无法对等。阿黛尔以放纵肉欲来弥补精神的空虚,不过是一种看似自由实则伪自由的状态。理查否定性,剥夺她的这种“自由”,使她彻底不自由,以惩罚其不忠。因为阿黛尔撕破了他苦心经营的“美好的生活”,他所渴望拥有的“真的生活”。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理查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控制欲,而这种生活理所当然包括了阿黛尔。阿黛尔是他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但唯独不是阿黛尔本身。他一厢情愿规划的美好生活只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可阿黛尔不但要抢走他的戏份,还要重写剧本。
阿黛尔从一开始便动机不纯,她视理查为自己最后的退路。早熟的阿黛尔深受父亲的影响,向往着万众瞩目、众星捧月般的“伟大生活”梦,但这种“伟大生活”本身也是浮于表面,“毒性”太强,“副作用”太大。她和父亲一样无法实现明星梦,而性欲肤浅的快感可以带来更迅速廉价的满足。她只是因为性而被需要。因性而存在,阿黛尔对自己是如此低微。结婚,并不是出于爱情,因为理查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她需要一个丈夫。怀孕,因为“她相信孩子会对她有好处”。(P32)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她起初为了向生活索取归属感与存在感,为自己的人设寻求掩护的保护色。然而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自己和别人其实没有不一样,丈夫和孩子一起成为了重负。发现却不甘于承认自己的平庸与胆怯,无力改变,连同窒息的日常,使原本轻盈飘摇如氢气球的她被系上了一块砝码,她从云端跌落,掉进了食人魔花园。
服毒自尽的包法利夫人,跳下站台的安娜·卡列尼那,出走的娜拉,如果要给阿黛尔增添一个结局,我希望她厌食而死。她与理查都不足够勇敢。当酒精与性欲的麻痹与癔症退去,她也许会回来,他则继续冷暴力。还有吕西安,还有,她没有办法离开,他没有办法赶走她。他们将维持着一种诡异的和谐、双重生活,互不放过,相互折磨。危险在于,阿黛尔的性欲过于饱和,失控成为了“瘾”。厌食的人多半也是厌世的,阿黛尔的性瘾多半与她的抑郁焦虑有关,奈何性并不是灵药。扮演一个伪善的被妻子背叛的丈夫,沉浸在拯救失足妇女的角色中,企图把一切拉回正轨,恢复生活原本的秩序,这是理查的“瘾”。诚然,阿黛尔的心声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她大胆地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但这并不是被平庸的日常所禁锢与爱无能的不自由的灵魂们发起的挑战,而是躲避式的消极反叛,以及对公然反抗所可能带来的悲剧性结果的预判与畏惧,让对日常的抵抗失去了方向与力量。自我的存在感并不能通过依附于他者而得到充实的满足,当你轻易把生命交付出去,就注定会很容易被此击碎整个人生。只是可以感知到存在,却找不到意义或价值。丧失了主动去爱人的能力的现代人,又是如此渴望着被爱,而爱是不对等的,深谙世故的人们相信施爱者总是比被爱者先付出,所以孤独、错位的灵魂之间总是充满了无法沟通、无法和解的迷之悲剧。因为看得太清楚,所以想得更迷茫。肉体只是一个容器,要用它盛起生命的轻与重,实在是一个难题。
书里竟没有一个女人们所谓的“好男人”,讽刺而悲哀。失去灵魂约束的肉体,欲望一点即燃,婚恋关系脆弱不堪,乏味无趣的性,崩坏的道德。想来,阿黛尔的选择是“正确”的。毕竟,最能符合时下年轻女性们婚恋要求的,真的只能是那个禁欲的理查了。可有时,过于理性难道不也是一种非理性?
《食人魔花园》读后感(二):关于“瘾”这回事儿
关于“瘾”这回事儿——译后记
作者:袁筱一
2011年的5月15日,对于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SK)来说也许是噩梦般的一天。他被控在纽约索芙特酒店性侵女服务员。随后,这位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号人物,下一届法国总统的热门候选人不仅眼见得自己的支持率从46%暴跌到17%,甚至连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和他的支持率一般急剧下跌。一时间,他的人尚在美国不得脱身,法国媒体上已经铺天盖地的满是这一事件。
然而大众传媒的时代里,公众热情的变化之快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一有可能改变了法国乃至欧洲——甚至说世界也并不过分——局势走向的事件,包括事件中的男主人公也的确和其他事件一般,不过维持了一两个月的热度。如今,因为卡恩的存在,原本可能没有机会的奥朗德已经结束他的任期,法国在今年已然又迎来了新一届的总统,虽然与卡恩事件的性质迥然不同,也算是自带“花边”,为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映衬下显得略有些平淡无奇的法国政坛赢了一点人气。
的确,已经不再有人关注当年的真相究竟如何。卡恩很快辞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更是与法国总统大选擦肩而过,以终结政治前途为代价与指控人达成“和解”。即便当事人都还在世,有还原“事实”的可能,真相却早已碎裂,溢出公众的视野之外。
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正是要到这样的时刻,蕾拉·斯利玛尼才饶有兴趣地捡起了“DSK事件”中的一片真相,等着它在自己的掌心里不断发酵,生长出自己的枝蔓,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真相”(绝不是事实)。事件本身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其实这早已不再重要——,但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情境之一得到呈现,这是写作者赋予自己的任务。
《食人魔花园》是蕾拉·斯利玛尼的处女作,也为她后来凭借《温柔之歌》在2016年拿到龚古尔文学奖打下了基础。让人吃惊的是,虽然手握“DSK事件”的一片真相,蕾拉却灵巧地让她的《食人魔花园》摆脱了故事本身:没有政治阴谋,没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总统大选这些能够成为美剧桥段的因素,总之,她聪明地摒弃了一切有可能成为过于“好看”的因素,就只剩下了一个“瘾”字。“瘾”作为动机,“瘾”作为对象,“瘾”作为故事本身。甚至“DSK”的性别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平常生活里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阿黛尔。和“DSK”相反,阿黛尔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甚至也谈不上特别美,特别耀眼,既不特别女性主义,更不是文化传统的牺牲品,她只是——特别。
她特别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对象是无所谓的,能够像亚当那样“既不聪明又不深刻”,而且懂得沉默的,固然是好的对象,但是,每一个在欲望无法控制的时候来到她眼前的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她欲望的对象。可能是酒吧里偶然遇到的男子,也可能是丈夫的同事。随便什么人,也意味着总是需要一点额外的什么东西才能沉醉到这种偶然的欲望中去:酒精,甚至是毒品。因为所有的欲望满足之后,却都是一样的无聊。
是的,她有丈夫,有看起来正常,甚至可以称得上幸福的生活。丈夫是外科医生,在巴黎的十八区租了一套很漂亮的大房子。阿黛尔也通过人情关系进了一家报社工作,挣钱不多,她之所以工作,也只是为了有出门去与男人偶遇的借口。如果我们从来不曾受控于“瘾”,哪怕是烟瘾,酒瘾,或者更小的一点点迷恋,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不惜付出正常生活的代价来换取一片虚空。而且,哪怕是像“DSK”那样,具有超乎寻常的智力。即便平凡如阿黛尔,她不也是有着超乎寻常的透彻吗?何至于就为了一时的沉沦将苦心经营的生活拱手送出呢?
可这就是“瘾”啊。明知生活是不可逃离的,却仍然寄希望于不需要任何负担的迷醉来营造哪怕是片刻的幻觉。在某种以意义上,阿黛尔难道不是无处不在吗?又何止DSK?如果政治是虚无,爱情是虚无,权力是虚无,甚至理想是虚无,信仰是虚无,变化多端,不可依靠,难道不是那些不需要用智慧去谋求的东西才是最美妙的吗?错误地认为,在那一刻不需要付出——小到烟、酒所带来的“口唇区的快感”,大到性和毒品——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沉醉于这份“不能承受之轻”而永远不用醒来。
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这样定义文艺青年钟爱的杜拉斯,她的传主:“杜拉斯曾经有过肉欲的满足。情人,她有过很多。一夜风流,生活中的伴侣,笨拙但是美妙的男人,心爱的人。但是她这一生当中唯一忠实不变的是酒精。她想让自己纵欲,所有意义上的纵欲,想让自己气喘吁吁,她顽固地追索着,而酒精是她最喜欢的达到欢娱的道路”。
杜拉斯几乎死于酒精,就好像阿黛尔差点死于她在幻觉中追求的性的极致。这仿佛是对人类“向死”的最好的注解。然后生活就跳出来对一时的沉迷进行惩罚:因为倘若生不容易,死更不容易。没有人能够在极致的欢娱中死去。在极致的欢娱与死亡之间,是漫长的痛苦。哪怕痛苦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它也会像一个世纪一般漫长。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是理性是反理性的救赎,还是反过来,反理性是理性的救赎。如果说,《包法利夫人》肯定的是前面一个命题,《食人魔花园》却放佛在陈述后面一个。阿黛尔的丈夫理查·罗宾逊也是一个医生,与包法利不同的是,他精于规划,生活井井有条,唯一失败的只是被阿黛尔蒙蔽了双眼。在发现事实的那一瞬,他愤怒,甚至想到过要将阿黛尔逐出他的生活,但是当阿黛尔彻底地退出他的生活时,有过“十五年的实践”,“十分了解人类的身体”,“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害怕”的罗宾逊医生竟然要从无理性的等待里寻求希望:
他会去找她,不管她藏在哪里。他都要把她领回来。他再也不会让她逃离他的视野。他们会有另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儿,继承了母亲的眼神,父亲强劲的心脏。一个占据她一切的女孩儿,她发疯般爱着的女孩儿。也许有一天,她能够满足于平庸的生活琐事,那他会很幸福,幸福得要命,她会重新装饰客厅,她花好多好多时间为小女儿的房间选择新的墙纸。她说很多很多的话,她会心血来潮。
也许没有比《食人魔花园》更恶毒的“剧情反转”:能够给出“瘾”以科学解释的理查是不懂得爱,甚至不能够爱的,也不懂得欢娱。他本来能够等待阿黛尔的“瘾”发作,从而给出一个科学的医治方案,就像当年他救治流浪汉一样。然而阿黛尔没有给他“科学”解决“瘾”的机会,却以消失的方式给了他成“瘾”的可能:如果“瘾”不是欲望与虚空之间的无穷错过,又还能是什么呢?
如果爱不是欲望与虚空之间的无穷错过,又还能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多少勇气,又需要用逻辑绕出多少个弯子,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蕾拉的轻盈,在于避开了逻辑的这许多弯子,用另一个“瘾”的开始去填补一个“瘾”的结束所留下的空白。由是要去除一切能构成跌宕起伏的情节的因素:惟其纯粹,才是直抵要害的真相。我们也终于相信,在食人魔的“元”故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关于将灵魂和身体交付给“魔”的故事。
《食人魔花园》读后感(三):食人魔花园:在绽放的欲望中找回彼此
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包法利夫人爱玛不满足于平淡而庸常的婚姻生活,只局限在她想入非非的自我爱情幻境中,转而“慷慨的委身于那些卑劣的家伙”。一个有夫之妇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徘徊犹疑在福楼拜的笔下纤毫毕现。
法国女作家蕾拉的《食人魔花园》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出轨的妻子,而她们的丈夫都是庸碌平常的医生。但蕾拉笔下的女主人公阿黛尔显然对“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而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则是被包裹在自己“诗化”的爱情世界里。福楼拜虽然描写的是女性的心理,但他更侧重《包法利夫人》这个故事的社会内涵,并未如蕾拉一般将叙事的角度着重放在女性内心世界的层面。从性格角度来说,蕾拉笔下的阿黛尔和福楼拜笔下的爱玛本就是极具差异性的两种人格。爱玛虽然对丈夫不忠,但她在自我构筑的世界中可称得上是一种“高尚”,而阿黛尔的偷情,则已经沦入了成瘾的地步,这显然是一种病态。
我们无意探究对“性”如此上瘾的阿黛尔性格的源起、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影响。事实上,每种人格的成因或多或少都隐含着早年经历的积淀。在蕾拉的文本中,作者也并未否认这一点,蕾拉写就的这部女性的黑色童话充满了阴郁、暗淡、潮湿、粘腻的气味。我们通过阅读阿黛尔前前后后的偷情的经过,得知她在童年时期受到过一些暗黑的情色画面的影响,但这种视觉上的影响很难说是日后阿黛尔对“性”如此上瘾的成因,只能说它诱发或者加强了阿黛尔性格中的某种偏执面,让她不由自主的深陷于这种得到/得不到性欲的满足的尴尬处境。
蕾拉对于阿黛尔形象的处理,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主人公的文学特质,而不是将其描绘成一个十足的荡妇。尽管阿黛尔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人偷情,但作者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视女主人公,“食人魔花园”——多精妙多浪漫的譬喻,“性欲”就像吃人的魔鬼,一触即发,将人吞噬;而“花园”又是那么诗意那么曼妙、飘逸着芳香的园地,在这个长满食人魔的花园里,潜滋暗长着暗黑的力量,就像一片幽暗的沼泽,拖拽着你,让你无法自拔。
其实,主人公阿黛尔自己都不清楚对于丈夫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虽然她一再的背叛丈夫,但在丈夫生病时,她也悉心照料,而当丈夫得知阿黛尔的行径之后,并没有跟她离婚,而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对于丈夫,阿黛尔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对于自己的儿子,她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但是,如果为阿黛尔打上自私、病态、神经质等标签,又有违蕾拉创作的初衷。在婚姻里,往往看不清自己对于配偶的身份的重要性;而在一次次放纵的激情中,却能够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阿黛尔们生存处境的荒谬之处。
在小说的结尾,蕾拉并未给出一个最终的结局,我们推测,这场“身体游戏”终将使人疲乏,而陪伴阿黛尔年华老去的,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在激情的尾音退潮之后,阿黛尔仍将忆起曾经与丈夫的相守相依。欲望与责任在爱的天平上来回摇摆,这只能是爱,在无穷欲望与无限虚空中,我们一再错过彼此,却终将找回彼此。
《食人魔花园》读后感(四):性瘾者
作者蕾拉说过,她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诠释无论看起来多么完美的人,其实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每个人都一样,痛苦自饮,别人无法帮助你。 ——写在前面的话
阿黛尔有事业体面的丈夫,有可爱的孩子,有别人艳羡的体面生活,可她感觉不到幸福,反而更难以融入到这很多人羡慕的人生中去,为什么?因为,她的心被一种瘾紧紧缠绕,直至窒息,她是性瘾者。
性瘾,在看《食人魔花园》之前,自己机缘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大学一门选修课的课业论文,我们小组的课题就是以电影《羞耻》为引子走进生活中的性瘾者。为此搜集过很多资料,这种瘾症和抑郁症一样,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疾病,更是一种生理上的病症,性瘾者往往放纵自己的同时又伴随着强烈自我厌恶与焦虑。印象很深的是资料中一个重症性瘾受访者说过,自己哪怕在上班的时候,心中就会一阵一阵地涌起无法遏制的欲望,强烈到想要呕吐,只能立刻逃离公司解决后才会有多余的精力听清别人在说什么。不是为了寻乐,整个过程,都伴随着痛苦。女主角阿黛尔上班前要到男人那里上一次床才能止住颤抖的手,与这个现实中的受访者是多么相似。
作者用一段段性描写贯穿故事的始终,也间接拼凑出阿黛尔没有出口的生活。在瘾的作用相爱,她幻想渴望被随便一个、所有的陌生男人粗暴对待,她也是这么做的,而之后就独自消化痛苦与麻木。后期,作者很高明地在行文中分出一条丈夫理查的视角,在发现妻子的秘密之后,他渴望带妻子回归正常的生活,但他靠的不是爱,而是自顾自地代表了一种所有人都认为你在犯错误的道德高点。肯定的是,曾经阿黛尔和丈夫理查之间是有爱的存在,哪怕阿黛尔选择理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认为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她依然想要在他面前藏起写满秘密的翻盖手机与日记本,维系这段关系。可在性瘾症催生的欲望之下,这份爱太微薄,交流缺缺的夫妻关系不足以为她提供安心的栖息之所,反而加重了她的瘾。阿黛尔曾经从症状中获得过短暂的解脱,那就是在她怀孕的时候,生命在自己身体内孕育,从没有另外一个人与自己如此紧密连接,这让她安心,可是当孩子出生,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另外一个小理查,阿黛尔又一次走入堕落。在这种瘾症面前,任何表面的解脱都是短暂的。
丈夫孩子如此、父母如此、朋友如此,那些自己的裙下之臣更不值一提,所有人从根本上就认为“我”是错的,是淫荡的,只会让“我”改正,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我无法回头!没有人真正走入到阿黛尔的内心,当然,也有她的原因,她的“不正常”让她与正常生活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所以,她一边在逃离正常的轨道,同时她又渴望爱与依靠,最终在矛盾中迷失,继而进入恶性循环,因为没有足够的爱,所以只能靠着继续放纵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见过她的人会说阿黛尔这么优雅漂亮的女人,心中一定有芬芳的花园吧,是的,阿黛尔心中有花园,只是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个花园中住的其实是食人魔。最后的结局,没有拯救,阿黛尔彻彻底底地逃离了,真爱都很难战胜的瘾症,怎么会靠着岌岌可危的婚姻拯救呢?
生活在继续,沉沦在继续,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好真实细腻的描写,细腻到可怕。
《食人魔花园》读后感(五):生活的“瘾”,心底的“湖”
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知道蕾拉的时候,我是在巴塞罗那的民宿里,躺在床上刷到了一条关于蕾拉——这位被马克龙新任命的全球法语推广大使的采访视频。视频里的她有着精致小巧的五官,眉宇间透着自信的优雅,说话时一直带着亲切的微笑。当时就被她深深迷住了。
很巧的是今年3月,蕾拉带着她的作品来南京做了读者分享会了。还记得自己当时紧张得心提到嗓子眼的心情,发现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低头发短信的样子时,就涌出的很亲切又带着些感动的感情。她就像是在巴黎地铁里,你偶然一瞥,发现正在低头读书的年轻的女大学生,身上带着让你想靠近的专注,但又散发着有些疏离的优雅。
先读完的是她的《温柔之歌》,小说起篇就是两个孩子被保姆杀害的惨案现场,人们的唏嘘,父母的震惊,然后小说顺时间轴从头叙述。“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与别人无关的生活。”所以初为人母的米利亚姆决心雇佣一个保姆照看孩子,而自己重新返回事业,甚至是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了事业。一个人舍弃与相爱的人相处的时间,带着壮烈的牺牲的情绪去投入“体现自己真正价值”的事情,用自怜的悲怀去代替触手可及的平凡之爱的琐碎。可是这些琐碎,却偏偏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元素,我们无法被轰轰烈烈地渴求被给予,生活是倦了却还要拥抱的双手,是酸了却还要忍住的眼泪,是激烈涌起却一瞬即逝的爱和愤怒,是暗暗滋生却一瞬爆发的欲望。初为人父的保罗有作父亲的骄傲,却又常常涌起想要回到无所拘束只为自己拼搏的日子。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塑造着角色,同时也被角色塑造。仙女般的保姆路易丝,沉迷于她于这一个年轻的家庭带去的整洁完美,孩子们和年轻的夫妇对她的依赖与信任。小说里有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路易丝很喜欢和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她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静静观察孩子们从兴奋的寻找,到累了之后的停顿,最后歇斯底里的害怕,这时候她才会慢慢从角落里走出来。在那一刻,路易丝享受到了的是被强烈渴望需求的快感,生活的一个不露声色的“瘾”。路易丝为什么会选择杀死孩子?一个溺水快要死亡的人为什么还要挣扎着去抓水?年轻的家庭对路易丝的需求是整洁的房间、可口的饭菜、听话的孩子,是一份被分担了的责任。而路易丝对这个家庭渴望的又是什么?是杀死两个孩子后,一个新出生的孩子可以给她带回的她被强烈渴求强烈信任没有缝隙的雇主友谊。
越是长大,越发现“坏”和“好”才是这个世上最敷衍的形容词,是缺乏耐心去了解真相的人给自己的定心丸。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事情的发生,是种种因素的诱导。所以我越来越不愿意去对一个事情作出评价,我们能做的只是抛去自己对事实的主观陈述部分,用最真实简单的语言去陈述。
看完了《温柔之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蕾拉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比起《温柔之歌》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感到更加的沉重。“不满足的人会毁了身边的一切”。小说的开篇就在极力描写性瘾重度患者阿黛尔那种被欲望掐紧喉咙,生活无法自控地被要求多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但她又是控制地那么好,单独使用白色翻盖的手机,压在枕头下的黑色笔记本,把一切可能暴露“罪行”的痕迹都隐藏的干干净净。但就像她的丈夫查理在发现一切后,歇斯底里地说“人都得为他的谎言付出代价”。是的,他们的代价是,表面上平静幸福的生活终于被揭穿了,每个人都被从自己单方面设想的世界里拉出来了,他们不得不一起面对生活这琐碎的可怕与残酷。他们不是因为纯粹的爱而结合,阿黛尔需要的是一份可以逃脱一切永远被原谅接纳的安全感,而查理要的是被需要的个人满足感。”这一切都没有结束,阿黛尔。不,没有结束。爱,就只是耐心。能够吞噬一切的、发疯的、专制的耐心。毫无由来的乐观的耐心。“所以,爱是什么?除了爱,人与人之间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又是什么?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直在我心里的一幅画,那是当我坐在公车上,看着赫尔辛基从市中心到机场一路高高光秃秃的树木,一闪而过的灵感。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件开衫,脸上笑盈盈的,一只手敞开一边的衣服,展开,看见她的心里有一片深幽幽的湖,湖里淹着一个缩小版的她自己。
不禁也想问自己,生活于我,”瘾”是什么?
在读第二本小说的时候,听的是《c'est un chapeu!》。觉得配合在一起,别有一番感觉。纯碎与复杂,也许从来不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