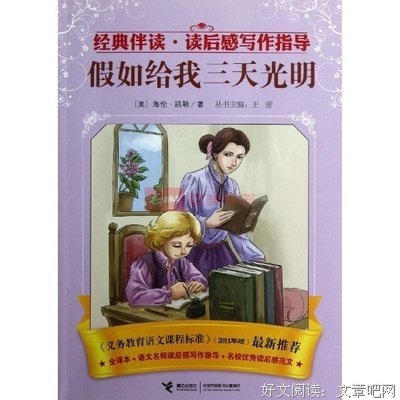《惊悦》经典读后感10篇
《惊悦》是一本由[英] C.S.刘易斯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惊悦》译者前言
丁骏
1.
出版于1954年的《惊悦》是英国作家C.S.刘易斯的自传,这一年他56岁。自传从他出生的1898年写起,止于他皈依有神论的1930年前后,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的前半生”。在最后一章“开端”里,刘易斯告诉读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有神论过渡到基督教信仰的,他给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也是婉转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继续去写1930年之后的二十多年生命经历。因为,刘易斯觉得,在拥有信仰之后,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是终于“走出自己”了。
对于有信仰者来说,刘易斯的所谓“走出自己”应该不难理解。上帝是万物之源,仰望上帝便是生而为人的本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不再为我自己而活,“我”也因此变得微不足道。刘易斯对于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二十多年的人生感受,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微不足道”了。
细读《惊悦》的前十四章,最让人震撼的是作者强大的记忆力。一位55岁的男子,竟然可以清晰地记得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某个时刻,周围的情景,内心的思绪,某种强烈的感触,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只发生在昨日。刘易斯大脑中的回忆触角几乎可以探伸至岁月深处的每个角落——一只盖着苔藓和嫩枝小花的饼干桶带给仍是幼儿的他关于美的第一次体验;童年恶梦的昆虫主题是因为育儿室里的一册绘本,上面有一只带着活动触角的鹿角甲虫;而第一句直击7岁少年灵魂的诗歌至今还在他耳畔回响: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
美丽的巴尔德尔
死了,死了——
就是一个有着这样惊人的记忆力的刘易斯,对于离他自己最近的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生命经历却说: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们知道的是,在那二十几年里,刘易斯写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奇幻小说《纳尼亚传奇》;二战期间他的名字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因为他应邀在BBC电台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系列讲座,成功鼓舞了英国民众抵抗纳粹德国的士气,战后这些演讲稿被结集出版,名为《返璞归真》;而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基督教书店,都会发现《返璞归真》仍然是那里畅销书榜单上的第一名。几乎刘易斯所有最重要的仍然拥有广泛读者的书,都是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写成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竟然让我想起托尔斯泰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许在刘易斯看来,他的后半生不必写进自传,恰恰因为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与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并无本质不同,他们的人生都已进入同样的完全臣服于上帝的“忘我”境界,而在他自己看来,这显然正是他作为人应该过的唯一一种正当而幸福的生活。至于他在现世的成败得失,与他的精神生活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管他取得多少世俗眼光中的“成就”,在他内心深处永远是“微不足道”这四个字。与此相反,他的前半生既背离上帝,也便充满了各种独特的“不幸”,各种跌宕起伏,各种“堕落”、痛苦、挣扎、绝望,以及最终的希望和救赎。回忆这些经历并用文字如实记录下来,对刘易斯来说,也是在整理追溯自己走向信仰的精神之旅,而这份真诚的追忆,当然更是他基督教信仰的见证,又一份独一无二的见证。
2.
记得翻译《惊悦》期间,一位诗人朋友曾经随口问起我眼下在译什么书,我告诉他是C. S.刘易斯的自传。“可是,有谁会看这本书呢?”他脱口而出。虽然在这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旦问题被提出来,我倒觉得提问者的困惑既真实也容易理解。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刘易斯的书,也不知道他是谁,自然不会想到读他的自传。而我和我的编辑朋友之所以一拍即合,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立即动手翻译刘易斯的自传,也是因为我们俩早已是刘易斯的“粉丝”,他重要的护教类作品几乎都读过一遍。所以,似乎确实可以这么说,《惊悦》这本书首先是为熟悉并喜爱刘易斯的读者们准备的,而这样一个读者群在中国显然也是存在的。刘易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著名作品在两岸三地都早已有了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即便是我自己小小的朋友圈里也总能找到愿意坐下来聊聊刘易斯的朋友。
另一方面,如果是一位从没有接触过刘易斯的读者,当他翻开《惊悦》,会不会也有如书题所言的体验呢——惊讶于意想不到的喜悦?我想这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凡这位读者会对我说到的以下几点中的任何一点生发出兴趣。
如果你相信,或者哪怕只是怀疑,生长在现代社会的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也是可以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学者,英国中世纪文学研究者,儿童文学作家,剑桥大学终身教授,是如何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全英格兰“最不情愿的一个皈依者”;如果你好奇于这样一个皈依者如何自始至终保持着最清醒的理性主义,他又是如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理解信仰,并最终接受信仰,为信仰而辩护——你可以读《惊悦》。
如果你是英国文学的爱好者,或者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应该很容易就会喜欢上《惊悦》,并且同意这是一本供茶余饭后“闲读”的好书。我已经记不清刘易斯在他的传记里提到了多少西方作家和作品,其中大多数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经典,你不一定认同他对书的个人品味,但很可能他的某句话,某个暗示、揶揄,就会让同样熟悉经典的你唇角泛起会心的一笑。而你若碰巧也常读英国散文,那么刘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肯定会让你的阅读倍添欢乐,惊喜连连。
如果你相信童年经历对人的性格形成和精神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并且想了解一些个体真实的经历,那么刘易斯在《惊悦》中所记录的正是他对于自己早年人生的细致入微的回忆以及内省式的思考批评。刘易斯幼年丧母,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可以说直到他父亲去世,父子之间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这种始于童年的与父辈的精神隔阂,其实也正是我自己以及很多同龄人共有的经历,读来难免唏嘘感慨。但更重要的乃是刘易斯的反省精神,他在描述父亲的种种不可理喻的同时,总不会忘记强调自己因年轻无知而表现出的任性、自私、不体谅甚至残忍。而刘易斯与他唯一的哥哥始终兄弟情深,面对父亲很早达成攻守同盟,不乏令人捧腹又耐人寻味的童年趣闻。至于每个人此生会交到的第一个朋友,遇到的第一位让你或恐惧或敬畏的老师,第一位终生难忘的启蒙导师,第一次这样那样的致命诱惑,刘易斯都会向你娓娓道来,诚实地与你分享他大脑中每一寸或美丽或高贵或痛苦或羞辱的记忆之地。
最后,对我个人来说,翻译《惊悦》最大的收获在于,刘易斯在这本书里努力记录描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一种徘徊于灵魂深处的渴望;刘易斯用了一个最初来自德语的词汇“Sehnsucht”来命名这种渴望,大致可以解释为对不明之物的强烈渴望。至于“喜悦”这个中心词,只是用来描述当这份渴望获得满足时那种稍纵即逝的、极大的、幸福到锥心彻骨的感觉。这正是我一直感觉到却苦于无法把握、难以名状的存在体验,如果你也有着同样的让你充满困惑的渴望,那么《惊悦》也许正是你该读的下一本书。刘易斯认为自己的前半生始终没有弄明白这种渴望的对象,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味追求“喜悦”,错把这种感觉本身当作了渴望的目标。在他接受信仰之后,目标当然立即明确了,就是上帝,刘易斯对天堂的解释便是与上帝同在,既深刻又简单。而值得回味探究,值得与人分享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个充满彷徨和困惑的过程,给后来的朝圣者们一点提醒,一些慰藉。
3.
2015年是我做文学翻译的第十个年头,但我译书并不勤快,最近完成的《惊悦》只是第7部作品。《惊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整本书的翻译过程相比我之前的经历,无疑是最顺畅的一次,有点儿一气呵成的感觉。原因应该有很多,自传的结构相对简洁,刘易斯的用词平实,风格流畅,字数也不多,但这都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从翻译一开始便接连亲历“惊悦”,翻译中一些主要的困难随之不攻自破。
前文提到,刘易斯在自传中提到了无数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事实上,他兴之所至,还常常会引用某部作品中的原话,却又不说明出处。作为一个西方经典阅读量不及作者万一的译者,这些每隔两三页就会出现的人名书名,以及突然冒出来的引文,着实挺让我头疼。他提到或者引用的作者作品虽然大都是文学界认可的大家,但有些也相当冷僻,并非普通读者所喜闻乐见,有些甚至维基百科上都难觅踪迹。所幸我的烦恼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因为翻译到第二章时,我就无意间遇到了一个题为“LEWISIANA.NL”的网页 ,细看之下,是一位北欧人为《惊悦》全书出现的引用和典故所做的完整注解,按章节索引。内容极其细致全面,很多注解不仅包括作者和原著基本信息,甚至详细到引文出现在原著第几章第几页,也常常提供上下文给读者做参考。我当时的感觉,说如获至宝、喜出望外,都不算夸张。
过了没多久,又一个惊喜不期而至。《惊悦》全文共十五章,每一章开头都会有一句独立引文,呼应暗示本章内容的精神,所以充分理解这些引文对于做好整个章节的翻译显得至关重要。LEWISANA.NL对这些引文虽然也都做了出处说明,但也仅限于此。有一次,我又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找到了一篇刘易斯研究专家约翰•布莱莫专门讨论《惊悦》各个章节标题以及题头引文的长篇论文 ,可以想像那一刻我心头的雀跃。所以读者们在中译本中读到的关于题头引文的注解大部分内容是基于布莱莫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我把握每个章节的要旨也有很大帮助,几乎是立竿见影地提高了我的翻译效率。
最后一个惊喜出现在翻译的尾声阶段,2015年夏天我去了离伦敦不远的苏塞克斯郡开会,旅途全部的空余时间都用来完成《惊悦》最后三章的翻译。我按计划在离开英国前去了一趟牛津大学,寻访刘易斯故居。一路滂沱大雨,坐了火车又换汽车,中午时分终于到达牛津镇,下车时雨刚好停了。在步行去故居的路上,我经过了牛津的圣三一教堂,记起那里是刘易斯生前常去的教堂。于是当然要进去看看。眼前的入口似乎通向一个弄堂,走进去,果然是个窄窄长长蜿蜒向前的石弄,两边石墙上爬满了青藤,虽是阴雨天气,路面却也干爽。石弄里暗影憧憧,格外清凉幽静,我一路走着,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还有偶尔几声雀鸣,感觉就像走在梦境里。百余米之后,走到尽头,推开矮矮的院门,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就是教堂前的空地和公墓了。一片青草地上立着高高低低形状各异的墓碑,还有好几棵葱郁的大树。我径直朝教堂走去,大门关着,推不开。
于是我又退到公墓边,一眼看到一块小小的牌子上写着“刘易斯墓地”。我怎么没想到他有可能就是葬在这里呢?我放轻脚步向前走,心里琢磨着,这么多墓碑,恐怕得好一会儿才能找到刘易斯。正想着,走到一棵树下,一低头,一块长方形水平放置的墓碑上正写着“怀念我的弟弟克莱夫•斯坦布斯•刘易斯(1898-1963)”,再往下是刘易斯哥哥沃伦的生卒年月,这应该先是沃伦为刘易斯立的墓碑,后来沃伦自己也与弟弟合葬于此。我在墓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心里起伏感动,难以描摹。随后我在墓碑边一截湿漉漉的老树根上坐了下来,看到旁边一丛不能辨识的紫花,正开得热闹,毕竟是八月。我享受了一会儿少有的内心与周遭完全合拍的宁静感,直到天又开始下雨,我看着落在自己赤裸的臂膊和同样赤裸光滑的墓碑上的雨滴,8月的雨让身体感到清凉的惊喜。这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愉悦传到大脑,我身在梦里的感觉却不减反增,这时想起了刘易斯谈什么是我们最清晰的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碎片的、昙花一现的本质,觉醒到我们并非做了一个梦,我们就是一个梦而已。”
两天后,我完成了《惊悦》全书的翻译。
全名为克里夫·斯坦普斯·刘易斯[CliveStaplesLewis,(C.S.Lewis 1898-1963)],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文学批评家兼作家,对于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尤有研究。中国的读者会认识他,多半拜他的系列儿童故事《纳尼亚年代记》所赐。
刘易斯1898年11月29日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一个清教徒之家。童年时代生活平静安逸,但9岁时母亲不幸去世,随后他就被送往英格兰一所严格的寄宿学校。在丧母的悲痛与学校环境的压抑中,他很自然地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里寻求安慰,并对形而上学和终极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的刘易斯迷上了瓦格纳歌剧中的北欧神话世界,16岁时为准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接受父亲的老校长柯克·派崔克的指导,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古典式训练。但入校攻读哲学后不久,刘易斯就在1917年应征入伍,调往法国前线。翌年四月他中弹受伤,辗转遣返伦敦疗养。1925至1954年在牛津大学任教,当选为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研究员,担任英语与文学教职长达29年,教授古典文学。1954至1963年任剑桥大学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教授。1944年2月到4月间,刘易斯每天上午在BBC电台发表“超越个人”的广播讲话,向战时的人们,尤其是士兵和伤员们解释基督教信仰。这些广播讲话在大西洋两岸广受欢迎,确立了他作为二十世纪基督教最重要阐释者与宣扬者的名声。58岁时,他同一位比他年轻17岁、离过婚的美国妇女海伦结婚,但几年后海伦即患癌症去世。刘易斯本人卒于1963年11月22日。 刘易斯曾经是唯物主义者,也曾经是个神秘主义者,多年来他一直在哲学与信仰的道中上寻寻觅觅。1931年,刘易斯在朋友J.R.R.托尔金的影响下成为基督徒。他信奉基督教人道主义,主张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反对世俗的现代主义。他以寓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较为有名的有《魔鬼书信集》。该书用魔鬼的口吻写成,写魔鬼在书信中教育侄儿如何诱惑人类。 刘易斯一生著述甚丰,是大约四十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若干关于英国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评论作品。在学术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有《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十六世纪英语文学》、《个人的异端》等,在宗教方面有《痛苦问题》、《纯粹基督教信仰》等,在文学创作上则有科幻小说“空间三部曲”与《纳尼亚年代记》。空间三部曲包括1938年的《沉寂的行星之外》[OutoftheSilentPlanet]、1943年的《皮尔兰德拉》[Perelandra]和1945年的《骇人的力量》[ThatHideousStrength]。故事讲述了英国语言学家兰森[Ransom]的遭遇。他在从火星到金星的旅途中,卷入了太阳系内的正邪之战。空间三部曲被认为是史上最佳的科幻三部曲之一。
《惊悦》读后感(三):《惊悦》之惊悦
没有任何的写评论的技巧,我只能凭着自己个人的喜好和平时的阅读对自己所读的书所留下的印象做一些简单的记录,而由于在豆瓣之中超过一定的字数就需要算作书评了,而不是短评了,为了避免写短评时要看字数的尴尬,我干脆就直接来写书评好了。
关于此书的“非”与“是”
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记,这个和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刘易斯对于精神的觉察更为敏锐,在表达或者说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描述更加高超。(其实两本书的意识形态部分的大部分描写我都没看懂,林语堂的甚至因为其引用了大量文言文,我就直接跳过去了)。倘若有读者希望通过《惊悦》一书了解刘易斯一生的履历,生命中经历的跌宕起伏,我想大多是要失望的。其实我原本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看这本书,但是,虽没有满足这个小小的愿望,确实给了我更大的满足,如同书名一般“惊悦”。
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刘易斯的思想转变逐步归入基督被基督“拉入门内”的一个过程。惊讶于刘易斯对自身意识的敏锐,妹妹我读到他描写自己内心状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倘若刘易斯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从全书来看,几乎有一半以上在描述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动态(姑且用这种不恰当的词语来形容),然后逐步的描述自己怎样的被“对手”一步步将死,然后拖入门内,领受恩典的过程。
对于我个人之“惊悦”,恰逢小女要入学一年级,而七月份又参加了CCE论坛,深深觉得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必要性,在没有经过论坛学习之前,犹如井底之蛙一无所知,而结束论坛回到家中再次拿起这本读到一半书,发现刘易斯所受的,虽然称不上是基督教古典教育,也算是古典教育了。而其中多处提到对于教育的观念,也是深深的契合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思想,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在论坛之后又补上了一课,令我虽念之涩涩,又及其喜悦的读完了余下的部分。
《惊悦》读后感(四):对友谊和喜悦的观察
刘易斯的作品文字都非常优美,《返璞归真》更是基督徒的经典读物。刘易斯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里从小有着大量的藏书,这也让小时候的刘易斯已经开始阅读父亲书柜里的书籍。在中学,公学和导师制的教育也让刘易斯接触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阅读新书的每一天都让刘易斯心中充满快乐。这是文艺青年投入文学生涯的基础。而在这本自传中,刘易斯对友谊和喜悦的观察最为细微:
友谊的不同表现。刘易斯对友谊非常敏感,和哥哥的相互依赖、和同学并肩去体会世界、分享同样的品味,长大以后刘易斯还意识到了两种好友,第一种是和自己完全一样的,第二种是处处与自己抬杠,但是最终也会成为自己的好朋友。
喜悦感来自放弃对喜悦感的思考和追求。就像禅定一样,你在思考是否进入禅定的时候,你就永远无法进入禅定。如果在喜悦中思考喜悦感,那么喜悦感就会消失。就像我们发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梦就会醒来一样。反过来,当你思考你的恐惧感时,恐惧也会消失。所以,要保持一种美好的感觉,就要多去接触而不是去剖析。要远离一种罪恶,就要多去分析而少去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