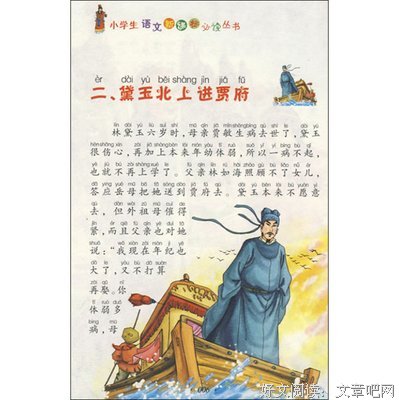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10篇
《莎士比亚书店》是一本由[美] 西尔薇娅·毕奇著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312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大家都感叹书店难以在这个商业时代存活下来时,犹让人想起那些著名的书店,它们以人文彰显自己的特色。而“莎士比亚书店”就是其中的个案,它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也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至今仍让全世界的爱书人津津乐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许在其店主西尔薇娅·毕奇所著的《莎士比亚书店》中能寻找到些许答案。
要想探寻这家书店的秘密,我们不妨先来看书店的历史。1919年,毕奇在巴黎左岸开了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1922年,她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为乔伊斯出版了英美两国列为禁书的巨著《尤利西斯》,因而名噪一时。然而在盗版、 战争、经济萧条的威胁下,1933年开始书店多次面临困境,还好在法国文艺界的支持下,仍继续经营了下来。1941年,她因拒绝卖给德国纳粹军官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守灵记》而受到威胁,不得不将书店关门。随后,美国加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毕奇小姐因为是美国人而被纳粹逮捕,投送进集中营。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到1951年,在得到她的授权后,乔治·惠特曼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书店,取名叫“莎士比亚书店”。1956年,毕奇小姐写下自传作品《莎士比亚书店》。6年后,她逝世于巴黎。
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它诞生开始,就在机缘巧合下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成为英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心,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从它出版《尤利西斯》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书店的活力,特别是它做的一系列活动,比如阅读沙龙比如新作朗读会等等,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值得独立书店效仿的案例,并且兼有图书馆、邮局和银行等多种功能。它的开创之举,也还是有着自己的特色。小说家安德烈·尚松说:“她就像只传播花粉的蜜蜂,作家们都透过她才能互利互助,英、美、爱、法四国在她的促成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国大使的功劳加起来也没有她大。”
关于这家书店的传奇,总离不开那些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的种种做派,梁文道说,这本回忆录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闻异行,而是他们都过度符合大家对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贡果然是这么的超现实;萨提果然是这么的冷静节制,不论晴天雨天总要带一把伞上街。至于费兹杰罗,就和传说一样的挥霍无度。“总是把钱放在他们住家大厅里的盘子上,如此一来,那些要来结账或者要小费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拿钱。”今天的书店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步了。
在这本回忆录中,毕奇不仅讲述了书店经营中的欢喜、哀愁、成就、遗憾和与很多知名作家交往中的细节,也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里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事实上,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莎士比亚书店和它的缔造者毕奇小姐都已成为永远的传奇。毕奇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在今天看来,不仅仅是一个巴黎的文化坐标,也还兼有对文化传承的功用,从毕奇的叙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书店所营造的气场,好像并不是一个商业场所,而是一个人的书房,在这一点上,时下的书店做法却恰恰相反。我当然不是说,后者做得更差劲一些,只是在读者眼里,对书店的舒服感就缺少了点。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二):毕姐的述职报告
毕姐做为一名怀抱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同志,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不远万里来到法国,秉承“五湖四海皆兄弟”的革命原则,于巴黎剧院街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从开业的青葱岁月到二战期间书店寿终正寝的二十余年间,毕姐交友无数,非正式代理了詹姆斯•乔依斯的外宣业务,出版了万世景仰的奇书《尤利西斯》。1956年,毕姐扭转白发苍苍的头颅,回望着自己的一生,于一切喧嚣皆烟消云散过后,郑重写下了自己的述职报告,就是这本《莎士比亚书店》。
说毕姐的自传是述职报告,是因为手中的这一本,确确实实与大家在年终时不得不挠破头皮,极度诚恳地说着敷衍话,极端认真地说着大假话,极其实在地说着大空话,以及实实在在地说着牛皮大话的年终总结或者述职报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党的大政策方针指导下,在单位领导的有力领导和支持下,在同事们的积极帮助及配合下,本人取得了等等等等等等方面的成绩。如果真要说到不同,唯一的不同之处便是:毕姐没有展望未来——年届七十的老人,也实在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不是吗?
与我们这些红尘中翻滚的俗人不同的是,毕姐本身已经够强大,实在无需说那些假大空的无聊话。这本述职报告想来应该是出自毕姐的口述,无比质朴的语言,寥寥几笔的人物速写,无论毕姐是否握着一支生花妙笔,她都不必刻意卖弄,只单把那些名字直白地列出来,就足以让铺展在人们面前的那些篇章熠熠生辉了。
这本述职报告的一大噱头当然是毕姐那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坛重量级人物的交友名单,聪明如毕姐想必也了然于心该指望什么来抓人眼球。于是,在书中,毕姐几乎将自己所认识的——甭管交情厚薄——只要是维基百科能查到的人物,皆一一列出,无一漏网。但是,如果你暗自摩拳擦掌,期待能有什么麻辣爆料,那就只能是大失所望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毕姐的描述都中规中矩,无懈可击。仿佛是久经杀场的律师有朝一日坐到了证人席上,任对方百般拷问,回答永远是滴水不漏。看似言无不尽,真诚坦荡,但却绝没有你迫切想知道的,也绝不会有任何让朋友难堪的言论或轶事出现在字里行间。也许是因为在写书的时候,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人世;也许是因为毕姐原本就是个“老派”的谦谦君子。所以,没有丑闻,没有独家爆料,精挑细选的雅致趣事,以及斟酌再三的措词就是你即将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全部。
即便是曾经与某些人交恶,让毕姐描述起来,也是那般地隐晦,那般地克制,那般地温文尔雅。例如说到与斯泰因的小小不合,“突然失去两位顾客我当然很遗憾,但是有谁能逼她们留下呢?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住在剧院街的人不敢高攀那种朋友。”瞧,前一句话是外交辞令式的废话,而重点在后一句,我们可以隐约品味出,在失去了斯泰因友谊的多年之后,毕姐日渐衰老的胸膛里仍然鼓荡着小小的不满与不平。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毕姐不曾说起,我们也永远无从得知。
至于乔伊斯的背叛,毕姐处理起来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将整个事件加以原生态还原,我想,当年在毕姐心中引发的震荡,应该不啻于一枚深水炸弹。尽管毕姐只是就事论事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在最后,“……我向奥德赛出版社表示,不必理会我跟乔伊斯签的合约,但是正派的他们坚持要给我版税,既然这笔版税不会影响到乔伊斯,我就接受了。”毕姐的委屈,仍然是一目了然。
二十世纪上半期,在遥远的巴黎,有那么一家小小的书店。它静静发送出的电波波及到整个的世界,那些永远载入文学史册的人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围拢了过来,又尽皆散去。
“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着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饭店(Ritz)的酒窖。”到此,毕姐的述职报告便爽爽利利地结束了,仿佛一甩满头的短发,决绝地扭身便走,空荡荡的剧院街上只留下她寂寥的背影——好一个老派拉拉的飒爽风范。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三):书店,汇聚城市的人心与灵魂——《莎士比亚书店》里的时代印刻
文/沙迎风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经典杰作《双城记》,讲的就是巴黎。巴黎的历史丰富多彩,但最好又最坏的年代里,一定会有“莎士比亚书店”这一节。
1936年,“莎士比亚书店”已岌岌可危,经营陷入困境。昔日因为英美两国的保守文化政策而流落巴黎的作家们,也逐渐开始离开大战日益临近的欧洲。当书店创办者,美国人毕奇小姐告诉法国作家纪德,她想关掉书店之时,纪德大声喊道:“我们不能放弃莎士比亚书店!”
不论在哪个城市,小书店的生存从古至今都是难题。它生意太小,无法赚钱;它安静寂寥,没有太多顾客;它无声无息,关掉也没人在意……跟今日一样,昔日的莎士比亚书店年轻女老板也只是为了开书店的理想而苦撑。但她终于没有撑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拒绝将最后一本《芬尼根守灵夜》卖给一位纳粹德国军官,她关闭书店,让这家传说中的书店从此消失。
这座书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一提及它,就想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黄金时代,于是把它说成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更有很多人不忍心让它消失,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纽约,新的“莎士比亚书店”招牌仍然屹立,并努力延续着它昔日的精神。
如果你想知道这家书店为何如此让人难以遗忘,那么应该读一读毕奇小姐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读了它,你就知道书店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有多宝贵。书店静静地藏于城市的某个角落,让城市经历的时代、人物烙印都刻在它的墙上、书上、相框上。如果想要读懂一座城市,一定要到它的书店,去看一看印刻在书店里的人心和灵魂。因此有人就说:去巴黎的人,可以不去铁塔,一定要去莎士比亚书店。
如今去莎士比亚书店的人,大多是带着朝圣的心情抵达的。而曾经去那里的格特鲁德·斯坦因、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文学大师,当年却是带着被庇护的心情抵达这一伟大书店。莎士比亚书店既是他们的流放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书店接纳了他们,也就是巴黎接纳了他们。他们“让来自新世界的愤怒、渴望和激情以文学和诗歌形式在巴黎左岸回响”,让巴黎拥有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当欧洲陷入动荡之后,这些人又乘船回到大西洋彼岸的纽约,将新的文学、艺术、社会思潮带到了美国。纽约接手巴黎,成为了新的世界文化中心,格林威治村也成为引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变革的中心地带。
这一传承的源头是显而易见的。梁文道先生说:“(莎士比亚书店是)现代主义的震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产房”,这话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记录的,不是一家小书店的生存悲喜录,而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而理所当然的,作者毕奇小姐也并不仅仅是一家小书店的老板,而是时代的女儿。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四):流动于莎士比亚书店的飨宴
一家书店见证及深度参与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如今是极难想象的,若有,多半也是前朝往事了。因为既要有时代的风云际会,亦要有虔诚于文化的助产士与出类拔萃的作家汇集一处,而这些,均已风流云散不见踪迹,于是,曾经的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了可供追怀的传奇,源于其别无分号、独此一家。西尔薇娅•毕奇是书店的主人,《莎士比亚书店》是她的回忆,她写下这些文字只为溯往念怀与立此存照,而我们,从中知晓了曾经流动于巴黎剧院街上的迷人飨宴。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格拉鲁德•斯坦因、纪德、庞德、瓦乐希、阿拉贡、艾略特……如此的一系列文坛人物,我们只能在文学史中挨章拜望,而他们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常客与西尔薇娅•毕奇的老朋友,许多人每天必来,也未必有什么事,就是进来转转,看能碰到谁。不知哪位作家先斩后奏地将“剧院街 莎士比亚书店”作为自己的信函、电报与包裹邮寄地址,从此毕奇凭空多了一项义务,不过毕奇不会不耐烦,现代主义“保姆”的名衔不是白白叫的。
虽然群贤毕至、众星云集,但西尔薇娅•毕奇将最多的精力放在了詹姆斯•乔伊斯这里,因为这位《尤利西斯》的作者是她最为钦佩的作家。个人的偏向使毕奇说出,“如今乔伊斯已经成为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且是最显赫的一个”,尽管必定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毕奇女士不管这些,她就愿意这么讲。毕奇自己认为,我们后世也都认可,她与莎士比亚书店最辉煌的功绩是出版了《尤利西斯》,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基于“淫秽”的理由,这部巨著在英语系国家屡屡碰壁,无望出版,西尔薇娅•毕奇慨然施以援手,决定帮助乔伊斯在法国出版《尤利西斯》。过程曲折,结局美好,一位业余的出版人促成了文学史上一部伟大著作的诞生。
这位出版人的业余不仅表现在对《尤利西斯》的出版不进行成本控制(乔伊斯在校对稿上反复修改,毕奇听之任之,多支出不少钱),而且拒绝了一战成名后蜂拥而至的所有书稿(其中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北回归线》),只因为她的莎士比亚书店仅出版一个人的作品,也即乔伊斯。这是出版史上的奇谈,亦为毕奇的痴气。即使十二年后,乔伊斯将《尤利西斯》交予兰登书屋出版美国版,未尊重毕奇的版权,毕奇亦没有太多的怨言,当初出版乔伊斯的书,收益几乎都给了作家本人,她本不为赚钱,如今只要乔伊斯觉得满意,那他尽管去做好了。
关于乔伊斯的章节与段落几乎占西尔薇娅•毕奇回忆录的泰半篇幅,可见乔伊斯在毕奇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之重。我读之,总感到两人关系的奇特,毕奇初识乔伊斯,是仰视与崇拜,随着时日的流逝,从毕奇的角度,乔伊斯似乎变为天才小说家与被宠溺的顽童的合体,毕奇对之亦是尊重与迁就合一,尽量满足乔伊斯的要求,有很重的母性成分。如毕奇叙述自己与友人要休假,乔伊斯怏怏不乐,不愿意让去,即使成行,他也要为不甚紧要的事打电报,让毕奇度假亦不踏实。我感觉,毕奇表面在抱怨,实质上并不为忤,她享受着这种打搅,如一个母亲对待孩童。
自然,“流动的飨宴”是人来人往的,以毕奇的话说,“我店里的顾客每天至少会有一位是曾在《小评论》与《日晷》上面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原因大致有,大西洋彼岸的作家受到打压,以及其时的巴黎是事实上的世界文化之都。有西尔薇娅•毕奇这样的文化热爱者,莎士比亚书店门迎四方客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我们读毕奇的回忆录,能够感到她的记述的平面化,手录曾经的所闻所见,未有纵横捭阖地深入剖析,除去对詹姆斯•乔伊斯的描画比较详尽,其他的作家更多的是素描,匆匆而过,让读者未免不过瘾。如格拉鲁德•斯坦因在巴黎的活动,以及与海明威的关系,都太简略,当然这也是源于毕奇只写她亲眼见到的,其他未及。在如此的点状素描之外,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自行去挖掘与填补了。
梁文道曾将莎士比亚书店与中国上海曾经的内山书店放在一起比较,都是外国人于另一国办的书店,且均存在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杰出的作家与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内中亦有区别,内山书店主要与鲁迅先生交往,莎士比亚书店与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家群落结盟,各自的时代特点与风云变幻亦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却都是独立书店的传奇。这样的传奇可遇而不可求,不可复制,因为人,因为时代,而两者的交汇更是如彗星划过天际般难以捉摸。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莎士比亚书店的传奇更是成为了只可远观的空谷绝响,独立书店遭遇难解的生存危机,挣扎图存是不得不面对的窘境,文化人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更接近于奢望。如今回望西尔薇娅•毕奇女士,怎不令人羡慕?她亲近书籍、崇敬文化的热望在那个时代获得了正面的回报,即使将一生的时光投入,亦其犹未悔。或许,于艰难中的坚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现实,即使飨宴不再,亦不能任由答卷空白,不管涂抹上如何的图画,也是向上的点滴努力。在此种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传奇。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五):了解巴黎文化的一个侧面
巴黎是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文化中心,她的书店还兼出版社,邮局,银行,文人云集,蔚为壮观。 书最后提到二战,那时期书店和人命运哪,唏嘘不已。 作为一个美国人,毕奇有一位神父父亲,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是美女演员,诗人阿拉贡追求过,艾德丽安 则帮助她最多。
书中提到饱受盗版之苦的作者生态,出乎意料。
1
怕狗的乔伊斯
《尤利西斯》(三分之一是在校对时加上的)因为文字太暴露,被英文国家禁止,而乔伊斯生活也拮据,得靠家教过活,他的老婆只会骂他“窝囊废”。他同乡萧伯纳拒绝购买《尤》,回信里的理由很有趣。而《尤》在美国的发行,是靠海明威每天一两本搭船渡河带过关的。。。 《芬尼根守灵夜》主角参照了歌手 john maccormack。书店还出版了 乔伊斯的诗集《一首诗一便士》。
2
海明威
第一次到书店还是个慷慨帅小伙新人,最后就是战地记者大叔了,毕奇赞赏海明威的那些书名,同感。
3
其他文学大咖们
收藏玩具兵的Valery Larbaud , 瓦乐西 和 于勒 罗曼 ,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都很有趣 ,布赖尔(bryher)是一位独立正能量的姑娘。 舍伍德. 安德森,他举荐了两位学生——厄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 福克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名人还有叶芝,艾略特,安德烈 纪德。格特鲁德·斯坦因,被誉为“现代主义之母”(与毕加索有交集)。
因为她出版的《尤利西斯》,当时是淫书,所以很多作者慕名而来。意外的是毕奇拒绝了 亨利 米勒(南北回归线),也拒绝了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跑腿也没有用。法兰克 哈里斯(frank harris)太搞笑,以为《小妇人》是辛辣的书。。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六):“好家伙”们趣传
这是一本有趣又信息量大的书,读完掩卷,仿佛自己就坐在毕奇小姐的书店里,看着“那一群人”在面前晃来晃去,在书店进进出出。“嗨,老海!”“嗨,小勃!”他们简短地打招呼,然后各自去找自己喜欢的书读,风风火火地来去自如。
这儿就像他们自家的书房,在这里读书、会客、访友、办朗诵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可以借钱、收信、托办事务……这是他们这群流浪在巴黎的文学圈的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毕奇小姐的性格就像她的面容一样,生动活泼,她乐于热心地为年轻的作家朋友们办事,想看着他们有所成就,想让法国的朋友认识自己祖国的新兴文学作品和作家,不知不觉间,她竟成了联结几个国家文学交流的纽带,“那一群人”后来真的走向了国际视野的文坛。就像别人说的,莎士比亚书店的文化影响比大使馆的外交影响力还要大。
毕奇的朋友们在她看来一个个都很可爱有趣,又都个性十足,乔伊斯、海明威、庞德、瓦乐希、纪德……如今他们一个个的名字都震烁文学界,不得不感慨莎士比亚书店曾有过多么辉煌温馨的旧日子。那些日子里,大家虽然同是“迷惘的一代”,时不时遭受着财务上的困难,但总是热忱地相互帮忙,一起渡过难关。在毕奇的怀念里,他们都是那么地惹人喜爱。
她的作家、作曲家、画家、演员、出版社朋友们风云际会,擦出了很多后来成为文坛逸事的火花,而她竭力帮乔伊斯出《尤利西斯》,则成了莎士比亚书店最负盛名的事情。前前后后多年,她为乔伊斯这本“禁书”的出版费尽心力,又出了他其他一些作品,俨然成了乔伊斯的义务经纪人。敏感、友善又天才的乔伊斯从她崇拜的作家变成了她的好友,而莎士比亚书店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就像英国查令十字街84号的那家书店成为爱书人的圣地一般,巴黎剧院街12号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追慕文学名家往日风采的文化圣地,虽是时代使然,那个时候巴黎的英文书店不多,人们期待这样一个书店的到来,但毕奇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她对欧美英语系作家的关爱都是发自骨子里的,他们,是互相成全。
刚读过《流动的盛宴》,在《莎士比亚书店》里,我还是乐于寻找海明威的影子,他第一次到书店的情形、他怎样帮忙偷运禁书、他怎样打响名声、最后怎样在二战快结束时带人“解放”了剧院街和书店,真是好样的。
这两本书交相辉映,描摹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左岸的文艺风情,相较而言,《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涉及的人物非常多,事件也丰富而精彩,别有味道,就像梁文道在序言中说的一样,是热爱欧美现代文学的人不可错过的一本书。
那一群人确实都是“好家伙”,那时的他们,每个人都像一道绚丽的花火,共同点燃了不那么亮丽的时代天空,也筑就了一个璀璨的精神世界。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七):阳光下的阴影
这是一本放在我房间很久都未曾拆封的书。一月份的时候,我想好好阅读书籍,立下每个月两本书的目标,就撕开了这本书的塑料封面。这本书断断续续的看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今天终于看完了。是的,我很不喜欢这本书。原因如下:
第一,作者一个女人,一个美国女人,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在法国左岸的书店,命名为“莎士比亚书名”。可见作者的能力非同一般,这是作者的回忆录,我本以为这本书是写作者开书店遇到的一些趣事。可是通篇都是作者跟那些现在看来是伟大作家的互动,特别是乔伊斯。她说,她为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完全是兴趣。没看到结尾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作者生活在这群伟大作家的阴影之下,特别是乔伊斯。在文章的末尾,作者陈述了乔伊斯为了在美国出版《尤利西斯》“背弃”作者。最终两人几乎也是“撕破了脸”。看到这里,我没有感到自己的预测正确,而是为作者感到可惜。真诚相待的人,却换不来等价的情感对待。
第二,是我自身的原因。书里的人名太多了,我记不住!这是我看这本书拖了这么久才看完的原因。如果一边看书,一边运用思维导图标记一下会比较好!可惜有些人名只出现一次,人生中的匆匆过客,作者也是如数家珍,可见作者对这些大人物的崇敬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书中有写乔布斯出版了绿色封面的诗歌集,其中十三本赠送给了谁。作者也是将这十三个人的名字一一列举。
以上只是本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八):最美的书店
在法国的剧场街,有一个闻名世界的书店,它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莎士比亚书店。它不仅曾经出现在电影中,还频繁在电视剧里亮相,不仅仅因为它独特的装潢(书店里挂满了作家们的画像),更因为“从它诞生开始,就在机缘巧合下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成为英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心,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 ”莎士比亚书店作为一间独立出版社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让它声名大燥,从此奠定了它在法国书店里的重要地位。
作者西尔薇娅•毕奇,也就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办人,这是一本她的自传书,讲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意义的一段生活经历,当然与莎士比亚书店紧紧相系。在艾德丽亚这位同性友人的帮助下,毕奇小姐开了这间英文书店,专门介绍她的祖国美国的文学作品,并因此吸引了大批文学爱好者,又因她为人和蔼可爱,个性坚强,经常不顾自己囊中羞涩而慷慨助人,再者她有很独特的文学嗅觉,使得她交上了很多名人作家,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其中最值得传颂的自然是乔伊斯,当时他的作品《尤利西斯》没人出版商愿意出版,毕奇小姐本来就是乔伊斯的忠实书迷,因此愿意为他倾尽所有,竭尽全力促成它的面世。
书中主要围绕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文学作家、艺术家们与作者的交往的故事,透过作者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大人物可爱俏皮又独具个人风采的一面。只可惜我的阅读范围太小,很多都不认识,唯独读过一两本海明威的作品,还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两部,其实不容易读出什么共鸣。但因为看过《午夜巴黎》这部电影,对当时的文学氛围和所中提及的人物有些许印象,还是能大概跟得上节奏。但总的来说,我读得很无趣,总是不得不在中途想放弃的时候迫使自己读完它。也许,如果能对文中所讲到的作品和文学流派、作家都了解,再来读,会有更大的收获。
除了论及文学,本书也从侧面看到了西尔薇娅•毕奇这批女性文艺工作者的个人魅力。她们抛开传统赋予的角色,在文学界大放光彩。甚至在面对战争,面对纳粹的摧残,她们依旧不卑不亢,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勇敢地斗争。
人生的意义本就重质不重量,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将它转为自己的工作动力,并脚踏实地地做好它,无论结果如何,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女性。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九):无法企及的时代
如果有人问起,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上世纪20-40年代的巴黎。
根本不需要更多一条的理由,只要将目光锁定那座1919年11月19日诞生于巴黎杜皮特行街8号(两年后迁址至剧院街12号直至1941年关闭)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已足够。
书店主人西尔薇娅·毕奇,一个单身的美国女人,书店开张那年,她32岁。开书店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在遇到终生好友(也有人认为两人是同性恋人)、拥有一家法文书店的艾德丽安·莫里耶后,这一心愿更是变成一种无法自拔的渴望。
最终,西尔薇娅借助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微薄积蓄,在艾德丽安书店附近开出了这间以售卖英文图书为主的莎士比亚书店。
其实,她们的书店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私人图书馆:由于书价昂贵,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更愿意借阅图书,从而以会员的形式团结在书店周围。而书店除了提供图书,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类似读书会的活动。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巴黎街头徘徊着许多来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这些来自遥远新大陆的年青作家们,在经历了一战的炮火和杀戮后,对人类与社会充满了失望情绪。真的有所谓美国梦吗?他们带着怀疑来到了巴黎,更像是为了寻根。这些人里面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菲兹杰拉德、艾略特……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
这些人全部都成为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以及西尔薇娅的朋友。 首先是因为当时的巴黎英文书店并不多见,更重要的则是西尔薇娅的个人魅力。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我们得以窥见:
“西尔薇娅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双眼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似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里。她的腿很美,她对人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照片上的西尔薇娅有着尖尖的鼻子和下巴,嘴唇很薄,眼睛不大但能想象得到它们的好动灵活,她的额头平坦开阔,因而让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更显露出几分男子气。我想,这位后来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保姆“的西尔薇娅小姐在她的尊贵顾客心目中早已被模糊了性别。
我爱读她晚年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借由这本书,我仿佛去了那个年代的巴黎剧院街12号。
那里有英俊青涩的海明威(不太像后来大胡子的硬汉形象),海明威被西尔薇娅封为莎士比亚书店的”最佳顾客“,不单单是因为他每次来书店都会买上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站在西尔薇娅的周围。在二战结束德军投降之际,正是身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带领一队人马”解放“了剧院街——
“有天一辆吉普车开进街上,在我书店门口停下。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喊: ‘西尔薇娅!’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艾德丽安大叫说:‘是海明威!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一边转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旁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
那里有充满正义感的纪德。纪德的书我只读过两本,一本是他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另一本则是小说《窄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没想到纪德原来是个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上天保佑他的”爱管闲事“,如果没有他,莎士比亚书店书店不会撑到1941年。
当然,在莎士比亚书店,最有名的大人物当然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式的人物 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和西尔薇娅(或者说莎士比亚书店)的重要关系在于:当《尤利西斯》在英语世界被判为”淫书“,出版无望时,是莎士比亚书店首先在法国出版了它,使它的作者乔伊斯能看到它所引起的轰动,而不至于像很多失意的作家那样,生前碌碌无名,死后才获得迟来的荣耀。
是西尔薇娅拯救了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西尔薇娅的回忆录,有一多半都与乔伊斯有关。我们得以知道乔伊斯怕狗怕得要命,却爱猫。我们看到那个总是拄着一根梣木杖、带着四支表(每一支的时间都不一样)的乔伊斯,有时候他很羞涩(当人们在外面大声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总躲在后面),有时候他很孩子气(每次西尔薇娅休假,他都很惶恐,总想阻挠),有时候他很执拗(出版《尤利西斯》时,印刷工人不得一遍又一遍的修订,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着不休不竭的修改),有时候他又很单纯(他从没有金钱概念,收入并不丰裕的西尔薇娅只好充当他的”金主“,并把《尤利西斯》的全部收益如数交给乔伊斯,而他却挥霍无度——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西尔薇娅似乎从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或许她并不一定能当个优秀的作家。但她的书店本身就足以令她的文字精彩——她根本无须加工什么,那些有趣的细节就足够了。
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出版商——莎士比亚书店只出版过乔伊斯的三本著作,因为西尔薇娅的出版生意只考虑作家和作品的价值,从不考虑商业价值(她未从中牟取丝毫私利,她帮助乔伊斯纯粹只因为崇拜),因此绝非成功的商业案例。而且,西尔薇娅竟然拒绝过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一家书店,只要出版过一本《尤利西斯》,就已经足以奠定它的声名和历史地位。
我是多么喜欢那个时代的巴黎。
20年代的莎士比亚书店书店,30年代的花神咖啡馆,那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存的时代,代表了西方文学界和思想界最高峰的时代。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时代。
令此世的我们不仅有些淡淡的忧伤。
人类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顶点与高峰,波浪状前进。顶点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更多的时代则平淡无奇——全部的意义只是为下一次的爆发积聚能量。
在这样的攀爬中,我们该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当人类的思想总体处于一个碌碌无为的状态,我们又该如何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我们自我的价值何在?
唯有等待多年后,回首过往的那一天才有答案吧。
《莎士比亚书店》读后感(十):书店
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Company)已经成为传奇。1956年,她写下自传《莎士比亚书店》(中文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此纪念那些难忘的岁月,6年后,去世于巴黎。虽然巴黎左岸拉丁区至今仍然还有一家名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且经过毕奇小姐授权使用店名,但人们心目中的“莎士比亚书店”,还是那家曾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之所以出名,无疑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重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而美洲新大陆的文化正以不可遏制之势勃兴,这些文化亟需找到一条进入欧洲的通道,以获取欧洲主流文化界的认同;相比保守的英国和败落的德国,当时欧洲唯一能执文化牛耳的只有法国,或者说,只有巴黎;此外,以毕奇小姐显赫的家世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能够吸引到包括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一大批名头响当当的人物聚集周围,莎士比亚书店要是还不能成为巴黎的英语文学交流中心,那就反而有些奇怪了。
毕奇小姐在《莎士比亚书店》中对詹姆斯 .乔伊斯着墨甚多。除了毕奇本人对乔伊斯无以复加的崇拜外,也是因为这位爱尔兰作家即便在当时,也已经名满天下了。1922年《尤利西斯》的出版,与其说确立了乔伊斯在英语文学中不可动摇的语言大师地位,毋宁说成就了莎士比亚书店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
《尤利西斯》颇具戏剧性的出版和发行过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尤利西斯》的版权问题上,乔伊斯最后并没有投桃报李。
十年后,美国法官约翰.伍尔西(John M .Woolsey)对《尤利西斯》作出无罪判决,兰登书屋立刻打算出版此书。令人诧异的是,在这过程中,竟没有人认为曾费尽辛苦率先出版此书的莎士比亚书店是这本书的版权所有者,甚至包括乔伊斯本人。最终,出于多种考虑,毕奇小姐放弃了对《尤利西斯》版权的坚持。在书中,她是这样解释的:“至于《尤利西斯》,是我要乔伊斯照自己的意思去处理的。毕竟书是乔伊斯写出来的——就像小孩天生是属于母亲的,跟帮忙催生的助产士无关,不是吗?”虽说如此,言语中多少还是透着点落寞。
有趣的是, 当年《尤利西斯》问世后,莎士比亚书店立刻成为“刺激、辛辣”的“淫书”出版商的代名词,许多禁书作者纷纷找上门来。其中就有D.H.劳伦斯那本大名鼎鼎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了此书在巴黎的出版,英国作家阿尔多斯.赫胥黎特意登门拜访,希望莎士比亚书店能够帮忙出版他朋友的这本小说。对此,毕奇小姐的评价是:“我觉得他为好友劳伦斯的牺牲实在很大,因为他不喜欢《尤利西斯》,结果居然要委屈自己前来乔伊斯的大本营。” 当然,最终毕奇小姐还是拒绝出版此书。虽然表面的理由有很多,但我觉得她对劳伦斯看似不经意地一句评价,才是拒绝的真实动机,“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像他这种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写出能够符合读者期待的作品?”原来,毕奇小姐并不喜欢查泰来夫人。
整部自传中,此类有趣的闪光点不少。当毕奇小姐暮年回首往事之际,留在记忆中的,大多是有趣的人和有趣事。至于所有的不愉快都已经风轻云淡,能娓娓道来,恰恰表明对一切都已释怀。
巴黎左岸的那家书店曾经存在过,今后却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