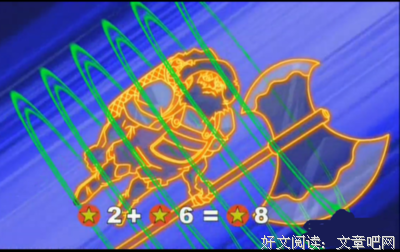新刊试读 | 不与时人同调,是对创作者的恩赐(下)
编者按
朱天心成长于一个文学家庭,从小便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四十三年过去了,她仍秉持着那股诚实和英勇,护卫少年时代的理想,将与现实搏斗的痕迹化为飞翔的诗意。在本期访谈中,她谈那些发生在异国他乡、发生在记忆、梦境中的故事,那些自由轻盈的“漫游”。
朱天心X《萌芽》
没一个为读者而生,
是对读者真正的尊重,
不三心二意地
《萌芽》:从出生起到15岁,您都住在眷村里,您曾在《眷村里的游戏》一文中写道:那时经常和小伙伴“你家待待我家探探”,看看别人家里的老结婚照,瞧瞧爷爷、奶奶的古装剧照片,妈妈的绣花缎旗袍、珠珠鞋和残缺的首饰;还一起远征到山陵和河边。想请问时至今日,您觉得在眷村的童年经历在您的生命底色与写作上留下了什么烙印?
朱天心:眷村海纳了各省的语言、生活习俗、饮食、信仰,是五湖三江的缩影,也因为幼时听多了父辈邻居的故事,会对历史特别持有一种同情和责任感。
眷村的物质生活一穷二白,反倒四海好兄弟似的你我不分一起共享,那股子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呼群保义的热血,尽管随年长和离开眷村降温了些,但仍一直烙印在血管里,我知道。
《萌芽》:父亲是著名作家朱西甯,母亲是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刘慕沙,姐姐朱天文也是著名的作家和编剧,在这样的文学家庭里成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朱天心:他们既认真又敷衍着过眼下的现实生活,又其实父不父母不母、心不在焉的,时常像活在另一个更有意思的世界似的,好叫人向往,引我尾随。
《萌芽》:您很早就发表了作品,16岁便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17岁创作长篇自传《击壤歌》。我们想问得更早一些,您最初是怎么喜欢上写作的?小时候您写些什么?
朱天心:写第一篇小说的16岁之前,我当了十四年的读者吧。(识字前,母亲会念父亲的小说或我们都喜欢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度过没有电视年代的晚间。)
所以十五六岁多感触的年纪,拿起笔来写字,于我是个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萌芽》:此后三四十年,您都专心于写作,您曾说和您一样从精英女校出来的朋友们如今社会经济地位很高,都不理解您的这种生活方式,有些好朋友还把您看作“栏外迷途的羊”。面对这种世俗的压力,您是怎么坚定于自己的选择的?这期间有没有过不想写作的时候?
朱天心:我常常萌生不想写的念头。(倒并非因为写作太辛苦了。)看到好小说时觉得自己可以不用写了,因觉文学殿堂有能人撑持不致倾颓;看到坏小说,更不想再写,因羞与为伍。
必须清楚自己的行业所需,豪宅、名车、华服、名流来往……于我写作半点没用,我要的是时间和自由(爱说爱写什么或不说不写什么的自由),想清楚了,就不至于动辄浮动,或心神混乱。
……
《萌芽》:在《击壤歌》中的少女小虾看来,小说并不是单纯玩玩的、“玩物丧志”的东西。您今天依然这样认为吗?您心目中了不起的小说家是怎样的呢?
朱天心:就引萨义德的这些话吧:“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不能适应、不愿适应,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知识分子是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知识分子如同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非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当取悦大众或雇主取代了依赖其他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判断时——知识分子这一行不是被废掉就是必然受到约束”……
事实上,我以为把整本《知识分子论》的“知识分子”替换成“小说家”,便完全是多年来我心向往之的了不起的小说家的完整造像。
……
《萌芽》:您曾说,不同的时代也会对创作有不同的形塑,以前的社会资源匮乏,步调比较慢,人们很可能花二十年喜欢一个乐团、一个作家,慢慢消化,养成一个生命独特的基因图谱。而现在信息和资源过于丰富,反而导致大家的精神养料都很趋同,吸收得也很匆忙,对于创作来说倒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文学艺术最讲那种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请问您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应该怎样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性?
朱天心:横向信息的取得(或曰被灌爆刷屏)如核爆瞬间烧夷为一体,我会更勤于向纵向的历史、传统借智慧偷法宝,而不致让自己沦为只存在于当下的动物。
我会练功修行式地勇敢面对、接受、善养自己的“不与时人同调”,那对于群居的人或感孤立甚至危险,但对于创作的人,那是恩赐。
《萌芽》:您曾说,网络加强了同侪之间的影响,或者是很强大的约束,强过了对“纵”的学习,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脸书上看他的朋友在做什么,可是他不会花同样的时间,关心几百年前某部作品中的人在做什么。您觉得这里所缺失的对“纵”的学习指的是什么?
朱天心:时间拉长,人类的善念和恶行的花样着实不多,我将自己短短的尚嫌不够的肉身经历置于历史脉络下,可以更澄澈地辨识出何者轻何者重、哪样新哪样旧、哪个怪哪个寻常……而不致随众瞎起舞。
……
《萌芽》:您曾说作家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您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有愤怒、有不满、不轻易被驯服的人。这种不温顺的“叛逆”,您认为是写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吗?
朱天心:是个有利条件,但很多人容易局限在叛逆“传统”和“体制”,但叛逆自己的生物状态如何?年龄状态如何?存在的状态如何?叛逆整个人族世界如何?这些不都是各个作家在处理着的他人视为理所当然、对凡事凡物的叛逆吗?这或会让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安不适,但,却能给予创作的人启动的动能。
《萌芽》:您曾在《三十三年梦》中强调,作家应当拥有一种“不写的自由”,但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拥有读者也是很多作者天然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会让写作者陷入为读者、评论者所裹挟的状态中。您认为作者应该如何在想要获得读者的愿望与拥有“不写的自由”中取得相对的平衡?您个人有怎样的经验?
朱天心:我敬重和喜欢的作者,没一个为读者而生,更遑论回应甚至满足读者的期待。所以我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我期许,我从不认为那是傲慢,而是敬业,是对读者真正的尊重,不三心二意地专心做好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多年前,我曾经在公开场合谈过“不写的自由”,后来遭年轻世代断章取义几乎传成笑柄,硬把我描绘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贵妇作家。这里我愿意一字不易再重复一次这“不写的自由”:不须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写,以致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不回头炒冷饭,不跳针[1]。因为我们通常都深知作家失去写作自由的可怕,但鲜少意识到失去“不写的自由”对作家的另一种难喻的伤害。
[1] 跳针:原意指唱片机在播放唱片时唱针跳动造成播放不正常,产生走音或一直重复某片段的现象。此处指写作者重复之前写过、说过的话。
本文为节选,刊于2018年第十期《萌芽》。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