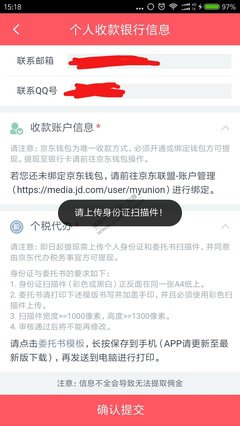我的一张“声份证”
当面听我说话,还能勉强看唇型、猜大意,接听我的电话时,她就抓狂了,甚至到了血压升高、手心淌汗的地步。
现代人的流动性大,上午天南,下午海北。出门在外,几样必带,有人给了一个生活提醒——“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和钱包。身份证太重要了,我有两张,而且一张是永远丢不掉的“身份证”,准确地说,是“声份证”。这话怎么说?
《视听界》杂志的朋友鼓动我开个专栏,说说电视台那些事。专栏好写,最后的“作者简介”难住了我。没有显赫的学历资历,没有骄人的研究业绩,几易其稿,决定“自毁形象”一回:年近半百,电视老人;话不普通,人很普通;分量不重,口音特重;恋旧恋自己,偏爱新媒体。
我的“不懂话”,流传已久,可谓几十年如一日。我下笔,随笔、杂感早就发在《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上,没人说不懂。但开起口来,我是一个满嘴跑方言土语的人。
工作单位是电视台,这是讲和用普通话者最为密集的地方,多数帅哥靓妹的普通话水平都是一级乙等以上。突然闯进我这样的另类,可以想象,同事们会觉得有多奇葩。
最尴尬、困窘的反应,来自美女编导俞,在我们共事几年后才知道,她一直听不懂我说的话。最初,她会赶紧转身悄悄地求助一边的同事,把我的讲话翻译给她听。幸好本部门记者编辑好多来自苏北,基本可以理解我的原意。当面听我说话,还能勉强看唇型、猜大意,接听我的电话时,她就抓狂了,甚至到了血压升高、手心淌汗的地步。她怕领会错了意思,耽误采访或发稿。据同事们举报,本人打电话的套路,一般开头都会憋几句普通话“你好”“你在哪儿”,话题一长,就飙起方言,而且越说越快,害得好多年轻同事多少回辗转反侧,琢磨我的电话意图。罪过,罪过。
补充交代一下,俞编导来自南京高淳,她那旮旯,方言更是奇葩。譬如,“外面在下小雨”,当地方言是,“外头来头落蒙丝花”。网上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有人讲高淳话。高淳话又咋样?高淳人不也怕我的东台话吗?我老家一公司的总经理,一次给莅临视察的上级领导介绍情况:我们还有很多hang mo(项目)正在调研。对方惊奇不解:调研“蛤蟆”?本人多年观察后发现,老家出生长大的人,口音都很重,可能是因为环境一度封闭,人的流动性弱也。
好多次栏目组开策划会,我现学现卖一些网络段子,调节气氛,哄堂大笑之间,总有几位地缘关系较远的同事一脸茫然。经人翻译一遍,才延时大笑。所以,我的笑话总是可以赢得两次以上笑声。若干年前,到饭店吃饭,请服务员拿些“水杯”过来,我还刻意憋了两个“普通话字”。过会儿,服务员拿来一大瓶“雪碧”。估计她也嘀咕,这人怎么菜不点,上来就喝雪碧?但也奇怪,每次K歌,我都飙出一口纯正普通话歌词,年轻同事一致反映,唱得比说得好听。
电视台的几任主管都试图改造过我的普通话,安排普通话一级甲等的主持人与我邻座办公。结果呢?文化反输出。我的发音没有改善,他们倒免费学到一门“外语”,东台话“听”“说”能力可达六级。另一方面,稿件里有些生僻字的读音,主持人们一般总会问询于我。普通话说不顺溜,“普通字”还是可以的,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哑巴汉语”了吧?
N次反思过我的普通话之差。千真万确,小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每天晨读的领读者:我—爱—北—京—天—安—门。普通话不标准,能领读吗?小学阶段,我也做过广播体操的喊操者,在几百人面前喊口令:1—2—3—4,2—2—3—4……普通话不行,能喊操吗?当然还需要勇气、中气。可是过了识字、读字阶段,就不严格按照拼音说话了,我的周边也全是方言土话。而且,对那些外地读书、工作或打工回来开始憋普通话、用书面语的同龄人乃至长辈,我内心都有鄙视、抵触。在我的理论框架里,他们是忘本,是摆甩,是轻浮,是浅薄。老家有一句方言形容他们说:洋而粕痴(装腔作势)。现在想想,可能是出自一种自卑心理。人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排外反应。(爱情故事大全 www.wenzhangba.com)
现代文明社会,当然要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发音作为传播媒介,节省沟通成本。但是,方言又是不能废弃的,它是语言的活化石、文化的DNA,除此宏大视角,方言还有好多日常的实用功能。读大学时,去省报送稿,估计一口“东台普通话”,让接待我的编辑谦和地问我哪里人,我如实相告,他立即伸出右手:好!老乡!那个姿势,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家乡公安部门,一次侦破刑事案件,依据一句本土方言“神滴杲昃(什么东西)”,准确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常住方位。两位老乡住在省城一个小区,并不熟识。某次因为社区物业纠纷,吵得不可开交。两人被喊到派出所,各自向家人电话通报案情,这才听出口音相近。腆着脸一问,果然是同乡,一声乡音泯恩仇。前天看朋友圈,常州好友包小慢发帖说,儿子把她的硅胶洗脸刷当作chang ken的东西擦屁股了,一看那组拼音字母乐了,这是家乡方言“搓灰”的意思,专家考证,本字是“磢硍”。他们怎么也这么说?许多年前难道是同脉同根?其间有哪些演变?一句方言,勾起一串身世追问。
我的“不懂话”,更有意想不到的符号意义。主持人小傅,籍贯河北邯郸,最初来电视台应聘时,看到现场好多人听我用方言高谈阔论,反响热烈。他一句没有听懂,但是据此判断,这个单位的领导一定包容,这个单位的用人也一定不拘一格。哈哈,他蒙对了。
这位兄弟现在可以给我当东台话的同声翻译了。语言的习得,在于环境,在于听说。假如我早年被扔在英国某条大街,我现在应该一口英语,可能是伦敦腔吧。——那是一张可以通行世界的“声份证”了。
(本微信与上观APP朝花时文栏目专稿)
点击下面链接,可读“朝花时文”上月热读文章:
喻军:李叔同,“十分像人,十分少有”
安谅:阿婆黄鱼面
何柏青:霉干菜㸆肉
石毅: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孙丽丽:秋虫咬碎一地月光,人间一味清欢
陈连官:新场前世,为浦东打开“历史大片”
郑宪:北加州,北加州
这是“朝花时文”第1349期。请直接点右下角“写评论”发表对这篇文章的高见。投稿邮箱wbb037@jfdaily.com。 投稿类型:散文随笔,尤喜有思想有观点有干货不无病呻吟;当下热点文化现象、热门影视剧评论、热门舞台演出评论、热门长篇小说评论,尤喜针对热点、切中时弊、抓住创作倾向趋势者;请特别注意:不接受诗歌投稿。也许你可以在这里见到有你自己出现的一期,特优者也有可能被选入全新上线的上海观察“朝花时文”栏目或解放日报“朝花”版。来稿请务必注明地址邮编身份证号。
“朝花时文”上可查询曾为解放日报“朝花”写作的从80岁到八零后的200多位作家、评论家、艺术家和媒体名作者的力作,猜猜他们是谁,把你想要的姓名回复在首页对话框,如果我们已建这位作者目录,你就可静待发送过来该作者为本副刊或微信撰写的文章。你也可回到上页,看屏幕下方的三个子目录,阅读近期力作。
苹果用户请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向编辑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