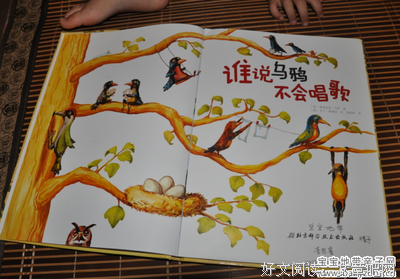我歌唱的理由读后感精选10篇
《我歌唱的理由》是一本由[奥]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等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328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01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歌唱的理由》读后感(一):闲来翻阅,且歌且吟
读诗,有时是漫无目的的。只因为那些文字的深沉与宁静,可以在那瞬间使人获得好心情。
当你读到弗罗斯特那熟悉的两句: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你读到里尔克的《秋日》:
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文字就是如此神奇,它会连接两个毫不认识的人,即使他们相隔万里,即使他们相差百年。诗歌的文字更因其优美而具有神力,再好不经意间击中你,从而沉迷在一方小乐园。
这本诗集将如此多的优秀诗歌汇集起来,我无需再费力找寻,得以遇见,实乃幸甚。
《我歌唱的理由》读后感(二):我感动,故我歌唱
比起从小吟诵的“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的中国古诗,与外国的诗歌的接触毕竟还是有限。与外国诗歌的接触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松尾芭蕉的“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这首,当时怀着戏谑地心情去了解,也并未能够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物哀幽玄之美。接着,印象深刻的便是电影《心之全蚀》中魏尔伦对兰波念的那首“我已将泪水流尽,心碎的黎明”,魏尔伦与兰波的爱恋情仇使我觉得这些情诗也似乎不再遥远,因为它是如此的真挚真诚。再后来,便是T.S.艾略特那首著名的“April is the crullest month,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这首阴郁又隐约闪烁着希望的长诗,虽然一时看不懂,倒也在心头留下了对于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好奇。
与西方诗歌的结缘不深,所以开始读这本《我歌唱的理由》的时候,内心是敬畏又惶恐的。这本集结了27位诗人诗歌的小书,展现的是20世纪的诗歌版图,乍一听感觉阔大得不得了,仿佛是一项难以完成的阅读。然而,慢慢读过来,在这一首首流淌的小诗中,我感受到了诗人纯正的诗心,无论是指向外在自然,还是涉及内在心灵,它们都是诗人的个人感发。钟嵘的《诗品·序》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中国的诗论概念中,兴发感动是作诗极为重要的环节,是一个由物及心的过程,所以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感慨。而诗心,诗人之心,这一个人类普遍的精神反应,理应在世界各国都有所共鸣,“感发”的诗心自然也是如此。
同名诗歌“我歌唱的理由”出自日本古川俊太郎之手:
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崽被雨浇透后死去一只小猫崽我歌唱是因为一棵山毛榉根糜烂枯死一棵山毛榉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孩子瞠目结舌 呆立不动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背过脸蹲下一个单身汉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清泪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可能是因为目睹了一只被雨浇透后死去的小猫崽,也可能是因为见到一棵根糜烂枯死的山毛榉,是因为看到一个瞠目结舌,呆立不动的孩子,是因为路过的背过脸蹲下的一个单身汉,甚至只是因为流下的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清泪。
诗人通过寥寥数字,将他细腻柔软的内心呈现给大家——我所歌唱的,并不是那些佶屈聱牙的东西;我想要歌唱的,不过只是那些令我感动的生活。而正因为感动常在,诗人才能时常歌唱,于是我们能够通过诗人的心灵,去触摸更为广阔的天地。而这正是诗留给后人的意义——经典可能会被暂时遗忘,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歌唱的理由》选录了这些伟大诗人的广阔心灵,使我们在接近诗人的过程中,更能通过诗人的心灵俯仰天地,传递感动,传递歌唱的火种。
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周遭纷扰喧嚣,心烦意乱之际,随手拿起这本二十世纪经典诗歌集,抄写塔比泽的一首诗:
我出生在花飞如瀑的四月
雨绵绵
仿佛眼泪
仿佛无尽的花瓣燃烧似火
……
生疏的字迹落在纸上,一颗心渐渐平静下来。窗外的操场上遥遥地传来Romance熟悉的旋律,这曲被公认为古典音乐史上最优美的浪漫曲,似乎也在这个不起眼的傍晚找回了它往昔的绝代风华,文字与音符交融,妙不可言,也随之染上了一抹蓝色。
一首美妙的诗对心灵的净化启迪,就如同偶然间被一则偈子点化的俗世凡人,境随心转,一念转过,已是清风霁月。与无门慧开禅师口中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有异曲同工之妙。
偷得浮生半日闲,在现如今也早已不是件易事。庆幸还能在一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从诗里借得一抹凉风,醒醒头脑。
某日又看到那首德国表现主义伟大诗人贝恩写给爱人的《丹麦女人》,诗中提到一段希腊传说中的典故,只言片语,却让我对人生际遇生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传说中从特洛伊出逃的王子埃涅阿斯来到迦太基,与当时的女王狄多相爱,女王对他情真意切,愿意与他共治国家。一年后,在神明的驱使下,心怀建国使命,埃涅阿斯不辞而别,大概也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如此深爱他的人。狄多伤心欲绝,焚火自尽,火光烧红了天空,为爱人泣血送别。
读过荷马史诗的人应该都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人物有某种主观意念产生,往往紧跟着就会说是某某神将这种观念放到了他的心中,由此引出了他的某种行为,或情理之中,或超乎情理。人与神、人与宿命的关系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去神秘化的关联:命运似乎可以被参透,被预见,因而顺乎命运也就转而变成了一种主动性的追求。
而《圣经·传道书》3:1-11节中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获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也许,命定与人为,随波逐流与追名逐利归根到底,并无分别。其中的差别,不过是,土豆之于马铃薯、番茄之于西红柿。而人在天地间,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找到自己位置的过程。即《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又何尝不是。
《我歌唱的理由》读后感(四):【转】编后记:诗歌,记忆,初春的祝福
我们总在忙碌,我们似乎越来越忙碌。忙碌中,时间是不知不觉的,心理是紧张纠结的。这时,一支歌,或者一首诗,兴许能让我们进入片刻的宁静。初春,当我再次读到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时,我便沉浸于那片刻的宁静:
春天回来了。大地像个女孩读过许多诗篇;许多,啊许多……她得到奖励为了长期学习的辛酸……那宁静是贴心的,是舒展的,是令人醒悟的,也是让人回溯的。宁静中,我忽然意识到,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在莫名的感动中,我竟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文字。那些亲爱的文字,尽管有着缺陷和稚嫩,可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改动。就让它们保持最初的样子吧。起码,可以帮助我暂时回到过去。时常,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只有过去。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走向过去。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我曾译过她的一首机智又有趣的短诗《三个最古怪的词》:
当我读出“未来”这一词时,第一个音节已属于过去。当我读出“寂静”这一词时,寂静已被我破坏。当我读出“虚无”这一词时,我制造出某种事物,虚无难以把握。一开始,女诗人就试图消解一个虚拟的时间维度:未来。想想也是。倘若时间总在流逝,那么,哪里还有现在?哪里还有未来?这特别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但辛波斯卡仿佛决绝地说:就连虚无都值得怀疑。
幸好还有记忆,幸好还有记忆储存的痕迹,我们的人生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我们的劳作也才有了真真切切的依据和动力。因此,任何写作,包括诗歌写作,严格而言,都是记忆写作。而所有的想象,究其根本,都是记忆的启示,拓展,蔓延,和发挥。因此,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一门记忆艺术。活着,并且记住,并且将一切难忘的痕迹用文字艺术地呈现出来,这是写作者的责任,也是阅读者的幸福。阅读时,同样是记忆,让共鸣和感动成为可能。
而此刻,记忆和诗歌,诗歌和记忆,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不少诗歌都是从《世界文学》读到的。坦率地说,当时,有些诗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就是觉得美和好,就是愿意反复地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时间读,都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优秀的诗歌文本,正需要经得起反复阅读,且常常能激发起读者的心灵互动。这几乎成为一项审美标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世界文学》的不少诗作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世界文学》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谈到《世界文学》的诗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希梅内斯等等世界杰出诗人的诗篇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阿波利奈尔、埃利蒂斯、阿莱克桑德莱、米沃什、勃莱、博尔赫斯等等诗歌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诗歌的力量,在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是如此的显著,如此的巨大。甚至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依然处于人们阅读生活的中心。就连约会,恋人们都往往会手捧着一册诗集。广播里和电影中也都会不时地响起诗歌的声音。“当你的眼睑发暗,也许是因为困乏,/ 我将点燃双手/ 把你奉献,像献出我的一个发现,/ 仿佛上帝正一无所有。”(霍朗《恋歌》)诗歌的力量,有时,就如同爱的力量,神奇,而美好。创刊至今,《世界文学》一直和诗歌有着紧密的、恒久的关联。前辈编辑和编委中,冯至先生,陈敬容先生,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邹荻帆先生,罗大冈先生,李光鉴先生……都是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诗歌,同小说和散文一道,成为《世界文学》三大品牌栏目。几乎每期,读者都能在《世界文学》遇见一些闪光的诗人和诗篇。有些读者,尤其是那些诗歌写作者,甚至就冲着诗歌而捧起了《世界文学》。因此,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我又接着写道:“可以说,没有诗歌,《世界文学》也就会变得残缺,狭隘,少了份光泽,缺了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中的诗歌,也就是译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诗人车前子承认:“译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隐秘部分,是可以和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相对应的。译诗影响、参与和共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影响、参与和共建了译诗。”车前子甚至断言:“当代汉语诗人没有不受到过译诗影响。”
这其实从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文学》中的诗歌存在的深长意味和基本理由。
六十多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无疑已经绘制出一幅世界诗歌地图。山峰,丘陵,河流,路途,森林,湖泊……各式风貌,各种形势,各类气候,应有尽有。抒情的,沉思的,精致的,玄妙的,拙朴的,传统的,前卫的,实验的,清晰的,朦胧的,深沉内向的,热烈奔放的,机智幽默的,轻盈的,厚重的,注重意象提炼的,捕捉日常瞬间的,深入内心世界的,揭示人性幽微的,富含宗教意味和神秘气息的,指向人类高度和宇宙本质的……各种声音,各种味道,各种手法,无所不包。但由于篇幅和版权等缘由,我们仅仅将编选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并且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二十七名诗人的短诗上。依照车前子的说法,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编选《我歌唱的理由》,就有点像是诗歌联合国召集了一场诗歌国际会议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编选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经典性,又看重代表性和丰富性,既注重诗人地位,同样也重视译诗水准。译者中大多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其中许多身兼诗人和译者双重身份。一流的诗人,一流的诗作,一流的译笔,成就一本别具魅力的诗选集。这起码是我们的艺术追求。
诗歌阅读最美妙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对此,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回答。思考此问题时,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诗歌《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忽然在我耳边轻轻响起,仿佛回应,又像是拯救:
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向你飘去,你也和它们一起飘,你将自己投入——我们不解的、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在你面前不尽地展现大海、田野、山峦、森林,鸟儿在自由的高空彼此呼唤,云雾升腾,天穹泛起红晕。而在这地面上,尘埃里,卑贱中,他瞬间看到了你不朽的面容,默默无闻的奴仆充满着灵感,歌颂你,你对他却置若罔闻。在人群中你不会将他识辨,不会赏赐他一丝笑影,当时,这不自由的人正在后面追望,刹那间品味到你的永恒。我多么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这部诗选时,也能随着那一道道“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一起飘,将自己投入“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并且,如果足够专注,足够幸运,也能在刹那间品味到诗歌的永恒,和无尽的美好!
如此看来,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记忆,也是祝福,初春的祝福。
高 兴
2018 年初春于北京
《我歌唱的理由》读后感(五):我歌唱,是因为遇见一首诗的缘故
不论是在孩童咿呀学语之时,还是以一个被现实的负累打击得遍体鳞伤的成年人身份之时,如果愿意沉下心来阅读任何一本普通的诗集,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极其愉悦内心的浪漫之举。诗集不同于篇幅足以吓退读者的长篇小说,简短的篇章里,甚至是短小的几个句子,不敢谓之包罗万象,但也足以洞见于一个诗人每一点细微的情绪、每一滴饱满的泪水。更不用说,很多中国的千古名诗,仅仅是结尾的一个韵脚,就能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方式为此诗铺垫已久的韵律之美画下文体上的句号。
在书柜里,在堆满书籍的大社会里找不到诗人的诗集,就像我一样孤单…………我的诗集将遗失在灰尘里,光无法找到他——【格鲁吉亚】塔比泽《我的诗集》
然而当我的视线停驻在格鲁尼亚诗人塔比泽的《我的诗集》时,当塔比泽早在上世纪就为诗歌命运的担忧之时,我不禁反观自己的内心: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一首诗了?” 在塔比泽单纯的心灵世界里,仍然还是存留着一份人们对书籍的爱,只是诗集在堆满书籍的社会中可能并不招人喜欢,没有立足之地。可是一个世纪之后,现代工业社会、智能时代,堆满的可能已经不再是书籍了,而是比书籍高级一千倍一万倍各式各样的科技成品,以及人们越来越忙碌的一颗急躁的心。此情此景之下,不知多少人对于完整朗读、领略一首诗歌的回忆,已经停留在了中学时代的必背诗文?
我想,朗读诗歌的人群,会一代一代更迭交替,前辈大师给我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可能会在这个更迭交替的过程中被人遗忘,但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可能会被暂时遗忘,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当一个小小却积聚万千能量的种子,遇到适合生长的土壤和滋润得恰到好处的甘露时,便会再次生根发芽,将美好的灵魂再次传承下去。这种奇妙又微妙的体验,在当我打开这本《我歌唱的理由》时,尤其深刻。
《我歌唱的理由》收录于《世界文学》六十多年来译介过的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这里有世界诗歌文学大观园里前辈们留下来的最精彩的果实,和最经典的喟叹。其中有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在《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对生命的脆弱注入无限的哀思,并一反常态得表示:
和平它不是旗帜是肮脏的内衣和平它不是绘画是陈旧的画匾也有依然用神秘的语调形容万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
(玫瑰)忽然它像是荣誉停在天空 可是,我们不像会称呼它,我们猜…… 我们从可以呼唤来的时间 求得回忆 回转到它的身边还有稍显生疏,但是视角极其新颖,从最细微之物窥见博大之处的瓦格纳:
仍在那里,我们早已离开之后 房子、街道,和小镇都消失了 它的注目仍在—如此坚韧不拔 遥远,如此闪光,如此超越东方西方 以至于人们可以在黑暗中 由它导航,给老航海家带去慰藉——《钉子》
初次赏读获得过德语最高文学奖的瓦格纳的诗歌,让我惊艳之感,是带着景仰的拜读。《青蛙》中青蛙交流秘密而塑造的“宁静”,《香菇》中奶奶的香菇引起的回忆,《蚯蚓》构成的肃穆,瓦格纳在代表作中呈现出的对自然万物通感般的观察点,虽然可能是因为不同母语的语言而导致的生涩,仿佛是隔了一层膜,让我只能远观这种气象神奇的艺术诗作,但是那种顺流直下、恰到好处的延展和扩充,十分充分得发掘出了每一个小物体的特点,怎一个妙字可言!
《世界文学》这座大观园里,奇观百态,又气象万千,没有苍白的浅尝辄止,没有韵脚束缚的做作,种种新鲜可感的诗歌作品,不一而足。每一位诗人的诗作,在我看来也是打开了解诗人国家背景的新窗口,在诗人所处国家的特定时代里,他们或许是自由高歌、放声呐喊的,所以诗歌读来总有一种激情昂扬的旋律;也可能受制于现实,只能将无尽的哀思,藏匿在自己简短的诗作中。
可是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止,不断碾压、影响着每一个人而前进,但是如果一辆车轮行驶过诗人的视界,甚至是世界,那么很有希望会留下经受住考验的经典,呈现在后世每一个愿意走进诗歌世界的读者。当两颗心灵再度碰撞、交谈,这颗“诗歌之种”,便再度生根发芽,幻化出更深刻的羽翼,游离于诗歌开启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