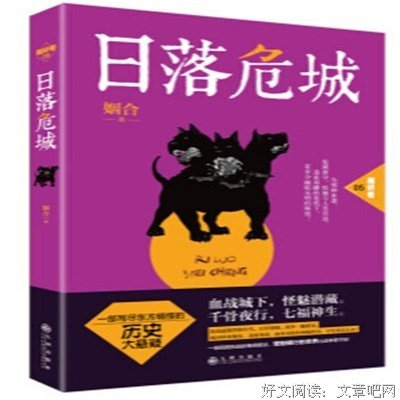《危城之恋》好看吗?经典观后感10篇
《危城之恋》是一部由郑大圣执导,闵春晓 / 周帅 / 刘姝辰主演的一部剧情 / 爱情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城之恋》观后感(一):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花了一个半小时把《危城》看完,之前在豆瓣上搜索的影评总体6分,看过觉得这个分数太不公道,相比目前上档的不中不洋的国产片,这部电影给人的诚意和感动却是远远超出。
中国目前的年代戏很多,打开电视,几乎就没断过,不是抗日就是剿匪,如今再加些特工解密之类戏码,好让观众跟着动动脑子,殊不知多少都是阴沟里翻船,弄巧成拙,投资再大,阵容再强也看不到诚意,粗制滥造实属交差之作。
《危城》是一部集真善美的作品,也是深得中国文学之冲淡意境的作品,一部小投资的名不见经传的影片,能做到如此实在是让人惊喜!
所谓美,不用说,自然是镜头摄影。我看到网上有人吐槽《二次曝光》,是看完就头晕的电影,故事让人晕,镜头也让人晕。好像摇晃的镜头已成电影拍摄的定例,无论是必要还是跟风,不得不承认,好像多了两个摇摆不定的处理整个片子就好像被点了睛。
但回过头看看《危城》所有的镜头都是非常平静的,像一个人老老实实的坐在你面前给你讲一个故事,娓娓道来,反而让人觉得平实,没有那么多无谓的躁动。每一停顿都是一幅画,是一种诗意,是有意境的电影。袅袅青烟,紫藤枝枝蔓蔓,在几株青竹间隐约能见的一株兰花。大概就是苏轼说的不可居无竹。
也不奇怪北美的观众会喜欢,对现代手法的膜拜而对自己本身精神的无所适从,倒让用摩登手法表现的故事有些阿谀之意,模仿终究是没有出路的。
而所谓善,即整个故事的主题。战争来临的不安和惶恐,还有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哪怕是对旧学颇有研究的宁婉儿也是敢想敢做的女性。这才是久违了的真正的人的激情!
我姑且把描写抗战前夕的民国青年的影视作品叫做五四作品(当然按照年代不能这么划分是不严密的),但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屏,印象最深的也就只有《橘子红了》。如果说耀华是真正的五四青年,那么萱之就当是读着五四的文章成长成熟的一代人,和巴曹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这个故事和曹禺的戏剧一样,所有故事都充满命运的偶然性,似乎是命运的手推动着这两个年轻人彼此错过,婚礼上萱之和婉儿的意外之礼是有些可笑的误会,萱之的生死,都是在人自身的安排中那个不能逃过的小玩笑。不要费力去思考所谓人性之类的课题,而是回到古典时代。
但不同于旧时人对于大家庭的抵触,新时代人已经没有那么多怨气,能心平气和的看待这种环境。封建大家庭里的人不再是勾心斗角的图谋钱财,或是各自怀揣一个龌龊秘密隐身于此。侯家上下更多的是让人觉得希望在人间,就算是老二也是离得远远地,不再搅得这个家庭乌烟瘴气。长辈也明事理,所有人都疼惜着有希望的年轻人。尤其是最后萱之的生还,让这个本以为以悲剧收场的故事有了曙光!
这才是艺术的意义!在思索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向往!否则未来就是死路。所谓:人为了善和爱就不该让死亡统治自己。这也是这部电影让我在看完之后能呼一口气的原因。
然而缺憾也有,比如这个男猪脚,没有大家公子南开学子的气质,倒像是从乡下来城里闯荡的淳朴少年,表演也太刻意夸张,而且单调。红鹅这个小胖子倒是不错。春晓的表演非常到位,赞一个!
最喜欢的是婉儿在教堂里扮兰小姐和自己对话的那段,也拍得最好。婉儿相比时下的古典才女形象是个会喘气的女人。喜欢就去追,哪怕是小小的尝试也是踏出去的一步。我最不喜欢像甄嬛一样的女人,无趣得很,美则美矣却没有生气,就像是被放在供桌上供起来的女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倒是连人都算不上。世间男子有才情者虽喜欢佳人德才兼备,但并不一定喜欢过分端庄持重情趣无从谈起的冷美人。
如果放在所有中外影片中,这部不一定能算得上佳片,但是相对如今乌烟瘴气的国产电影而言,却是一缕吹过的清新之风,如果那些所谓商业电影的探索之作能做到真正真诚,那中国电影的兴起也算是指日可待了。
《危城之恋》观后感(二):两座危城
国难当前,小日本即将攻陷的天津卫是一座大的危城,身在天津卫对小叔子产生爱慕之情的婉儿心里也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小的危城。前者沦陷在鬼子铁蹄之下,后者深陷于社会伦理所不容的感情中。
据说《危城之恋》和《天津闲人》是姐妹篇,除了地域背景都选在了天津以外,最能说明二者关联的就是郑福山先生扮演的独眼说书人,神情恍惚地闯入了在街头同样不知所措的婉儿视线中。天津闲人的影片色彩更多是接近黑白,危城之恋则是怀旧的昏黄,前者是民国逗比风,后者是民国文艺风。说到津味,《天津闲人》因为掺杂了诸多群众角色和人文表现的桥段,所以具有更浓重的地方特色。
这次不得不说下演员,《天津闲人》男主是有曲艺功底的,女主角是科班演员,在戏谑的剧情中表演得算是中规中矩。《危城之恋》则完全是女主角压过男主角,一个对旧学颇为精通的大家闺秀被演绎得至少有七分林黛玉的即视感。不仅是举手投足甚至包括台词表现,尤其是以竹子为背景的画面,活脱脱就是潇湘妃子在世。于是百度女主角,果然是红楼选秀比赛林黛玉组的亚军,可能是演员本人的气场就是林黛玉那型的吧。只是个人认为宁婉儿的性格是处于传统向现代递进的阶段,黛玉式的言行有些过于古早和舞台腔了。
所谓危城之恋,危城二字有些名不副实,时局描述显得蜻蜓点水,导演把大量笔墨放在女主角的小危城之恋,整个电影的格局似乎就做小了。战争大环境下,原本可歌可泣的感情,最后变得可割可弃。于是我自行臆想这样一个隐忍的爱情故事放置在那样的时代,用意恐怕主要还是在大的危城,天津卫惨遭日寇蹂躏,加速了两个年轻人欲说还休的感情在历史洪流中湮没。
同样,《危城之恋》也有贯穿全剧的道具——兰花,从新婚夜独守空房的婉儿为了首先保护兰花不受夜风侵袭,没能顾及熄灭的子孙灯。当三少爷好奇读者身份时,婉儿立刻想到了给自己起笔名为兰小姐。而有次佣人要给她房间熏驱蚊香,婉儿怕烟气伤了兰花,最后好像也隐喻了战火狼烟把兰小姐和三少爷活活拆散了。三少爷第一篇发表的诗《走出来吧》,有心的婉儿听出了自己活寡妇的孤寂沉闷,其他人听到的是祖国召唤他们走出家门奔赴前线对抗倭寇。
剧中有诸多细节体现了婉儿在伦理与情感之间反复徘徊。在小黑屋洗印照片时与三少爷的肢体接触时的敏感表情,进三少爷的宅院时不知是否该关上院门。她不敢挑明对小叔子的感情,她被大嫂劝说为了经济有依靠不要离婚,所以哪怕最后能收到那封充满激情的邀请信,婉儿应该也不会随萱之加入腥风血雨的抗日浪潮中。被传伦理统道德观念束缚的女主角,始终无法挣脱去抵抗两座一大一小的危城。
《危城之恋》观后感(三):是身处危城,还是心有危城?
这部电影我很喜欢,要不是觉得结尾没收好我想打五星。
看好些短评和影评都说剪辑比较混乱,对于战争和城市现状的表现不够饱满,说点自己的看法,其实好多电影不好,在于贪多嚼不烂,明明没有足够有力的故事和情节,却偏偏要搭建一个宏大的架构;明明只能说好一件事情,偏偏想要面面俱到哪里都想说一句。这个电影就讲了一件事,我认为主要在于“恋”字,女主角对于三弟的那种情愫,仰慕但是又压制,关心但是欲言又止的感觉拿捏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好电影了吧。
影片当然也有国仇家恨,但是这种国仇家恨的表现并不是像战争题材的电影那样直给的,我认为这部片子是以女主角的视角来讲述的,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能懂什么,只知道诗词歌赋,弹琴浇花,所以很多画面构图,包括滤镜和影片节奏都比较古典唯美,她所有关于国仇家恨的信息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三弟,所以在影片里会觉得突兀或者画风不同,如果不是上街寄信,大宅里的她只能看到报纸的文章,只能听到墙外的游行口号,国仇家恨和大家闺秀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事情,她对于战争的认识只有“宣之,你不要去”。
大嫂说“大宅之中,是熬日子”,作为那样的媳妇,有这么个值得爱慕的人,倒真不如一辈子都没有爱情,国仇家恨和道德人伦,把抱着这情爱的自己放进一座危城。女主角颇像那盆陪嫁的兰草,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气质,青翠则矣,却无花无香,风雨之下如何安身。
心在危城中,小心翼翼,“昨儿他还管我叫妹妹呢”无论多甜蜜,“我也只能是他的嫂子”,现实是一只飞在天上的大鸟,无论飞得多高多远,投下来的阴影都是如此真实。
身在这危城,即便是老爷子,也只能想着如何保住一家人,不像热血青年生出那么多“何以家为”的感慨和抱负,身为深闺女子,更是无法可想无力可用,只能倾己所有去换一人安好罢了。
《危城之恋》观后感(四):无可奈何花落去
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狂飙突进般高速增长,每年上院线的电影至有超过百部之多,市场表面上的一片繁荣热闹掩盖不住大多数影片的粗制滥造与低级趣味。笔者作为影迷,近年来看过的国产片仍然屈指可数,这是一件即讽刺又无可奈何的事。在这样浮躁投机的环境下,郑大圣执导的《危城之恋》带来了国产片久违的精彩与感动。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书香门第的宁婉儿奉媒妁之言嫁给了天津侯家的顽劣子弟二少爷,而后者根本没打算要这桩婚事,婚后就在外姘居。婚姻有名无实的婉儿与有现代思想、颇具才华的三少爷宣之情投意合,发展出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虽然男主角直到经历死亡边缘死才明确意识到对婉儿的爱情。
本片摄影将中式住宅的庭院园林之美表现得极富诗意,宁婉儿在美景的衬托下更显女神风姿,但电影里表现她的镜头画框很多是由门窗,院墙、栅栏等都构成的限制和封闭性空间,这是对她命运的反复注解。美丽的女主角实际是囚禁于笼中的金丝雀,供人欣赏猎奇,借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术语来说,她是“凝视的对象”和“欲望的客体”。她出现在宣之的摄影照片里,更强化其欲望客体地位。
既阳光又有现代意识的三少爷为女主角悲惨的命运凭添了生命的活力和触手可及的爱情。本片最打动人心的情节就在于婉儿和宣之爱情过程中欲说还休的含蓄克制之美,女主角扮演者闵春晓的出色发挥尤其值得肯定。虽然倾心宣之,但碍于伦理,婉儿只能通过笔友的书信往来与男主角谈情说爱。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礼教约束但又有真性情的女性,在与宣之的单边恋爱中,婉儿一方面克制隐忍,一方面也有情不自禁的动情之处。片中对这种矛盾表现的刻画都极为传神,比如摄影暗房内与宣之独处时的紧张与春心萌动,进入宣之宅院关门时的犹豫和保留,教堂里多情又无望的自言自语。在与宣之告别的最后一刻,婉儿泪流满面,真情呼之欲出,但宣之为抗日去意已决,不过那一瞬间男主角似乎明白了她的心意。
宣之对一个理想化虚幻的知音痴迷不已,对深情款款活生生的婉儿却视而不见(当然有伦理这层阻隔),这借用了希区柯克《迷魂记》里男主角迷恋被扮演的玛德莲,却无法喜欢上现实中的扮演者朱蒂这个经典双层结构。不过本片只是形式上的借用而已,没有《迷魂记》里潜在的多层次隐喻。婉儿扮演的笔友成为宣之精神上的知己,现实中前者也与后者朝夕相处,这是一对非典型的柏拉图式情侣。在婉儿的努力下,宣之取代了她丈夫二少爷的角色,除了没有夫妻之实。片中被婉儿和宣之共同照看的大少爷之子红鹅是则像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三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是对女主角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的补偿和替代。不过,宣之的诗情才华与他对婉儿的不解风情似乎很不匹配,某种程度上,导演为了情节的张力扭曲了男主角应有的性格。
男主角两首被全文展现的抒情诗(附于正文后)别具深意。第一首诗即喻示了婉儿的悲惨境况,亦召唤她冲破虚伪婚姻的牢笼,当然宣之的诗本意并非如此,这是导演设计的一个形成对照的潜在文本。得知三少爷死后,婉儿读了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诗名即是本片片名,文本上强烈地表达了出宣之对笔友(婉儿)的深情,与宣之朗读的第一首前后呼应,女主角追悔莫及,悲剧已注定。另外,两首诗亦流露出男主角对民族未来的期望和对日本侵略的愤慨。
片名《危城之恋》的危城指日军大兵压境下的天津,但婉儿自己也住在一座“危”楼里,影片多次在夜景中用仰视镜头拍摄这座黑漆漆的闺楼,暗示了女主角个人命运的不幸,也是对天津命运前途的隐喻。片中时代大环境的因素随着情节的展开逐渐加强,最终因男主角为抗日“牺牲”达到高潮:宁婉儿的痛哭声从宣之的书房延伸到日军占领天津的黑白资料片里,她不只是为宣之哭,更是象征意义上为天津(乃至中国)沦陷的悲鸣哀嚎。个人、家族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苦难紧绑在一起,而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
上述的情绪高潮后,本片结尾阶段的一扬一抑再显编导的功力。侯家收到宣之的来信,原来他意外获救。在信中他向婉儿挑明了感情,并热切召唤她去处于大后方的长沙再续前缘,与两首诗里无意识的呼唤前后照应(这是一扬,之后则相反),但对婉儿一个文弱女子来说太不切实际了。电影最后一个镜头看起来唯美,灿烂阳光下女主角抚琴独奏,但画框里的宁婉儿实际是在侯家院门院墙围成的封闭空间里,那孤寂的琴音正照应着当年她深夜独守空房时的弹琴自娱。现在两情相知,却无缘厮守,活着的宣之更令宁婉儿难耐相思之苦,比之《红楼梦》里“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她的痛苦没有解药。
宁婉儿没能自主地选择婚姻,她不够独立勇敢,不敢离婚,不敢光明正大地追求爱情与人生,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道德伦理的约束下,选择离婚并与自己的小叔子结合是极其离经叛道之举。宁婉儿不完美,但她所代表的受到良好教育、矜持委婉、以柔克刚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一种无法重现的古典之美,她们的气质、神采与风韵,注定随着时代变迁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而香消玉殒。
附片中的两首诗:
走出来吧
夜,无尽的幔帐让你迷失方向,
墙,冷酷的阻挡锁住你年轻的心房,
星,软弱的照亮不能带来一丝希望,
走出来吧,冲出夜色,
突破围墙,跟随星光,
走出来吧,迎接曙光。
危城
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雷电和飓风袭扰了它的安宁,
余我在空无一人的街头徘徊,
困顿中寻觅你的倩影。
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忧虑和愤怒坏毁了它的天庭,
盼你从遥不可及的彼处现身,
暗夜里带来我的明灯。
《危城之恋》观后感(五):一片《危城》未畫成……
导演大概并不同意我现场给的评论吧。
我說,這部片子我只打3分。
更重要的是,我說片子不應該叫《危城》,因為我看不到太多危城的意思——儘管導演將背景放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後,儘管也出現兵荒馬亂的場景,尽管报纸也写了时局……但,整部电影依旧没能铺垫出危城的感觉——
尽管,结局的时候,导演给婉儿送了一首萱之写的诗,诗写得很好,开头叫「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一、
婉儿穿过之前还与萱之路谈的拐角,来到教堂前。门对面的雕塑没有变化,广场一篇空无寂静。
静止了稍许,婉儿推开教堂栏杆——宁静瞬间消逝,毫无转折地,兵荒马乱立时呈现在教堂挤迫的空间……
整部电影与这个镜头完全可以对应。
前部分,片子在宁静中缓慢推进。二嫂婉儿与三弟萱之,以文会友。萱之却不知道会友的那位淑女就是眼前最谈得话的二嫂。画面清幽,有着日系的小清新,淡淡地将情愫慢慢铺垫和衬托。婉儿的灵慧与萱之的热情迟钝,因两个演员的气质相符而显得可亲。观众也不断地为故事中小俏皮情节而轻笑。
故事刻意做了两个细节。
在教堂中,婉儿一人分扮两角。左手扮做与萱之相知相契的笔友,右手则是代替萱之去会笔友多智的二嫂。那种被珍惜的喜悦演得放好,如同初恋的高中女生,完全不曾意识倘被揭破的可怕后果,及被家族发觉的阴影。
另外一个情节,是相别之夜。婉儿情绪激动,险险儿扑向萱之怀中。而萱之提起箱子走过大门,突然转回头,怔怔看着婉儿。知道是导演在暗示他的知觉,可惜从演员表演中不曾看出来。
两个情节看得出编剧导演的用心,因这都是小说中没有提到的——其实,电影早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与林希的原著几无相同细节。
在那么多的小清新爱情故事,甚至这个故事没有任何
我入场得比较晚,《危城》刚刚演到婉儿与萱之都开始讨论是否要约笔友见面的情节。
其后的情节都如同MV一般的小清新,是我喜欢的情调。直至快结束了,才突然地横插一笔——日本人侵略中国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了。
就如同我前面描写的婉儿入教堂前后的画面一样,转折得毫无过渡。整个情节画面猛然就加速起来。萱之离家,萱之被铺,全家救人,萱之的船被炸沉,婉儿哀伤而去……节奏驟快,生離死別不過在婉兒一個人獨坐庭院靜待消息中呈現,但卻不曾真正打動到人。所以,牟然的一年後,萱之來了消息,而婉兒已經不見蹤跡的哀傷就沒能把觀眾情緒推向高處,仿如那美好故事與後邊離別是兩齣不同的戲碼。
二、
林希原著中,婉兒其實內心強大,有膽量與學識,傳統家教中出來的叛逆者。原著特別安排她作畫,唱昆曲(竟然唱了我最愛的那段杜麗娘的詞),還有臨最後向大嫂的那段告白,甚至對萱之毫無城府的擔憂,都教人唏噓與佩服。
相比之下,電影中的婉兒則如小家碧玉,初入大學,未諳世事苦艱。女主角其時正坐在我這排,氣質與形象同電影一般無二。導演說拍戲的時候,喜歡按演員的情緒走,大概英雌電影就成了與原著完全不同的故事與味道。
而萱之的形象与小时候读《家春秋》中的觉慧对上号。而原著中的萱之更有古樸感覺,因了小說中描繪他吹笛彈琴。電影中他更多的是打籃球,甚至一度我把他當成了《山楂樹》中的那個女主角了。
但印象最深的卻是大哥去南開大學探聽萱之下落之後,回來那種興奮的摸樣,一口天津腔說得極好聽。土匪二哥陳述救人流程的那段也很有趣,一氣呵成。
三、
观影结束的时候,告诉导演说他的《危城》和《天津闲人》都是我喜欢的电影。
这是真心话。我从这些好看的画面场景,精心安排的细节情节,还有演员的表演中看到真诚,也看到我喜欢的很多元素。
其實,豆瓣不能打半分,我想打的是3.5分。因為整部電影大部份給人留下的感覺是一部拉長了的MV。兩個人筆友相交的情節並不新奇,鋪排的雖然有條不紊,但依舊未能從中道出什麽內涵來。
想起《感官世界》中,雖然多是室內男女故事,卻偶然出一個男主角在街邊與皇軍擦肩而過的畫面,整個大背景就被帶出來,而在這種不是隱現的背景中,片子才給人有了沉重與別的情色片差別的感覺。
原諒我以此做比,只是爲了說明,《危城》拍得斷了節,如果婉兒與萱之的交往中,不時地能讓讀者感受到大背景,那麼他們之間的那種愛情就不僅僅是小清新,而會被賦予更多含義,結尾也不會顯得窘迫與匆忙。
四、
導演用40多天,就拍出了《危城》《天津閒人》兩部電影,而且畫面與質量都很不錯。
真心佩服。
所以挑BUG顯得有些不仗義。
但忍不住還是寫寫:
萱之與婉兒見筆友那段情節,後面背景走過的人,幾乎都一樣打扮,提著相同的行李箱,走著相同的匆匆步伐,好生彆扭。
七七事變發生的時候,大家穿得竟然依舊那麼厚實。——後來導演說電影是在冬天拍成的,那麼我也無話可說。
另外,教堂前的場景真的很像天津意大利風景區的羅馬廣場……導演竟然說全部是在上海拍成的……
五、
小說中昆曲唱的是:
「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與小說基調相符。
電影中用「我的心,是一座危城」是現代詩來做結,可惜,整個基調不曾合拍。
《危城之恋》观后感(六):笔记
[危城]和[天津闲人]是姊妹篇,改编自天津本土作家林希的小说,故事背景放置在七七事变前夕的天津城,一个是旧封建家庭中两个知识青年/新青年的爱情,一个是市井小人物的倾城之恋。[天津闲人]果断是2012看过的最棒的国产电影,电影语言颇为复杂,这里按下不表,单说说[危城]。之所以提到[天津闲人],是因为在两部电影的比较中大约可以看出大圣导演(可以叫他猴导么……)的一些硬伤。
[危城]最大的问题是结构,从一个小清新的爱情故事陡转到抗日,尽管前半部分埋了一些伏线,但以婉儿赴约误闯医院(教堂?)一场戏直接转场到抗日还是过于突兀了,毋宁说还有一个“峰回路转”的大团圆结局(尼玛,这片子既然进不了院线搞这种幺蛾子干嘛……),真是四分五裂啊。遗憾,太遗憾了。
也直接暴露出导演对剧本的把握能力电影结构的掌控仍显稚嫩,[天津闲人]的好也在于它有一个极其过硬的剧本(编剧伟大,其实和[危城]有一个共同编剧的),最后闲人和说书人戏台相见一场根本就是神来之笔!
除了三个大的情节点缺乏足够的铺垫,电影里插入的纪录(图)片的节奏也有些问题,很生硬。
其次是演员的表演。婉儿的表演略显稚嫩,却绝对称得上是钟灵毓秀的可人儿,加分。去搜了一下她的扮演者闵春晓的资料,她的博客里有很多自己作的诗词,腹有诗书气自华便是如此。
但,男演员……那就通通拖出去枪毙好了……其实在看前大半部分的时候甚至产生了猴导是不是在致敬文明戏的想法。。。同样的问题也出现的[天津闲人]里,但那种夸张的戏剧化表演与角色本身的无赖地痞气颇为切合,不至于影响电影的整体品质,相比之下,闲人里女主的表演更弱。话说回来,[危城]的问题就在于导演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表演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里呢啊啊啊啊啊!!!!为什么导演如此钟爱这厮小品式的男演员呢呢呢!!!以至于到了要致整个小清新于滑稽的地步么么么么么…………
好了,发泄完毕。说说这部戏里让我觉得不俗的地方。(这才是想写这篇笔记的原因)
[危城]最妙的地方在于猴导是以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建构视听语言的。[天津闲人]里的语言很惊艳也很繁杂,但却缺乏[危城]这里对电影语言民族性的探索,闲人里更多的是呈现出导演的西学背景,很多欧洲艺术电影语言被创新再运用。但[危城]以四合院的结构(门廊、庭院、隔扇、藤蔓等)布置了摄影机运动,四合院成为真正的幕后调度者,国际化的电影语言以这样别致的方式融入到四合院——融入到天津古城之中。
猴导一直有意探索镜像的表现功能。举两处精巧的运用。一次是家宣和同学拍话剧,在阁廊上与闺中的婉儿对话,镜头在婉儿背后,通过桌上的镜子反射出婉儿的表情。镜子在这里恰好起到“隔”的作用,把婉儿的羞怯及与家宣之间微妙的心理距离把握地恰到好处。一次是晚上婉儿在闺中以“知音”的身份给家宣回信,摄影机从侧面拍摄婉儿,同时镜头捕捉到对面门上玻璃中婉儿的镜像,闺中的寂寥在镜中影影幢幢地落下,而写信的亲密与这种寂寥的对比深化了电影的情感结构。
这部电影还在有意地探索对光线的呈现,最著名的一场戏是婉儿的第一次赴约,她与家宣在草坪上的谈话光线变幻极为细腻,美妙动人。多次强调光线,可见导演在布光上还是很下功夫的。
出现了不止一处“上帝视角”(大约三四处),但处理得很有新意也很微妙,与人物变动的心理相得益彰。
还有一场戏是我特别喜欢的,拿出来单独说说。婉儿听到家宣意外身亡的消息悲痛难捱,抚竹哭泣。这里用竹子实在是太妙了,因为它看似纤细实则柔韧,且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竹子一直象征着一种挺拔高洁的品格,更有趣的是,竹子常常用来比拟男性,而电影用它来印衬这个柔弱却内心刚强的女子,景语即情语。
最后,还有一点疑惑,电影是以婉儿为叙事主体呈现整个故事的,但它的叙事似乎并没有明确主观视点,(亦或是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总之整体看下来觉得视点略显混乱。
《危城之恋》观后感(七):兰萱一梦
——记 电影《危城之恋》宁婉儿 心如危城,雨朦胧。 孤琴幽声,怀故人。 兰香清冷,相思渐浓。 花上尘,只一瞬,风过无痕。 兰萱入梦,错相逢。 云间书文,隐情衷。 残夜一程,原是浮生。 君若问,乱世沉,明灯。
这首词是两年前写的了,灵感是一部电影:《危城之恋》。两年前看,被虐得很惨,两年后再看,还是难过到落泪。
很雅致的影片,所谓阳春白雪,知音之情。加上古色古香之美,各方面都很称我心。于是翻出了这首两年前写的词。来纪念这部可以说是我十分难忘的电影。
缠绵悱恻,与君再难遇。
另附上剧中我很喜欢的新诗: 《危城》林希 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雷电和飓风袭扰了它的安宁 余我在空无一人的街头徘徊 困顿中寻觅你的倩影 我的心是一座危城 忧虑和愤怒坏毁了它的天庭 盼你从遥不可及的彼处现身 暗夜里带来我的明灯
《危城之恋》观后感(八):用熟滥的煽情来诠释闷骚
《危城之恋》。由于“之恋”两个字很小,还是红色的篆书印章,闹得老花眼的豆瓣上只是电影《危城》。
3月11日的凌晨两点在电影频道播出。
电影频道出品。郑大圣导演。一看片头这两样,顿觉索然。
电影频道按理说有可能拍出好东西来,至少它是严肃的,不是香港老油子,又没有观众票房压力,可以完全不管观众,拍出艺术家自己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它大量出品垃圾。水浒系列,就是用了原来的人物名字,情节完全瞎来,朱仝与雷横拍成了主持正义的探长与贪官县令的生死搏斗,金枪将徐宁拍成了梁山好汉从牢里救徐宁的经过,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有病。
郑大圣,名字一看就记住,所以记住了,别的电影电视的导演,都没记住。有一个“下半身诗派”的女诗人,改邪归正拍起主弦律电视电影,叫马什么,我就没记住。(这女的,跟那个香港脱星当了省“政委”放言要拍主旋律影视有的一拼。)《大众电影》介绍说是黄佐临的外孙、黄蜀芹的儿子,父亲是美工师,这就印象更深了,名门之后。不久前电影频道放了他导演的电视电影《天津闲人》,我看了,拍得很烂,前后风格不一致,抗日部分狗血得滥熟恶俗,人物性格的变化完全讲不通,看到后面实在看不下去了,电视机开着做别的事去了,导演郑大圣1968年生,名门之后,45岁了,正宗大叔,居然拍个电视电影还这么青涩,还真比不上香港老油子。再一查,我特别反感的一部现代派的雷人狗血获奖电视电影《王勃之死》就是他拍的,这下前仇旧恨涌上心头。因此,我对郑大圣印象很不好。
两个不好碰一块儿。这片子果然看不下去。其实,我不是很挑剔,今晚上前一部《爱情钥匙》我就看完了,再前面23点改掉《骑弹飞行》而临时插换的《白头神探2》我也复习了。问题是,这《危城之恋》又闷又煽情又不靠谱。
闷在小叔子与嫂子的朦胧暗恋,这情节不吸引人。里面充斥了煽情,很不舒服。全片真实感很弱,各种不靠谱,画人人不像,画鬼鬼不像。比如在父亲的寿宴上,二哥带了个“大露露”回来要求父亲同意自己娶妾,三弟则站起来护住二嫂,当众劝二嫂离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煽情完全是台湾电视剧的风情,而真实感更是不存在,天津封建家族里是这样的吗?已经这样煽情了,女主角只是默默流泪,什么别的反应都没有,完全不出所料,闷到极致,无趣。
相比之下,原著小说林希《醉月婶娘》就好得多。里面的大家族,很多很多人,不像《危城之恋》老太爷寿宴仅仅两个少爷两个少奶奶(老二不在,老三未婚),不是大家族,只是个小康人家,假装封建大家庭。也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仅仅最后婶娘的死很戏剧化(该煽也得煽一次),不像电影里时时刻刻煽情,除了家庭矛盾还用抗日来煽情。原作是真正的优雅,电影是十分滥熟。
煽情煽得厉害,却不给出路。原作里,婶娘的父亲在北京好好的,“二土匪”则成月成月不回家,几十年不进她的房,她过的也还平静。电影里她父母双亡,只有一个穷形恶相的叔伯哥哥,等于无家可归,都已经说出“离婚”了,却缺乏物质基础,而丈夫回来抢家用,搜寻陪嫁的古书,在家里也让她活不好。这样改,真是压抑。(要一笔钱,离婚了先搬出去租个小公寓,而后找个人另嫁,只有这条路了。而且历史上似乎不少人都走得好好的。)
后来看评论,说是《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只用了四十天。不知是一部戏四十天,还是两部同时开拍四十天。
总之这个片子,既没看出导演的追求,也没看出导演对观众的尊重。要么你有艺术追求,不在乎观众,就是《王勃之死》那种变态恶心的作品,令人反胃,但是能得奖,而且写评论骂都能挑出东西可骂。要么你拍一部观众看了喜欢的作品,看完之后真切感受到精神愉悦。
拍到了四十多岁,似乎导演对电影的领悟,就是煽情。原作里二土匪不成器,电影里就加上带舞女给父亲拜寿,抢老婆家用。原作有抗战背景,电影里就加上处处口号,在自己家里也大喊口号。电影增添最大的情节是主要故事:二嫂冒充读者化名给三弟写信。这里也被拍得喊喊吵吵的。其实生活中接到自己心悦的笔友来信,多半是悄悄的一个人看。
有个可爱的胖小子叫侯红鹅。这就是作家林希的本名。小说里就是姓侯。可惜胖小子后一半失踪了,导演真心糗。
《危城之恋》观后感(九):《天津闲人》与《危城之恋》
《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讲述了在1937年间沦陷前的天津所发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天津籍观众孙炎在观影后说:“一个下里巴人,一个阳春白雪,搭配起来,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这座城市的精、气、神”。豆瓣上很多热爱电影的网友在帖子里评论,这两部电影在艺术语言上流畅细腻,并且内涵丰富、深刻,令人回味,“将天津这座城市的味道、天津人的特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还有不少网友认为,影片“是近期国产片的佳作”,“国产电影这样拍才有看头,有希望”。原著作者林希在看完两部电影后对改编很满意,并表示,“‘百年百城’是一个富有想象力、极富活力的创意,它选择了近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来改编,展现这些作品中表现的城市,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文化背景,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源于文学贴近民生的生命力,又预示着将来文学走向世界,无论哪一个都是一件大事情”。
《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的导演郑大圣出身于电影世家,外祖父为《腐蚀》的导演黄佐临,母亲是《围城》的导演黄蜀芹。或许正因如此,在他身上也有着很深的文学情结。郑大圣认为,按照他的理解,作家出版社类似于德国的兰登书屋或日本的角川书店,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团结着全国最大数量的作家,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营养”的积累,同时,它也应该最能发现或者说最靠近好的叙事作品的源头,即好的小说、好的故事。拍电影的人永远都在寻找好故事,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总能找到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他最为注重的,也是文学电影应有的品质。他说,虽然《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可以说是“三无产品”,一没有大明星,二没有视觉奇观,三没有明确的类型符号,这三点就明确了它们不能是主流的商业影片,但这恰恰是文学电影的一种自觉。郑大圣说,作为“文学电影”很难有非常大的投资,所以在这两部片子里不能够做出一个城市沦陷的宏大场面。而且,作为文学化电影的自觉,也不需要那种CG特效。在影片里不需要看到建筑物在崩塌,难民潮在涌动,在处理“沦陷”这个主题情境时,他采取了更文学的方式:不要物理上的沦陷,而是要从精神层面把它体现出来。这是一种文学式的解读,也是在创作中的一个美学选择——当硬件不足时,就在美学上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郑大圣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是一部“贫困”的电影,但绝不是一部思想“贫瘠”的电影,这个并不矛盾。而且,观众对文学电影的诉求也并不是视觉、听觉等感官体验,而是有着更深层面的需求。
《危城之恋》观后感(十):高山流水觅知音
高山流水觅知音
TT:
前些日子我忽然接到一个开会通知,到北京去开一个关于电影的会。我就很激动。人很好玩的,工作的时候我最怕的事情一是开会,二是填表,但辞职之后有会可开,又产生了一种还没有被行业遗忘的安慰感:)。开完会后有一个饭局——这是一个巨大的饭局,二十好几桌,像婚宴一样。我认识的人很少,偷偷东张西望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光头特别眼熟,但因为是一个光头的后脑勺,就也不能肯定。正想着过会儿绕过去确认一下正面,他就转过身走过来了,呀,真的是郑大圣!
十年前,正好是十年前啊,2002年我刚到北京,常常参加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组织的观影活动看电影。有一回看到《王勃之死》,觉得真好啊,写了个小影评贴在网上。不久后的一天,在清华附近的盒子咖啡馆的另一个活动里遇到了郑大圣。我们聊了几句天,我说:“我叫苏七七。”他想了一下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影评,作者叫苏七七……”我笑起来说:“那就是我啊!”——我们一下子就像认识很久一样地说起话来。这真是美好的一种导演与影迷的关系,纯粹的欣赏,真正的理解,一下子就带来了一种亲密感。
多年来我们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来往频率,我看他的电影,他有时也看到我写的文章,再上一次见面,居然要推到七年之前了。他在绍兴排了一出越剧《唐婉》,我去看戏,看完戏我们和演员啊乐师啊在路边摊聊天聊到快天亮。戏,电影,生活,好像因为见面的频率很低,就要做到每次聊天的密度很大,质量很高:)。
然后就说到我们在巨大饭局上的重逢啦。我坐的这一桌有一个他的熟人,他走过来跟那位姑娘重逢拥抱了一下时,我就像在边上排队似的,也等着跟他来一个重逢拥抱:)。他说:“七七,是你啊!”每次我们都既很意外,但又像在意料之中一样,遇到了。他还是一点也没有变,在电影上,他能让自己认真,沉着,能干,胸有成竹,但到内心里,他有他永远不愿意长大的小男孩的那一面。我在想,他的这一面对他的电影是不是有影响呢?
这次见面后,我回去在1905电影上找了大圣的一个新作看,片名叫做《危城》。故事背景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一个传统大家庭侯家,大少爷能继承家业,三少爷是革命加文艺青年,二少爷却是一个粗暴横蛮的逆子,父亲作主为他娶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姑娘婉儿,但他已经在花街柳巷有了相好,对婉儿不屑一顾,从不回家。婉儿在侯家的平常日子不过是浇浇花,写写字,课侄读书而已,三少爷萱之常在报纸上发表些新诗,并请婉儿评点,婉儿不愿当面评点,却写了读者来信到报社去,成了他的笔友“兰小姐”。这两个人,一个满怀豪情却少不更事,一个兰心慧质却孤苦伶仃,他们之间的处境,是白先勇玉卿嫂式的处境,但他们的情谊,却被描写得优美,纯净,很少在华语电影里看到这样的爱情叙事。
——这个电影真是很难写剧情介绍,因为这么写下来,实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地方,但这个电影却是很好看的,并且很感动我。为什么呢?因为郑大圣拍出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人与一种特别美好的感情,而且他拍得非常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一个反封建情节剧的框架里,郑大圣却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情怀,他拍出是古典的美,却有生机与灵气,他拍的是小儿女情怀,却有林下之风,浩然之气在里头。
我很少在当代华语电影里看到导演以诗人为主人公,但郑大圣却拍了两次——一次是《王勃之死》,拍一个古代诗人,一次是《危城》,拍一个写现代诗的诗人,而且他都是从很正面的角度去拍诗人,对一个诗歌在文化版图中日益边缘的时代来说,郑大圣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与坚持。诗歌是什么呢?在他的电影里,诗歌总是向着美,真挚的情感,和自由。婉儿与萱之的爱情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上的,她从他的诗里读到自己,而他从她的信里读到对自己的理解。在萱之的同情与支持里,婉儿的自己能更焕发出来,她原来只是显得那么柔美与柔弱,但慢慢地,她在柔美与柔弱之外呈现了更多东西,她其实是那么聪慧的,有学问有见解;她其实是那么勇敢的,偷偷出门去寄信;她其实是那么可爱淘气的,把萱之哄得团团转;她其实还有心底的侠气,能将一生酬知己。她就像片头里那一株兰花,那么柔弱,那么容易就像要被摧折了,可是略微地有一点阳光雨露的护惜,她就静静地开放了,一室含香。
这是婉儿的美,她的美近于一种美的理想,但在电影里却是有生活气息的,可以着落到生活中去的,她的内心的凄苦,雀跃,欢喜,伤怀,她最后在萱之书房里的徘徊,都是看电影的人可以从内心共鸣的吧。而婉儿与萱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爱,却又不止于男女之爱,他们是什么呢?是知音。高山邈邈,流水杳杳,这份情怀是超乎男女之情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用这个打底子的,因此,这个爱情戏拍得不俗气,不是打了柔光的“纯爱”戏,不只有你猜我猜或者你侬我侬,它要大气得多,深远得多。
在《危城》里,大宅门并不是一个樊笼,相反它倒成为一处荫庇之地,有长嫂理家,有小侄顽皮,有萱之找她很唠叨地说这说那,说对“兰小姐”的仰慕。婉儿的琴与书,本来就该配这样的地方。然而城危矣——一个是内心的危城,叔嫂之爱,一个是外在的危城,家国之恨。在情节的设置上,恰恰在外在的危城化解了内心的危城,萱之得以走出“城”,因此从城外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给了电影的一个美好的期待的结局。
但这也是我对这个电影表示一点儿不满足的地方,因为这个电影的主题,我觉得完全不在叔嫂之爱或家国之恨,它既不是一个反封建伦理电影,也不是一个爱国主义电影,而《危城》这个题目,却混淆了主题的方向。为了把情节结构搭得结实一点,还费了些很笨重的镜头去拍婚礼场面与国难场面,这个电影的语言,在描写人物之美与情怀之美时,都是既从容又轻盈的,但一到要进入情节关键时,就显得刻意笨重起来。这个情节框架也许是必要的,但它与内在的人物与情怀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更好一点的平衡关系。
在当代电影导演里,我所喜欢的郑大圣和娄烨——这两个人的风格真是截然不同,他们都是长于拍女性的,郑大圣能拍一种理想的美,但他的好处在于,他从不在电影让这些女性替男性去担负什么,这种美像是独立的,如露如珠,微光恒照,而且他能从生活细节中拍出这种美,可见他对这种美也并不是得之于想像,而是来自于观察与欣赏,这种理想是连接着生活的理想。而娄烨呢,他能拍真实的女性,在生活中挣扎的,在情感中挣扎的,姿态都那么不好看的,他总是拍做爱中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是与肉体的痛感快感纠结在一起的。她们无望地满怀着生命的渴念。
真是奇怪啊。TT,女人是有这两面的,这两面一样的真实。
七七。
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