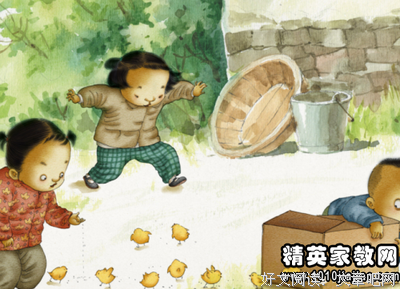禹域鸿爪读后感1000字
《禹域鸿爪》是一本由[日]内藤湖南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路上看的书,文风隽秀语言清新,也兼具哲理,半文半白看得有些难受
●2018年已读061:内藤湖南的汉学修为着实厉害,他的中国游记绝非简单的山河形胜、世俗民情、古迹凭吊,而是旁征博引、古今穿插,赋予无生命的风景以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意蕴,并从今昔对照中发怀古之幽情,写盛衰兴亡之嬗替,展现了一名学者的博识与关怀。对作者所写北京的风霾晦暝、江南的劫后凋敝印象深刻,风物之外,臧否人物,评骘时政,与众位名士的笔谈、对晚清积弊的洞察、对折冲御侮之策的建议,皆言之恳切,认同他对康有为的评价: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
●“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最新一期单读“艳遇图书馆”,许知远推荐了内藤湖南大师的《禹域鸿爪》——“我更热爱那个假的苏州”!
●学者的中国游记
●1899.1902.1918三次来中国的行迹
●19.09.14 01A翻译相当到位,有意思的。快速阅读。
●是譯者太厲害還是原文就是古風???
●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无限倾心,与对清末中国和满清统治下如蝼蚁般的中国人的鄙夷之情混合于其书中(尤其是对有清一代中国文明的堕落和康乾之虚假盛世的讽刺十分入骨)。其汉学功底之深厚令人不得不佩服。
《禹域鸿爪》读后感(一):史家眼中之旅行中国
这本书是和之前看过的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一系列的。相比润一郎文人的寻色之旅,我更喜欢湖南先生的访古之行。
史学家的眼睛是可以穿透空间的禁锢,上溯千百年时光发现一个地方的历史与趣味。他所走过的地方,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我几乎都去过,北京南京又分外熟悉,而在他的引导下再去看这些地方,觉得自己根本不算在这里去过生活过。我们普通人是活在短暂的现世里的,而先生这样的人是活在几个时空里的。
我觉得很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化都有着深深的乡愁似的东西,先生不例外,而且尤胜。在学生的评价里说,湖南先生厌恶许多东西,而所喜好的: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虽如此,先生在旅行途中之所见闻亦多有批判。对于中国的衰落,他是痛心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也是关切的。旅行之余,他与一些智识高尚之人以及社会名士也多有交流,以此了解中国之现状以及知识阶层对于未来之打算计划,对于一些名人也自有评价,由此,我有了对原本历史名人的新认识,也认识了一些历史上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颇有学识见解的人物。
从戊戌政变之后到1918年先生三次来中国的见闻里也可看出中国在这十八年前的许多变化。南京明故宫毁了,砖瓦树木被政府卖了;曾文正公祠堂毁了,成了革命烈士祠堂,在此他表示了自己的痛心,也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尝获救助者为谁,中国人之于当时救济其地其民,即有大功德于世人者,均极易淡忘。对于政府不能出面保护古迹,先生也很无奈。中国没有保护古迹这一传统,历来前朝之物若无实用,不破坏算好的了。这与日本大不相同。日本人特别注重传统传承,故而他也提到书法之变化,日本依旧保留六朝唐之笔法,而中国人已忘记了,多年变化早无古意。
总之,这是又一本丰富我知识,愉悦我情感之书。
对了,译者也是相当厉害之人,译文很符合先生之汉学家史学家之文笔。
《禹域鸿爪》读后感(二):阅读记余
这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的书装帧很漂亮,带有纤维质感的封面和洒金的装饰很有日本的感觉,而略显圆润的字体由使它不至过于严肃(在一本书上同时看到这种可爱的字体和内藤湖南先生的脸有种奇妙的感觉)。
整本书中最喜欢“鸿爪余记”部分,语约意丰。我想,内藤湖南先生作为外域者,在短时间内游历了从北到南的中国,因而会对中国的南北风俗人情差异有直观的体会,再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南北差异的产生,写下了很具有启发性的小札记(是否正确暂且不论),譬如《家屋之结构》一篇结尾:“概言之,江南之家屋多用木材,不若北方之多用泥土。其竹椽茅屋之贫穷人家,与吾邦相仿佛。在此不妨披露一独断之史论:南方人种,本与吾邦相同,属来自热带之茅屋人种;北方汉族则由穴居进化而来,住土石造家屋。文明开化之播布,由北极南,故南人亦次第住进土石造家屋,以至其木造家屋之制式,亦当日益模拟土石屋建制矣。”
而《南北之字体》一文亦由南北人之性格不同而论字体差异:“北人质朴,近于迟钝,每事忌变移。南人轻锐,多儇薄,每事喜新异”,因此北方店铺招牌多馆阁体,而上海张贴启示多六朝风字体,“此虽琐事,实南北风气夐异之不可遮掩者。”
大佬就是大佬,即使出来游玩,走的还是歪果仁经典旅游线路,亦时常有感,行文中杂有考据。
书前有施小炜先生所作总序,对如何正确看待外国人所作中国游记有精到阐述,谨摘录如下: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迷人的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较好方才心满意足么?”
《禹域鸿爪》读后感(三):读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记略
新购浙江文艺出版社“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游记四种,读了两种,内藤湖南氏这本是第二种,按照译者李长声的说法,也是“唯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正是这个缘故,这本书读得稍稍艰难些,文字密度太大,很难一目十行,只能一字一句地啃,还要不时反顾,前后对照,加上随手查找资料,方不至于遗失太多信息。饶是如此,自忖所得仍是十不足一。
内藤氏看世界是能见其大的人。友人野口宁斋称其“书卷在胸,山河在眼,语不犹人,理固当然”,并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吹捧之词。内藤氏与中国诸名流的笔谈记录最可见出这一点,即以与张元济笔谈为例,谈时政云“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不论可行与否,至少着眼点是大的;谈世风云“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又云“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等,都是切中肯綮。因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品评人物更是肆意敢言,说张之洞“其人亡则其政息”,康有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梁启超“恃才自炫,……为人低鄙”,皆足发人深思。
内藤氏也是有野心的人。他游钟山而有感慨曰“且如钟山,山不甚大,而富于雄特之姿,远近野色,百里高城,策马于孝陵庙前至朝阳门一带之高原,令人追怀驱驰千军万马、旌旗蔽野之古时英雄。我尝语于本愿寺一柳氏曰:为金陵总督者,若不起谋叛之心,其人想必庸愚。”这番心思伸展开来,怕不就是“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如何”?
内藤氏身处日本兴盛的时代,面对积弊丛生的邻邦,不免有种种优越感,加上读书人的清介,鄙薄嫌憎之情表露无遗。最惹眼的是这句:“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得不快”。与中国名流交接,他的态度却又算是谦恭有礼。见肃亲王善耆时,基本都是恭维之词了:“亲王及王世子,风采皆极拙朴,犹以亲王为甚。……其谈话亦极快豁。作微笑时,则洋溢一种爱娇。”这样揪出两个极端例子来比较,似乎有误导之嫌,但对寻常人作恶劣嘴脸,确实让人很不舒服,虽然他宣称“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但还是得承认,内藤氏真是能领略中国各种好处的人。如谈长江沿岸景致:“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百里绵延不绝。时方孟冬,叶枯花开,似霜如雪,极目无涯。”又谈北京鸽哨:“若远若近,浏亮悠扬,声自天半坠下,闻之真有若空中鸣銮。”其余如谈当日最常用的门联为“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商家则多用“越国大夫增贸易,孔门弟子亦生涯”,虽不无褒贬,却是我在别处没看到过的旧日街衢景象。谈南北店铺招牌,京津尽为馆阁体,沪上则多半为秦篆、汉八分、魏晋楷行,可见其人处处留心,在我也是颇增新知。
对翻译满意,因为很难期望更妥帖的文字了。
《禹域鸿爪》读后感(四):译后记(李振声)
《禹域鸿爪》著者内藤湖南的一些背景性传记材料,这套译丛的策划人施小炜先生,在其所撰的《总序》中已有很好的论列,读者自可从容参读。我只是想补上一句,《禹》是收入本译丛的这几种书里边,惟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学者有学问垫底,游山观水之时,始终不会忘情于史地的考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般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骞翮远翥的学术视野。于深情回眸间贯穿学问兴味,在流连忘返中蕴含明慧关照,本是内滕湖南这种不世出的学者所独擅的胜场。但随时随地,总要倚重书袋,比起单凭直感的长驱直入,走访者之于山水之间,终究多了层间隔,而讲究旁征博引的结果,又不免会让行文显得滞重。凡事有得有失,原是世间常理,更何况,乐山乐水,无有定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相信喜欢这种类型的游记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还有一点,也与著者的学问颇有关系。内藤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这本书又写于差不多百年之前,原著用的是一种颇带古奥气息、文笔专骛渊雅的文言体日文,因而转译时也让译者颇费踌躇。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百年前中国世事世情的文化史料,将其译为平白直爽的现代汉语,反而觉得跟文本原有的性质不相对称,倘若某种直接就能提示其历史感的东西,却因为转译文体的不相称合而致使那份本可直接感知的历史感就此流失,这无论如何也是件遗憾的事。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这本译书最终还是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文体,虽然半文不白,两不讨好,但还是希望读者诸君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地对译者的此番用心,多少有些体察与谅解。
1907年(明治四十年),京都大学创设东洋史讲座,内藤应邀讲授中国近世史,由报人(先后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等报刊记者)转型为东洋史学家,并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共创二十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京都学派”(另一派则是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内藤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史学上提倡清代实证史学;“唐宋变革论”则是其在中国史研究中所提示的富有魅力的话题之一,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其在敦煌学与中国古代书法、绘画方面,也均有独步一时的专门研究。学风阔达,造诣精深,尤其是思路、方法的独到,确立了内藤在日本东洋史学发展史上开山与奠基者的地位。其主要著述《读史丛录》、《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近年已多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翻译出版,读者诸君自不妨留意参看。与那个时代日本一众东洋学研究家一样,内藤湖南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其时现实中全方面羸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这在收入本书的内藤的几种游记里,几乎在在可见,读者诸君自不难察识。
译者谨记
1998年清秋草,2016年暮春稍改
补记未译入本书的内藤湖南与中国游历有关的纪行文字,尚有《韩、满视察旅行记》、《北韩、吉林旅行记》及《间岛、吉林旅行谈》等。
《禹域鸿爪》读后感(五):内藤湖南与张元济对谈记录
汉口归来,滞留上海仅四日。其间,与罗叔韫振玉讨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刘氏学询谈论时务,乃成此行最后之佳兴。张氏乃戊戌政变以前,与康南海等同为湘抚陈宝箴等所保荐之五人才之一。时年三十三岁,浙江秀水县(即嘉兴府治)人氏,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在北京时,尝创办通艺学堂,引导后进。颇通英文,盖亦江浙间之才俊矣。与其所谈如下:
张 先生此行,由苏杭至武昌,共勾留几旬?途中起居,安好否?
我 弟苏杭之游,勾留二礼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观南中民物蕃盛,与京畿夐然不侔,窃以为将来甚有希望。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放言为彼之势力范围,我以为乃贵国士大夫之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张 国事至此,夫复何言?!先生曾上北方之长安乎?何匆匆言归,而不作北地之游耶?
我 若为秦、蜀之游,当须半岁。今时迫近岁杪,归心方急,只得将之留待他日矣。意想关中民物,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亦无能如江南者。近日如康南海,乃倡一度迁都关中之说,甚为弟所不解,不知高见如何?
张 关中王气已尽,迁都之议,中朝士夫,亦有言之者,则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耳。康南海近时亦作斯言,且不说此事之无法实行,即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亦必出而阻挠,而将来宗社之重地,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我 忸古难移,乃贵邦在朝之大弊。迁都之议,暂且不论。以弟之见,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之捉襟见肘,意想此亦为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此形势之谈。若夫人才养成之说,固然有较此更为急迫者在焉。
张 南方各省,为自卫之计,此自大有可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业?其有权者,非特不敢为,且不敢知。知之而敢为者,又一无凭借。草泽奸雄,虽无处蔑有,然皆犷悍无识之流,又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且南方民物富庶,财力似尚有余,而民智遏塞,与北方无异,以此自卫,恐亦难也。先生游苏杭、溯长江而达武昌,内地民风,亦略见一二,岂能足以自立哉?悲夫!
我 贵邦地广民庶,弟窃观其士人,亦自有大国规度,惟忸古之弊,遽难改易耳。泰西新政,即今日行之,恐未享其利,而其弊亦已随之而至矣。陶铸士风,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此绝非朝夕之谈所可解决之事。闻先生方从事于培育精英,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南洋公学生员规制,未知能得闻其一斑否?
张 高论极佩。弊国前四十余年,即已有变法之说,所效法于西人者,其事亦复不少,然成效茫然。且今之所谓洋务人才,亦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不揣其本而仅得其末矣,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养为先也。我从事于南洋公学,专理译书事务,至生徒、学术,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督导。学期大约八年。普通政治学略备,现仅有二年程度,规模尚未确定。我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可请先生指教。
我 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意想数年之后,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如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矣。贵邦人士,义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
张 《天演论》一书,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喜读者亦不乏其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先生在武汉时,曾见何人?
我 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均未遇,其余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谒,然闻其礼数繁重,遂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其事固伟,然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此虽限于其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虽为创业之才,终非守成之器也。
张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当为不刊之论。亦曾读其《劝学篇》乎?
我 《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则于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贻笑于识者处。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然其切当处,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闻何君尚有《康说书后》、《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
张 《康说书后》等书,前也闻有此名,然上海无能觅购,当求之香港。坊间有《翼教丛编》,未知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我 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此其自限势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见如此。(张曰: 甚佩此论。)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于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
张 康之为人,欲以所学范围众人,转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自此以后,皆为蛇足而已。梁启超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
我 梁亦见过一面。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后,颇自抑损。然在敝邦,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仿而效之,且其太过自我辩疏,其攻讦西太后,动辄语涉猥琐。(张此处附言: 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适见其为人之低鄙,故为弟所不取。敝邦维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渐惯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张 尊论佩服之极。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见之否?
我 曾得一见。盖木讷倔强之人,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非能担当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祸难,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
张 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氏析居。
我 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未审近状如何。王君望乡之心甚切,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云。其情至可愍也。
张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1],未知今复如何?
我 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仍庇之。
张 畅谈大教,欣佩无已。先生明日即启程,未获畅叙,是为恨事。谨口占一绝,以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1] 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史称隈板内阁。1914年再度组阁,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