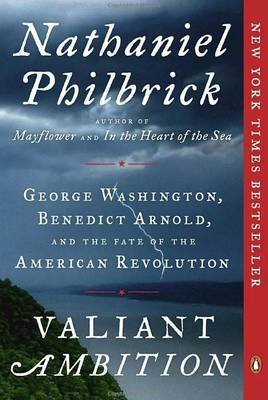《神武军容耀天威》读后感1000字
《神武军容耀天威》是一本由〔美〕鲁大维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武军容耀天威》读后感(一):田猎、骑射与明代宫廷内亚性的政治表演
鲁大维沿着爱尔森对欧亚大陆皇室狩猎传统的观察,回顾了商周以来中原王朝的狩猎传统。作者认为皇室田猎对于皇权展示、军事操练、政治外交有着莫大的助益。明朝政权巩固后,明初诸帝很快承袭了这一悠久而又普遍的礼仪、军事与政治传统。从永乐帝利用田猎构建自身皇权的正统性(“古者天子岁三田”)、发动对蒙战争(“肃清沙漠”)、展开与女真、蒙古诸贵族的外交。到宣德帝通过田猎亲近军事将领、笼络蒙古盟友,从而加强对北方军队的控制。明初的君主很好地利用了田猎活动实现了自身的诸多诉求。
《神武军容耀天威》读后感(二):【转】鲁大维:全球史视野下的明朝尚武展示
【摘要】明朝积极利用了各种媒体塑造并传播军事大典壮观场面,在信息科技尚未发达条件之下,皇帝希望借此与外界接轨,利用文臣诗赋的平台来传播圣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皇帝与廷臣之间冲突层出不穷,但是至少在明初时期,在颂扬军事大典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排斥了大规模军事大典,将其描述为极其虚伪、毫无实质意义之举,军事大典很难起到展现皇帝魅力、彰显王朝军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军事大典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它是一种消遣方式、一种运动爱好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政治符号、宫廷典制等。
明武宗在中东、印度、亚洲中部和中国,从古代到19世纪,皇家狩猎一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能够标榜贵族身份,皇家狩猎还可以起到外出巡查、促进皇室进步和确保皇室威严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组织良好的狩猎活动常被用于训练军队、展示军事实力和传达外交理念。《神武军容耀天威》读后感(三):【转】鲁大维: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
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
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年正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阔。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就是在他奠定中原内地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关于朱氏政权如何吸收邻近的人户和土地,如何建立有效的政治、经济、思想控制体系,相关研究丰硕,不需多讲。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明军进发到东北、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的时候,朱氏政权已经累积了比较丰富的边疆经验,对如何处理新占领土地、新归附人口等问题绝不陌生。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付大元政府的军事、政治以及文化权威,从而让新征服地区的臣民和尚未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弃大元而归顺大明,并不碍于忠臣观念。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多次强调“元运将终”、“胡运既终”,来概括新时代的政治环境。大元帝国已经完全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汉族、蒙古族、色目人等不必守节于大元。为了证明天命有所归,朱氏政权已经取代了元朝为正统王朝,朱元璋想方设法说服大元的各民族官员、士大夫以及老百姓,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归顺于明朝。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之一就是这种宣传工作,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赢得当地基层支持,第二是尽可能减少新占领地区的反抗。出兵北伐前夕,朱氏政权颁布的所谓《谕中原檄》就是一个例子。它断定大元已丧失天命,也因此失去了统治中原的资格。接着它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在此一刻,所谓边疆不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的,而是汉族和汉族群雄之间的边区。由此观之,说《谕中原檄》是朱元璋的早期边疆扩张运动的宣传工具似不为过。
同样,明廷征伐云南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军事需要是次要的。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梁王仍坚守云南,奉北方的元朝为正朔,并且每年遣使去漠北觐见北元皇帝,执臣节如故。除此之外,梁王管辖之下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回回、彝族、白族、壮族等。总之,对刚建立不久的明朝而言,梁王构成一种政治势力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因此明太祖数次派遣使臣劝降。同时朱元璋也知道1365年梁王冤杀大理总管段功。梁王和大理段氏从此之后势同水火,所以对段氏和其他土著势家展开思想工作,千方百计让他们抛弃元朝投靠大明。1381年9月,太祖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统帅30万大军进攻云南,半年之内,明军大胜,梁王和臣下或自杀身亡,或兵败被捉。但打败梁王只不过是云南建设的第一步,而当务之急则是设立有效的行政、军事控制以抚辑土著。因此,在云南等地明朝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设立了土司进行管理。
按照上述逻辑,我们也许会下一个结论,即明朝廷就应该把元帝国所有的臣民都变为新天子的子民,但是朱元璋并非如此。元朝领土远远辽阔于明朝,辖下各族臣民比明朝多得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明朝是如何决定国家疆域具体位置所在,它决定究竟哪些民族一定要纳入明朝行政机构,哪些可以任其自然。要解答这一问题,恐怕就要看元朝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蒙古帝国的哪一些地方和臣民编入了大元了,元朝后半期,汉族、色目人等士大夫多次颂赞蒙古帝国疆土之大、人口之众远迈汉唐,当时的地理书、地图等对中亚、中东、非洲,甚至西欧都有所提及。但汉籍资料表明,在汉族知识分子意识中,辽东、云南、宁夏与远离中原的区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元大一统志》、《经世大典》、《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等歌颂:生民以来,集大成而盛者,莫盛于孔子;有天下之广者,莫加于有元。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猗欤大哉。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当时连辽东、云南、宁夏等边区也建立儒学。朱元璋、朱棣等在许多方面都向元帝国看齐,所以既然想要在国内国外塑造正统王朝形象,赢得普遍认可,那么至少要达到元朝所建立的统治标准。倘若抛弃元朝所控制的,并且为汉族知识分子所认可的疆域等于承认新生明朝还不如朱元璋辱骂为丑虏的“胡元”。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
明朝中央政府利用卫所、土司等制度以巩固边疆控制的同时,它也力图让皇帝的恩宠与扶持,即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权威,从京师渗透到边区。这一政治策略包罗万象,在此只举一两个例子。明初不少边疆望族归附明朝后,亲自去京师觐见天子,将元朝所封赐的印章、诰敕等献给皇帝,然后接受明朝君主赐予的新印章、诰敕以及礼物。假如只靠明朝官方资料,采用朝贡制度这一概念去理解,这种仪式容易流于表象,显得空洞无物。但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即改朝换代之际,朱元璋试图用这一仪式建立君臣关系,让边区望族视明朝为正统王朝,让他们认朱元璋为自己的君主而非抽象象征性的君主,就是说构建个人君主关系,这与每次蒙古可汗去世,新可汗当权后,各地部属长官都要去京师亲自向新君主发誓要尽忠尽诚的仪式,具有同样的意义。无疑,明朝中央政府通过向边疆地区势家提供物质援助、经济资源,从而建立起“小君主”与“大君主”的关系,这也成为对双方有利的政治资源。另外,边疆地区的领袖去世时,明朝皇帝也要表示哀悼,譬如洪武十五年皇帝遣行人贾勉谕祭于指挥同知锁南之灵时说“惟尔世居西土,慕义来归。朕知尔诚,俾任军职。边陲辑睦,予惟汝嘉”(《河州志》卷三)。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也能说明边疆势家与明朝君主的关系。当然,久而久之,皇帝,魅力权威自然而然会转变为韦伯所说的常规的权威形式,边疆望族与君主关系便制度化了。
以上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央政府的立场,如朝廷如何利用卫所制度等拉拢控制地方,如何将皇帝魅力权威扩张到边疆等问题,但与此同时,土著望族也积极利用他们与明朝的特殊关系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如甘肃省永登连城鲁氏土司、河州何氏、岷州后氏、云南段氏等,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权利,与明廷的经济支援、朝贡贸易、文化(包括宗教)交流以及军事援助密不可分。由于班丹扎释的贡献,大崇教寺得到了朝廷的恩宠和扶持,其势力在河陇一带炙手可热。其上层僧人更频繁往来于岷州与京城之间,成为明代朝廷联系岷州藏区诸番部的纽带。而“净觉慈济大国师”的封号则由其家族出身的高僧世代承袭。可以说这些望族拥有一种双重地位,他们既属于明帝国的精英阶层,同时又是土著势家。他们既熟习明朝朝廷仪式、政治文化,以及汉族行政规定,又因为家族、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所以势力深深植根于当地。不言而喻,这种双重地位让明廷对边疆望族的看法也很复杂,因为他们有时是一种政治资源,有时也是政治劲敌。
三、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
最近一二十年以来,西方学界日益意识到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说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较简单,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即探讨中国与东亚、欧亚大陆,甚至南亚、东南亚、非洲,还包括与新大陆的互动关系,强调中国未曾孤立或封闭于世界。大英博物馆2014年秋天所举办的明代文物展“明代:改变中国的五十年”,便是这种新学术趋势的具体结果和体现。第二层含义则是在建构历史概念社会科学理论之际,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经验。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以来不少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大家如韦伯、沃勒斯坦、艾森思塔特等探讨近代国家、官僚制度、世界体系理论等问题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他们学术成果非常丰硕,影响深远,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有限。近年随着全球史、世界比较史的再盛行,相关的学术讨论会也剧增,举办帝国史、移民史、军事史、经济史等跨国或多国课题的研讨会时,多半都会邀请一两个人谈中国的历史经验。虽然如此,但中国历史往往不被当作重点讨论,学者先从古代罗马、中世西欧的发展趋势得出一些理论或规律,然后看奥斯曼帝国或清朝的具体情况加以点缀。
现在在西方学界,边疆政策、疆域概念、主权形式等成为热门课题。不言而喻,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地都跟北美洲和欧洲今日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同样,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说多半都渊源于北美洲或西欧的历史经验。疆域概念、多重主权(即在同一个区域多种主权并存,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帝国在新大陆同一个地方号称持有主权或欧洲帝国与土著政权同时拥有主权)等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引起了极为激烈的辩论。当然把这些观点公式化地套用于明代历史极不妥当,但同样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概念只根据北美洲历史经验产生的而置之不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开放、灵活的态度对待新观点。假如它们能提供一些新启发,让我们重新认识明代的历史面貌,便可以做选择性的吸收;如果发现它们起不了这一作用,也就作罢。
更重要的是拿明代历史经验重新评价全球史、世界比较史等领域中的核心解释和前提,这就是上述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第二层含义。也许中国学者不十分关心外国学界如何理解中国史,但也不妨对这个问题稍微留心。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或多或少与小学、中学、大学所用的教科书都有关,对下一代中国观的形成会产生影响。“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复兴”等口号都与历史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西方不少人就下了一个结论,想要了解中国将来在国际舞台上会怎么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中国过去怎么样。在讨论、编写新全球史过程中,中国同仁具有优越条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愿他们积极参与并做出贡献。
《神武军容耀天威》读后感(四):【转】魯大維教授演講紀要兩場
「明朝初期皇室的元朝話語」
主講人: 魯大維 (David M. Robinson) 教授 (Ho Professor in Asian Studies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Colgate University, USA)
主持人: 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11 月 3 日(五)下午 4:00 至 5: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
撰寫人: 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假該所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邀請柯蓋德大學魯大維教授以洪武年間「明朝初期皇室的元朝話語」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演講由該所副研究員陳熙遠教授主持。
演講開始,魯大維教授首先說明講題中所提到的話語對應的是英文中的 narrative (又譯為敘事),雖然主要談的是明朝皇室,但是皇室本身並不封閉,而且和外界有所交流。
魯大維教授認為,歐亞大陸經過蒙古帝國一百五十年的統治後,對後來的各個政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蒙古帝國促進了各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族群的交流與整合,並且深化了各地區之間的彼此了解。而在蒙古帝國崩潰後,如何理解並利用它複雜多樣的遺產,包括歷史記憶、人際網絡、民族分布與宮廷文化等,便成為十四世紀中葉歐亞大陸各地新興政權都要面對的共同挑戰。這些新興政權如莫斯科大公國、帖木兒帝國以及明朝,都試圖說明它們與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並且編造對自己有利的蒙古話語。例如帖木兒帝國就主張自己是蒙古帝國的繼承人,以恢復蒙古帝國的權威。明朝也把元朝的崛起、發展與滅亡等說得頭頭是道,以說明朱元璋興起的合法性。並且說服國內外的人民元朝已徹底崩潰,不可能再復興。元朝滅亡是出於天意,並非出於朱元璋個人的野心,因此所有人都應該歸順大明。
在 1368 年蒙古撤回草原後,殘餘勢力被稱為北元。而研究北元的學者都面臨相關史料較少的問題。不過俄國考古學者在黑水城(Qara-qoto,位於今日內蒙古額濟納旗)發掘出許多古文書,其中有四千多件為元代文書,有十八件北元文書,時間約從 1368 至 1372 年左右。魯大維教授以宣光二年 (1372) 亦集乃路總管府鋪馬駝隻文書殘尾為例,說明北元雖退回草原,但還是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態維持其他地方政府的運作,因此這些文書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訊息。
正因如此,1368 年以後的大元(北元)仍舊是明朝初期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強敵。因此明朝試圖透過施加政治壓力、經濟援助,以及本演講所提到的敘事策略來跟北元競爭。在洪武年間明朝皇室的元氏話語 (Chinggisid narratives) 中有三個關鍵概念:一是天意(或是天命、運數);二是邊緣性,認為北元偏居一隅,不足以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三是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明朝的正當性、減少元朝的號召力,以及將明朝的政治行為合理化,說服元朝的同盟者轉而支持大明。而說服的對象為大元與大明雙方都想爭奪的重要人才,基本上包括了懷念大元的漢人以及留在中原的蒙古人。而且當時所謂「國內」與「國外」的界線並不清楚,重疊面相當大。關於這種元朝話語的理解其實是奠立在包括了錢穆、蕭啟慶、陳高華、張佳、劉浦江與奇文瑛等學者的先行研究上。
魯大維教授也注意到,明朝其實不是第一個利用天命這種敘事話語的政權。在元末群雄就已經開始操弄這類元朝話語,來瓦解元朝的號召力。例如方國珍 (1319−1374) 政權底下的劉夏 (1314−1370) 曾言「自古夷狄之君無百年之運。」明玉珍 (1331−1366) 也曾提出「元運已去」、元朝「運祚衰微」,還有「邇者元運告衰」等說法。因此明朝利用這種語言的目的不在創新,而是溝通。它試圖以別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說服別人加入其陣營。
朱元璋試圖以天命說服華北人民放棄元朝的統治,響應明朝。例如在《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所收錄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中寫道:「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前言不謬 ……天運循環,中原氣盛。」洪武皇帝即位之後,在〈初即帝位詔〉中表示「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夫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直到二十餘年後,洪武皇帝對於北元勢力仍舊持此一態度,如《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慾為不清」。
另外,朱元璋也以蒙古人能理解的方式試圖以天命說服蒙古人。透過對照洪武年間編纂的《華夷譯語》中收錄的蒙文版〈諭阿札失里〉與《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收錄的〈諭遼王阿札失里等詔〉,我們可以得知漢文的「天」與「運」二字分別譯為蒙文的 tenggiri 與 ǰayā 。
關於邊緣性話語,魯大維教授認為主要存在於明朝官員的私人通訊之間,但是這種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官方影響。他們認為周邊民族與政權都已經向明朝稱臣,因此北元僅是個別現象,試圖孤立北元。例如宋濂 (1310−1381) 曾經表示「今當皇明在御,天威所至,西域諸戎稽手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書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而宋訥 (1311−1390) 則說「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尚煩聖慮。若置不治,則恐久為患」。
關於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明朝很清楚北元當時仍舊維持一個中原王朝的政治象徵。所以林右 (1356−1409) 在〈送曹國公北征序〉中就批評北元的作法:「竊議其可討之名有三……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彼夷狄耳,敢冒帝號,兀然南面以行天子之事。一宜討也。彼既無中國乃虛名其士,署中國官爵以居之。二宜討也。彼不知有天命在上,尚妄有所覬,使我邊鄙之民烽燧之設未息。三宜討也。」並否認大元的王朝地位。
明朝說服的對象不僅針對國內人士,也包括國外的民族與政權。例如在內陸,則是針對成吉思汗後裔。針對帖木兒帝國,帖木兒 (Tamerlane/Temür/Amir Timur, 1336−1405) 被明朝稱之為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而東察合台汗國 (ulus-i Moghul或the Moghul khanate) 在明代被稱為別失八里,其可汗為黑的兒火者 (Khiḍr Khwāja, r. 1389−1406)。明朝也是運用元朝話語去說服之。例如在《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中所收錄的〈賜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書〉中提到「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姦臣亂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大臣非人,綱紀盡弛。」雖然當時已經是十四世紀末,但是明太祖還是提到宋朝舊事,提到元朝的起源跟失政的原因,並以這點在國際舞臺上來合法化自己的統治。
有趣的是,每當明朝收到這方面的情報,就會立即加以反駁。即便已經立國八十餘年,明朝對於北元的號召力還是相當敏感。例如《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四年 (1449),明英宗致書達達(韃靼)可汗再次主張天命已歸大明,元運已去:「自古國家興衰皆出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為治皆有明效。若天命在漢在唐則漢唐諸君主之。漢唐運去則宋元諸君相繼主之。今元運久去,天命在我大明,則凡普天率土大小臣民皆我大明主之」。
到了嘉靖年間,明朝皇室打破了將近兩百年的祖宗舊制。原先明朝也承認元朝的正統性,在歷代帝王廟中奉祀元世祖,但到了 1546 年,嘉靖皇帝宣布撤銷歷代帝王廟中的元世祖牌位,以及南京歷代帝王廟中的元世祖像;另外,也停止了皇室對藏傳佛教的贊助。
最後,魯大維教授提出兩點初步想法:一是在十四、十五世紀,歐亞大陸各地政權將蒙古帝國的遺產視為政治文化資源,並且主動利用它以實現自身政治目的,元朝話語也成為歐亞大陸的共同語言。二是明朝對於說服工作的重視,也說明收集分析信息為明朝皇室興衰成敗的關鍵之一。沒有溝通方式或渠道,則無法達到說服目標。明朝雖然在說服工作上成效不彰,但是它一直都沒有放棄。
魯大維教授的演講引起與會學者熱烈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洪金富教授認為講題中的「話語」比較模糊,也許用明朝正統的建立會更加清楚,同時也分享他自己對「四十萬蒙古」意義的研究給魯大維教授參考。國家圖書館科技部補助延攬副研究學者戴彼得 (Peter B. Ditmanson) 教授則提問,明朝之元朝話語的聽眾具體為何?明朝的正統性是否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到了明代中葉是否真的還如此重要?魯大維教授回應,聽眾組成相當複雜,包括沒有撤退到草原的漢人官員以及西藏、蒙古、高麗等等。而元朝話語的重要性到了明代中葉確實有被淡化的現象,但仍然存在。其餘學者則提問明朝內部的非漢人如何看待這種元朝話語,以及南明以後是否還有這種元朝話語?魯大維教授回應,由於欠缺史料,很難得知他們的看法,清朝也仍舊接受天命的說法。而南明利用天命的說法則缺乏創新。
主持人陳熙遠教授認為,也許明朝皇室操弄元朝話語有許多層次的原因,背後也有士人臣民要求確立王朝正統性的壓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林富士教授也認為本次演講比較忽略漢人百姓的文化認同,特別是明朝試圖將後來的社會去蒙古化的努力。魯大維教授表示同意,只是在時間上的限制以及學術分工上的原因,未能納入本研究。該所副研究員陳雯怡教授則提問明朝在針對國內與國外聽眾時,是否也運用同樣的語言?魯大維教授回應,明朝確實在面對國內與國外聽眾時會有一些差別。例如面對越南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仍舊是以儒家式的天命語言來說服,但是由於他個人對越南文材料不了解,無法得知越南怎麼想。但是面對日本時,明朝皇帝就會提到元世祖攻打日本失敗的舊事,認為日本只是僥倖獲勝,明朝是全面擊敗元朝,因此日本應該早日歸順來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巫仁恕教授則提出明朝會不會是以天可汗的傳統去說服中亞的政權,特別是明成祖,因此跟前朝有所不同?魯大維教授認為天可汗也許不如成吉思汗來得有號召力,或是說成吉思汗是最成功的天可汗。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提問,明朝是否有利用元朝與西藏的藏傳佛教紐帶,去說服西藏接受明朝的統治。魯大維教授的回應是有的,但是限於語言能力問題,無法解讀藏文史料,必須借鑑他人研究。雖然現場仍有許多學者想提問,但礙於時間因素,本場演講便在熱烈掌聲中準時結束。
「明朝也有天可汗嗎?明前中葉帝王形象的內亞面目」
主講人: 魯大維 (David M. Robinson) 教授(美國柯蓋德大學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學)
主持人: 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18 年 4 月 17 日(二)下午 2:00 至 3:40
地點: 國家圖書館 文教區 301 會議室
撰寫人: 何幸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都嘗試建立對內亞地區的控制與權威,如唐太宗(598-649,626-649 在位)被西北諸部稱為「天可汗」,元世祖及其後裔也是名副其實的「內亞帝王」,清朝皇帝亦積極塑造其「內亞帝王」的形象。然而介於元、清之間,長期困擾於北方異族問題的明朝,目前關於歷任皇帝對外經營策略與國際視野的討論仍相當有限。魯大維教授此次於國家圖書館「寰宇漢學講座」進行的演講,即試圖利用文獻史料和圖像資料,探討明朝皇帝與內亞聯繫的一面。
魯大維教授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為美國柯蓋德大學 (Colgate University) 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學教授,研究領域著重近世東亞的軍制史、外交史、宮廷史、暴力與社會秩序史等。他在演講中以對明宣宗(1399-1435,1425-1435 在位)行樂圖、射獵圖的分析切入,指出內亞元素同樣也出現在宣宗為己塑造的帝王形象中。魯教授認為,皇室田獵在十四至十五世紀初期是歐亞大陸各國皇室的重要活動,無論是元朝、高麗、帖木兒帝國或者奧斯曼帝國,皆有相關文字或圖像材料留存。而在宣宗射獵圖中呈現的衣著、配備,諸如獵鷹、獵犬等動物的飼養及使用,乃至騎馬、射獵的姿態,都反映宣宗對此一元朝遺緒的承襲。
魯教授接著透過相關史料的分析,探討明朝皇帝承續上述形象的背景,以及背後涉及的政治需求。明朝建立後,元帝國的勢力並未全然瓦解,長城之外的北元政權,仍是明朝的重要威脅。故明太祖(1328-1398,1368-1398 在位)、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統治時期皆積極爭取國際人才,尤其是熟悉北方語言與情勢者,他們對北元大臣、蒙古人的收攬亦非只是政治演出,而是確實地重用。魯教授還指出,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九年(永樂七年,1409)的記載中,甚至同時提及「韃靼皇帝」和「皇帝」,足見當時朝鮮仍將明朝與北元視為兩個對等的政權,並心存觀望的態度。明成祖在接見女真部族時,也刻意以田獵的話題「懷柔遠人」,魯教授認為,這反映出明朝皇室的內亞面目,即永樂皇帝利用雙方熟悉的田獵文化以與女真領導階層順利進行溝通,目的在於建立信賴關係。
但有趣的是,明朝文官的相關書寫中,並未呈現上述對國際人才的需求與爭取,顯然難以承認此一事實,而採取明朝皇帝盛德廣布、外人順應天命的論述。例如永樂二十一年 (1423) 也先土干 (?-1431) 的覲見與投靠,其實是有條件並存有觀望意圖的,而成祖在接見、應對這些來自北方的投靠者時,也刻意與唐太宗作比較,甚至對其提出批評,顯見成祖確實具有經營自身「天可汗」地位的意識,但《明太宗實錄》對此類過程的書寫卻並非如此。這類書寫除了誤導後世研究者對明初實際政治文化的理解、造成對明朝內亞經營面向的忽略外,也反映文臣與皇帝之間生活經驗與政治理念的落差。永樂年間,與蒙古人進行田獵活動是成祖對其進行攏絡的手段之一,而對從小被成祖帶在身邊親自教育的宣宗而言,這也一直是他生活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他於謁陵之後與蒙人田獵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在文臣眼裡,此種行為極為不當,並提出批評和抗議。從類似的實例中,我們能看到皇帝與文臣之間對帝王應有的行為和作用有很不一致的理解。田獵對明朝皇帝而言,也是一個表演的平臺,可以展現財力、帝王形象,以及對狩獵裝備和馬匹、獵鷹、獵犬等層面的知識與講究。而就宣宗的場合來說,此類活動亦可成為奉母孝親的機會。
礙於時間的關係,原本預定要一併探討的後期發展,以及明代帝王對於西藏的經營——這也是其帝王意識及內亞面目重要的一環,同時亦影響西藏、青海、甘肅地區人們對於明朝皇帝形象的理解——便無暇細述。魯教授總結,對內亞政治文化的理解、利用內亞政治模式來實踐自身政治理念、將「內亞君主」融入其帝王形象的組成部分,以及爭取蒙古人、女真人、藏人對其君主地位的認同與投靠,若由這些層面來看,至少明中期以前的皇帝都算是及格,可以算是廣義上的「天可汗」了,其擁有「內亞面目」的事實自也無庸質疑。至於明朝後期的君主,看似已不再具備此種形象,但這究竟是歷史事實,抑或只是目前研究者尚未留意?魯教授引用顧時汗1641年寫的蒙藏對照的《持教法王諭令》說明,崇禎皇帝(1611-1644,1627-1644 在位)仍被視為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為例,指出即使到了明末,明代帝王依舊存有這類屬於內亞政治文化體系的形象。
魯大維教授的演講引發了熱烈討論。在中研院史語所訪問的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田浩教授 (Hoyt C. Tillman) 認為,魯教授的演講呈現出明朝皇帝除了漢人官僚體系之外的另一個圈子;對皇帝而言,這些前來投靠的蒙古與女真人反而會是更可靠的臣屬,明初皇帝們才有條件對漢人官僚那樣殘忍,多次展開政治肅清運動。有些與會學者也好奇,明朝皇帝展現的內亞形象,如何被其他歐亞國家理解與反應,以及明代官方所產出、以漢文呈現的對外宣傳材料,如何被不懂漢文的蒙古、女真及其他國家(也就是此類材料宣傳的主要對象)所理解和接收。魯教授指出,明朝在論述上刻意切割北元與元朝帝系的聯繫,明朝皇帝也會以元朝的歷史教訓為參考,擬定對外國的宣傳策略。例如明太祖在對日本的宣傳中,就極力強調其與元朝的差異。魯教授也說明,帖木兒王朝、日本當局等並沒有買明朝的帳,間接或直接地否認明朝皇帝的內亞論述。魯教授亦提及本次演講主要提及的都是漢文史料,其中朝鮮史料往往會保留未經明朝政治潤飾的記載,呈現與漢族文臣書寫截然不同的內亞情勢認知;此外,帖木兒帝國等內亞國家也有些許史料留存,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可用的史料確實具有侷限性,故解讀時也必須謹慎。至於有與會學者問及明朝君王展現的上述內亞形象,會否只不過是基於政治需求的一種演出?魯教授則回應,對北方情勢的考量一直是明朝皇帝施政上必須留意的重點,成祖之所以發動北征,也是基於對內亞局勢的掌握和判斷,他認為不應以「表面」與「內涵」二分法來理解明朝皇帝的相關經營,這些帝王所展現的內亞形象,應也能反映其內心的自我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