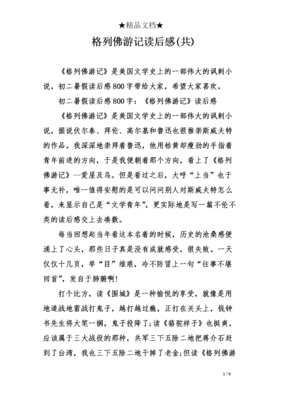奢侈与逸乐经典读后感有感
《奢侈与逸乐》是一本由【英】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奢侈与逸乐》精选点评:
●非专业人士实力劝退,太学术了。。。
●选题的初衷是做出一套关于“物”的历史的图书。又因为“物”的历史必然与它的生产、加工制造、流转、消费相关,所以我们又加入了“全球史”的视角。这套“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关注英国的新式奢侈品,关注中国的茶叶,关注大西洋沿岸的植物勘探,关注荷兰的地理书。我们以此通过“物”的全球视角,来理解历史的进程,追寻社会变迁的足迹,体察其对当下世界的改变。愿你在一个个“物”里看见大世界。这是第一本,其余三本今年会陆续出版。
●注意东方元素,但是对英国当时经济与技术机制语焉不详
●对我来说,这本书有点难读。人们为了发明、制造和购买新式英国商品投入巨大的热情,但这些商品也是人类用以自省、疑虑和社会排斥的对象。
●没头没脑支离破碎的翻译把这本书彻底沉入到书柜的角落。
●来自东方的商品散发着异域气息,在18世纪的英国大受好评
●东方奢侈品,瓷器、丝绸、白棉布、漆器,源自亚洲消费文化,但是它们很快改头换面并适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凭借着高效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高度复杂的贸易与分配网络, 这些货物在整个英国及其帝国领域内为中产阶级和乡绅所熟悉,成为他们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些用于家内的装饰品满足了人们对于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的喜爱,同时它们也推动了欧洲,尤其是英国自己的工业生产和设计能力。 除了对物品本身着迷外,由于隐藏在这些物质、颜色和类型背后的异域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并未为欧洲所掌握,这也是它们充满魅力的原因。 这时的欧洲尚缺乏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这些产品有着多重要求的生产过程,它包括大规模的生产、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商品化以及对全球市场多样性的适应能力。
●本书的语境下“奢侈品”这个概念相当广义,然后主要写的是17,18世纪的英国,(至于现代语境下的奢侈品的并没有怎么写(wedgewood的骨瓷写得好多啊,,,)
●也许是好书,但不对我胃口。感觉没有什么观点,也没有把事实串联起来的线索。三星给第三部分。
●挺好的,除了第一部分无聊到吐血之外,书快看完才对其有了认识。。 写的挺友好,各个理论简介也好,概念良好定义也好,都是我眼中的加分项,例子:书里花两页纸明确了中产阶级这个在其他著作里往往是默认但又模糊的概念。。。 当然特别乐的地方也有,比如某一页的鬼畜地图,泉州的奇妙漂流.jpg但估摸着是图例翻译时编辑的锅
《奢侈与逸乐》读后感(一):个么现在出书认真点估计是做不到的
书读一半看见的。我这么粗心的都能挑出这种错。
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
《奢侈与逸乐》读后感(二):欲望促进社会进步
《奢侈与逸乐》构建了整个工业社会的消费行为。这本书的初衷当然也是为了工业社会研究进行补充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构造了商品、工作,消费,这种统一性社会。当然本书也有些许遗憾,没有将随之而来的借贷金融领域的情况描述出来。
同时,消费者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个角度其实蛮有意思。大体上,我之前始终认为,社会的推进是由少部分人完成的。但是这本书用了另一个角度,其实整体消费也会对社会进行极大程度的推动。
那么联合到现在新冠问题,就更容易理解,当消费停摆之后,必然会有经济重创。
但不幸的是,现在消费社会已经不是人类谈论的主题,当然以前也不是主要议题。不过,现代的欲望更容易反射消费,这是由工业化大生产决定的。
所以,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世界史对于消费行为和消费者的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这对于理解全球化进程相当一致。
而对于阶级化,虽然非本书重点,但仍用了一大章对于中产阶级为了占有欲和体面,苦苦对于奢侈品的迷恋进行剖析。而促进大众消费欲望,是商人们至今都在深度研究的工作。
而我读完这本书的深刻感觉就是,如果想要富有,必须要放弃欲望……这样才能抵制住那些铺天盖地的陷阱。
《奢侈与逸乐》读后感(三):挥别“纵乐的困惑”之后:18 世纪英国的消费革命
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很多解释,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香料茶叶等的远程贸易刺激,糖和咖啡引发的“甘甜的资本主义”,以及涉及罪恶的奴隶买卖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等等。在《奢侈与逸乐:18 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一书中,英国学者马克辛·伯格将之归因于 18 世纪在英国发生的轻奢品消费革命,认为来自中产阶级对传统奢侈品仿制品及新型奢侈品的需求,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高歌猛进最主要的内生性推手。
奢侈品消费自古有之,被视为中国所谓近世开端的宋朝和有着资本主义“萌芽”之称的明朝,都出现了围绕奢侈品的消费浪潮。这本书里强调的是新型奢侈品消费的规模、深度、持久性和新颖性,只有这样的而非传统贵族式或暴富炫耀式奢侈品消费,才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可靠推手。
任何革命都是观念先行,消费革命也不例外。在前现代社会,无论西东,奢侈品消费从来缺乏好名声,总是和骄傲放纵和道德败坏有关,而且也总是被道学家们视为天下失序走向大乱的根源。关于这些争论,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其关于明朝消费文化研究的专著《纵乐的困惑》里给予了详尽的展示和剖析。一个社会要想过渡到消费社会,必须克服“纵乐的困惑”,为奢侈品消费正名,以消费为荣。
到了 17 世纪末,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伴随远程贸易出现的消费东方奢侈品的浪潮,英国旨在维系社会等级和限制下等人“过度”消费的抑奢法案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包括精美的瓷器在内的来自东方的货物,之所以生产并进口,不仅是为了供传统精英使用,也是为了供应迅速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使用。这些新崛起的消费者,对“品味问题”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自由感,他们珍惜新出现的东方奢侈品所代表的选择机会和自主性,视其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一种静止的社会秩序的挑战。
接下来发生的是英国版“山寨”传奇。中国瓷器、印度棉布和威尼斯水晶玻璃等不断攀升的价格,逼迫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制造商走上了一条仿制和进口替代之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东方奢侈品的高关税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仿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通过运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在吸收亚洲异域特色的基础上推出针对中产阶级口味的新创造物。在仿制的过程中,新型工艺、材料和生产销售的组织系统等等都发生了变革。在陶瓷产业,英国和欧陆制造商通过寻找新材料、混合物和生产秘方,以制造出更有成本效应的产品。在这方面,英国人走到了前头,推出了包括韦奇伍德瓷器等知名品牌在内的替代品。瓷器一举从上层阶级收藏的古董变成了轻奢消费品。有意思的是,不少本土瓷器经销商所使用的分销网络恰恰就是形成于东方瓷器畅销时代。
创新竞争的过程是激烈的,庞大的生产分工和销售网络贯穿很多地区,这改变了欧洲的物质文化,带来了新式的产品颜色、风格样式。其中出现的创造性艺术、设计和创新,又通过技工们在奢侈品和消费品行业的流动,便捷地融入各行业长久以来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亚当·斯密把仿制活动誉为奇迹的来源,认为它与审美革命和对产品的需求,共同构成了现代英国消费品得以出现的关键因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发生在当下中国市场上的由“山寨”而不断进阶的制造业和消费革命。
不过,真正标志本土轻奢品崛起的是英国小型金属消费品的勃兴。在马克辛·伯格看来,英国“先进消费品”的起点是伯明翰的“金属扣和纽扣”,这两个小玩意儿凸显了英国制造的先进性:新的材质、新的工艺和新的生产体系。比如,从 18 世纪早期起,伯明翰的生产商们就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渗碳处理技术和“水泡型”钢铁,使得纽扣的表面非常光滑整洁。煤炭的使用也令粗钢精炼成为可能,这些钢制品和合金制品后来在很多流行物上得到应用。而接下来机器的运用又实现生产过程的可复制性和可标准化,这又为质量管理、确定成本和价格奠定了基础。
英国技术的起飞,与殖民地贸易的飞速发展正好吻合,也和新出现的国内和欧洲市场对小型金属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有关。品种繁多的钢制饰品、镀银茶具和各种五金产品,作为日常物品和消费器皿不仅被英国人视为彰显自身特色的“民族产品”,也成为欧洲和美洲消费者抢购的对象:中产阶级们把自己拥有机械制造的新式发明品看做自己拥抱现代化的表现。那种认为英国制造业的发迹是因为掠夺殖民地原材料和向其倾销制成品的说法或多或少有点失之于简单化。
制造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助推了新一轮城市化和交通网络的发展,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中产的崛起。在这些新兴和新型城市中,不仅有工业群体、大资本家群体,以及管理、工匠和贸易群体,大型零售业、服务业、管理业、商贸业和其他职业从业人员也成为支柱人口。新中产的崛起反过来又激发了新一轮消费革命和制作业革新。具有高度流动性并处于快速变迁状态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学习如何消费,他们对流行、现代、个性、多样性和选择能力非常敏感。对他们来说,消费行为既是公共行为,也是私人活动,并且伴随其出现的还有中产阶级对归属感、体面感和个人特性的追求。高雅文化的普及,不断增加的对生活精致度的追求,屋内和桌面摆放饰品的习惯,以及对个人卫生的讲究,都在刺激着为个人使用而进行的商品生产。
作为现代消费象征的广告业也应运而生了,随着新型奢侈品和商品越来越多地被制造出来,新型消费者也需要被“制造”出来。发明家、制造商、经销商开始和广告商共同发起一场产品革命,旨在将新奢侈品和消费品直抵中产阶级和商贸阶层。他们共同营造的一个信息是,与旧式的代表腐败阶层的奢侈品不同,新型奢侈品和消费品有着不一样的美感、精致和便捷性。按照马克辛·伯格的说法,这些产品是反宫廷价值观的,带来了简约性对矫揉造作的工艺压制,体现着民主原则的启蒙,而非绝对主义的巩固。
在新的语境中,时尚品之所以成为时尚品,不是因为王公贵族使用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能与商品网络中其他美观和实用的产品有着联系,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材料优良、制作体系先进、劳动分工精密,而且最重要的是机械化生产。这种认同感还与塑造这些物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用这些物品就意味着拥抱其所承载的启蒙思想、现代性流行风和全球商贸往来。
上述分析或许不乏过度解读之嫌,不过确实能为所谓的东西方“大分流”的探讨提供一些新的启迪。中国学者蔡昉指出,和西方相比,中国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将蔡昉的观察和马克辛·伯格的分析相结合不难发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个有庞大中间层支持的规模消费经济,而建立在小农剩余经济基础上的城居地主的奢侈性消费乃至海外市场的需求,不足以产生类似英国 18 世纪建立在中产阶级“奢侈与逸乐”基础上的消费革命和技术创新。这或许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西方“大分流”何以出现。
以上,来自苏琦“好奇心日报·万物简史”专栏书评。
《奢侈与逸乐》读后感(四):奢侈消费开启工业革命之门
桑巴特早在1913年出版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打开大门,并使之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恰恰是消费的增长”(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确立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这一“桑巴特命题”,为奢侈消费与现代性展开的多维探讨埋下了伏笔,英国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辛·伯格的《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提供了通常在工业革命叙述史中所缺失的一环”(序言,第3页。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通过对18世纪英国新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说明了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实际上开启了工业革命之门。
一
《奢侈与逸乐》中所反映的18世纪英国物质世界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奢侈消费从宫廷和上层社会向全社会漫延,从而引发了全社会对奢侈消费的关注和讨论,大讨论扭转了人们对奢侈消费的观念,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主要围绕奢侈的定义、奢侈消费与社会道德、奢侈消费与经济发展、奢侈消费与健康等问题,正反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通过这次大讨论,奢侈的含义开始在17世纪晚期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奢侈的定义与道德脱钩,与经济发展挂钩。中世纪以来英国人秉承传统观念,把奢侈与铺张浪费甚至贪婪浮荡等同起来,认为是一项罪恶。当时居住在英国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私人的恶德带来的是公众的利益,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的就业。曼德维尔的观点引发了轩然大波,受到不少人的诋毁和抨击。之后,大卫•休谟、詹姆士•斯图尔特重新定义奢侈,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力量,明确指出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穷人就业,刺激工业发展,鼓励工匠改进工艺,认为“人们已经熟悉奢侈的快乐和商业的利润,他们的精巧和勤劳一旦被唤醒,就会在国内各贸易门类和外贸做出进一步的改良,这可能是与外国开展商业的主要优势”(David Hume,Political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通过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促进了英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其逐步摆脱了消费的道德意识形态困扰,能够理性平和地看待奢侈问题,也使人们也认识到了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他们看到“哪里变得越富有,哪里的消费就越庞大。”因此,“不管道德家或美学家如何聒噪,毫无疑问,城镇中对娱乐的追求在这一时期不仅增加,而且是显著增加。出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越来越多满足身体和精神的方法被开发出来。”从而导致“英国的普通男女比以前吃穿范围更广的商品。”消费的巨量增长推动了英国消费社会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左右的诞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英国走上了开发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的道路,社会史家巴里•科沃德认为:“不断增多的对制造品、奢侈品、服务和娱乐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话题已经被多次讨论。在近代早期,英国形成了一个足够富有的社会,能够提供有效需求促进英国制造业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工业化之前快速增长,甚至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前提。” (Barry Coward,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Longman,1997. p.80)
二
东方奢侈品的涌入和奢侈消费的繁荣促使英国人重新思考本国生产的消费品的特点,让他们认识到,英国人必须也能够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奢侈品和新的消费品来满足急剧增长的社会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了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创新,成为工业化的动力。
物质文化史家约翰•斯蒂尔斯认为从1550年到1750年两个世纪间在英国物质文化史上见证了无比非凡和前所未有的革新。一些产品是全新的,在那些英国发明或者至少彻底改型的加工品中,包括袖珍显微镜、用铅玻璃做的酒杯和钟表等。虽然有一些技术和产品英国还没有,但英国人善于学习、模仿和改进。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波斯特勒维特就对中国、印度、日本制造品的技术、质量和工艺极度着迷,他在《贸易和商业通用辞典》中“机械技艺”词条下,褒扬孟加拉、中国和日本的工匠,认为英国工匠应该从中学习:“总体而言,在机械或制造工艺方面,其他民族可能优于大不列颠,我们的能人随时留意,不仅仅是模仿,而且要超越……对于进口的物品,对于他们能够了解、操作和详细检查的物品,他们最好模仿或者超越。”(M. Postlethwayt,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London,1757.)
面对消费者的新需求,英国制造商受东方奢侈品启发,充分借鉴其设计、多样性和美学特性,再结合英国消费者的品味和时尚,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走出了一条从“仿制”到再创新的技术开发之路,终于成功开发出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或者说“新消费品”。马克辛·伯格在书中指出了英国制造商“仿制”东方奢侈品的方法:“他们对来自亚洲装饰品的技术、材质和设计进行研究,吸收其中一部分特点,改造另一部分,并且他们还推动了一系列原则的出现,他们把这些原则看作对西方固有的家具物品和装饰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第24页)这些新奢侈品具有诸多优点,一是具有“乐趣、舒适、便捷、实用和亲切”(第32页)等特点,遵循品味和美学原则,适应中等阶层以上消费者追求优雅生活的审美需求;二是这些新商品并不是以前国产产品的简单替代品,而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和风格做成的特殊物品,通常能够唤起异国情调;三是这些新商品以“能买得起的价格满足了中产阶级和乡绅消费者要求的优雅品味”(第125页) 。
这一模仿再创新战略最成功的新商品是英国陶器,英国的陶器和瓷器制造是从模仿荷兰代夫特陶器和中国瓷器开始的,英国制造商通过仿造、抄袭加上本国的设计,创造出了独具英国特色的新陶瓷,比如他们创制的英式奶油色陶器、伍斯特和德比瓷器、斯塔福德郡洁具是如此与众不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是英式商品成为国际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优质商品的典范。此外像茶具、茶几、漆器、搪瓷器皿、各种镀金器皿和金属饰件,以及随处可见的搭扣和纽扣都从过去的进口品,经过仿制再创新变成了英式新产品。其中得到最广泛消费和认同的英式新消费品是玻璃器具、陶瓷器具、镀银器皿、钢制品、黄铜制品和漆饰品。
三
英国成功走出一条“从仿制到创新”之路凭靠的是英国当时已经在消费需求的催生下形成了一个创新社会,从而为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打开了宽敞的大门。
英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已经成为创业者的黄金时代,在当时消费需求和社会氛围以及政府的鼓励下,许多人提出了各种计划和奇思妙想吸引大众投资,英国人开始自己发展新型工业技术,英国工匠开始扮演欧洲先进工艺先驱者的角色。约书亚•塔克1757年在《旅行者指南》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创新热潮的结果:“很少有国家能赶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英国用来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发明的数量。事实上荷兰在利用风力轮锯木、榨油、造纸等方面优于英国,但是涉及到采矿和冶炼各种金属方面,英国人在机械动力发明上罕见地灵巧。适合于在矿坑中提升矿石的发明,如吊车或马力机;其他的发明有抽水设备,如水力轮和蒸汽机;还有其他的发明来减少四轮马车的费用,如配上本制构架能让马车在倾斜或向下的路面奔驰的机械,同时能载运大量东西。对这些发明来说,在不同的工序中运用时必须添加各种操作杆。也包括黄铜系列部件,切割轮,轧板轮和制作各种精致金属线的设备。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奇妙,差不多是为了进一步操作和使用做准备。因此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在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谢菲尔德和其他制造业地区,几乎每一个制造商师傅都拥有一项自己的新发明,并且每天都在改进其他人的发明。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在英国的这些地区,这些发明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用技术的典范,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罕有。”(Josiah Tucker,Instructions to Travellers,Dublin,1758,p.20.)一位瑞士印染工在1766年就注意到英国人对外国实用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能力强大:“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工业和克服任何障碍的不屈不挠的耐心是超乎想像的,他们不敢夸口许多发明是他们的,但敢夸口的是他们完善了别人的发明,因此就有一句谚语,一件完美的东西一定是法国发明的,英国造出的。”(Alfred P. Wadsworth and Julia de Lacy Mann,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1600-1780,pp.413)正是在这种仿制和发明狂潮下,英国人的机械工艺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提到工业革命,总是会提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但实际上瓦特作为一名工匠师傅,也拥有多项发明,比如亚当·斯密就写信托别人给他购买瓦特发明的订书机。正如马克辛•伯格所说,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长期以来被18世纪史家看作是发明和创造的象征,但是18世纪本身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从镀银的咖啡壶到刻纹的黄铜器皿和上漆的纸型托盘等全新精细消费品的爆发。正是由于英国整个社会都陷入改良和发明的狂热之中,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开发出了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的“新奢侈品”,而且成为英国拓展世界市场的利器,桑巴特就指出“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从17世纪90年代起,英国的制造商已经把绝大多数外国竞争商品挤出了国内市场。此时小商贩的包里就塞满了小的奢侈品,丝吊袜带、袖珍镜子、长丝带和长花边、便宜的玩具、棉围巾、连身式内衣、牛角和象牙,以及许多其他细碎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普通家庭主妇意欲选择的被称为新消费品的“小玩意”,正是这些“充满了奢侈感、装饰感和乐趣性的物品激发了工匠和商人们的创造性”(第371页) 。马克辛·伯格此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李约瑟之谜的正确路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消费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工业世界的基石”(第374页)。
form 李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