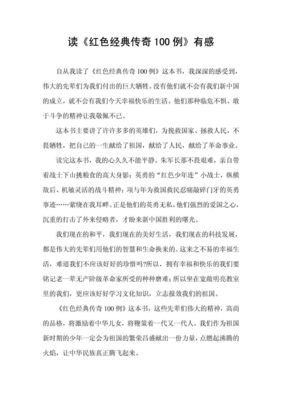Third World Modernism经典读后感有感
《Third World Modernism》是一本由Lu, Duanfang 编著作,Routledge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53.95,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ird World Modernism》精选点评:
●eye-opening
●只读了一个intro,因为这两天总看这位作者吹牛逼……但是我依然不明所以,嘻嘻
●Lu Duanfang's resourceful introduction
●只看完了前两篇,视角弹药,方法不够,有隔靴搔痒之感。或许应该配技术和人类学更精致有效。
《Third World Modernism》读后感(一):导言的读后感(四):旧史的困境与新史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建筑的语言系统、建造方式、教育模式等在“非西方”社会的大规模推进,使这些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建成环境呈现出相似的面貌。这样的结果经常被批评造成了全球城市景观和文化资源的枯竭——以及从专业角度来看更令人焦虑的——建筑学的枯竭。然而事实上,现代主义建筑的全球蔓延,只是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的一小阶段、一小部分或者说是一种表现。但是作为建筑史家和理论家,却有足够的敏感,意识到当下的历史写作和理论建构可能并没有对这个趋同的进程提供批评,反而经常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建筑之树”从弗莱彻到弗兰普顿愈来愈强烈的吸附性,反映的正是旧史的问题。
卢端芳所期待的新史,似乎是对全球建筑同质化的抵抗。在对本书9个案例的编撰中,可以看到她试图另立一个理论框架,从历史事实中建构出多样性的努力。读者可以体会到史学的目的已经不是建立另一首田园诗和另一种正统,而是用新的视野来刺激、或者更确切地来说是“合法化”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
然而,以“第三世界”来对知识碎片进行的整合和关联,恰恰也是“建筑之树”所采用的方法,而以旧史的方法,是否有可能解决旧史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建筑之树”的阴影下,能否长出另一棵大树,以及两棵树或者一打树,是否真的比一棵树更为丰富和多元?
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之前和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起止成败仍然在“西方”的框架内被讨论着,而“非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仍然被看做是现代建筑语言的无创造的复制和不成功的实现。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虽然经过各地学者数十年的努力,以及越来越多非西方建筑师对建筑学的原创性贡献之后,现代建筑学知识的仍然是“西方中心”的,在非西方发生的事情仍然通常被视作新的案例或者事件而不是新的议题,而这些案例也尚没有为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建筑挣得建筑史学中的一席之地。
《Third World Modernism》读后感(二):导言的读后感(一):陌生的“第三世界”
这本文集出版于2011年,如果从过去4年学界的反响来看,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语境里都算不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google scholar显示这书本的他引次数为26次,豆瓣读书显示4人读过,1人在读,22人想读。仅从这些数字来看,这本书在英文学界的“非西方”建筑研究领域算得上近年比较受关注的著作,而在中文学界,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兴趣。
我以前写过这本书的书评“现代建筑的历史的全部”,发表在2013年第6期的《时代建筑》。当时写这篇书评的想法,只是觉得这本书的主编卢端芳撰写的导论“Architecture,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the Third World”,十很厉害,值得向中文读者转述一下。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曾经立志要把书中的9篇文章一一读完。但文中陌生的案例和琐碎的细节把人绕得七荤八素,只能一直处于“读不下去”的状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第三世界”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按照维(jin)基(le)的说法, “第三世界”的说法最先由经济学家Alfred Sauvy于1952年8月14日的法国杂志《新观察家》中提出,原本是指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三阶级”。 “三个世界”的概念逐渐流行之后,一般以“第一世界”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以“第二世界”指称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而以 “第三世界”指称一些在国际政治上倾向中立,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中文语境下默认的对“第三世界”的理解。
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第三世界”这个词伴随着七点档的“新闻联播”一起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虽然我其实一直没明白“第三世界”是哪个世界,但是我一直明白,这是“咱们”的世界。然而“咱们”的世界发生的一切在我都如此陌生,这种感觉把我吓了一跳。
不过至少在建筑学界,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对“咱们”的陌生,以至于卢端芳在导论中试图绕开事实,而通过理论议题引起学界对“第三世界”的注意。因此这篇导论对于不熟悉“第三世界”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而言,是了解这些地区建筑历史的一条捷径。而两年之后,我自己再读这篇书评,仍然觉得卢借用“第三世界”猛击当下建筑理论构建的问题,十分过瘾。而她通过编撰这本文集试图探索的出路,似乎本身也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将时代旧文修改一下,供豆友们参看。
《Third World Modernism》读后感(三):导言的读后感(二):现代主义建筑之树
回想一下我们最熟悉的几部现代主义建筑史,比如吉迪恩的《空间、时间、建筑》(1941)、佩夫斯纳的《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1968)、柯林斯的《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1998),等等,会发现它们都是现代主义建筑在欧美的历史。很少人会质疑为什么欧美各国(或者西方)就可以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写一部历史,也很少人会深究现代主义建筑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即便“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蔓延是大家所熟悉的。
卢端芳认为,这种经典的现代主义建筑史的写作方法,以及一般读者对这种写作的习以为常,说明了“今天我们仍然很大程度上身处在19世纪的‘建筑之树’的阴影之下。”弗莱彻《比较建筑史》中著名的“建筑之树”,以“西方”建筑为唯一且粗壮的主干而将“非西方”建筑置于旁支,这种历史建构方式所反映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早在20世纪初已经受到伊东忠太等重要的建筑史学者的质疑,再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殖民理论的猛攻,似乎早已成为过去式。但是卢却提醒读者将注意力从“建筑之树”的树枝移向各个花骨朵。这样就可以发现,位于主干上的花骨朵们,比如希腊、罗马、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等,在实际上位于不连续的地理区域,只是通过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先于建筑史家完成了这个工作)的编撰和梳理,它们被整合成了一个西方。于是古代希腊和当代美国这两个相差甚远的时空概念被顺理成章地串在同一条树干的两头,建构起一条从“古典”通往“现代”的建筑发展轨迹。而位于旁支上的花骨朵们,比如亚述、印度、和中国/日本,却被分别放在完全不同的枝干上,完全看不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中的很大一部分在19世纪已经为知识界所了解。旁支与精心构筑的主干之间,则留出大片空白,强化了互不相干的感觉。
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叶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历史建构,采用了相似的历史梳理和编撰方法,强化了西方的一体性,而弱化了西方与非西方以及非西方之间的相关性。从吉迪恩到柯林斯,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历史编撰的空间视野基本上没有大的拓展,主要的拓展只发生在时间轴上,从而将原本作为“事件”(event)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逐渐建构成一个长达数世纪的建筑的现代化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cess)。而这种历史建构,使“现代主义建筑”从“先锋”走向“正统”,并且取代了弗莱彻建筑史中的“美国现代建筑”而成为目前唯一合法的一种“现代建筑”。
卢文中最警觉的一段,是指出了弗兰普顿的 “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中对传统西方中心论的突破和延续。卢指出,建筑理论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至今难以突破,因为它在专业领域已经不是如萨义德(Edward Said),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芭芭(Homi Bhabha)等后殖民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偏见(bias)或霸权(hegemony),而是成为建筑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西方的现代知识是核心,非西方的传统知识被碎片化地镶嵌进来,作为对核心的补充(inspiration)或者抵抗(resistance)。通过这种知识建构方式,非西方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却没有为非西方的现代留出任何空间。在弗氏的“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历史建构中,不同地域的“传统”(traditions)同样扮演着“补充”和“抵抗”西方中心的角色。它们分别借助“批判”这一西方理性工具的化妆术,以“另一种现代性”的面貌成为现代建筑学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成员。
回到“建筑之树”的比喻,也可以说“批判的地域主义” 与之前的建筑理论建构相比,开创性地建立了主干和旁支之间的关系,而且枝干的加入使主干越来越粗大。也就是说,从主流建筑理论的发展来看,建筑的历史从19世纪的一棵大雪松变成了21世纪的一棵大椰树。
《Third World Modernism》读后感(四):导言的读后感(三):现代主义建筑的全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后殖民理论的启发之下,现代主义建筑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试图在20世纪20-30年代殖民地建筑和规划实践中挖掘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根苗,比如切利克(Zeynep Çelik)、博兹多安(Sibel Bozdoğan)和其他学者对柯布西耶《东方之旅》( Le Voyage d'Orient)的解读,拉比诺(Paul Rabinow)、莱特(Gwendolyn Wright)等对法属殖民地的研究, 霍姆(Robert Home)对英属殖民地城市规划史的研究,等等。另一个同样受到注意的方向是二战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观念和实践在全球的传播,但是总体而言,欧美以外的现代主义建筑,除了少数重要建筑师和建筑作品以外,并没有进入主流的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建构之中。卢端芳认为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文化偏见的惯性所致,但更重要也更难克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对非西方建筑的研究都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而且无论是西方还是本土研究者,在试图通过这些案例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的,而很少有非西方建筑互相之间的参照与整合。
卢认为,非西方建筑相互之间所具有的共性如果得到整合和提炼,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对很多建筑议题的看法。卢选择了“第三世界”一词,便是试图将其作为连结不同“非西方”案例的一个框架,以期将过往30余年积累的个案整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并回应主流建筑理论关心的议题。卢解释,采用“第三世界”一词,一方面是因为无论在冷战时代还是在当代,它所指的那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相近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质,包括“非西方”的文化传统,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现代历史、以及都处在非工业化的经济阶段,因此对建筑理论研究而言它们有可能为理论建构划定一个合理的普遍化的范围。另一方面,和“发展中”、“不发达”和“非工业化”这些明显带有线性史观的术语比较,“第三世界”这个词本身就有站在边缘挑战中心的意思。在这本书所涵盖的二十世纪50-70年代,“第三世界”事实上通过“不结盟组织”等政治机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合作和经济互助,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过复杂的互相参照和交流,而这些关联因素在以往的建筑史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这本文集中的9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巴西、摩洛哥、秘鲁、以色列、锡兰、土耳其、印度的个案研究。卢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取出三个“非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所具有的共性:第一是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与建造方式和工业化的关系,战后的“第三世界”与战前的欧美发生了颠倒——从工业化的物化,变成了农业社会条件下对未实现的工业化的臆想,二战之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modernist movement)在巴西、摩洛哥和秘鲁在表象上的延续都具有这一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第二是“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象征意义的转变,第三世界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国际风格”建筑是大型公共建筑,比如政府总部,大学,会展中心等,建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成了“国际风格”在这些地区的新使命,而战前在欧美成型的刻意去历史和去地域的建筑语言,使“国际风格”在非西方落地时遭遇了根本的两难境地。第三是“现代主义建筑”对第三世界建筑学科及教育体系的影响。二战以后,面对各地的反殖民运动,西方在处理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刻意地回避政治企图,而转向表面上看起来中性的审美影响和技术支援,由此在 “第三世界”建立起了一种“正统的”现代主义审美准则和偏向科学技术化(technoscientific)的建筑学科。
这些个案的共呈与整合,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主义建筑在非西方世界发展成了一种在生产方式、象征意义和学科内核各个方面都与西方不同的事物。正如本书的编者所期许的那样,这些个案的汇集“让读者看到一个被忽视的主体世界(the majority world)。”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在这幅全景画中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