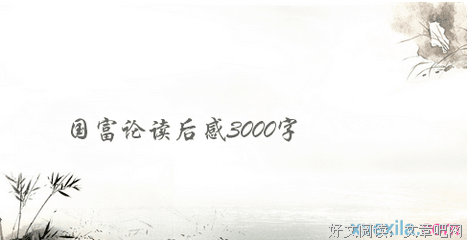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100字
《国富论(上下册)》是一本由亚当·斯密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80元,页数:7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富论(上下册)》精选点评:
●通篇只有两个字:“自由”。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的需求,读起来很温暖。书里面有提到到中国的政治状况相当深刻,所谓伟人,就要象斯密一样,是诚恳而又智慧的人。
●翻译的一般,有点晦涩
●读的时候需要查很多资料,与其说是经济学鼻祖,我更宁愿说是道德对经济的解读。时时刻刻的悲天悯人,时时刻刻的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均衡,自由市场--只有提高整体的财富,各个利益集团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非垄断。真是一个值得爱戴的道德学家
●躺在在医院的半年时光。。。
●些许观点被纳什均衡反驳
●只读了一半不到,唉~
●一步一跪一叩首的朝圣之路走了三年终于走完了→_→
●天才写的书; 即使现在学也不过时
●...感觉有点啰嗦
●基石,源泉
《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一):书是好书,可惜版本买错了
书在家放了很久,终于开始拿出来读了。很好的书,充满的智慧,可惜谢的翻译实在是太烂了,幸好自己有一些专业的功底知道作者大概要讲些什么,从字面的翻译看几乎读不下去,什么乱七八糟的的。现在开始悔恨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过关了,能轻松阅读原著就好了。目前只好先勉强读完,再把原著找来读了
《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二):不是非专业研究的,不推荐看
我不是研究经济的,只是业余爱好广泛,对经济感兴趣。
于是就买了一本,晚上睡前无聊的时候看看,也看了大半卷了。
总的来说,对于那个时期(十八九世纪?记不清了)的来说,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书,但是对于有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才来说,书中的内容已经有点“过时”。就好像想学用电脑,却抱着一本谭老师的c语言的书在看。另外一点,就是某些问题,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书中却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
因此,不是特别的爱好或者专业研究,就不要看了吧。
《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三):谈谈真实价值的长期尺度
lt;<国富论>>第五章中有句描述"就一百年到一百年来说,谷物是一个比白银更好的尺度.因为同等数量的谷物可以换取同等数量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对于谷物,在过去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时期,这种"劳动"的概念局限于"手工劳动",所以可以把谷物作为衡量劳动的"更好的尺度".
但是今天,很大程度上,真实价值除了"手工劳动"之外更多地受制于"生产力"的这个因素的支配,所以"同等数量的谷物可以换取同等数量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转移到现有真实价值的长期尺度这个话题.考虑一个稳定的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我认为资本会是一个长期的"更好的尺度".因为它不仅能体现目前资本对象的真实价值,还包括资本在短期中的产值,以及长期中通过生产力进步带来的自我更新从而实现的产值.
现有的股票是这种资本最好的体现.相信它会是接下来几十年真实价值的最好尺度.而货币会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条件下长期贬值.
《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四):推荐《国富论》(谢祖钧先生译本)
本来无意写此文。只是,我原先买《国富论》的时候,对比过三本,发现谢祖钧先生的译本最为平和、流畅、清晰、真实。后来,网上搜索谢祖钧先生翻译的其他书(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他翻译《国富论》都翻译的这么好,其他书也能翻译的很好),结果看到网上几篇显眼的帖子对谢祖钧先生翻译的《国富论》批判,而且转发也挺多,误导了很多想买书的读者。
对《国富论》谢祖钧译本的批评,主要是:语言不够经济学,术语不够专业。
然而,这些在我看来并不重要。一来:经济学本没有那么玄虚(计量除外);很多学科之所以难,并非本身难,而是很多“专家学者”弄了很多“高大上”的深奥晦涩术语,使得外行很难进入,显得自己很“专业高深”,例子不用举了,各位随便和外行人说几个自己行内的几个简单的名词概念,就可以验证这句话了;经济学的内容本身是我们身边的事物,美妙但不晦涩飘渺,倘若能用普通的语言来叙述,何必“拽”那些名词呢。二来:术语本身也是前人翻译的,前人翻译的就比后人好吗,本人看过一些经济学名词的英文,有些名词翻译的着实不敢恭维,然而我们却总是在用那些垃圾翻译却认为自己高深专业。
还有一些译本,语言比较简洁专业,但本人并不认可。因为,翻译要忠实原文,不仅忠实内容,还要忠实原著本身的历史文风、民族文化、语言风格、行文偏好、情感思想等等,这样才能真实准确地重现原著作者及作者思想与态度;就这方面来看,专业的翻译家比经济学专业的翻译家更有优势,尤其是在翻译这种融合了经济、政治、哲学、文化、历史的经典书籍书籍的时候;若说经济学专业的翻译优势,是在翻译一些经济学分支专业细分领域的专门书籍的时候。
我最初学经济学的时候就仰慕《国富论》,但在图书馆中接触了几个版本的译本,让我感觉太难太绕太晦涩,就没有再读。那些不用心的译本,浪费了我的时间和感情,也使我没能及早学习斯密的经典思想。后面遇到谢祖钧先生的译本,平和、流畅、清晰、真实、有味道,很是欣喜。后来和同学每提及《国富论》就推荐他的译本。希望对后面选择《国富论》译本的读者有所帮助。
译本的好与不好,还请读者在书店或图书馆自行比较,勿被一些观点误导。
《国富论(上下册)》读后感(五):英文版序言
我手头的版本是Bantom Book的英文原版,序言的作者是Alan B. Krueger,普林斯顿的教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61207/
我觉得序言写的还是很得体的,对没读过想读这本书的人很有帮助,所以把它译出来贴在这里。水平有限,欢迎指教。
无论是在经济学家的思维和经济政策的方面,或是拓展开来说,在全世界人民的物质富足的方面,历史上再没有哪本书会比亚当•斯密的这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更具影响力了。对这条论断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指出,《国富论》中的很多论点都可以追溯到之前的思想家,斯密实际上大量借鉴了同时代一些法国学者。也有一条很流行的观点指出,在古代中国,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而斯密对此毫不了解。不过,《国富论》还是以建立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一套工作公正地赢得了它的声誉。《国富论》的天才之处在于亚当•斯密作为一个合成者、观察者和叙述者的高超才能。最重要的是,斯密是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他认为经济行为根本上是由自利这一基本力量驱使着的,而他又把经济想象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在市场上按自己的意愿相互交易,经济的一般样式就从中显现出来,而不须外界权威力量的干涉。按亚当•斯密的经济的概念,当个人各自按自己的策略行事时,结果将是秩序,而非混乱的形成。
不过,亚当•斯密可以除去复杂的无关因素,而只关注起作用的那些基本作用,他提出,在完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些作用会联合起来促成最大化的公共福利,而市场的参与者无须盘算着这一幸运的结果,甚至不必知道他们在促使这一结果发生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斯密认为竞争是经济学有效率的:“每个人都在不断驱使自己去找出,在他掌握的全部资本下最有利的工作。这是指他的个人利益,没错,不是他的社会的利益。但通过他对个人利益的研究,自然地,或者说几乎必然地,他会倾向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那份工作。”(第四篇第二章)
斯密的思想核心是均衡的概念:经济体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按照其中的基于个人自利原则而形成的价格和工资水平,经济体中的买者和卖者、工人和企业都没有激励改变它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量)。“资源会寻找最有利润可图的用处,从而在均衡状态,同种资源用于不同用处的回报率相等,”诺贝尔获奖者George Stigler曾写道,“这一命题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实质性的命题。”
亚当•斯密日后成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1723年他出生在Kirkcaldy,苏格兰东海岸的一个小城时,肯定显得相当不可能。(斯密的确切出生日期不可考。他在1723年6月5日接受洗礼。)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苏格兰人,也叫做亚当•斯密,在斯密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斯密被母亲抚养长大,在他已故的父亲的朋友的帮助下(这是他父亲的遗嘱中明确了的),他一生都奉献给这位来自显赫家庭的母亲。斯密的婴儿和幼儿时期体弱多病,经常受婴儿常见的绞痛折磨,这伴随了他的一生。疾病阻止了他参与体育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学生时代被经典著作和历史吸引。他的同时代的人、第一位传记作者Dugald Stewart叙述道,斯密在三岁时被流窜作案的无赖绑架,被短时扣为俘虏,直到他的叔叔来解救他。Stewart将他称为“幸运的促成工具,为世界留下一位注定不仅要拓展科学的边界、更要启蒙和改革欧洲商业政策的天才”。
少年时期,这位天才在14岁进入格拉斯哥读大学,在18世纪这是进入大学的正常年龄。当时,格拉斯哥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温床。它不仅有一所很好的大学,而且还是家畜贸易的中心(用斯密的话说是“不间断的市集或市场”),这被很多传记作者认为是提供了他未来构建经济理论的有利基础。作为学生斯密专心致志、严肃认真,有些害羞、笨拙。他喜爱很多他的老师,尤其是他的道德哲学教授Francis Hutcheson,对他有着深刻的、“永远难忘的”影响,在斯密的生涯中很可能是他的模范、榜样。
1740年夏天斯密完成了在格拉斯哥的学习,进入英格兰牛津大学的Balliol College。他在那里停留了6年。然而在牛津的精英校园环境中斯密的体验不像在格拉斯哥那样有益。牛津有一项延续至今的传统,即相比美国学校,给学生更多的自我指导的空闲时间,而教师对于教学的专心程度小于斯密在格拉斯哥习惯的那种程度。根据Ross的说法,在牛津,亚当•斯密“觉得生活得尽可能轻松是每个人的关注点,如果某个人完成或者不完成一项麻烦的工作,回报是一样的,那么他要么会忽视它,要么在上司允许的程度下完成地越松懈越好……斯密指出,这样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即牛津的教授多年以来甚至连假装讲课都已经放弃了。”很可能是斯密在牛津的经历激起了他对竞争的长处的信念。
斯密离开牛津后回到Kirkcaldy的家。他用了5年时间找到了一个讲课职位。1751年斯密被一致同意地选为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一年后另一位教授退休,他就任道德哲学教授。作为受人欢迎的、专心致志的逻辑学、修辞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很受尊敬,任职教授直到1764年。斯密以心不在焉和被听到独处时自言自语著称,闲暇时热衷于玩一种叫惠斯特牌的纸牌游戏(类似于桥牌)。他后来将这段时间描述为“目前为止我的生命中最快乐、最荣耀的一段时期”。他也任了一些管理职位,包括1761年任学院院长。
1759年,他在格拉斯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用同情的情操解释了人类的道德。这本书受到了好评——包括Edmund Burke的大加赞美,以及斯密的老友David Hume——并确立了斯密作为文学家的声誉。因《道德情操论》出名后,斯密受Charles Townshend邀请,成为他继子Buccleuch第三公爵的旅行家教。
可能是疲倦于学院政治和劳累,并且受了慷慨的津贴和养老承诺的诱惑,斯密在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成为18岁的Buccleuch的家教。斯密和Buccleuch在法国和瑞士游玩一圈,在法国的Toulouse长居下来。他们是这么奇葩的一对搭档:心不在焉、法语水平糟透的斯密,以及他照顾的经常出入巴黎和日内瓦的知识分子沙龙的年轻人。做私人家教让斯密有了很多意外的空闲时间——这是每个教授的梦想。他利用这个时间结交了当时法国的很多学问家,包括d’Alembert,Turgot,Voltaire,还有最重要的Francois Quesnay,描述宏观经济流动的模型Tableau Economique(经济表)的作者。(作者注:斯密本打算将《国富论》献给Quesnay,但Quesnay在本书出版前不久去世。)不幸的是,他在法国的时间由于公爵的兄弟、曾加入他们的学习的Hew Campbell Scott的去世而缩短了。
1766年秋天,斯密协同公爵回到伦敦,把接下来的十年时间献给了《国富论》的研究和写作之中,靠Buccleuch公爵提供的年金维生大多数时间他在Kirkcaldy陪伴他年过九旬的母亲。斯密在1780年写给一个朋友说:“回到英国以后我退休在苏格兰一个小城镇里、我出生的地方,在这里我十分平静地继续生活了六年,几乎完全赋闲。在这段时间里我主要靠着我那关于国家财富的研究来作为消遣。”这是怎样的消遣!这本书1776年3月8日在伦敦出版,页数达到1100页,广泛涉及了现代与古代历史、哲学、第一手的观察、出版的报告——全部这些都整理妥当来阐发和支持对经济理论的敏锐洞察。
准备第一次读《国富论》的学生是幸运的。这本书很好读。斯密清晰、唤起感情的写作风格很像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Jonathan Swift。他对细节和知识广度的把握令人称赞。在斯密手中,经济学不再是沉闷的。
《国富论》的第一章通过对一家针厂的案例的仔细研究,生动描述了劳动的分配。斯密把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功于劳动的更精细的专业化分工。斯密观察到:“劳动生产率的最大提高,以及技能、熟练度、在任何场合指挥与实施的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第一篇第一章)用现代术语来说,他对劳动分工的讨论可以用生产函数来最合理地考察。分配给每个人更专业化的任务增加了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离开教室、来到工人场地给斯密的分析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好处,而这是现代经济学家缺少的一课。(作者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组织了一些让理论经济学家到不同行业的工厂,与工人实际接触的考察访问。这些访问恰到好处的称为“针厂”访问,以示对斯密的尊敬。)
也许《国富论》中最著名(和最常引用)的段落就是斯密涉及“看不见的手”的这一段了。这个提法在全书只出现了一次,是在下面一长段节选的接近末尾处:(第四篇第二章)(译者注:译文选自不知道谁的译本)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斯密特有的观点是,某些产业的生产者和商人所支持的那些对进口的限制,增加了这些产业的好处,但却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一般福利。
许多自由主义或保守的经济学家引申地阐释了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说法,例如指出是他贡献了市场上的个人交换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最大好处这种观点。Emma Rothschild对这种20世纪通行的解读提出了质疑,认为“斯密并没有特别重视‘看不见的手’”。她并不否认斯密是伟大的个人自由的辩护者。她也承认个人行为具有意料之外的结果、且这些意外结果有时促进社会好处这种观点渗透在《国富论》的字里行间。她论证的要点是,按18世纪的历史背景和斯密的其他作品来理解,斯密会对二十世纪的人们把“看不见的手”提高到他思想的核心概念这样的高度表示十分的怀疑。这个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但毋庸置疑的是,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的信心是被现代评论家夸张了的。他频繁地担忧,商人和生产商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会操纵政府的管制和资助措施,从而使“看不见的手”脱离它的轨道。这种担忧同样也可以应用到现代政策上来。而且,Rothschild强调,斯密在《国富论》中只使用了一次这个譬喻,使用范围相当狭窄,而且提出它的时候附带了多于他寻常的警告和限制条件。
无疑,斯密担心政府侵入经济活动。他对于教区委员会、教堂管理人、大型公司、同业公会和已确立的宗教组织的担心,比起对国家政府的担心来是相当小的,毕竟这些组织只是18世纪政府的一部分或一小批。不过当政府干预的目标是减少贫困时,他经常还是宽容的。例如,对于劳动条例,斯密热情地论述道:“所以,当管理条例是为了支持工人的时候,它总是公平而平等的;但它对雇主有利时,就不尽然了。”(第一篇第十章)他还看到了雇主们“总是、无论何处”将工资尽可能降低的不明言的阴谋。
斯密是一位哲学家John Rawls之前的罗尔斯主义者,他声称:“没有哪个绝大多数成员生活在贫穷和悲惨中的社会会繁荣、幸福。此外,只有那些供给了整个社会衣、食、住的人们拥有了自己劳动所得中的一部分,使他们自己获得不错的衣、食、住的条件,才算是公平。”(第一篇第八章)
他很显然对弱势群体有着宽厚同情的心。这就在他的思想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一个人必须决定要牺牲多少效率来提升那些为其他人提供衣、食、住的人的生活条件,如果那是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的话。答案对一个人来说不容易,对很多人的群体来说也不会得到普遍认可。斯密努力试图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结果是,斯密的一些论点模糊不清或者相互冲突,尽管他行文十分准确。实际上,在19世纪的世纪之交时,亚当•斯密的论点曾同时被支持最低工资的Samuel Whitbread和反对它的William Pitt用作论据。
一个相似的冲突是由累进税引起的,即税率随着个人收入提高而升高的趋势。斯密支持低税收,提出国民“应该按照他们分别具有的能力的比例,尽可能地为支持政府而缴税”。(第五篇第二章)这听起来像平头税(译者注:单一税率)。然而他又指出:“富人贡献给公共花费的不止应该正比于他们的收入,还应该稍高一些,这种方式是有合理性的。”(第五篇第二章)还有,斯密支持对豪华马车征税,这是对平头税的想法的诅咒。
斯密还支持施行普遍的政府资助的教育,这并不是出于效率或者再分配的理由,而是因为他相信劳动分工注定了工人要从事单调无聊、令人厌恶的抹杀他们才能的工作。他的经济政策具有社会和道德目标,而不仅仅旨在最大化国家收入。斯密相当程度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在《国富论》中斯密将人描述为通常情况下理性的决策者,虽然有时受“浪漫的希望”的诱惑而不理会他们的决定中内在的危险。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这个新近出现的研究人们是否理性地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经济领域,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认为市场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独有的:“交易、讨价还价、以物易物的习性……对人类是普遍的,而且没有任何动物身上具有这种习性。”(第一篇第二章)毫无疑问,他会惊讶于20世纪经济学家的发现,即老鼠和鸽子这样的动物在实验室条件下也会对经济学激励作反应,而且似乎总能展现始终一致的经济行为。不过,根据文献证明,推动市场活动在从共产主义到俘虏营的几乎所有人类环境发展起来似乎确是人类的趋势。就算对市场加以限制,市场的出现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斯密对市场运作最keen的观察归属于劳动市场。在第十章他提出了“平衡差异”的理论:“以不同方式使用的劳力和资本获得的净收益,在同一地区内,必须是相等或趋于相等的。”(第一篇第十章)这已成为现代的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均衡概念,它引出了工作条件的补偿差异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他提出了不同行业的工资不同的五个理由:(1)“劳动工资随着工作的难易程度、清洁程度、是否光彩而变化。”(2)“劳动工资随学习技艺时的简单、便宜和困难、昂贵而变化。”(3)“劳动工资随工作安定和不安定而变化。”(4)“劳动工资随工人受委托的责任大小而变化。”(5)“劳动工资随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大小而变化。”(第一篇第十章)
第一、三、五个理由可以认为是补偿差异:在一个充满流动性、信息充足(至少在边界上如此)的市场上,某些职位上的不合效率会被这些职位上高工资招募来的足够数量的工人而抵消。第二条理由是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均衡的直接陈述。第四条说明在与补偿差异一致的同时,可能解释为效率工资理论的原型更好,即付给工人工资津贴来确保他们负责任。斯密强调,个体经营不涉及责任问题;工人自己当自己老板不涉及有缺陷的监督和偷懒问题。
虽然我们必须尽力防止用21世纪的道德标准和经验来评判18世纪的哲学家,但考虑到斯密对劳动市场的敏锐洞察和他对个人自由的强有力的捍卫,他在奴隶制方面温顺的立场还是让人失望。斯密说:“我认为,所有年代的所有国家的经验证明了,奴隶完成的工作尽管看起来只耗费了维持他们的费用,但最后是所有可能中最昂贵的。一个不能获得任何财产的人出了吃得尽量多、干得尽量少,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兴趣。他做成的任何价值超过维持他的费用的工作,都只能是通过暴力从他身上榨取出来的,而不是处于他的任何个人兴趣。” (第三篇第二章)这种分析暗示奴隶制度不如付工资的劳动制度有利可图,是一种不可能在长期均衡中维持的状况。然而,在南部美国殖民地,没有出现任何奴隶制通过和平方式减轻的趋势。而且斯密指出,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释放奴隶的决定暗示着奴隶的数量一定不多,因为“假设他们是贵格会财产可观的一部分的话,这种决定不可能得到通过。”(第三篇第二章)另外,斯密关于奴隶劳动相当昂贵的论点与他关于糖行业比玉米行业获利高的结论是相悖的,其中前者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后者在英国殖民地不用太多奴隶生产。不管怎样,斯密并没有声明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原则性的立场,尽管它可憎地偏离完全自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预见了美洲殖民地会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不好说他是否预见了他的作品会对美国的发展产生影响。当斯密与Benjamin Franklin通信时,而且很可能在苏格兰或英格兰与他会过面,他对建国之父的影响是深远的。Samuel Adams,Thomas Jefferson,James Madison和Alexander Hamilton都研究过《国富论》。尤其是Madison,受斯密作品影响,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为完全的宗教自由而斗争。几年以前我的助教Melissa Clark发现George Washington也有一份《国富论》的拷贝,因为注意到了他在目录页的签名。那是这本书的第四版,出版于1789年1月,现在藏于Princeton大学的Firestone图书馆。(作者注:在第四版中斯密出了增加一个致谢外没有做改动。1789年晚些出版的第五版是斯密本人修改的最后一版。)
《国富论》第一次出版时斯密53岁。(作者注:也许是巧合,经济学领域接下来几本最有影响的著作都大约在作者相似的年纪时出版。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那年51岁;Karl Marx出版《资本论》那年49岁;Milton Friedman出版《消费函数理论》那年45岁,出版《美国货币史》时51岁(另一作者Anna J. Schwartz当时48岁)。关于经济学家们中年后就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巅峰的看法就说到这里。)他那时搬到了伦敦去监督这本书出版的最后阶段,并在他的好友David Hume生命的尾声时陪在他身边。本书出版后斯密在伦敦停留了两年。1778年他被指派为爱丁堡海关专员回到苏格兰,在他父亲曾工作的部门工作。他仍是一个单身汉,和他的妈妈和一个未婚的cousin平静地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由他照顾他另一个cousin的九岁的儿子。1790年7月17日斯密在爱丁堡逝世。讽刺的是,斯密对他一生没能成就更多有些失望。十有八九,他死时坚信《道德情操论》是他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如果学术成就是由后世评判的话,那么毫无争议,《国富论》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成功。确实,大多数战后的经济学,都可以理解为对理论上、实践上、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会失灵的解读。现代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强调,福利第一定理,即认为竞争均衡下一个人不可能情况变好而不使另一个人情况变坏的定理,在信息有缺陷或不对称的情况下不适用。类似地,未被注意的外部性(即私人交易溢出的效应不只影响直接参与交易的团体和个人)意味着政府干预可以改善自由放任时的均衡。交易成本和非理性决策也可能使经济背离最大效率。而非竞争的市场力量的运用,比如产品或劳动市场中雇主的勾结,也会降低市场经济的效率,正如斯密警告的那样。
现代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是,量化与斯密提供的完全自由的基准模型的偏差的重要性,并确定政府作为自由市场的替代,是否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比现状更好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亚当•斯密排好的议程表。亚当•斯密关于均衡的构想在225年后仍然是经济学的前沿,这是经济学作为科学进展缓慢的证明,也印证了他天才的先见之明。《国富论》继续着它对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哲学、历史和社会学领域,我怀疑斯密也会对此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