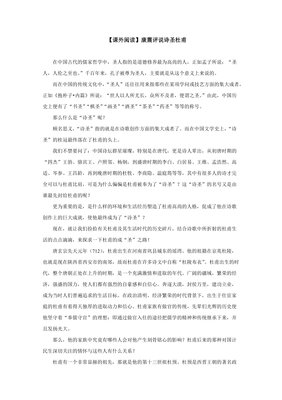杜甫选集读后感精选
《杜甫选集》是一本由邓魁英 聂石樵 选注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甫选集》精选点评:
●经典著作,
●2017年夏购于成都杜甫草堂,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多,总算读完了。
●2017
●生命中最后五年产量最高。这部分诗艺方面感觉更加无懈可击,一字不可易。然衰飒之气扑面而来,不复「树立甚宏达」「叹息肠内热」热血涌动矣。
●秋兴八首在技术上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如同大部分律诗一样,特定主题的作品,除了对从业人员,很难说能引起一般的当代兴趣。
●等我明年去成都看你
●不是我的菜,不懂ing
●比萧本好点
●赞
●前言写的不好。
《杜甫选集》读后感(一):妄言杜诗
对于杜诗,前贤之述,可谓备矣。然则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读诗所感,得无异乎?故妄言一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乃“老杜一篇心迹论”,仇兆鳌谓该诗“悲愤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可议矣”。其中“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数句,《杜臆》言“叙父子夫妇之情,极其悲惨。”乍一读不知悲惨何在?平铺直叙,毫无波澜。玩味多次,方知其悲惨在“里巷亦呜咽”五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邻居呜咽,如哭其子,乃非常情,可知诗人悲哀感人至深。极其悲惨,诚非虚言。
“人非西喻蜀,兴在北坑赵”,前句用司马相如事而加一“非”字,后句典出白起而着一“兴”字,诗人之意,不言自明。朱鹤龄云:“臧玠之徒,非可檄论,必尽坑之乃快尔”,应是不刊之论。然以今人视角观止,诗人之言,得无太过乎?但时代所限,加之诗人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出此愤激语,亦在情理之中。
另,该书《堂成》颈联“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而在《杜诗详注》中“飞鸟”作“飞乌”。不知该书何据?抑或是校对问题?
《杜甫选集》读后感(二):读杜甫诗
●下午读《杜甫选集》,极震撼,极心动,少陵年少之铿锵骨力又不同于建安诸子,少陵浑,字刚,建安悲,字劲。此亦可从苏李——建安——阮籍——初唐——少陵一脉观之。 少陵渐老,世事悲沉而笔力愈浑,遂隐刚以成雄。雄者,骨力自沉其中。 太白以心力所至,豪笔亦至,字出奇,想落天外;少陵以才力所至,驾轻就熟,运笔造字浑然从心。
●至梦李白二首,读“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直欲落泪,几下沉吟,痛怀难消,少陵之沉郁如此!沉郁者,深情之至也!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结发为夫妻,席不暖君床”“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真真是谁人忍读!不读又更有所失。 ●少陵中年时,历安史之乱,国家残破,民生潦落,诗中愤讽忧国之情力透纸背,流离颠沛,微躯困顿,忧民伤怀、思念之情深入骨髓。 年岁既去,白发生,体多病,遂变浩荡淋漓之情为广远含蓄之意,至此而雄浑再进一格,乃为《秋兴八首》。
●少陵居草堂,亦有萧散自然之风。将其写景句一同放入,则有:“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灯前细雨檐花落”
“水花晚色净”
“红稠屋角花,碧秀墙隅草”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细泉兼轻冰”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
“清江一曲抱村流”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江边一树垂垂发”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来花鸟莫深愁”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轻薄桃花逐水流”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春草满空堂”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清秋燕子故飞飞”
“佳人拾翠春相问”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细雨荷锄立”
“春岸桃花水”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尤为善用叠字。
《杜甫选集》读后感(三):“绮艳、清新与老成” ——论杜甫对六朝诗人庾信诗歌的扬弃
“绮艳、清新与老成”
——论杜甫对六朝诗人庾信诗歌的扬弃
杜甫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人,在诗歌的全盛时期唐朝,他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他开创了“沉郁顿挫”诗风,是律诗成就最高的人,除了忧国忧民之外,他的诗歌汇集了多种多样的风格,有清新、俊逸、明快等等,可以说杜甫是诗歌的集大成者。秦观曾经评价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秦观《韩愈论》)。关于杜甫集大成的论断后代学者大多认同。而杜甫集大成的原因在于他对前人诗歌的用心学习,他自己也曾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不仅学习先秦汉魏的诗歌风骨,也向六朝诗人学习诗歌技艺。在六朝诗人中,庾信对杜甫的影响最为深远,杜甫正确认识了庾信诗歌的价值,称赞其为“清新庾开府”,并向庾信学习,但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庾信。本文主要探讨庾信对杜甫的影响、以及杜甫对庾信的继承与超越。
诗史与诗圣
杜甫,字子美,自称“杜陵野老”,所处时代为盛唐到中唐的时期,经历了开元盛事和安史之乱。由于目睹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杜甫的诗记录了时代的兴衰,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他被人称作“诗史”。同时,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使杜甫的思想境界高于一般诗人。杜甫志在天下,有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政治上,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文学上,他力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不仅如此,他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仁爱之心,对家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诗圣”的称号给杜甫当之无愧。
杜甫的文学成就并不像李白那样来自“天才”,他从不讳言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做出的努力。意象方面,他“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歌结构方面,追求完美,“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诗律方面,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六朝诗人追求严谨格律的传统,在所创作的诗歌中达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的效果;关于诗歌的境界,他崇尚“凌云健笔意纵横” (《戏为六绝句》其一)。杜甫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杜甫思想平正笃实,并不排斥异端,他对汉魏晋和六朝诗人的诗歌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在诗歌上的苦心钻研,使他融汇了前代诗歌的精华,是诗歌的集大成者。
在魏晋南北朝中,对杜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六朝时期的庾信。后世有“杜诗本庾子山”[ 郭绍庾主编,富寿苏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5页]的说法,又有“庾开府是少陵前模”[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页。]的论断。这些评价说明了庾信对杜甫影响之深。
词赋罪人
庾信,字子山,他的创作经历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身处梁朝高位的时期,这个时期他的诗歌题材比较狭窄,不脱宫体诗的范畴,充满绮艳之风。第二个时期是他出史西魏,被强制留在北方的时期。虽然这时候他的诗歌仍有应酬之作,但他诗歌题材已经扩大,有了十分显著的“乡关之思”,感怀身世,诗风苍劲悲凉,跳出了宫体诗轻艳流荡的局限,更多对个人与国家、生命和宇宙的感慨和思考。
虽然庾信在六朝时期备受推崇,但在隋朝或初唐庾信却被扣上宫体诗人的帽子,大加批判,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如是评价庾信:
“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废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称庾信是“词罪赋人”,可以理解为隋唐变革齐梁绮丽诗风的需要,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庾信,他们没有注意庾信后期咏怀诗的价值,实际上却受到庾信咏怀诗的影响。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庾信后期诗作的人是杜甫。
杜甫对庾信的正确认识与时代分不开,杜甫所处的时代宫体诗风已逐渐褪去,此时可以不再以否定的形式来看待庾信的诗文,而注意到他后期诗文的重要价值。此外,杜甫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庾信相似,因此能够更好地和庾信产生共鸣。庾信经历侯景之乱,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上是一个为朝廷显贵作诗的傀儡,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无不在他的咏怀诗中体现出来。杜甫经历安史之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同样目睹了国家的丧乱,此时他更能理解庾信的“哀”。他在《上兜率寺》中写到“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此外还有“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论述。
绮艳、清新与老成
杜甫和庾信同样是集大成的诗人,庾信可以说是“六朝文学最后一个大作家”[ 鲁同群:《庾信论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在空间上,他以特殊的经历从南到北,融合了南北的文化;在时间上,他融合了魏晋文化和六朝文化,带着魏晋的风骨和六朝的声色。
庾信为梁朝臣子之时,其诗赋已享誉全国,有着极高的地位。这时他的时多是唱和应酬之作,后世流传的诗作不多。有《奉和泛江》、《奉和山池》、《舞媚娘》等,赋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三篇。《春赋》中“出华丽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池来里,花落山中。”“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等语句,充分展示了庾信早期诗歌绮艳的特点。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写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以庾信的清新和鲍照的俊逸来称赞李白的诗歌。“清新”也成了后世用来评价庾信的重要词语。什么样的诗歌能够称得上是清新呢?南朝诗论的“清新”指的是诗歌的省净、自然、清拔之气,更在于写景状物时的自然流丽。庾信即使是绮艳的宫廷诗中也不乏清新之句。如“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奉和山池》),“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奉和泛江》)。虽然晚期的庾信诗歌跳出了宫体诗风的局限,融合了北朝文化中那种开阔、豪迈、苍劲和悲凉的特点,但他仍然继承了在南朝流传下来的清新之风。清新与绮艳的不同在于,绮艳的侧重点是对诗歌内容轻浮奢靡的评判,而清新是对诗歌形式艺术的肯定。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句诗涉及到唐代诗人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和接受的问题,今人指的是庾信和初唐四杰等作家,而古人指的是先秦汉魏时期的作家。初唐诗歌,为了摆脱齐梁留下的浮艳之风,采取了厚古薄今的做法。他们一方面主张复兴先秦汉魏的古风,另一方面对于六朝诗人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诗歌创作进行否定。但杜甫认为,所谓今人的诗歌仍有可取的地方。可取之处便在于对诗歌语言艺术的锤炼。杜甫认为,诗歌本身是语言的艺术,应在推崇古人风骨的同时,兼收今人诗歌技艺上的成就。庾信诗歌尤其讲究对仗、炼字和用典,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是杜诗艺术上成就的渊源,黄庭坚曾评价:“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后山诗话》)[ 张忠纲 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01页]
再说到杜甫对庾信的另一个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关于“老更成”,一种说法是庾信文章到了晚年风格更加成熟;另一种说法是庾信晚年的文章成就更高。庾信后期的代表作
庾信的晚年和杜甫的晚年是契合的,他们有着相似的的生活经历,杜甫在国家动乱中更加更够理解庾信晚期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甫早年的诗歌洋溢着着一些盛唐时期的轻狂和浪漫,在《望岳》中,他用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出自己攀登山顶的雄心与气魄。而杜甫最为困顿的漂泊西南的时期,正好是他创作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创作出了“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闻军官收河南河北》等许多优秀的诗篇。“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荡人耳目、震撼人心的诗句,和庾信后期诗歌有相似之处,又超越了庾信。
集大成的超越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之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淮海秦少游《进论》)[张忠纲 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99页]
虽说杜甫受庾信影响很大,但杜甫并不仅仅局限与模仿庾信,他还向各家诗人学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同为“集大成”的诗人,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庾信,开创出自己“千汇万状、茹古涵今”的诗歌格局。
后记
或许现代人再谈到杜甫,除了小学中学时期背诵的一些诗歌之外,只有网络上那次轰轰烈烈的涂鸦风潮了。许多人在这次涂鸦浪潮中发泄了自己对传统教育的不满,然而他们并不会去关注杜甫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贡献,更不会去关注杜甫的思想人格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猥琐艺术的时代,杜甫式的严肃和忧愁会令人嘲笑,而娱乐和戏谑才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可以说,研究杜甫是个很难的任务,对杜甫以及杜诗的研究,前人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我迎难而上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杜甫是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越过的经典,不论我的研究成果如何,他的人和他的诗,都会对我的生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杜甫。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清]仇兆鳌 注,中华书局,1979年
【2】《杜甫选集》,邓魁英、聂石樵 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杜甫诗话六种校注》,张忠纲 编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
【4】《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吴怀东 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杜甫评传》,莫砺锋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庾信论传》,鲁同群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庾子山集注》,[清]倪璠 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8】《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杜甫选集》读后感(四):杜甫与巴蜀:见证盛世梦碎的痛苦灵魂
杜甫与巴蜀:见证盛世梦碎的痛苦灵魂
和运超
杜甫,中华文化里一座耀眼的丰碑,诗歌造诣和艺术思想都光芒万丈,但杜甫不像李白,他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甚至整个唐朝,除了元稹、韩愈、张籍等数人,赞许过杜甫诗歌的人也不算多。杜甫真的属于那个光环笼罩的唐朝吗?唐诗的荣耀在今天已经被扭曲或误解成田园山水的旅行日记,古诗的灵魂已经被当代人拆解的粉碎。
尽管游历四方是唐朝的风气,依靠比较完善的驿站驿馆制度,当时文人游历或出塞都是潮流。杜甫除了年轻时有过一段时间游历外,真正属于他的关键词是飘零甚至流浪!从唐朝盛世的迷恋到安史乱世的失望,残酷的社会给诗人服下一剂强迫清醒的猛药,无奈的现实教会杜甫如何做一个伟大的诗人。
从关中经历丧乱到寄居巴蜀苟且偷安——辗转流离十多年,杜甫从成都到梓州、阆州再到夔州,这七八年时间留下600多首诗,几乎接近他全部总量的一半(杜诗总共流传有1400多首)。杜甫的不幸换来中国古典诗歌最壮丽的丰碑,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感到五味杂陈,正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在关中:仕宦的绝望
在唐朝,从名相杜如晦开始,京兆杜氏家族达官显宦辈出。杜甫一家很早就迁居襄阳,以西晋名臣杜预为祖宗,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就自认是襄阳人。但杜审言其实是杜依艺在河南巩县做县令时所生,若论出生地,杜甫也要算巩县人。不过唐朝一般都尊崇祖籍郡望,所以一般还是算襄阳人。
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两人是宰相,崔融是皇帝近臣,中宗李显当太子时侍读,武则天和中宗有许多诏命都是他所写。而杜审言却官位很普通,最后是修文馆直学士,因为长年位居下层,在武则天后期为了出头而巴结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其实张易之也写诗,水准也还可以,《全唐诗》收录有几首),遭中宗流放峰州(今属于越南)。杜审言在“四友”中往往认为成就最高,他的诗有壮志难酬的郁结之气,显然后来被杜甫所继承。
杜甫年轻时曾游历,包括结识李白、高适一起游山玩水,当时创作应该不少,但他满意或者留下的比较少。杜甫显然并非天生就是“诗圣”的料,在那个“开元全盛”高手如云的黄金时代,他基本处于高手的下游。何况,杜甫前半生要算是“官迷”,背负京兆杜氏的家族荣耀,他自小聪慧,很有天赋,深受功名思想影响,渴望“致君尧舜上”,性格也一度桀骜,渴望到处交友互相攀援,然后顺利出仕,这是一种沉浸于六朝门阀习俗的方式,在唐朝依然大量存在。哪怕杜甫的出身并不差,可盛唐时代号称人才济济啊,孟浩然这类才子也多年隐居无人问津,“英俊沉下僚”一直是常态,一切都没有那么顺利。杜甫等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参加考试,结果落第。继续到处游历,到天宝三载(744)在洛阳同诗坛明星李白相遇。
无须忌讳,李白才华非凡,但也是积极经营名声的典型,他是通过道士吴筠疏通皇帝的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才把名声传到唐玄宗那里,李白的朋友圈多数都是道教信徒,终于被皇帝欣赏。可当真亲近了皇帝,不过把他当“道友”来礼敬,丝毫没有启用的意思。因为开元后期的唐玄宗已经疏于政务,痴迷修道,否则李白可能也没有机会真正接近皇帝。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前后把持朝政十几年,李白从长安灰心失意地离开了。据说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十分崇拜李白,两人关系暧昧。李白的诗中是一副铮铮傲骨,众所周知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名句,但李白对权贵的态度很难轻易说清。李白的第一个妻子是孟浩然介绍的许氏,为高宗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许圉师当年为人并不算多差,但时常以宽厚的名义袒护一些违法的事迹。李白和许氏生了儿子伯禽,据说算是倒插门,许氏开元后期病故。后来的妻子宗氏则是武后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而宗楚客的为人和名声就不算好。李白又与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关系复杂,所以,李白对权贵的态度很难轻易下结论,许多唐朝文人都为功名积极奔走,后人无须替古人遮遮掩掩。
杜甫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受到李白影响打算修道。直到天宝七载(748),杜甫才结束“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响应唐玄宗的求贤。但李林甫根本不打算推举人才,居然对皇帝说“野无遗贤”。杜甫仍然不死心,过几年进献《大礼赋》希望得到赏识,可唐玄宗不是汉武帝,杜甫也不是司马相如。论写诗,杜甫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公认是第一流,说他和李白是古典诗歌代言人,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但写文章,杜甫并不擅长,他不如李白,更不如后来继承他名号的“小杜”——杜牧。
杜甫的转变,在天宝中开始,李林甫专权、杨氏家族专宠,唐玄宗的昏庸越来越严重,杜甫敏感的艺术细胞忠实的记录了时代的不幸。古诗伟大的成就正是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但今天推崇的古诗基本是吟风弄月的雕虫小技,敢于撕开唐朝繁荣面纱的诗人从来不少,杜甫却无疑是划时代的一个!
《丽人行》《兵车行》《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歌,已经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也没有称颂“饮中八仙”的艳羡,年过四旬的杜甫开始“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代将这个一心想要做官求发达的儒家子弟磨砺成一面“风月宝鉴”,照出“繁荣盛世”之下的破败真相。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敢于写杨家姐妹和杨国忠的嚣张,这只是小试手笔,《兵车行》记述真实见闻,“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犹如镜头画面一样呈现帝都长安城外的一幅哀鸿遍野的乱象,这哪里是什么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杜甫出城询问路人,才知道这是朝廷“征兵”,强拉民夫入伍,“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什么样的作品才叫一首诗?情感往往被认为是第一位,但伟大的诗歌情感一定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杜甫所处的时代丧钟已经敲响,他不像王维隐居山间别墅,靠着躲避现实沉迷佛学隐藏情感,杜甫的情感一直是那么饱满!“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样的诗句简直是对号称圣君在位时代的强烈控诉!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既有激烈的批判,更有血淋淋的现实描绘,这背后正是一个异常勇敢而悲天悯人的伟大灵魂。
安史之乱爆发,盛世唐朝没有悬念的天翻地覆了,杜甫开始下半生的飘荡!《羌村》《悲陈陶》《北征》《瘦马行》《三吏》《三别》《洗兵行》《哀江头》《春望》,天宝后期到安史之乱间一系列的大作,注定会使杜甫载入煌煌史册!
杜甫陷入被乱军占领的长安,但他的地位很低,没有像王维那样被强迫拉出来接受官职,但杜甫亲眼目睹长安的悲剧,然后一心要去投靠在灵武继位的肃宗。由于曾经陷入乱军,虽然出于满腔忠心被任命为左拾遗,杜甫和他敬佩的李白遭遇一样,在皇帝的身边,却从来没有过要重用的意思!似乎还颇受排挤。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内心很感激天子,做事很认真,没多久,宰相房琯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接连上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好在有人在皇帝面前说,杜甫是在大乱中千里迢迢来投奔的忠心官员,这才把他放回家去。杜甫很郁闷,他送别在长安有共同经历的画师郑虔,他在送别的诗中感叹,郑虔临老被嫉恨接受过安禄山的任命而遭流放台州,这,就是苦苦等来要扭转乾坤的大唐中兴之新君!而郑虔在玄宗时代被皇帝评价为“诗书画三绝”,是否郑虔的流放背后还有其他的弦外之音?对于一个已经年过七旬的老者,杜甫饱含深情的写《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可谓字字心酸,句句含泪:“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果然,七年后郑虔死于台州,两人再无缘重逢。
杜甫对成王(后来的代宗李俶)、郭子仪、李光弼等充满期待,但战事并不如预期,一开始,唐军连连败绩,大量减员。为了扩充兵力,唐军疯狂征兵。杜甫被贬官后开始四处漂泊,把百姓的苦难灾祸统统写在诗里,正是杜诗被誉为“诗史”的宝贵价值。像《北征》和《三吏三别》都是非常深刻的纪实之作,可见当时唐朝的狼狈和殃及普通民众的悲剧!
就在写《三吏三别》的这一年,杜甫48岁,安史之乱进入第五年,关中发生饥荒,他被贬官到华州,生活落魄无奈,半生官迷的杜甫终于决定放弃官职,选择投奔亲友,先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那里有侄儿杜佐和个别友人,留下作品有《秦州杂诗》等,没多久他又去秦州南面的同谷,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记录了自己的惨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这种自我调侃的作品,无奈表达了当时的落魄,然而,同谷的日子不过是他凄凉后半生的序幕而已。
在同谷的时候,他打听到好友高适出任彭州刺史(今四川成都市所属彭州市),同僚裴冕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一度为宰相),杜甫为了改善生活,决定南下蜀中投奔好友故旧。伴随唐玄宗逃难入蜀,大批朝廷官员和长安富户大族都纷纷举家迁徙入蜀,形成一股移民潮流,正是唐玄宗和之后唐僖宗前后两次入蜀,为四川历史上北方世家大族迁居巴蜀的高峰,也因此促成五代两宋巴蜀文化300年的空前繁荣。其实除了朋友,杜甫也有亲戚在巴蜀,像舅父崔明府,表弟王司马等。
二、在巴蜀:天地一沙鸥
杜甫迁居巴蜀,寄居草堂,最后东迁夔州离开巴蜀,是奠定其伟大地位的重要支撑,也是发现其价值的最佳切入点。
杜甫在前往成都的路上就开始写诗给裴冕,各种称赞。另外高适年轻时就与杜甫结识,算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但裴冕曾是杜甫上级,所以杜甫刻意讨好裴冕。裴冕在拥戴肃宗登位时最为积极,前后上书六次。裴冕起初在成都,而玄宗也在成都,居然不知道眼皮底下的人已经改换门庭,可见当时玄宗的落魄和昏庸。史书说,裴冕从哥舒翰军中改任御史中丞,入蜀途中遇到北上经过平凉的太子李亨,裴冕深入为李亨分析形势,大胆劝进,成为有定策大功的人,很快被提升为宰相,召去皇帝身边。杜甫来到成都没多久,裴冕就离开了。
平心而论,裴冕对前来投奔的杜甫是照顾的,起初安排居住在西郊的寺庙。之后,杜甫的表弟王司马帮助建造了草堂。众所周知,草堂是十分简陋的“茅屋”,经常需要修整,杜甫已经很落魄,到处筹款,寻求好心人,这都散见于他的诗,如《王录事许修草堂资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资,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把催款这种尴尬的事情都忠实写下,杜甫的“诗史”之名,也非全都是宏大叙事,这种生活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光是催款这类事情,杜甫还到处讨要桃树苗、松树苗、竹子和一些果树苗,这才把草堂周围经营的像个样子,此外,他还有讨要瓷碗等生活用品的诗歌。
尽管杜甫在成都日子艰苦,却成为他后半生相对平静的阶段。据统计,杜甫一生1400余首诗,仅在成都就作了约475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后到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又做了410首诗,因此在巴蜀之地,他的诗歌就占到一生创作总量的一半多。
从诗歌选材看,杜甫在四川的写作范围有所拓展,相较于前期的关注时事政治、社会现实,杜甫在川开始创作关注百姓生活的农事诗,比如《为农》《种莴苣》《刈稻了咏怀》等。另外,可以得知杜甫在蜀中曾游览许多古迹名胜:成都武侯祠、相如琴台,蜀州新津修觉寺、东亭、四安寺、青城山,梓州射洪县陈子昂故居,牛头寺、兜率寺、玄武观,汉州房公西湖,忠州大禹庙、龙兴寺,夔州白帝城、武侯庙、白盐山、先主庙等。这些巴蜀名胜古迹,有些已经堙没不存,通过杜甫的作品,一方面可以了解唐代杜甫所处时代巴蜀文物存留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巴蜀的名胜古迹起到推广介绍的作用。 像成都武侯祠,杜甫的名作《蜀相》影响流传非常深远,这是杜甫初到成都不久去武侯祠瞻仰诸葛亮遗迹所作的名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传诵的名句,对成都武侯祠的闻名天下起到了极大的传播作用。
历史上,巴蜀民俗与中原民俗有很大不同,杜甫在蜀中的诗歌创作便有所反映。比如,杜诗中的“远烟盐井上”(《出郭》)记录了唐代成都人食井盐的习俗。“鸬鹚西日照”(《田舍》)、“鸬鹚莫漫喜”(《春水生二绝》之一)等诗句表现了成都地区喜好养鸬鹚的民俗。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杜甫的诗歌记载了不少蜀中特产。比如“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记录蜀中盛产美酒;“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谢严中垂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记载青城山特产的乳酒;“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记载大邑特产瓷碗;“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记载了四川的雅鱼及郫筒酒。此外,杜甫在成都所作的《石笋行》《石犀行》还对四川的土俗迷信进了批评。
但在巴蜀时期,杜甫依然有大量痛斥现实,哀叹民生的经典,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冬狩行》、《登高》、《秋兴八首》、《江汉》《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耳熟能详的经典笔者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提一些相对冷门的作品。如《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通过一个寡妇的扑枣,到处蜀中虽无战事,但民众依然受征兵的困苦,家中妇孺无依无靠的残酷现实。另外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尖锐指出唐代府兵制崩坏,男子服役已经没有年限的事实,诗歌写的老汉之子正因为严中丞严武到任改变,大儿子得以回乡务农为老汉家里带来一些希望,且就算朝廷增加苛捐杂税,宁愿一家人死在一起。从一种调侃和奉承的“酒话”中道出当时严酷的社会真相!
再如《冬狩行》是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在梓州所作。全诗最后写:“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施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前面写蜀中兵马狩猎演武如何威风凛凛,最后却直指代宗因躲避吐蕃而仓皇逃离长安,躲到河南陕州等着救驾,简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在裴冕离开后,后继者严武给了杜甫很多照顾,严家与杜家算是世交,严武为剑南节度使,经常到草堂探望杜甫。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曾短时间出任中书令,后被李林甫排挤离开,最后郁郁而终。严武也是从哥舒翰军中跟从肃宗到灵武登位的功勋大臣,因此派严武出镇西川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充剑南节度使,为了对付吐蕃,合剑南、东川、西川为一道,支度、营田、招讨、经略等统为一体,严武的权力就相当大了。
宝应元年(762)代宗登位,严武被召还朝,杜甫送他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市),恰巧发生徐知道之乱。杜甫在梓州(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阆州(今四川南充市所辖阆中市)避乱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杜甫的心情和想法发生了变化,担心此后一家在蜀中的生计,所以一路送严武到绵州,表现很纠结。新登基的代宗推翻了一些肃宗时的旧案,部分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是在肃宗时因力挺房琯而被排挤,此时新君登位不免心痒,可能希望严武回到朝廷以后设法相助。而严武多次打算推荐杜甫,都被灰心失望的杜甫三番五次婉拒了。
不久,严武第三次镇蜀,杜甫不待严武相请,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杜甫一生最高官衔莫过于此。这段时间里,杜甫或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协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泛舟,此时严武的权力地位达到巅峰,久而久之,年长十四岁的杜甫对严武的“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新唐书·严武传》)产生异议,并作《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和《说旱》一文进行讽谕和谏诤;同时又打起退堂鼓,在诗中多次表示辞幕归隐的意愿:“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到村》)、“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
杜甫的幻想彻底消逝,与严武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由于杜甫反复要求离开幕府,使严武颇为心烦,也颇为心寒。杜甫托病辞归后,虽然作有《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一诗,盼望严武再次光临草堂,但从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诗,也看不到严武再来“草堂”的痕迹,甚至连诗歌唱酬也没有了。杜甫与严武的关系为何急转直下,历史上众说纷纭,成了杜甫研究中的重要疑点。
最让人疑惑的还有杜甫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史籍所载严武的反应截然不同。第一种是“不以为忤”,如《旧唐书·杜甫传》:“(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但“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如《唐摭言》卷十二说杜甫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严武:‘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面色大变,正待发作。杜甫赶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审言的孙子。”勉强缓解了尴尬气氛。第三种是怒至欲杀。《新唐书·杜甫传》说严武耿耿于怀,表面上原谅杜甫,有一天瞅准机会就要杀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幸亏有人去通报严武的母亲,严母深明大义,“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云溪友议》),杜甫得以保全,可与杜甫交情甚笃的章彝却成了刀下之鬼。章彝就是杜甫在梓州写《冬狩行》中的主将,客观上说该诗有赞美也有讽喻,但杜甫在梓州很受照顾,章彝也想推举杜甫,可能与严武之间发生了不愉快。
虽然最后一种要杀杜甫的说法可信度不算高,但杜甫与严武之间到了非常敏感和紧张的地步,却是事实。杜甫在严武患病之前就离开成都去了夔州,没继续在成都住下去也是事实。不光严武和他关系崩坏,其他人在严武权势地位的影响下,也就再没有谁肯去资助杜甫,这种生存环境压力导致杜甫离开了成都,相信距离事实差距不会太远。
像严武这种过去关系非常好的故旧朋友,也就是一个地方大员,但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已经彻底没落,地方大员变相成为“藩镇”,几乎轻易掌握了官员和民众的生杀大权,这种时代风气完全改变,这还是杜甫所盼望的“中兴”之兆吗?
永泰元年(765),严武患病暴毙于成都,年仅四十岁。严武母亲护送严武的灵柩顺江东下,途经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杜甫写了《哭严仆射归榇》:“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杜甫一生交友不少,除了李白这种聚少离多,交浅情深的特例,事实上严武要算杜甫交往非常密切,也非常重要的人。严武年龄小杜甫十几岁,也作诗,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武将,个性、见识和追求各方面都与杜甫有较大差别。二人有过关系非常好的时期,当杜甫亲眼见到严武故去,还是写了一首诗。即便如此,与哭悼房琯、高适、郑虔这一类友人的感觉很不同。
杜甫从嘉州、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于大历元年(766)至夔州,次年在肃杀的秋天气氛中,他写下了悲壮的《登高》,号称他最后的压卷之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抒发了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悲哀之情。
其实夔州都督柏茂林对他多有帮助,他第二年迁居夔西,经营有四十亩柑橘园,又租得东屯的一些公田雇人耕种,生活再次算相对稳定下来。在夔州近两年,杜甫作诗达430多首,除了《登高》,另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名篇也作于此时。
步入晚年的杜甫依然有关切普通民众的作品,像《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还有像《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因为当时到处战祸连连,晚年杜甫思乡心切,在巴蜀继续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出夔门到江陵,南下公安到岳阳,杜甫一直都住在一艘小船上,几乎沿途乞讨。杜甫想要去郴州(今湖南郴州)投奔舅父崔湋,南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到耒阳遇到江水暴涨,无法前进,五天没有进食。最后县令给他送来食物,决定北返,却因为长期饥饿,凄凉死在了从潭州返回岳阳的那艘飘泊无依的小船上。
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离开巴蜀后,竟是这样暗淡的结束了一生。
不光一个杜甫,之前761年(肃宗上元二年),半官半隐的王维因“安史之乱”中有不良记录而被降职留用,不久死在尚书右丞任上。次年,侥幸从流放夜郎途中获得赦免的诗仙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765年(代宗永泰元年),杜甫的至交好友、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死在刑部尚书任上,追赠礼部尚书。
就在杜甫病故的同一年,同居巴蜀的另一个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也从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市)任上罢官,在杜甫曾经待过的成都一家旅舍中含恨告别了人世。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文人墨客的凋零和退场,这是号称李唐时代最辉煌一幕的徐徐落下。如果仔细品读杜甫,包括一众唐代伟大诗人们的诗歌,其实骨子里全都是目睹这场繁华盛世美梦粉碎的声音……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