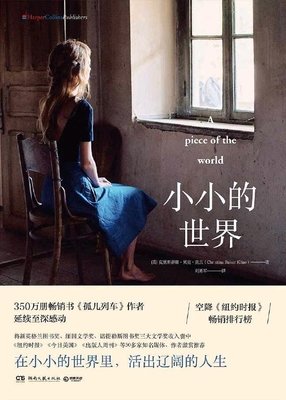《地下伦敦》读后感摘抄
《地下伦敦》是一本由[英]史蒂芬·史密斯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4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下伦敦》精选点评:
●本来这样的内容可以写得很有趣,但原文流水帐,而译者又自作多情……我对译者那“归化”翻译很想死……如果意译得有趣、体现英式幽默也没什么,但那些词太穿越了啊,他以为伦敦是老北京呢……(而且很多已经有固定俗名的东西都被改掉了,摔!)
●翻译太差太差了 有那种自以为很俏皮的多余感 翻了四十页发现真的忍不了
●看看。翻譯不太行。
●書本身是不錯的,可這翻譯是在是太浮華,看似文采斐然,實則孔乙己式的之乎者也。若沉靜用功,是可塑之才。
●如果我是译者以后就没脸见人了= =
●译者太造作了。
●话说,坐了那么长时间的伦敦地铁,怎么就没发现你说的那些呢
●很有趣
●地下啊啊 写得乱七八糟啊啊
●此书翻译真是有一股神奇的地底之气....
《地下伦敦》读后感(一):更污秽,更黑暗,也可能更真实
地上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下,时时炫耀着表象,这些东西断不了氧,所以才能用奢靡、浮华和光鲜示人,等到哪天它们被深埋入地下,我们才更容易剥掉阳光给它们镀的金,接近它们已是过去时的真相:更污秽,更黑暗,也可能更真实。
还在读,已经发现这本书的趣味所在了。路过正在修的地铁线,总要忍不住在心里笑一下。
《地下伦敦》读后感(二):翻译的问题
书挺有趣,翻译还行但有些地方刻意追求音意相照反而让人读的有点不舒服。我英文是很糟糕的,能指出的只是一些常识性错误,现在还没看完,待补充。
1,63页译者注2——这个错得相当劲爆,竟然说“《1984》里的101号房间是主角史密斯的房间”。
2,把“我来,我见,我征服”翻译成“孤来矣,孤见矣,孤胜矣”倒是蛮有趣,不过孤是帝王专称,却不知原文是不是也一样?
3,297页译者注:“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怪兽]”……拜托没有知识也请有点常识……
《地下伦敦》读后感(三):地下世界
在深圳的图书馆无意间邂逅的一本书。只因找不到合适的书本,顺手拾起别人看过的名目。看书养成的习惯是看到优美的字句总会刻意的摘录。一本可以让我边看边摘录的好书。
可能是封面黑色衬底的缘故,亦或是字体的大小很符合我的感官的需求,也可能是摸着纸张从手指传来的温柔舒服的触感。让我想一慨真书真不错的想法。
地下会有什么你感兴趣的,地铁,隧道,漆黑一片闲置不用的通道,或是某个传说中的宝藏地点。
地底的世界,渴望呼吸的新鲜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伦敦是个古老的城市,不善变,保留历史的原味,或许有机会探访他的地底世界,我会准备一把手电筒,带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出发。
《地下伦敦》读后感(四):不说话的历史
长安街边上两幢五十年代的大楼计划炸毁,准备给全球化腾地儿。轰隆一声倒下多么的壮观,象征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可是不能这样干,因为下面有庞大市政管网,犹如城市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下面是更庞大的地铁系统。地铁下面还有未知的军防设施,再下面,可能还蕴藏着一座文物古城。
90年代中期珠海巨人大厦烂尾,欠一屁股债的史玉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因为楼只刚到正负零,他硬说钱已经花了70%。10年之后,人们发现史玉柱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一方面他还清了巨债,另一方面,人人都搞了一回房地产,明白地下工程花钱如流水。
小时侯,小朋友们最热爱的聚会场所,就是防空洞。县城的医院背后就有一个,而且停尸房就因地制宜建在防空洞的入口一侧。经常洞里都能发现残缺的死婴,甚至说不定被遗弃的女婴。当年胆子大是因为没看过那么多恐怖片,大家在洞子里打着手电人吓人。
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人对黑暗有着天性的迷恋,一如对未知的好奇。第二个故事说明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只是冰山一角。第一个故事意味更深:城市不会自己说出自己的历史,城市的历史,就象手上的掌纹。
史蒂芬史密斯写《地下伦敦》,就是源自这样的天性,深入伦敦地下,把人们不知道的伦敦历史翻出来晒太阳。
《地下伦敦》读后感(五):不是每个译者都可以成为林纾
如果抛开翻译的问题,<Underground London>这本书至少是可以打四星的。译者在译后记中说“英伦风土人物的专名,原则上从俗从众,但很多并无定译,或无人译,不才即随心为之”。因此,将“忏悔者爱德华”译为“忏愆悔罪王爱德华”、“征服者威廉”译作“跨海平西王威廉”,是“不从普通辞典”;将俗译的“舰队街”译作“弗沴街”,是为了“音义相称,不忍拟音而废义也”;将“白厅”译作“玉堂”,是“希望译名中能昭彰出英伦王家的气象来”。在译者看来这些处理或许是为了追求情趣,彰显雅言之魅力,可惜译者的功力不比林纾,很多细节上可以看出对英伦风土人物也不了解,就是中文的功底也不见得多么出色。
如征服者威廉、忏悔者爱德华这样的人物,学界早已公认,“忏愆悔罪王”“跨海平西王”这样的翻译着实不伦不类,“不从普通辞典”在LZ看来更像译者的借口——试问译者,风土人物不从普通辞典,专有名词不从俗从众,为何伦敦要译作伦敦,白金汉宫要译作白金汉宫?大名鼎鼎的布赖顿您不是已经译作“伯瑞屯”、格拉斯顿伯里都成为“玻璃岛”了么?
为了音义相称,“葵蔻林地”和Cricklewood、“西寒鸶台”和West Hampstead可没有联系呀,这几个地名看上去仿佛是意译来的,实际上完全是译者用他阳春白雪的思维和古僻的字句生造的音译,是不是可以算因音骇义了呢?
再有,蒲珀被译作“波普”,迪斯累利被译作“迪兹瑞利”,兰姆和劳合·乔治的名字均被译错,甚至将波尔图译作波尔多,连美国爱荷华州的首府也被擅自改名了,译者对“英伦风土”的执着是不是太普世了一些?
抑或,译者真的没有好好查阅翻译工具书吧?
LZ为商务印书馆译过书稿,随原稿寄来的第一份文件便是四页纸的翻译注意事项,详细规定标点符号的使用、容易混淆的字词用法,以及人名地名的翻译。LZ和许多译者都遵守的规矩,怎么在这位译者手里,因为一个轻飘飘的“并无定译,或无人译”就给抹杀了呢?敢问译者说无定译的,您是否查过地名学会的手册和工具书了?那无人译的,是真的几十年来无人译过,还是译者您没有读过所以不知?不服“从俗从众”的原则就能彰显译者的才情和水平了,您那佶屈聱牙的译名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和理解负担呢?大家熟知的温布利球场被您译作“稳步里”,这就显得您才高八斗了?帕丁顿被译作“葩町屯”,就衬托出您的旷世才情了?试问大家都向这样“随心为之”,翻译界要乱到什么地步?所有风土人物不标原文怕是没人能参透其原貌了吧?如果这样,还要译作中文作什么?
LZ觉得这样轻率的解释,完全是译者的态度不够踏实、工事浮华之故。以下是LZ读书时记下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由于没有本书的英文版,个别句段只能凭揣测了。
.03
圣若望林地(St John's Wood)这个译名不合适。因为St John's Wood是在约翰王将之赐给庇护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之后得名的,这个骑士团别名圣约翰骑士团,St John's Wood中的St John就是指骑士团的守护圣徒。
.04
Lord's Cricket Ground被译作“贵族板球场”。
事实上,Lord是这座板球场建造者的姓氏,故此处当以音译为宜。
.11
南渥坷(Southwark)是大伦敦的一个区,地名学会是颁布了标准译名的,应当作“萨瑟克”。
.20
Colosseum被译者译作“圆形大剧场”。
首先,这个东西国内一般译为“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是拉丁语中“巨大、庞大”的意思(参考现代英语中的colossal)。并且,罗马斗兽场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矗立在其近旁的尼禄巨像,而非斗兽场本身的体积。
其次,斗兽场和剧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古希腊罗马的剧场通常为半圆形,罗马人首创将半圆形剧场建造为整圆或椭圆的Amphitheatre,主要进行斗兽、竞技等活动,戏剧仍然在传统的剧场表演。Amphitheatre这个字来自希腊语,amphi-意为“围绕、双方”,théātron则是“观看的地方”,不是什么“剧场”。
.36
Fleet Street在这里被译作弗沴街,我们通常的译名是“舰队街”,虽然是误译但毕竟深入人心,这里总觉得还是别扭。
不过,这个是小问题。这一页主要的问题是“僧侣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和圣巴塞罗谬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两个译法上。
Knights Hospitaller在网上一般被译作“医院骑士团”,因为hospital在当代的确是医院的意思。不过在中世纪,hospital指的是收容病患、接济穷人、供朝圣者投宿的收容所;也因此,英语中的hospitality是“好客”之意,和“医院”毫无关系。然而将Knights Hospitaller译作”僧侣骑士团“确实出格太多,译名和原文根本没有关系。
接下来是圣巴塞罗谬医院。hospital的涵义在上一段中已经解释了,因此下一句中“就诊”完全是无稽之谈(希望有英文版的读者能提供原文比照)。Bartholomew是《圣经》中记载的使徒,和合本译作巴多罗买。作为传统教名,一般译作巴塞洛缪。译者在这里将其译作“巴塞罗谬”,但在下文中又作“巴尔多禄茂”,已经不是“图存其神气”能够解释的了。
.41
Mansfield Road被译作“力田街”。Mansfield一般译作曼斯菲尔德。
.42
Cressfield Close被译作“堇田圃”。Close在英式英语中的确有“教堂围地”的意思,但就LZ在英国生活旅游的经验看来,Close在地名中更多指“小巷”、“过道”。
.43
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珀(Alexander Pope)在这里被译作“波普”。
.45
“在教堂南边,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拱门高耸。”
这一句疑有误。St Pancras Old Church位于伦敦城北,维多利亚车站位于城南。且根据下文接着介绍国王十字车站(亦位于城北)来看,这里的“火车站”指的可能是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该车站建于维多利亚时期,邻近St Pancras Old Church,与国王十字车站只有一墙之隔。
.47
ewcastle Close被译作“新堡圃”。
Close的问题不想再多说了,既然下文说这个Newcastle Close这个地名是由于“自打十二世纪起从英格兰东北运到伦敦的煤都在这里卸货”,Newcastle为何不亦称大家熟识的“纽卡斯尔”?纽卡斯尔建于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纪,是金雀花王朝在英格兰北方的重要壁垒。
.57
enjamin Disraeli的通译是“迪斯累利”而非“迪兹瑞利”。
.59
“伦敦各大学校长”一句不解,伦敦大部分大学到十九世纪才创立,在十四世纪的法案里出现颇为诡异。怀疑原文是chancellor(天主教司铎,教区事务管理者),求真相。
.60
将Whitehall译作“玉堂”。虽然译者在后记中解释如此行事是为了凸显英国王家气派,但是LZ觉得,白厅(Whitehall)和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要分清楚吧?前者是一个地名,后者才是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宫所在——而且,它哪里气派了?
.86
凯撒的名言“吾来,吾见,吾胜”被译成“孤来矣,孤见矣,孤胜矣”。
首先,凯撒生前从未称帝,自称为“孤”是不妥,译者自作主张用“孤”,则不知道是不熟悉罗马历史,还是不熟悉汉语尊卑了。
其次,凯撒此句之所以成为名言,是因为其简洁有力。拉丁文原文为Vini, vidi, vici。中文无法像拉丁文一样以动词变格来表现人称时态,故在翻译时必须加上了主语,但再在句尾加“矣”则画蛇添足,凯撒原文的气魄便没有了。
.91
稳步里球场(Wembley),更加通用的译法应该是“温布利球场”吧?
以及,艾米丽·勃朗特的姓Brontë被打成了Bront?(92页)……
.94
萨里郡(Surrey)被译成“瑟瑞”。
伦敦大火纪念碑(The Monument)被译成“大灾纪念柱”,应该是译者对十七世纪历史缺乏了解?
.95
“他还是摩托车赛和极品飞车的车迷。”
译者他知道极品飞车是一款游戏么?而且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专名了不可以随意借用。求“极品飞车”原文真相(该不会是F1……吧)
顺求本页脚“提心吊胆”一段原文真相……
.107
祆教的光明神密斯拉(Mithras)被译作“秘特拉斯”。
.109
帕丁顿(Paddington)被译作“葩町屯”。
.110
小伦敦城被称为The Square Mile,是因为伦敦城墙以内土地的面积只有1平方英里——但是译成“一亩三分地”是不是离谱得过头了?
.112
达拉谟(Durham)的通译是“达勒姆”。
.140
古罗马的海神尼普顿(Neptune)被译成“奈波涛”。
.165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被译作“玻璃岛”。
.167
“京兆尹”……我猜原文是Mayor of London——伦敦市长吧?
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被译作“牡鹿津郡”。
.175
里士满(Richmond)被译作“列治文”。
.176
The Mall的通译为“林荫路”,是圣詹姆士公园和白金汉宫之间的道路。
译者将St James's Park译作“圣雅各公园”,须知《圣经》中雅各的拼法是Jacob。
.181
tar Chamber是英国中世纪的王室法庭,内战前夕迫于民愤才被取缔,而非什么“星辰厅”。国内一般译作“星室法庭”或“星星法院”。
.195
eaker's Court被译作“言事院”。事实上,Speaker指的是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而非“发言者”。
.196
t Stephen Chapel被译作“圣斯德望礼拜堂”。Stephen是《圣经》中记载的使徒,和合本译作“司提反”;作为常用教名,通常译为“斯蒂芬”或“史蒂芬”。
.200
梵蒂冈(Vatican)被译“梵谛冈”。
.224
查尔斯·兰穆(Charles Lamb)和玛丽·兰穆(Mary Lamb)
姐弟俩的姓当作兰姆。兰姆是著名散文家,著有《伊利亚随笔》,姐弟俩还一起编纂了《莎士比亚故事集》。
.242
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应当指Athenaeum Club,是伦敦的一家高级俱乐部,马修·阿诺德、J.M.巴里(《彼得·潘》的作者)、阿斯奎思、柯南·道尔、丘吉尔、达尔文、狄更斯、T.S.艾略特、托马斯·哈代、沃尔特·司各特和叶芝都是其会员。‘
.253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波尔多”葡萄酒,英汉对照给出的是“波尔多(Porto)”,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orto的标准译法是“波尔图”,位于葡萄牙;红酒之乡波尔多拼作Bordeaux,位于法国西南部。
.254
德国的特拉贝特汽车(Trabant)被译成“拖大笨”。
.256
avoire-faire是“社交手腕”、“交际能力”之意,不是什么“慧眼独具”。
.259
《故园风雪后》(Brideshead Revisited)
我记得这部电影的名字是《故园风雨后》……
.265
中土银行(Midland Bank)——不是一般叫米兰银行的么?
.267
英格兰海滨城市布赖顿(Brighton)被译作“伯瑞屯”……
之所以对这条特别敏感是因为LZ在英国的时候就住布赖顿= =
.287
桑给巴尔(Zanzibar)被译作“赞吉坝”,我认为这么大一座岛屿的名字如此随意地处理了真的很不好。
.288
Duke of Sussex被译作苏塞克斯公爵,事实上Sussex的发音是“萨塞克斯”。下文中又将萨塞克斯公爵的第二任妻子称作“填房”,之后又称其为“第二位皇妃”,完全没有搞清等级尊卑。
萨塞克斯公爵是乔治三世的第六子,书中提及去世的威廉四世是他的兄长。萨塞克斯公爵的确娶过两位妻子,二人均是贵族出身。第一位妻子Augusta Murray由于结婚手续不合法(1772年《王室婚姻法》),无权享受公爵夫人的头衔和王子妃的地位;第二位妻子Cecilia Letitia Buggin在嫁给公爵的前一年将自己的姓氏改为Underwood(是她母亲的姓),但其父是第二代Arran伯爵,论出身算是正统贵族。Cecilia生前亦不曾享有“萨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但维多利亚女王在1840年授予她因弗内斯女公爵的封号。
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公爵的两位妻子最多有资格称为Princess(王子妃),而不是王后,和“皇妃”更是两码事。
.291
爱荷华州的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被译成“迪莫伊”。
.303
Cyprus一般译作塞浦路斯吧?这里是伦敦城东轻轨的一个车站,但是既然Little Venice能译成“小威尼斯”,为何Cyprus要译作“青铜屿”?
.332
贝克街(Baker Street)被译作“焙烤街”。
这大概又是译者想太多,贝克街得名于其建造者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和面包房师傅没有关系。
.333
在LZ的印象中,Finchley Road通常被称为“芬奇利路”,而不是“飞禽畾路”。
.335
天使车站不是“死站”,今天仍然在使用中。废弃的仅仅是一部分旧站台。
.338
大卫·洛易得·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应为“劳合·乔治”。
.340
eachy Head的官方译名为“比奇角”,位于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市和布赖顿市之间,而非“伦敦的跳崖圣地”。
.344
“莫拉蒂”(Moriarty)——既然指明是福尔摩斯的对头,为何不从俗译为“莫里亚蒂”?
.375
Tesco译成“特易购”。我不记得这是哪个地区的译法了,不过Tesco中国采纳的官方译名是“乐购”对吧?
以及(感谢无机客提供修正^_^)↓
特易购是Tesco在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译名,而乐购原本是台湾顶新集团经营的品牌,Tesco逐步收购,接管了经营,但保留了乐购的名字,品牌名由“Hymall乐购”修正为“TESCO乐购”。
.376
《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被译成《奇情博士》。
.392
“圣潘格拉车站那座无中生有的站台让哈利·波特搭上了去魔法学校的火车。”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在国王十字车站而非圣潘格拉斯车站,国王十字车站位于伦敦的圣潘格拉斯区。
.406
理查德·道尔2003年的小说《洪水》(Flood)
我记得改编的电影是叫《水啸雾都》吧?
.429
City of Dis被译作“抵死城”
Dis Pater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王,与希腊神话中的普路托(Pluto,又名Hades)相仿。在基督教神话中,Dis亦为魔王撒旦的别名。但丁在《神曲》中描写了la città ch'ha nome Dite,是地狱九圈的第六圈,中文一般译作“狄斯”。
.432
ond Street被译作“证券街”。
这又是译者太过执着于意译导致的错误,Bond Street得名于托马斯·邦德爵士(Sir Thomas Bond),和“证券”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