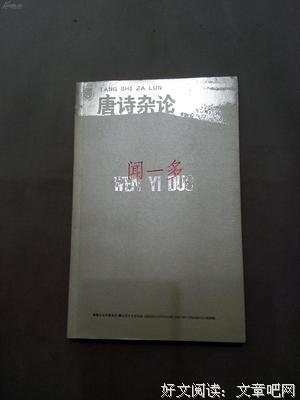唐诗杂论读后感精选
《唐诗杂论》是一本由闻一多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诗杂论》精选点评:
●三星半,遗憾此书未完成。格外喜欢讲宫体诗和杜甫的两篇。虽然作者“杜甫品格高于李白”的论断过于简单粗暴,但颇得中国传统的诗话精髓,有别于new criticism,是美术化的、情感的意象体悟:只有诗人才能理解诗人。
●条理清晰,酣畅淋漓,特别喜欢《宫体诗的自赎》。
●两篇年谱不忍卒读=_=继续研究……
●记得读到闻先生讲春江
●“宫体诗的自赎”写的诗意十足,看得出闻一多先生的诗词研究与文字功底都是上佳的。
●之前只听过闻先生慷慨就义的事迹,未能亲读其文。这本书除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因为学术性太强没能读完,读完其他几篇文章,深感文如其人。全书毫无现在常见的消毒水味,而是常有一种热烈的感情来,受教。
●有文化的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能把这种书写的这么轻松活泼让人印象深刻,膜拜。
●狂拍杜甫彩虹屁。
●好几处观点都上了文学史,最感动的还是闻先生对杜甫的评价,一字一句都是对杜甫的钦佩与热爱。我之前没有很喜欢杜甫,可看下来,就越能感受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歌机理,让我对杜甫产生的以往未有的情绪,深受感动。
《唐诗杂论》读后感(一):诗人评诗的杰作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地道的诗人评诗的文字,很优美,很生动,几乎没有学究气,很多地方能感受到作者的个性。比如他写孟浩然的:
“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盂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做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
虽然听说书中很多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不太站得住脚(我是纯外行,无从判断,见笑了),但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是相当惊喜的。
《唐诗杂论》读后感(二):关于杜甫的八卦
总结一下书中杜甫年谱里的一些小八卦:
36岁时,皇帝突发奇想,要征召天下的人才,任才施用。李林甫是宰相,怕那些读书人选上來向皇帝透漏了自己的贪腐事情就糟了,于是建议按照常例考试选拔。考完以后,一个都不录用,然后跟皇帝说,皇上英明神武,天下人才一个都没漏,全都已经在朝廷了。结果杜甫一生当中的第一次就这么献给了李林甫。
杜甫因为不招皇帝待见,辞官后,后半生穷困潦倒。全靠亲戚朋友周济。话说即使如此,也有好几处宅子啊。除了成都的草堂,湖南,长安附近(堵少陵之称就来自于他的住处),少室山下都住过不少时间。每次都是亲戚朋友帮他凑够了钱,然后上路周游各处,最后找一个地方盖房子。虽然都称作是草堂,可也是少则一亩,多则数亩的大hourse了。湖南的宅子还有果园什么的,想想都羡慕啊。穷的都已经衣食无着了,还能有这么大的房子住,唉…..
杜甫晚年在成都跟在另一个诗人,四川省长严武手底下混,两人也是诗友。做他的幕僚。只是唐朝时候的幕僚不好混,早起晚归,不请假连衙门口都不能出,比现在的公务员忙的多了。杜甫混了一年就受不了了,写诗给严武,说规矩太多,我还是不做了。
本以为李白在船上喝多了捞月亮淹死就够传奇的了,没想到唐朝诗人传说中的死法还真不止李白这一种。杜甫之死的传说也是很八卦的:杜甫在旅途中因为生病不能行走,住在船里,正赶上河水大涨,半个月没饭吃。当地县令知道后,派人飞马送来好多酒肉。几个月后杜甫就死了。结果江湖上传成了杜甫是在船上吃了那些酒肉撑死的。其实唐朝诗人中还真有一个吃死的。那就是孟浩然。王昌龄到襄阳,孟浩然请吃饭,结果吃完饭后,孟浩然就疾发身亡了。
《唐诗杂论》读后感(三):诗人与斗士
深夜读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读完,睡不着了。
若只许作一字书评,当然是“好!”,若可宽限到四字,则是“再来一本!”。可惜,再来不成了。先生以后,再无人能写出这样的诗论。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本诗论,而是史论。相对而言,评论诗要简单得多。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解释词句典故,分析创作手法(金性尧),亦不是揣度诗人用意,讲解诗歌意象(叶嘉莹)。他力图去讲的是有唐一代的文化气象和诗歌风貌。这便是先生所擅长与潜心研求的,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探讨。
他讲的“类书”“宫体诗”“四杰”,是和初唐的背景与风气分不开的。因为那是“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是百废俱兴、继往开来的一个开始,所以从文学创作上来讲难免继承六朝遗风,或有专注在辞藻与音韵上做文章者;可在这种“萎靡不振”“自甘堕落”的气氛中,却因时代的破旧除陈,吐故纳新,带来了一声又一声的霹雳,一阵又一阵的狂风急雨,冲刷出一片清新、健康、开阔的天地,从而“扯开了六朝的罩纱,露出了自家面貌”。如此,诗人才有足够宽裕的情绪去领略自然的和谐,万物的美丽,诗歌才能有力量、有气魄、有感情。
他讲贾岛生活在唐朝衰败的时期,“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因了曾做过僧人的缘故,贾岛作诗经常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这或许是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与诗人早年的荒凉、寂寞、空虚相契合之故,即“如同一个三棱镜,毫无主见的准备接受并解析日光中各种层次的色调,无奈‘世纪末’的云翳总不给他放晴。”所以,对于时代,他觉得亲切、融洽、调和,“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
这便是我喜欢此书的原因。因为他分析,而非揣度。对诗词的研究往往难免走向两极:要么逐字考据,详加索隐,最终死于句下;要么天马行空,擅自想象,抒发自身情感,弃诗人作品于不顾,恨不能自行创作。然而,要如先生般站在史学家的高度分析研究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精深广博的文学、史学修为自不待言,而且要做深入的、与现实相关的思考,想要考量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甚至藉由文学的欣赏作从“时代背景”到“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史的研讨,则需要更加有气度有魄力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曾经提到: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由此傅璇琮先生认为“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种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当前的伟大斗争相联系,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命运作理智的思索。”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这也让他为后来人树立了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毕竟学者中的斗士太少,而诗人却未免太多了些。
《唐诗杂论》读后感(四):有关《唐诗杂论》
“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的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
仅有129页的书,却分为9个篇章,分别是: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孟浩然、贾岛、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杜甫、英译李太白诗。单从书目来看它并不像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更像是一本关于唐诗发展与诗人名家生平品评的论文杂议,其间关联性不大,故名“杂论”也无可非议了。
谈及闻一多先生,我不禁想到了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死水》,此诗是“三美”格律诗的典型,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无不给人美的感受。今日读到《唐诗杂论》,且不论内容如何,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其诗化得语言让人惊叹不已。例如《类书与诗》中的第一段: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语言言简意赅,如诗如画,颇有美文的韵味。与此同时,闻一多先生把传统的诗歌学术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来,他从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着眼,批判传统文化,力图从新的角度来诠释他对唐诗的理解。
在《类书与诗》中,闻一多先生认为类书是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对唐太宗对文学的影响也持否定态度,在太宗的呼声中,“用事而忘意”成为了诗歌的通病,舍去了“诗言志”的古训,诗歌创作变成了大规模征集辞藻的写作。
《宫体诗的自赎》,读此题目便可知闻一多先生别出心裁之所在,本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到了卢照邻、骆宾王的出现有了真情实感,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最终诗歌回返常态,出现了初唐巅峰之作刘希夷《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
《四杰》,根据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作风的不同派,使命的不同,闻一多先生将四杰一分为二,卢骆一组,王杨一组。
《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孟浩然画像的精神相合,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闻一多先生认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自然矛盾较少,因此他的诗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然而情比学重要得多。闻先生认为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诗如其人”的境界。苏东坡批评过孟浩然,说他“韵高而才短”。闻先生说,苏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于才太多。
《贾岛》一文中,闻先生道出了他对贾岛只顾作诗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唯有作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蒲团生涯与时代背景的撞击造就了贾岛诗歌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历经了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大力十才子的秀媚之后,贾岛带来了幻灭的滋味,这正是贾岛成功的原因。
闻一多先生是很喜欢杜甫的诗歌的,被后人美誉为“诗史”、“情圣”的杜甫,在闻先生的笔下变得鲜活起来。闻先生精密的考察了杜甫的生平,以诗化的文字勾勒出了杜甫的一生。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杜甫与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李白的会面,闻一多先生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为世人重现了当时精彩的画面。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在闻先生如诗的文字中,我仿佛置身其中,在星光隐约的瓜棚下,子美与太白饮酒对诗,或叹息或沉默……
:应付公事,不堪入目……
《唐诗杂论》读后感(五):我在长安看月亮
《闻一多说唐诗》书评,文中简称“说唐诗”。
德语里有个单词叫“fernweh”,没有任何一个中文词汇能够与之对应,它的意思是对尚未到达的远方怀着有如乡愁一般的眷恋。而它的读音犹如一声叹息。我在阅读“说唐诗”的过程中想起这个词。承载唐诗的国度——唐朝,已不是地理概念上的“远方”,那是一个逝去了千百余年的朝代。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远方。然“虽不能至”,却总是“心向往之”。
说起闻一多先生,常被敬仰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以及早期同盟会的领导人。在这些身份之外,少有人提起的是他还是一位学者,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政治与革命缺少温度,但闻一多先生是有温度有热情的人。他为唐诗写下的数篇文论足以为证。在此之前,我尚不知竟有人可以把文论写得如此富有诗意情趣。
他写唐诗的发展、写唐诗的意境、与写下这些历久弥新的诗篇的大唐诗人交流对答……想来他走笔酣畅,我因此也读得入神,胡韵唐风吹过心间荡漾起那宛如乡愁般的眷恋。“fernweh”,是一声惊艳的叹息。
长安月下,一壶清酒一树桃花。但诗的国度不是一日就能形成的,唐诗如同群星般璀璨的光华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宫体诗的自赎》中,谈及谢朓去后直至陈子昂末生这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伟大的诗人。充盈在人们耳目中的,是“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空而无物,眼里见淫。闻一多先生骂这宫体诗是“没筋骨,没心肝”。好在这样的诗风也有终结之时,高宗时,上官仪伏诛,风靡盛行的“上官体”没了依靠,“江左余风”消散在天地间。齐梁诗无病呻吟的秾艳风格有了了结,这结局却也正好成为了唐代诗歌的开头。
初唐,诗歌的新气象是随着陈子昂震人发聩的一声呐喊而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从此,再也闻不见六朝脂粉之气,我们的诗人开始向天地宇宙发问,面对浩渺的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慨叹作为个体的渺小。“谁会凭栏意”?没有人理解他,更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疑惑。但他的姿态是孤独而高贵的。紧随其后的是“四杰”,王、杨、卢、骆。他们一出现,如暴风骤雨,整个诗坛的气象为之一振。及至刘希夷,那快马加鞭般催促诗歌发展的声音才缓和下来,是“宁静爽朗的黄昏”。而遇到下一座高峰时,闻一多先生大力赞扬它“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绵渺浩荡的空间构思,夐绝冲淡的宇宙意识,那样辽远广阔的意境。我一度以为诗歌只有走到了盛唐甚至是晚唐时期才能出现这样的华章。所有的夸赞与惊叹都是徒劳,惟是坚定地相信唐代诗歌繁荣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因为仅这一轮“春江夜月”就足以洗刷六朝宫体诗的艳俗,也能够照亮近在眼前的火树银花似的诗坛繁华。
盛唐,我没有见过你,但我曾无数次地肖想过你。
想遥遥眺望气势恢宏的大明宫,想象万国来朝的威仪;想闻一闻春风吹拂在长安城东南两街一百一十坊的上空的花香的气息;想看如今只出现在莫高窟壁画上的胡旋舞,臂缠丝帛脚系铜铃旋转如风;想见淡扫蛾眉的贵族女子头戴幂笠骑马踏青的神态;还有轻裘缓带的少年游侠儿,“窈窕相过,翩跹却步”的绳技女……
物华天宝的盛世,哪里少得了诗歌?少不了诗,也就少不了诗人。
孟浩然从山野田园间走来,真如闻一多先生所言,我在孟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身影就是“颀而长,峭而瘦”的。诗影或即是身影,那一身布衣白衫更添了仙风道骨般的神韵,与孟浩然同时代的王士源在介绍孟的序文里写“骨貌淑清,风神散朗”。闻一多先生说,“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清淡,甚至让人疑心到底有没有诗。”他曾怀抱“羡鱼情”,只是“求之不可得”,于是干脆“沼月棹歌还”。这大概是他的骄傲与恬淡,与盛唐时洋溢着自信豪放气象的边塞诗大有不同。
年纪再小一些的时候,最不喜欢杜甫的诗,所读到的大都是如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类感伤山河破碎的诗,或哽咽在喉哭不得,或泪下岑岑衣裳湿,那份忧国忧民的心肠实在太遥远,也太深沉痛彻,哪里有李白的诗读来爽气。于是每每见于人前谈诗好带喜恶。如今想来实在是幼稚荒唐的“黑历史”。
李杜并举于诗坛,历来虽难免存在褒贬扬抑,但皆无定论。而我慢慢领悟到如果没有认真了解一个人的生命史,就不要断章取义地对他下定义。我们只觉得杜工部遭受罹难故诗作沉郁顿挫,其贫病老弱的长者形象深入人心,殊不知他也写过“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这样狂放的诗句。我不敢再去做褒贬取舍,于心不忍,他们是那么认真甚至是心酸地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
闻一多先生写到杜甫,说他是早慧,同时也说早慧的诗人尤其多,但极少有诗人的开笔像他那样有重大意义。杜甫的独特在于他拥有伟大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在安史之乱那一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激荡出诗人内心最深切炙热的情感,落笔成诗千年不朽,可这哪里是“江山不幸诗家幸”?分明是“诗家不幸今人幸”。
闻一多先生提起李白,说他有杜甫的天才但没有那样的人格。李白的诗是“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还有三分啸成剑气 秀口一吐 就是半个盛唐”。李太白非常富有个人魅力,潇洒自在,飘然如谪仙,他的迷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经营“小我”、发展个性。不要误解,李白也是积极入世的,但他的追求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不相契合,在他的想象中最得意的活法应该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杜甫的政治理想始终是“致君尧舜上”,并且在国将不国的乱世依然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闻一多先生在文中写到 “……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杜甫给李白写过很多诗。
说起晚唐的诗,我总会想到芭蕾伶娜Uilianna Lopatkina的“天鹅之死”,明知无法再次展翅翱翔也要用尽全力谱写最后的生命颂歌。比起盛唐,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少了骄傲自信的气骨,却更多了几分思考与忧虑无奈中的沉静韵味。国势的衰颓不可挽回,那有如夕阳向晚的诗歌让唐朝以最优雅的姿态走向终点。
我深爱唐诗,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唐诗却是兼有了皮相与骨相的。千千首挥洒自如的古体、工整雅重的律诗、玲珑别致的绝句织就一张绵密的网,将大唐的气象定格,也将千百年后中国人的气质定格。即使我泼墨绘不出大唐的牡丹,穷尽歧路不见永远的长安,那又如何?“月本无今古”,我望月观想唐诗意境便也算作此生到过了梦中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