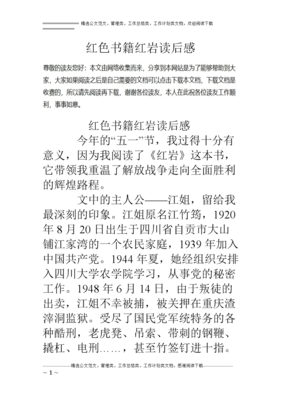《骑行200年》经典读后感有感
《骑行200年》是一本由【英】迈克尔·哈钦森著作,社科文献出版社 • 方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骑行200年》读后感(一):车轮转过200年
最近工作繁忙,赶上办公室搬家,读的匆匆。
这本书优点是细致入微,不放过关键时刻。然而因此有点絮叨。
自行车运动的竞技历史比自行车造型的历史更有意思,人类果然是好斗的赌徒本色。
最感兴趣的是自行车运动对女性解放的意义,书中分阶段贯穿到了历史中去。赞美技术助力女性解放自己、解放身体的步伐。
总之还是本得以消遣的书。
《骑行200年》读后感(二):骑行的荣耀
就像上一本《力量的进化》一般,这本新知课的语言依然是轻松幽默的,读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压力,就好像看了一场有关自行车200年历史的电影一般,没有听专业讲座的劳累与疲惫感,只有满足和意犹未尽。
我对第一辆自行车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个大轮子带着一个小轮子的庞然大物,没想到那已经是经历过大改良的“便士法新”,事实上第一辆自行车是脚踏都没有,只是一个木头横梁加上两个轮子的简单到粗糙的玩意。而它的出现却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的大爆发,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怎么也接受不了亚洲的一个火山爆发导致欧洲出现了第一辆自行车这样的事情的,但有时候事实就是如此的奇妙。火山的爆发导致欧洲草料的缺少,进而没有马匹可用,德赖斯男爵便整出了第一辆自行车用以代替马匹把木材拉出森林。
书中对近几十年的自行车与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着墨,多的是讲述诸如第一辆自行车这类诞生之初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看得没有带入感与亲切感,但这完全不影响我读起来不愿意放手,因为其中多的是新鲜感。原来早在一百多年前,自行车就在欧洲掀起了热潮,骑行还曾经一度是上层社会的活动,人们在风景秀丽的公园穿着灯笼裤便社交边骑车,还有骑行社团在周末结伴骑车去乡间逃离城市的喧嚣。那时的自行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运动器械,更能算得上是一个社交工具。
书中讲述较多的另一方面便是自行车运动,出人意料的是在自行车还停留在比便士法新还简单的震骨车时就有了自行车比赛,可以说当骑自行车还能算作是一种杂技时就有了自行车比赛。更神奇的是,从前居然有真正的骑行六天六夜的比赛,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导致我为自己早出生许久而错过了这样神奇的比赛失落了一小阵子,因为那已经不仅仅算作是自行车比赛了,更可以说是属于骑行者六天六夜的狂欢。
书中还谈到了许多有关自行车影响社会文化的地方,比如促进欧洲的女权运动之类的,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作者应该加入一些中国的内容,虽然我国作为自行车大国是在四五十年前相比欧洲有些太迟了,但自行车对于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绝对不逊于一百多年前它对欧洲世界的影响的。
自行车经历了两百年起起伏伏的发展,但正如作者所说“自行车和骑行者都有着无限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低谷之时自行车也从未从世界上淡去,仍有众多的爱好者们坚持着骑行这项运动。“因为骑行有种凭自己的汗水去丈量天地之宽的荣耀感”。
《骑行200年》读后感(三):两个车轮,两段历史,两种文化
生活在中国,自行车在你的日常中简直无处不在:走在街上,自行车随时都会从你的身侧经过;在公司、学校或小区楼外,总有一块土地成为自行车们的专属“领地”;几乎每一座城市也总是会有一条布满自行车店的街道(当然,最近这些自行车店都升级为了电动自行车店);更何况,你本人很有可能就会骑、并且经常骑自行车:骑着它通勤、锻炼、买菜甚至开电脑跑程序(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就此而言,我们是有着自行车文化的,或者可以更夸张地说:自行车本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哪怕是背景板)。
此时自然需要祭出这张网红照片,但相信我,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自行车上做出同样难度,甚至更高难度的动作,只是不要尝试就好了那么,自行车究竟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自行车的社会文化又究竟呈现出一些怎样的面相?作为“方寸·新知课”系列的第9部作品,《骑行200年:车轮上的社会史》(Re:Cyclists—200 Years on Two Wheels)将关注视角置于自行车从发明到如今,在欧美社会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之中,着力展现了一段飞驰于车轮之上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上述疑问。
本书的作者迈克尔·哈钦森(Michale Hutchinson)除作为一名作家、记者之外,更曾是英国最优秀的计时赛自行车运动员之一,无疑是一位“老骑行者”。由此,他对自行车活动的熟稔与热爱得以充分体现于《骑行200年》一书的字里行间;同时,作为一位面向公众的文字工作者,哈钦森亦深知大众史学的写作要领,因而全书条理清晰(大多数章节标题附带了涉及的具体年代)、文字诙谐幽默,加之篇幅适中(200多页,共分为15章),使得本书除作为获取新知的工具之外,也可以很好地充当日常的消遣读物。
两段历史:器物史与社会史
由《骑行200年》的书名自然可以知道,本书的重点仍旧是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就器物而言,全书前6章对自行车从发明到基本定型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且清晰地展现:从没有脚蹬的德赖斯双轮木马,到难以驾驭的震骨车,再到前后轮大小不一差异巨大的便士法新,最后到与我们如今所见几乎无异的安全自行车,自行车的定型史实际上是一个器物效用不断优化的过程。
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插图之一,看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所骑的自行车有多么优秀了而在这一器物形成的历史进程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紧密围绕在其周围的社会环境之变迁:在被发明并不断改良的前数十年间,自行车骑行通常被作为一种游戏或体育竞技活动,被局限于公园乃至赛道这样的封闭场所,除器物本身的不完善外,工业化早期糟糕的城乡道路环境恐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自行车真正走出公园和赛道,走向公路和大众日常生活,自然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工业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改良与自行车批量生产不无关系。而随着自行车的大众化、社会化,关于女性是否应该骑自行车,以及骑车时穿什么(方便但“叛逆”的裤装还是正统但不便的长裙)的争论又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这又为自行车的发展添加了性别平等问题的因素。由此,自行车的二百年发展史也确如本书副标题所言,是自行车不断优化的器物史,同时更是包含了工业现代化、社会大众化与性别平等化诸因素的社会史。
两种文化:交通工具or经济消遣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骑行200年》所为我们展现的一种自行车文化,或称“骑行文化”。作者在本书开篇部分即指出“骑行者(cyclist)是指过去或现在将自行车竞技和消遣作为一种身份特征的人对自己的称呼。”与之相对,“这个概念中没有涵盖那些单纯把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自行车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作为大众日常生活与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文化,以及作为竞技体育和消遣的自行车文化。
作者本身是职业自行车运动员,其对自行车发展史的关注自然也更多聚焦于其作为竞技体育的一面。事实上本书的后半部分篇幅也确是几乎都在讲述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历史,对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自行车面向鲜有论及——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目前对于自行车文化的主流认识,使得《骑行200年》的后半部分读起来确是略有疏离感。但我认为这也并非作者的写作失误,考虑到欧美社会的人口密度,以及马车与汽车的无缝对接(书中也大量提及了马车、汽车同自行车运动的“道路争夺史”),自行车或许从未能够成为一种主流性的交通工具——这多少与我国的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行车被作为主流交通工具)和社会现状(城市人口密度、道路条件、公共交通等因素都使得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仍有用武之地)产生了差异,形成对自行车文化的不同偏重或许也就并不意外了。
当然,也有入乡随俗的时候,比如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的这张经典照片当然,这种偏重本身确无优劣之分,正如作者在结尾所说:“骑行的功能实在太多了,但实际上人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看着它潮起又潮落。就在人们以为骑行可能会就这么消失的时候,它存活了下来,甚至比原来更加繁荣”——作为运动文化的自行车在欧美得以焕发生机。而在中国,当我们以为自行车即将被其他交通工具取代时,转眼间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共享单车却又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作为大众生活文化的自行车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
—— end ——
本书的单数页右下角放了不同时期的几辆小自行车,翻页的时候自行车也可以跟着“动”起来,十分有心了《骑行200年》读后感(四):当我谈自行车时,我谈些什么
开始知道这个题目,是阅读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也并非原创,再往远说,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用这样的句式作为标题,会给人一种确定感,又有一些神秘的延展性在里面。它会不经意的透露出一些哲学的思辨意味,令人审视其中的意义,所以今天权且拿来一用。
通常我们谈论一件事的时候,都不是在谈论这件事的本身,或者说对本身的谈论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兴趣点都在于探讨这件事背后的行为,过程,结果,甚至是动机和逻辑。我们讨论自行车,不单单是在叙述自行车这件交通工具的形成和发展,而是通过自行车的历史,呈现这200年当中的交通历史,人文历史与社会历史。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形容的那样,我们谈论自行车的时候,是在谈论自行车本身,更是在谈论自行车以外的事情。
你觉得自行车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发明出来的?几个宅男在自家车库里的技术实践?某个科技大牛的灵光一闪?如果你跟我想的一样,那就错了。自行车的发明纯粹属于客观需要,1816年的一次超大规模火山爆发,客观上改变了地球的气候,那一年变成“无夏之年”,粮食歉收,饥荒席卷世界各地。因为气温急剧下降,草料马上变得短缺,马匹没有了足够的口粮。甚至因为没有食物,许多马被人们杀掉吃肉。所以理论上需要一种能够可以作为运输工具,还不用吃草喝水的东西,来代替马匹。
冯·德赖斯男爵是自行车的发明人,或者确切的说,他发明了一种和现代自行车非常相似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当时被亲切的称为“人力两轮马车”,可能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它如何代替马车的功能。它中间有一根木头横梁,前后各加装一个车轮,人力驱动的主要含义就是坐在上面,需要用双脚蹬地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它前进。它甚至没有脚蹬,1个小时也只能骑10英里,考虑到当时充满车辙与深沟的马路,这已经算是很棒的速度了。
男爵先生把“人力两轮马车”带到了巴黎和伦敦,企图在当地掀起一股时尚浪潮,也为自己碰碰运气。法国人对此宽容,而英国人充满了冷嘲热讽,大家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装置,骑上它的人比马还要蠢。在男爵的创意被剽窃之后,两轮马车也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就好像任何新事物在一开始总是冲击着人们的旧观念一样,两轮马车虽然消失了,但它展示了潜力,并且预示了自行车的光明未来。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的发明者是谁?苏格兰铁匠麦克米伦据说有可能,法国人勒菲弗尔也有嫌疑,还有传闻说是米肖父子,靠着卖自行车发了大财的商人,他们的助理拉勒芒,甚至有人说是达芬奇。作者说他非常吃惊,居然没有任何明确记载。但作者本人也坦言,他喜欢这种神秘感,发明人的真相虽然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但这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自行车是一种深含民主基因的东西,它深深的扎根在民间。整件事情也许不需要一个明白的开始,甚至可能就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众智慧的结晶。
有了自行车的世界和没有自行车的世界终究是不同的,当米肖父子开始销售震骨车的时候,全世界都有了不同的反应。法国人把它当做时尚,在当时学会骑车是和跳舞,骑马一样重要的事情。美国人把它应用于杂技马戏。只有英国人真正的给予了这项新兴事物以应有的尊重,自行车也在英国逐渐发展壮大。罗利·特纳把巴黎的震骨车带回了伦敦,詹姆斯·斯塔利开始了设计与修改,安装脚踏板,缩小后轮尺寸,使上下车变得更加容易,姿势也变得更加绅士。也许英国人一开始不接受自行车,是因为骑这种东西还需要助跑,太像一个小丑演员了。
有了自行车,学会了骑车,下一步就是要去到更远的地方。也许人类天生就有去探索未知,征服自然的基因,两个轮子作为腿的延伸,承载着人类的欲望和理想,一次又一次的向着远方出发。有了这种壮举,加上媒体的报道,比比谁快的想法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自行车赛在巴黎圣克卢公园举行,但据说冠军的归属有不小的争议。在这之后的5年间,法国和英国又相继举办了长距离自行车大赛。现在回过头看看,比赛视同儿戏,作弊,抄近路,不守规矩的观众,甚至有选手扛着车穿过农田跑步冲刺。作者用了两个词形容那些比赛,“离奇有趣”而且“混乱不堪”。但令人庆幸的是,一个新的时期将要到来,它承接了人们对自行车的理念,又发展了人们对自行车的期望,如果能够骑的更快,为什么不呢?
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改良版的被称为“便士法新”自行车开始流行。它有更大尺寸的车轮,使用钢丝辐条,最可贵的改进是脚踏板直接装在前轮车轴上,更省力,而且更快。这种技术革新的结果就是彻底打败了震骨车,虽然它也有不容易保持平衡,上下车困难,不适合于爬坡等缺点,但突出的优点直接促进了自行车俱乐部的诞生。俱乐部的骑行活动是了解那个时代自行车发展的重要线索,英国绅士们在每周末聚集在一起,他们行事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律称呼代号而不是自己的真名。这种文化是从什么时间形成的,据无可查。也许他们一方面渴望放飞自我,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社会偏见的压力,不让自己的爱好为外人所知。
先进技术的出现,往往它的第一个敌人不是落后的技术,而是社会陈旧的观念。俱乐部虽然成立了,但令人遗憾的是,选择骑行同伴的标准不是技术,而是“社会地位”。同时骑三轮车的人也会时常抨击骑自行车的人,主要的理由竟然是自行车的骑行方式“不体面”,容易被人耻笑。特别的理由是女性可以骑三轮车,而不能以叉开双腿的挑逗姿势骑自行车。就这样,自行车的普及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摇摆,社会观念也在民主与无政府之间演进,它太慢了。在这方面,年轻的美国先生给老派绅士们做出了榜样。
如果你没听到过艾伯特·波普上校的大名,那你对美国自行车发展的历程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此君堪称美国自行车业的教父级人物。主要贡献在于,他把自行车的制造从小作坊式的手工零敲碎打,变为流程化的工厂统一采购,统一制造,统一检验。他开展了现代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利用广告,赞助,比赛,一切手段推广自行车产品。另外最具有商业意味的是,他是所有制造自行车的人里最具有专利意识的,他购买了市场上几乎能买到的所有与自行车有关的专利,谁生产自行车都要交给他专利费,就这样,他好像有了一个“可以流淌黄金的水龙头”。鼎盛时期,他甚至赞助大学里的科学家开展城市路况研究,以证明自行车在什么样的路面上能够发挥最大功能。如果有谁敢说马路只属于汽车和马车,他会不择一切手段把那人告上法庭。
以技术和金钱,倒逼社会制度的改进,也造就了美国自行车行业的黄金时期。在那个时期,自行车骑行者在路上与路人和马车简直水火不容。通过诉讼的手段,争取到了骑行者的路权。在法律层面争取到平等,为社会接纳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出行铺平了道路。
技术的变革往往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充气轮胎和链传动装置,换句话说,那时的自行车和现在相比,大体上已经基本相同。轮胎的改变可以让人骑起来更稳,而链式传动结构的发明,把脚蹬从前轴挪到车中部,可以更好的把握方向。骑车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尤其当一位无畏的骑行者墨菲先生与铁路公司合作,以作秀的方式展示极限骑行。他在几乎没什么保护的情况下,跟在火车后面用57.8秒骑行了1英里,人们沸腾了,这种搏命式的招牌挑战是最好的宣传语。人们争相购买自行车,自行车走入市井阶层,变成了一种普及型的交通工具。
人们的观念也同时改变着。也许你还记得之前提起过女性只能骑三轮车不能骑自行车的这种社会偏见,谢天谢地,女性终于可以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女权主义的抗争有了效果,虽然社会仍然赋予女性不小的压力,在骑车时的着装也被人挑三拣四,但起码女性可以在长途旅行时不用再穿过脚踝的长裙了。女性骑行者不再受到歧视和责难,她们也不应该受到歧视和责任,与其说是社会的进步,不如说社会欠女性骑行者一个道歉。
在短暂的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自行车回到了民间。也许军队方面和当局者心知肚明,这种扎根于民间的交通工具根本不适合于战场那种环境,自行车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与战争通行的法则也是格格不入。回到战后重建社会的自行车慢慢的在转变着职能,从一个新鲜的,显示自己身份的时髦物件,转变成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在城市里工作了一周的人们,周末可以骑行放松,来一次短途郊游。可以到乡下过一个令人惬意的周末,要上班时再骑回城市。自行车更加融入到了生活的角落当中,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作为一个自行车大国,如果不在比赛当中证明自己,对于英国人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英国的赛车手在世界比赛当中的成绩非常差。这一切的原因在于英国的保守主义思维。世界早就开始流行集体出发的职业公路自行车赛,英国仍然死抱着自己的业余计时赛不撒手,可想而知,英国的自行车运动一早就处于边缘化了。1937年英国选手查尔斯·霍兰德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可惜他没有坚持到最后。
受到刺激的本土选手开始自己组织自己的职业公路自行车赛,在那些崭露头角的骑行者当中,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两位杰出的女性运动员,她们是艾琳·谢里丹和贝丽尔·伯顿,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她们的身份是业余运动员,阻碍她们代表英国走向世界。国内媒体的只言片语,也让人们无法了解到这两位杰出女性的成绩。作者无不可惜的说,女子自行车赛的格局太小了,但幸好她们坚持到了最后。
进入20世纪中期,自行车已经变成了每个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它已经和这个社会牢牢的结为一体。周末骑行的现代人会用骑行的方式不断突破自己,积极地选择磨难,也就是选择一种人生态度。到此为止,自行车也许不是一种人人都喜欢的运动,但它却是你生活中离不开的好伙伴与好帮手。在书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骑行的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而是由乐观者书写。在过去的200年中,自行车从一种先锋极限运动,变成了普通的运动,生活方式,健身方式。它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如果问它为什么能够存活到今天,也许就是因为它有一代一代热爱自行车运动的人。请让我们向自行车的辉煌历史致敬,更向所有喜爱自行车的人致敬。
最后的结尾,有个意味深长的对话,一名骑行者向作者问路,“从这里到剑桥哪条路线最合适?”作者反问“最短的路线还是最长的?”“哦,我是说最长的路线。”骑行者回答。
意料之中的回答。
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