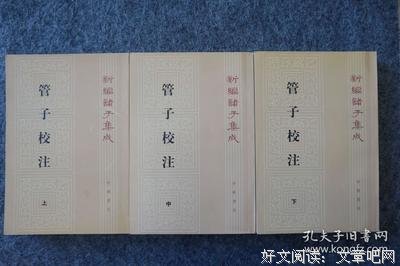管子校注读后感精选
《管子校注》是一本由黎翔凤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0元,页数:15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管子校注》精选点评:
●磨洋工。。
●上中下三册
●管夷吾真神人也
●不是只靠战国秦汉人就能“建构”得出来的。
● 好
●终于学完了。
●没有时间性。永远都是经典。
●快来加入群【读书看电影听歌互怼群】(群号689454341),发现精彩内容。
●整理水平不高。
●黎注迂曲难明
《管子校注》读后感(一):管子校注值得一读
正在读,原著好,校注也好,受益很多。比如“幼官”一篇,不仅可以从原著中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从校注中得到很多扩展性的知识。原著幽微深奥,校注功力深厚,非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功底难以发现其中妙处,也不容易有兴趣看下去。校注中,不仅详列历代精彩注解,让读者有所取舍,而且黎先生的按语也是不厌其详,以深厚的专业功底为基础,把自己的见解说的鲜明透彻,极有利于对原著的理解。
《管子校注》读后感(二):读书札记
最近在看《管子》,当然选择了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这也是出于对中华书局的信任,但是,读下来却不是特别满意,特别是对于黎翔凤先生的校注,还有中华书局的排版。现在列举几条读书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黎先生在引用大量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贾谊为习《管子》最早之书者,知《牧民篇》本无“则”字,有“则”字为《轻重甲》。或作“而”,则依《史记》也。鄙见:根据《轻重甲》,应该有“则”字,并且根据《牧民篇》的上下文的行文,都有“则”,所以,此处也应该有“则”字。黎先生在此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用后代的引文去校正原文,其实我们知道在引文与原文不一致的时候,通常是应该根据原文校正引文的,黎先生就是根据《新书》中的引文校正《牧民篇》。
16,“右士经”。注:顾广圻云:“士”字当是“十一”二字并写之误。黎先生的结论为:房训“士”为事,是也。其证极多。……本节偶为十一事,顾牵合之,凿矣。鄙见:黎先生引用房注“士,事也”,只能说明唐代的本子,该字写为“士”,不能代表原本为“士”字。认真数一下,该段确实讲了十一方面,并且就整个《牧民篇》来看,小标题都是“四顺”、“四维”、“六亲五法”之类的,都含有数字,不知黎先生有什么理由能证明顾广圻的“十一”说是穿凿。
这是我的疑问,希望大家能予以批评指教,发现问题也能交流。
《管子校注》读后感(三):读黎翔凤《管子校注》
字字珠玑,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学的珍宝。这本书的伟大之处被严重低估了。
《管子》一书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阐述可以总结为三个内容:民本、集权、
法治。在《管子》书中,许多篇章都提到了“以人(民)为本”的观点,如: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霸言》);“齐国百姓,公(齐桓公)
之本也”(《霸形》);“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
所谓石民,即基础、根基之民。之所以强调以人(民)为本,一是因为人在
社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有了人才会
有一切;二是因为民心可用,顺民者昌。“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
争人的关键在争得人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参患》),
警告君主如得不到民心拥护,那将成为孤家寡人。而得民心的关键又在于政
顺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具
体体现则是“爱民”与“富民”的政策。《管子》书中有许多篇章是专门论
述如何实施“爱民”和“富民”政策的,如《牧民》、《五辅》、《权修》、
《枢言》、《大匡》、《治国》等等。史称管仲为政“论卑而易行”(《齐
太公世家》),也就是不唱高调,崇尚实干,政出易行,切合民情。这种领
导作风正是以民情、民心为出发点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民本思潮(孔
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民贵君轻”等等),对我国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管子,无疑是这股思潮
的开创者和先驱。
有的篇幅中既阐述了礼义道德
的重要,又阐述了法的重要,主张德政与法治并重,严刑重赏与礼义教化并
举。因此,《管子》一书的政治主张其实是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礼法并
用的统治术,它的设想是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主张正
好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了。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
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
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
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读《乘马》,可以知道当时的民情和治理方式。
政令重于珍宝,国家重于亲戚,法度重于人民,权威重于爵禄
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可见法也是服务于政治和军事。
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未之以忠信,远者未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
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
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
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
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
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
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
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霸言》是管子霸道精髓。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
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正,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
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
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形危之。二而伐之,武也;
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
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强国
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
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
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至今,
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
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
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
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考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
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
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
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夫抟国不在敦古,治世不在善故,霸王不在成典。夫举失而国危,形过
而权倒,谋易而祸及,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因其数也。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
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闻
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缁缘缁,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
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
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
使,谗贼是舍。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兽,无
所就处。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譬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
进其徘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獠猎毕
弋,暴遇诸父,驰娉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
《管子校注》读后感(四):民本、集权、法治、理财
管子所行,唯民本、集权、法治、理财是也。
民本
《牧民篇》乃倡导顺民所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辅篇》乃劝得民之欲“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甚至首言民众监督之权,《桓公问》有言“察民所恶,以自为戒……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由此展开,为政之出发点,首先在富民。《治国篇》曰:“凡治国,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立政篇》则论到“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八观篇》有云,“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集权(国家主义)
管子免死,以辅佐桓公霸业为使,“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大匡篇》)是为行王霸之业,成集权之国。然管子为相之下,遂成仁人之霸业。何谓仁人,与民一体方为管子之霸业。所谓《君臣上》曰,“合而听之则圣……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
法治
《任法篇》云,“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七法篇》、《法法篇》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凡立法在于保民。所谓“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法治的目的也甚明确,《牧民篇》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可谓富民得礼四字者也。管子认为无法治则礼制无所实施,“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篇》)以至于最终达到“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的境界。
理财
管子论国之财政,先定财之意义。乃论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是也。正所谓“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由此观念在先,方可言管子之理财思想。其一,奖励生产。“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尽地利、劝农桑是也。其二,均节消费。“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八观篇》)讲求不奢侈靡费,精简财政支出是也。其三,调剂轻重。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如不注意此事,“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古今中外,社会平稳运行后,必会有通胀及贫富分化之压力。西方资本兴起后,更甚之,后方有社会主义之论说。均贫富者乃社会中一大问题也。管子身处农业社会,以货币与谷物,运用国家调控之力,缓解贫民之困,谷不足则补币,币不足则补谷。经济、金融大事全操于国家之手,谨防豪强素封之趁机渔利。此乃为国家干预主义是也,可见《轻重篇》。其四,财政调节。“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必危。”(《权修篇》)财政之取于民众,需施之有度。何谓有度?收取盐、铁之利为是。《海王篇》详谈国家垄断资源,以收税供给国家之策。此策开辟之后数千年国家垄断资源或寻租之源。
五百年后,《盐铁论》出世,奠定帝国体制下的官方专卖制度,传至今日仍存。此策颇受诟病,为历代志士所反对,企图修正者有之,废除者有之,再造者有之。管子因此饱受株连。实则大谬矣。管子行盐铁垄断之前提乃“不收他税”,“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国蓄篇》)然试问此后天下谁人能行之?几人能记之?农商之税累重,垄断日深,循环往复,民不堪负,直至水亦覆舟。
管子之可贵,在于春秋初年便定王霸之制,乡举里选,以民本为根,国家为体,法治为用,再辅之以轻重权衡,财税金融,成一代之霸业。然齐国之于九州,乃十一之国,物产独特,民众不多,方可行之。大一统后如何操作,未置可否,此其一。君王国家之权重,民众监察之权轻,法治政令之权大,生废修补之权小,虽有啧室之议,如何实施亦成问题。开明之君尚可,传至后世如之奈何?此其二。管子之政治经济学,为列国之冠。明夷待复兴文艺,定以管子为标杆,力倡啧室之,民本之,法治之,集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