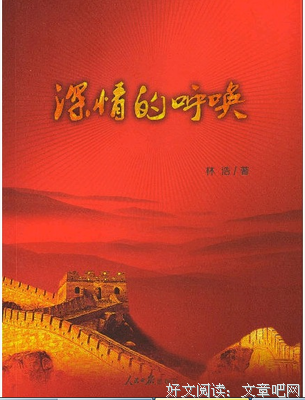革命与历史读后感1000字
《革命与历史》是一本由[美] 阿里夫·德里克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与历史》精选点评:
●故事的讲法不新鲜,但是故事本身很精彩。
●《读书杂志》的编辑们真是厉害!
●看不大懂
●这是可以与《动物庄园》《1984》媲美的书。。。只是视角不同。。看这本书你会理解很多现实存在的诸多“政治笑话”。
●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化解读,与高中教科书对读当别有一番风味。稍感遗憾的是,Dirlik的讨论截至1937年。而毛在延安时期于Stalin启发下,假手范文澜、吕振羽等人以“原奴封资社”的教条化五阶段论重修古代史(与此同时,又倚重陈伯达、胡乔木重修近代史),或许才是塑造此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真正源头。而这种机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观,似乎又与当下国人对于国外“信念政治”的普遍怀疑有着密切联系。
●匆匆一读,他日再来
●对理论不熟,所以读起来颇为费劲。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景一章,对更为现实的革命背景并未交待清楚,稍微显得单薄,但在此之后展开的分析与论述,颇为精彩,涉及论战的内容,颇有一种打架的架势。
●一般。
●分析和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传播和论战,可窥民族国家,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等这些“常识”性的历史概念和历史观念对国民意识的塑造。“一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替代性的革命策略与历史分析就变得不相关了:是政治上的胜利者自己,选择那些与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历史成就最为符合的历史解释,作为史学领域的胜利者。”“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谁掌握了过去的解释,谁就控制了未来。而哪些故纸堆和考古场实证考据出来的真东西,就能代表现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吗?可见历史不能一味的讲真话而不讲立场,不然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导致国民意识的混乱和秩序的崩溃!
●历史谈得很多 革命谈得不多
《革命与历史》读后感(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征服中国的知识分子?
之前的假设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是自卑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嫌弃的。而马克思主义恰恰提供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是有缺限的,中国不必对资本主义自卑,双方在社会主义面前是平等的,中西方处于同一时间分期;另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有更迭性的,儒家思想不能完全代表中国。这种假设只是单方面考虑到知识分子,过于单薄。
第二个假设是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从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
《革命与历史》读后感(二):.
有点喜欢这样严肃的批(吐)判(槽)风格。自己可能有一种主观的偏见:国外对马的厌恶可能源于苏和中……另外,如果能将具现当时的革命情景和讨论的代表人物个体心境变化再结合其篇章的内容一定能更好地展现这个主题吧?
有一点挺迷的,个人认为就逻辑上说,也许德里克认为的朱佩我的理论张力其实可以自洽(除了他对马的“超经济剥削”的误解)。朱通过贬斥商业资本在瓦解自然经济基础的作用主张帝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而又认为中未能从封建主义继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商业的停滞。我觉得这点恰恰体现了朱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忠诚。因为朱认为处于封建社会的关键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发展的不完善,其不能改变经济基础,要改变就应立基于资本的继续发展。
《革命与历史》读后感(三):历史的历史
我们会从哪里来,将会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不过如果换一个不那么终极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归结为历史的事实以及由这些历史事实中抽离出的社会发展轨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世界都作为过程而存在,哲学点讲,具体的形态也不过就是发展过程中的某一形式而已,历史学科也摆脱不了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性质,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怎么产生的,《革命与历史》就给出了一个好的回答。
《革命与历史》将中国革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联系,通过对一场社会史论战各家观点的分析得出结论,即各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带着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史学,自产生起,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裂的关系。典型如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直接指向了中国革命的对象能否如同欧洲一般成立,进一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中国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革命作为一个对当前确定秩序的否定,必然需要正当理由,亦即合法性或者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提供了社会必然的解释,即阶级对抗直接导致了革命,借由革命,被压迫的阶级才能恢复正义。马克思分析欧洲历史,将欧洲历史进行分期,而每一社会形态的过度,都是通过革命的形式实现,如地主阶级反抗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反抗地主阶级,都是先进阶级对落后阶级的否定,而且否定的结果社会进步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将历史与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十分适合中国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其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神秘的上天,以及现实政治的腐败。辛亥革命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以人权为基石的革命理论,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人看到了一条新路,也为革命提供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也就是说革命居然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路径,这已然摆脱了传统的皇帝轮流做的朴素革命观。
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作者在书中也很明确指出,“困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实是源于史学家们既想谨慎地遵循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字面意义,又想顾及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并且认为“它们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应用于非欧洲社会时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P196)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其实也一直延续到当今。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不得不说,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期发展的研究实现了对未来的预言(70年代的预言),历史分期的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问题,依然是当前史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
《革命与历史》读后感(四):一些笔记
本书讨论如下主题: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如何征服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作者把这一问题与1925-27年的革命运动相联系,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其实就源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往何处去的忧虑(p.44)。早在1927年前即与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官方史学分道扬镳的托派,两者之间的最重要分别在于是否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托派基于世界革命的理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同样是需要革命的。1930年代前夕有关中国社会的分析分成三派:1.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在周代中期就因为商业的发展而消失了。对于现状,国民党左派不甚强调地主的剥削,更强调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流入回报更高更快的土地和城市投机,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任何推动作用,流入乡村的资本则加深了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农村的凋敝就是明显征兆(p.65)。国民党开出的药方是孙中山的方案: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上的统一,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2.共产党人认为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资本主义存在于沿海的外国控制的少数城市和经济领域,这些地区又成为其他地区的剥削者。CCP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抱有强大的封建关系、走向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国家,革命应由无产阶级带领农民进行,矛头直指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者,此后再开始“非资本主义”的进程。3.中国的托派比托洛茨基走的更远,他们的资产阶级似乎涵盖了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外的所有中国人,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也极大的缩小了他们的同志。在三派对中国现状的不同认知下,他们都向历史寻求论据来支撑其论点,因此开启了中国史学家以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史的序幕。
1.陶希圣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发展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制约,其理论来自拉德克,其思想的根源则是列宁,正是他首先运用商业来解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马克思理论不相符的问题。
2.郭沫若:对中国奴隶制度的讨论,认为商末周初是一个可与西方希腊罗马社会相比的奴隶社会,他援引马克思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经典论述“风车带来的是封建领主,蒸汽机车带来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对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非常看重,体现在他对铁的使用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郭的思想导师是摩尔根和恩格斯。
另一个重要的讨论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从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革命失败的争论开始发酵,最重要的著作是马扎尔的《中国农村经济分析》,他基本上认为中国自晚周兴起的商业化破坏了氏族社会,私有制开始普遍,但私有财产的观念却一直未能发展,这是因法律制度的缺乏所致。魏特夫描述的灌溉社会需要集权化的政府管理才能达成。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于地理决定论。
1933年以后论战消退,出现以1.陶希圣为代表的北大社会经济史派与2.周谷城3.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所秉持的五阶段论。
《革命与历史》读后感(五):革命与历史,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学相联结的推手
刘东教授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一套很有意思的书。
如[美]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美]艾志端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美]艾尔曼的《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与文化》、[美] 卢韦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日]中岛乐章的《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美]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黄卫总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事》、[日]吉川中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美]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刘新的《他者》、[美]魏定熙的《身份的权力: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
这类的海外译介,可以新一轮的海外学术引进,以填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大陆的文化锁国政策带来的“学术文化真空”,其意义与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丛书”相当。
从选取的书目看,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空间理论)、文学、女性文化、都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类等。
在这里重点推荐的是[美]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
论述认为在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历史学提供的方法论:一是“通史”的写作,中国知识分子便视为“通史”为创造“新史学”的要点。因有一套因果解释揭示历史的进程,并进行专题性研究的积累。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现象中的等级制度的看法被视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出发点和解释工作的一套内在一致的组织原则:唯物史观将社会经济现象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揭示出在社会经济进程中将历史广大的不同领域联结在一起的环节,从而提供了一个构建通史的基础。另一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尽管唯物史观背后的基本的政治动机使得许多人拒斥其作为一种史学理论的有效性。然而,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只有那些同意卡尔(E•H•Carr)“越是社会的历史学,越是历史的社会学,两者相得益彰”( E•H•Carr卡尔.What History? 《历史是什么》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4.p.84.)这个论断的史学家才会愿意考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先是从日本转译。在1920年左右,恽代英翻译了卡尔•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戴季陶从日文转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已在1925年左右译介入中国。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的崭新兴趣,以此来检视中国现实问题答案明确。1919年9月,《建设》发表了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尔后,《建设》又发表了胡汉民关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宗族组织演进的两篇长文,这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的最具野心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尝试。
有意思的是这表明唯物史观的最早运用是由民国党人进行的。
直到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2期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 以上的论文基本穷尽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成书,收录了他在1928年到1929年发表的论文。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书一普出,迅即售罄,数月之间3次印刷,至1931年秋已印7000册,便激发了论战者对于早期中国历史的兴趣了。当时参加论战的主要人物有顾孟余、陶希圣、梅思平、陈独秀等。
论战的主要内容为:
(1) 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在春秋时已经崩溃?
(2) 士大夫阶级是不是应当重视?
(3) 殷周时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4) 现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顾颉刚评价道:“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闻一多曾说:“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1884)中的历史发展观点的极大影响;并且在历史分期上,亦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影响。郭沫若大胆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恩格斯一书在中国的续篇。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主流的看法认为所谓亚细亚社会是原始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一种社会形式,它是和欧洲历史上的奴隶社和封建社会相对应的。这样的看法视中国为一个亚细亚社会,而稳定性或停滞性是中国历史的突出特征。
亚细亚社会的提倡者将中国政治权力溯源于国家在社会经济生计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相比起欧洲“干”(dry)的农业,中国的农业是“湿”(wet)的,也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高度依赖于水资源的规制,即所谓的“灌溉社会”,只有具有一个广为延伸的官僚机构的集权化的政府管理才能达到水资源控制的组织要求。另外,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威胁,也要求中原政府加重集权的需要。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政治上层建筑完全地控制了社会。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有三次推手。第一次是国民党人陶希圣在1935年的一个不经意的申明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一微妙转向做了推手。那年的7月1日在新出版的《食货》上,陶希圣号召暑假临近,人们得以有时间抽身出来专心进行史学写作和讨论。当时陶希圣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史学家之一,也是北大最欢迎的教师之一。
第二次推手主要代表人物周谷城,他的《中国通史》,初版于1939年,到1947年已经9次印刷。周谷城在“社会史论战”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
第三次推手主要代表有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等1949年之后中国学界大名鼎鼎的史学家。
至此,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学紧密的联结了。
2014-5-15于锦城清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