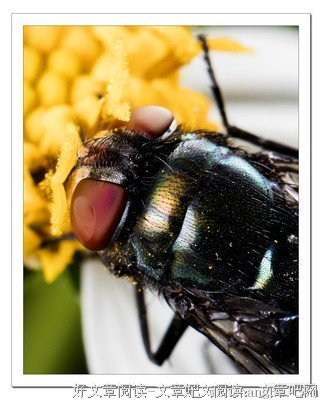《复眼的映像》读后感1000字
《复眼的映像》是一本由[日] 桥本忍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页数:3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一):没有黑泽明,谁知道你是个6啊?
这本书有俩问题:
一是作者无时无刻的大师自我感觉良好,口气透着对黑泽明的不服,他甚至觉得是自己成就了黑泽明。以至对黑泽明作品的评价也那么保守,对于《影武者》和《乱》简直可以说是恶评,很明显是出于嫉妒。作者说自己看电影的习惯是看不舒服就退场,不管几分钟还是几秒钟。请问,像《乱》这种讲究故事铺排的影片,你看个几分钟能够嘛?还说人家为了形式舍弃了内容,还说镜头好只是摄影师的功劳,请问你真的去过拍摄现场吗???如果没有黑泽明,谁知道你是个6啊!
二是内容杂乱无章啊,一会儿将自己的出身,一会儿又把剧本放上,一会儿又说和黑泽明的合作,请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呢?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木有一个主线?
不太懂为啥这本书评分这么高!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二):喜欢黑泽明的人读起来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烈
对电影剧本创作来说很具有启发性,但作者孤傲的语气和一己之见着实让人生厌,在写完《七武士》之后,作者说黑泽明肯定再也拍不出比《七武士》更好的作品是不是有点武断?除了《罗生门》《生之欲》《七武士》,作者对黑泽明其他作品几乎都是负面评价,认为《影武士》和《乱》等作品之所以受到好评,是因为电影评论期刊为避免与制作公司发生冲突而说的违心话,这些作品实际上差的不可理喻等言论让喜爱黑泽明电影的人实在读不下去。还多次提到自己与黑泽明合作的不情愿,认为自己与黑泽明旗鼓相当……完成《七武士》后,身为编剧,却说帮黑泽写剧本自己并没有上心的意愿......大概是作者本身性格也孤傲,作者对黑泽明应该是夹杂着许多复杂的情感,但既然要回忆黑泽明了,还是不要过多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之上为好。
如果想了解黑泽明的剧本创作过程,这本书是很好的参考,但想真正了解黑泽明的为人和导演天赋,个人认为这本书没有很好地展现出来。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三):推荐一下1966卡拉杨指挥柏林爱乐版本。
“桥本君……”我一惊,抬起头。黑泽明面朝着我,翻阅完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他的面前也是一沓稿纸。他好像想到了些什么,双臂抱在胸前,眉尾略略上挑。“关于这次的剧本……桥本君,你知道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吗?”“嗯,我还有唱片,是我喜欢的曲子,经常会听。”“我想依据《自新世界》的音乐来创作剧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黑泽明屏气凝神地注视着我的脸。“您是说接下来要写的剧本的质感……或者说读剧本时候要能感受到的抑扬顿挫,类似于那种节奏韵律吧?”“嗯,是啊,对的……”“开篇就如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的黑人灵歌,恰好可以用于农民们的苦恼。”黑泽明点点头。心情好像放松了。“轻快而有节奏的第三乐章,这个对应前半部分的调子。尤其要说的是最后,辽阔壮丽的结尾……这是决战的部分。拉——希、哆、希、拉拉的小节的不断重复,如同波涛的旋涡一般,盛大的第四乐章……没有比这个更贴合最后决战的调子了。”黑泽明用力点了两三下头。心底里的放心,化作了满面的笑容。“好啊……那么,桥本,那么这部《七武士》就以《自新世界》为调性来创作看看。”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四):一本电影教科书
第一次听说桥本忍的名字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看《罗生门》的时候,当时老师只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创作背景,后面的时间都是在解析影片本身,所以我对这个人一直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黑泽明的名字要更加响亮,其实在看过这本书并且加以查实之后,我发现黑泽明的成功确实是离不开帮助他的那几个人的。桥本忍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他这传奇电影人生之路,让们有机会重新认识那些部伟大的日本电影。
在他和黑泽明共事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和我们一样是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敬佩的去看待这位艺术家。如果不去了解他们创作时的过程,也就不会体会到那些细节之处有多么惊人。黑泽明对于电影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看到他对剧本创作时的那种灵感与天赋,让我也不禁惊叹自己与他的差距,也许我这辈子都追赶不上这样一个天才。
通过这段回忆,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其实讲述的更像是当时那个年代里整个日本的电影发展。那段时期也是日本电影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超越,其实还是和人本身有关。本来我对电影的看法是时代影响电影人的创作方向,而黑泽明他们可以说是通过人们自己去影响一个社会。
关于电影人的传记我看过很多,当然绝大多数都是老师让看的,因为要交作业。但这种作品实在是难得,因为桥本忍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电影来叙事的,这也就把当时很多拍摄过程中的秘密展示了出来。我敢说只要是搞电影的,看这本书绝对能够得到不小的收获。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谁传承下来的,而是被这几位黄金搭档所摸索出来的新鲜技法。
虽说编剧和导演都同等重要,但他们的工作却基本完全不同,熟悉电影行业的人应该都知道,基本上很少有导演和编剧是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的。想要完成一部电影,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做不同的人员搭配,像桥本忍和黑泽明这种搭档实在是难得。一个负责创造出故事,一个负责赋予它生命。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特长,相辅相成才出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
这本书的写作角度也很独特,桥本忍在自己的回忆中总结自己的感情,他不是为了给黑泽明写传记,更确切的说法就是一本回忆录。以这种主观的形式去回忆,反而比客观更让们嗯容易起了解一个人和一段事。这本书的真正用途也不是为了让我们一味的去怀念过去,而是把方法告诉我们,让读者能够在未来从事电影行业道路上走的更加顺畅。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五):序曲:东京进行曲
看个电影去吧 喝喝小茶去吧 干脆搭乘小田急线 逃离尘嚣吧 新宿啊 日日换新颜……
我是土生土长的关西人,来自兵库县的乡下。
我之所以知道东京圈内有条叫小田急线的民营铁路,并非因为我曾任职于国铁( JR2 的前身),而是受到昭和初期——昭和四五年 3那阵子非常流行的《东京进行曲》(西条八十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影响。在轻快活泼的旋律中,一句句的歌词宛如地图指南,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了还未曾谋面的东京。
及至我来到现实中的东京,已是那首歌风行了十几年之后。无论是歌词中充满了恋爱气息的丸之内大厦,还是风情迷人的浅草,抑或是日新月异的新宿,都成了一片荒凉的焦土野地。
昭和十三年,我以现役兵身份加入鸟取连队,因感染肺结核而被豁免兵役。历经陆军医院和日本红十字会的诊疗,在伤病军人疗养所窝了四年,总算是活着重返尘世,但已经留下了重创的身体,让我无缘再回国铁复职,于是我转行做了军需公司的一名职员。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奉公司之命出差,终于才第一次踏上我憧憬已久的东京的土地。
我要去的是新宿伊势丹的辅楼,战时的军需省——类似现在产经省的政府机构。由于电梯发生故障,我得费老大劲爬上六楼,时不时地得在楼梯间歇口气。万里晴空之下,战后东京废墟无边无际,我突然想起《东京进行曲》里的歌词“新宿啊日日换新颜,连那武藏野的月亮哟,也高挂在百货大楼的楼顶上哟”,其中的百货大楼恐怕指的就是这幢伊势丹吧?
时隔不久,公司在靠近台东区御徒町站的昭和大道上设立了出差办事处,打那以后,我来东京出差便都在那里落脚。
“东京虽然看似广阔,谈起恋爱却显局促。”这是出自《东京进行曲》的一句歌词。我在东京仅有一个熟人,就是新东宝的电影导演佐伯清。佐伯先生担任我的剧本老师伊丹万作的副导演,他从京都太秦的JO(电影公司)和伊丹先生一起被选派到东宝电影公司工作,来到东京。不过几年后,伊丹先生因肺结核卧病在床,又回到了长住的京都大映摄影所静养。佐伯先生继续留在了东宝,并在新东宝成立之初被擢升为新人导演。
佐伯先生的家位于世田谷区的鸟山,我从御图町乘坐山手线来到神田,再乘坐中央线到新宿,在新宿坐京王线到千岁鸟山,换乘山手线到涩谷,而后坐井之头线到明大前换乘京王线,常常这样去拜访他(因为他与伊丹先生是故交,我出于亲近感,唤他佐伯大哥。其他人都称呼这位新锐导演为佐伯兄)。总而言之,为了往返佐伯府邸,我常常乘坐京王线和井之头线,但要说起小田急线,我可一次都没坐过。
这是昭和二十四年的早春。
冬日余威未尽的寒风在昭和大道家家户户的上空呼啸盘旋,从上野方向吹来的干风特别寒冷刺骨。
我身上套着大衣,提着一个包,走出公司的东京出差办事处,在御图町坐上外圈的山手线。到涩谷下车,换乘井之头线。那部电车眼见就要进入下北泽站的时候,小田急线的下行电车从高架上的井之头线下方与之交错而过,从眼前飞驰而去。小田急线下行电车的大车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下北泽站下车后,我东张西望地借助着指示牌摸到了小田急线的站台,等了一会儿,坐上了下一部下行电车。这是我初次乘坐小田急线,去往成城学园下一站再下一站,狛江。此行是去拜访住在小田急沿线狛江的黑泽先生——电影导演黑泽明。
我的电影剧本《雌雄》(后更名为《罗生门》)被黑泽先生选定,打算将其拍成电影。制片人本木庄二郎先生打来电话与我约定了和黑泽先生的面谈时日。今天就是初次会面,就剧本进行第一轮讨论。
黑泽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我虽预感到这即将到来的会面会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却无法预先揣摩出个中究竟。多想无益,不管怎样,哪怕想破脑袋也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于是我把专注的目光投向小田急列车的车窗,凝望那流逝而过的风景。
空地、农田、树木、房屋、房屋……小田急沿线看不出太多空袭的痕迹。闸道口、车站、商店街、公寓楼、蔬菜田、收割后的黑乎乎的稻田、房屋、房屋、空地、闸道口,又是新的公寓楼。轰隆轰隆,放眼望去,都是房屋、房屋、房屋……刚才就余韵袅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的歌声,逐渐变得清晰响亮。东京虽然看似广阔,谈起恋爱也显局促;浅草的风情让人心驰神往……我坐在头一回乘坐的小田急5列车上,目光虽然锁定在窗外的风景上,脑海深处却像留声机一样,反复地响起这首二十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东京进行曲》。
看个电影去吧 喝喝小茶去吧 干脆搭乘小田急线 逃离尘嚣吧 新宿啊 日日换新颜 连那武藏野的月亮哟……
《复眼的映像》读后感(六):天生的编剧
作者/时间之葬
2018年7月19日,日本著名编剧桥本忍因肺炎辞世,享年一百岁整。
对于任何一位对日影稍有了解的影迷而言,桥本忍,都是一个不可能绕过去的名字。如果你未曾看过他的作品,你就没有看过日本电影史上最好的一批电影。
桥本忍入行的处女作,便是名满天下的《罗生门》。
《罗生门》的影史地位,应该已经无需赘言,不但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为日本电影的魅力所倾倒,更因其开创了一种“罗生门式”的叙事手法而成为后人不断效仿的标杆。《罗生门》的剧本,由桥本忍与黑泽明合作完成,两人也因此相识,就此开启了后来长时间的合作。
《罗生门》在编剧事业的起步阶段,能遇见黑泽明这样百年难遇的大师,是桥本忍的幸运。在与黑泽明合作的早期,黑泽明之于桥本忍,是亦师亦友的存在。在这一时期,黑泽明拍片遵循的是“编剧先行”的原则。
所谓的“编剧先行”,也即黑泽自己在脑海中事先勾勒了一个主题,然后把这一主题交给他最信任的几位合作编剧(除了桥本忍,另一位主要编剧是小国英雄),然后交由编剧进行头脑风暴,商议细节。对于细节的考究,落实到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场景,每一句台词。如此计议妥当,剧本完成后才交给黑泽明准备拍摄。
桥本忍(左)和黑泽明这种“编剧先行”的做法,正是黑泽明这一时期接连推出的几部杰作最重要的基础。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也就是凸显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根基地位,对剧本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务求在拍摄前做到心中有数,拍摄时自然不易出错。
这一时期桥本忍与黑泽明合作的作品,包括《罗生门》、《生之欲》和《七武士》等几部最优秀的作品。
《罗生门》《生之欲》《七武士》就桥本忍自己说,往往被公认为日影史上最伟大电影的《七武士》,就是这么拍出来的。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绝非心血来潮的偶然产物,而是经过黑泽明和几位编剧力求完美的结果。
《七武士》但这么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过于费时费力。如果剧本未能达到理想中的完美状态,电影就无法开拍。给黑泽明写一部剧本所花的时间,往往够给其他导演写三部。这样的效率,自然很难让制片厂满意。
所以从1955年的《活人的记录》开始,黑泽明也不再采用这种“编剧先行”的方式写作剧本,而是改用了一种更普遍的方式,也即桥本忍所说的“一枪定稿法”。
所谓的“一枪定稿法”,就是黑泽明让自己的编剧团队,根据自己的设想与要求,同时写同一场戏,最后由黑泽明选择最佳的版本使用。如果在不同版本间各有优劣,便摘取各自出色的部分使用。
《活人的记录》这样一来,编剧之间不再进行碰撞和交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某些细节反复斟酌与探讨,最后的成品,自然也难以十全十美。黑泽明采用“一枪定稿法”完成的桥本忍编剧作品,有《活人的记录》、《蜘蛛巢城》、《战国英豪》、《懒汉睡夫》等片。
《战国英豪》《蜘蛛巢城》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桥本忍自然更尊重黑泽明早先的做法,而对后来的“一枪定稿法”颇有微辞。他曾批评《战国英豪》的剧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从那时开始,他与黑泽明不再是过去那对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到了60年代,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但即便如此,桥本忍这十年的资历已经足够煊赫和骄傲,凭借与黑泽明合作的这些作品,他已经足以跻身当世最伟大的编剧行列。而且那十年间,他靠写剧本获得的收入,也十分可观。
虽然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桥本忍在50年代初的剧本费已经可以领到30万日元,以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大概每写三到四部戏就可以买一套房子。这样的资历与收入,可以说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然而,在与黑泽明“分手”后,桥本忍却并未停止其继续求索的脚步。如果说黑泽明是把他领进电影这一行,并教给了他受益终生的编剧技巧。那么后来的桥本忍,则是彻底摆脱了外界的约束(在与黑泽明合作时,剧本最终总是要黑泽明定夺,甚至在编剧团队中,小国英雄的话语权也要更高一些),可以肆意展现自己的态度与才华。
在桥本忍的“后黑泽明时代”,他的作品水准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日益精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与小林正树合作的《切腹》和《夺命剑》,与冈本喜八合作的《大菩萨岭》、《侍》和《日本最长的一天》,与五社英雄合作的《人斩》,与今井正合作的《报仇》,以及与野村芳太郎合作的《砂之器》。
《大菩萨岭》《人斩》《报仇》《砂之器》不难看出,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武士片。如果再算上之前与黑泽明合作的《七武士》、《蜘蛛巢城》和《战国英豪》,我们基本可以说,桥本忍一个人写出了史上最出色的武士片。
桥本忍的这些武士片看似各具风格,故事与主题也不尽相同,但是背后殊途同归的一点,是对武士道的质疑,是把传统的武士放在现代的语境下去描写其挣扎与困境,因此而得出的冲突,往往变成了个人与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冲突。因其无法化解,而显出雄浑苍凉的悲剧气质。
如果说《七武士》拷问的是武士行侠仗义的意义,那么像《侍》和《人斩》这样的作品,质疑的就是武士本身。作为日本的骄傲,平民向往的贵族阶级,武士却只不过是家主手下的杀手和棋子,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找到拼搏的意义。
而在《切腹》和《夺命剑》里,这种悲剧是宿命般的与时代的对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津云半四郎和笹原伊三郎,都是符合武士道要义的最杰出代表,他们始终都保持了作为一位武士的高贵。但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武士道里自相矛盾的部分,本质上,是其虚伪和服务权力的部分。而他们最后的死亡,不仅意味着权力对个体无情的碾压,更意味着属于刀剑的旧时代被属于火枪的新时代淘汰的大势。
《切腹》《夺命剑》看透了这一点的桥本忍,算是真正看透了武士。所以这些影片虽然由不同的导演执导,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作者——桥本忍。而离开了武士这一题材,桥本忍也没能创作出与这些影片达到同一高度的作品。
虽然不是导演,但桥本忍依然可被视为具有鲜明作者属性的电影创作者,在编剧里,实属罕见。而桥本忍自己当导演的作品却都不成功,他似乎天生就擅长用文字而非影像去表现人物和世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桥本忍生来就注定要成为一名编剧,也只适合做一名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