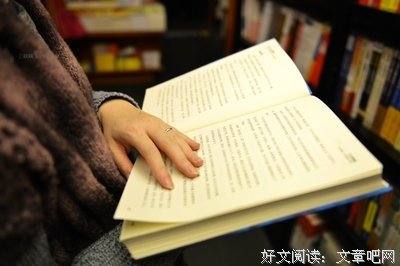《重于天堂》读后感摘抄
《重于天堂》是一本由(美) 查尔斯·R.克罗斯 (Charles R. Cross)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于天堂》精选点评:
●这个时代里千千万万个无能且迷茫的青春期,想从操蛋的生活与家庭中挣脱出来的青春期,都是你在为我们写配乐,谢谢你Kurt
●#新书上架#4月5日是科特·柯本逝世25周年。美国著名音乐记者查尔斯·R.克罗斯通过4年调查、400多次采访,生动再现这位摇滚巨星短暂而炽烈的生命足迹。不仅呈现了20世纪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地下摇滚乐的辉煌群像,更讲述了一个始终渴望爱、孤独的孩子的故事。
●两天两晚差不多7小时读完。如果那个年代没有毒品会是怎样的世界!
●“我是破碎的娃娃,烂掉的皮肤,娃娃的心,代表着刀子,在我的余生,剥下我小小的心脏,攒在你的左手里。”
●一下子,突然就成了rockstar
●校对是吃屎的吗
●不文明用语过多 不符合出版规范
●读完好像才觉得有那么点认识科特科本
●25年了。希望你安息。
●好多别字………
《重于天堂》读后感(一):不是书评,是一些私人的读后感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遗忘了他或者说是有意的躲着他。最近读《重于天堂.科特柯本传》,才知道他比我想的还要痛苦的很多。我那些听涅槃乐队的日子似乎从岁月的湖底慢慢浮现上水面。那时的我或许如同柯本万分之一的苦闷,或许是有一些羞耻的和不愿意诉说的事情积压在心底,伴着升学的压力和青春期的荷尔蒙或者是情欲的起伏,但是现在回头看,比起当时的无意识自我代入的共鸣,现在的冷静旁观却也窥得了别样的景致。当你在其中的时候,你只是体验;而当你不在那里的时候,你得以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个岁数回头看,当年在社交网站写着“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的青春居然觉得有一丝的邪恶,我为自己的恶意而后悔,我好奇当初的我是什么心态拿别人的死来标榜自己,或许我当时真的以为和柯本有共鸣,而现在我想我当时肯定错了,误读了柯本。我只是一些苦闷,而他是真的痛苦;我可能是一些跟风,而他是真的善良和难以忍受。当我随着岁月的渐渐流逝而变得对自己越发诚实的时候,我能够以一种悲悯而非对抗的思维去看待众生和自己的时候,我似乎从那些直白惨淡的话,从那些看起来假大空的文字中明白真正的道理。
柯本是不幸的。众人都知道他是摇滚乐历史上有名的27岁俱乐部成员,可是比起莫里森亨得利克斯乔普林们的被动死亡,柯本是以一种极其极端的方式自杀,那种自杀的方式与其说是勇气,倒不如说是绝望。柯本有着一个缺爱的童年,父母的离异和再度组建家庭,加上他天性敏感,这样的成长背景可想而知对一个人日后心里塑造的影响。这不需要用太多的文字去表述,当我们活到这个岁数,回望自己的人生就会明白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对一个人一生性格近乎定型的影响。
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性心理。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柯本是极度羞愧的,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一直担心自己的阴毛长得少,要长得足够多才称得上男子汉;还有他的初次性体验,他试图和一个残障女生做爱未遂,被对方的父亲告性侵犯,而柯本因年龄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到后来他终于很不顺利的完成人生的第一个性交,他在第二天走在大街上还把手放进裤裆里,摸着然后把手放在鼻子上闻那种味道,我真的挺感谢作者可以把这种细微的事情写出来,通过这种细节,我并不是当成八卦,而是极其严肃的从中窥得一个人的心理。我记得我最尊敬的瑞典导演伯格曼在青春期也面临着很严重的性心理问题,他甚至一度想到奸尸,而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和尸体做爱对一个极度压抑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伯格曼后来有机会和很多女人做爱,然而似乎他在性方面并没有达到一种和谐。
再说到音乐,音乐对柯本来说是一种出路。出路,这个字眼现在很少有人严肃的去看待它了。当一个人真正无路可走的时候,不是崩溃就是自杀,而这时候出路就是一道光。柯本在遗书里或者是什么我记不清楚的场合,说来世愿意做Leonard Cohen,Cohen或许对他来说是一道光,一道可以从他人生裂缝和心灵的黑暗裂痕中射进来的光。柯本有着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觉得做音乐是自己的事情,很讨厌唱片工业和娱乐圈,一方面又似乎为听众不多或者观看量这种唱片工业指标数字而不满,当然如果刻薄的说,他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不在乎,还是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欲望。
柯本的人生很短,我听柯本的时候不大而现在我已经活到比他去世的时候还大几岁的年纪了;柯本的人生很长,那么多的爱恨情仇,那么多压制的情绪,那么多的不伤害他人而无法释放的自我,那么多的矛盾和对立,现在我会想他如何忍受着剧烈的胃疼和娱乐圈的重负还有那大量的毒品摄入,还有一个家庭,而最后到他决定去死。爱一个人,祝福一个人,自己去死,而留给对方一次崩溃。书里写道康妮在最后,剪下柯本的一小撮阴毛,然后双腿跨在柯本的尸体上,伏在他的胸口痛哭的场景,看起来有点cult和惊悚,但是也回到了一个我早已不再熟悉的人类最开始的那种情感,超越或者无视所谓的文明礼仪,发自性情的真正哀悼,那里面有一种深情,那种看起来变态的举止中有一种或许我们无法理解的真爱。
合上书,我想再次说,柯本比我想象的要痛苦很多。如果可以的话,以后我尽量对他保持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一种我理解之后的对生命和他人的尊重。我在一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似乎有不少人愿意看,但是现在的话,似乎很多人也不太明白我在想着什么,我觉得这并不重要,一个人如果决心做自己的话,那就是径直地走下去,而不是去过分的考虑其他。我想柯本也是一个决心做自己的人,只是他不够爱自己,似乎也不愿意伤害其他人,这给他造成了很多矛盾。有时候我想,他或许只是一个纯真而躁动的大男孩,一如Patti Smith写给他的那首歌《About a boy》唱到的那样,just a little boy who will never grow。这样也好,他的人生定格在那里,而我,和读着这篇文章的你们,已经在渐渐老去,或许有一天当你我再次相遇的时候,我们从彼此的凝视中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重于天堂》读后感(二):To Kurt:提前的生日祝福
中英译本 原版是在孔夫子淘的 算是同学送我的18岁礼物透过层层夸大和防御,也许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kurt。印象中MTV那场不插电,他抱着吉他在台上唱歌,金发蓝眼睛浅浅的酒窝,我以为他一直如此温柔。可没想到他当时就已深受毒瘾折磨,上台前害怕僵硬不敢登台。
可是一个温柔的人又是怎么会唱出绝望的rapeme,那些戏谑多变的节奏背后他装作轻松地带过对父爱的渴望,ultimate love to Love. 挣扎,但一己之力无法阻挡下坠。
不知道当初love对他吸毒的纵容是否正确。如果两个人为女儿诞生的戒毒能坚持下来,如果柯本无数次戒毒能不以复吸告终,如果他的胃病能变好不至于要沉溺幻境抵御痛楚……如果如果。就算没有现在的柯本也不要紧,希望他能快乐。
1993不插电(unplugged)忧郁他有些表里不一的可爱,表面说MTV一直播放他的歌实在太烦,私底下和经纪人吐槽MTV宣传力度还不够大。他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结束一段关系或是解雇一名乐队成员都靠拖延、回避问题。如果你要问一个小天使是怎么成长为阴暗的少年,可能是家庭无穷无尽的吵架吧。
看到最后真的很难过,他明明很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队友。
不想要女儿Francis生长在一个他阴魂不散的家中,“Empathy”,绝命书中反复提到的同理心,他拿着毛巾去了阳台外方便处理血迹的地方自杀。
注射了大量毒品,猎枪散弹打破了他的头盖骨,面目全非。他太过敏感。
他需要无穷无尽的爱,他只是不够爱自己。He needs Love (namely connie love.
但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也许这只能是最后的举措,heavier than heaven.
书中插图 原版插图会更多一点说说这本书吧。翻译对杂七杂八的这些乐队文化也都了解,很自然流畅。尤其到最后的最后,真的快哭出来。谢谢作者能够费心费力还原一个众说纷纭中的柯本。
意识到他这一生都在挣扎之中,自我挣扎和毒品挣扎这样平常的事情。
和猫和bean褪去巨星身上的光环的他,也只是一个需要人爱的大男孩。
但这和他在词曲唱绘画的天赋绝不矛盾。而健康快乐的生活和艺术才华只能二者择一吗。
如果美妙的旋律和歌喉是要以年轮为代价的,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太致郁。
二十七岁俱乐部,每一个名字念出来都是长串的叹息。
这本书是在高三时候豆瓣雅众文化抽奖中的,学业重,后来又去武汉上学,拖到现在才看完。
那么这个和我同月同日生的大男孩,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吧。
记得要快乐。我们爱你。
2019.2.12 20:20
《重于天堂》读后感(三):致敬科特•柯本身上决绝抗争的摇滚精神
当电声乐器发展到饱和期时,不插电演唱会诞生了。和时下兴起的电音不同,这种旨在不使用电子乐器,不经过电子设备的修饰加工的现场化的流行音乐表演形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迅速赢得了音乐人的青睐,也斩获了大批粉丝的好感。
提到不插电,几乎很难绕过涅槃乐队在1993年举办的《涅槃:MTV不插电演唱会》。主唱科特·柯本难得地穿着宽松的毛衣,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用力唱着“来吧,保持现在的样子,保持一贯的作风”,唱完之后,他会像小孩一样调皮地吐舌,笑着跟观众说谢谢。
然而,就在这场为涅槃赚足了名声的不插电演唱会结束后的5个月,这位27岁的摇滚巨星,选择在自家温室里吞枪自尽。在科特·柯本遗体的不远处的土地上,有他钉在地上的遗书,遗书里写满了对妻子科特尼·拉芙的爱和对2岁女儿的眷恋,但这些牵挂,也没能牵绊住他求死的心。
《重于天堂》是美国著名音乐记者查尔斯·R·克罗斯撰写的科特·柯本人物传记,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摇滚巨星科特•柯本,是如何从乡下小镇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叛逆青年,成长为一代摇滚巨星的经历。
机缘巧合的是,作者查尔斯曾在美国西北部地区音乐与娱乐杂志《火箭》任编辑一职,这家杂志社,也是科特·柯本在乐队创立初期,收到他音乐小样的3家公司或团体之一。由曾在《火箭》任职的记者,来撰写曾指望《火箭》杂志发掘自己的科特·柯本传,真是再完美不过了。
从小镇青年到摇滚巨星
逃学、嗑药、酗酒,少年时的科特·柯本,是镇上所谓正派人士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坏小孩。几乎和所有的辍学青年一样,不上学之后,家里就想方设法来安排一个没前途但很稳定的工作。但这个无论是工作还是念书都让人头疼的坏小孩,在遇到音乐后忽然沉静下来。整日整日地把时间花在练吉他和写歌上。
19岁,他开始作为乐队设备管理员,跟着小妖精乐队去奥林匹亚做演出,并通过在小妖精乐队学到的经验,自己组建了乐队,这就是涅槃的雏形;20岁,柯本带着乐队首次离开阿伯丁去外地演出,同年他们就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第一支单曲《爱情嗡嗡》。
这距离他以粉丝的身份,在乐池里仰望小妖精乐队不过2年多的时间,涅槃乐队的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地不可思议。
2年后,柯本和他的涅槃乐队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摇滚乐队,唱片销量一度挤掉迈克尔·杰克逊,成为雄踞公告牌数月之久的人气冠军。
迅速地蹿红,为柯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沦为瘾君子,经常在参加电视节目时,也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
女儿的诞生,让柯本想过去戒毒,然而剧烈胃痛的折磨,又让他一次次借嗑药麻痹身体的痛苦,到后来,连麻醉剂也无法缓解他的疼痛,走红之后,科特·柯本一次次地处于戒断反应的折磨里,柯本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边饥饿一边呕吐,我感受着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胃痛”。
从第一次以乐队主唱身份登上舞台的无人问津,到万人演唱会的座无虚席,科特·柯本已经从阿伯丁的那个不被人看好的小镇青年,涅槃成为举世瞩目的摇滚巨星。但走红并没有为他带来更多的快乐,反而让他陷入深深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中。
封闭自我又袒露内心的矛盾个体
9岁那年,父母离婚并双双重新组建家庭,也许柯本的父母都害怕再经历一次离婚,所以,当柯本与他们的新伴侣发生冲突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另一半。
在父亲和继母的家里,柯本仿佛是多余的那个,于是他提出想和母亲一起生活。可是母亲也不要他。于是,他把行李装进垃圾袋里,开始了在父母家周边的流浪。
7年后,在歌曲《something in the way》中,柯本还原了这段流浪的经历:歌曲中的歌者住在荒芜的大桥下,每天靠捉鱼果腹。但实际上,柯本的这段日子远比歌词更悲惨。他睡过阿伯丁居民的门廊,寄宿在社区医院的等待室,还靠着假装病人家属从社区医院食堂骗饭吃。
这段被父母抛弃的经历,让柯本深深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渴望被爱,却又吝于表达;渴望被观众认可,却又反感闪耀的镁光灯。他仿佛一个矛盾个体,一边对周围的人锁上心房,一边又在歌词里肆无忌惮地袒露内心。
他为长期同居的女友写下《关于一个女孩》,在歌词里说虽然女孩对自己冷眼相待,但自己依然希望能抽空和女孩约会;但现实里,对女友的苛责,柯本只是一味地逃避,讽刺的是,直到柯本去世很多年后,女孩才知道,当年那首红遍全球的歌是写给自己的。
对柯本来说,音乐绝不只是用于和女孩谈情说爱的手段,它更是一种自我表达和变革。指责虚伪,批判歧视,鼓励平权,看起来是公益力量才会做的事,在涅槃的音乐里都能找得到。
单曲《风华正茂》的歌词中,自然繁茂,男生边哼唱边放枪,看起来好不和谐的元素,实际上是锐利的讽刺,柯本在谈到这首歌的歌词时说,“我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的人,我不喜欢侵略性强的人,这首歌,就是在抨击这样的人”。
柯本短暂的一生中,写过很多信,有抨击虚伪乐评人的抱怨,也有尝试同父母重归于好的恳切之言,可惜大多数信都没有被寄出去。但抱怨也好,让人无法释怀的抛弃也好,那些科特·柯本始终没说出口的话,都在涅槃的歌曲中被全世界听到。
从容赴死中的摇滚精神
在那场著名的不插电演唱会前,柯本请假2个钟头出去嗑药,彼时精神的顽疾加上剧烈的胃痛,让柯本只有靠药物才能维持健康的舞台状态。尽管身体状态并不是最佳,他却在演唱时完美发挥。
几个月后,就在大家都觉得柯本的状态又回来了时,科特·柯本在自家花房里饮弹自尽。极盛时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谢下人生的大幕,这种谢幕的方式,仿佛对现实痛苦最颓废的逃避,却也是对两极人生最激烈的反抗。
童年时被全家人捧在手心里,少年时却遭遇所有人的抛弃,成名后有钱有爱人有孩子,却又遭到全世界的质疑,人生的起起落落大抵如此。
少年时,当被父母抛弃时,他毅然出走;拼搏时,被唱片公司压榨,他果断解约;成名后,媒体攻击他妻子时,他公开反击。他为少数群体发声,也向不公宣战,这个连分手都不敢当面和女友说的懦夫,在该硬气的时候从来没有选择逃避。
穷过,孤独过,被全世界抛弃过,命运决定送他一份功成名就的大礼,在柯本成名后,即使是不善表达的父亲也尝试着与他重归于好,一切仿佛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时,柯本选择为自己写下人生的休止符。
在嘲讽了造物主,批判了不公后,他戏弄了命运。命运自以为是地送他一份名利双收的大礼,他恶作剧般地逃走了。谁能说,这不是摇滚人最激烈的反抗呢?
在科特·柯本那封长长的遗书最后,他说,“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柯本就像个以死抗争的悲剧英雄,在以抨击、讥讽和嘲笑的音乐表达了自己对世界无尽的爱后,决然地以死亡拯救那些向往改变又沉沦于现状的愚人。
究竟什么是摇滚人?
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用华丽辞藻嘲讽阴郁人性,他们是这世界的反叛者,他们也是倡导改变的先驱人。
柯本去世很多年后,涅槃开了演唱会。当年长发飘飘的少年贝斯手和鼓手都有了中年肥,只有大屏幕上的柯本,还是眼神清澈的年轻模样,他微笑地看着台下或流泪或尖叫的观众,唇边勾起嘲讽的微笑。
《重于天堂》读后感(四):关于一个男孩——科特.柯本
1993年11月18号的纽约MTV演播厅里,舞台点上了黑色的蜡烛,摆着占星百合,吊着水晶枝形吊灯。制片人之前问柯本:“是要打扮成葬礼的样子吗?”柯本说:“是的,就是要打扮成葬礼的样子。”
涅槃乐队在这场演唱会中演唱了十四首歌,其中五首都跟死亡划上了关系。特别是最后的安可曲《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歌词讲述了一个寻找出轨妻子的男人,在阳光永远无法照到的松林间身首异处的故事。科特.柯本对这首歌的诠释一开始冷静克制、浅唱低吟,直到最后情绪最高点爆发出了最原始的嚎叫,似乎绕梁三日,余音不断一般,完成了这首歌的最动人心魄的决定版。
这是一场放置于摇滚史上都可以永垂青史的演唱会,也是科特.柯本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最高点。
盛极而衰,就柯本当时的健康状况来说,几乎所有人都对他的未来不是很乐观。只是没有想到,才刚刚到达最高点的音乐天才科特.柯本,他的失败会来的那么迅猛而且惨烈——五个月后,柯本在华盛顿的住所,用猎枪轰掉了自己脑袋,时年27岁。
在绝命书中,柯本写下了摇滚巨星尼尔.杨的名句:“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而75岁高龄的尼尔.杨本人却弹唱至今。
把自己的生命燃烧成一团火,在它势头最盛的时候熄灭,只留下一缕供人垂叹的青烟。
在很早的时候,柯本同自己的朋友聊天时,他的朋友会想到自己三十岁之后的烦恼,但是柯本从来就没有,因为他总是会说自己根本活不到三十岁,在那之前,他一定会选择自杀。谁都能够轻易看出柯本内心痛苦的折磨,他走起路就像是一个自杀的实体,而且总是在谈论着自杀。
在他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痛苦一直掐住了他的咽喉,只有偶尔几次,才能从中缓口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生活当中察觉痛苦的敏锐触感是必不可少的,就像约翰.列侬因为家庭关系的缺失,成年后唱《Mother》如此撕心裂肺一样。
对于柯本来说,察觉生活本身的痛感非常容易,他能创作也能诠释会多让人感同身受的痛苦,只不过这种痛苦紧紧包围着他。仿佛把这些情绪诉诸于作品并不能够稀释这种痛感,反而让这种痛感把自己反噬得体无完肤。
就像是童年时代,父母的离异,导致他根本不能够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享受一个完整家庭的幸福。除此之外,因为自己内心的敏感,使得自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父亲和母亲之间踢来踢去,很多时候,他都在阿伯丁的纸盒子里或者汽车后座过夜。年幼的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写下了“我恨爸爸,我恨妈妈”的字样。
也正因为如此,柯本比很多人都清楚,其实那些家庭生活条件优渥并且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心中的朋克,同自己心目中的朋克是不一样的。那些人眼中的朋克是自由的,是一往无前并且不走回头路的。但是柯本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朋克也不过是标签而已,遵循朋克的规矩,其实要比它所反抗的循规蹈矩有更多的框架。
是为了自由而反抗,还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切的界限,已然模糊不清。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雅图的Grunge乐队会觉得柯本不够朋克,不够粗粝,有些风格太过于流行。柯本一面说自己根本不在乎那些媒体,不在乎所谓的流量,但是他的内心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担心自己的音乐赚不到钱。没有人会比他更加矛盾,一方面他渴望更多的知名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名声避之唯恐不及。
是勇敢做自己还是顺应这个世界的法则呢?在很多时候,柯本的身上都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站在人生岔路口的那种手足无措。
比如在NBC节目当中的演唱会上,柯本和克里斯特在一曲终了时,他们抱着对方舌吻起来(虽然NBC后来删除了这一段)。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里,柯本他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个为同性恋性取向撑腰的姿态出现的。这源于他内心骨子里的反抗精神,在他的故乡阿伯丁,那里有很多所谓的“红脖子的人和乡巴佬”,他们裹挟着偏见,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同性恋给吊死。柯本一直希望以这样的姿态向那种人表明自己的态度,摧毁他们的自信心。
可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妹妹金是同性恋时,他还是会劝自己的妹妹“不要完全放弃男性”。这是属于柯本的一种困惑和挣扎,也是属于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深不可测的鸿沟。柯本用自己的影响力和音乐,想要使得这个世界能够朝着美好的方向倾斜一些,可是他也知道,这一切只是螳臂当车,他要对抗的世界浩瀚到看不到边际。
一如约翰.列侬的死亡一样,对于很多摇滚乐手来说,死亡给他们的人生划上一道休止符,同时也使得他们成为后人心中定格的浪漫符号。但我不愿柯本是一个符号,他是一个人,拥有痛苦欢乐而且有血有肉曾经活过的人。
如果他被定格成为一个符号,活成了一个光辉伟岸的影子,那么属于柯本的那些私人情愫究竟该如何成立呢?天才的终点不是超越凡人,而是成为芸芸众生的一个典型。他拥有自己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弱点:童年的阴影、胃病、毒瘾以及对媒体的恐惧。
柯本爱惜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又无法自拔于毒瘾之中。他在英国开演唱会的时候,看着一群瘾君子少年拿着他的巨幅照片欢呼时,难过地哭出来。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在孩子们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面对着自己的堕落他又感到手足无措。这是我在读柯本传记时最感慨的一点,天才不会走到人们的对立面,他只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更为普遍而且能够共鸣的无奈。
在多次进入戒毒所无果之后,柯本尝试了很多次自杀的选择。在最后一次,当他坐在逃往华盛顿住宅的飞机上时,邻座就是枪炮玫瑰乐队的贝斯手达夫.麦卡甘。涅槃乐队和枪炮玫瑰乐队嫌隙已久,但是在那一次,柯本同麦卡甘聊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麦卡甘分享自己在戒毒所的经历,以此鼓励柯本尽快走出来。
同曾经的老对手化干戈为玉帛,一切看起来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这不过是时间的回光返照,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跳入时间的缝隙里,再也没有回头。
在那以后,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在为柯本创作的about a boy中唱到:just a little boy,who would never grow.柯本永远只会是一个27岁的男孩,再也长不大了。
等到有一天,作为他的歌迷,凭借着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终于能与他并肩时,你还会佩服他的勇气吗?等到有一天,终于将他甩在身后时,你会唏嘘他的看不开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曾为他可惜,为他感动不是吗?他的音乐比他更长寿,因此我们依旧能够穿越时光的缝隙,捕捉他的剪影,找寻我们最开始听摇滚乐的模样。
Unplugged in New York (Guitar Schoo评价人数不足Nirvana / 1995 / Hal Leonard Corporation《重于天堂》读后感(五):那年四月,他决定去死
1994年4月5日,西雅图上空的一记枪响,结束了一个27岁金发男人的生命,也把一个摇滚时代推向盛极而衰的顶峰。
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男人的脸被印在了大大小小的T恤上、手机壳上、杂志上、周边上。每年四月,从美国东西海岸到中国聚集着摇滚青年的角落,都有人缅怀他、纪念他。
他是涅槃乐队(Nirvana)的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27岁俱乐部"中名头可与约翰·列侬一较高下的摇滚巨星,一代人的文化符号。而在中国,虽然专辑从未正式被引进,在盗版CD和打口碟的哺育下成长的摇滚青年心中,科特·柯本是不可替代的。那句"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更成了众文青的座右铭。
柯本为何要去死?他痛苦的来源又是什么?
在英年早逝是家常便饭的摇滚圈,为何他的死格外被人铭记,甚至因此异化成一个文化符号?
1
科特也有过美好童年,以及他理想中"其乐融融"的家庭。但好景不长。科特的父母年轻时脑子一热草草成婚,之后老套地被柴米油盐击败——科特8岁那年,两人离婚了。
父母离婚对科特打击很大。科特反应激烈,闹个不停,母亲不堪他的吵闹,便把他送到父亲那里。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抛弃"的体验。科特和父亲在狭小的拖车房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父亲也向他承诺,自己不会再婚。
然而父亲很快食言,不仅迅速再婚组建新家,家中还多了弟弟妹妹。
还是个孩子的科特体会到了"背叛",更讨厌和弟弟妹妹们分享父亲的关注。他和继母关系不好,进入叛逆期后,更是处处和家里对着干。对着干的下场就是继母更加讨厌他——不久后,他被赶出家门。
2
科特的青少年时期是颠沛流离的。被赶出去后,他曾经和舅舅同住,和叔叔婶婶同住,和祖父母同住……却在哪里都待不长久,过不了几星期就得换地方。想必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还是母亲的爱。
10岁的科特兜兜转转后,他不得不回到父亲的新家,没多久后又被赶出家门,这次父亲做的更绝:科特八年级时,父亲直接把他的行李收拾好,开车把他丢在母亲家门口,然后绝尘而去。
母亲没有像科特渴望的那样敞开怀抱接纳他,而是愤怒他扰乱了自己的生活。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科特更愤怒,两人关系不断恶化。家庭关系带来的痛苦让科特开始抽大麻(这也是他吸毒的开始)、偷酒、砸商店玻璃、逃学,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更加不受母亲待见。
不久后,科特从高中辍学。他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大家都很假"。他从家搬了出来,四处流浪。他睡公寓走廊、睡医院的家属等候室、甚至睡在朋友家门口的纸箱里;与此同时,他还靠在学校当清洁工、给旅馆擦马桶等零工为生。直到和第一任女友崔西相恋,科特才得以搬到女友家去住,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quot;原生家庭"是一个被讨论了无数遍的概念。而破碎的原生家庭,颠沛流离的体验,加上科特格外敏感的性格,早早的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
3
郁郁寡欢,觉得全世界都没有自己容身之处的科特找到了精神寄托——朋克摇滚。彼时在他的老家阿伯丁,朋克摇滚唱片很难买到,他把好友兼朋克乐手巴兹·奥斯本(Buzz Osborne)寄给他的朋克摇滚磁带翻来覆去地听,一遍一遍地研究。
这种地下文化让科特第一次有了归属感。17岁那年,科特遇到了19岁的克里斯特·诺弗斯里克(Krist Novoselic),这个身高一米九几的男孩后来成了涅槃乐队的贝斯手。
17岁的科特乐队从朋友家的派对和无名俱乐部开始演起,辗转换了好几任鼓手,最终敲定了大卫·戈尔(Dave Grohl)。由于乐队几人住在不同的城市,每排练一次,他们都得轮流开十来个小时的车,才能把所有成员捎到排练现场。
技艺精进的同时,科特开始疯狂地给各大唱片公司寄小样(和日后"淡泊名利"姿态相矛盾的是,科特其实有强烈的成名意愿),终于被西雅图地下厂牌,后来大名鼎鼎的Sub Pop签下。
此时的涅槃乐队很穷,但Sub Pop也很穷。乐队巡演时不得不自掏腰包,几个人挤在一辆破车里,有时连油钱都付不起。最落魄的时候,实在没钱买吃的,乐队几人甚至得去给流浪汉开设的慈善食堂蹭饭。
那时科特的一大愿望就是乐队能混出个人样,他们能"live comfortably",过得舒服点。后来他真的成名了,有了钱,加得起油,吃得起饭,还住上了大房子。但他却从未实现"live comforably"这个愿望。
4
涅槃乐队充满个人情绪和不安的音乐很快引发了青少年们的共鸣。当时,没有哪支乐队的歌比涅槃乐队更能充当青春期痛楚的出口。大唱片公司一拥而上,纷纷伸出橄榄枝。涅槃乐队最终被格芬唱片(Geffen Records)签下。格芬唱片很有钱,这回,他们终于不用自掏腰包去巡演了。
MTV颁奖典礼上穿着睡衣演出的科特接下来是第二张专辑《Nevermind》的爆红,单曲登上各大排行榜的榜首,唱片销量急剧攀升,很快成为金唱片、白金唱片……不但如此,大家纷纷回购起涅槃在Sub Pop出的第一张专辑《Bleach》,grunge的各路小乐队也跟着鸡犬升天,纷纷被大厂牌签下。阿富汗辉格党乐队(The Afghan Whigs)的主唱就曾说:"要我说,我们(各路grunge乐队)都该给科特·柯本送果篮。要不是他,咱也不能获得这么多关注。"
Grunge这个地下摇滚流派被推上了流行舞台。全国各地的星探纷纷坐上飞机,前往西雅图挖人;时尚设计师马克·雅克布(Marc Jacobs)推出了主打grunge法兰绒衬衫元素的时装系列;甚至有洛杉矶和其他城市的乐队专程搬到西雅图,冒充西雅图本地grunge乐队,以期被唱片公司签下。
而最亮的聚光灯,自然对准了科特。
5
科特和柯特妮·拉芙(Courtney Love)的相恋被各路媒体形容为"新时代的Sid and Nancy"。柯特妮是个丰腴而漂亮的金发妞,洛杉矶朋克乐队Hole的主唱,早年跳过脱衣舞,抽烟喝酒吸毒骂街无所不干。这对摇滚情侣身上的爆点让媒体乐疯了,三天一小稿,五天一大稿,紧盯着他们的私生活不放。科特的女友粉们也很讨厌柯特妮,纷纷写信骂她是婊子。
除此之外,就像大家把约翰·列侬的放飞自我怪罪到大野洋子头上一样,科特深陷毒瘾的锅也被甩到了柯特妮头上——毕竟"红颜祸水"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甩锅大法。
实际上呢?两人半斤八两,臭味相投,谁也不是白莲花小白兔。从某种意义上说,柯特妮和他是平等的:他们都是朋克乐手,都有破碎童年,都觉得与周遭格格不入。
两人相互取暖似地走到了一起。很快,柯特妮怀了孕,两人成婚,幻想着女儿出生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组建一个他们俩此前都无福消受的美好家庭。
老婆虽然怀孕了,深陷毒瘾的二人依然没有戒毒。媒体嗅觉灵敏,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纷纷猜测科特的女儿出生后会不会是弱智——弗朗西斯在媒体的聚焦下出生了,并且一切健康。
科特一家三口对于媒体的恶意,科特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大家都想让我赶紧去死,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摇滚悲剧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
6
对于成名,科特感受复杂。一方面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名利都是身外之物,自己只关心把音乐做好";一方面他又很玻璃心,曾打电话给经纪人怒斥自己的歌曲MV在电视上的播放次数不够多。
爆火之后,评论界纷纷把科特推上"一代人的代言人"的神坛。采访时,追着问他"你作品里对社会冷漠的批判源自于哪里呢?你自己的思考呢?"科特回答时往往很无语:"我要说的都在歌里了,大家听歌就行了。"不禁让人想起众人围着流浪大师沈巍追问人生哲理的画面。
名利常常会带来巨大压力,何况是一夜成名。科特对周遭事物的感知是极度敏感的。这是他才华的来源之一,有了这种敏感,才有他在音乐上的表达。这种敏感的副作用就是,外界的非议带来的打击会在科特这里被十倍放大、扭曲。
柯特妮在好莱坞摸爬滚打过,心智强大,可以骂街了事。科特不行。种种纷扰,加上从没解开过的家庭心结,让他不堪其负。
最可怕的并不是梦想无法成真,而是梦想成真后,背后更大的空洞。对于科特来说,他是成了摇滚明星,但然后呢?
内心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不会因为实现理想而得到解决的。
此外,科特多年受胃痛折磨。去多家医院检查,都没有结果。极度痛苦时便会拿毒品镇痛,成瘾后的戒断反应往往会让他更痛,就这样恶性循环了下去。科特在日记里写到,他一方面希望胃痛消失不见,自己能恢复健康;一方面又害怕如果没了胃痛带来的痛苦,自己会失去创作能力。
7
科特是在具体哪个时刻决定去死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他的作品中已有端倪。在第三张专辑《In Utero》中,科特写了一首叫《I Hate Myself and I Want to Die》(我讨厌人生,我想去死)的歌。记者问他,这是你的心声吗?科特笑笑说,开玩笑的而已。
有意思的是,绿洲乐队(Oasis)吉他手诺亚·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搞不懂"科特·柯本这样的天才为什么想去死",从而灵感大发,写出了金曲《Live Forever》(永远活着)。
涅槃乐队1993年的MTV不插电演唱会是科特·柯本登上神坛的前兆,也是丧钟敲响的一刻。演唱会现场按照科特的意思,摆满了白色花朵和蜡烛,如同葬礼现场。此时的他,或许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
MTV不插电演唱会上的科特23年后,西雅图grunge乐队Soundgarden的主唱,科特生前的好友克里斯·康奈尔(Chris Cornell)在演出上翻唱了一首齐柏林飞艇的《我死之际》,之后回到宾馆,上吊自尽。
毒瘾一发不可收拾时,科特被多次送去戒毒所戒毒,还曾自杀未遂。然而进进出出,总是不起效果。到了最后,自己也在戒毒的柯特妮发动众人劝说他再度去戒毒,他同意了。
乐队队友克里斯特负责送他去机场,好飞往洛杉矶的戒毒所。在去机场的车上,科特突然反悔,要跳车。克里斯特强行把他送到机场,准备押他上飞机,科特大闹起来,两人扭打成一团,科特趁乱跑了。
克里斯特回去后大哭了一场。他觉得自己这个认识了十年的好友,就要离自己而去了。
科特最终去了戒毒所。但死心已决的他,不久便半夜从戒毒所翻墙出逃,坐上了回西雅图的飞机。飞机上,他遇到枪花乐队贝斯手达夫(Duff McKagan),两人寒暄了一番。那时的达夫不知道,他竟是科特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熟人。
然后是一记枪响。
8
一个人是否能被真正理解?
我们所试图理解的科特,也不过是我们自身情感与痛楚的投射罢了。
科特也不是没有动摇过。他在采访中说过,自己希望女儿不要经历自己经历过的破碎童年,"就算有一天我和柯特妮离婚,我也要尽可能的给她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给她最好的爱"。
结果他在女儿两岁时便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女儿的生活。
一个熟人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如果我喜欢的艺术家的才华和成就来自于自身的痛苦,那么我宁愿他/她一辈子庸庸碌碌毫无才华,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也不想让他经受这些痛苦。不值得的。
这么说的话,我宁愿科特·柯本是个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