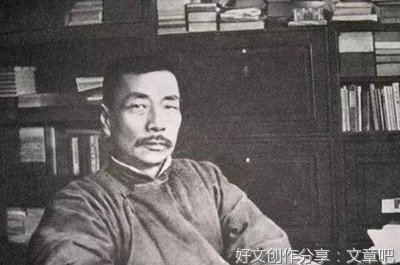《生者与余众》的读后感大全
《生者与余众》是一本由[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80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2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者与余众》读后感(一):最后三枪
读完小说结尾,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阿瓜卢萨朝我的心脏连开三枪。
第一枪来自穆维里。在堂娜“电影院”奶奶口中独自拯救了世界的小女孩名叫穆维里。在马库阿语中,这个名字意为“月亮”,她是另一个月亮“努埃尔”的变体。而根据小说的情节,星星的消失意味着世界的沉没或终结,当浩瀚的夜空再次出现星星时,世界迎来重生,因此,三个小女孩——作为月亮的穆维里和努埃尔与作为“星星”的特滕布阿形成了三位一体,她们分别对应着非洲的传说、非洲的苦难和非洲的未来。乌利在生前最后一抹光辉中霎时明白“她就是那个小女孩……”暗示,他懂得了这种神秘的联结。
阿瓜卢萨笔下的救世英雄摒弃了旧世界秩序的特征:不是背负父权叙事的部族英雄,不是好莱坞式的工业奇观,甚至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受难暗示也没有,一个幼小的女性形象,以近乎游戏的方式,“找齐所有的棍子并带到杧果林,接着把它们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从而固定住了苍穹和时间,使世界回归到正常的秩序。
天真的英雄不合现实的逻辑却符合文本的逻辑:因为堂娜“电影院”奶奶在叙述,叙述就意味着不断创造,如果叙述可以让潮水在满月下吞噬沙滩,叙述可以让孩子的双手挖掘出一个新世界,那么天真的英雄自然也可以在叙述中自足地存在。与其说阿瓜卢萨异想天开,不如说他对叙述的信任、对文学的信任超越了对现实的焦虑。这种纯粹的信任——我不得不承认——连我都感到难以置信,进而引发了我的羞愧: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竟然不能完全信赖文学?究竟是什么让我丧失了安哥拉作家身上的这种纯粹与轻快呢?
第二枪来自乌利之死。最初,我直接认定丹尼尔即是凶手。“就好像有人仅用一击,就从背后生生掏出了他的心脏”,丹尼尔从神秘文学之父手中读到自己的人生预言,为了捍卫家庭的幸福,背后偷袭,杀死了乌利。穿过乌利心脏的子弹也打中了我。
但再读时,这个笃定的判断开始动摇。乌利很早就表达过自己对水的恐惧,溺水的结局早已写在他的宿命中。阿瓜卢萨在写乌利之死时故意变焦,让镜头变得模糊,乌利“胸前一阵强烈的疼痛”,疼痛似乎来自外力,也有可能源自体内,而后面一句紧跟着似是而非的“好像”,更让死因变得暧昧不明。当乌利说“不要这样”时,他的对象是丹尼尔,还是一种更加无形的神秘力量呢?
从故事发生之始,阿瓜卢萨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反复打破现实和虚构的边界。无论是发现自己笔下的蟑螂女正在大街上狂奔的尼日利亚女作家科内利娅,还是在不同的小说中不断重写家族故事,直到醉酒后遇到去世多年的父亲的莫桑比克作家齐瓦内,他们都因为虚构角色介入现实生活受到触动,从而更新、拓展和修正了认知的边界。裘德书写的《桥梁建筑师》更是决定了世界的走向,随着作家的心态从封闭的城堡转向开放的建筑师,现实也从孤岛走向与大陆的再次联结。
虚构可以影响现实,现实也可以影响虚构,丹尼尔或许不是导致乌利之死的直接凶手,但当他以自己“认为的最好方式”处理稿件时,他的选择也和他最好的朋友乌利的命运关联在了一起。正是通过乌利之死,所有人的命运都进入了现实与虚构交融的混沌世界——也正是在这里,我恍然大悟阿瓜卢萨嵌置的设计,那些带着各自身份的人物,那些零散的奇幻故事,那些走马灯般转换的场景,都被纳入叙事线索的包裹之中。
第三枪来自落款的时间。一般来说,落款时间只是作者留下的可有可无的记号,不具有叙事功能,但阿瓜卢萨开了一个狡黠的玩笑。“2019年11月30日”也出现在神秘文学之父的故事的最后一行,它让整个故事如穿过针眼的骆驼,成了神秘文学之父的故事——即丹尼尔的人生之书的变体。
巧合的是,“2019年11月30日”在现实中可以视为疫情前后世界的分界线。或许这只是偶然,阿瓜卢萨只是恰好在这一天写完了故事,但故事中隔绝的孤岛、巨大的闪光、撕裂的夜晚无疑有了更加强烈的隐喻性意味,“一段纪元慢慢终结,另一段渐渐开始。但彼时无人知晓”不正是临界点降临时的真实写照吗?于此,小说和现实构成了巧妙、讽喻而诡异的镜像,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故事中依稀辨认出自己身处其间的魔幻世界的变形。
《生者与余众》读后感(二):这位非洲小说家的脑洞太大了太会讲故事
.
大雨连绵,水漫世界。只余一座孤岛,完全搭在一大块坚固的浮岩之上……(小说家露西的作品情节)
~~~
《生者与余众》
作者: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出品方: @世纪文景
.
阿瓜卢萨是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也是近年来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各种文学大奖都青睐他。
.
我很喜欢他的《遗忘通论》。一部描述战争中女人的遭遇的作品,内质残酷而文笔诗意优美,卢多把自己束缚在公寓里,寸步不离,像女版的《莫斯科绅士》。
.
《生者与余众》依然诗意优美,没那么残酷,探讨的主题宏大深邃,且很幽默。
.
这是一部末日幻想小说。故事的场景设置在偏远的莫桑比克岛。大雨连绵,水漫世界,一群参加笔会的非洲作家被困在这座孤岛上。这个故事不是科马克•麦卡锡式的那种凄惨荒凉氛围,除了打不通手机、没有互联网之外,这个小岛依然保持着文明的秩序,作家们还可以侃侃而谈文学、创作等等。
.
作家们一本正经地探讨非洲小说的出路、性别、身份问题等等。雨不停地落着,哪管它洪水滔天,这部小说具有一种文学反思和自嘲的意味。
桃花源的生活迟早要被打破的。有些混乱出现了,不是社会崩溃的暴烈场面,意外主要发生在作家和周围人的身上,那就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从书里出来了,把他们的生活搞得一团迷糊,真假虚实,难分难解。
.
阿瓜卢萨写得有趣,呈现了虚构的快乐感。
裘德的戏仿自传的主人公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两个裘德,他俩当然有些区别,没有哪本自传是完全真实的,而人们似乎更相信那个假裘德啊。
蟑螂女人就像是大哲学家,讨论人类繁杂且互不相容的Z教信仰,而蟑螂的繁衍能力和生存能力要远远胜过人类,它们会是世界的主宰吗?
.
小说采取了创S记式的七日叙事,互文特征明显,与《遗忘通论》也有关联,我们还能感觉到《圣径》《十日谈》《变形记》《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等文学作品的影子。
.
它还有点像是那种穿书式网文小说的高配版,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就是构筑了一个新的世界,可是,作家能否就充当上帝呢,作品人物有了自主意识后会怎样,那些被创造的新世界交错在一起之后,又会怎样呢?有趣的话题,文笔精彩,好看!
《生者与余众》读后感(三):七天时间,世界在文学中重生
2019年底,当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完成长篇新作《生者与余众》时,扉页上这段引语预言了一个即将来临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
撕裂的孤岛、被阻断的生活、封锁焦虑、核弹爆炸……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作家用澎湃的想象力书写对世界的隐忧,却与我们当下生活的困境构成奇特的暗合。
《生者与余众》是阿瓜卢萨继获得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的《遗忘通论》后最重要的作品,甫一推出便获得了2021年度葡萄牙笔会小说奖,在这个故事中,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不复存在,人们在绝境中探索,也在废墟上创造。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隔绝的小岛
《生者与余众》的主人公,正是《遗忘通论》中的记者丹尼尔·本西莫尔。
丹尼尔与女友莫伊拉定居于莫桑比克岛,他们邀请了非洲各国数十位作家来小岛参加文学节。这座充满诗歌与魔法的小岛仅以大桥与非洲大陆连接。
一天,小岛与外界沟通的方式突然全部中断,失去了网络、电力,暴风雨使船无法出海,大桥也神秘地无法通行。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节仍然照常进行,诸位作家之间也在不断进行交流、阅读与创作,直到他们猛然发现,真实与虚拟、现在与过去、生者与其他存在,一切边界都在悄然瓦解。
莫桑比克岛
尼日利亚女作家科内利娅写过一本《曾是蟑螂的女人》,她发现蟑螂女正在大街上狂奔,自己书中的人物进入了现实;
莫桑比克作家齐瓦内在不同的小说中不断重写自己的家族故事,直到他在醉酒后遇到去世多年的父亲;
尼日利亚作家裘德意识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正在四处招摇撞骗;
神秘的安哥拉文学之父恩扎基写下了丹尼尔的未来;
……
小说的主线故事采用了《圣经·创世记》的七日结构,每一天再划分为不同人物的主视角。作家们穿行于这座小岛的故事与记忆,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与身份,他们的奇思妙想不再停留在纸上,而是可以影响现实。上帝用七日造了世界,作家们也用七日经由写作走向重生。
与世隔绝的小岛映照着撕裂的世界,此外,书中还讨论了身份认同、贫富差距、女性权利、核安全等热点议题,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生者与余众》以魔幻之笔书写了切近而紧张的现实。
非洲文学的未来
2021年堪称“非洲文学年”,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及国际布克奖均被非洲及非裔作家收入囊中。《生者与余众》可谓是正在崛起的非洲文学的新声。
莫桑比克岛又名木希皮提,曾是非洲和东方之间最主要的商埠之一。在空间层面,莫桑比克岛是一个在历史和社会中实际存在之地,以民族、宗教和文化元素“光芒四射的混合”闻名。除了展示该岛作为岛民鲜活的生活环境外,阿瓜卢萨还通过描绘本地动植物,如黑冠鹤、天堂鸟和非洲黑木等,赋予非洲身份以实质。
莫桑比克岛
从个人层面,小岛也为陷入身份危机的非洲人提供了再生的机遇。在《生者与余众》中,作家们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作为非洲作家的身份危机。非洲文学一直被期望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即文中丹尼尔批判的、由来自非洲大陆之外的经纪人、记者和读者“想象出来的非洲”。
随着情节的推进,作家们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打破虚实界限的神力。他们此前虚构的人物在现实中出现,这种不可能的邂逅促使他们在岛上写下新的作品,从而创作了真正解决危机的新英雄。
最终,他们承担起创造者的角色,以写作促使小岛摆脱孤立状态。
非洲作家间的互动、友谊和爱,也引导作家走出了身份、创作和现实的多重危机,让他们对自身使命和身份认同有了新的理解。
非洲作家的挣扎与希望可以说是当代非洲文学创作的缩影,阿瓜卢萨本人也用这个故事表达对文学和写作的信仰和赞美。
正如葡萄牙媒体《表达》所言:“在一个充满极端威胁的时代,阿瓜卢萨的新小说是对纯粹的‘写作之乐’的实践,《生者与余众》是一首对文学力量的赞歌。”
文学宇宙
阿瓜卢萨1960 年出生在西非国家安哥拉,父母分别是来自巴西与葡萄牙的移民。年少时,他常常会随父亲沿着铁路旅行。多元的家庭背景和亲身经历,让阿瓜卢萨认识到非洲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同时也体会到身份的流动性和认同的复杂性。
同时,阿瓜卢萨居住于葡萄牙、安哥拉、巴西三地,他尽其所能,亲身以脚步丈量葡萄牙语世界的辽阔,足迹遍布葡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而在文学作品中、从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中探索现实问题的答案。
2007年,阿瓜卢萨凭借小说《贩卖过去的人》获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该奖项是英国文学界最具分量的翻译文学奖项(后与布克国际奖合并),阿瓜卢萨也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在《遗忘通论》摘得国际都柏林文学奖桂冠后,阿瓜卢萨近年来更是在英语世界声名鹊起,成为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葡萄牙作家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盛赞他是“当代最重要的葡语作家之一”,美国作家艾伦·考夫曼更是直言,阿瓜卢萨是葡语作家中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强力人选。
阿瓜卢萨既是文学大师,也是写作顽童。随着其作品不断增多,作品内部的互文愈发明显,一部小说中的配角或一闪而过的人物,常常在下一步小说中成为主角,用葡萄牙著名书评人托尔卡托•塞普尔维达的话说,阿瓜卢萨“正在创造一个独立的虚构世界”,他们互相交织,共享着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文学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