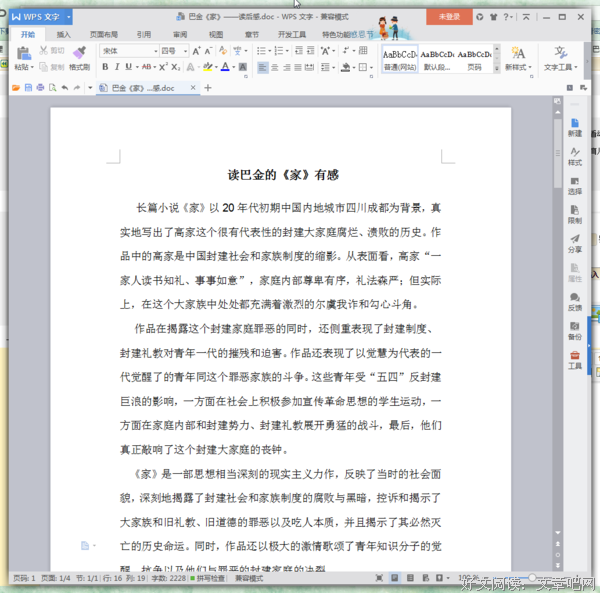随行巴金经典读后感有感
《随行巴金》是一本由陈喜儒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随行巴金》读后感(一):真实地存在与影响
一代大师巴金,我们这一代人的引领者。用文字歌颂真善美,用人品影响着国内外的读者。这边《随行巴金》,让我了解了生活中的巴金,心中更多一份敬意。
读书时,文学常识早已刻在记忆中的《家》《春》《秋》《雾》《雨》《电》,哪个学子不晓得啊!读师范的时候,从乡下走到城里的我终于在图书馆里看到了《家》,于是心怀敬意地捧着书读。那时,体会不到家,对进步青年的束缚,那种进步的,冲破牢笼的思想感受不深。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本书中的内含越发明白,也就越发感受到作者巴金的伟大。如今看到这本书,方晓得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尤其是对日本读者的影响,还有他在中日文学上的贡献!
百岁老人,八十岁时,依然活跃在文坛上,他与冰心老人之间的友谊,他对自己妻子的忠贞,他用一颗博大的心沟通着日本与中国的友谊。不过,当我看到巴老最后的日子,深深地为他艰难地活着而难过。高高隆起的肚子,呼吸机,管子……那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生命了?心疼老人!
作者把自己每一次和巴金老人在一起的生活记录下来,他那么善解人意,从不居功自傲,客人走了,要送到门口。在日本的时候,忙起来就忘记休息,但为了让别人满意,宁愿自己吃苦,多多为别人考虑,这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的人,怎么能不让人敬佩?
他尊重朋友,考虑事情周全,从不占便宜,在日本因为被采访所得到的钱,他捐了。请客吃饭,都是自己掏腰包,额外获得的收入,他都会捐出去。豁达、平和、看淡名利与金钱……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让人永远铭记?
经历文革,他却时常反思自己,当发现不是自己的问题后,他就开始专注内心。那段历史走过了,他没有怨恨,有的是反思,他接纳犯过错的人,只要改过,他理解人,体贴人。他每天用笔去思考,他说,一个作家,不要当官,当官就没有时间写作了。这些平实的话语,真实的想法,造就了一大大师。
仰慕巴老,带着崇敬读巴老。感谢作者,把一个伟大的人,用朴实的语言介绍他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了解一个人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在一言一行中都堪称典范。决定再读《家》《春》《秋》!
《随行巴金》读后感(二):巴金先生晚年的生活
巴金先生的一生,走过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也走过人人自危的政治风波,巴金先生以文人之心追求恬淡与家国平安的信念却从未改变。巴金先生所遗著作反映的不仅是人心与人性的挣扎,更是企求世间昌明的呼唤,巴金先生创作的人物形象众多,这些个性鲜明的群像无一不是敏锐的双眼所感触而成的结晶。敢于疾呼,敢于呼唤人间真、善、正义与公道,巴金先生由此而成文化领域里独具特色的存在。
陈喜儒先生早在七十年代便从事对外文学交流工作,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的日语专业的特长更增添了多样的观摩世界的方式。陈喜儒是巴金先生的日语翻译秘书,随同巴金先生左右,参与中国作家访问日本,以及日本作家与巴金的书信往来和访淡、交流活动。这部《随行巴金》展现了巴金晚年的生活,也对广大读者全面理解巴金先生的一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小细节见大真章,往往是倏忽即过的小事件反而更能引起日后触动人心的震撼。《随行巴金》里有着看似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平和抚慰人心灵的普通照片,有着三言两语的文字记录,而这些当时看起来随意与平淡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在巴金先生逝去后变得如此珍贵与深刻。人世间的痛,莫过于活生生在你面前的人总觉得还有时光可得,却不曾想,闭眸睁眼间却已天人永隔,音讯不再,痛与遗憾徒留心底,待轮回。
陈喜儒先生用短短七篇的文章将巴金先生丰富的精神世界,巴金先生的善念、巴金先生的坚持,巴金先生的人格尽在这七篇文章里。可见肉身总会归于虚无,但精神的遗存却不会因肉体消亡而消逝。巴金先生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社会稳定、政治昌明,人人和谐而处,在众多如同巴金先生自身般的人士大力推广下,会尽早实现的吧。正如陈喜儒先生在文章中所说,“永远忠于你们,忠于美,忠于爱......热爱自由,热爱孩子子,热爱和平......”
这部《随行巴金》也为读者展示了身为文化传播者的巴金先生的多彩人生,与国外文学人士,文化团体的广泛交流,国际论的文学创新理念,忧国忧民的士者情怀,这些都深深感动着读者,并 给读者带来正确的文学导向力。
《随行巴金》读后感(三):平常中蕴藏的力量
这本书自己开始看的时候正好赶上流感肆虐,全家人都中招,就这样看了一半就搁置到了床头,总是在劳累了一天后躺在床上,才发现这本书自己放的偌大的一个书签,还在那露着似乎向我招手。
生活在显露她的残酷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生活的沼泽中痛苦地挣扎着,似乎一直想着能够爬出去,找一个无风无浪的地方去避一避,这也是许多人一直坚持着活着的意义,我相信,特别是现在像我们这代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生活更是如此。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就成了这哭泣的生活中唯一的亮光,抓着这救命的稻草,才能在憋气的生活中苟延残喘。
读这本书的契机正好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中,我自己一个人担起了生活的磨难,照顾生病的孩子照顾生病的老人,照顾很多很多人,而把生病的自己忘记了。最明显的一个情景就是,自己陪着两个孩子玩耍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抱着孩子挂号看病的时候,我很少很少有抬头看看天空,看看周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是一个囚犯,被生活困住了。
巴金老人是我年轻时候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对于他和另一位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我心中都是举着圣火的崇拜。他的许多作品在改编为电视剧和影视剧后,我曾经看过很多遍,并且还曾经流下过那个年轻的记忆里苦涩的泪水。
为什么在写书评时写下自己的生活境地,因为当时我读的最多的巴金老师的书就是家春秋这个系列,当时的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艰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法感同身受,但是还是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如今自己走到了那样的一个年龄,才更加明白了他的笔触的细腻。
如今看到其他人写他的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巴金先生。我总是通过那些作品来想象巴金先生是如何如何的,但是看到这本书后才更加立体和全面地了解了这样一位大家的另一面。
书中从几次比较大的事件中来介绍巴金在对中日交流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思维是那样的缜密,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得体的考虑。
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图片,我也是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巴金的样子,还有我尊敬的冰心老人的样子,他们的样子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这些心目中的大家的距离,巴金老人与日本友人交流时那样的不卑不亢,同时与书的作者这样的晚辈交流时又非常的和蔼可亲,与自己的知己和友人在一起时又幽默而风趣,这样的小细节都在书中体现出来了。
巴金老人在生命的弥留之时让人心疼,那时的老人在病痛下真的让人心疼,人在那个时候总是很渺小的,很无力。
书中很多细节写的都很精彩,在自己的生活的悲凉下看这本书,无形中给了自己许多力量,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我的这些小苦痛真的算不得什么,他们肩上肩负的,远远重于自己的这些柴米油盐,而我们的生活稀疏平常中的酸楚真的算不了什么,继续前行吧。
《随行巴金》读后感(四):世纪老人巴金印象
说起作家巴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是他的“爱情三部曲”也就是《雾》《雨》《电》吗?还是“激流三部曲》”也就是《家》《春》《秋》呢?前者不消多说,重点在于后者,也就是“激流三部曲”,集中体现了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也奠定了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
当然,这是文学史上的巴金。而现实生活中的巴金呢?比如,他对爱情与婚姻的忠贞不渝。算起来,当32岁的巴金以《家》而成为当时青年人心中偶像的时候,他与一位女高中生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此时谓之笔友。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主动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而且是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从1936年到1944年,恋爱8年之后,40岁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27岁的女孩结为连理——直到“十年浩劫”中巴金受冲击,萧珊终因癌症病逝。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他始终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这份爱情或者说婚姻,即使不能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大概也相去不远了。换成别人,比如换成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期待中的爱情与婚姻,会以巴金和萧珊这样一种特别纯粹的爱情与婚姻为榜样吗?还是说,他们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快餐”般的爱情与婚姻呢?
巴金是一位大作家,他却从来都不以此自居,而是始终贯彻着“真”与“善”这两个字,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他的文学思想都是如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主要来自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他的这样一种“善”也做到了与时俱进——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特别是在解放后他的这样一种“善”也在越来越多地与人民大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巴金的“善”是与他的“真”密切相关的,是对时代的感受与提炼。巴金是百岁老人,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迁,特别是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近三十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那种奋勇向前,却始终不改他的“真”与“善”——在今天的中国作家群里边,如巴金这样的“真”与“善”,不能说没有,但说不多或者不够多还是很符合实际的。作家如果感受不到时代的节拍,就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脱节;但如果过于社会化、生活化,则难免失之于深刻、失之于宽广。
而作家巴金的另一面,即是说文学作品之外的巴金,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如今担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对外文学交流工作的陈喜儒所撰写的《随行巴金》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巴金与日本作家的互相探访和深厚友谊。虽然都是细微小事,却足以见微知著,却足以见证作品中的“真”与“善”之外,一位伟大作家的宽广胸怀。陈喜儒担任过巴金的日语翻译秘书,曾随同巴金参与中国作家团访日之行,也与巴金交往甚密——所以,他笔下的巴金,更多地流露出了一个智者因为对生活有所感悟进而更加朴实无华、本真的一面——比如他的争强好胜!真人真性情,这就很好。比之巴金,现代人做到“真”与“善”可真的不容易,真的不能“归罪”于环境的影响与时代使然。
为人处事,左右逢源固然长袖善舞,却总觉得要失去些另外的一些什么。读了《随行巴金》之后,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还需要点什么,无论如何都应该从内心底有所触动了!
《随行巴金》读后感(五):化名“黎德瑞”的巴金先生
黎德瑞,是鲜少有人知道的巴金先生的化名。
1934年,巴金三十岁时,曾经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完成了小说《神·鬼·人》和童话《长生塔》的创作。原本,出于对日本国度的好奇和对日本文学的喜爱,巴金先生计划在日本的学习时间是一年半。但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促使巴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将旅日时间缩短至十个月并提前回国。
而且,巴金先生从此打消了学习日语的念头。
虽然,晚年的巴金先生提到这段往事不胜唏嘘,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为没能够完成日语学习颇感遗憾。但是,这件事情对巴金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巴金曾在一次日本演讲时说:“1934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语,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收录《巴金全集》二十卷564页)
1980年,巴金先生和冰心老人一起带队中国作家协会出访日本。时年,巴金先生七十六岁,冰心老人八十岁。随团出行的翻译是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翻译陈喜儒,透过陈喜儒的作品《随行巴金》可以很好地了解巴金先生此次出访日本的细节,以及化名“黎德瑞”的巴金先生那一段昔年往事。
对日本心生“好感”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十九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四川省成都正通顺街98号,这是一所深宅大院,又称李家院子(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的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都曾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常常谈起日本的生活。异域外邦的新奇世界引起了少年巴金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度感到好奇。
另一方面,那一时期,日本小说开始由鲁迅、夏丐尊翻译引进国内,这也激起了 巴金对日本文学的喜爱。
巴金曾多次提到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他坦言自己是鲁迅作品狂热的崇拜者,有些篇章甚至能背诵如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研读,巴金学到了“驾驭文学的方法”。巴金曾说:“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1934年,曹禺和巴金谈起日本,并说到在日本时认识的一个姓武田的熟人可以接待巴金。曹禺提笔给武田写了一封信,信中询问武田是否愿意接待一位想去日本学习日文的书店职员。很快,曹禺收到了武田的回信,武田在信中对即将到来的朋友表示了欢迎。
就这样,巴金在1927年留学法国之后,于1934年乘坐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号到达横滨时由四号码头,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活。
“黎德瑞”的由来
1934年的时候,巴金已经出版了小说《灭亡》和《家》。因为对日本警察的行事方式早有耳闻,所以巴金决定改名换姓,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名字德瑞的由来,巴金全集20卷581页关于《长生塔》中有这样的讲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记答应。
巴金先生曾用过许多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等。其中,巴金是最广为人知的。
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意外生变故
对于溥仪的到来,日本不仅安排100架飞机组成编队,日本天皇更是主动前往车站进行迎接,将溥仪安排在日本最奢华的宫殿当中。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巴金全集》二十卷五六四页提到的巴金半夜被日本’刑事’关进神田区警察署一事,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巴金回忆初到日本时,说:“我住下来以后,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多少岁?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庆的字眼!或者结婚没有?经过几次这样的’考试’,我并没有露出破绽,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
然而,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4月6日凌晨,警察闯入了巴金的住处——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他们开始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小说《人——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描写的就是巴金受审拘留的情况。这篇文章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的一日记》,以巴金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
虽然,巴金在狱中经历了受审,经历了搜身,又被编以七十八号,不得不在满是臭味的牢房里与八个人一起挤在只有一张薄席的硬地板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日本警察没有发现破绽、疑点,更没有发现“黎德瑞”就是《家》的作者巴金先生(巴金旅日时,已经出版了小说《灭亡》和《家》)。
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十四小时。巴金无缘无故被关押审讯,又无缘无故放了出去。“为了什么?我始终莫明奇妙。但是我自由了。昂头走在街上,看见落日的余光,看见扰攘的人群,给自由的风吹着,给春天的空气包围着,我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巴金全集》十卷424页)
巴金先生的这一段旅日往事鲜少被提及,我也是在读了这本陈喜儒先生的《随行巴金》后,特意查阅了一番。
“黎德瑞”这个名字,伴随巴金月余,日本归国后不再复用。晚年的巴金也曾为1935年前后写下的一些“泄气”文字感到“羞耻”。巴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写的不公平的话感到羞耻,感到后悔了。你知道印在纸上的字是揩不掉的……我想这样也好,赖债是不行的,有错就改嘛。”(《巴金全集》十二卷588页)
巴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佩的人,他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正直真诚的人。正如著名翻译家萧乾说过的那样——“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怀念巴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