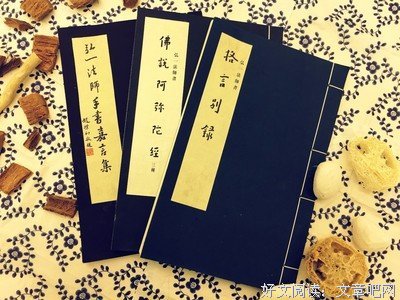跟李叔同学做教师
三天前,从图书馆借来三本书:次仁罗布的《放生羊》 席慕蓉散文《槭树下的家》和康蚂的《纠缠不是禅——李叔同的前半生》。从书架上取下时,每一本都爱不释手。回到家里,打算阅读时,还是不自觉地从这本牛皮纸色的《纠缠不是禅》开始。谁知一打开,便像遇到久违的故知,心想:这正是我当下想读的书。距离上班的日期只有三天,为了让自己排除干扰、专心阅读,我断开了网络。除了应付必须的生活杂务和人情事往,余下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两天多的时间读完这本书,感触颇深,从李叔同的人生经历中学到许多治学、处世和为师之道,并且也促成了我的一份禅修机缘。
李叔同出身于天津的官宦之家,家世显赫。父亲早逝,在母亲的严格管束下, 早年跟从名师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在诗词文章、文字学和书法篆刻方面打下深厚的功底,造诣颇高。少年时代能书善画,艺术才华出众,与当时的许多艺术名流交往甚深。青年时代迁居上海,广结名士,成立社团,编辑报纸,参与“抵制美国货”的爱国运动。25岁游学日本,在绘画、音乐和话剧表演等方面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出色才华。回国后,继续参与文学社团活动。在《太平洋报》担任编辑期间,大胆创新,精心筹划,成为中国近代广告的创始人。李叔同的前半生可谓多才多艺、才华盖世,思想先锋,像一块精雕细琢、品质绝世的玉石闪耀在中国近代最纷乱的历史舞台。在他的诸多身份中,我最敬慕、最受感染的是他那段不太长久的做教师的经历。
1912年8月,受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经亨颐邀请,李叔同赴杭州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师。
在教学中,李叔同是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教师。执教后,他尝试的第一项革新就是提倡写生。初学绘画的学生不用临摹,由写生入手。他认为,临摹会阻碍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和个性的养成,会消磨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从实物写生画起,由室内到室外,精心指导。等学生具备了一定对实物素描写生的基本技能后,开设了人体写生课。在写生之前,他担心引起误会,先向学生讲解了人物写生的目的和意义。鼓励学生放下顾虑,创造出有血有肉、有生气、有灵魂的作品。至此,李书同成为中国裸体写生的首创者。在他的精心传授下,培养出李鸿梁、丰子恺、潘天寿等天赋极高的学生。此后的数十年,中国绘画史被他们推向鼎盛。李叔同的画作,也成为中外书画收藏家竞相争抢的精品。
李叔同不仅在图画课程中独具一格,音乐方面亦独树一帜。在没有音乐教材的情况下,他根据学生的音乐基础和需要自己选曲填词,或者作词作曲,自编“学堂乐歌”,给学生当教材。这些乐歌曲调优美、歌词意境深远,深受学生喜爱。“‘学堂乐歌’为中国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先河。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西方基本音乐理论和技能开始系统地、大范围地在中国传播。”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李叔同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众所熟知、久唱不衰的乐歌《送别》,就产生于那个时期。
我们通常评价一个好老师,经常会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来作为标准。这个标准,在李叔同这里得到了切实地验证。
李叔同教学图画和音乐,但他的才华不止于这两个方面。他的同事夏丐尊说,李叔同在学生中有很好的威望,他像菩萨那样有“后光”,即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全面的文艺才华。他将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还重,这是有人格做背景的缘故。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1913年6月,李叔同以“浙一师友会”名义,创办校刊《白阳》。来稿主要向全校师生征集,数量不足成卷,则由李叔同以自己的作品填充。有散文、填词、文学论文、音乐论文、美术论文、合唱曲等。其中《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是一部最早出现的由中国人撰写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虽然只存一章,其余散失,却能从中看出李叔同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和简练、精准的语言概述能力。这一作品,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李叔同知识的广博和创作形式的丰富。
身为教师,光有丰厚的才学似乎并不足以令人敬仰,优良的为师品德更能彰显教师的人格魅力。
李叔同桃李满天下,他对学生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学生对她非常尊敬。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三位性格鲜明,天赋极高,与李叔同终生结下深厚情谊的学生。
学生刘质平在李叔同的精心栽培下考取了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音乐理论。但入学不久,因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陷入窘境。无奈之下,向李叔同写信诉苦。李叔同见信心急如焚,为他申请官费,没有成功后,毅然解囊相助,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拨出二十元作为刘质平的留学费用,直到毕业,并立下规矩“不许与第三人谈及。”当时,李叔同的薪水要分摊两个家庭,他自己的肺病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每月出资捐助自己的学生,可见他为人之诚厚。刘质平视李叔同为父,踏入社会后,用微薄的工资供养老师的后半生。后得到弘一法师书画字件多幅,精心装裱,守书如命。曾多次有人主动出高价收买,均被刘质平严词拒绝。文革期间,为保存弘一大师的遗墨,凛然不屈,险些丢掉性命。在他们师生之间,凝聚着一份足以生死相托的诚信与忠义。
在学生丰子恺的心中,李叔同“温而厉”教育方式留下很深的印象。学生犯错时,李叔同从不当面批评,而是下课后单独提醒,并向学生深鞠一躬,促其改悔。发现丰子恺的绘画天赋后,李叔同对他格外关注,并给予鼓励,使他打定注,专心学画,把毕生献给所钟爱的艺术。后来丰子恺因为与教导主任杨某发生争执,对方要求校方严惩丰子恺,开除他的学籍。李叔同主动提议:给予记过处分,并带领学生一道向主任赔礼道歉。事后,将丰子恺等几位同学叫到住所,打开《人谱》念了一段,使他们认识到:读书人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弘一法师圆寂后,为履行对恩师的诺言,丰子恺穷尽毕生精力完成六集《护生画集》。
学生李鸿梁生性耿直,不懂变通。李叔同多次宽宥并提醒他要学会韬光养晦,保护自己。在许多关键时候,替他考虑周全,为他提供极细微的帮助。
在李叔同身上,我学到了待人以诚、谅人以宽、助人以厚的为师品格。正是这种高尚的人格魅力,使得李叔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高山仰止的师者典范,也为他日后了却红尘,踏入空门修养更高的德行奠定了根基。
很喜欢文末的一句话:“人生只有一世,李叔同却活了两世,一世用来尝遍百味,一世用来修养德行。”这样的人生,自是我们普通人所仰慕和向往的。然而,先生已经以步为尺地走过,细细地用心品尝过。
跟李叔同学做教师,从这一刻起,广读厚积,丰富自己的学识;严于律己,修行自己的品德,让自己也像菩萨那样有“后光”,照亮别人,恬淡自己。